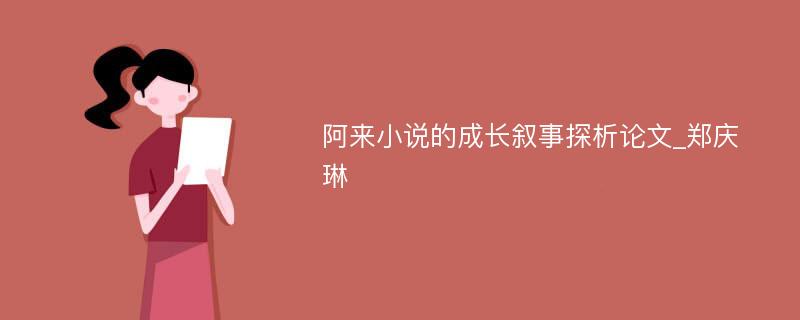
摘要:在近20年的创作过程中,阿来的小说始终关注川藏地区的生活与历史,从最初的为读者展现藏地奇景,到融入自己的沉痛和困惑情绪,为一个行将消失的机村立传,最后深入人性的考察。阿来的小说中围绕成长展开深入思索,无论是“傻子”二少爷,还是达瑟、索波,无论是晋美,还是桑吉、阿妈斯炯、王泽周,我们不难发现,阿来是在讲述他们的在历史潮流中的成长经历,他们都在时代的变化中成长、纠结、挣扎,生活在命运的阴影之中承受命定的无可奈何。
关键词:成长叙事;历史;人性;消费主义
文学作品不仅是对现实情态的描摹,还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思考与体悟,成长叙事不仅是单纯的个体生长史的记录,而且涉及社会、历史、人性等相关领域,富含多重文本寓意和精神内涵。阿来在《尘埃落定》《格拉长大》《三只虫草》等作品都围绕着“成长”展开深入思索。阿来的作品中有着他少年生活的烙印,他曾经用“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1]来描绘自己曾经的生活。嘉绒藏区特殊的自然地域环境和生活环境,藏汉之间的文化碰撞、藏回混血的不纯正的民族身份,都使聪慧而敏感的少年阿来内心承载着比他人更多的“身份焦虑”等沉重体验,这种体验对阿来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生命试炼,这些成长过程中苦痛都沉积在他的记忆深处,作用于他的写作。作品形成特定的风格同样也离不开时代环境的熏陶,阿来成长于时代新旧交替且未完成的阶段,过去的秩序被破坏,新的秩序还未完成,这决定了阿来的目光“始终聚焦于崩溃的秩序和退场的人物,以普世性的胸怀和悲悯的眼光关注着个体的成长历程。
一、历史变动时期的人物成长
阿来对历史情有独钟,他总是希望能够客观、真实地再现独特的藏民族,或者准确地再现他所生活“嘉绒”地方民族历史。阿来作品中的这些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而且是个体生命发展的试炼场。《尘埃落定》中,土司家族坍塌象征着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土崩瓦解。对于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和不可抗拒的历史命运,阿来认为“这种制度性东西的瓦解就是天经地义的一个过程,是历史必然”,作家关心的是制度瓦解过程中的个体生命。小说中不仅是傻子少爷,而是所有的人物都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历史的断裂推动了主人公命运、性格的改变。“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2]阿来书写了不可抵挡的历史巨轮之下的成长哀伤,现代文明以“强势”的姿态侵入到民族生活的内部,使得民族“根性”产生了动摇,对个体的生命成长而言,是如此的残酷。
在小说《空山》中机村大火开始的势态被用来比喻大革命爆发后被迷惑的人心,索波、央金这些年轻人陷入政治狂热中无法自拔。天火的开始、经过乃至熄灭,无不与人物的成长过程产生特殊的联系。“个体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个体的成长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3],历史以强势的姿态侵入到个体的成长之中,《空山》中的索波身上体现出年轻的一代人接受新鲜事物的激情和对政治运动的盲从心理。”痴迷于政治和权利而不择手段的索波,却没有达到他被重用的目标,这使得他无比落寞与失望。天火唤起了他对家乡的热爱,救援队的冷漠使他深感无能为力,遭受了各种挫折的他逐渐从迷途中走出,成长为了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成为小说的迷失者中能够自己醒悟,成功回归的典范。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人性迷失下的成长苦难
成长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场蜕变,伴随着苦痛与挣扎,在危机、苦难和挑战面前,人物的性格、心理发生变异,并显示出巨大的能量,从而具备成长叙事的价值。阿来对成长危机的叙述拓展到人性的纵深,从人性的复杂深邃和幽暗曲折中探寻成长的苦难。
在《格拉长大》中,“光明”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映照着一个少年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渴望被接纳,渴望被相信。然而,这些卑微的渴望,对格拉而言却是多么遥不可及。格拉被村民刻意伤害、恶语中伤,命运每次对格拉露出一道缝隙时,却又砰然关闭,残忍扑灭一个少年刚燃起的微小希望。“在那些地方,封建时代构筑的乡村基本伦理已经破败消失,精神的乡村,伦理的乡村早就破败不堪,成为了一片精神荒原。”[4]失去了精神文化的机村人,在历史断裂的冲击下,势必会产生动摇。
三、消费主义背景下的成长困境
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主要关注川西藏族人和边地大自然在消费主义大潮中的沧桑命运。阿来从青藏高原上被消费主义社会渴欲的虫草、松茸、岷江柏三种物产入手,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与消费主义带来的影响相互交织,写出了川藏边地的人心变化,批判了现代人的拜物症,呼唤现代人尊重藏族民间的朴素的生态伦理,重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当消费主义文化热风催生出现代人的拜物欲,从而直接导致川西藏区等边地的自然生态惨遭破坏时,这个世界总还会有一些清醒的人,心中保存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坚守着人性的朴素底线抵抗着时代大潮。《蘑菇圈》中,斯炯年轻时参加工作组,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在此历程中,守护蘑菇圈既与她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相交织,又成为她坚守传统的精神象征。《河上柏影》中,王泽周的生命历程、民族身份认同也和他对待岷江柏的生态伦理相交织。《三只虫草》承载了一个少年无限的渴望,虫草既是小说重要构成物,也是成人世界欲望的指代。欲望、金钱以“狂躁”的姿态冲击着古老的民族,古老大地上生命个体的躁动与困惑展示了民族成长的鸿沟。阿来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失去根底的民族,惶惑与迷茫在所难免,但他依然坚持从民族根脉之中寻求成长的力量。
结语
在宿命的牢笼、人性的羁绊面前,每个生命个体都无从回避、逃脱,阿来却从生存家园、古老精神和民族宗教之中升发开来,他接纳了民族衰败的历史命运,也清洗并拥抱了被宿命、人性所挟持的生命的残酷成长,行文之中充满诗性的关怀和深情的守望。
参考文献:
[1]阿来:《阿来文集?诗文卷》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2]巴赫金:《小说理论》,白仁春、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230页。
[3]翟文铖:《“70”后作家成长小说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
[4]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郑庆琳(1994-),女,汉族,山东临沂,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文作者:郑庆琳
论文发表刊物:《学习与科普》2019年3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2/26
标签:阿来论文; 历史论文; 个体论文; 民族论文; 人性论文; 生命论文; 小说论文; 《学习与科普》2019年39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