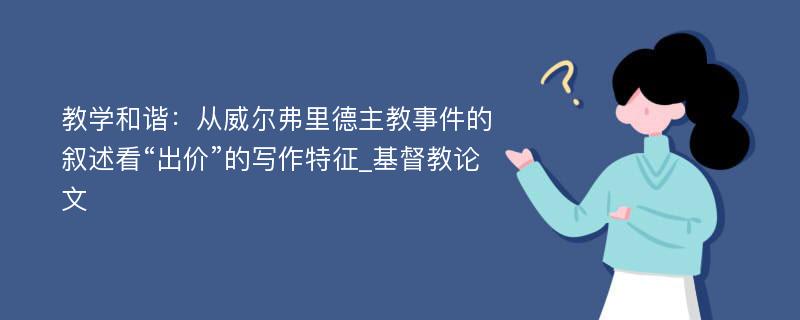
教诲和谐:从对主教威尔弗里德事件的叙述看比德的写作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教论文,威尔论文,弗里德论文,和谐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写作《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m Ecclesiasticam Gentis Anglorum)(以下简称《教会史》)①过程中,作者比德不仅广泛地调查史料,还注意交代材料的来源,证明其可靠性。比德的写作风格与现代历史学家的写作习惯暗合,从而备受学界肯定。②在前言中,比德甚至还探讨了“历史写作的真实法则”。他说:“我乞求读者,如果在我们的叙述中他发现真实之外的东西,请他不要为此责怪我们,因为历史写作的真实法则,只不过是我们从大众传闻中收集到的,为了教育后代而努力用文字简单地加以保留的那些。”③
1947年,查理·琼斯认为这段话表达的是“根据普通看法进行文学性表述”的意思,从而引起学术界的讨论。④最近,郭法特重申并发展了琼斯的解释,认为应该将“真实法则”理解为“率真地书写”。意思是说,如果不符合神学上的微言大义,请读者不要责怪他,因为他是率真地(非神学地)书写的。在此基础之上,郭法特割断了这段话与比德写作态度之间的关联。“许多作者称赞比德接近于现代史料征引和严谨阐释的原则。此类论断是真是假与这段话本身并没有干系。提供历史的史源和证明其可靠性都不是比德这里所关心的。”⑤不仅如此,郭法特甚至认为比德是别有用心的,《教会史》是反威尔弗里德派的政治作品。⑥本文拟以7世纪晚期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被革除教职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比较比德的记叙与其他当时记录尤其是艾迪·斯蒂芬所著《威尔弗里德传》的异同⑦,从材料取舍的角度,说明比德的取材偏向,揭示其写作目的。本文并不认为比德在写作中具有派别偏见,而是认为比德通过有意识地取舍材料,调和教会内部不同派别,淡化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充分展示英吉利教会和谐发展的历史图景。
一、主教威尔弗里德的坎坷一生
约公元634年,威尔弗里德(St.Wilfrid)出生于一个军事贵族家庭,14岁的时候出门修道,在诺森伯里亚王国奥斯维王(Oswiu)的王后伊恩弗莱德的推荐下,进入林迪斯凡修道院侍候修士。几年之后,他决心去罗马朝圣。在罗马,他有幸得到大助祭仆尼法斯的指点,学习《福音书》,甚至得到了教皇的接见。在返回不列颠的途中,在里昂停留三年,成为修士。
回到不列颠之后,奥斯维王之子、德伊勒王阿尔奇弗里德对他一见倾心,捐赠里彭修道院,让他出任院长。664年被任命为神父。随后出席惠特比宗教会议。同一年接替身染瘟疫去世的图达主教。但是威尔弗里德不愿意在国内接受任命,于是去法兰西举行授职仪式。
就在威尔弗里德逗留海外期间,奥斯维国王重新任命了查德为约克城主教。“奥斯维国王听信主教的老对手的谗言,同意不合规矩地安排其他人掌管威尔弗里德的主教区,违背教规无知地从阴历十四日派推荐的人选中任命虔诚的仆人、博学之士、来自爱尔兰岛的名叫查德的无名小卒为约克主教。”⑧直到66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塔尔苏斯的西奥多走马上任,巡视诺森伯里亚地区,将查德免职,让威尔弗里德复职。
670年,奥斯维王去世,随后继承王位的埃格弗里德(Ecgfrid)刚开始与主教的关系也不错,他的王后埃塞尔思里思最崇敬的人就是比德主教。但是,随着672年左右埃塞尔思里思隐修,埃格弗里德续弦,娶了埃尔敏伯格(Eormenburg),俩人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在斯蒂芬眼中,新王后妒忌主教,整天在国王耳边数落主教的世俗荣耀、财富、为数众多的修道院,宏大的教堂,以及无数随从,仪仗奢华。678年,她甚至用贿赂手段邀请大主教西奥多前来。“当大主教前来的时候,(国王)向他表明内心对主教的敌意,他就同意对没有罪责的主教加以惩处。他找到博萨、伊塔和伊德赫德三位主教,在我们的主教不在场的情形下,将这些不属于他的主教区的人在他的主教区非同寻常地加以任命。”⑨
威尔弗里德决定去罗马上诉。他在上诉状上写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及其他教士,违背了教规和教令,费尽心机地以强盗的方式侵犯、劫掠并占据了我治理了十多年的主教教座。在我的教区,他们不是提拔了一位,而是三位主教,而我还活着,也不知晓此事……对于大主教,我不敢指责,但是,真相很清楚,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形下,也没有违反任何教规,我被敌人赶走。此后,我既没有发动骚乱,也没有挑动教区,更没有反击对手,而是找来下属,将他们让予那些教省的主教们,我自己来上诉。”⑩
经过反复协商,罗马教皇阿加塞(Agatho)与宗教会议最终裁决:“恢复威尔弗里德的主教职位,由他经宗教会议同意挑选主教协助他。至于上次被任命的主教们,他应该与他们和平相处;至于在他离开之后新被任命的主教,一律废止。”(11)
当威尔弗里德回到不列颠,拿出教皇的信件和敕令,埃格弗里德国王认为这些文件都是他通过贿赂方式买来的,不予承认,并将他关押起来。九个月之后,由于科尔丁厄姆的院长嬷嬷埃巴(Aebba)的干预,威尔弗里德被释放,辗转各地,开始漫长的流亡生活。他脱离了羁押,被驱逐出祖国。(12)
幸好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决定与主教和解,忏悔自己的罪责。“现在我对上帝忏悔,我的主教们,请你们做个见证。为了免除我的罪责,我将给所有的王公们写信,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我要尽一切方式,使他们与你和解。”(13)但是,无论如何,埃格弗里德国王不肯回头。
685年,埃格弗里德兵败被杀,没有儿子,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长期流放在苏格兰的奥尔德弗里德(Aldfrid)继承王位。“根据大主教的命令,邀请威尔弗里德回来。”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690年,大主教西奥多去世。692年,威尔弗里德与奥尔德弗里德关系破裂,被迫再次流亡。703年,奥尔德弗里德招来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伯特沃尔德,召开宗教会议,再次将威尔弗里德驱逐出境,并开除教籍。
威尔弗里德决定再次去罗马申诉,并由教皇约翰召集宗教会议宣布无罪,重申了阿加塞教皇的裁决,建议由大主教伯特沃尔德与威尔弗里德负责召集宗教会议,依据教规投票裁定,不得再有任何争议,否则全体前往罗马接受裁决。(14)
威尔弗里德回来之后,首先派遣使节去见大主教,伯特沃尔德答应和解。但是,奥尔德弗里德国王只答应提供日用品,并不打算推翻此前的判决。随后,国王去世,继位的伊德伍尔夫不想改变既定政策,他对主教的使节说:“除非六天之内离开我的王国,一旦抓住,我的士兵会处死你。”(15)仅两个月后,发生政变,伊德伍尔夫被驱逐。年仅八岁的儿童国王奥斯雷德登基,随即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大家和解。威尔弗里德成为赫克瑟姆主教,收回里彭和阿古斯塔尔(Agustaldesia)修道院及其所属财产。四年后(709年),威尔弗里德病逝,安葬于里彭修道院教堂。
二、斯蒂芬和比德笔下不同的威尔弗里德事件
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先后三次被革职,前后持续了40年,他还两度亲赴罗马上诉,影响广泛。他被免职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重大的教会事务,笔者称之为“威尔弗里德事件”。比德虽然也耗费了许多笔墨叙述威尔弗里德的经历,有22节专门讲述威尔弗里德的生平,此外在介绍惠特比宗教会议的时候,记录了威尔弗里德的长篇大论。但是,他对威尔弗里德被革职的说明不仅轻描淡写,而且对围绕他而发生的教会内部的冲突几乎没有提及。
通过比较比德的作品和艾迪·斯蒂芬的《主教威尔弗里德传》的相关段落,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主要差异。
第一,比德将威尔弗里德被革职的原因归结为教会外部力量的干预,是“由于与这个埃格弗里德王不和”(16)。而《主教威尔弗里德传》则认为源自教会内部的冲突,是“老对手”“阴历十四日派分子”进谗言,使得国王采取行动。
第二,比德的笔下,威尔弗里德的主要同僚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和惠特比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希尔德(St.Hilda)似乎与他被革职毫无干系。而斯蒂芬则明确交代了俩人的参与,并将西奥多的任职一分为二,前期与后期为一段,属于治理英明时期;中期为一段,属于卷入冲突的时期。西奥多虽然是个智者,但是由于接受国王埃格弗里德的礼物而被蒙蔽了双眼,无端将威尔弗里德革职,并且派遣使节,上报罗马。到了晚年,他勇于忏悔自己对威尔弗里德的所作所为:“我的思虑压迫着我,我听信诸王所言,加害于你,在你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将你的财产剥夺,遣散你的随从,判决你长期流放。哦,多么可怜,一切的邪恶!现在我对着上帝忏悔,向圣彼得忏悔。而我的主教们,请你们做个见证。为了免除我的罪责,我将给所有的王公们写信,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我要尽一切方法使得他们与你和解。”(17)
678年第一次起诉威尔弗里德主教的代表人物,除了大主教西奥多就是希尔德。希尔德出身于德伊勒王室,尽管年幼的时候接受了罗马派约克大主教波莱纳斯的施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后来却认同于爱尔兰方式。664年,作为东道主,她站在苏格兰人一边。争论结果虽然是她失败了,但这只是暂时的,或者说表面的现象。因为得胜方威尔弗里德很快就由于“主教的老对手阴历十四日派分子的谗言”,被革除了主教职位。
678年,还是希尔德联合西奥多,重新将威尔弗里德免职,代之以出自本修道院的修士博萨。随后的50年间,惠特比修道院培养出了5位主教:博萨(约克主教)、艾特拉(多切斯特主教)、奥夫特弗(维卡斯主教)、约翰(赫克瑟姆主教)和小威尔弗里德(约克主教),如果加上本已得到任命但很快去世的塔特弗里德,就有6位主教。
而在比德的笔下,不仅没有提及希尔德参与此事,而且挑起争端的嬷嬷希尔德在“教导人们保持公义、虔诚、贞洁以及其他种种美德,尤其是和睦和博爱”(18)。她的临终遗言竟然也是“劝导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不应该说和所有人之间保持《福音书》上所说的那种和睦”。
第三,继西奥多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伯特沃尔德也直接卷入了这一事件。他不仅于703年应奥尔德弗里德的邀请到诺森伯里亚,重申前任西奥多对于威尔弗里德的谴责。当威尔弗里德表示不服加以谴责的时候,伯特沃尔德说:“(你)选择他们的判决而不是我们的判决,这一事实就足以让你受到谴责。”(19)不仅如此,他指责威尔弗里德傲慢无礼,以此为由将威尔弗里德告到了罗马,迫使威尔弗里德到罗马去应诉。而罗马教皇的裁决也是侧重于要求他与威尔弗里德和解,取得一致。
比德没有提及伯特沃尔德的这次参与,相反只是说,在接到约翰教皇的判决之后,伯特沃尔德迅速与威尔弗里德和解。“大主教伯特沃尔德和一度担任国王而当时已是修道院院长的埃塞尔雷德迅速地站到他一边。”(20)伯特沃尔德似乎特别偏向威尔弗里德似的。
第四,对于威尔弗里德本人,比德并没有描写他的好斗、个性强硬,而是强调了他的“不平凡的谦恭和温顺的美德”,“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长辈和同辈的喜爱和敬重。”(21)
第五,对于惠特比宗教会议,比德虽然承认这是“更为激烈的争论”,但是,也只是把争论当作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件通过开会就彻底解决了的事情。会议之后,“科尔曼因自己的教条受到谴责,自己的教派受到了批判,就带着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即拒绝接受普世复活节和冠冕式发型的那些人回到了苏格兰……所有的人,不管是坐着的还是站在一旁的,不管是地位较高的还是随从前来地位较低的,都表示赞同。他们在放弃了先前的那些不完美的习俗后,迅速地转而信从他们已得知是较为完美的习俗。”(22)
不仅现代学者发现,会议的主要功臣威尔弗里德此后终生坎坷,“清晰地表明了惠特比会议之后苏格兰派与改革派之间的长期争斗。”(23)斯蒂芬也充分意识到了冲突的长期存在,并认为冲突源自于他们的“老对手”“阴历十四日派分子”。
比德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详细经历。他曾经当面向威尔弗里德请教过问题,而威尔弗里德的接班人赫克瑟姆主教阿卡更是比德非常熟悉的人。“大多数比德的神学作品都是献给赫克瑟姆主教阿卡的,比德对他有明显的偏爱。”(24)不仅如此,学界普遍认为,当比德写作《教会史》的时候,应该读过斯蒂芬的作品。(25)
学者们一般都偏爱比德一些,认为斯蒂芬作为传记作者、威尔弗里德的随从,他的写作难免会过于感情化,过于维护威尔弗里德。而比德的写作要更加客观一些,也更加可信。(26)但是,斯蒂芬的写作目的也并不是要夸大教会内部的斗争,而是通过描写威尔弗里德的经历,神圣化威尔弗里德,为自己的修道院获得保护,从而得到上帝的眷顾和保护。“我们的主教见上帝之后,院长们和随从们害怕老对手的阴谋,他们说:‘当我们的首领在世的时候,我们经常忍受不列颠诸王和王公们的各种攻击。由于主教的虔诚和智慧,许多友人的帮助,通常有较好的结局。现在最好是信赖他,让他做我们的保护,通过十字旗和他最喜爱的使徒彼得和安德烈,在上帝面前,不停地做我们的保护者。’”(27)也就是说,斯蒂芬写作的动机在于自我保护。当自己一方无依无靠的时候,树立一个保护圣徒的形象。因此,他会夸大威尔弗里德的功德,夸大对手的忏悔和对手对威尔弗里德的赞美,但是没有必要通过写作,夸大敌对因素,增加对手的敌意。换言之,他对教会内部冲突的描写应该是较为客观的。而且,不论他的描写是否有夸大,至少这些冲突应该是存在的,实际发生过的。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的话,比较之后的结论自然是:比德并没有真实地记录下来围绕威尔弗里德被免职而发生的教会冲突。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故意做了淡化处理。不仅如此,在叙述英吉利人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比德一直都有淡化教会内部冲突的倾向。例如,他对被免职的主教几乎都没有什么交代,往往一笔带过。唯一交代较多的例子是替代威尔弗里德三年后被免职的约克主教切德。在这里,比德的主要目的是要表彰切德谦卑的美德和大主教西奥多的智慧和识人之能。(28)可以说,《英吉利教会史》是描写英吉利人接受基督教,传播基督教,发展基督教,逐步统一到罗马普世仪式中来的“主旋律”作品。这部作品的结尾写道:“这就是目前不列颠的整体状况,即英吉利人来到不列颠后大约第285年,公元731年。愿人间在主的永恒王国欢欣雀跃;既愿不列颠感戴主的信仰,愿众海岛安享欢乐;也愿铭记神圣的主而忏悔!”(29)
如果联想到如下事实,那么比德的良苦用心就更加明显了。708年左右,因为在《论计时》(De temporum ratione)中对历史分期抱有不同看法,比德本人被以异端的罪名起诉,带到主教威尔弗里德的面前受审。他为此进行了长篇申辩。但是,比德却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面对现实中激烈的教会内部斗争,在《教会史》中提倡教会内部的和谐,写作歌颂英吉利人教会和谐发展的主旋律作品。
三、比德的写作原则
前文提到,比德在作品前言中交代了写作目的,“是我们从大众传闻中收集到的,为了教育后代而努力用文字简单地加以保留的那些。”其具体实现方式是既记录“善人善行”,也记载“恶人恶行”。他记载“恶人恶行”的目的,不仅是让读者或者听众加以避免,而且是“更加自觉地追求他知道是合天主意的善事。”因此,比德的这段表述,与一般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并不尽相同,而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且因之从善如流”。这种具体的写作目的,使得比德倾向于记录善人善行。(30)
据不完全统计,在行文中,作者提到有18处为什么要记录善行。它们包括:1.教皇荷诺留斯的信,强调要有约克大主教;2.奥斯瓦尔德王的神迹;3.苏格兰学者见识奥斯瓦尔德的神迹;4.福尔萨所见地狱景象;5-6.埃塞尔伯格的修道院的神迹;7.奥斯瓦尔德王的神迹;8.怀特岛的两个小王子接纳基督教;9.对院长嬷嬷埃塞尔思里思王后的赞歌;10.囚徒锁链自行松脱的神迹;11.科尔丁厄姆修道院的毁灭;12-13.卡思伯特的神迹;14-15.主教约翰的神迹;16.死而复活的人的见闻;17.死时受惩罚的例子;18.亚当南关于圣地的书。(31)其中仅有2处(11、17)属于“恶人恶行”,总比例为11%。这表明比德确实是在从正面进行教诲,通过讲述善人善行使读者和听众受益。
正是基于这一写作原则,比德刻意淡化了威尔弗里德事件中教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淡化了英吉利人教会史中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写作了“主旋律式”作品。在他的笔下,各种宗教人物忽略差异和争执,折中调和,追求统一,谱写了英吉利人教会的伟大历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大概要数威尔弗里德的继承人、赫克瑟姆主教阿卡。他本是取代威尔弗里德为约克主教的博萨的弟子,是艾丹的再传弟子,后来改变立场追随威尔弗里德,被威尔弗里德临终时立为继承人,但在担任了二十多年的主教之后最终被革职。正是他授命斯蒂芬写作了《威尔弗里德传》。
阿卡的曲折经历是其师威尔弗里德命运的延续,反映了此时诺森伯里亚教会内部的继续冲突。但是,在比德的笔下,阿卡摇身一变成为虔诚向学、不断追求真知的典型。“他从小就在天主所宠爱的约克主教、最神圣的博萨属下的教士们中抚养长大,接受他们的教育;此后,为了更大的收益,他投奔威尔弗里德主教,毕生为其服务,直至他去世。他还和威尔弗里德一同去过罗马,在那里学到了本国无法学习到的对神圣教会的各项宗教仪式很有助益的知识。”(32)在他身上,根本就没有教会斗争的痕迹。
比德的这些记叙并非不准确,它们基本属实,但是又极不全面,严重忽略了英吉利人教会史中的冲突和斗争。作者不仅没有尽可能地反映全部的史事,而且还有意识地淡化某些方面,忽略某些史事,给读者和听众制造一种片面的认识,从而达到讲述“善人善行”,教诲读者做合天主意的善事的写作目的。
应该说,这种片面性是教会史写作的一种传统。凯萨里亚的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公元260-340年)被尊称为“教会史学之父”。通过写作《教会史》,他为教会史奠定了基本的写作原则,大体说来,以讲述教会主要神职人员的更替为主,兼及传播教义的名贤,其中也包括各种异端。因此,正统与异端之间的斗争,成为教会史的主要线索和叙述内容。此外,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争斗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殉道士是重点表彰的对象。与古典史学不同,尤西比乌对于世俗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是强调关于教义的说教、宗教实践、通过圣徒实现的奇迹和上帝的天启,以便证明信仰的正确性和必然性。(33)
尤西比乌之后,基督教逐渐战胜对手,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教会。继承尤西比乌续写教会史的苏格拉底自然更加关心教会内部的和谐,但是在写作中,表现得更多的是党派意识,对破坏教会和平的异端口诛笔伐,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抨击和批评。他的《教会史》以对阿里乌斯的谴责开篇,而收笔于期望和平降临教会。通过记录对手的错误,褒奖己方的德行,以此获得教会内部的和谐,似乎成为早期教会史的传统主题。6世纪晚期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写作《历史十书》(通俗名称为《法兰克人史》),其写作意图也是“把国王同敌对的人民、殉教者同异教徒、教会同异端之间的战争记录下来”(34)。
与这一教会史写作传统相比较,熟读诸位前辈史作的比德同样是根据基督教教义强调教会内部的和谐,但是他的实现方式却另有不同。(35)《教会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卷前22章,叙述在英吉利人之前控制不列颠群岛的不列颠人历史。在这一部分中,比德基本上遵循上述教会史写作传统来写作,讲述基督徒的殉道、正统派与异端之间的斗争,揭示不列颠人的罪恶。
一旦比德开始第二部分的叙述,讲述他自己的种族——英吉利人的皈依,叙述英吉利人的基督教教会史,文风为之一变。批评和攻讦色彩骤然淡化,很少提到因教义错误而发生的斗争,代之而起的是各种调和折中以达成英吉利人教会的和谐发展。个别的恶人恶行偶有记载,但是与善人善行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比德的教会史是歌颂自己的民族——英吉利人的教会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被称誉为“英国史学之父”,实至名归。
比德开创的英吉利人教会和谐发展的主旋律写作传统流传下来。半个世纪之后,另一位伟大的学者阿尔昆用韵文写作了一部《约克主教、列王和圣贤颂》,将历代约克主教、圣贤当作前后一贯、一脉相承的圣徒系列,加以歌颂。(36)直至今天,这一主旋律在主要依赖于比德叙述的现代学者中还有极大的影响。
注释:
①C.普卢默:《可敬的比德的历史作品》(C.Plummer,Venerabilis Baedae Opera Historica,tomus prior),牛津大学出版社1896年版;比德著,陈维振、周清民译:《英吉利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②A.M.瑟拉:《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A.M.Sellar,"Life of Bede",in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07年版,第xxxix页;C.吉文-威尔逊:《编年史: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写作》(C.Given-Wilson,Chronicles: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Medieval England),伦敦2004年版,第11页;E.布莱扎赫:《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史学史》(E.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A·格兰斯顿:《英国史学史550-1370》(A.Gransden,Historical Writings in Englandc.550-1370)第1卷,伦敦1996年版,第24-26页;C.郭瓦赫等主编:《中世纪辞典》(C.Gauward etc.eds.,Dictionnaire du Moyen Age),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比德著,陈维振、周清民:《英吉利教会史》,第7页。
③"Lectoremque suppliciter obsecro,ut,siqua in his,quae scripsimus,aliter quam se ueritas habet,posita reppererit,non hoc nobis imputet,qui,quod uera lex historiae est,simpliciter ea,quae fama uulgante collegimus,ad instructionem posteritatis litteris mandare studuimus."C.普卢默:《可敬的比德的历史作品》,前言。
④瑞伊不这么认为,R.瑞逸:《比德的“历史的真实法则”考》(R.Ray,“Bede's Vera Lex Historiae”),《棱镜》(Speculum)第55卷,1980年第1期,第1-21页。
⑤W.郭法特:《重释比德的“历史的真实法则”》(W.Goffart,“Bede's vera lex historiae explained”),《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Anglo-Saxon England)第34卷,2005年,第111-116页;M.A.佩妮:《历史的真实法则: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的圣徒和奇迹研究》(M.A.Payne,Vera Lex Historiae:Saints and Miracles in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路易斯维尔大学未刊硕士论文,2004年,UMI编号1420265。
⑥W.郭法特:《蛮族历史的编撰者们》(W.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海尔姆虽然质疑郭法特的具体结论,但是也重视比德的写作偏好,N.J.海尔姆:《重读比德》(N.J.Higham,Re-Reading Bede: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n Context),伦敦:2006年版,第58-69页。
⑦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Eddius Stephanus,“Vita Wilfridi Episcopi”),詹姆斯·芮尼主编:《约克教会的史家及其大主教们》(James Raine,The Historians of the Church of York and Its Archbishops),伦敦1879年版。我们并不能确知其作者为谁。一般认为是艾迪·斯蒂芬。这部作品大约写成于710年至715年间。D.P.科比:《比德,艾迪·斯蒂芬与〈威尔弗里德传〉》(D.P.Kirby,“Bede,Eddius Stephanus and the Life of Wilfrid”),《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98卷,1983年,第101-114页。
⑧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IV节。
⑨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V节。
⑩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XX节。
(11)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ⅩⅩⅫ节。
(12)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LI节。
(13)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LⅢ节。
(14)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LⅣ节。
(15)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LⅨ节。
(16)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4卷13章。
(17)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LⅢ节。
(18)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4卷23章。
(19)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XLⅦ节。
(20)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5卷19章。
(21)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5卷19章。
(22)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3卷26章。
(23)M.狄内斯里:《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教会》(M.Deanesly,The Pre-Conquest Church in England),伦敦1961年版,第101页;R.阿贝尔:《惠特比宗教会议》(R.Abels,“The Council of Whitby”)《不列颠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第23卷,1983年第1期,第1-25页。而强调会议的特殊意义,乐观估计形势的学者也不少。如H.梅尔-哈丁:《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基督教传播史》(H.Mayr-Harting,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24)普卢默编:《可敬的比德的历史作品》,第ⅫⅩ页。
(25)博礼提到了这种普遍流行的观点,但是他持保留态度。R.L.普尔:《圣威尔弗里德和里彭教区》(R.L.Poole,“St.Wilfrid and the See of Ripon”),奥斯丁·博礼编:《年代学和历史研究》(Austin L.Poole,ed.,Studies in Chronology and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56-81页。
(26)柯尔格雷夫总结这种流行观点后,为斯蒂芬稍作了辩护。B.柯尔格雷夫:《斯蒂芬的〈威尔弗里德传〉》(B.Colgrave,The Life of Bishop Wilfrid by Eddius Stephanu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电子版,第XI页。撒切尔通过比较发现比德“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A.撒切尔:《七世纪英格兰》(A.Thacher,“England in the Seventh Century”),弗拉库里主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Paul Fouracre,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
(27)艾迪·斯蒂芬:《威尔弗里德传》,第LXⅦ节。
(28)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4卷2章。
(29)"Hic est inpraesentiarum uniuersae status Brittaniae,anno aduentus Anglorum in Brittaniam circiter ducentesimo octogesimo quinto,dominicae autem incarnationis anno DCCXXXI; in cuius regno perpetuo exsultet terra,et congratulante in fide eius Brittania,laetentur insulae multae,et confiteantur memoriae sanctitatis eius."C.普卢默:《可敬的比德的历史作品》,第5卷24章。
(30)S.凯恩斯:《8至10世纪英格兰》(S.Keynes,“England 700-900”),麦基特里克主编:《新编剑桥中世纪史》(R.McKitterick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S.弗特:《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修道生活》(S.Foot,Monastica Life in Anglo-Saxon 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5页。
(31)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2卷18章,第3卷2章,13章,19章,第4卷7章,10章,14章,16章,20章,22章,25章,30章,32章,第5卷2章,6章,12章,13章,15章。
(32)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5卷21章。
(33)尤西比乌:《教会史》(Eusebius of Caesarea,Church History)电子版第1卷,1章1-3节。Kevin Knight.
(34)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卷一·前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35)关于比德对这些前辈作品的阅读,海尔姆:《重读比德》,第74-75页;R.瑞逸:《比德》(R.Ray,“Bede”),M.拉皮基主编:《布莱克维尔盎格鲁—撒克逊百科全书》(M.Lapidge,ed.,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Anglo-Saxon England),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7-59页;M.拉皮基:《盎格鲁—拉丁文学》(M.Lapidge,Anglo-Latin Literature,600-899),伦敦1996年版,第20页;A.H.汤普逊主编:《比德的生平、时代和作品》(A.H.Thompson,ed.,Bede:His Life,Times,and Writings),牛津大学出版社1935年版,第133页;G.博纳尔:《比德和中世纪文明》(G.Bonner,“Bede & Medieval Civilization”),《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1973年第2期,第71-90页。
(36)阿尔昆:《约克主教、列王和圣贤颂》(Alcuin,The Bishops,Kings and Saints of York,),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S.弗特:《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修道生活》,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