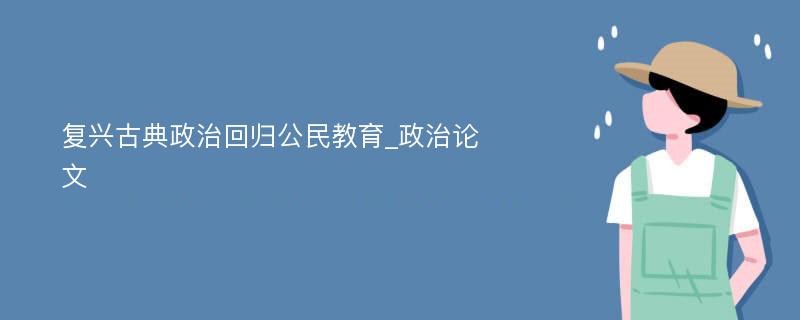
复兴古典政治学与回归公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公民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必须审视自身。学科及该学科学者的自我意识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遗憾的是,随着现代政治学研究范畴的丰富与研究方法的精密化,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功能——公民教育却逐渐淡出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学者普遍认为,“从一种科学降格为一种公民教育”,“会导致学科堕落”[1](第3页)。当现当代政治学从公民教育的立场上后撤的同时,政治学也日益成为僵化的、以唯现实论与唯物质论为特色的庸俗政治学,丧失了该学科在人类智识领域中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
一、公民教育的特定内涵
政治学的“堕落”与其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古典时代,公民教育为政治学研究提供动力,政治学研究为公民教育提供手段。政治学古典传统的湮灭,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学的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
一般的政治教育或政治社会化并不能称为公民教育。柏拉图认为,赚钱和健身的技能,甚至单纯获得知识的训练,都不能成为公民教育。他心目中的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2](第27页)。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教育是“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事”[3](第275页)。培养同政体相适应的公民精神成为他的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现代民主理论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知识也不过是铸造良善国民的方法之一,公共心和诚实比知识还重要[4](第80页)。
政治知识的拥有可以属于学者,政治技能的获得可以属于政客,只有真正的公民才拥有政治品德。所有的政体都会按照自己的政体精神推行自己的政治教育,只有共和政体中的公民才拥有优良的政治道德。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政治道德被称为公民美德。因此,公民美德的培养成为公民教育的本质规定;公民教育应该成为民主政治学的基本功能。
二、古典政治学中的公民教育
古典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同一的,国家体系就是一个教育体系;公民教育是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其手段。卢梭这样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著作,并不象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像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5](第11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美德”[3](第148页)。西塞罗认为:“对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6](第12页)因此,在古典政治学家的眼中,政治是道德与教育的联合体;公民教育的实施与公民美德的培养是为了使公民进入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公民教育获得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为了获得公民美德,政治学必须研究公民教育;由于对公民教育的研究,政治学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
希腊人认为知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古希腊理智活动开端的苏格拉底提出了可作为古典政治学学科基础的观点——美德即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观点的提出意味着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美德及其体现——优良的生活。美德的客观性意味着美德是可以传授的,它是以实现优良生活为目标的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此,马克斯·韦伯这样评价古希腊人的知识观:“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真正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掌握或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正确行为。”[7](第31页)因此,希腊人的知识观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为:美德→科学→教育。
既然优良生活是一种道德生活,以追求优良生活为目的的政治也就成为实现美德的一种工具,参与政治与弘扬政治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道义基础。由此,对古典政治学家提出了双重要求:他们不应只躲在学术的象牙塔中沉思冥想,探索政治与人生之理,还应该勇敢地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以自己的所知教育和引导芸芸众生走向幸福之路。西塞罗的观点在古典政治学家中最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有什么能比把参与和从事伟大的事业同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和认识结合起来更美好呢?”[7](第103页)公民教育就成为连接政治学家的两种生活——反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的一座桥梁;通过投身于公民教育,政治学家达到了反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的和谐统一。由此,政治学的学科之王地位与政治学家的先知角色得以成就。亚里士多德认为,保全城邦政体最重要的方法是“按照政体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3](第275页)。而古典共和国的生存取决于公民能够完全抛开自我利益,无私地投身于公共生活。忘我精神就成为公民美德的核心与公民教育的目标。但政治学家的知识只有通过诉诸感情渠道,才能成为多数公民所接受的美德。所以,古典公民教育实践不可避免地内含有某种蒙昧主义的因素。
由于古典政治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美德,所以古典政治学的最大特征是政治与伦理相互结合,伦理高于政治。古典政治学家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伦理诉求,伦理诉求体现了人的规定性与人的价值,所以参与政治生活就成为实现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的手段,公民教育就成为伦理与政治完美结合的手段。总之,古典政治学是一种追求个人道德善化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德性政治学,是一种超越现实利益与琐屑欲望的英雄政治学,更是一种弘扬个人主体性与自我实现的人文政治学。
当人类蹒跚着进入中世纪时,作为基督徒美德的沉思来世的生活逐渐高于作为现世荣光的行动的生活,政治被看作是对人生毫无意义的空虚浮华的活动,道德与政治的分离势不可免,政治学丧失其学术之王的地位,导致公民教育被漠视、被抛弃。
三、近代公民教育合法性的丧失
近代资产阶级将政治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同时又将其置于自己的狭隘自私的欲望算计之中。在古典时代,政治学与公共德性密不可分,公共德性指导着政治学;到了中世纪,神的德性隐蔽了政治学;而到了近代,人们索性将德性与政治学之间的内在链条彻底斩断。在这种执拗的努力之中,政治学成为实现个人物质欲望最大化的庸俗政治学,成为追求纯粹自然科学理性、抛弃人文关怀的机械政治学,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一己私利、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权力(利)政治学。政治学在德性上的堕落,使得公民教育丧失其核心目标:对公民美德的追求。
政治学庸俗化与公民教育丧失合法性的过程始于马基雅维利。人们认为,他是用“人的眼光”分析政治问题的先驱,在“他的作品中隐含着这样的命题:政治科学是自主的活动,它具有与道德和宗教不同的自身原则和规律”[8](第96页)。但是,马基雅维利眼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只不过是狡黠的、野心勃勃的、具有强烈的权力与财富攫取欲的、在寓言故事中以列那狐形象出现的资产阶级前身——市民阶层。马基雅维利不但使政治摆脱了道德的束缚,他还使德性服从于政治,使道德成为政治的婢女,把德性政治学改造为权力政治学。霍布斯与洛克接过了马基雅维利的旗帜,只不过将其涂上一层圣油而已——将权力政治学转化为权利政治学,使政治学中的非道德倾向继续合法化。
霍布斯试图将政治学建立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法则中引申出人的自我保存的本能,主张保有个人的肉体存在是人类走向政治的根本原因。自我保存的权利成为基本人权。这样,政治学就成为研究如何活命的学问。洛克认为,人不仅有维护肉体存在的权利,也有过舒适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样,洛克又将政治学变为如何发财的学问。显而易见,霍布斯、洛克的政治学是为新兴资产阶级辩护的政治学。在他们的教诲下,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放弃追求个人完善与公共福利的信念,坦然地享受起温暖舒适的个人生活。这样的政治学不关注通过政治参与扩展人的潜能,更不关注通过公民教育塑造大众的公共美德,它只着眼于通过制度设计抑制个人私欲的极端膨胀所导致的共同毁灭。
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导致了道德生活中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人们认为,道德只存在于私人领域,个人拥有选择信仰的权利,以及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合理性。这些主张使公民教育失去了必要性。19世纪末,现代大学的出现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分化又使政治学研究者努力追求学科的学术化,反对学科的人文化,拒绝使政治学承担人生选择与指导的角色,使其日益成为一门与其他学科相隔绝的孤立的学科。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科学语言的形式拒绝了政治学人文化的可能性,最终奠定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韦伯对政治学的公民教育功能的扼杀来自于他的事实与价值二元知识观。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政治理论研究中关注价值因素是无益的;韦伯则认为,在科学研究中考察价值的优劣是不可能的。两人合力将价值因素包括宗教与道德逐出社会科学的门墙。韦伯的核心命题为: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或开端是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即价值关联),但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避免将价值混同于事实,使价值观影响到自己的科学判断,做到价值中立。“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评价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信仰的事情。”[9](第6页)学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并对时下流行的政治理想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完全是有必要的,可以提高科学研究的有效性。但是,韦伯又进了一步。他说,学者不应向学生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要试图成为公民教育家。“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6](第37页)学者为什么不能宣讲价值问题呢?韦伯认为学者的职业伦理要求他坚持概念清晰与价值中立的科学理想,不能涉足于无法论证的价值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在教学上向来不容许不同的政治观点自由表达,学者保持公正的惟一方式是对价值问题闭口不谈。韦伯的结论是,为了保持“知识的诚实”,学者不应成为政治领袖。由此可以发现,韦伯反对学者成为公民教育家,割裂反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之间的统一,同样来自于一种无法加以科学证实的价值立场,即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从韦伯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公民教育的研究应该从政治学中驱逐出去,公民教育的功能不属于政治学家。但是,韦伯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尾巴,这同样也是出于价值的立场。韦伯认为,科学研究对价值问题的惟一贡献是它可以保持“头脑的清明”——即学者通过对各种价值观进行研究,有助于一个人对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进行选择,勇于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如果教师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我甚至愿意说,他就是在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创造了义务的意识,清明的头脑和责任感。”[6](第44页)由此可见,韦伯的方法论虽然坚持价值中立,但在政治研究中行动与价值的绝对分割是不可能的,韦伯也不能摆脱这种困境。
韦伯的方法论建立在反对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但尾随其尘的社会科学家们只读对了其思想的一半。在韦伯之后,“社会科学也卑躬屈膝地模仿自然科学,并被他们自身的法则即事实与价值的两分阻碍着去谈论政治与道德上的善好”[10](第339页)。这种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也侵入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摒弃价值判断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放弃对政治生活的形而上学的思索,致力于从权力的实际运作与利益的现实分配的角度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反对将道德问题与人生问题置于政治学中心位置的人文政治学,拒绝承担公民教育的职责。如政治学者卡特林就自诩自己是“政治实验科学家”[11](第32页),将具有无限可能性与自我完善能力的人视为政治实验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学的恶果在行为主义政治学这里已显露无遗。
考察自古典末期以来政治学的蜕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道德完善与自我实现为目标的古典政治学沦为以利益达成与权力获取为目标的庸俗政治学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民教育在政治学研究中丧失其合法性与存在权利的过程。
四、现代公民教育与走向新古典政治学
自由主义政治学认为,无须弘扬公民美德,通过制度设计魔鬼也可以解决优良政府的问题。但是,随着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公民日益以自我为中心而相互隔离,放弃自治精神而委身于巨灵般的福利国家。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当代中国的政治情境中,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与狂热的政治迫害浇灭了近代以来精英与大众的政治热情,人们退缩到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被视为怀旧情调,这一切使得政治学者认为“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也依赖于民主制度下公民的素质和态度”[11](第512页)。但是,改造政治问题必须首先正本清源,反思政治学漫长的蜕变过程,重新塑造政治学的自身基础。因此,当代政治形势向政治学者提出了通过复兴古典政治学传统、回归公民教育精神的要求。
复兴古典政治学不是要恢复古典政治学中的蒙昧主义与政治不宽容因素,而是要在现代理智条件下吸取古典政治学中道德与政治、自由与公益、理想与现实及理论与实践和谐统一的传统,建立一门新古典政治学。
新古典政治学的建立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问题是一门科学,人生理想可以通过理性的探讨加以把握。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才能将“意义”问题引入政治学研究中,恢复古典政治学的德性传统。在政治学的知识观上,我们可以将韦伯的终点作为起点,并将古典政治学的核心理念加以改造。韦伯认为,科学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客观的政治现象,从而为我们的政治决断提供知识基础,获得“头脑的清明”,这是科学为道德问题做出的惟一贡献。韦伯的这一最后立场可以作为政治学者从事政治研究的起点。政治学者首先要本着“知识的诚实”,尽量在研究过程中排除个人与社会的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但政治学者还应该树立“知识即美德”(将古典政治学的核心理念——美德即知识加以置换)的信念,从韦伯的立场上再进一步。就是说政治学者不但要将获得政治真理作为一种美德,还要将宣扬这种政治真理作为一种美德,以恢复古典政治学中反思与行动相统一的传统。新古典政治学还要以人的道德善化为指向,恢复古典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沉溺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古典政治学家将自己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考察与对理想社会政治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超越于资产阶级庸俗政治学之处就在于它不仅要实现民主政治,还要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获得人的全面发展。这和古典政治学的标准不谋而合。因此,新古典政治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观为指导,恢复古典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要在新古典政治学中实现德性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还必须致力于政治学的人文化。政治学的人文化要求政治学者打破近代以来人为形成的学科之间的分割与分工,探讨政治与人生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政治学在政治之外的其他生活领域的拓展,从而提高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新古典政治学得以构建的一个关键手段是回归公民教育传统。这种现代公民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古典公民教育,它以启蒙原则为基础,要求通过知识的传播与理智的探讨使人们自觉地接受公共利益,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和谐发展。只有通过现代公民教育,才能实现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伦理政治(正义)与现实政治(权力或权利)、理想政治与世俗政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理论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和谐统一,才能完成对当代政治学的学科改造,从而有助于解决当代政治问题。利奥·斯特劳斯通过对古典政治学的解读,发现了“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10](第8页)。为了挽救破碎的政治生活,为了解救人类的洞穴困境,政治学者必须勇敢地承担其职业伦理——重建古典政治学与回归公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