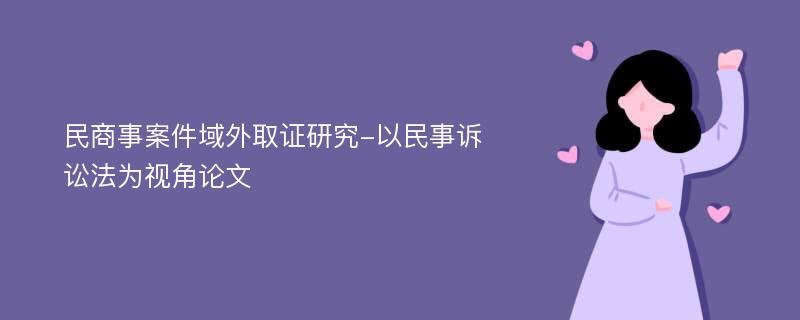
民商事案件域外取证研究
——以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曹 佳1,普 畅2
(1.中国政法大学 证据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2.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 随着涉外案件数量激增,民商事案件中域外取证问题日渐突出。域外取证本质上是民事诉讼中取证制度的一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此作出基本规定。就域外立法例来看,美国和欧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模式,前者充分贯彻了当事人主义基本精神,而后者则以职权主义为根基。以这两种基本模式为参照,我国应当综合两者之所长,既要将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作为基本取证路径之一进行规制,又要注重强化人民法院基于司法协助途径所进行的域外取证。在建构域外取证制度时,需要从程序规范和评价规范两个层面展开。域外取证的程序规范与评价规范是一体两面的。缺乏程序规范,评价规范便缺乏指向性;而缺乏评价规范,程序规范就会丧失其实质意义。二者共同构筑了我国域外取证制度的整体样态。
关键词: 民商事案件;域外取证;程序规范;评价规范;民事诉讼法
一、问题引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民商事案件中的“涉外”元素激增①。众所周知,“只有准确认定事实,才能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诉讼各方的合法权益”[1],而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就必须尽可能充分地获取相关证据。因此,在“涉外”纠纷中,域外取证制度便具有决定性意义。
就我国当前立法来看,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具体包括:《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取证公约》)、《民事诉讼法》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2001年8月27日最高院发布)、《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及其实施细则(2013年最高院发布)、《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2017年2月27日最高院发布)等。尽管相关法律规定看似丰富、繁多,然而其中也存在着严重不足。首先,“域外取证程序不清,实践不统一”[2]。虽然《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空疏之弊,但综观整个规则体系,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是否应当进行程序性规制,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域外取证程序等;此外,相关公约、条约的国内法转化较慢,并且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缺失了有关域外取证制度的基本规定。这不仅导致域外取证面临着操作性难题,而且致使该制度整体缺乏体系性。
就当前理论研究而言,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学界过多地从国际私法视角研究域外取证问题,将域外取证当作国际司法协助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过于强调通过缔结公约或条约来处理域外取证中的相关难题。然而,域外取证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中取证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其基本制度框架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得到规定。就此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对该主题的关注显得较为薄弱。
综上,无论是从当前的立法现状来看,还是就理论研究而言,民商事案件中的域外取证制度都是一个亟需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试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对民商事案件中的域外取证基本问题展开探讨。下文将首先从比较法角度探讨美国与欧盟在域外取证问题上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以此为背景,接着分别从域外取证的程序规范和评价规范两个层面探讨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建构域外取证基本制度的实现路径。概而言之,民事诉讼法应当为我国法院进行“涉外”诉讼所涉及的域外取证实践提供基本的、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的制度规范。在此基础上,当存在可适用之公约或条约时,便优先适用相应公约或条约;当不存在可适用之公约或条约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制度规范则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
二、比较法视野下域外取证的两种基本模式
大体而言,一国之域外取证制度,不仅受其诉讼模式影响,而且在根本上取决于该国在此问题上所奉行之价值选择。综观当前各国域外取证规范,大体存在着两种基本相反的制度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
(一)美国特立独行的域外取证制度
概而言之,美国域外取证制度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即《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中的相关规定以及有关域外取证的公约,后者主要包括《海牙取证公约》与《美洲国家间关于嘱托书的公约》(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Letters Rogatory)。通常而言,域外取证主要还是按照《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来实施②,由此形成了以《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为主,相关公约为补充的制度设计模式。此处,本文着重关注的是《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中有关域外取证的规定。
首先,1206 号文件主要规定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取证方式,即间接取证与直接取证。但与《海牙取证公约》的规定不同,这两种方式都被进行了改造以适应追求效率的价值需要。根据该文件Article 1(1)的规定,成员国可以要求(a)其他成员国适格法院收集证据;或者(b)直接在其他成员国收集证据。据此,1206 号文件允许域外取证的请求直接在法院与法院之间传递,从而避免了《海牙取证公约》所规定的繁琐传递程序。根据Article 2 和3 的规定,各国应当确定一份可以执行取证事项的法院清单和一个中央机构,其中中央机构不具体负责请求的传递,而仅仅是提供辅助性和协调性的帮助。就此而言,域外取证不仅程序简单清晰、可操作性强,而且提高了证据收集的效率。与此同时,各成员国还可以在其他成员国直接取证。根据该文件第2 章第4节的规定,在向证据所在国中央机构或适格机关提交申请后,成员国可以指派司法官员或其他人员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在其他成员国直接取证。不仅如此,直接域外取证的申请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够被拒绝。如此看来,直接域外取证可谓名副其实。
从诉讼角度来看,评价规范不仅影响着法官对域外证据的审查判断,而且有助于指引取证者在取证环节就注意收集满足庭审需要的域外证据。就此而言,注重评价规范的建构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⑩。大体来讲,对域外取证的评价应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即取证过程和取证结果,后者实际上就是指域外证据。
综上,美国域外取证制度基本上贯彻了当事人主义的基本精神,相关法律规范将域外取证的基本权利几乎交付到了当事人手中。可见,相对于其他国家对主权价值的过度强调,美国的域外取证制度更加注重真相和人权保障等价值。
按照每月练兵成绩,对照考核细则,对当月练兵成绩优秀的队员进行奖励,并对成绩不达标的队员进行惩罚,考核结果兑现在当月工资中。同时,全年的考核情况也为年底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练兵中出现不合格情况的队员,不在岗位标准作业流程先进个人评选范围。
(二)欧盟域外取证制度
总体上看,欧盟成员国在处理域外取证问题上实行了大致类似的制度。与美国不同,欧盟国家多数都非常看重主权问题。要保持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联合体的稳定性,对主权因素的处理和协调显然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域外取证的实施主要还是通过政府之间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但与一般政府合作的松散形式不同,针对该问题,欧盟以直接立法的方式替代了基于条约或公约的合作形式。具体来讲,欧盟理事会制定了《域外取证规则》(2001年欧盟第1206 号)(下文简称1206号文件)④。该规则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改善、简化和加速跨国取证,从而使欧盟内部市场的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4]。当然,在欧盟之外,各国主要还是基于《海牙取证公约》以及其他条约来实施域外取证⑤。本文重点关注的是1206 号文件中的域外取证制度。
要理解美国域外取证制度,首先必须理解“取证”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大体来讲,“在美国审判实践语境中,‘取证’指的是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收集事实信息的过程,这些事实信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他们的诉求或辩解。……取证不是法院去发现事实的过程,取证是当事人去发现事实的过程,由当事人将所发现的事实提交给法院”[3]。因此,在美国司法程序中,取证活动基本上由当事人主导。以此为基础,《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规定了独特的证据开示制度,即要求当事各方在开庭审理前将相应的证据向对方披露,从而使诉讼参与各方能够了解即将在法庭上使用的所有证据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由此保障诉讼的公平性。只要“诉讼一开始,当事人或其律师就有权对对方采用证据开示程序,并且不需要法院事先批准”③。而就开示的范围而言,根据《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26(b)(1)的规定,当事方可以要求开示与任何当事方之诉求或辩解相关的非保密特权范围内的事项。这一“相关性”要求范围极其广泛,不仅超越了《联邦证据规定》对“相关性”的定义,而且其他国家也很少有作如此宽泛设定的。就此而言,只要对证明案件事实有帮助的任何事项都可能成为证据开示的对象。综上所言,在域外取证问题上,当事人及其律师不仅可以自行直接展开域外取证活动,而且其取证范围往往非常宽泛——这便是美国域外取证制度最突出的特征。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欧盟国家非常注重主权问题——与美国不同,域外取证并非当事人来实施,而是由法院等国家机关全权处理;但另一方面,其对主权问题的处理其实已在一个更宏观的国家合作框架内,因而其在域外取证这样的基础问题上能够处理得更为顺畅。
(三)两种基本模式之简要比较
大体而言,美国和欧盟在域外取证模式上的差异与其所采用的诉讼模式息息相关。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实行的是最典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事实调查环节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在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几乎不对证据信息收集进行干预。相比之下,欧盟整体处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背景之下。“基于此种诉讼模式的取证制度,也是以法院或法官为中心展开的。法官凭借职权亲自搜索事实,听取证人和鉴定人的陈述,审查文件,保全证据。他们认为,取证属于一种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活动。”[5]因此,整体来看,在域外取证问题上,美国与欧盟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各自诉讼模式所引致的。
究其根本,诉讼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是价值理念的差异。就美国域外取证制度而言,其基础性价值预设是“基于自由的公平”,或者如罗尔斯所说,这是一种“自由的价值”,即“自由对于所有人是一律平等的,这是制度框架或制度环境,自由的实现则不同,它体现为不同价值的实现”[6]。简而言之,法律赋予当事人进行自由域外取证的权利,而是否能够进行充分的域外取证并进而收集尽可能多的域外证据,则几乎依赖于当事人自身的能力与资源。与之相反,欧盟在域外取证问题上的价值预设是“基于平等的公平”,即域外取证活动基本处于法院的管理之中,当事人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法院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域外取证,以保证当事人在取证能力和机会上地位平等,进而保障诉讼的公平。
进一步分析,这两种范式孰优孰劣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所采取的评价标准。如果单从司法效益的视角来看,即从“司法‘产出’与司法‘投入’之比”⑥来看,我们很难进行高低之判。因此,抛开主权这一意识形态因素不谈,本文认为,在建构我国域外取证制度时,我们应当同时吸收这两种范式的优点,尽量平衡上述两种价值理念,从而使得司法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价值和效率价值。简而言之,我国域外取证制度既要注重对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的规制,也要合理强化法院域外取证的能力和手段。
Influence of seismic wall layout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tructures
三、我国域外取证程序规范之建构
运用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整本书阅读不只在课堂上进行阅读和讨论,而是将阅读延展到家庭、社区等任意空间,且灵活采用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至少一部分是在线讨论、探究,至少一部分是在实体课堂上由教师介人指导的阅读学习,还有至少一部分是学生的自由自主阅读。课堂学习、在线互动、非课堂非在线自主阅读,至少这三个模块整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整本书阅读体验课程。
(一)当事人主导的域外取证及其程序控制
概而言之,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自行域外取证不仅在我国法律规范中不存在立法障碍,而且在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尽管这一取证方式相对简便易行,但也正因如此,对该种取证方式进行适当控制成为必要。
从基本原则来看,美国的相关规定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前文所述,根据《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规则28(b)和规则29,当事人可以对域外取证所采取的方式进行约定。这里,允许相互约定实际上体现的是意思自治原则。海因·科茨等指出,“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利”⑦。无论是在民法领域,还是在国际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都是适用的。“民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民事当事人实施的都是民事行为,这是由于无论是民法还是国际私法其都同属私法。”[7]因此,在我国,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也应当适用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即允许当事人双方对域外取证的具体方式作出约定。
从控制机制来看,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并非属于一种绝对自由的权利。实际上,这种行为往往受到两套以上法律体系的限制,即其他国家对于一般取证和域外取证的限制性规定以及本国有关取证活动的一般性规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理控制。
对于其他国家在取证方面的相关限制,在我国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予以遵守。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可以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在举证责任设定上,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即要求主张方提出相关当事人违反取证地强制性规定或侵犯他人正当权利的证据,包括具体的事实依据和相关法律规范。我国法院不主动审查当事人的取证行为是否符合取证地规定。如此,一方面可以促使当事人遵守他国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鼓励其他当事人进行合理监督,从而尽可能保证取证程序不侵害他国主权和人权。与此同时,法律可以鼓励当事人委托域外律师进行调查取证。这一做法在美国域外取证实践中常常被使用。域外律师必定熟知取证地法律,因此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取证程序的合法性。
我国法律对当事人域外取证的程序性控制,最为主要的控制机制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4年通过的《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存在很大争议⑧,但本文认为产生这种争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条规则本身,而在于规则的实施。李浩教授早就指出,“与其设置一条一般性的规则,规定法院在诉讼中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倒不如采用权衡排除的方式,授权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来决定是否予以排除”[8]。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控制民事取证行为从而避免其失序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域外取证这一问题上,由于取证行为发生在域外,我国相关机关很难进行管制,对于一些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取证行为要进行制裁时,排除适用该证据便是制裁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法官在这一问题上应当进行充分权衡。一般情况下,应以我国的相关标准为依据,当然如果依据他国法律完全不构成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所谓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取证方法要作特别限定。因为“公序良俗之具体的内容和范围,会随着不断生成发展之社会思想及人们的意识的变迁,而有差异”[9]。而取证行为所在地的公序良俗或与本土的公序良俗可能存在极大差异,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有关公序良俗条款的应用应作严格限制。
综上所言,一方面,我国应赋予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的基本权利,并在该问题上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另一方面,相关诉讼规则应对此进行严格控制,从而促进当事人域外取证的秩序化和合法化。
由于要研究农业生物质资源和地区贫困的关联,笔者对2016年伏牛山区域的17个县区的人均GDP与生物质资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讲,资源禀赋越丰富,则人均GDP就越高。但在伏牛山区域内,农业生物质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越是贫困的地区,就越会消耗掉更多的生物质资源,而对其他一些能源的使用却较少。
(二)人民法院主导的域外取证及其程序控制
与英美国家不同,无论是根据我国签订的国际公约和条约,还是根据《民事诉讼法》,我国法院都是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但在域外取证问题上,人民法院所主导的域外取证,具体应该如何启动和规制,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没有作特别明确的说明。
4.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根据《规定》和《意见》提出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理念的时间点,本文将2013年作为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的分界节点,来设计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变量(Inovation-Policy)。本文同时借鉴国际创新研究的惯例,选用了前后不同阶段三年的数据作为创新研究的时间跨度。[6]最终,当样本处于供给侧改革期间(2013—2015年),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变量(Inovation-Policy)取1;反之,当处于粗放发展转变期间(2010—2012年),变量(Inovation-Policy)取0。
就通常的取证启动程序而言,主要存在两种启动方式,即依申请启动和依职权启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时,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再结合《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来看,“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并未包含“域外证据”⑨。由此可见,人民法院不能单纯因证据形成于或处于域外,而依职权启动域外调查取证程序。进一步来看,《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作了明确限定,其中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域外取证只能适用第(三)种情形,即因其他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适用这一条款,并从而启动依申请进行域外取证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之所以设置第(三)项兜底条款,“一者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设置该条款确有必要;二者对该款的适用也要慎重,有必要由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所存在‘客观原因’及该原因导致其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问题予以举证说明”[10]。根据这种解释,一方面,是否具备相关“客观原因”,法官要对当事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当事人不能仅仅简单说明情况,而是要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何为“客观”,这里却没有明确标准。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举证标准和法院审查判断标准都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法院审查判断认为并非适格的“客观原因”,进而不予域外取证,从而实质性地影响了审判结果时,实际上就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权利。因此,建构明确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域外取证的启动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landslide in the southen plateau of Jingyang County ZHANG Qin-hua ZHANG Hua-xun ZHANG Zhi-pei(3)
正如奚玮教授所言,“应当根据中国国情,适度扩展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并通过阐明、诉讼风险告知等制度逐步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以渐进的方式向现代司法靠拢”[11]。本文认为,尤其在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制度尚未完善以及多数国家不接受此种取证方式的情况下,应当明确将域外调查取证纳入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而不能任其继续处于兜底条款的模糊状态中。当然,民事诉讼规范对此也应作一定限制,即仅局限为那些对案件事实认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域外证据或者相关信息。
四、我国域外取证评价规范之建构
除了上述的核心特征之外,就域外取证所涉及的管辖问题而言,《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甚至允许在属人管辖权被证明之前就可以对身处域外的当事人或证人进行取证;而就取证类型而言,主要涉及五种主要类型,即庭外作证、书面质询、书面文件、身体与精神检查以及自白要求。与此同时,根据《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28(b)的规定,在国外进行的庭外作证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开展:(A)根据可适用的条约或公约;(B)基于请求书,无论是否名之为嘱托书;(C)根据司法通知,在一个被联邦法律或询问地法律授权执行宣誓之人面前提供证言;或者(D)在一个被法院任命去执行任何必要之宣誓或获取证言的人面前提供证言。不仅如此,根据规则28(b)和规则29,当事方甚至可以约定所要采取的域外取证方式。就此而言,几乎很难说有任何强制性规则主导着域外取证活动。
(一)域外取证过程之评价规范
就当事人主导的域外取证过程而言,第一,对域外证人证言的取证来讲,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或证明证人作证的自愿性。这不仅涉及合法性,还涉及证言的可靠性。事实上,在证人作证问题上,合法性和可靠性问题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当证人作证的合法性存在问题时,其可靠性往往就会显得比较薄弱。与此同时,尽管很多时候证人作证的合法性不存在问题,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证人证言的可靠性通常也并非毫无疑问。对此,一方面,当事人取证过程中应当保留相应的证据材料或背景信息材料,法院在审查判断该证据时也应当着重对这方面资料进行审查;另一方面,评价规范的建构应当赋予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但异议的提出必须要以证据或证据线索为基础。如果域外证人证言相关的材料无法体现域外证人作证的自愿性,那么事实认定者便不能认定该证言的合法性与可靠性。具体来讲,当事人应提供该证人的年龄证明、作证环境说明、是否存在作证特免权的说明等。
第二,就实物证据的取证而言,主要涉及该证据的收集提取过程和保管过程。对此,当事人同样应提供相应的说明,从而使事实认定者能对其取证过程的可靠性形成基本判断。当然,若存在当事人以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之方法收集域外证人证言或实物证据的情况,法官应理性权衡是否对该证据进行排除。大体而言,由于当事人主导的域外取证过程往往并不完全处于公权力的监督之下,基于效益考量,事实认定者很难实质性地对取证过程进行充分审查评价。因此,就规则建构而言,一方面,事实认定者对取证过程不应该完全忽视或依赖于无法提供证明效力的公证认证手续;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地将证明责任转移给当事人,由当事人对域外取证过程进行举证证明或说明,从而保证事实认定者能够对其取证过程作出基本评价。
就人民法院主导的域外取证过程而言,其评价规范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其一,人民法院是否在审查当事人申请域外取证请求时提供了充分理由,是否存在怠于取证的不作为行为;其二,域外机关在进行调查取证时是否按照我国的要求进行,或者是否符合我国法律对于证人人权保障等事项的相关规定。就前者而言,其评价规范设定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当因人民法院之责而使当事人受到不利影响时,上诉法院或再审法院可依据该评价规范进行救济。就后者而言,尽管基于司法协助的域外取证一般在程序上具有可靠性,但各国在法治水平、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而域外取证之目的是为我国法院解决诉讼纠纷提供信息基础,故而不应因此造成对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侵害。
概而言之,域外取证的程序性评价规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当事人或法院遵守相应的程序规定,从而既保证域外取证活动的有序展开,又保障了最终所收集到的域外证据的可采性。就此而言,域外取证的程序性评价规范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具有积极的指引意义。
(二)域外取证结果之评价规范
按照何家弘教授的划分,证据评价规则或认证规则分为采纳规则和采信规则。“采纳是对证据的初步审查和认定,采信是对证据的深入审查和认定;……法官在决定证据能否采纳的时候,主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法官在决定证据能否采信的时候,主要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12]
1.域外证据之评价规范建构:采纳规则
总体来讲,域外取证的程序规范与评价规范是一体两面的。缺乏程序规范,评价规范便缺乏指向性;而缺乏评价规范,程序规范就会丧失其实质意义。按照逻辑顺序,下文将首先探讨我国域外取证程序规范之建构,然后再进入有关评价规范的讨论。根据程序主导者的不同,本文将域外取证之程序规范分为两大类,即当事人主导的域外取证程序和人民法院主导的域外取证程序。
大体而言,对域外证据的评价应当以相关性(或者关联性)为逻辑起点,这主要是一个经验判断过程。塞耶对此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对于所要证明之问题缺乏逻辑证明力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被采纳;第二,任何具有这种证明力的事物应当被采纳,除非存在明确的政策或法律理由要求排除它[13]。艾伦教授进一步指出,相关性实际上涉及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内涵,就其逻辑含义而言,“要求一个主张的清晰表达和支持该主张的证据。如果一个证据有助于证明或反驳所表达的主张,它就是相关的”。就其实质性层面而言,要求该主张与审判之间具备一定关系,大体而言,“一个主张如果在审判前就与诉讼有实际关系,它就是‘实质性的’”[14]。与其他证据相同,如果某个域外证据不具有相关性,那么其必然不能成为认证对象,进而更加不能成为裁判依据。从审查判断的效率层面来考虑,只有先确定了该证据的相关性,后续的证据评价才具有意义。总之,从相关性层面来看,域外证据的采纳规则应与一般证据相同。
从合法性层面来看,主要涉及对域外证据法定形式之要求的审查。根据《证据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在我国进行的诉讼中,当事人所提交的域外证据需要履行公证和认证的形式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要求,法官可径直以不具备合法性为由不予采纳该证据。也就是说,公证和认证成为了合法性的必要条件⑪。一般而言,“公证的内容是证明公证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15]。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就其对合法性的证明而言,一方面,经过公证的内容就一定是合法的吗?另一方面,未经过公证的材料就意味着一定缺乏合法性吗?⑫正如有学者所说的,“诉讼证据所要证明的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公证人无法亲历”,进而某一行为或事件到底是否具备合法性,公证人以及公证机构并无法确切知道,就此而言,所谓“公证”,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具有事后的形式意义[16]。还有学者认为,“经过公证的事实可以视为免证事实获得司法认知,然而,‘司法认知不过是表面的承认而已,对司法认知的事实提出异议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17]。所以,公证和认证应当是合法性的外在保障和证明机制,而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却将其作为合法性的内在必要条件。正如尹伟民教授所言,“将特别证明程序作为域外证据取得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存在三个立法上的不足,即:公证证明对证据能力认定无实质意义;证据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并非所有域外证据都能进行公证与认证;强制要求进行公证认证将带来诉讼的负效益[18]。就其本质而言,这也是违背一般逻辑原理的。因此,就形式要件而言,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但《证据规定》第十一条的“应当”条款需要加以修改,使其成为指导性规范。法官在审查判断域外证据之合法性时,也应当结合相关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及证据线索进行综合考量。
以班会课为例,众所周知,学校的主题班会向来都是投入巨大,场面隆重,但由于班会的主题、活动常常与升学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很多学生并不重视,导致班集体的道德教育、学生的人格引导等学校德育功能收效甚微。而在微课程引领下的微班会则不同,用“微”打开了学生的心理市场,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
2.域外证据之评价规范建构:采信规则
对域外证据的采信本质上是对域外取证活动的最终认可,设定科学合理的采信规则至关重要。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采信规则主要是指导性规则,而不应作机械性规定。
(1)域外实物证据采信规则
首先,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对待公证与认证手续的批判态度同样应适用于对域外实物证据采信规则的分析。简而言之,经过公证认证后的实物证据较之没有履行该证明程序的实物证据往往更加具有可靠性、真实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公证认证手续能够替代法院对实物证据真实性的审查⑬。
从外部视角来看,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是法官或事实认定者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权利只有法官才能享有”[19]。若认为存在公证认证手续进而就不再对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那么事实认定者便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此同时,这无异于将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权交付给了公证认证机构。从政治合法性层面来看,这样的规定或实践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就应该而且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
从内部视角来看,事实认定者对域外实物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直接影响着对该证据证明力的最终判断,进而影响着对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若不审慎审查这类证据,而仅仅以外部标准(是否具有公证形式、是否存在认证章印等)作为其真实性的标准,那么势必会导致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大打折扣⑭。本文认为,对于域外实物证据的采信应当将公证认证手续调整为补充性的辅助手段,应要求事实认定者根据常识和经验法则一般性地展开对域外实物证据的判断。
其次,尽管域外实物证据整体上属于一种证据类别,但其子类型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证据种类。整体而言,对域外实物证据的采信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来确定。但对于一些特殊形式域外实物证据的采信,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应当作出专门规定,以便为域外取证活动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指导。比如,针对一些以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形式存在的实物证据,相应的技术性标准就应当建立起来;针对一些域外书证,尤其是复印件、扫描件,法律应当规定较之一般书证更为严格的审查判断标准;针对那些基于司法协助而获得的域外实物证据,事实认定者在审查判断环节尤其要注意对证据保管链条的审查。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范应当是指导性的,否则便会产生与当前公证认证手续之规定一样的机械性效果。
大家在思维上有一个误区,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就是为了环保,然而新能源和环保只是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有了关联,实质上它们没有必然联系。比如使用纯电动汽车,汽车的排放等于零,但电厂的排放不等于零,仍然会产生污染。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本质是受到国家能源政策的指导。在国外,有很多种类的新能源汽车,比如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目前,我国很多专家也在讨论,纯电动汽车到底是不是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终极路线,只能说如今我们还处于尝试阶段。
(2)域外言词证据采信规则
相较于域外实物证据而言,域外言词证据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状况,因为言词证据与表达主体息息相关。根据证言三角形理论,“证言可信性涉及四种品质: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诚实性、叙述能力”[20]。这四种品质都并非外在的可观察的内容,也无法通过其他外部证明手段来对证人的这些品质进行证明,因此通常来讲,这四种品质都不能通过简单的公证认证等手续得以证明。与此同时,根据提供言词证据的主体不同,域外言词证据采信所关注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对此,本文将主要聚焦于对两种言词证据采信规则的简要探讨,即域外普通证人证言与域外专家证人证言。
① 本文所用“涉外”概念是广义的,即,不仅包括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所界定之“涉外民事案件”中的“涉外”概念,而且涵盖了纠纷之诉讼处理所可能涉及的其他一切域外要素。
与普通证人不同,所谓“专家证人”,是指“因其知识、技术、经验、所受训练或教育而具有专家资格的证人”[21]。专家证言的运用在英美法国家比较频繁,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这一证据形式及其运用也已经开始出现⑮。《证据规定》第六十一条就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而在诸如知识产权案件中,专家证人制度已经进入实践试验阶段。就此而言,在有些涉外案件中,域外专家证言必然就成为当事人收集的重点对象。
长期以来,有关我国域外取证制度的研究被局限于国际私法的学科视野之下,这不仅导致研究视野出现了盲点,而且使得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无法获得理论支撑。与此同时,作为取证制度的一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应对域外取证制度作出基本规定。就此而言,从民事诉讼法视角研究域外取证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从民事诉讼法视角研究域外取证,并不意味着国际私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无足轻重。相反,国际私法层面的研究以及我国与其他国家所缔结的相关条约、公约,对于建构科学、合理的域外取证制度至关重要。民事诉讼法学对于域外取证问题的研究应当从前述资源中汲取智识材料。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更为强调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在我国法院所进行之诉讼活动中的域外取证行为进行规制,因为这种取证本质上服务于我国的司法活动。尤其在相关条约、公约未曾建立的情况下,如果民事诉讼法不对此作出基本规定,那么相应的域外取证将无法可依。
五、结 语
然而,我们必须理解,一方面,由于科学原理或专业知识并非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对专家证人的采信应当保持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专家证人也是平常人,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诚实性也会出现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判断专家证言可信性时,既要重点审查其专家资质,又要对其诚信与否进行审慎判断。尤其对于专家的资质问题,当事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线索进行说明,事实认定者应当综合当事人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对专家证言的可信性作出合理判断。
政社共建。各级团组织通过自身的组织优势和相应工作职能,搭建孵化平台,扶持社会志愿服务团队,不断探寻合理有效对接方式,充实和扩大了“希望来吧”的志愿服务力量。“什么才是流动儿童的真实需求?”有着十余年志愿服务经历的南京市云谷山庄社区“希望来吧”负责人马连平开设“四点半课堂”和类型丰富的兴趣课程,供孩子们自由选择。
以上述基本理念为指导,本文比较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代表性政治实体在域外取证问题上的法律规定,进而认为我国应当注意吸收这两种基本模式的优点,既要将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作为基本取证路径之一进行规制,又要注重强化人民法院基于司法协助途径所进行的域外取证。我国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本身实际上兼具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之要素,因此在基础性制度层面并不存在障碍。进而,本文分别探讨了我国域外取证程序规范和评价规范的建构。正如上文所述,程序规范和评价规范是一体两面的,二者共同构筑了我国民商事案件中域外取证制度的整体样态。尤其是对于域外证据的评价,学界通常认为这已经不属于取证制度的研究范围。但当我们将域外取证作为一套系统性机制来看待时,有关域外证据的评价规范对于取证便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域外取证制度的研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当注重其系统性。
总体而言,事实问题取决于证据,所有问题都取决于事实,域外取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关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对域外取证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建构,既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具体要求和审判中心主义的应然之义。
注释:
普通证人,是指对案件事实具有亲身感知的证人。按照直接言辞原则,这类证人应当在法庭上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在这种情况下,意见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等便能形成对证人作证的控制。一般而言,在通过信息技术域外远程作证的情况下,对普通域外证人可信性的审查判断可以采用与域内证人相同的采信规则。有关普通证人证言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书面证言的采信上。由于无法就相关证言内容向域外证人作及时、有效的询问,且很难在庭外对此作进一步核实,因此,书面域外证言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本文认为,在采信书面域外证言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以佐证该证言的真实性,或者事实认定者应能从当事人所提供的其他证据中印证该域外证人之证言。当然,对基于司法协助而获取的域外书面证言也可以参照适用这种采信规则。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我们可以认为在外国公权力机关主持或监督下所获取的域外书面证据通常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② 在美国理论界,有关证据开示规则与《海牙取证公约》的关系存在两种主要观点,即选择说和礼让说。前者将海牙证据公约视为实施域外证据开示的途径之一,后者则认为应当尽可能适用海牙证据公约来获得证据,唯有在公约不能适用时,才适用本国的证据开示规则。很显然,在实践中,《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发挥着主要作用。有关上述关系的争论,可参见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470页。
③ “在美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若要公正有效地解决讼争,就必须赋予当事人以法定权力,使其能够不受阻碍地获得所有与解决讼争相关的信息。”参见刘力主编:《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立法研究:管辖权与司法协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页。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国家对各层次人才需求的增加,民办院校已逐渐被学生和家长所接受,同时,人们对民办院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民办院校的发展,硬件设施方面已逐渐完善,但在教师教学能力及专业水平上还有待加强。在大多数民办院校中,大学数学课程是各类专业的基础课,是学生取得良好发展的基石,数学学科对民办院校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此外,民办院校的教师流动性大,数学学科以青年教师居多。因此,要不断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实践水平,从而提升民办院校数学学科的整体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④ 1206 号文件文本,参见 COUNCIL REGULATION(EC)No.1206/2001 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rts of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载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1年 27卷第 6 期,第 1-24页。
标准必要专利适用禁令救济时过错的认定............................................................................................祝建军 03.46
⑤ 需要注意的是,丹麦在签署《欧盟条约》时明确表示不参加司法合作方面的事项,因此1206 号文件对丹麦不具有效力。但是《海牙取证公约》仍然在丹麦和欧盟中的签约国之间发生效力。有关1206 号文件制定根据及其意义的简要说明可参见肖永平主编:《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2页。
⑥ 对司法效益的概念与价值剖析,参见江必新:《良善司法的制度逻辑与理性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137页。
⑦ 参见[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转引自李永军:《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⑧ 这种争议不仅局限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2014年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解释实际上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改进,比如限定:“严重”情况下才将相关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且就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前置性问题都是存在极大争议的。张立平教授就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不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参见张立平:《中国民事诉讼不宜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 期,第227-242页。
⑨ 《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即公益诉讼案件);(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当然,这五种情形可能会与域外证据重叠,但单纯因证据是域外证据,人民法院并不能依职权启动调查取证。
课题组参照相关文献[2,3]自行设计并编制“毕业生就业心态调查问卷”,经预调查修改完善后用于现场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毕业生个人基本信息、工作落实状况、自我认知状况、职业探索状况、决策行动状况共5个维度20个条目。调查人员由该院各专业分管就业工作的辅导员组成,问卷统一发放、集中填写。在学生填写问卷前,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现场说明问卷填写的方式和注意事项,并适当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在已填写问卷中随机抽取5.00%的人群进行抽检复查,一致率达92.00%以上。
⑩ 有关“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界一般将研究视野拓宽到侦查等程序中,也即着重关注证据收集的过程。相较之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似乎比较薄弱,认为民事诉讼就是从审判环节开始的,因而不存在审判中心之说,即便存在,也是将庭审作为中心,进而研究立案受理等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以及庭审机制本身的改革。对此,典型研究可参见杨俊一主编:《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127页。对此,本文认为,应当对民事诉讼语境下的“审判中心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和改革。如何引导当事人科学、有效取证(包括域外取证),正是民事诉讼中审判中心主义议题的研究要点。
⑪ 甚至有学者主张,将“审判人员采信当事人提供的域外证据没有经过公证或相关部门的认证”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条件之一。虽然其用的是“采信”这个概念,但其用法中包含了“采纳”之内涵。参见徐汉明、蔡虹:《中国民事法律监督程序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 216-218页。
⑫ 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实践,而且与各国公证制度的性质相关。“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具有准司法功能,公证文书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法定证据效力;而英美法系的公证文书一般仅对文书上签名、盖章的真实性负责,而不对文书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具备法定证据效力,故经过公证认证之证据也不能保证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参见孙建国编著:《知识产权司法前沿2010》,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版,第 69页。
⑬ 有学者就明确指出,“要求域外证据必须履行证明手续对确定其真实性其实并无多大的益处,该条规定似乎成为法官简化审核认定域外证据的工具,并形成一种依赖”。参见许俊强:《民事诉讼域外证据证明制度之检讨——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为中心》,载《2008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国际法)论文集》,第440页。
⑭ 实际上,在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相关回复函以及《商标评审规则》等法律文件中,相关部门已经对此作出了调整。但这些调整尚未真正上升为法律规定的层面。
⑮ 有学者指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有共性,两者对于‘专家’的范围界定都没有严格的限制,都是只要具有与案件争议事实有关的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都可以归入‘专家’的范围之内”。参见王继福:《民事科技证据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版,第 86页。
参考文献:
[1]张保生.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J].法学研究,2008(2):126.
[2]乔雄兵.《海牙取证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分析[J].政法论丛,2010(4):86-87.
[3]American Bar Association.Obtain Discovery Abroad:2nd[M].ABA Publishing,2005:1.
[4]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40.
[5]刘力.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立法研究:管辖权与司法协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237.
[6]龚群.罗尔斯政治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05-306.
[7]刘懿彤,周紫薇.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对国际私法的影响[M]//赵秉志.京师法律评论:第10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158.
[8]李浩.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J].法学研究,2006(3):52.
[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33.
[10]杜万华,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逐条适用解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55.
[11]奚玮.民事当事人证明权保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91.
[12]何家弘.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J].法学研究,2011(3):146.
[13]James Bradley Thayer.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98:530.
[14]罗纳德·J·艾伦.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J].证据科学,2010(3):378.
[15]左卫民.中国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240.
[1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课题组.域外证据的证明手续[M]//蒋志培.知识产权民事审判证据实务.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52.
[17]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诉讼实务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395.
[18]尹伟民,于政文.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M]//民法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7-48.
[19]张旭.证据法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53.
[20]张保生.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35.
[21]廖永安.马萨诸塞州证据规则指南[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133.
A Study of Obtaining Evidence from Abroad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Procedure Law
CAO Jia1,PU Chang2
(1.Institute of Evidence Law and Forensic Science,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2.Civil,Commerical and Economic Law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Abstract: With th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foreign-related cases,obtaining evidence from abroad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ssue.It is essentially part of the system of evidence collection in civil lawsuits and China’s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make basic provisions for this.Generall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basic models.The former fully implements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adversary system,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authority principle.With reference to these two basic models,China should combine the strengths of the two.While requiring that the litigant should obtain evidence from abroad,the court must also do so through ways of judicial assistance.When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obtaining evidence from abroad,it is necessary to proceed from both procedural and evaluative norms.They are the two sides of a coin and they both contribute to the entire system。
Key words: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obtaining evidence from abroad;procedural norms;evaluative norms;civil procedure law
中图分类号: D997.3;D925.1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9)03-0024-10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3.003
收稿日期: 2018-05-1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民商事域外证据规则比较研究”(2016KFKT10);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域外证据分类及采信标准研究”(2016KFKT11)
作者简介: 曹 佳,男,江苏泰兴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生,美国西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普 畅,女,云南石屏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刘伊念
(Email:lynsy@jhun.edu.cn)
标签:民商事案件论文; 域外取证论文; 程序规范论文; 评价规范论文; 民事诉讼法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