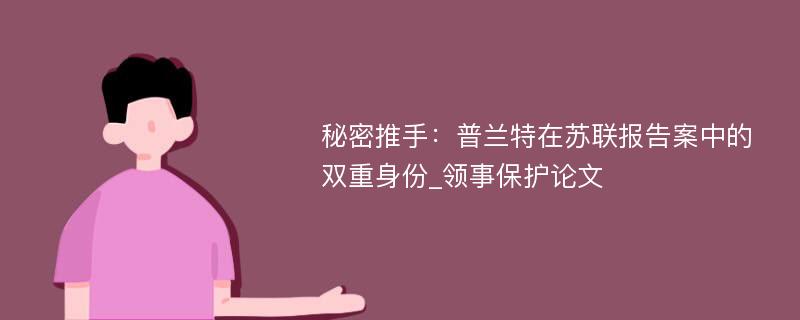
隐秘的推手:濮兰德在苏报案中的双重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秘论文,身份论文,濮兰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03年的上海苏报案是晚清政治史和新闻史上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苏报案研究已有60年历史,作为热点之一的相关人物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中方人员,包括《苏报》革命者和报馆相关人员以及负责查办案件的清朝官吏。”[1]然而,清政府在苏报案的中外交涉中始终处于下风,列强才是决定案件走向的一方。“苏报案的终了表面上是清朝政府与在华列强外交妥协的产物,但其实质是在华列强彼此博弈的结果。[2]对于在案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列强一方的人员,目前尚无具体研究。濮兰德(J.O.P.Bland)是当时上海公租界工部局总办、英国《泰晤士报》驻沪记者。本文将探讨濮如何以总办身份直接干涉案件从而被清朝官员评价为“侵权最辣”、及如何以“上海煽动案”系列报道在客观上主导了该事件中外舆论潮的史实,从而揭示他在苏报案中以双重身份扮演的一个表面隐秘实则重要的角色。 二、苏报案发生时的工部局与濮兰德 由1899年英美租界扩界后而成的公共租界,是一个独立于清朝管理权的自治区域,其最高管理机构是工部局。工部局由9人董事会领导,每届董事任期一年,每年换届,也可连选连任。“由于董事会的董事及其所属委员会的委员均为名誉职,各董事及委员都有自己的事业需要经营,所以工部局的日常事务概由该局聘用的有薪人员办理,工部局的最高有薪人员为主持该局日常总体事务的总办。”[3] 濮兰德于1883年来华,先进入中国海关,1896年开始在工部局任职。根据工部局会议记录,濮在局内初为帮办,后升为代理总办,1897年12月开始任总办,全面主管局内日常事务。1903年苏报案发生时,濮在总办任上已逾六年,而同期的董事人员则更换频繁。以1903年至1905年为例,共有17人入选董事会,9人只当选一次,超过半数,6人两年连任,仅有两人三年连任。这几年的总董人选也屡屡变动,1902年为泼兰的斯,1903年初为金尼,后金尼自愿请辞,换为贝恩,1904年和1905年为安徒生。董事的非专职性和流动性决定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统管日常事务的总办。董事会每周例会都留有会议记录,包括出席与缺席人员,董事总是不全,总办濮兰德却几乎逢会必到。 三、濮兰德对苏报案的干涉 (一)拖延逮捕行动,为革命人士提供逃匿时间。 1903年5月,《苏报》馆延请章士钊为主笔,开始走革命路线,并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6月21日,清廷外务部致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要求将举行集会要求清廷拒俄抗法的爱国革命人士“严密查拿,随时惩办”,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序,尤肆无忌惮”,两江总督魏光焘指示上海道袁树勋,点名要求将两人“密拿”。[4]领事团在与袁树勋达成案犯被捕后在租界审讯、租界惩办的协议后,同意逮捕《苏报》相关诸人。因《苏报》馆在公租界,具体抓捕行动由工部局负责。捕人时,工部局巡捕房并不积极,不但场面滑稽,还故意为当事者提供足够的逃匿时间。 6月29日上午,巡捕拿着写有陈范、陈梦坡(即陈范)、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等七人(实为六人)的拘票来到报馆,先到账房,一见程吉甫便问:“你是程吉甫么?”回答说是的,于是抓到了程吉甫。下午,又有巡捕来问:“陈范在么?”陈范自己说不在,巡捕也就走了。至6月30日晚,先后抓到章炳麟、陈范之子陈仲彝及钱宝仁。[5] 工部局先逮捕账房先生及执行公务时的敷衍了事,目的显然是要给其他当事者传递警觉信号。从29日上午到30日晚,陈范逃走,章太炎却能逃而不逃。章入狱后通过书简或口信招龙积之与邹容投案,邹当时也已逃走了,藏匿于虹口一传教士家中,邹后来是主动投案。工部局巡捕房在抓捕革命者时的“怠工”,实乃濮兰德一贯的作风。苏报案发生前,濮传讯革命人士时也只是走形式: 据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故就余所知,捕房传讯,凡有六次,好像两次在五月前,四次在五月后。传去者,有蔡孑民、宗仰、徐敬吾、章太炎及我。我则被传四次:第一次与宗仰、敬吾,第二次与孑民,第三次与太炎,皆至四马路老巡捕房。第四次已在五月二十后,传余一人,至老巡捕房后面三间两厢房石库门内(今已翻为大石厦),见余者,即英国中国通濮兰德是也。每次所问之话,大略相同。终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果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我们回说没有军火,即点头而别。”[6] 濮袒护改革人士早有前科。戊戌变法时,他便以工部局总办身份出面安排康有为从重庆轮改搭英国轮船公司的“琶理瑞”号前往香港。[7]此次工部局巡捕房捉人,很明显执行的是濮的策略。 (二)反对封闭《苏报》馆,在最终封馆行动中故行拖延。 在逮捕《苏报》馆诸人时,租界会审公廨的中方谳员还同时签发了一份要求封闭报馆的文件,对此工部局董事会的意见是:“在审讯并判决前不准执行,即使执行也应由工部局巡捕负责。”[8]《苏报》由此得以继续发行,其反满言论引起了清政府的进一步干涉。7月5日,湖广总督端方向张之洞建议由外务部出面与在京公使商洽:“此事仅恃沪道办理,力量较薄,非由外务部商诸公使主持。”[9]紧接着7月6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也建议将此事上升一个外交等级:“交涉之事,领事无不秉命各公使”。[10]清廷并没有马上回应端、魏二人的建议,但此后封闭报馆时工部局的再次拖延使其不得不开启最高层面的干涉模式。当时驻沪领事团已经同意封馆,封馆命令在7月6日下午由会审公廨送至工部局,但警务处没有马上执行。报馆是在7月7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才被封闭的。警务处的慢动作使“会审公堂谳员知道道台会对这样的推迟执行命令感到愤慨,于是命令会审公堂当天停止办公。”《字林西报》刊登的批评文章还认为警务处是无故拖延,使“工部局与本地官厅之间引起了不和”,文章很不赞成这么做,“凡是深切关心租界安宁的人都竭力反对董事会采取任何会与本地官厅、领事团或中国官方的一方或二方发生不和的举动”,而“近来董事会方面似乎有一些对抗领事团之倾向,在反对中国官方时采取自己的一套做法”。[11]对此工部局给出的解释是:警务处执行命令时,发现报馆所处为一英国侨民所占有,对方声称持有地产所有权而拒绝警官进入,警官请示总巡后才实际封闭报馆。[12] 不管工部局的解释是真是假,可以确定的是在封馆行动中警务处依然走的是濮式拖延路线。濮兰德的拖字诀,将清廷“逼”上了端方和魏光焘前所建议的由中央政府出面斡旋之路。7月9日,外务部侍郎联芳以庆亲王奕劻名义拜访代理英国驻华公使焘讷里,恳请他就交出苏报案犯一事从中调停,北京公使团开始介入案件。 (三)致函使领团,表明工部局立场;与领事会面,间接向清政府施压。 后续交涉的结果表明,清政府请京使出力的路走得并不顺畅,公使团迟迟不能达成统一意见,使案件陷入长时间的停滞。就是否应该将苏报案诸人移交给清政府,公使团历经了三个多月的商讨,多数意见由最初的“同意移交”变为“反对移交”。7月底,俄、法领衔支持清政府的要求,获得公使团多数公使附议,只有英、日尚在犹豫。之后发生的两个事件对公使团的决议变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7月31日沈荩未经审讯惨遭慈禧下令杖毙促使英国政府最终做出反对移交的决定。二是在沈荩案的影响与英国的积极斡旋下法、比倒戈,支持移交的俄法联盟瓦解,反对移交的列强成为大多数。然而,不管公使团如何协商,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苏报案案犯始终掌握在工部局手中,而工部局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移交案犯。公使团作出最终决定前,工部局曾三次致函使领团干预此事。[13]信件与同时间濮兰德报道的对比显示,虽然信函以总董名义发出,但总办濮兰德对它们的内容是十分熟悉的。 7月23日信函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苏报案,工部局敬请外交团注意以下事实:在过去的很多年,本地的管理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的原则,即未经审讯并证明有罪,本地居民不能够被逮捕或被带离租界,租界的持续繁荣和安全依靠的是对这条原则的坚守。去年外交团支持这个观点,在6月28日正式表示同意,据此这个原则明确地建立起来。 其次,在本案中,领袖领事签字是基于与中国官方达成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协议,逮捕被告以在租界审讯,如证明有罪,在租界执行为前提。工部局斗胆建议,应告知清政府,以往公认的建立的程序应该坚持。 最后,工部局建议外交团应该告知清政府,为了防止将来煽动性言论在租界出版,外交团、领事团以及工部局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使对本地报纸的监控成为本地立法的主题,考虑依据《土地章程》第34条附则发给它们执照,这个办法无疑会消除未来出现麻烦的可能性。 签名:Bayne 工部局主席 Council Room 上海,1903年7月23日[14] 7月25日,工部局又致电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表示“工部局的意见是应该防止顺从清政府的要求”,并再次建议“立即就此立法可阻止苏报案这样事件的发生。”[15] 两封信主要表达三点内容:一、未经审讯并证明有罪,本地居民不能够被逮捕或被带离租界,这是公使团已承认的原则。二、领袖领事批捕是以与道台达成的协议为前提的,应尊重这一协议。三、应通过立法给本地报纸发放执照,加强监管。两封信在9月3日见于《字林西报》,在此之前,具体内容外人应无从知晓。而濮兰德在7月21日和7月28日所发报道涵盖了两封信所述这三点。 7月21日濮在电报中提到: 苏报案出现新情况。会审公廨审判进程无限期等待,因为问题成为外交问题,要由北京解决。南京总督魏光焘指责上海道台和领事团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将案犯移交给省级政府处理,领事团正在等待北京公使的决定。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北京公使同意了这样一条原则:不经会审公廨审判在租界内不得逮捕和送交本地人。外国人群体认为恪守这个原则是第一位的。[16] 这篇报道比23日函还早两天写成,于21日发稿、23日刊出,强调了未经审讯不得将人从租界带离的原则,这正是23日函的第一点。7月28日报道的篇幅较短:“关于苏报案一事,工部局向外交团发去一封电文,建议就租界内报刊控制和牌照化进行立法,电文还要求中国政府人道对待苏报案案犯,承认此前上海道台同意的审判和处罚方式和程序。”[17]该报道于28日发稿、29日见报,虽然篇幅短,但言简意赅地披露了工部局致信外交团的内幕,内容涉及23日函的第二、三点与25日函。通过21日和28日的报道,濮不露声色地将工部局的两封信函公之于众。 10月,在公使团达成拒绝移交意见并通知清政府后,工部局在10月28日的董事会上决定致信领事团,该信大约在11月初向领事团发出,《字林西报》在11月19日刊登。信件内容如下: 自从苏报案犯被逮捕并被指控出版煽动性文章等,至今四个月已经过去了,领事通知工部局说已经尽力再三正式请求会审公廨或者继续指控程序,或者将案犯释放,但毫无结果。对他们关而不审的惩罚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如果还继续拖延,工部局建议,不管审讯的时间什么时候定下来,被关押者在保证法庭随叫随到的条件下释放。[18] 这封信的主旨只有一个,就是指出如果不能尽早继续审讯,案犯应被释放。11月4日,濮兰德在报道中披露了这封信:“关于苏报案,工部局去函领事团,指出被告已经被关押了四个月而没有受到审判,这种状态不应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工部局建议,如果南京总督不能遵守早日委派官员听审的要求,关押者应该在保证法庭传唤时能出庭的前提下被释放。”所述与信函如出一辙。[19] 从时间上看,三篇报道在三封信发出前后,从内容上看,报道均披露了信件要点,这表明濮兰德对信函内容是十分熟知的。而濮与他的同事、《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之间的通信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佐证,至少证明11月初工部局发出的信就是濮写的。 莫理循在11月6日写给濮的信中说: 萨道义爵士今天早晨告诉我你给克莱门诺夫写信的事。他对此非常气愤,他说完全没有必要在信里指责他等等。他还说他已尽一切可能把一封令人满意的公函寄交总督,又说你根本想象不到这里对工部局有多么大的敌意,就连美国公使也只是勉强而犹豫不决地给他以非常靠不住的支持,等等。[20] 这里明确提到濮给驻沪领袖领事写信,该信下文还提到濮在发信时并没有征求萨道义和驻沪英国领事的意见。根据莫的日记,工部局在7月发出的信惹恼了公使团的公使们,法国公使尤其愤怒。[21]莫与驻京英国使团联系紧密,和代理公使焘讷里、公使萨道义经常互相拜访。萨道义私下在莫面前的抱怨,给人的感觉是濮与工部局之间几乎是划等号的,公使团对工部局的敌意和愤怒具体到个人上,就是濮兰德。由此可以看出濮写信并非仅仅是执笔者,在使团的人眼里,他是个利用工部局权力为他们制造麻烦的“刺头”。 事实上,濮的确不把领事放在眼里。驻京代理英使焘讷里最初认为苏报案犯“应该被‘引渡’”,濮曾猛烈批评他。[22]驻沪英国领事霍必澜到职时,濮“衷心感到高兴”,因为同代理领事满思礼“打交道就好像同爆炸物住在一起,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做出愚蠢透顶的事情来。”[23]尽管濮并非工部局头衔最高的人,他手中的权力却是不小。一是因为工部局董事会的流动性与非专职性决定了濮在实务中手握重权。二是租界自治的“独立性”使领事团也无可奈何。莫理循曾建议濮利用手中权利直接将犯人释放:“我说你在你们的团体里(指工部局)很有权势,应该显示出你的力量而不要把它隐藏起来;我告诉他(指萨道义),我坚决主张工部局应立即结束这场滑稽剧,先把人犯释放,过些天再通知领事团,以便使人犯能够有逃走的充裕时间,我说你已经这样做了。”[24]魏光焘在致端方的电文中说“此事阻力全在工局,其局董权势远过领事。”[25]魏对苏报案权力关系的认识只对了一半:阻力的确全在工局,“局董权势远过领事”却所言非也。对真正操纵权力的人,清政府另一名官员看得更清楚。金鼎在给梁鼎芬的电报中直言“(濮兰德)在工部局办文案多年,英政府信任之,驻沪英领事屡换人,故权反落在局董之下,而濮以多年文案,自命为总办,其权力能操纵全界,理财最糟,侵权最辣。”[26]一语道出领事、局董、总办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租界内,领事不如局董;在工部局,局董不如总办。一针见血指出了濮在苏报案中幕后弄权的实情。 濮兰德不仅给领事团写信,还亲自会见驻沪英国领事和领袖领事,通过外交使团向清政府施压。10月26日,领事团将公使团拒绝移交的决议通知清政府。11月11日,在工部局董事会上,“总办说,关于这个事件他已晋见了领袖领事,领袖领事同意如在下周二之前尚无两江总督的答复,他将代表领事团电请总督立即作出决定。”[27]领袖领事依言而行,“先是发函给总督,继而给他发了电报,要求他安排审讯。”[28]当时莫理循在报上讽刺说使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达成一致,“总督自然似乎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来考虑”。[29]然而仅约两周后,11月14日,两江总督魏江焘就表示同意在会审公廨审讯。清政府从接到列强决定到表示接受仅时隔半月余,和濮以释放犯人相要挟有重要干系。 四、濮兰德对苏报案的报道 除了工部局总办的正职,濮兰德还兼任《泰晤士报》驻沪记者,他是该报苏报案报道主力,一共发表系列报道和评论21篇,多以“上海煽动案”为题,占《泰》报苏报案发稿量近一半。濮在报道中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批评清廷保守政权,同情改革者。庚子之变后,俄国企图永久占领满洲全境,中国各地民情汹涌,爱国热情高涨。苏报案发生前,沪上绅商和学生就已多次在张园集会,谴责清廷卖国亲俄。濮从中国爱国者的角度痛批清政权:“他们对满洲三省的丧失和危及帝国的各种内忧外患无动于衷,对一小群爱国人士的活动却高度警惕。这些爱国人士的目的只不过是敦促政府进行改革、遏制满人贵族的特权。”[30]“希望英国政府不要同意移交,因为就地正法也比在中国监狱里坐牢更仁慈。”[31] 二是指出苏报案反映了清廷派系之争及列强利益之争。在濮看来,苏报案意味着保守派重新掌权及湘党与其对手的斗争。“苏报案被告成了一场游戏中的旗子,在这场游戏中保守官僚势力得到巩固,防止公众在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在北京,以张之洞为首的湘党对手正拿此事大做文章捞取资本,因为湘派的魏光焘和上海道台没能执行朝廷的谕令,将案犯处死。”[32]“南京总督在北京有敌手,如果他没能将苏报报人处死,他的敌人将会以此针对他大做文章,而他也在各个方向用钱去获取对中国引渡要求的支持。”[33] 二十世纪之交,列强掀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高潮,俄国盘踞满洲,法国固守西南,德国强霸山东,长江流域则被英国视为老牌地盘。濮认为俄法德在苏报案中与英国唱对台戏,是借此向清廷谄媚,以捞取更大政治资本、攫取更多在华利益,与英国争利。“苏报案正好给了对方一个绝佳机会来证明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并不是永固的。”[34]对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径,濮持有双重标准。他在一篇评论中认为英国和其他列强是有区别的,英国参加势力范围的划分是被动的,目的是平衡势力,而别的列强则是主动瓜分。[35]此外,他还指出如果苏报案诸人被戮,“对本地报界舆论肯定是一个重挫,改革者发表言论以后会很难。”[36]总的来说,濮的言论基本上反映的是一个支持改革运动、批评保守政权、关注列强利益争夺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形象。 苏报案引起了当时中外报纸的极大关注。在英文报中,《泰晤士报》是苏报案发稿量最多的报纸,从1903年6月事件肇端到1904年5月判决尘埃落定,期间总稿数为48篇,[37]包括自采新闻、议院消息、新闻社消息、社论。在29篇自采新闻中,濮兰德写了21篇,莫理循写了6篇,其余两篇来自《泰》报驻布鲁塞尔和巴黎记者。同时间的《纽约时报》稿量次之,各类稿件共21篇。[38]此外,《洛杉矶时报》11篇,《字林西报》11篇,《华盛顿邮报》10篇,《文汇西报》9篇,《上海泰晤士报》8篇,《中法新汇报》8篇。[39]《纽约时报》基本上将《泰》报作为主要消息源,手法包括将一段时间内《泰》的报道综合到一天中进行转述,或在内容完全引用《泰》报的情况下对标题作出改变。这两种做法都会标明消息来源于《泰》报记者。据笔者统计,《纽》报共采纳濮兰德报道9篇,占自身稿量近半。《纽约时报》尚且如此,其他英文报自不待言,造成的舆论局面是“外文报纸对苏报案的报道和评论大同小异”。[4]而英文报又成为了当时中文报的信息源。“上海《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国民日日报》、天津《大公报》、《奉天时报》、香港《华字日报》、《中国日报》等,都刊登了苏报案相关消息,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转译自英文报纸。”[41]就这样,通过英文报的二次传播和中文报的三次传播,濮兰德实际上成为了《苏报》案舆论潮的领导者。 濮的报道能被中外舆论市场接受,原因固然和当时《泰晤士报》在报界中的权威地位有关,但更重要还是在于濮对清朝保守政权的批评与对革命的支持既符合西方主流文明观,也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爱国与改革的发展趋势。庚子之乱、八国侵华之痛迫使清廷在1901年1月出台新政措施,此后几年,改革、思变、图强成为有识之士的主流共识,而清廷为维护自身利益又做出镇压改革运动、野蛮屠戮改革者等倒行逆施之举,必然遭受舆论唾弃,濮的言论自然容易赢得共鸣。在这一点上,辜鸿铭恰是濮氏反例。在沈荩案后辜鸿铭在《字林西报》发表《中国的政治犯罪和惩罚》一文,试图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为清政府的野蛮撇清罪恶,结果却是“不论中外文报纸,均无人支持”。[42] 从上述可以看出,濮兰德在苏报案中是一个厉害角色,“侵权最辣”是他,在舆论潮中居领导地位也是他,而这种厉害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报界又都是隐秘的:他并非工部局名义上的头面人物;《泰晤士报》的报道依照当时惯例并不透露记者姓名,[43]因此濮的影响并不容易被察觉。濮的双重身份是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列强对清末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租界的存在给在华外人以操纵权力的空间和可能。从新闻业的角度看,霍恩伯格评价十九世纪末是驻外记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左右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4]这主要是指驻外记者通过舆论影响取得了令当地政客忌惮的政治影响。濮兰德在苏报案中的双重身份使他比其同行们更进了一步:他不仅以言论政并掀起舆论攻势,他本人同时也是其所论之政的重要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濮兰德与苏报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记者亲历与构建中国历史事件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