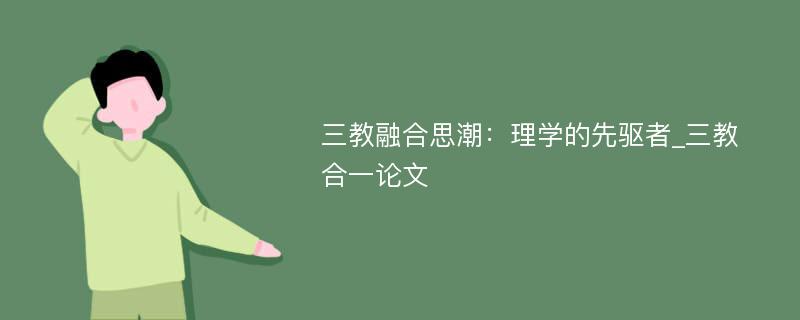
三教合一思潮——理学的先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声论文,思潮论文,理学论文,三教合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五代时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潮。这股思潮有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并为后来新儒学的振兴准备了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三教合流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
三教合流思潮的形成是与唐代经济政治的变化相联系的。唐代经历着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均田制的破环使封建国家在经济方面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统治手段。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使封建国家大一统政局被破坏,中央集权制度大大削弱。社会动乱使佛教进一步流行,动摇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举国上下争相奉佛,“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1〕。 这种状况使一些官僚士大夫深感不安。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削除藩镇,加强中央集权,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在思想上希望复兴儒学,结束三教并立局面。因为儒学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及其所宣扬的君臣原则正适合削除藩镇、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为此他们提出了意识形态统一的必要性。白居易《白氏长庆集·议释教》说:“臣闻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义无二。盖上率下以一德,则下应上无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于五帝,道释二教不及于三王。”而近世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以及当时佛教盛行的现象都不正常,三教“虽臻其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异名则殊俗,足以贰乎人心”,使政局发生混乱,“令一则理二,则乱若参”,因此要恢复“古先惟一无二之化也”。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应统一于何处,而只是模糊、笼统地求助于先王之道。这正反映了思想界的彷徨:两汉经学已经僵死,失去其正统地位,传统被否定了,意识形态的重新统一,又“一”于何处呢?
贞元、元和之际,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以古文运动为旗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个运动自唐中叶起延续到北宋,其早期代表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吸取和改造了佛老理论,不同程度地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思想发展成果,从而使儒学具有了新的特色和更深的内容。
三教合流思潮形成的思想渊源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不仅同其物质存在条件相联系,而且同其思想传统相关联。唐末五代的社会思潮,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三教合流的第一个阶段。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儒学主要表现为朴素的政论和伦理形态,其哲学所宣扬的“天命”和“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比较粗陋,缺少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这种浅薄的神学目的论是不具备发展为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内在根据的。因此儒释道的融合不仅是统治阶级实行思想统治的需要,也是儒学自身发展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玄学化和佛学的玄学化正是三教融合的产物,儒学以其入世的现实性排斥佛道的出世信仰主义,而佛道的精湛哲理克服了儒学理论的浅薄。总之,儒学只有吸取佛道理论,才可能深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儒学虽然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但是其维系和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作用始终未被统治者所忽视。儒学如一条主轴线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其它思想,如玄学、佛学虽然盛极一时,似乎取代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但实质上始终是作为儒学的辅助思想出现的,围绕着儒学这条主轴线上下波动,而不可能取代这条主轴线。
魏晋以来主要是儒道异同的争论。自然与名教关系之争的实质就是儒道异同之争。西晋流行自然与名教“将无同”之说,亦即主张同孔老庄殊途同归,东晋儒道合流趋势更为明显。稍后,东晋出现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合流,即是佛道的融合。僧肇《肇论》以道家名词概念宣扬佛教大乘性空中道观。随着佛教的逐步确立,出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以及夷夏之辨的争论,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调合三教的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与隋唐时期相比,有所不同。佛道所表现的三教调合思想虽然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但三教关系表现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同归说。三教合一未明确提出以儒教为主的会同三教,三教各自以己教为本,它教为末来会同三教。如葛洪《抱朴子·朔本》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此乃以道为本会同儒道。《高僧传·慧严传》载:“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明僧绍《正二教论》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此皆推崇佛教为本,以孔老为末者。可见,尽管儒学从未遭到佛道的正面反对,但是比起两汉儒学独尊的地位则是大大地衰落了。再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主张三教调合论者往往把三教进行一些简单的比附、对照,只是泛泛地提倡三教合一,事实上三教在理论上并未融合。
隋唐时期是三教融合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从三教鼎立的局面转向以儒学为主的三教融合;从空洞提倡三教合一,发展成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为宋代理学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隋王朝建立后,在重建的大一统政局下,曾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体、会合三教为一的要求。王通《文中子》认为政出多门对于大一统的政局不利,因此提出以儒学为中心的三教合一说。这是一种复兴儒学的尝试,但未能成功。前此的某些统治者也进行过调整统治思想的试验,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都以行政命令手段灭佛,但佛教反而大盛,正如《文中子》所说:“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可见,单纯的政治灭绝手段和统一意识形态的主观愿望,都不能代替思想发展自身的逻辑。这种现实影响到唐王朝对三教的政策。
大一统的政局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由于历史的积淀,没有形成三教统一于儒学的条件。唐初,高祖曾经打算接受傅奕废佛的建议,但遭到绝大多数朝臣反对,只得作罢。到唐太宗也只能采取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下诏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这是利用抬高道教的手段打击佛教势力。唐太宗还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统一,但是孔氏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其所撰《五经正义》只是把前人的经注疏通,使经学在诠解上达到统一,并未创出时代需要的义理经学。总之,唐初统治者种种企图调整三教关系的作法,都无法改变三教鼎立的现实。尽管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斗争需要不同,总体上各代统治者基本奉行三教并存政策。这既是对三教鼎立现实的承认,又促进了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在理论上唐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以利王朝统治。高祖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2〕太宗说:“老君垂范,义在清虚, 释迦贻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盖之风齐致。”〔3〕高宗、武后、睿宗、玄宗等人都是三教合一的鼓吹者, 有些皇帝在三教中有所偏重,武宗甚至一度灭佛,但三教并行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三教并存政策对三教关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使三教在思想理论上的融合成为必然,并且加快了三教融合的速度。
有唐一代学风深受三教融合之影响。唐朝廷继承南北朝风习,提倡同堂讲习三教。《旧唐书·儒学传上》载:高祖亲临太学释莫,“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慧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三人并展开辩论,高祖对此大为嘉奖。唐初三教论辩还比较尖锐,内容涉及到佛道先后,以及对教义的看法等等。唐中期以后,朝廷召集三教名人论辩成为一种惯例,作为皇帝生辰或其它庆典的一种例行活动,三教在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冲突。《白氏长庆集》中保留的《三教论衡》,即是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辰那天,白居易“对御三教论衡”的记录。《南部新书》说,彼时三教讲论的格式“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由此可见三教融合的发展过程。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学子士人,多对三教典籍有所研究。如玄宗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中宗自称“以万机之暇,略寻三教”〔4〕。 士大夫中三教兼修者更为普遍。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又自称“栖心释典,浪迹老庄”〔5〕。韦处厚“通五经,博览史籍”, 并“雅信释氏因果”〔6〕。裴休精通儒学,“尤深释典”。 梁肃既是古文学者,又是禅宗天台宗学者,曾就学于荆溪湛然,著有《止观统例》等。李商隐“一代文宗,时无伦辈”,以弟子礼事高僧知玄。总之,当时士大夫中很少有人不受时代氛围影响,甚至出现了韦渠牟这种迎合时风者,“初为道士,后为僧”,又进入仕途,以善讲三教为德宗宠幸〔7〕。
三教融合已成为各界人士之共识。中唐名僧神清认为儒释道三教“各运当时之器,相资为美”〔8〕。宗密《原人论》认为:“孔、老、 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没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儒家学者柳宗元、刘禹锡都主张融合三教,认为佛教是儒学的一种必要补充。柳宗元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9〕。刘禹锡认为儒佛“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众,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儒佛不同的妙用对于维系封建统治的功效是一致的,张彦远《三祖大师碑阴记》说:“夫禀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释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三教融合说至五代仍很流行,南唐中主李璟认为:“菩提之教,与政通焉。”〔10〕《十国春秋》引五代黄滔《丈六金身碑文》说:“帝王之道理世也,释迦之教化人也。理世与化人,盖殊路而同归。”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原因以及思想发展的逻辑要求,儒释道相互渗透、融合乃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的时代思潮。
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与渗透
中唐以来三教融合不仅停留在简单的比附、对照,而开始在理论上互相渗透、融合,在唐末五代形成一股三教合一的思潮,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教关系主要指佛教和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教融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及其中国化,一是儒道对佛教的借鉴吸收,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化。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深受儒道等中国文化的影响,日益中国化、世俗化。唐代佛教向中国文化靠拢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通过吸取儒道思想而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禅宗是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典型,它深受道家自然主义以及魏晋玄学“得意忘言”理论的影响,认为一切语言文字都是阻止人们把握认识真实本体的障碍,提倡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禅宗在道家自然主义影响下,主张“平常心即道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悟道成佛,即“砍柴担水,无非妙道”。这无疑降低了佛教出世性质,使之进一步世俗化。儒学的影响使佛教更深刻地世俗化。在儒家名教影响下,佛教出现了专门讲孝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宣扬应报父母养育之恩,还出现了以孝道著称的僧人,如僧浚、元暠、浚上人等。怀海《百丈清规》是以忠孝为思想内容、以家族为组织形式的禅律,堪与儒家礼法相比。佛性论亦深受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论影响,晋宋之际的竺道生提倡“一阐提”也能成佛,唐代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也都主张人人能够成佛。中国佛教不仅从人、心方面讲佛性,还从境、理方面讲佛性。“境”指主体认识对象,亦即事物的本性,亦称为“理”。人们如果把握了理,也就获得其理,体现为法身,也就成为佛。这种理论把佛性与儒家仁政理想结合起来,使佛教神学日益以超脱变为世俗。这种佛儒结合思想在士大夫中甚为流行,姚崇反对过多营造寺庙,扰乱百姓,认为“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11〕。这种说法不仅把佛教世俗化,也把儒家政治伦理哲理化、神学化,使之不再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硬性规定,而是被上升为“理”,即宇宙规律,本体存在。宋代理学于此可窥其端倪了。
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在给予佛教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从佛教中吸收本身所缺乏的万分,使自身日益丰富。许多道教经典都是直接在佛教经典影响下形成的,如《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经》源于《法华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源于《涅槃经》,《太玄真一本际经》源于《般若经》。佛性论也影响了道性论的形成,即主张修心,把追求长生的物质手段变为心理的体验,把追求肉体长生变为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儒学也从佛教中吸收了自身所缺乏的哲理因素,使儒学重建成为可能。与佛老相比儒学相当忽视理论思维,这种缺陷使佛老思想有了发展余地。儒学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不能满足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超脱政治、遁世在野者的需要,佛老思想却能够补此不足。因此,士大夫在思想上几乎都存在二重性,即在政治上尊崇儒学,排拒佛老,而在个人情趣上无不出入佛老。如白居易在《论释教》中表达排拒佛老的政治抱负,而其自为墓志铭又称:“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刘禹锡《送僧远皓东游行》也说明其奉佛原因:“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柳宗元《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亦说:“佛之道,大而能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可见佛教不但能够满足士大夫的多重需要,而且于维护封建秩序也有儒学不及之功效。因此,儒学复兴说必须吸收佛教思想。
韩愈、柳宗元和李翱是儒学复兴运动早期的三个代表人物。韩愈从封建国家的国计军防出发,陈言佛道弊害,企图建立新儒学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佛道,《原道》、《原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其理论。为反对佛老,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他认为孟轲死后,儒家道位不得其传,暗示到他本人才得以重新接上。他认为佛老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佛教又用夷变夏,不合乎中国历史传统,应予排除。他希望恢复儒术独尊的局面,反对儒学与其它学说交流融合,也不承认两汉经学的正统地位,其道统上承三代周孔。韩愈反对佛老振兴名教,符合统一意识形态的时代需要。从长远发展看,韩愈起了某种承接汉代儒学与宋代理学的作用。但是韩愈反对佛老有很大局限性,他无视当时三教鼎立的现实,盲目地排斥佛老,不符合三教合流的发展趋势。
柳宗元在本质上是一位儒家学者,但是他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像韩愈那样盲目、简单地排斥佛老。他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儒学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必须善于吸收佛老的思维成果,这样才可能真正复兴儒学。他破除排斥百家唯儒独尊的偏狭态度,发扬以儒学为主,兼取众长的求实学风。他虽然主张“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12〕,但是他还主张“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认为诸家之书“皆有以佐世”,而应“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在孔子之道的基础上“通而同之”。柳宗元对于佛教也采取这种态度。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提出“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的主张,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称赞元十八山人善于统合儒释:“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踬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申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韩愈见此,责柳宗元“不斥浮图”,柳氏在《送僧浩初序》中回答了韩愈的责问。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他批评韩愈狭隘的治学态度,盲目排斥佛教等外来文化:“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他认为韩愈不能采取佛教的合理内核以丰富儒学。韩、柳在政治上尊儒的主张并无大分歧,而在思想理论上,柳宗元较之韩愈更为自觉,更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李翱在理论上对儒释进行了融合的尝试,其《复性书》三篇可以说是援佛释儒的代表作,体现了儒学在表面上排斥佛老,却又从哲理上吸收融合佛老的实质。《复性书》所用语言据儒家经典《中庸》。《中庸》一书集中讲性与情,李翱企图以此对抗佛教的佛性理论。宋人欧阳修尝谓,始读《复性书》,以为《中庸》之义疏而已。但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复性书》正是以儒家的语句,讲佛教的佛性论。李翱认为,人性本善,由于被情所昏蔽,才使人性败坏,产生恶,所以要复性。他所谓“性”,即相当于佛教的“佛性”或“本心”,所谓“情”即相当于佛教的“无明”“妄念”等。按佛教说法,众生本心都是净明圆觉的,只因为无明所遮蔽才不能显露,所以必须去无明才能恢复其净明圆觉的本心。《复性书》体现了儒释在理论上的融合,其特点就是在反佛的旗号下,暗用佛教的佛性理论,建立起新儒学去人欲复天理的人性理论。由上述可见,韩愈、柳宗元和李翱是唐代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做了总结,为宋代理学的到来做了思想准备,其说虽然较为幼稚肤浅,但宋代理学却渊源于此。
唐末五代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是宋代理学形成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两宋是三教融合的第三阶段,儒释道在理论上进一步融合,形成宋代理学,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宋代理学的形成,结束了三教鼎立的局面,理学虽然吸取佛道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修养方法,但是佛道对儒学却表现为公开的依附和屈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进行精神控制的有效工具。
注释:
〔1〕《资治通鉴》,唐代宗大楞二年。
〔2〕《册府元龟·帝王部》。
〔3〕《大正藏·集古今佛道论衡》。
〔4〕《佛祖统纪》。
〔5〕《旧唐书·白居易传》。
〔6〕《旧唐书·韦处厚传》。
〔7〕《旧唐书·韦渠牟传》。
〔8〕《北山录》
〔9〕《送僧浩初序》。
〔10〕冯延己:《开元禅完碑记》。
〔11〕《旧唐书·姚崇传》。
〔12〕《报表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标签:三教合一论文; 儒家论文; 韩愈论文; 国学论文; 理学论文; 柳宗元论文; 读书论文; 宋代理学论文; 儒道论文; 中庸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