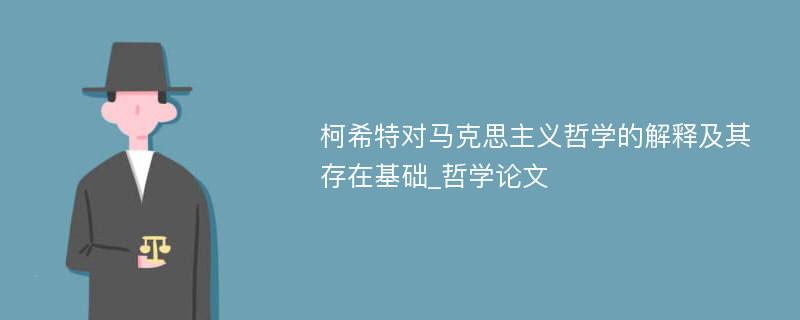
柯尔施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及其存在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柯尔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与卢卡奇、葛兰西的立场颇为一致,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激烈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的宿命论和机械论倾向;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哲学之间最关紧要的历史联系,并通过这种历史联系来揭示和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前提”。柯尔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首先是与人们遗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相联系的。他指证说,在一般的学院中,马克思主义仅只被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从而实际上被排除在正统的哲学史之外而不予考虑;或者就像朗格那样,仅仅把马克思描述为“现存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史专家”,而完全忽视其哲学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看上去“最正统地依照导师指示行事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虽则出于与学院教授们完全不同的理由,却同样地轻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方面”,并且同样以散宕随便的方式去对待黑格尔哲学乃至全部哲学。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对“哲学”的否定态度中,力图使马克思主义被实证主义地知性科学化;而这种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直接意味着从根基上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质或革命性质,并从而使之沦落为“庸俗马克思主义”。
因此,柯尔施把矛头直指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所谓正统观点,亦即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试图在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方面”的同时,诉诸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的本质重要性或决定意义,诉诸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直接衔接,并以此来拒斥费尔巴哈在基础阐释中的优先地位。柯尔施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指出:那种十足的费尔巴哈式的方法在于,把全部意识形态表象归结为它们的物质的和世界的核心;但若满足于这一点,则这种方法就是抽象的和非辩证法的。更加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方法是抽象的和非辩证法的,所以真正说来,它还完全是“非唯物主义的”和“非科学的”——在马克思所确定的原则立场上是非唯物主义的和非科学的。在这里,柯尔施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立场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使之对立于“抽象的唯物主义”方法,而后者正是“费尔巴哈式的”并在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突出表现的基本立场。
那么,在柯尔施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明显地表现出其“完全是非唯物主义的”性质或方向呢?回答是:它特别地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先验的蔑视”,对国家和政治行动的“先验的蔑视”。这种“先验的蔑视”,简单地说来,就是在全部社会现实中,实质上取消意识形态、国家和政治行动的真正现实性,而把本质的现实性仅仅置放在所谓经济生活的领域中。这样一来,精神现象或全部意识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就只是在一种“纯粹否定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被想像和规定,国家和政治行动的本质重要性也实际上被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活动及其意义应当仅仅被限制在直接的经济范围之内。如果说,这种抽象的、机械论性质的“经济决定论”可以被看成是唯物主义的话,那么,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这里,全部意识现象的现实性完全被取消了,因而也根本谈不上意识现象与经济现象的辩证关系,谈不上解决经济问题所必须凭借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柯尔施看来,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恢复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现实”的观念,恢复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的现实性。
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庸俗化的理论根源又何在呢?柯尔施的回答是:它来自于二元论,来自于全然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正是由于把全部意识现象和作为实在过程的经济运动形而上学地劈分开来,并完全以一种二元论的方式来加以对待,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机械的宿命论,并相应地导致对政治行动和意识形态的“先验的蔑视”。当经济运动和意识现象被形而上学地分割开来并以“二元论方式”来对待时,前者就变成了惟一客观的和非观念性的现实,而后者则变成了空想或幻相意义上的“伪现实”。于是后者便被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并完全依赖于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认为后者是“相对独立的”,事情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它最终“仍然是依赖的”,谈不上二者之间真正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运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二元论并非一般意义上与哲学一元论相对峙的东西,毋宁说,它倒是属于现代哲学之基本前提或建制背景上的东西——大体上属于迄至黑格尔哲学(即现代辩证法)以前的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无论如何,正是这一根本之点深刻地形成了马克思(以及黑格尔)同庸俗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对立。前者立足于意识与现实的一致,即意识和现实的辩证法,而后者则立足于意识与现实之关系的本质上的二元论。
柯尔施把这种二元论看成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深处的要害。应当承认,柯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大体说来乃是有效的和切近的,特别是对本质上的二元论的揭示,是颇为深刻的;而且他还敏锐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庸俗马克思主义恰恰在哲学上是前黑格尔性质的,约言之,退到了黑格尔以前。
二
然而,柯尔施及其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究竟在哪样一个基地上、取哪样一种立脚点来瓦解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并来克服这种形而上学关于意识与现实关系的二元论呢?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柯尔施本人的基本哲学立场,而且关乎他对马克思哲学之根本的阐释基础与定向,关乎他对第二国际“正统”行使批判的理由、有效程度,以及这一批判可能开展出来的深度和广度。而当这个问题以其全部尖锐性呈现出来时,我们将不得不见到这样一种情形:柯尔施的基地或立脚点在一方面是明晰的和确凿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模糊的和暧昧的。这前一个方面乃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共同的一端,即辩证法;后一个方面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存在论基础上与黑格尔的原则差别。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当柯尔施把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归结为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又把这种实证主义科学在哲学上的要害归结为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时,他已经把这种二元论的真正克服或扬弃理解为辩证法,亦即理解为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共同的辩证法了。“因为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1](P47)柯尔施特别强调,无论是现代社会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还是现代社会之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都坚执意识和其对象之间的二元论(在二者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唯独辩证法——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黑格尔的——方始真正越出了这条分界线并且把握住了二者的真正一致。不仅如此,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是唯赖意识和现实的辩证一致方始成为可能的:“把任何哲学的考虑放在一边,就会明白,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是必然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不再是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不到这种现实和意识相一致的辩证概念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它必定在理论上是虚假的和非科学的。”[1](P47~48)
如果说上述的第一个方面是明晰而且确凿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面,即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真正说来却是颇为含混的。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有两个明显的区别。其第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对前者来说,一切意识,不再超越于并对立于世界(自然的和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意识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之真实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而黑格尔虽然认为个人的理论意识不能跳过他自己的时代和他的世界,但黑格尔“不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更多地是把世界嵌入哲学之中”。[1](P50~51)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更多地”嵌入或“更少地”嵌入,而在于这种“嵌入”的可能性前提或基础本身。但柯尔施还根本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个前提或基础本身,或者毋宁说,它本身还是未经澄明的。这使柯尔施不得不面临如下的严峻问题:如果说“把哲学嵌入世界”是合法的,那么这必然意味着“世界”要大于“哲学”,“现实”或“意识的对象”要大于“意识”。这样一来,不仅将从前提上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立即成为不可能,而且在哲学与世界之间、意识与现实之间立即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差额”或“余数”——这个“差额”或“余数”显然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并且正因为它是一个“差额”或“余数”,所以无论它多大或多小,它总是一个“不一致”的领域,因而也是一个辩证法所通不过的区域,而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二元论的恢复。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第二个区别”事实上就在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按照柯尔施的见解,辩证法之由黑格尔的“神秘形式”向马克思的“合理形式”的转变,实质上意味着它成为“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亦即那种“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这里的核心之点,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理论批判活动和实践变革活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辩证统一中,如果整个现存社会的全部真实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毋宁说,它们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本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但是,如果柯尔施仅仅诉诸于哲学和世界、理论和实践在此种联系中的统一,他还未必一定能得出上述的推论来,因为反过来的推论也是可能的,即:如果整个现存社会的全部真实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物质生产关系也不能仅仅通过“客观-实践”被推翻,而必须使之同时在思想和意识上加以消灭。为了要得出前一个推论,不仅要承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且还得承认“实践”作为物质活动在存在论上的优先性,亦即把意识现象的本质性彻底地导回到物质实践中去。但是这样一来,柯尔施关于“精神现实”的提法就变得难以成立了,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这使得柯尔施再度面临这样的困难(这个困难类似于他在谈到马克思和黑格尔之第一个区别时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且特别地在于这种统一由以建立起来的存在论前提或基础本身,而这样的前提或基础本身恰恰又是柯尔施未曾真正地深究过的。我们曾经看到,正是由于这方面的薄弱,所以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等同于费尔巴哈的“生活”、“实践”时,[1](P776~777)卢卡奇却对马克思的实践原则作出了费希特主义的理解。[3](P12~13)这种根基上的晦暗同样使柯尔施的说法不免含混和模糊:一方面,他颇为隐晦地承认实践的优先地位,称其为“客观-实践”,而把意识现象主要地领会为“形式”,亦即物质关系的形式方面或形式规定;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使得精神的现实性得以成立和保持,他又在“精神现实”的概念中要求把全部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现实”,认为“它们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非常客观的和非常实际的’社会现实”。[1](P53)
三
以上两个方面的彼此对峙,在柯尔施那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的意思是说,并没有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得到根本的澄清与克服。当他把全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理解为社会现实时,他主张它们的现实性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必须以实践的和客观的方式来消灭”。但这样一种主张是内在矛盾的:如果意识现象本身是一种足够强大的社会现实,那么,它何以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必须借重于实践的和客观的方式呢?如果说它毕竟还不具备物质实践的客观性,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本质性难道不就应当归诸作为物质实践的客观领域吗?甚至可以更简单地这样设问:既然意识形态与意识形式也就是社会现实,那么从意识出发和从物质实践出发还有什么区别呢?柯尔施无法真正避开这样的矛盾,他只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在这种情况下,柯尔施在诉诸马克思的时候实际上仍然是在诉诸黑格尔,所以他在谈论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时立即引证了黑格尔的下述说法:“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人一方面是思维,另一方面是意志,他一个口袋装着思维,另一个口袋装着意志,因为这是一种不实在的想法。”[1](P52)
柯尔施当然不愿意维持以二元论为基调的机械决定论,所以他诉诸辩证法,试图以统一的方式把对立的两端——意识与现实、哲学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综合地结合起来。在这里,辩证统一的综合要求确实是重要地出现了。它要求使得在形而上学二元论建制中设定并持存的相反的方面能够彼此渗透、彼此生成,能够有机地和生动活泼地彼此建立起来并开展出来。按照柯尔施的观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正应当在这样一种视域中得到理解和把握,而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恰恰在于全然抹煞了这个唯赖辩证法才得以开启的视域。但是,就我们在这里如此这般地谈论的辩证领域——其核心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难道不是已经在黑格尔那里得到决定性的阐述了么?于是,柯尔施费力地想要指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区别。但是,当他试图以某种肯定的方式来标识辩证法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根本差别时,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证的那样,主要由于在存在论基础上未曾获得真正深入的进展,他却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之中。
柯尔施为了打击庸俗马克思主义而诉诸辩证法,这一打击是正当的、有效的和意义重大的;但柯尔施为了保全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必须指证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本质区别,然而这一指证却是含糊的、歧义的和力有未逮的。关于后一点的一个主要证据就是柯尔施陷入了上述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的出现乃从属于柯尔施对马克思哲学的实际阐释,意味着柯尔施未能真正地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那个意义至为深刻的“颠倒”。这里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内容包括:(1)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主要是意识的内在性)的贯穿与瓦解;[4](2)从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路向及其全部天真性中解脱出来;[5](P119~127)(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践纲领的真正奠基并从而彻底终止“理论态度”。无论如何,它意味着一场全面的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存在论根基上做起并且可以说是这一根基之彻底地改弦更张。然而,这场革命的深刻内容及意义,从根本上来说终究还是落在了柯尔施的视野之外。他未能看到,正是由于这一存在论基础的革命,不仅使得黑格尔辩证法所建立起来的统一被决定性地标识为虚假的统一,而且使得其哲学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而被归结为最高的和最后的形而上学。柯尔施在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时所遭遇到的矛盾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但为了使得这种矛盾不致引起整个阐释体系的自行瓦解,他在辩证法这个主题上就不得不——也许违背他本人的初始意愿,但从其实质来说——最终倒向黑格尔。这一“倒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柯尔施所面临的矛盾,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样是从其实质来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获得了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定向。
标签:哲学论文; 存在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二元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