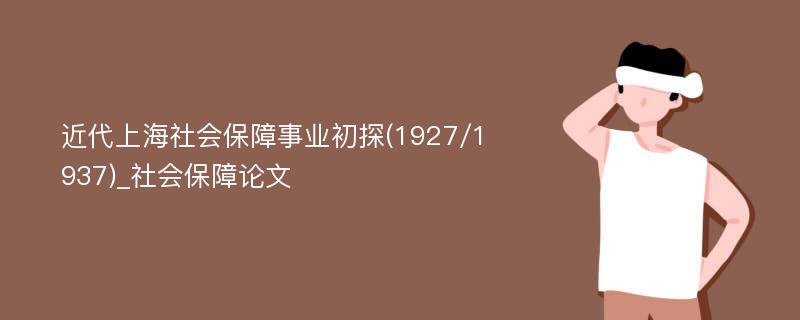
近代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初探(1927-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社会保障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上海发展的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造成这一稳定繁荣局面的因素或许有多种,但具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在其中所提供的稳定与保障功能显然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人们对上海史在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颇多,而对于社会稳定机制却鲜有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1927-1937年间上海社会保障事业作一初步探讨,一方面对上海史整体研究作一些补充,另一方面拟为今天城市社会保障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近代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进程
现代社会保障事业发端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之下。考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充分的地方,莫过于“我国第一通商巨埠”的上海。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通商,一时“船舶麇集,车马如织,工厂众多,商务之繁盛,均非他埠所能及”(注:《申报》,1923年7月2日。)。日臻发达的工商业,一方面为近代上海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日趋动荡。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社会安全机制,现代社会保障的产生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逻辑要求。
作为一项强制性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的建立与运作,必须在统一国家体系之内、以国家立法为依据、以政府行政为手段,方能得以进行。而上海被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统一行政体系之内,应始自1927年上海特别市的建立。(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同时期的租界当局——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也是近代上海市政格局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不能不提及租界。但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明显体现帝国主义殖民性的租界当局,没有也不可能将其注意力放在对其界内社会贫困成员的关怀上,尽管在治安、防务、税收、市政建设等其它行政权限方面,租界当局寸步不让,管权必争,但对于需要政府一定财力、人力投入的对社会贫困成员的救助事业,租界当局通常总是借辞推诿。无论从两租界的机构设置、经费支出、制度法规等来看都不曾经常性开展面向社会贫困人员的保障活动的任何明确迹象。但在另一方面,租界行政机构内部职员却享受着较高程度的福利保障,不过,作为一个单位的内部福利,其各项保障措施并不具备“社会”的意义,所以讨论以政府为保障主体、以立法为保障依据、以社会弱势成员为保障对象、以国家责任为保障理念的社会保障,本文将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所组织举办的事业为主。)
根据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十二次会议决议,上海被定为中华民国特别市。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新政府建立之初,便从制度上、组织上着手准备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制度安排,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在“几无成例可援”的探索中艰难起步,至30年代中期便初具雏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包含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为便于叙述起见,本文将十年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大体分成三个阶段加以考察。
(一)组织建设与法规实施时期(1927-1931)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社会保障事业由市府下属二级机构公益局和农工商局分别执掌。公益局主要负责救济及预防市民贫困、灾害,监督慈善机关,改良市民生计以及其它有关社会公益事项;农工商局则主要掌理劳动行政。1927年9月,公益、农工商两局合并。1928年8月1日,农工商局改组为社会局,这是近代上海实施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政府机构。
在设置社会保障专门机构的同时,市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作为社会保障实施的法律依据。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于1927年8月拟具《上海特别市劳资调节暂行条例》,对雇员的待遇及相关保障均作了基本规定。1927年10月,市政府颁行了《上海特别市政府公益局监督慈善机关暂行条例》,稍后,又制定《上海特别市公益团体注册暂行规则》(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Q113-4-5。),这些法规通过对慈善机关、团体实行监督、管理,来参与、干预社会救济事业,并最终试图将长期以来一直由民间举办的救济事业纳入政府管理体制之中。
1928年11月和12月,上海特别市先后颁布了《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和《上海特别市职工待遇暂行规则》(注: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特别市市政法规汇编二集》。)两部地方性法规。在这两部法规中,对在职雇员的工作时间、工伤津贴与补助、女工生育津贴以及职工储蓄保险和退职雇员的退职条件与退职金的给予,都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可以说,以这两部法规的出台为标志,近代上海以政府为组织主体的社会保障的现代性开始得以体现。
社会局的建立与一系列相关法规的颁行,事实上形成了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上海社会保障事业的组织与制度基础。
(二)战后艰难重建时期(1932-1934)
1932年一·二八事变对处于起步中的上海社会保障事业无疑构成了巨大冲击。据社会局的统计,一·二八事变后,“失业工人骤增,现失业工人二十四万余名,工资损失一千万余元。”(注:《申报》,1932年7月17日。)劳资纠纷案件急剧增加,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先前制定的社会保障法规权威性在战争冲击下显然受到动摇,对雇主与雇员之间权力义务的调整和规范功能有所削弱,如三友实业社、双宫丝厂、英商公共汽车等资方纷纷借机裁人或变相降低工人福利待遇,法律权威直接受到冲击。当然,在战后极其孱弱的社会实际情况下,政府亦不得不主动降低社会保障的规范功能。如为贯彻劳动保障政策而进行的工厂检查,迫于形势,社会局亦主动降低检查标准和要求,“如将《工厂法》全部实施,恐多滞碍,特将初期范围酌量减小,……各厂惨经战乱,处境不无困难,故经饬员于执行检查时注意厂方实际情形,审慎从事,以恤商艰。”(注:《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25期,1932年10月10日,第124页。)
一·二八事变对社会局所创设的旨在帮助贫民谋生的贫民借本事业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二八事变突起,市郊各借本处皆受战事影响,事业无从进行,而闸北之第二贫民借本处尤为战事冲要之区,……借户逃避一空。截至五月八日为止,所有贷出款项本息银九千三百六十六元四角四分,完全到期,无法收回;”(注:《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21期,1932年6月10日,第88页。)“战区各处,借户星散,十室九空,欲复旧观,颇难着手。”(注:《申报》,1932年6月5日。)
一·二八事变对社会保障实施的直接影响是财税收入的锐减。应该说,自1927年以来,上海市财政“经悉心整顿,……逐年兴革,稍有成效,市政设施,得以按步进行”,但至“二十年度,适值一·二八沪战发生,税收锐减,而临时救济之费用大增,迨二十一年度,地方元气未复,税收仍受影响”。(注:民国廿四年《上海市年鉴》上册,中华书局,1936年,J3页。)一·二八事变以前,财政收入每年大约以一百万元的速度递增,而1932年度财税收入增幅明显下跌;收入锐减的同时,支出却因战后重建而增加,1932年度的财政赤字为历年最高,入不敷出竟达150余万元(注:《上海市年鉴》1936年,J3页。),上海市财政状况之窘迫,于此可见一斑。社会局于1932年7月在给市府的呈文中,不得不承认:“一·二八之役创巨痛深,尤非短期间可复元气。本局职责所在,目击心伤”。(注:《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25期,1932年10月10日,第125页。)就现有资料分析,1932年之后,上海市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几乎再无大的举措。无论从制度、组织,乃至于具体业务等方面,几乎均未能突破此前既有的保障水平。一直到3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方始有所改观。
(三)再度中兴时期(1935-1937)
为全面实施社会建设、引导全民参与起见,上海市政府将1935年定为“社会建设年”(注:民国廿四年《上海市年鉴》上册,中华书局,1936年,B115页。)。这一举措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政府开始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改善视作政府的当然责任。1935年初,上海市政府设立了两个委员会: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和识字教育委员会。前者准备大规模地建筑平民住宅三千间,希望使上海三十万住草棚的贫民,能部分地解决住的问题;同时由政府制造相当数量的黄包车,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低微的价格租于黄包车夫,最后实现“拉者有其车”。后者准备设立民众学校三百所,希望使上海文盲全部扫除,并规定实行强制劳工识字教育,要求适龄劳工都要接受相当程度的文化教育。(注:健民:《对本市社会建设年的展望》,《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4号,1935年3月25日,第1页。)
标志30年代中后期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再度中兴的另一举措是1935年开始进行的识字运动。1935年,教育、社会两局一方面动员全体社会成员积极参与识字教育运动,另一方面,由社会局出面专门组织实施强迫劳工识字教育,并制定了《劳工识字教育实施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各厂场公司商店等设立劳工识字学校之经费由各该厂场公司商店等自行负担”,对于逾期未遵办理者,除“处以一百元以下罚金外,并令其限期办理”(注:《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72期,1936年9月10日,第120页。)。应该说,这种强制性的劳工识字教育在当时社会经济十分不景气的情况下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5年至1937年间,上海市政府还先后举办了儿童福利、督促实施劳工储蓄与保险、举办劳动托儿所和婴孩寄托室等多项社会事业。这样,一个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日渐成熟。
二、十年上海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
1927至1937年间,上海社会保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一个多级层次、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保障网络体系。从低级保障层次的社会救济到体现社会保障现代性的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较高层次的社会福利,基本涵盖了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主要方面。
(一)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与社会向由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组成的社会成员提供旨在维持其最低生存需求的救助活动。在社会保障诸子系统中,社会救济是最低层次的保障行为。
根据救济活动性质的不同,1927-1937年间上海社会救济事业,举其大端,可以分为公益慈善救济、失业工人救济和借本扶贫事业等三个方面内容。下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上海近代特殊的市政格局,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近代中国连年不断的人祸天灾,又给慈善事业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舞台。自清末以来,“沪上善堂林立,……凡恤嫠、赡老、施棺、舍药、栖流、救生,以及孤幼、残疾,无不有养”(注:王韬:《瀛壖杂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页。),据社会局统计,至1935年,全市各类慈善机构多达177个,(注:民国廿四年《上海市年鉴》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页T134。)其事业包括施衣、施米、施粥、收容、施医、施药、育婴、恤嫠、掩埋、助殓等多方面内容。
从现有资料看,当时每年所举办的冬令庇寒收容或施粥等善举,规模颇为壮观,收容庇寒所往往开办数日,收容人数便逾数千,有时竟致“后至者无插足地”(注:《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56期,1935年5月10月。),除冬令庇寒收容、施粥施衣外,各慈善组织还积极举办了其它经常性救济,如夏令施医种痘、收养妇孺、残废,教化游民、施棺助殓等多种形式的善举。在这些活动中,社会局依法对其实施监督、管理。应该说,慈善组织在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救济事业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一些由民间慈善组织难以单独举办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必须要求政府来出面组织实施。如二、三十年代的贫民借本事业便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社会救济事业中较为成功的一例。
近代上海,游民丛生,他们或行乞于闾里,或滋事于街头,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1929年初,社会局曾对1400余游民进行问话调查,“深以若得贷以些许资本,贩物取利,或不难化游惰为生利,当以市内无贫民借本机关,遂拟以市府先行试办,”(注:《申报》,1929年4月12日。)因于1929年4月正式创办上海特别市贫民借本处,该处隶属于社会局。因市库支绌,初期借本业务的开展只能分期分区办理,第一期先后于南市、闸北两地指定区域分别设立第一、第二贫民借本处。两贫民借本处后经数次扩充,借本范围不断扩大。稍后不久,市社会局又于各平民住所附设借本处。1931年,为“取缔侨沪印人在租界重利盘剥”(注:《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第81期,1931年1月20日,第25页。),社会局决定在租界设立特区贫民借本处。这样,一张覆盖全市的贫民小额借贷网络基本形成。后几经调整,社会局所办贫民借本业务不断扩大。到1935年,贫民借本已在高桥、高行、洋泾、陆行、塘桥、杨思、蒲淞、彭浦、真如、江湾、吴淞、殷行、引翔等十三地设立分处。(注:《申报》,1935年8月30日。)应该说,这种以向贫民借本助其营生为主要内容的扶贫救济措施,为部分地解决贫民生计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针对一般贫民的扶贫救济外,上海市政当局还曾专门举办了各种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活动。
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是二、三十年代上海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上海特别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救济失业为当今急不容缓之要务”(注:《申报》,1928年10月5日。)。自市府成立之初,便命农工商局草拟失业职工救济计划。为堵住工人失业的源头,避免雇主任意解雇职工,农工商局于1928年初发布布告,声称进退职工应有限定日期,并规定“阴历正月初二日资方得依营业状况,决定进退工友”(注:《申报》,1928年1月11日。)。尽管这种办法事实上无法执行,但此举至少表明政府已将失业救济办法置于其考虑之中。1928年社会局成立后,即着手举办失业职工登记,并会同市总商会、区商会、闸北商会、商民协会、工整会等几大团体共同设立失业职工介绍所(注:《申报》,1928年8月23日。),以谋失业职工救济。一二八事变后,大批工人因战争而失业,1932年3月23日由上海市社会局、公安局联合市商会等各团体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战区失业工人救济会,并规定凡失业工人请求救济者须事先来会登记,由该会逐日分业统计,依次设法为其介绍工作。(注:《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20期,1932年5月10日,第28、86页。)自5月4日开始登记,至11日止,短短7天共有16911失业工人前来登记。(注:《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21期,1932年6月10日,第72页。)因资料所限,现暂无法确知社会局究竟解决了多少失业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但从其筹办职业介绍与失业登记的举措来看,政府一直在着力筹谋失业工人再就业办法。
(二)社会保险
所谓社会保险(注:社会保险有区别于商业保险,后者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前者则更多地关注社会效益。),是指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的生活保障制度,它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采取的是受益者与雇用单位等共同供款和强制实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的安定。(注: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页。)
上海特别市成立后,著农工商局掌劳动行政。1928年,农工商局在其1-7月劳动行政计划书中,明确将实施劳动保险列为其工作计划之一部。1929年11月31日、12月8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先后公布了《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和《上海特别市职工待遇暂行规则》。在《上海特别市职工待遇暂行规则》中,对关于雇主应对雇员在工伤、疾病、死亡、生育等方面所负的责任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职工因公受伤或致病,确有实据者,雇主负担其医药费。在医治期间三个月内不得解雇并照给工资;前条伤病治愈后,视其残废程度,分别给与赡养费”,“职工因公死亡时,雇主应给与五十元以上之丧葬费,并给与工资两年以上之遗族抚恤金”,“雇主对于女工之产前产后就应共给假六星期,工资照给。(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特别市市政法规汇编二集》,1929年,第173-174页。)”这种事前预防性保障措施,实质上是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保险责任全在雇主一方。对于年老退休,《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也作了具体规定,“凡服务继续三年以上,年满六十岁之职员、年满五十岁之劳工,身体衰弱,不堪工作,而被解雇或自行告退时,雇主须给与退职金,其金额以该职工最后一月所得之工资,按照其服务年数计算,满一年者给一月,余类推”,“职工确系直接因公残废而被解雇时,雇主除照前项发给退职金外,须再酌给赡养费。(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特别市市政法规汇编二集》,1929年,第171页。)”这两部法规奠定了近代上海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能够真正体现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形式,是由农工商局首倡的职工储蓄保险。1928年该局要求“各工厂附设工友储蓄部”,职工可以“将每月所得工资扣出一小部分,使其储存生息。日储另星,持之以恒,日久不难汇成巨数,可备疾病、失业之预防,可作年老养息之绸缪”(注:《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业务报告》1928年,第28页。)。事先以一部分投资作失业、疾病、年老之预防,这正是工业化社会中实施社会保险的要旨所在。随后组建的社会局,亦曾拟具鼓励各工厂设立工友储蓄部办法,截止1928年底,办理职工储蓄的单位至少有英美烟草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商务印书馆和南洋烟草公司等(注:《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业务报告》1928年,第193页。)。此后,社会局将饬令各厂场公司商店举办职工储蓄作为经常性工作。1932年对工人储蓄实行强制办法,规定“劳资双方各出工资5%,设立储备会之事务,责成工厂担任”(注:《申报》,1932年10月27日。)。社会局实施的这种以职工储蓄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保险至少在形式上在很大范围内得以推行,这从现有的档案资料中可以得到反映。上海市档案馆目前馆藏有1933、1934年度上海市各工厂、公司、商店的职工待遇规则,如中华铁工厂、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一心牙刷厂、梁新记牙刷厂、家庭牙刷厂、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Q6-18-248,Q6-18-250。)等单位,对职工储蓄保险,都作了不同形式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在督促各厂场公司商店办理职工储蓄保险的同时,市府各部门也曾制定各自职员储蓄保险办法,如1929年9月市公安局(注:《申报》,1929年9月11日。)、1930年市公用局(注:上海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78期,1931年1月10日,第33页。)、市社会局(注:上海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80期,1931年1月31日,第49页。)、1934年市工务局(注:上海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46期,1934年7月10日。)等都曾先后组织办理了不同形式的职员储蓄保险。
(三)社会福利
如果说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的目的是解决和预防社会成员生存问题的话,那么社会福利则是力图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社会保障系统中较高层次的保障内容。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但市府仍着手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方面的措施,诸如消费合作事业、职工教育、儿童福利、平民住宅、贫妇保产及育婴等多种福利事业。
消费合作通常是由政府提倡并予以支持的惠民事业。1928年市社会局成立后,即颁行了《上海特别市消费合作社暂行通则》(注:《申报》,1928年10月1日。),1931年又对此通则进行了修正。所谓消费合作社,1931年1月8日公布的《修正上海市消费合作社暂行通则》作了明确界定,“凡以平等互助精神,集合资金,用最经济方法,供给人生需要品,以图改良社会生活状况及实现公平普利之经济制度而组织之社团,为消费合作社”,其运作方法是由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市民七人以上发起,每位社员各认股若干,集资筹办消费合作社,商品仅以极低价售于本社社员,以省却中间商人的剥削。其宗旨,除经济上惠利社会成员外,“并应增加社员精神上福利之设施”。市府虽没有直接拨款筹设消费合作社,但通过允许“消费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及所得税”的形式,来体现政府对此项事业的支持。(注:上海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78期,1931年1月10日,第40页。)为规范和进一步扩大消费合作事业,社会局曾举办合作人员养成所,并于1930年2月举行合作运动宣传周,“以期引起大众之注意。(注:《申报》,1930年2月。)”客观地说,这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作消费方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自社会局积极提倡以来,殊有蓬勃之气象,而一般市民亦渐明了合作社之意义,能自动组织者颇不乏人。(注:《上海市合作事业最近实施概况》,《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4号,1935年3月25日,第49页。)”
职工教育也是二、三十年代上海市社会福利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政府筹办的早期职工教育,应数上海特别市教育局设立的职工补习学校。1927年12月,市教育局为普及店员、工友教育起见,在本市设立五所职工补习学校,其中四校专收男生,一校专收女生,“期于工作之暇,补充店员工友以知识技能。(注:《申报》,1927年12月8日。)”在农工商局以及后来的社会局业务报告中,每年都将实施职工教育列为其年度工作计划之一。1933年底,上海市社会、教育两局联合颁布了《上海市劳工教育实行细则》,细则规定,本市各厂场公司商店等雇用职工在50人以上者,应该设立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满50人时,可将职工送往市私立劳工学校或其它学校附设劳工班学习。细则同时规定,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收学费及其它费用,所有书籍、文具等,一概由劳工学校、劳工班或原设立机关供给。(注:《申报》,1934年1月13日。)1935年为进一步推行劳工识字教育,社会局制定了《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实施办法》,该法及稍后于1936年8月修正的《修正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实施办法》为实施劳工识字教育的法律依据。本次劳工识字教育为强迫性质,凡“本市区域内(四十五岁以下)不识字之工人一律受识字教育,……如至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后仍未受识字教育者,应即日勒令停止工作”(注: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市年鉴》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O43页。)。修正后的办法规定,实施强迫劳工识字教育以一年为期,自1935年7月1日至1936年6月30日,后又展期一年,自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办法同时规定,对无故不参加入学的工人和逾期不设立学校的厂场公司商店,均作相应处罚。这种以立法强制性的劳工教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上海产业工人的文化水平,改善了工人队伍的文化素质结构。
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儿童福利事业的推进,应以1933年为标志。是年3月,上海各界联合组织上海市各界庆祝儿童节大会筹备委员会时,公安、社会、教育、卫生四局行政人员及一般热心社会事业者“鉴于儿童运动之重要”,决议组织成立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为主持儿童事业、促进儿童幸福之总机关”,(注: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市年鉴》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B145页。)市长吴铁城任该委员会会长,市政要人潘公展、李廷安、陈鹤琴、胡叔异、刘王立明等被选举担任常务委员。这是领导上海儿童福利事业建设的主要机构,该机构下设儿童保障部、儿童健康部、儿童研究部和儿童事业部,并附设劳动托儿所、儿童图书馆和儿童电影院等。
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成立以后,开展了一系列儿童福利事业,其中将儿童福利事业推向高潮的是1934年“儿童年”的规定(全国儿童年为1935年)。儿童幸福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提议定1934年为儿童年,“以资宣传,并谋儿童幸福事业之更大进展”。(注: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市年鉴》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B145页。)
二、三十年代上海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平民住宅、平民村的建设。1928年,市府第十九次市政会议上,市长张岳军鉴于本市“工人及一般平民,多搭盖草棚居住,偏促其中,上无以蔽风雨,下无以去污湿”,乃提议建筑平民住屋,廉价出租,“俾一般人民得以安居其中”,(注:《申报》,1928年10月18日。)并组织成立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1929年10月,市政府颁布了《上海特别市平民住所管理规则》,对平民住所建设宗旨、平民住所的日常管理作了具体规定。(注:《上海特别市市政法规汇编二集》,1929年。)截至1931年8月,已有三处平民住所先后落成。第一平民住所在全家庵路,1929年5月造毕,共有住房100间;第二平民住所在斜土路,落成于1930年10月,计造住房420间;第三平民住所在交通路,1931年8月造就,计有住房290间,(注:《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22期,1932年5月30日,第191页。)这些住宅均以极低廉的价格租于一般平民居住,对于一些极贫住户因房租难以月清,社会局曾订立分期缴租办法,以示体恤。(注:《申报》,1932年9月17日。)1935年,市府筹拔100万元,作为建筑平民新村经费。至年底,共有860间平民住宅先后在其美路、中山路、大木桥路和普善路竣工落成。(注:《申报》,1935年12月7日。)根据1935年12月26日公布的《上海市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平民村居住规则》规定,凡本市现有一定职业,全家月收入在40元以下者,均可向各该平民村主任申请租住。(注:《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64期,1936年1月10日,第130页。)此后,政府继续推进平民住宅建设。1936、1937年社会局曾计划建设公共食堂、调查工人住房并筹建职工福利住宅等,(注:上海档案馆档案,卷宗号:Q6-18-134,第25-41页,第65-69页。)但遗憾的是,不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使这些计划都付之东流。
除上述提到的办得较有成绩的各项社会福利外,上海市政府还在此十年间实施了其它诸如贫妇保产育婴、女工生育补贴、劳动安全与卫生、职工给假、最低工资、工人俱乐部等多项福利举措,限于篇幅,本文不拟一一详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所享受到的各项社会福利政策,早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便已有很大程度的实现了,尽管其实施范围小、保障水平低,但相对于传统社会里官办或民间组织的慈善事业,这毕竟更具现代性了。
三、十年间上海社会保障事业的成效
1927年之后的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年历程。十年上海社会保障具体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本文试从下述两个方面对其作一些探讨。
(一)成效考察之一
上海特别市成立以后,市政府着手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对慈善事业的监督与管理、平民住宅的建造、贫民借本的实施、督促企业、工会组织兴办储蓄保险、职工教育等等。这些措施的具体实现情况怎样呢?笔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统计,于此略作说明。
社会救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各类慈善事业的举办。慈善事业的具体实施情况,因资料的匮乏,现已无法对其作一个完整的十年统计,但通过对若干年份资料的分析,大体能窥其在上海城市社会建设中所具有的作用之一二。如1927年度,上海各慈善组织向贫民共施发衣物31466件,除去小部分发往外地,这数万件衣物对于贫民御寒过冬自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年,各团体共施给米粮6023石,(注:上海市政府秘书处《市政统计概要》1928年,据第74页资料计算。)如果按每人每月0.14石计,这些米粮约能维持43000余人过完一个严冬。无论对社会贫困成员的生存维持,抑或对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个数字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小浜正子对1928年末至1929年初上海慈善事业的研究也证明了类似的结果。1928年阴历年底约两个月内,上海各慈善团体向贫民无偿施发米粮约2750石,据其计算,2个月内这些米粮可以供一万人维持生存。(注:葛涛:《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和国家〉介绍》,《史林》2001年第1期。)
社会局所举办的另一项较有成效的救济措施是始于1929年4月的贫民借本事业。中途尽管一度受战争影响,这种旨在扶助贫民经营谋生的借本事业仍取得了一些成绩。借本机构的不断增加、借本区域的数次扩张、借本资金的持续投入,是借本事业取得了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好例证。据资料显示,1929年贫民借本处借贷户数为2450户,借出本银37837元;1930年批准借本户数4565户,借出本银68735元,比上年度增加82%(注:《上海市政府市政公报》,第106期,1931年10月30日,第32页。)。再看一组数据。1930年上海市在建造平民村的同时,又在各平民住所附设了平民住所借本处,专门借款与“平民住所之居民”。从1930至1935年这六年间,三个平民住所借本处累计放借小额借款6701人次。(注:据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统计》1933年编,第16页;《上海市统计补充材料》1934年编,第97页;《上海市统计第二次补充材料》1936年编,第138页等资料计算。)而这六年中,三处平民住所年平均住户人数为3968人次(注:据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统计》1933年编,第16页;《上海市统计补充材料》1934年编,第97页;《上海市统计第二次补充材料》1936年编,第138页等资料计算。)。照此计算,住于平民住所的居民每人约有1.7次借款的机会,它至少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数千名居住于平民村的居民每人都至少一次以上地受到政府所实施的这种扶贫借款的救助,这对于一般贫困市民寻找再就业机会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再看社会保险方面的具体成效。社会局所实施的关于劳动保险方面的大部分举措,明显具有强制性。从1928年 《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上海特别市职工待遇暂行规则》至稍后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对各类企业所应组织的劳动保险都作了立法强制性规定。前文曾谈到自1932年前后,上海市众多企业都将实施职工工伤津贴、疾病津贴、女工生育津贴、残废及老年津贴和部分地实行雇主雇员双重责任的储蓄保险明确列入其职工待遇规章之中,(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Q6-18-248,Q6-18-250。)这至少在制度上体现了政府所实施的劳动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推行。社会局曾于1934年7月对全市各工厂、工会在劳动保险方面所办的事业作过一次调查,其中实施疾病津贴的有89家,解雇津贴有9家,年老津贴有4家,残废津贴34家,保险处有38家,死亡津贴有65家,储蓄处58家,女工生育津贴有11家。(注: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报告》,1935年,第72页。)
在社会福利方面,应该说,成绩是明显的。就政府为解决贫困市民的住房问题而从事的平民住宅建设而言,从1929年第一处平民住所兴建以来,这项事业在解决城市贫民的居住问题上,长期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具体例证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第一、第二和第三平民住所每年都能解决约四千左右平民的住房问题(注:综合上海市地方协会1933年编《上海市统计》第16页、1934年编《上海市统计补充材料》,第97页、1936年编《上海市第二次统计材料》第138页等文献资料中有关数据测算。)。从1930年至1935年这6年间,仅此三处平民住所就解决了不少于24000余人次的住房问题。在现有三处平民住所的基础上,1935年上海市又添建了四处平民新村。是年年底竣工住宅计达860余间,至少在1936年初该四处新村就已有600余户入住,(注:民国廿四年《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6年,B156页。)按每户3-4口算,四村共计解决了不少于2000左右市民的住房问题。相对于数十万上海贫困人口,这二万余人的数目委实有如沧海之一粟,但相对于昔日政府根本无此项设施而言,这毕竟是一大进步。再则,每年有数千人免于流浪或窝居草棚之苦,对于近代上海的社会秩序而言,显然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
始于1935年的职工识字教育措施的全面实施,也是上海市政当局所实施的一项较有成效的福利举措。1935年以后直至抗战爆发,政府先后不惜用强制性的办法来要求各企业单位实施强迫劳工识字教育。正是通过这种立法强制,短短年余时间里,劳工识字教育明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笔者曾对1936年8月至12月这5个月之内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情况粗作统计,短短五个月内,新增劳工识字学校122所,开办338个识字班,入学劳工人数达4456人;同时,应届毕业劳工人数2742人,其中考试及格准予毕业者2071人,占应届毕业人数的76%(注:根据《上海市政公报》第176期至180期有关资料汇总统计。)。应该说,在提高劳工的文化程度,改善其生活质量方面,上海市政府的社会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成效考察之二
1927-1937年间上海社会保障事业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工人的就业,以尽可能地减小社会失业率。这方面的成效怎样呢?笔者曾对1936年出版的《上海市年鉴》中一组数据进行整理、计算,结果发现,从1930年至1935年这六年期间,工人就业率呈明显上升,而同期社会无业人员的比例则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30年工人人数占全上海总人口的19.1%(注:此数仅为华界人数,租界尚不在内。),193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9.6%。在此后的几年中,工人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保持缓慢增长,直到1935年这个比例增加到22.1%。六年中净增3个百分点;而同期社会无业人员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930年的18.2%持续下降到1935年的15.8%,其跌落幅度与工人比例的增幅大体相当。(注:据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6年,C26-27页中有关资料计算。)
上述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或许由于多种原因所致,但社会保障在关于劳动者就业保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显然是促成此种情况发生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一个能说明社会保障在减缓近代上海社会异动程度的例子是较长一个时期内上海劳资冲突的明显趋缓。事实上,无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或是仅就近代上海而言,社会保障的实施初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化解劳资冲突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的考虑。从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上海市所颁行的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来看,其背后实质上体现了政府在雇主应对雇员所负的责任以及雇员在多大空间内享有政府所规定的权利方面所作出的限定。这种限定实质上反映了政府急于缓解劳资冲突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实现状况可以从30年代劳资纠纷案件发生情况中进行分析。笔者对1928-1936这9年期间的劳资纠纷作过一次整理统计。见下表:
1928-1936年上海劳资纠纷情况统计表
纠纷案件总数 关系厂号数 关系职工人数
1928 237 3477 121983
1929 338 4237 56946
1930 339 2017 118317
1931 324 616 131713
1932 253 1452 55822
1933 301 721 94923
1934 233 891 35919
1935 221 402 47418
1936 187 335 32984
资料来源:1928-1932年数据系根据《上海市年鉴》1936年,O30页,1933-1936年数据系根据《近四年来上海的劳资纠纷》,载《劳工月刊》第2卷第11-12号,第10页中有关资料整理。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9年期间,上海劳资纠纷案件呈明显下降趋势,发生劳资纠纷的范围也急剧减小。就关系厂号数而言,从1928、1929年的3477家、4237家,锐减到1936年的335家;涉及职工人数也从1928年的121983人急剧下降到1936年的32984人。劳资纠纷的减小幅度是明显的。此外,在这9年期间的劳资纠纷案件中,围绕工资、工作时间、雇用或解雇条件及其他待遇方面的纠纷数也大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下表:
表十五 1928-1936年间上海劳资间因待遇问题发生纠纷数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75291315
264210
285
225
241
181
资料来源:同上表。
通过上述对工人就业情况、社会无业状况以及劳资双方的冲突原因所作的量化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27-1937年间上海社会的异动程度明显趋于缓和,这其中原因或许有多种,但社会保障在其中所具有的减震与缓冲作用应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