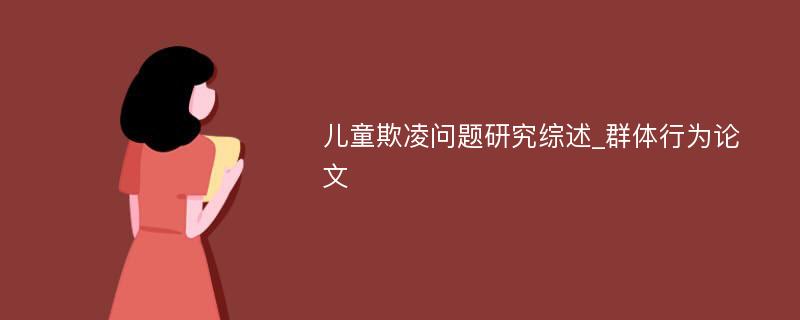
儿童欺侮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4.1
欺侮(bullying)是儿童间尤其是中小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性行为。欺侮对受欺侮者的身心健康具有很大的伤害性。经常受欺侮通常会导致儿童情绪抑郁、注意力分散、感到孤独、逃学、学习成绩下降和失眠,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自杀[1,2]; 而对欺侮者来讲,欺侮他人则可能会造成以后的暴力犯罪或行为失调,因为欺侮行为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现象[2]。可见, 儿童欺侮问题的研究是发展心理学和学校心理学研究中极具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虽然儿童攻击性行为在本世纪初以来就受到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但是关于学校情景中儿童之间欺侮问题的系统研究直到本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而且这些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只局限在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地区[2]。到80 年代末90年代初,中小学生的欺侮问题开始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公众、教育行政机构和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如日本、英国、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研究。近20年来,国外心理学家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但在国内,关于儿童欺侮行为发展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在较广泛地参阅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集中介绍了当前西方儿童欺侮行为研究的主要结论与最新动态,希望能为开展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欺侮行为的研究提供某些参考。
1 欺侮的定义及儿童欺侮发生的一般特点
英国哥德斯密斯学院的Smith[3]认为:“欺侮行为可以被归属为攻击行为的一个子集(subset)。与一般意义上的攻击性行为一样,欺侮行为是指有意地造成接受者的伤害,这种伤害可能是身体的或心理的。欺侮通常采取打、推、勒索钱等方式,也包括讲下流的故事或社会拒斥等。欺侮可由一个或多个儿童卷入”。Smith认为, 欺侮与一般的攻击性行为相比具有三个特征:(1)未受激惹性(有意性);(2)重复发生性;(3)欺侮者和被欺侮者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性。在形式上, 欺侮可以分为直接欺侮(包括直接身体欺侮如打、踢和直接言语欺侮如辱骂、起外号)和间接欺侮(如背后说人坏话、群体排斥)两种类型。有关研究表明,与直接欺侮相比,间接欺侮通常不易为人们察觉,应予以特别的重视[1,2]。 关于儿童欺侮发生特点的研究主要涉及欺侮发生的普遍性、欺侮的性别差异、欺侮随儿童年龄变化的趋势以及欺侮发生的地点等问题。
1.1 儿童欺侮发生的普遍性
在“有多少儿童卷入欺侮行为”这个问题上,Olweus[2] 用欺侮问卷对挪威715所学校13万名8—16岁的中小学生调查研究发现,大约15%的儿童“有时”或“经常”卷入欺侮行为,其中约9%为受欺侮者,7%为欺侮者。严重卷入欺侮行为的约占5%(一周一次或更多),约3%以上为受伤害者,2%为欺侮者。与此同时,Olweus 还受瑞典政府的委托对瑞典60所学校的1.7万名3—9 年级的中小学儿童也进行了同样的问卷调查,发现了更高的比率。Olweus的这两次调查是目前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查研究。
在英国,Whitney和Smith[4]利用修订的Olweus问卷对在24 所学校的6758名中小学生的欺侮发生的普遍性进行了调查,发现:“一学期至少1次”有过被欺侮经历的儿童在小学和中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7 %和10%。而“一周至少1 次”这样频繁受欺侮的儿童在小学和中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和4%。另外,研究者[4]发现,在小学,有12%的儿童每学期欺侮别人超过1次,有4%的儿童每周欺侮别人的频率在1次或1次以上;在中学,有6%的儿童每学期欺侮别人超过1次,有1 %的儿童每周欺侮别人的频率在1次或1次以上。其他国家也得到了相似或更高的比率,如芬兰、美国、加拿大、日本、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2]。
由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或对欺侮的定义不同,在欺侮发生的普遍性问题上至今没能取得一致的结论。当然,即使使用了相同的方法,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及儿童对欺侮性质的理解不同,也仍然不可能得到相同的比率。但是已有的研究结果已充分表明,欺侮是存在于儿童之间的普遍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
1.2 儿童欺侮随年龄变化的情况
Olweus[2]对挪威和瑞典中小学儿童欺侮行为的研究表明, 在中小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报告的被欺侮的比率呈下降的趋势;而欺侮他人的比率,女孩随年龄的增长而有下降趋势,男孩则呈上升的趋势(只在14岁刚上中学时有一点下降)。导致欺侮或被欺侮发生率随年龄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儿童通常被其他同龄或年长儿童欺侮,因此,当他们长大些时,欺侮他们的年长儿童就相对减少了;二是随年龄的增长,学生逐渐“社会化”,他们比以前更清楚什么行为是可接受的,而且更能体会到别人被欺侮的“感情”[5]。Whitney和Smith[4,5]在英国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1.2 儿童欺侮的性别差异
儿童的欺侮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差异既表现在男女儿童参与欺侮的比率上, 同时也存在于欺侮的方式中。 早在本世纪70 年代末,
Lowenstein[6]对在1774名儿童(分5—7岁、7—11岁、11—16岁三个年龄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欺侮发生的频率方面,男生成为欺侮者的可能性大约是女生的两倍。近期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男孩比女孩更多地卷入欺侮行为[7]。
欺侮方式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女生更多地使用言语和心理欺侮,而男生则更多地使用身体欺侮。Bjorkqvist等人[8] 用同伴评定法测量了8—15岁儿童的三种攻击类型及其随年龄变化的情况, 发现男孩最为普遍地使用直接身体攻击,而女孩使用间接攻击最普遍,但是在言语攻击上无明显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从直接身体攻击逐渐变为更多地采用其他攻击方式。为验证这一结论在儿童欺侮问题上的适用性,Ahmad和Smith[5]利用个别访谈和修订的Olweus问卷对8—11岁和13—15岁儿童欺侮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定义中加入了诸如“送恶意的纸条”和“没有人与他们说话”之类的间接欺侮方式,得到与上面类似的结果。
上述欺侮方式的性别差异与男女儿童体格和同伴交往方面的差异相联系。一方面,男孩比女孩更强壮,尤其是青春期以后两性体格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因此,他们更多地采用身体欺侮的方式。另一方面,男孩和女孩的同伴交往各有其特点。男孩社会友谊网络通常比女孩的大,但相对比较分散和开放。而女孩则容易结成规模较小但关系密切的小群体。这种小群体的友谊特点是不愿吸收新成员加入,且关系易破裂。不同的友谊网络,使得间接欺侮对男孩可能不太有效,而女孩则可通过社会孤立和散布谣言等手段更有效地伤害别人。间接欺侮的特点在于难以被察觉,平时学生也很少向老师或父母报告。因此,女孩欺侮的普遍性容易被低估。但Ahmad和Smith[5]的研究认为, 即使将间接欺侮包括进去,男孩仍然比女孩更多的卷入欺侮事件。
欺侮的性别差异除反映在以上方面外,还表现在欺侮发生的地点、欺侮的对象以及儿童对欺侮的态度等方面。Ahmad和Smith的上述研究发现:小学阶段,男孩倾向于用身体欺侮的方式欺侮男孩和女孩,但在中学阶段这种欺侮则主要指向男生。男生欺侮多发生在教师监督较差的操场上。女孩通常只用间接方式欺侮其他女生,但这种欺侮常发生在教室和走廊等地方。此外,Hoover等人[9]对207名美国7—12 岁儿童的调查发现,女孩比男孩更倾向于支持“欺侮者比受伤害者具有更高社交地位”的观点。这也许表明,一些女孩(尤其在中学)可能崇拜有较高地位的欺侮者。Rigby和Slee[10]在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2 关于儿童欺侮产生原因的几种理论假设
迄今为止,关于欺侮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描述性研究阶段。尽管欺侮的起因问题是该领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并且直接制约着干预策略的提出,但是研究者至今还没有对此提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解释。近年来,有关研究者就欺侮产生原因的理论探索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竞争假设和外部特异性假设
“竞争假设”和“外部特异性”假设是关于儿童欺侮产生原因的两个比较流行观点[2]。前者认为, 儿童的欺侮行为是在学校里参与竞争和追求成绩的结果,即儿童对他人的这类攻击行为是对在校受到挫折和失败的一种反应。然而Olweus[2]对斯德哥尔摩6—9年级的444名男孩的研究发现,虽然儿童的学习成绩差与其攻击性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并不证明成绩差是导致儿童欺侮的原因。“外部特异性假设”(external deviation)则认为, 儿童之所以受欺侮是由于其本身具有一些“外部异常特征”,如肥胖、红头发、戴眼镜或讲异地方言等。为了检验这一假设,Olweus[2]对两组男孩被试做了比较研究, 发现与控制组中没有受过欺侮的男孩相比,被欺侮过的男孩一般并无“外部异常特征”。
2.2 心理理论假设
80年代以来,在攻击性研究领域中,有关研究者试图从认知能力或信息加工能力方面探讨儿童攻击发生的原因。其基本观点是:高攻击性儿童之所以攻击他人或者采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人际问题,是因为他们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加工存在偏差,或者由于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低下所导致的。Dodge等人[11] 曾提出一个儿童攻击发生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认为儿童对性社会信息的认知加工包括“评价—解释—寻找反应—决定反应—做出反应”这五个子过程,从环境中输入信息依次通过上述五个加工阶段,而后作出行为反应。如果儿童不能按顺序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或者在某个加工环节发生偏差,就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Dodge等人[12]研究表明, 高攻击性儿童更多地倾向于将他人的意图进行敌意归因,并据此作出攻击性反应。那么,经常欺侮他人的儿童是否象Dodge所说的那样存在社会认知的缺陷或偏见呢? Smith 和Boulton[13]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欺侮他人的一些儿童并不象Dodge所说的缺乏信息加工的技能, 而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事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研究者通过对欺侮他人的儿童进行个别访谈发现,这些儿童将操场看作是粗暴的地方。在这儿,为了避免被人欺侮,就必须支配或役使他人。由此可见,在欺侮者是否存在认知或社会信息加工缺陷的问题上,研究者还存在争议。
鉴于关于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信息加工能力低下”假设在解释欺侮发生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近年来有关研究者试图从刚刚兴起的儿童“心理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对儿童欺侮发生原因的解释。所谓儿童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就是在儿童头脑中形成的一种理解自己和别人思想、感情和动机的方式。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关研究者[14]发现,欺侮他人的儿童在欺侮情境中知道如何去伤害对方,如何选择逃跑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儿童对对方的心理有较好的把握。一些欺侮他人的儿童首领在“心理能力”上得分较高,他们能较好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却喜欢给别人造成痛苦,即缺乏移情能力。他们把经常欺侮他人的儿童的这种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但却缺乏移情能力的现象称为“冷认知”(cold cognition)。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儿童欺侮产生的原因,但是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儿童虽然能够理解他人但往往缺乏移情这个问题。
2.3 依恋理论假设
关于欺侮产生原因的依恋理论认为,儿童早期与照看者之间形成的依恋类型(回避型、安全型和反抗型)影响着儿童将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IWM)。在婴儿期形成不安全的IWM,可能会造成儿童以后在学校里产生不安全的和焦虑的行为,从而导致欺侮的发生[15]。到目前为止,关于依恋与欺侮行为关系的研究尚甚少。这一假设最早是由美国的Troy和Sroufe[16]提出的。他们将具有不同依恋的儿童作了匹配,观察他们在自由游戏中的表现,结果发现,具有不安全依恋历史的儿童对子比其他儿童更多地表现了欺侮行为,而具有安全依恋历史的儿童则能回避欺侮行为。Myron-Wilson和Smith[15]对196名(平均9 岁)儿童的研究发现了与Troy等人类似的结果。
3 儿童欺侮与家庭、学校及同伴群体的关系
近年来,在系统理论指导下,西方不少研究者试图从儿童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社会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等角度考察欺侮发生的原因或者这些因素对儿童欺侮发生的影响。
3.1 家庭
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基本动因,对儿童早期行为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关于家庭因素与儿童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早已表明,缺乏温暖的家庭、不良的家庭管教方式以及对儿童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导和活动监督都可能造成儿童以后的高攻击性[2,3]。 这同样适用于儿童的欺侮行为。欺侮他人的儿童不仅成人后仍可能成为欺侮者,而且有可能“培养”出欺侮他人的孩子。
3.2 学校
不少研究发现,欺侮发生率因学校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这显然不是儿童个体或家庭因素造成的,而与学校的文化有重要的联系。Smith[3]认为,学校是否有反欺侮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欺侮的普遍性。不同的学校准则和学校风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儿童的欺侮发生情况。但学校和班级大小及学校位置与欺侮的比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已被有关研究所证实[4]。此外,Olweus[2]的研究发现,课余时间监督的教师越多,欺侮发生率就越低。在欺侮情境中,教师对欺侮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着欺侮行为的产生。
3.3 同伴群体
在影响儿童欺侮行为的因素中, 同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Olweus[2]认为,欺侮行为作为一种群体现象, 产生时一定有某些群体机制在起作用。他总结出欺侮发生的四种群体机制:(1 )社会感染机制,即儿童的欺侮行为是社会习得的结果;(2 )对攻击倾向控制力的减弱机制。在欺侮情境中,一般的或非攻击的儿童会因欺侮行为受到奖赏或得到较少的否定评价而减弱了自己对此行为的控制;(3 )责任分散机制。儿童会因为有很多人参与欺侮行为而降低了自己的责任感,这种责任的分散或减弱导致对事件产生较少的负罪感;(4 )追随欺侮者的儿童对受伤害者感知发生变化。由于被欺侮者经常受到攻击和消极评价,他(她)将被认为是无用的人,应该受到攻击。正是由于这些机制的作用,导致群体欺侮的产生。
致谢英国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Goldsmith College,London University)的Peter Smith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部分资料支持,谨此致谢。
本文于1998—10—09收到。
标签:群体行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