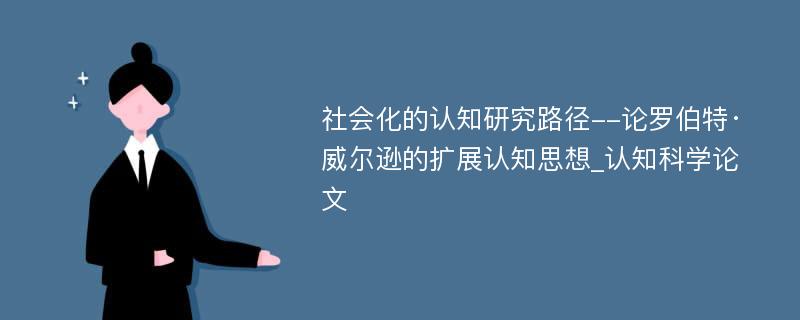
社会化的认知研究路径——论罗伯特#183;威尔逊的延展认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罗伯特论文,威尔论文,路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4)01-0001-05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机器人的研究领域开始使用涉身方法,探索机器人的智能行为。在此基础上,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提出了“无表征的智能”,设想计算智能的控制不再依靠内部的算法和表征,而是立足于行为和世界的交互作用。克拉克甚至主张,心灵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维,而是解决问题的行为。在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中,计算机系统中的智能行为观念,实际上类似于认知以支架式、嵌入式、延展式突现的思想。既然认知就是一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可以分为涉身行为与嵌入社会的行为。为了统一这两种行为,克拉克和查默斯提出了延展心灵论题,建议自主体的心灵及认知加工不受颅骨和身体的限制,可以延展到世界中,以此作为新的认知科学的基础。然而,延展心灵论题无法合理地说明认知加工中的主体间性。对此,威尔逊采用一种保守的策略,把这个问题转换为确定认知加工主体的问题。他接受传统方法对认知的主体与自主体的区分,把主体确定为在自主体身体中的认知系统控制点,认知系统由认知加工实现。在他看来,这种认知系统是延展的。这就从新的视角拓展了认知的研究路径。
这一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呈方兴未艾之势,但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文本试图通过评价威尔逊的延展认知思想,展示这一研究方向的新进展。
一、涉身认知科学的困境
按照传统的认知主义,心灵是表征符号加工的输入-输出设备,依据句法转换产生的语义特征获得自身的符号(或亚符号)结构。认知过程的操作只在感觉器官的符号传输中进行,认知的开始与结束只涉及神经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不需要与真实世界交互作用。然而,认知主义无法解决“符号接地问题(symbol grounding problem)”,即符号系统的语义解释构成系统的方式,或者说自主体获得符号及其结构意义的方式。事实上,要说明表征如何获得意义,只有借助涉身性的概念。从“涉身”的观念来看,传统的认知架构对(负责感知与活动的)低级外围系统、(负责思维的)高级中枢系统、(负责非感觉形式表征的)加工操作的划分,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1)特定感觉形式的表征构成了思想的“原料”;(2)知觉、思维和行为之间不只有因果关系,也有构成关系。以感觉运动为核心,涉身认知划分、“在线”与“离线”两种感觉能力运行方式,“在线”处理依据的是身体,“离线”处理依据的是大脑。“在线”的涉身性指认知对(感觉运动的)大脑与感觉器官、四肢、感觉和运动神经等身体的相关部分的动态交互作用的依赖性,它不只涉及感知和行为还涉及思维。“离线”的涉身性则指在没有感觉输入与动作输出的情况下,认知功能仅仅依赖于大脑的感觉运动区。在这种涉身性中,身体的作用只是间接的,主要由脑区处理身体的特定信息。对涉身性两种作用的区分表明,并非所有涉身性都依赖于身体。从涉身性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研究只关注基于感觉运动的大脑认知,基于身体的涉身认知明显不足。加拉格尔(Gallagher)试图通过身体意象与身体图示的区分,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但他没法解决两个问题:认知的物理实现,取决于大脑还是身体的感觉运动?如何从因果性与构成性的视角,解释涉身性的概念?这些考虑,仍然局限于生物个体,事实上认知的运作还涉及嵌入式的行为,这种行为把认知任务转移给环境,从而提高认知效率并扩大了认知的范围。从转移认知负荷的视角来考虑,认知的行为是一种设计好的行动,它揭示出心理计算难以提供的信息,从而促进了问题的求解。通过这样的方式,减轻内部记忆尤其是工作记忆的任务,达到减轻认知负担的目的。
如果用认知主义作为判断认知科学与涉身认知科学的准绳,那么无论是涉身行为还是嵌入式行为都不能作为新科学的基础,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选择。为此,克拉克与查默斯设计了延展认知,把认知系统的边界扩展到个体的生物膜之外,使之具有物理与社会环境的特征。与此相应,心灵也渗透到世界中,认知活动分布到个体和情境中。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动力系统理论,通过这个理论工具,用精确的数学方式描述认知系统在各种状态间的关联变化,反映出这些状态的变化如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心灵构想为动态系统,它就能延展到身体也能延展至世界。这种激进的方法极大地撼动了以笛卡尔内在主义为基础思考心灵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克拉克与查默斯提出了延展心灵论,但这种心灵概念与一般的直觉相矛盾。只有把因果性与构成性结合起来说明,才能克服这个矛盾,但这又产生了“因果构成谬误”,即认知活动涉及系统与外在事物的因果作用,一旦外在事物构成认知过程,就会产生概念鸿沟。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通过重新阐释主体间性,提供新的解释方式。具体来说,他认为认知科学中的心灵观体现了个体主义,认知科学中的心灵以个体为边界,但“人”这个主体作为典型的个体,既不是唯一的实体,也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一些较小或较大的实体概念化后,也可以充当个体或具备典型个体的属性,如信息加工的模块与物种。以典型的个体为基础,个体与心灵的关联必然体现为心灵的先天论形式,从而将心灵限定在个体中,拒斥群体、社会与文化。显然,个体主义坚持“自治原则”是方法论的唯我论。个体与心灵的这种强关联以“微粒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把基本属性看作天生的,用基本属性解释实体的属性。但是,基本属性不能用于解释实体的关系属性,这就需要超越个体绑定,探索个体与其功能成分在世界中的因果关系。
二、“实现”概念构建的延展认知
认知科学中的个体主义典型地表现为方法论的唯我论,而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卡尔纳普,因为他最早提出,思想就是对大脑中语义关系的推理。弗雷格与罗素主张说话者的描述决定着指称,从而在他们的描述性指称理论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普特南明确地把卡尔纳普的思想称为“方法论的唯我论”,也通过“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揭示出个体主义的缺陷。在普特南的基础之上,福多构建了心灵“模块”论,进一步发展了方法论的唯我论。传统上,心灵结构只是生理的机能,对心灵的研究无外乎两个视角:一是“水平”视角。把心理过程看作非定域机能之间的交互作用。二是“垂直”理论。即认为心理机能是一个由遗传决定的确定领域,并与不同的神经结构关联。“垂直”理论可上溯到19世纪的颅相学运动,他们把心理机能与大脑的特定物理区域相关联。福多于20世纪80年代复兴了这个理论。心理模块具有信息封装(informational encapsulation)与定域性(domain specificity)的基本属性,这两种属性把心理的功能结构与心理内容连接起来,而个体只需依据这两种属性就可以在背景信念中独立加工出信息,对心理内容的概念给出原子论的因果说明。
除了方法论的唯我论,认知科学中还有另一种个体主义的形式,即斯蒂克的“自治原则”。他的“原则”改变了界定个体主义的标准方法,强调“心理学家应当考虑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是那些随附于生命体当下的、内在的物理状态”[1]。斯蒂克对个体主义的随附性概念的界定比其他人的界定更为严格,他要求一组属性S(随附属性)随附于另一组属性B(基本属性),需要满足随附属性S与基本属性B完全一致的条件。这样的定义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随附性是物理主义的一种形式,而物理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另一方面,普特南的思想实验在原子层面构想了一个个体的“分身”,所依据的也是随附性的思想,这样的构想已成为表述个体主义的典型方式。福多与斯蒂克都不考虑心理状态在大脑之外的情形,因为心灵的表征理论只针对大脑内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通过表征世界影响我们的知觉和行为,进而影响我们与世界的交互作用。如果生命体内在的表征状态保持不变,环境就不影响认知。随附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决定”(determination),个体主义就是指内在的物理状态“决定”个体的心理状态。环境因素只是个体产生思想及其心灵的一个原因,世界是心灵内容的作用因或动力因。但是,内在特征完全相同的个体是否有相同的心理内容?这需要从心理状态的分类上来考虑,因为我们在使用“心理的”、“精神的”或“认知的”这些形容词的时候,实际上表述了某种具体的心理状态、属性、过程或活动。根据福多的论证,一般情况下,科学分类依据的是因果力,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的分类也遵循这个原则,由于任何因果力都随附于事物内在的物理属性,对实体的分类只能依据这种属性,因此科学与心理学都是个体化的。[2]但是很容易找到一些反例,进化生物学中的物种分类发生在系统发育中。这就意味着,延伸意义或非标准意义上的“个体”不遵循因果力原则,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途径:要么扩展因果力,要么解除因果力与个体内在物理属性的随附关系。
威尔逊选择了第二种解决方案,用“实现关系”替代“随附性关系”。实现是心理与物理状态的二元关系(two-place relation),也是这个关系的实现者。从“实现关系”来理解,个体的物理状态,或者说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是个体心理状态的物理实现,这些实现者(物理状态)对于实现的心理状态来说,在形而上学上是充分的。这是对“实现关系”的标准解释,具有个体主义的倾向。标准解释也可以表述为“形而上学充分”与“物理构成”两个论题。问题在于“形而上学充分”的实现,不完全是个体的物理成分,这两个论题有时候并不能同时用于同一个实现者。由此,威尔逊试图否定“物理构成”论题,以便为心理状态的“广义实现”提供空间。[3]在他看来,个体主义支持心灵的计算和表征理论,在认知科学中有广泛的影响,但是用个体主义的方式解释认知科学的知识论基础更像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证据。
尽管计算机制需要用某种关于世界的假定解决决定性的问题,但是这种假定只是为计算机制服务,而不是认知架构所内在固有的。也就是说,这种假设涉及外在世界特征的关系,或者说涉及内在的视觉显示的属性与外在世界属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假定并不是生命体的编码。我们的知觉系统和认知系统只是利用而不是编码这些与世界相关的信息。
威尔逊用“广义计算主义”的思想反驳个体主义。他认为计算能够延展出生命体的大脑,牵涉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广义计算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能够嵌入信息丰富而复杂的环境中,大脑中的计算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代表完全的计算系统。计算单元既包括大脑中的计算,也包括大脑外的环境。因此,广义计算系统涉及的心灵可以从颅骨延展到世界中。广义计算主义通过区分“位置上的”与“分类的”心理状态概念使计算主义脱离个体主义。个体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区分通常表现为如何对心理状态进行分类(或个体化),但是两者都假定心理状态是在“位置上个体化”,即它们都位于生命体的包膜上。对于这个假定,两者的分歧在于心理状态在“位置上的个体化”是否意味着心理状态也必须在分类上个体化。然而,广义计算主义认为构成计算系统的心理状态并不位于个体的头部而是在环境中,从而否定了位置上的个体主义。广义计算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特征:(1)使用形式化(或计算)的方式描述生命体的环境,大脑成为统一计算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关于大脑的假定不成立,广义计算主义就是不合理的。(2)这个心灵—世界的计算系统不只是大脑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可认知的。如果没有这条假定,广义计算主义就无法划分可计算的世界,这个主张并不打算告诉我们认知在大脑中的真实情况,只是试图对大脑中的认知问题做出答复。威尔逊在马尔的视觉理论中检验他提出的“开发式”表征与计算概念的合理性。他认为马尔所用的是“可编码的”计算与表征观,而非“开发式”的观点。马尔的视觉理论假定了一个在位置上个体化的计算系统,它以早期的视觉神经通路作为计算的起点,这些通路对方向、空间频率、对比度与空间相位的敏感度各异。威尔逊认为任何视觉情景都可以分解为这四种属性,计算系统只有延展到世界中才能通过因果作用,促使视觉通道借助转换规则模拟外来的刺激,而不是简单地在视觉神经通路中编码这些属性,把大脑中的部分知觉形式当作可利用的世界的形式属性。广义计算主义的难题是马尔的“空间一致性假定”与“立体视觉假定”,这两个假定从物理上限定了如何反映世界的结构。威尔逊的策略是延展马尔视觉理论的时间纬度,致使早期的基本视觉作用从世界中产生而非大脑中。以广义计算主义为基础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心理学[4],它为认知方法从个体扩展到社会开辟了道路。
三、群体心灵实现延展认知
威尔逊的广义计算主义是一种“窄主体、宽实现”的延展心灵框架,可以概括为:A是典型的认知自主体,它具有心理属性(状态、过程与倾向)P的条件是,A要么自身含有一个实体绑定(entity-bound)的系统,要么成为“宽系统”的一部分,“宽系统”实现P的生成过程或物理构成。根据他的理解,我们感觉到“疼痛”是因为体内有“反映疼痛的系统”,我们产生“雪是白的”信念是因为我们置身于民众心理系统中。既然心灵可以延展,那它延展到哪里?威尔逊提出延展心灵论是为了解决先天论与经验论之争,因为认知自主体只需要有心理状态的核心实现就能控制行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用“强”的方式理解心灵。认知科学中的个体主义体现了强先天论形式,而生物学与社会学中的群体心灵假设则是一种强经验论,它过于强调环境在认知中的作用。既然个体的概念并不局限于认知科学中的典型形式,那就可以在一般科学中考虑个体与心灵的关系,为此,威尔逊把认知科学的视角扩展到生物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重新思考这些学科中个体与心灵的关系。事实上,精神分裂症与神经功能缺失为这样的思考提供了一些依据,因为这两种患者很可能将民众心理状态归属于实体绑定的系统,与此类似,群体心灵假设也可能使用“宽”系统实现心理状态。群体心灵假设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字面”理解,群体具有个体那样的心灵形式,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中是一种高阶个体,但是这种心灵只是个体心理状态的某个子集;二是“认知隐喻”理解,群体不具有个体的心灵形式,它们只在某些方面类似。这两种理解方式分别存在于社会心理学的集体心理传统与进化生物学的超个体传统中,它们通过假定群体心灵来解释群体所具有的自我行动能力。群体心灵的突现,是集体心理传统中的“多级特性”(multilevel trait),也是超个体传统中“群体仅有的特性”(group-only)。根据群体心灵假设,群体的属性不需要还原为个体,但是从社会表现论题(social manifestation thesis)来看,群体的心理属性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的,而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可以相互独立,显然,很容易混淆这两种观点。在集体心理学传统中,群体心灵假设与社会表现论题就经常交替使用,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对“心理群体”的理解表明“社会关联具有个体意识那样的实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社会群体的集体意识谈论群体的思想与情感的关联,也可以把民众的意志倾向当作集体意志”。[5]他的这个观点首先表达的是社会表现论题,其次才是群体心灵假设。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描述了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群体对个体认知表现的弱化影响,提出了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这条定律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关个体转化为群体的方式,正因为这样,社会学家麦克菲尔(Clark McPhail)称其为“转化论题”。勒庞定律意味着群体心灵假设是个体转化为群体的结果。考虑到个体组成群体后,它的能力可能发生改变,而社会表现论题无法反映这种情况,这就需要对群体心灵假设与社会表现论题进行区分。事实上,在集体心理学中,群体心灵假设更像社会表现论题。另一位也叫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的学者在宗教思想与社会组织本质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群体心灵的方式,他通过建立宗教思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把社会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当作生物体,这样一来宗教就成为维持社会生物体的文化适应性体征,并以此反对群体选择的多层级理论,他的策略是把宗教当作群体层面的适应性,他的理解方式是在这两种传统中保持中立。采用这样的理解方式,就不能用大脑中的神经元类比大系统中的社会分布式自主体,因为能够感知、记忆与计划的不是个体的神经元,而是作为自主体的个体,只有这些属性才是社会分布式认知所有的。这就说明,群体心灵只涉及那些群体才有的特性,而不是多层级的特性,但是它又必须通过社会表现论题来理解。[6]
简言之,罗伯特·威尔逊在当代认知科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调解了激进的笛卡尔个体主义与黑格尔的超个体社会意识,因为他的群体心灵假设可以表达为外在主义的心灵理论:“群体意识的对话”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个体意识的一部分”。他的社会表现论题强调个体具有体现社会群体心理状态的倾向。对于他来说,“个体的心灵就是个体在群体中的心灵[7]”。
四、走向社会化的延展心灵
按照威尔逊的理解,个体的概念是我们思考心灵、生物以及社会世界的中心,为此他区分了各种个体概念。认知科学中的个体是计算程序与模块的所在、生物学中的个体是有特定系统发育史与生态位的有机体、人类学中的个体是文化、宗教与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他的社会延展认知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通过分析所有个体纬度,提出了一个个体与社会文化环境支架(scaffolding)关系的理论。威尔逊把我们解释心灵的能力理解为一种身体生成和扩展的技术。他把民众心理概念分为简单与成熟两种,简单的民众心理是命题态度的浓缩物,而成熟的民众心理包括情感状态和感觉。因为它归属于具有宽内容的个体意向状态,成熟的民众心理在分类上是宽的。此外,因为它涉及(通过第一人称的身体经验到的那些状态可知的)情感状态的作用,成熟的民众心理是身体生成的,因此它在定位上是宽的。然而,威尔逊把测心术的宽度进一步推进,认为当我们在进行复杂的心理叙事或操作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民众心理的运用场合是复杂的、涉及世界的(world-involving),它不仅仅是编码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复杂的社会世界操作的过程,我们互动和参与其他人的心理状态,并利用他们的丰富度。这样一来,不只是单一的实体才构成意向的主体,群体也具有最低限度的心灵,个体体现出只有当其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时才具有的心理状态,从而把认知的外在资源等同于内在资源,表明了心灵的意向操作实际上整合了认知的内外两方面资源。
由此可见,认知系统由认知加工实现,认知系统是延展的,认知不仅仅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这就从新的视角拓展了延展认知的研究路径。在这方面,威尔逊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