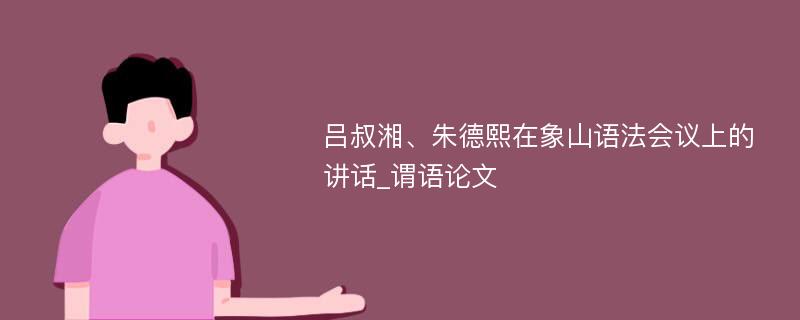
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香山语法会议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山论文,语法论文,朱德论文,讲话论文,会议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吕叔湘
(1982—06—24)
我看今天搞得挺正式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以为大家随便谈谈就完啦。
今天本来有个打印东西都发了。原来我能否参加这个会没有把握,预备六月中旬到外地去休假,现在改了日期,所以还是来参加啦。临定同志(李临定)对我说,你得有个书面发言,那么,我就书面发言啦。书面发言已经印好了,现在还要发言;那么我就亏了。现在很多小孩喜欢讲“亏了”,我今天真是亏了。没有什么东西讲,只能随便扯一阵子。
早几天看《北京晚报》。有人写了一段话,中小学里头教师强调死记硬背,压得这些学生喘不过气来,他反对,认为死记硬背不是好的教学法。我非常同意。这个话我本来也是经常说的。我遇到这些教师常说这些,死记硬背不是好办法。我们现在教育上面问题很多,经费不够,教师待遇差,校舍不够用,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学法的问题。现在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是死记硬背,已经到大学里了还是主要是死记硬背,这样子能否培养出很好的人材,我很怀疑。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很灵活的脑筋,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这个脑子很灵活,他遇到问题自己会想办法。他要找知识,反正有的是书。这就好办啦。学理工的人能够动手做实验,用现成的知识往他脑子里灌,他头脑能灌多少?总有装满的时候、装不进去的时候,而且怎么使用也是个问题。
培养人材,人出来嘛,各行各业有各种工作做,其中有一种叫研究工作。这个研究工作也特别需要有个灵活的脑筋。完全用死记硬背的办法训练出来的人,那研究工作做不下去。现在听说有些大学招了研究生,这研究生还要求导师讲,我听呀,你跟我多讲呀,希望能引出研究的路子。在研究当中无非是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个方面是材料,一个方面是一些想法。这好比我们做馒头,要发面,要有一个面团,同时要有一些发酵粉,然后面粉就发啦。光有面团,等于说光有材料没有发酵粉,发不起来;光有发酵粉,没有面团,也发不成。你死记硬背,只能是多给一点面粉,光有面团在那儿,它不发,你有什么用呢?发酵这个东西,决不是说等他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受了那个死记硬背的训练,到了当研究生的时候,说那个研究生导师轻轻拨动两下他的脑子就灵啦,没那么容易。他的脑子已经搞死啦,搞僵化啦。所以说,现在的教育,从小学一直上去,要逐步地把他的脑子搞灵才成。这个条件没有的话,种种工作都做不好,都不理想。
早几天,为了今天要到这儿来,要说几句,没有办法,我就翻了翻一本什么杂志,一本在国外的一些华裔科学家办的《科学导报》。《导报》上谈到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79年得诺贝尔奖的,这个人叫Vabo,杂志上介绍他说的话,我看很有意思。我念一下,就交卷。
“第一条: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都没有贴上标签,告诉我们它的解决是需要伟大的发现,还是只差小小的一步。”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好解决还是难解决,不知道。
“第二条:如果你过早地卷进一个你不愿意去研究的问题,那将是一个错误。”说明研究问题不能勉强,奉命研究搞不好。因为对某些事情特别感兴趣,至少显示出这些事情适应你的才能,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个很大的错误。
“另外一条:科学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是对于自然的进攻性。不要安于书本上给你的答案,要去尝试下一步。这种素质可能比智力更重要。”对于自然的进攻性,好奇嘛,为了解决问题,钻研去。“素质比智力更重要,往往是区别最好的学生和次要的学生的标准。”最好的学生有个钻劲。智力当然是需要的。
“另外一条:挑选人不能只靠考试,因为考试只能考出一定范围内的知识。要注意思路活,敢于创新的素质。”
我就作个传声筒,把这些话传一传。我看这些话讲得有些道理。
朱德熙
(1982—06—24)
我坐下来讲不太习惯。我本来说不来的,李临定同志强调我非来不可。我就漫谈吧。在这屋里随便谈谈。
前天商务印书馆要我编一套书《中国语法丛书》,就是从《马氏文通》开始一直到解放,国内一些书,把它重印一下,我给它写个序。写序时我想,从《马氏文通》到现在89年,快一个世纪了,我们的语法研究到底有多大进步?当然,考虑的范围,国外的也算。
主要说解放以后,论文我不说。王力先生、吕先生的书是解放以前的,我们也不说。解放后拿成本的汉语语法书来说,如果要挑出来作为推荐的书,我想只有一本书就是《语法讲话》(丁声树等著——整理者)。这是我的估计,不知对不对?《语法讲话》是1952、1953年问世的,到现在已经30年。30年书出了不少,我估计现代汉语语法有上百本左右,但是我想不出有哪一本,水平超出《语法讲话》的。当然我没有看全。我想,好像没有。这样讲不是说《语法讲话》就怎么了不起,《语法讲话》有好些不足的地方,而且不平衡,因为是集体创作,但是我想不出30年来有哪一本超过它,我看不出来。30年不算短。如果从《马氏文通》算起,王力先生那本书,1943年,吕先生的书,1941年。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差不多,到现在也不过40年的样子。如果从20年代黎锦熙先生《国语文法》算起,相隔20年,但吕先生王先生的书,和《国语文法》比起来,跨了一大步。现在30年过去了,还没有一本书,超过了《语法讲话》。这个现象怎么说呢?不好。当然这里头要分析原因。有客观原因,说的是30年,“文化大革命”刨掉10年,那就剩下20年,20年里那个17年有很多时间用在干别的去了。当然还应看主观努力。没有什么特点,都差不多,都大同小异,还比较空。现在的现代汉语语法就是介绍语法架子,什么词类啦,什么主语宾语啦,一些术语,一些架子,讲完没有多少事实,它是空的。我不是批评别人,说我们写的书就怎么样好,人家写的书就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北京大学写的书也是这个样子。北大1962年写的《现代汉语》我认为就是空的。有人说这本书写得很清楚。它是空的,没有多少事实,没有多少规律,有什么用?语法要有语言事实和语法规律。《语法讲话》提出事实和规律。事实和规律很难划。北大的书也是这样。吕先生讲过多次,语法应研究具体问题,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是不是注意理论问题?离开事实没有理论,是空的理论,没有用。我觉得问题就是不研究事实,都是一些教材性的,不深入,也不解决实际问题。我讲话比较偏激一点。不去研究事实,所以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事实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出来。我们去研究事实,新的东西和新的想法就会出来,离开事实就不可能。
汉语语法研究不应该摹仿印欧语,古汉语也一样。中国本来没有语法,对外来的东西可以学习、吸收、借鉴,这并不错。问题是你老跟别人走,看不到自己的特点,就不对。王先生、吕先生的书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汉语有我们自己的规律,但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仍受印欧语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往前走,问题早就提出来,但摆脱不了,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各个学科都有这个问题。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这不光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是这样。物理学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受一些老框框限制住啦。先入为主和传统观念对科学的束缚非常大。有的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限制,总觉得这是大家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真理。我们语言学也不例外。有些讲法,我想早就不应该那样讲啦。
下面讲两个问题,先说倒装。倒装我现在没有想清楚,倒装跟主宾语有关。这不像是从印欧语来的。请教吕先生,主语是施事,宾语是受事,这个观念不知从哪儿来的?其实,印欧语也不是这样。印欧语里主语不一定是施事,它可以是被动句,不晓得后来这个观念在我们脑子里就生根,生根以后就永远排除不了。有些问题讲来讲去就把主宾语跟施事受事看作一回事。因为看作一回事,主语必然是施事,主语为受事就说是提前、倒装。倒装的说法很可能有些变化,我想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抛弃这个观念。陆俭明写了一篇《易位句》,其实是倒装。我认为这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他讲的完全符合事实,他举的是主语倒装,述宾倒过来,动词放到宾语后头去,还有连动也可以叫倒装。我跟他说,补语也可以倒装。这是真正的倒装,移到后面去的必须轻读,这是非常重要的。汉语倒装是有形式标记的,“不去,我”。比如说“这辆车修好了”,陆俭明说是易位“修好了,这辆车”。照过去的说法是倒装句,现在《易位句》告诉我们“修好了,这辆车”才是倒装句。受事主语句不能看作倒装,“什么好东西你都吃了”因为不是疑问,所以不是倒装。“什么好东西你都吃了”,也可以是问句,那就是倒装句。陆这篇文章,讨论倒装就深入一步。我的目的不是说倒装不对,是说要研究具体问题。
再说时间处所词是不是主语。“今天种树,明天开会”。时间处所词到底是不是主语?我一直认为是主语,但我不敢说我的看法就一定对。过去讨论时间词是从逻辑上讲的,印欧语时间词作状语。不能因为时间词在印欧语是副词,在汉语就也是副词,比如说“去年种树,今年种树”是典型主语,“马上种树”是典型状语。“今年种树”像主语还是像状语?第一,汉语主谓结构谓语部分可变为选择问“我们种不种树”,“马上种不种树”不行。第二,“我们所种的树”“今年所种的树”,不能说“马上所种的树”。第三点,加连词,“我们要是种树”“今年要是种树”,不能说“马上要是种树”。说到底,时间词是体词性的,体词性的不能作状语。我左看右看不像状语。现在很多书还这样讲,时间词不是主语,唯一理由不是行动主体,不是施事,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不是鼓动大家要把时间处所词看作主语,而是要大家研究语言事实,把问题搞得深一点。
所谓语法,要从不同角度看,不要混为一谈。任何句法结构要从三方面来看:1.句法syntatic。2.语义学。3.语用学。普通语法学是广义的。这三个名词是从数理逻辑来的。syntatic是形式的东西,讨论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把符号连起来的规则。第一,研究语法一定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这句话不错,但不排斥完全研究形式。从前帽子很多,你这样研究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光研究形式不研究意义。研究主谓结构,从形式看,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在前的就是易位,主语必须轻读。主语和谓语中间有停顿,而且可以加上语气词,不要小看加语气词。动宾结构不可能加词,要引起我们注意。主语谓语还有词类上的限制。如主语是动词、形容词,谓语有约束,这就是形式上限制。谓语部分常常可以变为询问,“去不去?”“去了没有?”第二,看主语表示意义,在“我们种树”里,“我们”是施事,还可以是别的;“这个人你不跟他说话”“这个杯子可以喝茶”,当然还可以是时间处所词“今天我们开会”。本来主语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宾语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动宾关系多种多样。动宾关系说不完,格的语法也说不完。主谓关系也多种多样,这样看眼光就开阔。施受是语义问题,与主语在前是两个角度。第三,从语用学角度即从表达角度看,为什么一句话主语可以换:“我跟陈章太写了一封信”“昨天我跟陈章太写了一封信”“陈章太我跟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跟陈章太写的”。主语是说话人的自由,用哪个词做主语有自由,有人不叫主语叫话题。话题跟施事受事两码事,话题是可以选择的,是语用学问题。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有很多形式标志,不仅是由词序决定的。
讲汉语特点,有人说汉语没有形态,词序很重要。有点自相矛盾。汉语语法特点是什么?有比较才能看出它的特点。跟印欧语比较,汉语语法特点可以列举一些(形态不说):1.汉语动词形容词不变形做主语。印欧语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形要变形,这就引起很大争论,汉语有无名物化,名词化?我在有些文章已分析过这个问题,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认为这是汉语的重要特点,因它引起一系列问题。我去年在密云会上说印欧语构词与造句是两套,而汉语是一套。因为有这种区别,汉语语法体系应与印欧语不同。印欧语词组构造与句子构造不同,原因在于动词形容词做主宾语要变形,它的词组要有另外一套,就是说在谓语里动词是谓语,在主语必须变成To,或者是加ing,或者是用代词that、which变成修饰的东西。汉语没有这些问题。汉语词组结构原则与句子结构原则基本一致。印欧语词组与句子是两套,必须分开。词组与句子是包含关系,词组是部分,句子是全体,一层包一层。汉语词组不一定比句子小,是实现了的。任何词组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句子。“我去”就是词组,“我去好,你去不好”也是词组。独立时“我去”是句子。就是说,词组也可以成句子。不能老是句子的一部分。这样,描写汉语语法就要简单得多。“暂拟体系”的“定+主+状+谓+定+宾”里,宾语又可以是个复杂的东西,怎么弄也不好。我老提复杂谓语,你看成谓语的东西,它不一定在谓语位置上,如“请他吃饭是对的。”所以吕冀平管主语位置上叫复谓结构。我们承认汉语词组与句子看作一套,句子是词组的实现,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可以不讲句子,光讲零件,零件讲完,一搭起来就是句子。《语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这本书的特点在于:(1)用了层次分析。在传统语法里层次分析不受重视。(2)以词组为坐标的分析法,起码在《语法讲话》里已有这个意思。研究汉语,乃至汉藏语应该有这个做法,可以减少矛盾和混乱。(3 )讲了很多事实。尽管看起来有些琐碎,但我们不应怕琐碎。我们国内讲的语法体系是对语法规律和语法事实的表述系统,表述系统就是用怎样的话说出来,你叫它动词,我叫它谓词,你叫单位词,我叫量词,这都是表述系统,都是语法教学,不是纯理论问题。纯理论是“三品说”“转换语法”。表述出来有时候比较麻烦,不同语法体系不是实质不同,只是表述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语法体系意义不大,以词组为中心也是一种表述系统,并不是高深的语法理论,从大的方面讲它强调汉语语法的特点。
我刚才讲了几点,说乱了,(1)动形在主宾语位置上是动形。(2)汉语词组和句子是一套。(3)主谓结构做谓语。这是汉语很自然的句子。SVO这种写法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不喜欢”, 有人说是不正常句,这是没有根据的。印欧语主谓结构和汉语完全不一样。布龙菲尔德把句法结构分向心离心两种。主谓结构他认为是离心,在我看来,主谓结构是谓词性的,当然主谓结构和没有主语的谓语结构有点区别,说话总得有主语。事实上不是所有句子都是主谓结构,所以主谓结构作谓语应充分估计它的意义。过去讲的主谓谓语的范围还不够大,古书里主谓谓语非常多。
我要讲的具体东西就是这些。
刚才吕先生念的文章,搞自然科学的人写的,我很感兴趣。语法研究要研究具体问题,不要老是那几个问题。把外国人的题目跟我们的比较一下,他们的题目老是变化。他们爱标新立异。我们的框框太多,思想僵化。儿童语言咱们不研究,失语症也不研究。现代汉语研究也不要死守这框框。研究现代不涉及古汉语怎么行?要解放思想,科学家讲的话,研究事实就会解放思想。还是举陆俭明的文章,那些易位句早应发现,说明研究事实,思路就会开放,会给你刺激,给你启发。研究现代汉语还有个框框,大家只会研究抽象的普通话,连北京话也不研究。光研究北京话不行,还得研究方言。方言语法有极大启发。拿现代汉语来说,比它早点的是什么?如有兴趣,稍微往上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看我研究的现象这些书有没有。如“我开的灯”“是我开的灯”“我昨天进的城”。搞宋元的太远了。北京话“我开的灯”,方言怎样说?最近我给汉藏语学会年会写了篇文章。拿张盛裕潮阳话象声词和孟琮北京话象声词作比较,发现里边挺有意思,发现一种类型学“的”字。广州话是一种类型,福州话是一种类型。重迭不但是方言,汉藏语系也有,我们可以研究重迭的类型。不要狭隘,外国人研究工作不太严,但面比较宽,看得比较高。我们是自杀政策。研究汉语的人不管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现代汉语的人不管古代汉语,研究北京话的不管方言,这就非憋死不可。这怎么能培养出人才?一定要打破这东西,这牵涉体制问题。为什么把“少数民族语言所”跟“语言所”分开?我是关起门来随便说说,不一定对。我有点担心,特别是人才的培养。
最后讲一点学风问题。过去写文章无所谓。现在人家要我写,应接不暇。文章要有点内容的话,你一辈子写不了多少有份量的文章。现在有那么多学会,当理事顾问,然后要你写文章。一年能写一篇有份量文章就不少了。一年写三四篇文章肯定写不好。不要求量,真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写作,对自己不要宽恕,要有求真理的豪气。我讲的丧气话比较多,请吕先生批评指正,请各位批评指正。
吕叔湘
(1982—06—24)
朱先生讲了很多,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朱先生讲的是学风问题。大家喜欢谈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具体问题不太热心。这个,30年来一贯如此。这个学风不是跟语言学学风一家的事情,是整个学风的问题。拿历史来讲很明显。历史学界就是反对考据,说考据不成学问,不是搞史学,是搞史料,所以呢,要以论带史,拿论就可以把史带起来。带来带去现在也没有带出多少,说明以论带史,这个话抽象看好像有道理,具体做起来效果并不太好。具体问题还得具体研究。有位研究生写信给我,问论文做什么题目,我给他写了个具体题目,他说搞不了,要搞很多材料,所以他还是搞理论。搞理论不会有好的结果。大家觉得搞理论容易,搞具体问题难。但是,我说看错了。搞理论问题是表面上容易着手,事实上很难有结果。你没有那个基础呀,没有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你搞理论搞不出个结果来。搞具体问题呢,表面上是难,实际上比较容易,你反正泡在材料里边总多少有点收获,在一段时间中总有点收获,不像搞理论问题可能完全落空。另一点,提到研究具体问题,我觉得在语法问题上,限于在syntatic,在符号那里做文章,语义语用很疏忽,没做多少工作。举个简单例子“今天你去,明天我去”,也可以说“你今天去,我明天去”,你可以研究哪个是主语,是“今天”?还是“我”“你”?老在这上面去研究没意思,开个讨论会是相持不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能有高低。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研究?这两句回答什么问题,那两句回答什么问题?“今天我去”是回答“今天谁去?”“我今天去”是回答“我什么时候去?”回答的问题不同。这两句话不等价。我们对这些句子在什么地方用,为什么目的用的,不感兴趣。这里大有文章,大可研究,要花点功夫,可以有很多收获。一九五几年写主宾语,很多人请我写文章,我就顶住。五六十年代有两个问题顶住,一是主宾语,还有一个是讨论叫“文法”还是叫“语法”。陈望老亲笔写信给我一定要表态,我婉转回他的信,不表态。
吕叔湘总结发言
(1982—06—26)
谈点感想。第一点,参加了两天会,听了许多同志的论文讨论,跟去年在密云会议比较的话,很可喜。但是也引起一些忧虑,我看它是过虑。我们前进了一步,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有一些,遇到一些,怎么说呢,迷途啦等等。什么意思呢?在这两天会上,听到的看到的,有的没报告,也有文章印出来,武器装备比去年大有进步,装备是现代化得多啦。好像精密仪器都摆出来了。光谱仪、质谱仪、射电天文镜,什么都出来了。哎,这些精密仪器呢,当时很有用,可是有个条件,就是要让用的人用起来很方便,不费事。要是用起来很麻烦,那么精密仪器的作用就减少了。比如说,为了使照相机的效果好,就给它设计得更加繁复。但是照相机要人用,你要是很繁复,大家不大能掌握,也是个麻烦。听说现在外国有一种照相机,它里头的构造很复杂,但是用起来很方便。你不要怎么样去调光度呀、距离呀什么的,你拿起来看到的,你要照的东西都在里头,按一下就行了,一切都是自动调节,这样的仪器很好。假如仪器功能提高,用起来困难也增加的话,那仪器的效益就不大了。这个比喻不大恰当。换句话说,制造某个东西,工序很复杂。报道某个工人或技术员说工序有改进,原来是十道工序,一改进以后剩下五道,就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那就证明,原来的工序不很好,他可以改进。原来的工序可能有的是多余的,拿掉以后照样可以达到那个目的。还有的可能原来两道工序可以用一道工序代替它,或者用一道工序来代替几道工序的。再说零件,一个机器里头的零件,比如说原来有十五个零件装配起来的,经过改进,只要十二个零件也许就行啦。总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研究最后还是拿出去给人用的。要是研究的东西很精密,但是人家不能用,或看起来很费劲,我们就达不到目的。我们写一篇论文,总是希望比较多的人能看懂,并且能够了解,要是我这个论文写了以后,很多人看不懂,或者看后似懂非懂,那就达不到写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自己总是可以费很多劲儿,曲里拐弯地走进去,最后能走到一条路比较直,比较短,那么,读者不走我原来的那一条路,而走我后来发现的那条路,比较直的、比较短的路,他就方便一些。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看起来很费劲,才能懂,懂了以后呢,读者要是脑子比较灵活的话,啊,原来如此啊!那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说也是一样呀,这样说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懂。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想到,要容易读,读起来方便,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容易懂,那么他就更容易接受我的意见了。他要是不终篇,看一半放下来了,就无所谓接受不接受。有些文章很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懂,就是太多太繁,繁了以后弄不清楚。当中不一定要那么繁,有些地方可以省掉一些。就是说,工序可省掉一些,零件可以省掉一些,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这当中,不能绝对的。有的不能省,有的只要努力一下是能够省的,这就要花功夫。有时候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很繁,一篇文章比较简单,一般总以为写得繁的文章花的力气大,花的功夫大,写得简单的花的功夫小。实际不然,往往是写得简单的文章花的功夫大,它已经过一番很繁复的过程,最后他把它搞得很简单。我们还是要多花一点力气,少兜圈子,想办法把话说清楚。
第二点,前人跟我做同一个题目,他已经做过的工作,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一般的通例,上来就得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谁谁谁,在什么地方谈过,他的主要的结论有哪些?当然有的可以不提,因为,他的文章没有多大道理,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那根本就可以不管。但是,对我这个研究是有些用处的,上来提一提,比较好,比之在文章当中好像附带说一句要好一些。就是上来说一下,随着附带提一提呢,这个方式不是不能用,是用于跟我这个专题无关的,他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专题的,他是谈另外一个问题,一个通论等等,那我不必在头上去说明,但是我行文当中有时候要提到它,我就在行文当中提也就行啦。最后,文章完了,还是要把我参考的文献列个目录,三篇,五篇,都可以列上。关于列举参考文献,自然科学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后头附上参考文献的。当中也会有偏差,有人列了十二篇,实际上只看过九篇,有三篇他是知道有这个文章,他就写上去,他没有看。当然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刚才说的我看过一些,就是说我参考了,做研究的也用上了,我的说明是比较不正式,随便,在当中插一句的,那么,最好还是在头上正式说一下,交代一下,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从前人说过,比如有三篇文章,我只提一篇,没提那两篇,那两篇我没有看。在国外,跟专题有关的文章都应找来看看。他们那儿条件比较好,有论文索引,一下子就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文章,然后你再找那些文章也很容易,他们能想办法帮你办。我们所在那个单位,或地方图书馆,资料可能有,可能不全,没有外国便利,因此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应该找来看看就是找不着,这个情况常常有的。但是也有人不去理会它,反正我研究这个问题,我去研究就是,前人讲过什么,好像与我关系不大。要是采取这个姿态,对自己来讲也是个损失。科学工作是一种集体的事业,跟几百年前不一样了。现在,总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往上攀。要是有人站在那儿,有肩膀你不攀,你要站在这个平地上往上攀,你就费很大劲儿。有时候攀得比前人高一点,有时候攀得还不如前人。所以,前人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话,一定要想办法知道。刚才说了,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在这样不好的条件下,应尽我们的能力,想办法,看不全,至少也要看到我所能看到的东西。在外国的学校里头,研究生,甚至大学本科生,开始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导师首先告诉他你要查文献。这个工序是不能省的,第一步就要查文献。
现在,研究成果是不得了的。每年出来,不要说一年,就说一天,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一天会,全世界出版的,今天6月26号,这一天, 各个学科,数学、物理、化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总起来,一天起码是三五万篇文章,不得了呀。现在在国外做研究工作,很苦恼的一件事情,第一道工序要化很多时间,查目录,把文章找来看看,看有没有可以吸收的东西,这道工序有时候要花好几个月。他那个文章多呀,比如我们知道的,美国出的化学论文索引,它是全世界的,索引不限于美国出版的,一个月出两厚本。我们语言学论文索引大概抵它一本的几分之几,那我们是好多年文章的索引,它那是一个月两本,一年二十四本,订起来这么一摞。你还非在那里头去找不可,跟我这个研究题有关的,一定要找来看,看人家做工作做到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语言学,尤其是在中国,情况相去很远,但是我们的趋势是在朝那方面走。你可以看看1981年发表的文章,肯定比1980年多得多,1982年比1981年还要多。假如我们不再遇到什么“四人帮”之类的灾难的话,我们是会从现在起,就把这个办法用起来,或者说把这种制度建立起来,这对整个研究工作是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