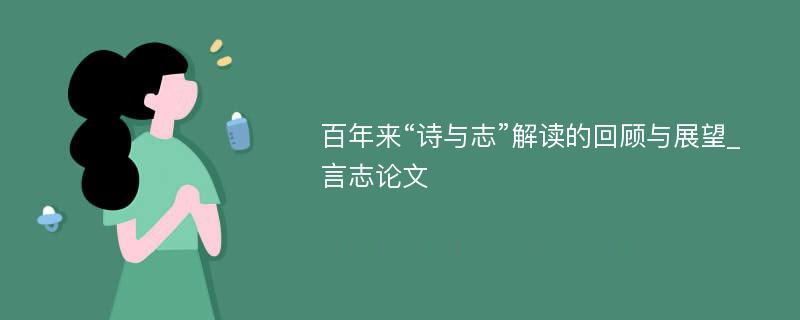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百论文,年来论文,诗言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5-0157-06
一
“诗言志”这一古代诗学理论范畴,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应该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论者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先生先后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遗憾的是,早期陈钟凡、郭绍虞各自《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先秦的文学观念“诗言志”说均无直接的话语。在谈及汉代《毛诗序》时,竟然说:“《毛诗大序》一篇对后世的文学批评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不出儒家论诗的意见,没有什么新义,所以也不多讲了。”[1]可惜的是,对继承先秦文学观念的“诗言志”说的汉代《诗大序》不加阐释和评价,忽略过去,表明了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并未引起当时著名学者郭先生的注意和重视。不过,那时有对“诗言志”出自大舜之口提出质疑。如罗根泽先生认为:“声律的起源很晚,自然不能认为是尧舜时代之说,即:‘诗言志,歌永言’,也不能信其出于大舜,因为虞书编辑,已被古史大家顾颉刚先生推定在西汉之时了。但‘诗言志’,我们可以断定是较早的说法,大约周代已经有了。”[2]据此,他从雅、颂的作者虽没有明言“诗言志”,但已显示出“诗言志”的含义中,认为读者可以归纳此语。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云“诗以言志”、荀子倡“诗言是其志也”,认为此说的产生很早了。
对“诗言志”说进行令人信服的详细阐释,是著名的学者及民主战士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先生。闻一多先生在他的《歌与诗》里从文字学角度看“诗”与“志”,他认为“志”有三个意义,即记忆、记录、怀抱,证明“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由“志”的三种意义进而分析诗的发展的三个阶段。[3]这样的阐释,确实是独树一帜。在中国诗论史上,第一位以“诗言志”为题著书立说的是朱自清先生,他专门著述《诗言志辨》,在《诗言志辨·序》里对“诗言志”作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他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作了考察和阐析,并且还谈及比兴论诗,谈及诗教,述及正变,对诗作了多方面分析。尤其“作诗言志”一节,将“诗言志”意义的引申、扩展,论及极为详细,仔细品味,可以体会到朱氏的分析包含创作与接受的双向内涵,比如《诗言志辨》论述过程中数次涉及“作诗人”、“读诗人”、“听诗人。不过《诗言志辨》侧重对于文献资料的考辨,没有就创作与接受的双向内涵阐释“诗言志”,这样给后人留下了研究阐释的空间。可以说,朱自清先生集古人研究之大成,在“诗言志”研究领域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学术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趋势,尤其是“文革”十年学术处于更加凋敝、萧条状态,那时“诗言志”研究亦然,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学者都纷纷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涉及并论述了“诗言志”,使“诗言志”的研究处于崭新的阶段,焕发出一派生机景象。蔡钟翔、敏泽、叶朗、李泽厚、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陈炎、陈良运、詹福瑞,鲁文忠等在各自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中国诗学批评史》、《中国审美文化史》、《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等著作里对“诗言志”进行了阐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诗言志”产生的时代引起普遍的质疑。许多论者承续了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和罗根泽先生的论述,怀疑“诗言志”产生于尧舜时代。陈良运先生指出:“实际上,尧舜时代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明断的诗论,因为连‘诗’字也是西周时候才出现。据陈梦家《尚书通论》的推断,《虞书》之《尧典》、《舜典》均为战国时代的著作;近人蒋善国综合古今各家学者的考证成果,并将《尧典》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物和语义特征,与先秦诸子著作及其他有关典籍作了详细的比较,勘定《尧典》出现于公元前372-289年之间,即墨子之后、孟子宫所生活的时代。笔者以为,这一判断是不可信的,还有些其他的理由,笔者已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中作了陈述,此不赘言。这就是说,《尧典》中历来被认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段话,是战国中期某位无名氏整理史书时的拟作,《诗》已流传甚久,算是晚进的诗论了。”[4]他还从文字学、文献学、先秦诸子论诗的情况加以考察和辨析,认为:“‘诗言志’出自舜之说应予彻底否定。否定了此说,我们便可以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国诗学到底发端于何时,便可对其具有诗学意义的理论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5]最后他推断“诗言志”这一观念的出现,当在秦汉之际。王运熙、顾易生说:“‘诗言志’的说法却是很早就产生了的。《今文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自然不能想念是上古时代的文献,但是可以肯定在春秋战国期间,这种认识却是相当普遍的。”[6]后来他们又说:“‘诗言志’产生的时代,当与上述诗篇大致相当,或许更早。今首见于《今文尚书·尧典》,谓为虞舜对乐师夔的指示……这段话自然不可能是上古时代的原始文献。”[7]廖群则说:“按《尚书》中的《虞书》乃后人根据传说所补充不能作为尧舜史料,已是定论,但《虞书》的出现至迟不会晚于春秋中期,《左传·文公十八年》已经提到‘虞书’之名。这样,‘诗言志’之说作为春秋时代的产物,正与《诗经》的艺术实践相呼。”[8]张少康先生说:“因为《尚书·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9]对“诗言志”产生的时代进行怀疑,其实早在汉代郑玄“诗谱序”中就怀疑诗歌产生于“上皇之世”,也怀疑舜有“诗言志”之说,因为无史籍记载可证,商代也不见风诗、雅诗。
(二)对“志”的阐释。中国古代诗学发端于“言志”说,对“志”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便会有对“言志”说的不同发挥。“志”的阐释是“诗言志”说的核心,许多论者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罗根泽先生对“志”的内涵有独到的解释:“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地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分。”[10]也就是说,“志”包蕴了理性与性情的内涵。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认为:“‘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志’既然是诗人的思想感情,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11]把“志”表述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概括了诗歌的本质特点。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也认为“志”就是“思想感情”,如说:“从对事物发表意见方面来说,是美刺;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方面来说,就是言志……美刺和言志是一种思想从两个角度提出来的,它们都表明了古代人们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12]后来他们进一步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对诗歌表现作者思想感情这一特征的最早理论概括是‘诗言志’。……其一,‘志’与‘意’,在先秦时已有通用的,不始于汉人……其二,‘言志’在先秦时包括‘言情’的内容,那时‘情’‘志’是不分的……其三,‘志’作‘记忆’、‘记录’的意义,在‘诗言志’中还是存在的。”[13]叶朗对“诗言志”的“志”的涵义作了仔细分析,认为在先秦,所谓“诗言志”,主要就是指用诗歌表现作者或赋诗者的思想、志向、抱负。这种思想、志向、抱负,是和政治、教化密切联系着的,并指出后来汉代的史学家和经学家把“志”释为“意”,还是“符合‘诗言志’原意的”[14]。同时又指出“在先秦和汉代的这些提法中,‘志’所标示的思想、志向、抱负,还都是一种藏在人心中的静止的东西,因而都还停留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15]。他还指出,先秦典籍中的“诗言志”的命题,在美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很大。而经过孔颖达重新解释了“诗言志”的命题,则在美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陈良运先生则说:“考察先民的诗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言之‘志’也就是言身边之事,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秦汉以前,即使是‘作诗言志’,也还有抒情的自觉性,因为‘志’是思想意识中本质性的东西……‘志’既然属于理性范畴而不属感情范畴,强调‘言’概念性的‘志’自然不可能同时注重抒情性与形象性,由此可说:中国古代诗歌发端于志,也就是发端于理念。”[16]张少康先生认为,“志”即是“心”;“心”借助语言来体现,即为“志”。“志”也有“情”的因素,因为“情”亦是蕴藏于心的。所以“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17]。鲁文忠说:“所谓言志,无论是先秦时期解释的‘赋诗言志’或‘言诗人之志’,还是尔后说的‘述圣道之志’,虽重在思想、志向、抱负的阐发,但也并非单纯理性的述志活动。一般说来,‘诗言志’的志,偏重于指思想、志向;‘情动于中’的情,侧重于指情性、情感。实际上,在创作实践中,志和情作为一种心理内容,本来就是浑然交融、相互渗透的。也就是说,‘志’中不是没有情感的因素,‘情’也并不能排斥思想、志向的制约。”[18]李铎则说:“周代已有‘诗言志’之说,而‘志’又包含记事、记诵、抒情多种涵义,但先秦时对抒情作用研究并不深入。”[19]我们知道,《尚书·尧典》记载的“诗言志”,其志所指在当时还是不甚明确的,其中含有情志的因素,也有浓厚的宗教祭祀的因素。这一点,正如李泽厚、刘纲纪所论述的那样:“……由祀礼而生的诗,在《诗经》的《颂》和《大雅》中还可见到它的遗迹。《颂》之中有不少是所谓‘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之词,所以,向神明昭告王者的功德和记述政治历史的大事,是所谓‘诗言志’最早的实际含义。直到《国风》之中的《诗》产生以后,才开始有了带有个人抒情意义的诗的产生。”[20]
综上所述,现当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一种观点认为“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排斥个人情感因素。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认为“志”就是怀抱,这种怀抱与“礼”分不开,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叶朗、李泽厚、刘纲纪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意和情的结合。持此看法的有罗根泽、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周振甫、陈良运、张少康、鲁文忠等。
当然,除了上述文学批评史和美学论著述及“诗言志”之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有许多人争先恐后撰写文章探讨它。值得注意的是:王志明在《“诗言志”“以意逆志”说和接受理论》中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接受理论源远流长,其源头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诗言志’说……‘诗言志’的内涵包蕴着作诗言志和读诗言志的双向性。”同时高度评价了作为古代文论中接受理论源头的“诗言志”说,重视诗歌的影响和效应,肯定了读者在解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诗言志”不仅是创作理论的开山纲领,也是接受理论的开山纲领。本人拙作《春秋时期的“诗言志”与接受意识》一文认为: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实际而言,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接受理论。接着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分析“诗言志”内涵包蕴着阅读接受、表现读者思想感情的另一维面,最后指出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概念的“诗言志”,在春秋时期包蕴着作者作诗言志和读者读诗言志的双向内涵。尤其是张利群在《“诗言志”的多层多质系统观》中解释了广为流传的“诗言志”说。他认为:“诗言志”是一个立体结构系统,它具有多层多质性质和特征。并从“诗本说”、“诗比说”、“诗用说”、“诗教说”四个方面详细地透视“诗言志”说,进而指出,对“诗言志”的各结构层次要素的分析和解剖,已涉及诗的本质、特征、作用、功用、价值和意义等诗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并确定中国诗歌、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大胆地认为,“诗言志”不惟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而且是中国诗学的基本大纲、基本构架。作者还告诫人们:对“诗言志”的理解也不应该囿于某一说,而应该充分展示出“诗言志”的各结构层次,使之形成“诗言志”的多层多质的内涵和蕴义。可以说,作者以上的论述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独特的见解,显现出作者敏锐的学识目光和深刻的透视力。
二
以上是对“诗言志”近百年的阐释了作了一番梳理与审视。回眸过去,我们认为:尽管前人和今人对中国最早的诗学命题——“诗言志”的阐释和表述不乏深入探微之处,如有的论者对“志”的分析与考辨,对这一理论命题产生的背景的探索和涉及读者的接受意识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没有从综合思维的角度去把握“诗言志”的美学命题,即过去对“诗言志”的研究可谓微观透视有独到之处,却忽视了宏观把握。鉴于过去对“诗言志”的阐释和发挥存在着单向思维的倾向,我们企盼在这一研究领域采用多维度思维,将“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第一,从辩证发展的视角出发,对“诗言志”的含义作动态性的透视和阐释。对于“诗言志”含义,历来就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先秦,“诗言志”主要指用诗歌表现作诗者或赋诗者的思想、志向,抱负,即“志”所揭示的思想、志向、抱负,过多属于理性内涵。直至汉代《诗大序》的出现,“志”就明显含有“情”的内涵。《毛诗序》在“诗言志”之外,又提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的说法。到了魏晋南北朝,陆机在《文赋》中常常把“志”与“情”并举,如“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文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将“志”与“七情”视为同一东西,但并没有用语言直接表述,直至唐代孔颖达,“诗言志”说有重大发展。他明确地把情、志统一起来,并说“情、志一也”。按照他的观点,由于外物的感动,人心中产生哀乐的情感,就叫“志”,把这种情感抒发出来,就叫“诗”。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逐渐改变,人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对“诗言志”命题的阐释也如此。后来“诗言志”这个命题的美学内涵也就大大超出了先秦典籍中的“诗言志”。“诗言志”是什么?有的视“得意”与“失意”为“志”,有的认为“志”是“意向、怀抱”,有的认为“志”就是闪耀着理性的光辉,等等。在笔者看来,对“诗言志”这样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的理解,不能囿于某一说法,正如清代袁枚所说的,不可将“志”看杀也。因为“志”不应视为一种稳定不变的理念,而应该将它视为处于一种不断运动的诗学理论的系统中,不断地补充、完善和发展它的丰富多样、比较活跃的诗学内涵,并将它的内涵不断丰富,意义不断延伸,使它免于成为一种僵化的理念,使它于动态中显出活力,具有更深厚的美学意蕴。
第二,多方位、多维度地阐释和发挥“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1.从历史角度看“诗言志”在中国诗学理论上的延伸与发展。“诗言志”说从先秦到晚清可以找到发展的轨迹,一方面是深受儒家政教观念的影响,自孔子倡导“思无邪”并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观点来规范诗的教化作用之后,后世对“志”的分析看成是“圣道之志”,具有理性内涵。如汉代经学家董仲舒,南朝梁代的裴子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宋代的理学家邵雍,清代的翁方纲等。另一方面,继承了汉代《毛诗序》的阐释和发挥,从魏晋南北朝的刘勰、钟嵘、挚虞等人的发挥,到唐代的孔颖达、白居易一直到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钱谦益等,都标举“情志”说,认为诗歌不单纯是理性活动,而是伴随着情感,将“志”视为理性与情感的交融,这是我国“诗言志”说的主流。
2.从诗人创作角度和读者接受视角出发详细地阐释“诗言志”的内涵。虽然曾有陈良运先生等从接受角度看“《诗》以言志”,认为“《诗》以言志”应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接受理论。但人们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的分析,过多地认为“诗言志”是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其实,将中国诗学之渊薮——“诗言志”说置于先秦文学批评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和审视的话,发觉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论重视读者之特点的是被誉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这样重要命题,从中可以挖掘出其包涵了作诗言志与读诗言志的双向内涵。
3.从中国传统诗学主潮的视角出发,对这个诗学命题进行剖析。从一个迥异于前人的新的视角切入并理解“诗言志”的意义,在此领域,披荆斩棘,找出并去填补尚未被人诠释的“空白”,这是一个阐释者必须具备的治学态度。漫步中国文学批评史,考察传统诗学观念的发展变化,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主潮,并非言过其实。从“诗言志”的提出到后来“道志”、“载道”观念以及宋明理学家提出的文学观念,还有清代叶燮、王夫之、钱谦益等人的关于“诗言志”的说法,贯穿于文学批评发展史的始终,而且居主导地位。可以说,“诗言志”不仅是中国传统诗学之渊薮,也是中国传统诗学之主潮。
〔收稿日期〕2002-03-10
标签:言志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诗言志辨论文; 读书论文; 汉朝论文; 毛诗序论文; 虞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