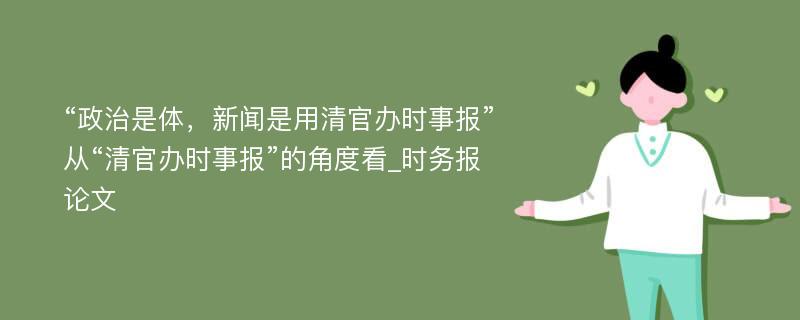
“政治为体、新闻为用”视阈下的清廷官办《时务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廷论文,时务论文,政治论文,新闻论文,视阈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官方与中国早期报刊的关系,一些学者做过相关研究。[1]一般来说,帝制时代的舆论中心媒介——邸报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士人往往通过邸报知晓朝廷的政治动态和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随着新式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关注新式报刊的舆论作用,而这些作用是旧式传播媒介——邸报所不具备的。基于新报在舆论中所起的作用,一些封疆大吏或经济支持,或政治保障,使之朝着有利于官方的一面发展。故在这类新式报刊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官立化的意味。而创办这类新式报刊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使之更加复杂。因此,在新闻理论模式中,有“政治为体、新闻为用”之说,即官方对新闻事业的或捧或压,是为其政治服务的。[2]在这方面,《时务报》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由梁启超、汪康年和黄遵宪等创办的《时务报》从民办到官办及停办的过程,既能体现出官方与中国早期报刊复杂的关系,亦能体现出官方在对待舆论的矛盾心情。 一、早期《时务报》与官方的关系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册中发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明宗义,表达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通上下中外”。[3]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舆论骄子”,对新报和邸报的认识非常清醒。新报“通上下中外”的作用有利于弥补邸报“上通下达”的弊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派要想维新,必须破除邸报不利的一面,而新报正好提供了这种契机,《时务报》更是“敷陈剀切,援据确核,实能补塘报之不及,而兼综西报之长。”[4] 《时务报》的创办应该是为维新造势的,因此,从一开始,《时务报》便有官方的背景。从对《时务报》告白的解读来看,多处打下了官方的烙印。“本馆自出报以来,叠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现已分派至七千余分,惟各省府尚多未能遍派之处,倘该处士商有欲代为经手者,请寄函本馆商议可也。”[5]“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将以明岁力图推广并加整顿,惜才力绵薄,惧弗克任耳,伏望海内君子更有以导之,辱承扶掖,铭感实深,事关公义未敢言谢。”[6] 不仅如此,一些封疆大吏更是成为《时务报》的推销者。张之洞在《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附单)》中评价《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因此,他要求在其管辖内的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7]此外,浙江巡抚要求其治下官员以公款订购《时务报》,分发各级官员阅读,“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以长智能。”[8]大力推行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用公款订购《时务报》,希望全省各书院学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9] 此外,一些官员为《时务报》提供经济支持。如李鸿章一次捐二百元给报馆,[10]道员朱采“附助报馆经费百元”。[11]根据闫小波的研究,对《时务报》的捐款达96人次。[12] 对于有官方背景的《时务报》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办报者也努力在寻求一种自保。在《时务报》创刊之前,作为创办者之一的黄遵宪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为守旧党计,为言官计,所谓本馆论说绝无讥讽,已立脚跟踏实地矣。其他一切忧谗畏讥,伤禽恶弦,无怪其然也……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宦途,尤畏弹射,然公然明目张胆为之,见义则为,无所顾忌。上年强学会太过恢张,弟虽厕名,而意所不欲,然一蹶而不复振,弟实印以为耻。但弟虑其费少不克久持耳,他非所恤也。”[13] 《时务报》的影响日渐扩大后,黄遵宪又表达了这样的隐忧:“夫都中论者仍多以报馆为谤书,前刻某君来稿(大僚阅者尚少,然有日新月盛之象),语侵台谏,乃当世所敛手推服者,则以为犯不韪。弟言偶失检耳,照章程例不论人,非有意也,此后当力守此诫。其他泛论之语,既事寝,不足介意也。又照章外来之稿应附卷末,此又误也。”[14] 但不管办报者有怎样的隐忧,由于《时务报》主办者的政见不同,《时务报》的内讧造成其分裂。梁启超离去后,汪康年成为《时务报》的负责人。为重新夺回《时务报》这块舆论阵地,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人士希望《时务报》官办,在一定程度上也埋下了《时务报》停刊的隐患。 二、清廷官办《时务报》及各方势力应映 由于《时务报》的舆论作用,促使官方意识到新式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官方接受报章这一新型媒介的表现是《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的创立。负责创办的工部尚书孙家鼐在《官书局开设缘由》中强调泰西富强之道在于“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15]但《官书局汇报》规定“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16]因此,官方的新媒体《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在开风气等方面不如商办的《时务报》。一些官员希望光绪皇帝“为报馆亟宜遍设,请敕实力劝办”。[17]官方需寻求已有成就的新媒体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此时《时务报》的内讧为清廷官立《时务报》提供了契机。 关于《时务报》的内讧,近年来出现了新的解读。但不管怎样,内讧的结果是分化了《时务报》作为维新变法的各派势力,也使以康有为为首的康门与汪康年为首的汪派走向了对立。康门近两年在《时务报》的努力几乎丧失。因此,康有为借助帝党的力量,欲将《时务报》收为官报,以梁启超主持《时务报》大局。 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上奏折,希望改《时务报》为官报,取得《时务报》的主办权:“为政之道,贵通不贵塞,贵新不贵陈,而欲求通、欲求新,则报馆为急务矣。昔日日本维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历欧美,讨论变法次第,及归,则首请设官报局于东京,报章一依西例。而伊藤自著笔记,乃至举西人一切富强之原,皆归功于报馆。”[18]此举无疑正中清廷改革派的下怀。光绪帝即日明确表明同意此折:“御史宋伯鲁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著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鼎酌核妥议,奏明办理。”[19] 光绪帝表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导。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册,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20] 对于清政府官办《时务报》,与《时务报》休戚相关的各方势力表现不一。具体来说,负责此事的孙家鼐积极主动地完成光绪帝官立《时务报》的任务:“一、《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今既改为官报,宜令主笔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官书局向有《汇报》,系遵总理衙门奏定章程,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俾阅者略知各国情形。今新开官报,既得随时进呈,胪陈利弊,将来《官书局报》亦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政。惟各处报纸送到,臣仍督饬书局办事人员,详慎选择,不得滥为印送。三、原奏官报经费一节,臣查官书局印报例,令阅报者出价;惟所售无多,故每月经费不足,由书局贴补。兹新设官报,阅报者自应一体出价,拟请将此项官报,随时寄送各省督抚,通行道府州县,均令阅看,每月出价银一两,统十八省一千数百州县,约计每月得价近一千两,常年核算约在两万四千之谱,加以官商士庶阅报出价经费。惟创设之始,需费必需数千金,若在上海开办,或由上海道代为设法,可令该员自行筹商。”[21]并且,孙家鼐还表示:“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报馆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监听之明,无偏听之蔽,如此则皇上虽法宫高拱,万里之外如在目前,于用人行政,似有裨益。”[22]孙家鼐乃光绪帝的师傅,是光绪帝最为信赖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学部大臣。不仅如此,孙家鼐续上《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为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23] 从孙家鼐请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报》的情形考查,可知清廷内部改革派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既涉及到权力之争,也涉及到学术之争,所以孙想将康请出京师,远离政治中心。这是康有为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康有为本希望在京师遥控梁启超主持《时务官报》,但孙家鼐的建议使之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康有为不得不离开京师。 当汪康年收到康有为官办《时务报》的消息后,马上电告张之洞,以寻求应对之策。他认为《时务报》的创办“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24]如果改为官报,会留下更大的祸患,“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暇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25]在不得不交出《时务报》的前提下,1989年8月17日,汪康年撤出《时务报》主要人员,另组《昌言报》,由梁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与《时务报》相同。[26]同时,汪康年在《昌言报》第一册上谕中将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各类折子汇编,以示抗议。[27]此外,汪康年欲借助地方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支持,期望光绪皇帝取消对《时务报》的官办。 但不管怎样,清政府在“咸与维新”的推动下,以上谕发布的谕旨不可能更改。8月21日,当康有为知道此事后,立即发电各地,令各地禁止订阅《昌言报》。光绪皇帝对汪康年变相抗旨的行为大为恼火,令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查明此事。8月22日,汪康年认为《昌言报》他一人“何能独自擅交”,“商款仍归商办,此则康年另办《昌言报》之缘由也。”[28] 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的张之洞有着敏锐的政治动态和矛盾的心情。从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态度来看,其心态颇为复杂。当《时务报》创刊之时,张之洞希望《时务报》办刊讲求“韬略”。后期《时务报》达到了“士人必读”的地步时,张之洞反而“紧张”,“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29]因此,张之洞由支持《时务报》转变为与《时务报》划分界限,以求得在政治上的安稳。在其看来:“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通经济之要端,不可不尽力匡救维持。望速告乡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于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与有责焉,似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30] 张之洞后来对报刊的举措正是这一“划清界限”的体现。1898年5月6日,张之洞以《湘学报》谬论太多表示不再订购:“查近来《湘学报》谬论甚多,应俟本部堂派员将各册谬论摘出抽去后,再行札发。所有以前报费,应由该局先行寄湘以清款目。现已咨明湖南学院,《湘学报》一项,湖北难于行销,以后勿庸续行寄鄂。”[31]同时,张之洞还建议湖南学政徐仁铸不再订购《湘学报》:“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窃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所有以前报资,已饬善后局发给,以后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另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察阅。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32]张之洞的举动引起众多人士的关注,但在张之洞看来,包括《时务报》在内的新式报刊的言论已超过了保守势力的容忍范围,变法失败是迟早的事。 从上可以看出,清政府官办《时务报》不仅将《时务报》牢牢控制在手中,作为其舆论宣传的工具,而且以此为契机,推动官报的发展,希望创办更多的官报“以开风气而扩见闻,期于时局有所补益”。[33]以此体现官方在利用报刊上的“政治为体、新闻为用”模式。 对中国新闻史来说,清廷实现对《时务报》的官办无疑是一件舆论大事,它开创了官方影响舆论的模式。在此之前,官方与报章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一些报章对官方的政事进行揭露,而负责此事的官员难以接受。最典型的是左宗棠与《申报》之间的冲突,以至于左宗棠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之语。[34]《时务报》的创办及影响为官方所接受,一方面,官方开始注重舆论的作用并期望朝着官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各方势力在其中的博弈使这一事件变得复杂。应该来说,清廷官办《时务报》使政府与报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丝缓和,特别是这种政论性报刊。 康有为引官方势力强入《时务报》颇受诟病,争论的焦点在于《时务报》作为一份“商办”的报刊,中央强行官办,是否表示政府可以任意干涉新闻舆论。对于早期报人来说,他们对新报的认识来源于西报,西报多半由私人主办,用来监督政府。可是,当政府也创办新报的时候,舆论就掌握在官方的手中,即所谓的“政府喉舌”,对于民办报业而言,对政府的监督无从谈起。但一些士人对官方强办《时务报》的抗议几无影响,因为“大部分的反对声音多半在私人信件间流传,并没有在公开的管道集结成够强大的力量。”[35] 一般说来,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是官立《时务报》的最大赢家,但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推进,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反扑。戊戌变法失败,帝党的一切遭到清算,《时务报》的停办也标志着戊戌变法告上一段落。 三、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清廷停办《时务报》 从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上谕旨到9月19日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月,而这两个月就决定了《时务报》的命运。光绪帝及其帝党官办《时务报》的意图很明显:企图通过《时务报》的舆论为维新变法造势,但随后的戊戌政变使其期望很快落空。此时的张之洞的第一反应是《时务报》可能不会改为官报,仍会交汪康年创办。张之洞致电孙家鼐:“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列。方今朝廷正论赖公主持,天下瞻仰,企祷企祷。窃思如有品学兼优之人,接办官报固好,否则不如暂停,从缓再议。至《时务报》本系捐款,似应仍归商办,即令汪康年照旧接续办理,不必改官报,较为平允。官报另作一事,自有巨款,岂藉区区捐凑余资哉?”[36] 但事态的发展不是朝张之洞想象的方向。光绪帝及其帝党期望以舆论为变法造势的行径遭到清算。戊戌政变后,慈禧及其后党要对开设报馆一事明确表态:“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应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37]同时,对于报馆也禁制:“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生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饬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38] 清政府对报刊政策的转变对报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时务报》的停刊标志着在国内创办政论性报刊的消沉。在慈禧及后党的打压下,维新变法时期出现的刊物纷纷停刊,留下的报刊也多半转移到国外或租界。办刊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康梁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继续推行维新思想。但对于国内的汪康年而言,清政府官办《时务报》使其躲过戊戌政变的“杀头之罪”,延续其报人生涯。 此后,清政府对于知识分子创办报刊采取审慎的态度,对于报刊进行规范化管理。在清朝灭亡的前几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进行管理,如《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例》、《大清报律》、《著作权律》等,对办报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一系列的报律阻挡不了革命的步伐,清廷在“士变”的摧毁下,最终走向了覆亡。 将清廷官办《时务报》纳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角度进行解读,或许会发现不一样的意味。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在新的格局下诉求新型媒介的政治化成为他们影响政治的途径。将报刊加入到政治的框架内,无疑是一大创举。 官方作用于报章的方式,无疑深刻揭示出晚清初识报章所经历的曲折,甚至可以说,这也成为晚清“自改革”彻底失败的写照。以官方对于报章之立场,不仅意味着近代兴起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影响着历史进程,同时读书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社会变革中。詹姆斯·凯瑞认为“符号即是现实的表征,又为现实提供表征”[39],那么,《时务报》既是维新变法的表征,又为维新变法提供表征,只是这种表征超过了利益集团所能容忍的范围。套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媒介的四种理论》来说,“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谁有权使用媒体。”[40]在这个问题上,晚清报人及政府内部对待报刊的态度或许决定《时务报》的命运。 从晚清报人的立场来说,早期报人被誉为“末路文人”,而这些报人在科举失意时选择办报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政局。《时务报》的政治化使他们上升的渠道多元化,成为一种“生意经”。他们试图通过报刊建构属于自己领域的合法空间。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康有为带着“设报达聪”的目的,希望将报刊推向政治的前台,“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41]从其本身的建构来说,康有为希望建构属于维新变法合法的空间,而报刊正好提供了这一话语权。 从清政府的角度考虑,危机倒逼改革的事实摆在面前。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意识到非改革不可,但如何利用舆论推动改革,如何挽救危机,是摆在当前最重要的议题。“中日战后,朝野力图自强,广征善后的方策,而普设报馆,以通民情,尤为时贤新主张。……国人重视报纸之心既起,于是研究新闻纸之学术的需求以生。”[42]这种由政治到报刊,由报刊到政治的模式,体现出“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推动力就是《时务报》,即报刊的“喉舌”作用。即便如此,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使《时务报》成为牺牲品。 “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43]将清廷官办《时务报》纳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模式进行解读,或许会发现,舆论的政治化一直是报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廷官办《时务报》作为政治改革一个失败的例子,没有解决好“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模式,在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中政府不得不连续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