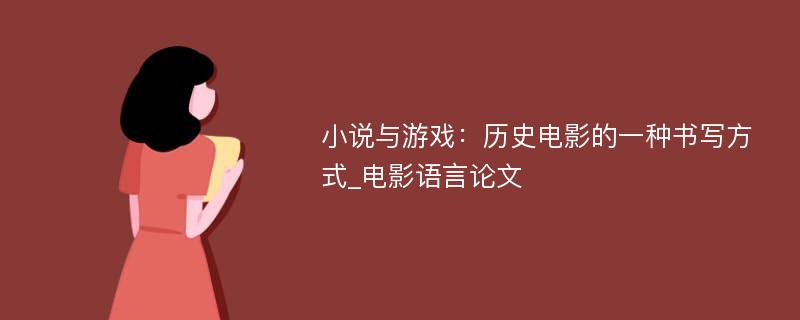
虚构与游戏:历史电影的一种写作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式论文,历史论文,电影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1999)04-0068-0071
电影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风云变幻在电影机器“重述”之中,如何成为大众的欲望对象?如何唤醒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一直是电影史家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引入深思,在于它与一系列复杂的理论命题纠缠在一起:历史/电影的关系,历史电影的概念,以及历史的电影写作及其叙述方式等等。本文选择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电影的界定:一般是把曾得史书记载的人、事与引人注目的历史时空相交织并以此为框架进行虚构的电影为历史电影。这类电影借用史事以造成真实感,可以造成观众对特定时代及文化的兴趣,引发其对历史变化的思索与探究的愿望。
一
毫无疑问,20世纪电影文类的介入已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对历史的看法。电影的物理技术条件所创造的视听形象统一和镜头画面本身的透视功能都为人们提供了对历史现实逼真“再现”的可能。对历史的书写出与呈现,不断地成为电影工作者的欲望目标。安德列·巴赞的真实影像论和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的还原”观无疑把电影的再现摹仿功能推崇到极致。巴赞说:“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注: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由摄影机记录的电影“影像上不再出现艺术家随意处理的痕迹,影像也不再受时间的不可逆的影响”。(注: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巴赞认为,历史根本的目的在于超越时间,而电影的完整性就在于可以再现本真现实,电影中“事物的影像第一次映现了事物的时间延续”(注: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不仅可以抗拒时间,甚至可以征服时间,实现了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巴赞企图通过电影达到对现实的抗争与历史意义的回归。
然而,电影真得能负荷起扭转光阴,再现本真历史/现实的重担吗?
日本导演黑泽明有所谓“摄影师的工作,要让观众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之论,但这却并非说明摄影机能够再现完整的现实,甚至相反,几近透明的摄影机时常逃脱不了历史/现实叙述话语的操纵。他的《罗生门》,围绕着“武士被杀”这一事件展开。强盗多襄丸,武士的妻子真砂、武士武弘和樵夫,都是“武士被杀”这一事件的当事者或见证人,但他们所提供的本文却充满歧义,相互矛盾。四个不同的见证人有四种不同的叙述。历史真相的揭示却成了历史迷雾的形成,询问调查过程是无法再现事件真相与重重迷障设置的过程。陈述历史的真相反而堕落于历史的迷宫。这或许是由于影片在“武士被杀”这一历史事件的探究时,是以对事件的叙述者的询问调查展开,人们对“武士被杀”这一事件的“询问调查”,只能在“语言”中进行。这便意味着历史/现实,也只有转换为语言才能进入人的视野。而任何历史的叙述必然因为叙述者的欲望、动机或潜意识而使得历史话语无法再现历史的真实。在《罗生门》中,黑泽明的“感觉不到”“存在”的摄影机实质上是受叙述话语操纵着,在各自利己欲望中编织着欺世盗名的谎言,使历史注定是一座永远走不出的迷宫。对“历史真实性”的关切最终只是一切空。
麦茨在其著名的《故事与话语》中,将19世纪的历史小说与历史电影建立起一种可类比性。“就像布满着情节和主人公的19世纪小说一样,电影在模仿着它,电影是19世纪小说的延续,并取代了后者”。(注:麦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87年北京第1版。)19世纪历史小说的基本特征,用卢卡契的话说:“历史小说不在于重述伟大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将史实中出现的人物以诗的方式加以复活”。(注:Donden,"The Historical Novel",1962.)应该说,好莱坞的经典电影对历史的表达正是表明了它与19世纪历史小说的深刻关联。作为文字出现的历史小说写作与作为视听形象出现的历史电影写作都是在某一特定语言/生存状况下“重述”历史的尝试,就其本质,对历史的“再现”与一切历史写作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在再现着在特定文化/语言状态中文本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运作过程,而不是所述历史时空的“真实”。若有区别,只是电影通过整个“机器”的复杂运作,创造了远比小说更能让观影者信服的途径,在银幕的背后更加深刻隐蔽着历史重新编码者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陈述,观影者在对银幕影像声音的沉醉幻觉之中,更容易以为重历了历史的发生过程。
实际上,海登·怀特对历史写作的讨论,早已帮助我们探索了历史叙述的虚构性。在他的代表作《元历史》中,怀特认为,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都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这个历史文体的深层结构“从本质上说是诗性的,而且具有语言特性”,(注: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isity Press,1973.)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历史文本叙述活动不可能是超然的、绝对的,必然与其语境有关,与意识形态和语言的运作方式有关。因此,对“历史真实性”的每一次关注,不过是叙述者所处的当代语言/生存处境下的回应,我们对历史的判断源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背景与美学立场,而非某种认识论的“真”。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历史陈述就其本质而言,可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甚或毋宁是想象力的产物”。(注:"Ledisco-urs de phistarie",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6.4(1967).)正是在“想象力”这一点上,历史的话语写作与历史的电影写作找到了共通点。历史电影并不因为它是一种艺术而失去书写历史的权力,相反的更因为想象的真实还原程度比谁都高而更具有影响力与震撼力。
“我们若要研究所有的历史,我们必须先解答一个迄今未提出的问题:‘历史为谁而存在?’这问题看来是荒谬的。因为很明显地,历史为每一个人而存在,每一个人及其整个的存在与意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注:《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揭示的深刻之处,在于提出“历史为谁而存在”这一深刻命题。历史为个人而存在,其真正意义不在于历史存在的终极目的,而在于暗示了一种属于个人的可能和权利——即虚构历史的可能与权利。个人对历史的解说方式,事实上已成为主体与历史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不是主体对历史存在的被动描述,而是主体依凭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作出新的编码。
人类对过去历史的占有只能通过人类的主体选择,借助语言中介进行描述。因此,对历史的任何描述只是一种人类的记忆,这种追忆无法以还原的面目出现,而是被诉诸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虚构。
诚如福柯所认为的,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我以为”的话语的历史,历史的逻辑在叙述游戏中,被处理得颠来倒去,假假真真。历史成为一种虚构游戏的娱乐存在。
二
把历史说成是虚构游戏的娱乐所在,这是许多维护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人所无法的接受的。对于一个曾经创造过《左传》、《史记》这样卓越历史文体的国度,深厚的编史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明,无疑促使中国人更加关注历史本身。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魏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记述历史的基本框架与叙事原则。无论是记录史实还是讲说演义,都是以道德褒贬的叙述原则构成。在伦理评判的前提下,历史不再是单纯的“事实”或“根据”的信史,而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寄托着历史叙述者的喜怒爱憎,人生感怀与政治意识。
鲁迅在谈到《故事新编》时说:“对于历史小说,则以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艰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须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得水,冷暖自知’”。显然,鲁迅笔下的大禹、后羿、伯夷、孔子等故事,是他所体察到的现代社会人际冷暖世态炎凉的话语表达。其实,鲁迅以及新文艺的后随者,在以历史为叙述对象的文体中,在展示历史本然图景的同时,更加追求的是表达叙述者在特定意识形态要求下对历史的理解与批判,换句话说,他们面对历史是在承担其启蒙与救亡这一二十世纪双重时代命题中对历史的某种“再现”尝试,某种寻找对这一时代的进行重构和再编码的努力。历史,成为新文艺家(小说家、电影家)对现实关注,变革愿望,政治革命的实现形式。可以说,这种历史/文艺观念及其表现模式成为五四以后中国新文艺(文学、电影等)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范式与价值标准。
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代表了一种新历史的改写,同时也是一种革命政治的选择。当新政权的缔造者回溯历史时,“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代表历史进步的社会政治革命成为一种必然与胜利的自豪。因此,围绕了权力主导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无形中便要求新中国文艺对原本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图景进行单一化的处理:许多时候,历史的复杂性被简化为单一的社会政治历史图景;历史的丰厚性逐渐被一种革命化的历史注释所代替,革命化的文本几乎占据了历史叙述的整体。“文革”前中国电影,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史学记载,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形象化解说,可以说体现了国家政权的一种理想,用电影来阐释历史或者在银幕上再造历史。当历史电影按照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编码系统来书写时,历史/电影达到“共谋”:历史语境制约了电影文本的写作,电影文本的写作又重新编造了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情境。而那些无法成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的理想抒情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则受到排斥。由于以阶级斗争视角去观照丰富生动的社会历史生活,从而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历史话语的固定模式,并指称为“历史的真实”。现在看来,这种以政治、阶级的评判所构成的叙述原则,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历史叙事模式,是一种对历史的单一化处理,它可能具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叙事文本再次火爆。伴随着文学创作与电影电视媒介的积极参与,反观历史成为中国20世纪文艺终结时期出现的一个热闹景象。尤其是电影中历史叙事所呈现出的的历史观念的演化与多角度审美追求,无疑给中国文艺带来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有益的探索。应该说,与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互动的中国当代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宣告了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文化、代表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品格的大众文化,开始在各自明确的文化版图上守卫自己特定的文化意图和话语表达。在这股历史电影创作热潮中,其对历史所作的时代反省与独特的历史虚构与游戏给观影者留下独特的风采。
第五代电影的90年代主题,常常热衷于讲述一个年代久远的家族故事——封闭的宅院,宅院中残酷和原始的情欲仇杀。这显然是原本被权威历史话语的叙事/修辞策略所遮蔽与遗忘的。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遮蔽下,具体生动的个人,家族的兴衰,心灵化的情感历史被弃置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等等,从单纯的社会压迫转变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上来,从阶级矛盾与政治斗争的层面转变到作为人自身的性变态、心理压抑,甚至上升到国民性格“劣根性”评判,电影以新的姿态参与历史“排演”,实现与历史的互动。陈凯歌《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命运遭际所跨越的近半个世纪复杂的艰难却通过程蝶衣对于段小楼那种超乎寻常的迷恋所暗示的“同性恋”故事而在银幕上产生巨大视觉震撼力;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企图把一群无法无天的少年冲动制作成“文化大革命史”的原因所在,对人性痛苦的历史记忆被挤出视觉流畅的观影空间,而尽情洋溢着荷尔蒙的冲动;《红粉》将历史写在观众对“妓女/性”的想象性空间里;《红樱桃》把纳粹的人性的罪恶历史,写在少女楚楚那贞洁的裸背上;《秦颂》以儿女之私的情杀演义着历史上义节之士的复仇故事。这种反叛传统史传精神的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不再把历史当作严肃的、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来对待,而随意虚构与游戏历史。他们戏说历史、演义历史,对历史充满了生动的挑逗和自由想象的欢快宣泄。
《三毛从军记》、《古今大战泰俑情》更是在影像活动可能性上,把历史从人的记忆深处放逐出去,并把“历史”交还给大众感官的直觉活动及其娱乐性满足。其中历史的影像虽然清晰,但在颠来倒去,真假难辨的历史逻辑中却是凸现出叙述的游戏策略。《三毛从军记》让漫画中的三毛置身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空间之中,通过征兵、军训、狙击和嘉奖等这些战争中典型的事件,使得漫画中的三毛拥有某种历史感。正是在这种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本之间展示叙述,使得历史及其战争都成为一场游戏。因此,当我们看到三毛套着成人的肥大军装在军训,以斗牛闯敌阵大获全胜而发出笑声时,历史已经不再有负荷沉重的原罪,不再具有试图回归所谓终极的目的。程小东《古今年内大战秦俑情》中,二千多年前监管营造皇陵的秦朝将领蒙天放与东渡蓬莱寻觅仙丹的美人韩冬儿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穿越时间的隧道,被移置到了本世纪30年代,古时的英雄美人生离死别,在两千年后现代重演恋情,远古的豪气和柔情沿袭至今。“复活”了的蒙天放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笑话百出,而当年自焚殉情的韩冬儿却转世而成三流影星,对风流倜傥的大明星白云飞百般献媚,山盟海誓的古典爱情悲剧而今成了三角恋爱的现代喜剧。这里,古典与现代两套文化代码相互游戏,让历史摆脱时间的束缚而纵情于想象的自由和生存的娱乐。
90年代以来,诸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戏说慈禧》、《包青天》、《新白娘子传奇》、《新龙门客栈》、《唐伯虎点秋香》、《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视剧作无不以“古今游戏”的面目出现,这在文化潜意识深处体现了当代大众文化中逃出时间序列的需要。大众文化中怀旧的产品和幻想产品一样,不是把历史还原和预测未来,而是现在对过去将来的侵蚀,现在成为唯一存在的时间,诸如科幻题材的大众读物、影视作品,通常用未来不可知的年月和遥远不可及的星球抹去时间感;当代武侠故事中出神入化的武功也要以时间感的剥夺为条件。大众文化致力于时间感的解构和对现在的着力扩散,无非告诉我们,历史是虚构的,人们唯一拥有的就是现在,是现在而不是未来包容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