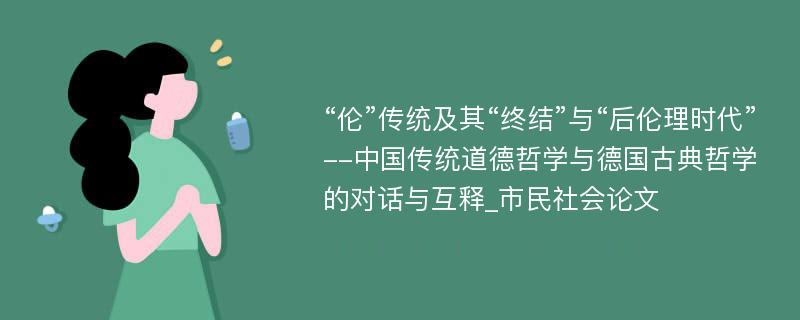
“伦”的传统及其“终结”与“后伦理时代”——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与互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德国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伦理观念”与“关于伦理的观念”
如果用一个字诠释中国传统伦理的精髓,那就是“伦”;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现代中国伦理所遭遇的根本性挑战和最大难题,那也是“伦”。
孟子曾经这样诠释伦理的发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段依据传说并带有明显思辨色彩的解释,日后之所以被奉为伦理的经典并积淀为中国伦理的传统,就是因为它揭示并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最为重要的文化内核和道德哲学基石:中国伦理在人兽之分的意义上给人性立论;“人伦”,是人兽之分的根本,是人自我肯定即“肯定自己是一个人”的根本;“教以人伦”,是超越“近于禽兽”的文明忧患的根本解决之道。由孟子这段话可以演绎的结论是:“伦”,准确地说,“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始点。可以支持这一立论的直觉根据是:中国哲学将“伦理”与“道德”相接相连,“伦理道德”是从“伦”开始的。所以,如果借用孔子的话语方式,那么,“伦”或者说“人伦”,就是中国传统伦理与伦理传统的“一以贯之”之“道”。
时至今日,中国的伦理传统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无论揭示还是研究这些变化,以往的努力往往都聚焦于伦理的现象形态,尤其是伦理观念和伦理存在(如伦理关系、伦理生活等)诸方面,结果正如人们已经感受到的那样,虽然可以现象地部分复原已经发生的变化,但解释和解释者本身最终却不幸陷入解释的“碎片”之中,而不能为这些变化提供完整的现象学图景和更具哲学根据尤其是精神哲学根据的合理而有力的解释。其原因在于:解释的触须只游刃于“伦理现象”而未深入到“伦理本身”,即伦理的概念或人们关于伦理的观念经过时代的涤荡在道德哲学层面所发生的那些更具根本意义的变化。造成这种状况的逻辑原因是,无论“伦”还是“人伦”,都内在着两种可能的规定或理解:一是现象形态,主要是伦理观念和伦理存在;一是概念形态或本质形态,即“关于伦理”的观念、理念、信念等等。
我的观点是: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为彻底和最为深刻的变化,不在伦理观念和伦理存在方面,而在人们关于伦理的观念和“伦理”方式方面;当代中国伦理发展与道德建设的最为深刻的难题,不是关涉伦理观念、伦理生活和伦理关系方面的重大改变,而是关涉伦理本身,关涉人们对伦理的观念、理念和信念,即人们对“什么才是伦理”、“如何达到伦理”等哲学规定方面的根本性改变。一句话,在伦理传统方面发生的最深刻、最重要但未被充分揭示和研究的变化,不是在人们的“伦理观念”方面,而是在人们“关于伦理的观念”方面。“关于伦理的观念”,概而言之,就是所谓“伦理观”。
“伦理观念”和“关于伦理的观念”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域:前者虽具主观性与内在性,但仍处于现象界;后者则是人们关于伦理的概念、理念和信念等更具形上意义的问题,是伦理观的问题。中国伦理传统在经过近现代古今中西交汇的百年沧桑之后,最需关切而又最缺少关切的就是对于“关于伦理的观念”的变化的反思。当伦理观念和伦理存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持续不断的巨变之后,传统的变革已经深入到“关于伦理的观念”这个对传统更具颠覆力的层面。“伦理观念”的变革已经发生,“关于伦理的观念”的变革正在发生。
现代中国道德哲学“关于伦理的观念”的最深刻的变化,首先并集中表现在“伦”或“人伦”方面。
二、“伦理”的道德哲学本性及其两种观点
如何把握“伦理”的本性?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黑格尔,1996年a,第173页)黑格尔这里讲得很绝对:“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显然,他肯定“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否定“原子式探讨”的观点,而否定的理由只有一个:它“没有精神”。
如果黑格尔的论断具有真理性,那么,“从实体性出发”和“原子式探讨”这两种“永远”的可能,便是共时又历时的两种“关于伦理的观念”和伦理方式。
“从实体性出发”的真义是什么?我们先来看黑格尔讲这段话的语境。这段话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和展开他的一个立论:“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同上)伦理性的实体即家庭与民族,家庭与民族的现实精神就是伦理性实体的真理性的自我意识;由此,“从实体性出发”的基本内涵就是从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或伦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伦理的现实性在于它在实体性中扬弃个人的抽象性。“伦理性的东西不像善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强烈地现实的。精神具有现实性,现实性的偶性是个人。”(同上)“精神”为何具有现实性?“精神”何以使“伦理性的东西”具有现实性?因为“精神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精神使“伦理性东西”中的个体与伦理实体达到统一,使伦理实体的现象性存在与它的实体性概念本质达到统一,从而使伦理实体具有现实性。由此,从“实体性出发”的真义,也就是从“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精神出发,亦即从“家庭与民族的现实精神”出发。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伦理本性的揭示更为直截了当:“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同上,1996年b,第8页)。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家庭与民族作为“普遍的东西”的伦理性或它们作为两个基本伦理实体的本质,不是指家庭与民族中个体性成员之间的自然关联,而是这些自然关联的“精神本质”,即个别性的人与家庭或民族这两个实体之间的那种“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的那种“现实精神”。换句话说,个别性的人只有作为家庭成员或民族公民而行动时,亦即从家庭与民族的“实体性出发”而行动时,才是伦理性的存在。“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同上,第9页)黑格尔在这里为伦理、伦理关系和伦理行为提供了一个判断标准:伦理不是个别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个别性的人与他们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伦理行为不是个体与个体相关涉的行为,而是并只是个别性的人与他的共体或公共本质相关涉的行为。一句话,伦理就是个别性的人作为家庭成员或民族公民而存在;伦理行为就是个体作为家庭成员和民族公民而行动。
黑格尔以家庭关系诠释“伦理是本性普遍的东西”的抽象规定。在家庭伦理实体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不是情感关系和爱的关系”,而是“个别性的家庭成员”与“对其作为实体的家庭整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澄清了一种混乱与误解,即将家庭伦理关系当作个别性家庭成员如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间的情感关系或爱的关系。家庭伦理关系的本质是个体与家庭实体之间的关系,其精髓是“个别家庭成员的行动和现实”“以家庭为其目的和内容”(黑格尔,1996年b,第8-9页)。
黑格尔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规定,很容易让人想起《论语》中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种“亲亲相隐”的著名伦理逻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何“直”之有?“直”于什么?根据黑格尔以上关于伦理本质的规定,意思就很明白了:它“直”面家庭的伦理实体本性,“直”就直在在家庭伦理实体中个体作为家庭成员而行动的伦理诉求。如果将伦理当作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那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显然就是非伦理和不道德的;但是,如果将伦理理解为个别性的人与他的伦理实体之间的关系,那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在特殊境遇下“直”面伦理的本性,是伦理本性的特殊显现,是家庭成员“从实体性出发”在特殊境遇下对于伦理本性的固持。这句话可以作如下道德哲学上的演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伦理就在其中,伦理的真谛就在其中。孔子以一种极端的情境彰显了家庭伦理的一个根本要求和绝对逻辑:“个别家庭成员的行动和现实”“以家庭为其目的和内容”。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伦理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假设如果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而行之,那么,结果便是两个:瓦解家庭的自然伦理实体性;个别性的人丧失作为“家庭成员”的伦理本性和伦理资质。争议在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现实后果是一种道德上的恶。但是,其一,如果将孔子这段话理解为对伦理本性的道德哲学诠释,那么其真理性与合理性便显而易见;其二,即便它会造成个体道德行为的恶,但与伦理实体的本性丧失的“大恶”相比,它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因为,家庭作为直接的和自然的伦理实体,是全部伦理的基础,因此家庭伦理实体的瓦解必将导致整个伦理世界的崩溃,其严重后果已经在历史上的诸多社会试验包括中国“文革”时期的伦理生活中得到体现。
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伦理作为“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本性集中体现和表达为一个“伦”字,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伦”或“人伦”正是“从实体性出发”“考察伦理”的观点。无论在道德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生活世界中,“伦”或“人伦”的内核都指向由个体之间的诸多关联所构成的实体,其真义并不是指个别性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指个别性的“人”与他所处的那个实体性即“伦”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伦理关系,不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伦”之间的关系,所谓“人伦”是也,其现实性是个体与他所处的伦理份位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安伦尽份才是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而按照伦理实体要求而行动的“正名”,自孔子以来就是应对伦理失序的基本对策。台湾学者黄建中在其《比较伦理学》中,对“伦”与“伦理”作了比较详尽的辞源学考证,他认为,“伦为人群相倚待相倚之生活关系”,“伦理者,群道也”(黄建中,第21、25页)。“伦”是人与他所处的群体的关系,也是个体复合为群体的关系。“伦”的关系虽然是具体的,在传统社会中具有范型意义的是“五伦”关系,但无论父子、兄弟、夫妇的家庭伦理关系三伦,还是君臣、朋友的社会伦理关系二伦,其要义都不是单个的人如父与子之间的关系,而是父或子与他所处的父子关系的复合体之间的关系,即父或子与父子之伦之间的关系。由于单个的人在不同伦理情境中具有多重伦理角色,因而人伦关系根本上是“人”与“伦”即人与伦理实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伦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之所在,否则便是“不伦”、“乱伦”。中国文字以“辈”、以“类”、以“序”训“伦”①,实体、秩序、区别都是内在于“伦”的概念规定,这些规定所体现的道德哲学方法的根本要求就是:“从实体性出发”。
以上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伦”是中西道德哲学传统“在考察伦理时”的方法论或把握伦理真谛方面的会通点,也是古今中西道德哲学和伦理传统的基本会通点。
三、“伦理”的现象形态与“伦”的传统的“终结”
考察“伦”的传统概念裂变也许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直观的办法是分析它在现象领域即伦理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化。
“伦理世界”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一个道德哲学概念,其本意不仅指伦理作为“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现象形态,也是指他所说的客观精神的自在形态。在他看来,伦理世界是由“伦理实体”、“伦理规律”和“男人、女人”构成的“无限和整体”。家庭与民族是“伦理实体”的两种形态,它们是“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实体性表现或外化;家庭与民族分别遵循“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这两大“伦理规律”或伦理势力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过渡,由此造就伦理世界的整体;“男人、女人”是伦理世界的两个“原素”,在伦理性质上分别指向家庭与民族两个不同性质的伦理实体,在伦理世界的缔造中构成结构性的互补。这样,“诸伦理本质以民族和家庭为其普遍现实,但以男人和女人为其天然的自我能动的个体性。”(黑格尔,1996年b,第17页)
黑格尔在思辨中所建构的“伦理世界”的概念,经过文化翻译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伦”的世界。伦理的自在形态是伦理实体。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家与国构成社会的两极,因而家庭与民族作为两大基本伦理实体,便不仅是黑格尔式的道德哲学思辨,而且是直接的历史现实性。伦理的自为形态是伦理规律。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世界的两大伦理规律,即“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在中国道德哲学的话语系统和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中便是所谓“天伦”与“人伦”,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天道”与“人道”。② 天伦与天道是家庭伦理实体的规律,人伦与人道是民族伦理实体的规律。伦理的自在自为形态是伦理精神。伦理精神是使“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从而达到“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那种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将伦理与道德相连,形成“伦—→理—→道—→德”的伦理精神发展的辩证过程。“伦”是自在的普遍性即伦理实体。“理”与“道”可以诠释为自为的普遍性,即伦理规律。其区别在于,“理”是意识形态或在意识中把握的普遍性或伦理规律,“道”是意志形态或冲动形态的普遍性与伦理规律,二者构成“精神”的一体两面。“德”则是既自在又自为的伦理普遍性。“德者,得也。”“得”什么?得“道”,“德”就是“伦理上的造诣”。由此,伦理的实体便内化为道德的主体,伦理普遍性便外化为既自在又自为的伦理精神。
这样,伦理实体—→伦理规律—→伦理精神,便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伦理世界。这是一个中西方民族、中西方文明共有的世界,也是一个在传统社会中已经证明是可以共享也应当共享的世界。
“伦”的实体性内核“伦理”作为“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本质,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概念基础,也是中国伦理“关于伦理”的根本观念与信念。以实体性和“本性上普遍的东西”为概念规定的“伦”,构成了中国道德哲学和中国伦理精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文化气质和民族特质。然而,随着传统伦理的终结,随着伦理传统的不断被涤荡和摧廓,“伦”作为“本性上普遍的东西”的概念与观念传统逐渐被消解,甚至在相当意义上“退隐”和“终结”。这种情景与现代性的西方伦理具有十分相似的性质,它是现代中国道德哲学与伦理精神建构面临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难题与挑战。
伦理实体以及关于伦理实体的观念方面所发生的最大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所谓“市民社会”及其概念的出现。“市民社会”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概念。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伦理实体有家庭与民族两个形态;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伦理实体的结构。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在《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很强思辨色彩的过渡性质的伦理实体,是伦理实体的否定性环节。但是,在后来尤其是当代学术研究中,“市民社会”却成为现代社会的特质,甚至被用来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事实上,无论是在黑格尔的原意中还是就概念本身而言,市民社会都是伦理世界与伦理精神的“法权状态”。法权状态是社会的“原子状态”,其基本伦理特质是原初实体性的丧失,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认为只有过渡到国家它才具有合理性。个别性的人以自身为目的而形成的“需要的体系”,以及个体与个体互为中介而构成的形式普遍性,是市民社会及其伦理实体的两个基本原则(参见黑格尔,1996年a,第197页),所以,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市民社会”否定了家庭伦理实体的自然质朴性,但还没有达到民族国家的伦理实体意识。“市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工具性和原子式的伦理实体的自我意识,与“家庭成员”和“民族公民”的伦理实体意识具有原则区分。与家庭和民族相分离的抽象的市民社会观念,可能既是对家庭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消解性因素,也是对民族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消解因素;而当遭遇全球化思潮和浪潮时,它便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消解性因素。当今中国“伦”的观念和伦理实体性意识的动摇和消解,在伦理世界和伦理生活中的第一种表现,便是抽象的市民社会意识的生成,以抽象的“市民”取代“家庭成员”和“民族公民”的伦理实体意识。③
“伦”的传统的消解和伦理实体的退隐在伦理规律方面的体现,就是“人伦关系”向“人际关系”的蜕变。“人伦”是“伦”的传统及其观念的基本内核;“人伦”的本质是个体性的人与“伦”即他的实体的关系;“人伦关系”概念的道德哲学精髓,是以对人的“实体性存在”的肯定为前提的。而“人际关系”作为现代性的概念,以对个体的殊异与对立及对个体“原子式存在”的肯定为前提。现代道德哲学和伦理生活中“人伦关系”概念的退隐和“人际关系”概念的兴起,表征着对传统伦理世界中“天伦”、“人伦”伦理规律的否定以及一种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人际”伦理规律的生成。“人际关系”的概念代替“人伦关系”,表征着“人际”伦理规律取代了“人伦”伦理规律。这种变化可以从婚姻伦理观念中窥见一斑。现代婚姻关系之所以不稳定、离婚率呈上升趋势,一个道德哲学上的重要原因在于:现代人往往只是将婚姻关系看成男女两个个体性存在之间的原子式关系,或者是两个单子之间的“情感或爱的关系”,而不是看成婚姻中的个体性存在与婚姻所构成的家庭实体之间的关系。于是,离婚便成为两个单子之间的私事,其中任何一个单子都可以对婚姻行使否决权,甚至在此过程中可以不考虑婚姻关系中的第三相关者如子女的利益和命运,从而使婚姻关系逐渐丧失其伦理性。婚姻伦理观念中实体性意识的丧失,是现代家庭关系日趋脆弱的道德哲学根源。
伦理精神方面变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感和伦理能力的式微。伦理这个“本性上普遍的东西”,透过“精神”才能达到个体与实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然而,在“市民社会”中,人们正愈益沦为“无精神的单子”,“伦—→理—→道—→德”中那种向实体的回归和冲动,逐渐为“利益驱动机制”所取代,从而形成“个人利益的战场”。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伦理”与“道德”的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分。“伦理”向“道德”转换的实质,是由实体向主体,即由外在实体性(普遍性)向内在实体性(主体性)的运动。市场逻辑改变了这一运动的道德哲学意义,这种改变可以从“德性论”向“正义论”的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中获得启示。传统德性论的道德哲学精义是强调个体至善,强调“德”作为“伦理上的造诣”的道德哲学意义;正义论的道德哲学精义是强调社会至善,强调社会合理性包括伦理合理性对个体德性建构的意义。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德性论强调实体、伦理普遍性对个体的绝对意义;正义论本质上以个体、确切地说以“集合并列”的个体存在及其判断为“普遍物”的绝对价值,“正义”的结果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市民社会”中个体利益的博弈。如果说极端发展的德性论可能导致伦理专制主义,那么,极端发展的正义论则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与伦理虚无主义。德性伦理精神向正义伦理精神的演变,伴随着也表征着“伦”的传统的解构和社会的伦理同一性能力的式微。
“伦”传统的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是黑格尔所说的“考察伦理”的“观点”的变化,或“关于伦理的观点”即伦理观的变化,变化的实质是在道德哲学的方法论方面由“从实体出发”演变到“原子式探讨”。自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社会与西方伦理日益消解其实体性,造就了一个以法权社会为基础的“原子式探讨”的伦理观念和伦理世界。经过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沐浴,中国社会在不断解构“伦理的传统”的过程中,也逐渐解构了“关于伦理的传统”。可以说,中国社会虽然没有经历西方式的现代性,但“原子式探讨”的现代性的“关于伦理的观念”,已经侵蚀并颠覆了“从实体出发”的“伦”的传统。应该说,中西方伦理发展中的这种历史演变从一开始就概念地或逻辑地内在于“伦理”之中,否则黑格尔也不能如此武断地说“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西方伦理的这种演变早就为黑格尔所思辨地预言。
四、“后伦理时代”及其“集体记忆”
现代中西方社会“关于伦理的观念”以及由此所建构的伦理世界,愈益具有“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性征。问题在于,“现存”的这种演变是否具有现实性与合理性?黑格尔用一句话描述了“原子式探讨”的特质:“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也用一句话击中其要害:“没有精神”,“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原子式探讨”的伦理观也试图并努力达到伦理的普遍性,但它将个体视为单子即原子式的存在,试图透过某种外在性如规范、法律、利益(即市民社会中的所谓“需要的体系”)等建立同一性与普遍性,最终只能做到无“精神”的“集合并列”,而不能达到“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所以,“原子式探讨”的最为严重的缺陷在于人与它的实体性本质或个体与实体相分离和对立,它使伦理也使社会丧失自己的同一性本性和同一性能力。现代社会中愈益深重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与分裂,在道德哲学上就是“原子式探讨”的伦理观的必然后果,是人与他所处的自然实体、社会实体和生命实体的对立与分裂。
内在于“原子式探讨”的伦理观中的这种深刻缺陷,要求人们超越“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这种缺乏创造性和反思精神的思维定势,对正在伦理世界和伦理精神中发生的深刻变化采取批判的态度。前文已经指出,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深刻的伦理变革,不是表现在人们的伦理观念、社会的伦理存在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伦理传统方面,而是表现在关于伦理的概念、观念、理念、信念方面,是“关于伦理的观念”或所谓伦理观的根本改变,即由“从实体出发”并指向实体的、绝对的、神圣的伦理概念、观念、理念、信念,向从个体出发并指向个体的自我的、主观的、相对的、世俗的伦理概念、观念、理念、信念转化。伦理的概念不再是“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而是原子式个体的“集合并列”;伦理观念和理念的灵魂不再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精神,而是个体性的固持;伦理信念的内核不再是个体内在的实体性或普遍本性即所谓“德”的建构,而是个体性与个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从根本上“祛魅”了,一种伦理“终结”了,社会似乎进入了一种“后伦理时代”,至少具有某些“后伦理时代”的特征。“后伦理时代”是消解伦理的同一性和神圣性、代之以主观性和世俗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说的那种“伦理的神”退隐了、死亡了。它不是一般的“伦理失序”或“道德失范”,也不是一般的无伦理,而是像尼采所言说的:我就是伦理!我就是道德!正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坚持和坚信自己的主观而缺乏客观公度性的良心,结果都“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这是“原子式探讨”的“法权状态”所奉行的必然逻辑。
因此,对于现代中国伦理变革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敏锐地发现并指出在“关于伦理的观念”即伦理观方面发生的那些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而不应将研究的触角只流连于“伦理观念”的那些现象层面的变迁;二是对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关于伦理的观念”的变化进行反思性批判,合理而能动地引导这场变革。如果说一场伦理观方面的“悄悄的革命”正在发生,那么,亟待进行的是关于这场革命的再革命。伦理观的变革——在中国集中表现为“伦”的观念传统的变革,这当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这个变革留下的最大难题是伦理普遍性与社会同一性的解构与重构。一些智慧的伦理学家已经发现这个基本难题并对此作出了回应,如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一定意义上便可视为在“原子时代”和“法权状态”下建构伦理普遍性与社会同一性的努力。
胡适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说过,新思潮本质上是一种新态度。“关于伦理的观念”或伦理观变革的关键,是形成对待“伦”的传统的新的合理态度。关于传统的意义认同也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法国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个复杂而重要的难题的诠释与解决。哈布瓦赫认为,任何记忆实质上都是“集体记忆”,它必须透过对集体生活及其情境的表象而被唤醒。如果将这个概念移植到道德哲学中,一种新的解释便是:传统,尤其是伦理传统,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精神历史的“集体记忆”。伦理同一性的丧失、伦理精神的式微,最终将消解民族凝聚力而使之陷于涣散的绝境;而对传统的根本的和无节制的否定,则标志着一个民族彻底丧失自己的记忆和记忆能力,这个民族将成为无历史、无延续能力的无精神、无灵魂、无同一性的存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关于伦理的观念”或伦理观方面的深刻变化,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唤起人们对“伦”的传统、对伦理作为“本性上普遍性东西”的“集体记忆”,否则一旦失忆,我们就只能成为无根源、非现实的单子式存在。这就是本文对中国道德哲学“伦”的传统进行梳理的意旨所在。
注释:
①许慎《说文解字·人部》曰:“伦,辈也。”杨琼《〈荀子·富国篇〉注》:“伦,类也。”赵歧《〈孟子·离娄下〉注》云:“伦,序。”
②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天伦-人伦”与“天道-人道”的范畴既相通又具有不同的指谓。前者一般就伦理而言,后者一般就道德而言,二者在交叉重叠中也具有彼此不能包含的某些内涵。
③我并不一般地否定和反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市民”意识,更不否定市民社会问题讨论的学术意义,而只是认为,如果脱离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民族)”的伦理实体的辩证结构,无论“市民社会”还是“市民”都将变得抽象而不合理,消解了伦理的实体性本质。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道德哲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精神现象学论文; 文化论文; 法哲学原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人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家庭成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