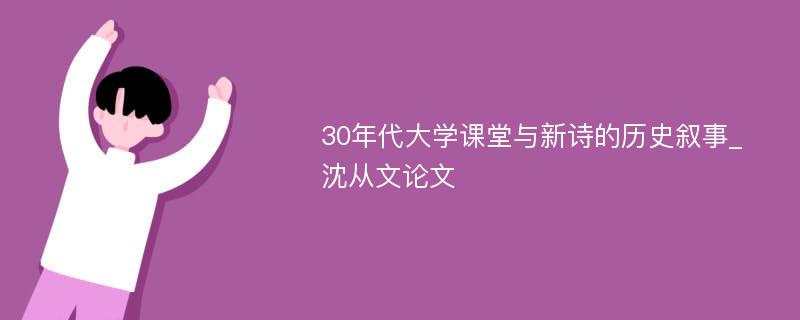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课堂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97—08
一、从“看不懂的新文艺”说起
1937年6月13日,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238号上,梁实秋化名“絮如”,以一个中学教师的口气,发表了一封题为《看不懂的新文艺》的来信,指责“现在竟有一部分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做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在编者的后记中,胡适也对“絮如”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胡、梁二人的搭配出演,在当时的北平文坛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不仅有周作人、沈从文撰文为“看不懂的新文艺”辩护,就连“像老衲似的废名,激于义愤,亲找胡适,当面提出了强烈质问”。这场论争涉及的诸多问题,如现代诗学观念的演进、新诗阅读的困境、两代诗人的差异、乃至具体的文坛纠纷,后人已多有阐发。然而,在论争背后,似乎还有另一条线索较少被论及,那就是梁实秋对“中学教员”身份的冒用。从这一虚拟的身份出发,梁实秋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所谓“看不懂的新文艺”,已不仅是新文学内部的问题,它的恶劣影响已波及下一代人(中学生)正当文学趣味的养成。正是因为“教育”层面的忧虑,他的责难也有了更充分的根据。
在新文学的发生与确立过程中,“教育”因素的介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教育部规定国文教材改用国语,还是国文课本里选入新文学作品,都不仅在传播的层面扩张了新文学的影响,还以一种制度的方式,确立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如果说针对“看不懂”的责难,无非是新诗批评中常弹的“老调”,那么梁实秋的发难方式——暗中调动“教育”的潜在权威,倒是颇具独创性。“新文艺”的辩护者们,如周作人、沈从文,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各自的回应。尤其是沈从文,他不仅激烈地反驳梁实秋的观点,还将中学教员与新文学的隔膜,归咎于培养“中学教员”的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疏忽,最后呼吁大学打破惯例,开放课程,接纳“至少有两个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①。在文章中,沈从文还提到新文学的发展过快,致使一些老前辈已“渐渐疏忽隔膜”了,矛头所指耐人寻味。身为“老前辈”的胡适或许受了一点刺激,在编辑后记中也不忘反讽一下:“现代文学不需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②
沈从文的呼吁与胡适的反诘,在某种程度上已偏离了争论的主线,勾连出了另一重背景:在30年代,“新文学”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已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与此相关,为了满足现代教育“知识生产”的需要,新文学史的写作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潮”③。在这个背景下,“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一句,当然也是有所指向的:20年代末,沈从文正是因为胡适的推荐,才进入中国公学讲授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而他讲授的重点也是研究“价值”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的新诗④;在这一场论争中,曾经找胡适当面理论的废名,此前也刚刚在北大的课堂上,进行了他对新诗的著名讲授⑤。对这些背景性因素的追溯,其实已使本文的中心话题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在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新诗作为“新文艺”的代表是如何进入、又是如何被讲述的。
二、“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也同时是一个知识的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空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因而,“新文学”在30年代被“大学课堂”接纳为研究对象,似乎也象征着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最终得到了某种认可,成为“高级”知识的一部分。对于这种“接纳”的程度,后人也难免会作乐观的估计。但事实上,在30年代“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即使已成为大学国文系里一句颇为时兴的口号,新文学在课程设置中的实际位置,并不十分理想。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为例,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开设,始于杨振声担任系主任的时期(1928—1930),不仅有朱自清自己主讲新文学研究,系主任杨振声也曾于1928年演讲过《新文学的将来》,并于次年客座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⑥ 然而,到了1933年,国文系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标发生了显著改变。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虽仍保留在课表里,但重心已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课,也是终止于这一年。以至几年以后,喜好新文艺的学生王瑶就抱怨:大学一览里所列的七八十门课程中,虽然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两门涉及“近代文学”,但也只是空留其名,“也有好几年没开班了”。⑦ 关于这一“变化”,相关的研究也只是交代了事实,而对于具体的过程则语焉不详⑧。
“新文学研究”在清华大学被打入冷宫,但毕竟开创了先河。与清华相比,北大国文系对“新文学”的接纳就晚了很多。虽然在30年代初,北大中国文学系制定的课表里已出现“新文艺试作”一课⑨,但它的性质仍属于“习作”练习,而非专门“研究”⑩,在北大国文系,全部课程分为共同必修科目、分组必修与选修科目、共同选修科目三类。三类课程内容有别、功能不同,在知识等级上自然也有所区分。“新文艺试作”就属于各专业可以自由选修的第三类,只有一个学分,位于学科等级的最末端(在课表中一般被排在最后)。可以参照的是,有关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却列为第二类分组(文学)选修课,地位明显高于“新文艺”。(11)
1932年,废名由周作人推荐,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他所讲授的就是“新文艺试作”这门课。虽然在1935—1936年,废名在此课之外又开出“散文选读”课(12),但多年来只承担一门“习作”,他作为教员在国文系中的影响力必然有限(13)。到了1936年下半年,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在1936—1937年度国文系的课表上,赫然出现了“现代文艺”一科,其课程的规划相对完整。在作品“鉴赏”之外,还有“批评”和“研究”,这一点与“新文艺试作”的习作性质判然有别。与此相关的,此课被列入文学组选修课的行列,从第三类进入第二类,“新文学”在学科等级中的位置,稍有上升。
上面谈及的虽然只是清华、北大两个学校,但反映的可能是“新文学”在大学里普遍的边缘化境遇。站在“新文学”的立场去评价,这种状况当然要归咎于大学国文系“守旧的空气”。但从换一个角度,这也与大学中文系特定的学科定位、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的相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在中国现代学科体制的建构中,“文学”作为大学的一个专科,它之所以能够凸显,起初就与一种维系文化传统的诉求相关联。(14) 大学之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都脱不了这一文化政治的制约。正如朱光潜在《文学院》一文中所阐述的:“大学教育对于文化学术有两重任务:其一为对于已有传统加以流传广布,以维持历史的赓续性;其一则为从已有传统出发,根据新经验与新需求,孜孜研究,以求发展与新创。”(15) 作为经典,古典文学体现的是民族的传统,对该传统的承袭与不断阐释,正是“文学”一科的价值与目的所在。因此,从目的上说,“民国以来的东西”本来就不在大学“文学”一科的范围之内,“不讲”显示了一种对学科边界的维护。
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所谓“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也可有两种理解:他表达的不仅是对“新文学”实际成就的怀疑,或许还有对其文化角色的看法。此期“新文学”在社会上已站稳了脚跟,甚至对一般青年读者产生巨大影响,但作为前卫的、激进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似乎尚不能在功能上凝聚民族精神、在角色上成为文化传承的经典。当它被引入大学,也只有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安全”(边缘)的位置上,才不至于破坏原有的知识秩序。后来,新文学能够成为显学,除自身实力的壮大、影响力的扩张之外,特殊意识形态条件下文学教育功能的变化,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或许正是因为面临“文学”学科内在的排斥,“新文学”课程的开设本身,就必须包含了自我辩护、说明的性质,以谋求学院知识等级中的一席之地。一个现象颇值得关注,那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新诗”往往是新文学讲授的重点。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新诗”一章就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精彩的部分。这与朱自清新诗人身份自然有关,但谈及这个问题时,王瑶还指出:“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是首先结有创作果实的部分,争论最多,受到的压力也最大。”(16) 要为新文学的整体合法性辩护,在新诗方面一定要费更多的口舌与笔墨。在他之前,杨振声也在清华发表过新文学的演讲,开场白之后就作出如下判断:在新文学包括的四种文体中,“最易成功,也最有成功的,为散文;次之为短篇小说,戏曲更次之,成功最难而也最少的为诗”(17)。这一“判断”本身无甚稀奇,但有意思的是,杨振声的演讲却从“成功最难而也最少”的诗开始,次序完全颠倒,最后甚至因时间有限,最能体现新文学“实绩”的散文和小说,竟然只字未讲。同样,沈从文1929年在中国公学开讲新文学,作为小说家的他也作了类似的选择,在1930年给友人信中这样写道:“去年到此就讲诗,别的不说。”(18) 后来,废名在他的《谈新诗》开篇,就开宗明义地道破了这一点:“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19) 他本来受命讲授整体性的“现代文艺”,结果还是全部讲了诗,后面的内容因为战争也只能中断。
或许这只是一些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不足以代表全部状态,但在偶然、个别现象的背后,也暗含了某种特定的文化逻辑。在学院的评价机制中,当新文学是否值得成为“研究对象”还是个疑问之时,开讲新文学首要的任务,自然就是解决新文学中合法性最成问题的一部分。新诗作为整个新文学的急先锋,在美学形式及文化形态上构成的反叛最为激烈,内含的现代性紧张也最为鲜明,这或许正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背后的逻辑所在。虽然在读者接受、社会影响的层面,新诗不及小说和散文,但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备受争议的“新诗”却成为学院研究、教授的重点,这样一种特殊的张力,就贯穿在30年代讲授“新诗”的大学课堂上。
三、系统讲授与“分期”的想象
在大学课堂上,新诗作为新文学的代表,勉强站住了脚跟。但是要解决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问题,除了要为它的自身文学价值、社会价值辩护外,还有一点也相当关键,那就是在大学课堂上,一种“有价值的知识”是必须能够被“系统”讲授的。正在发生的、不断流变的新诗以及新文学,能否被这种现代大学的知识方式容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大学里最初出现的“新文学”课程,给人一种鉴赏性、漫谈性的印象。然而,在大学课堂上,如果只是介绍、鉴赏、阅读,并不能真正提高“新文学”的知识等级,要进入学科的正统,它必须还要成为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纲要》严密详尽、体制完备,可以说十分完整地体现了一种将新文学研究化、学术化的诉求。也许因为他的影响,在当时“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的气氛中,他的学生余冠英的毕业论文,竟然是以新诗为题(20)。
然而,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文学”在大学里地位虽然不高,但要讲好、讲成一门“学问”,却并非没有难度,甚至难度还极大。30年代苏雪林在武汉大学任教,学校让她接手新文学研究一课,她起初并不情愿,因为深知教这门课任务之艰巨。困难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文学运动发生不过十几年,史料缺乏,不成系统;其二,所有作家都在世,创作还在发展,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其三,时代变动剧烈,作家思想、写作都流变不居,捕捉他们的面影如“摄取飓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后来,她被迫接手,果然“苦”字临头,为了编选讲义所费的“光阴与劳力”,比她同时进行的“中国文学史”多出一倍。(21) 对于她的前任——没有受过系统教育、阴差阳错登上大学讲坛的沈从文来说,压力的巨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1929年,沈从文由胡适举荐,进入中国公学任教。对于自己在学院中可能的位置,他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任职之前在给胡适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22) 此时的中文系,也正将“创造新的中国文学”列为办学的目标之一,拟订开出“现代中国文学”与“新文艺试作”两门课,(23) 如此,教学的需求与教员的能力,可以说一拍即合。依照一般的想象,一个新文学的作家讲他熟悉的新文学,应该随意挥洒,不受学院教法的羁绊。但事实上,在教学准备方面沈从文恰恰十分认真。据当时一位学生的回忆,沈从文虽然不会讲课,只在黑板上不断写字却说不出话来,“但他在上课之前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我看见学校图书馆里文学方面的书,差不多每本后面的借书卡片上都签了他的名字”(24)。现在看来,他编写的《新文学研究》讲义的确也体现出系统“研究”的特色:讲义正文分两个部分,前半部是依照新诗发展的不同阶段编选的分类引例,作为学生的阅读参考,后半部是六篇论文,分述六位代表性诗人。在学院体制无形的规训之下,像沈从文这样一位体制外的作家,也必得费心劳神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这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为课堂讲义,废名、沈从文等关于新诗的论述,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总会多少保留一些现场的风格。阅读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讲义,读者也很容易注意到他独特的行文风格,譬如,在文章的开头,常常就以一种定义的方式,确定某个诗人的位置,“以……的,是某某”的句式已成他个人文风的标记。这种“开门见山就作风格评定”的写法,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与课堂教学的需要相关,往往能够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个作家的历史位置(25)。然而,在特定的文风之外,课堂教学更为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他讲授的方式和内容上,有关新诗历史“分期”的讨论,就是沈从文一个核心的话题。
1930年10月,沈从文在《现代学生》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他在大学讲授新诗一个副产品。文章开头劈空而出一句:“要明白它,先应当略略知道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随后,文章就将短短十几年的新诗历史划分为尝试、创作、成熟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细分为两段,对每一期、每一段的特点及代表诗人也进行了细致、清晰地描述。虽然此文的目的只是“常识”的普及,但与一般的观念阐释、诗人介绍不同,为了塑造更为高级的“阅读”能力(“要明白它”),一种“系统”的历史研究的意图(“略知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也表露无遗:“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新诗,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在中国此时还无一个人着手。”(26) 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工作,沈从文是有相当的期待的。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他似乎也有着充分的觉悟。《新文学研究》讲义,虽然没有采用“分期”的框架,但三个时期的划分,仍潜在支配了沈从文的叙述:前半部的分类引例,每一组作品都对应于新诗的某一期、某一段,而在后半部分的诗人论中,谈到一个诗人,也要在相应的“分期表”以及与其他诗人的比较中确定其位置,一幅完整的早期新诗的历史图景,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出于大学教学的知识需要,沈从文的讲义明显多了系统性和研究性,从而与同一时期其他新诗论述区别开来。(27)
沈从文自认是对新诗进行“分期”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但对“新诗”尝试分期论述的,当时并非仅有他一个。早在1927年,饶孟侃应光华大学文艺团体新光社邀请,演讲《中国新文学》时,就将新诗历史分成尝试、过渡、入轨三期,分别以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28) 在30年代,新诗的“分期”问题似乎已成为相关讨论的热点,余冠英在《新诗的前后两期》一文中,甚至依照一般的论文惯例,首先做了一番“综述”:梳理了杨振声、朱自清、草川未雨、沈从文等人有关新诗的“分期”论述,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自己的观点(29)。废名开讲新诗,从《尝试集》、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一路讲下来,讲到冰心的时候,开篇就挑明:前面所讲的是初期新诗,现在要讲第二期了。(30) 虽然在立意上他独辟蹊径,但在讲法上也不能完全免俗,“分期”的想象仍然发生潜在的作用。
当然,历史“分期”是一般文学史著述都要涉及的问题,上述关于“分期”的讨论,也都发生于公共演讲、文学史写作、课堂讲授中。然而,对于新诗而言,“分期”问题似乎尤为关键。在发生之后的十数年内,新诗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充满了争议,只有被安排到某种具有内在线索的“叙述”当中,这段历史才能从不确定的、实验的氛围中凸显出来,获得稳定的意义和不断展开的前景。这似乎暗示了“分期”问题与新诗合法性确立之间的内在关联。另外,在这短短的十数年内,相关的论争十分频繁,不同的流派、诗风交错杂陈,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如时人所言:“十年来新诗的演变,甚至比旧诗在几百年内的变化更为庞杂。到现在,像我们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欲知当时的‘兴替之迹’,已经恍若隔世,有些茫然起来。”(31) 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展开,让二十几岁青年感到茫然,但同时也为系统研究提供了一种知识可能。因为,寻找历史线索,把握文体流变的规律,恰恰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传统的文章流别与印象批评的区别之处。这或许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的另一个原因:新诗的价值虽然备受质疑,但它的展开却包含了丰富的“情节”,这种历史决定它非常适合成为大学课堂上的“研究对象”。
伴随着“新诗”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无论是在大学课堂上还是在文学史叙述中),“分期”也成为日后新诗讨论的一个基本模式。应该指出,“分期”并非是现象的简单归纳,在分期的内部,往往包含了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进步”的想象,对新诗内在演进动力的构想,也包含其中。诸如“草创”、“萌芽”、“入轨”、“进步”等命名,也无不暗示出一条“进化”的线索。有意味的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将“十年来的诗坛”分为自由、格律、象征三派时,还曾有一位朋友对他“按而不断”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的。”(32) 如何不同的诗歌群体、写作方式之中构造出一条内在演变的、进化的历史线索,如何在错综的、偶然的现象中找到一种线性的必然,使之更明快、更具概括性,至今似乎仍是新诗研究的一个重点。
四、“历史的兴趣”与诗坛的重建
出于系统研究的要求,关于新诗历史分期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成了一个公共话题。但在大学课堂上,对新诗历史的呈现也并非一元。由于立场、眼光的差异,不同的讲授者自然会在公共的话题中“偷运”进独特的个人色彩,“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仍深刻地制约着这些早期讲述的展开。在本文论及的几种课堂讲义中,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出现最早。虽然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这部讲义仍带有“当代评论”的性质,没有与当时的文坛完全拉开距离(33),但一种力求客观的历史整理态度,仍是它最突出的特色。虽然在文章的最后,将十年来的新诗强分为自由、格律、象征三个流派,但“按而不断”的做法,暗示作为一个研究者,“历史的兴趣”比树立“榜样”要更为重要:“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时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34)“历史的兴趣”带来了特定的讲授风格,也使得历史的存留成为可能:在“新诗”这一章中,过于明快的历史分期并没有被朱自清采用(依余冠英的说法,只大致分为初期与后期)。与之相关的是,新诗内在的演进线索也没有着重突出(对三个流派“按而不断”),对早期新诗杂陈交错的多种陈述,以及不同的诗歌方式的记录,反而较之以后脉络清晰的新诗史叙述,保留了更多的历史原貌。
对于系统的研究而言,“历史的兴趣”自然至关重要,但大学课堂并非孤立于历史的现场之外。学院之中的系统研究,也会以某种方式介入当下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价值冲突的场所。与朱自清相比,这种张力更多地体现在沈从文、废名那里。先谈沈从文的讲义。上文已提及,《新文学研究》讲义也暗中设定了历史分期,但从总体上看,早期新诗的图景被勾勒得并不完整。沈从文讲授的重点还是在诗人身上,而他所选择的六位诗人,也似乎不那么具有历史代表性:开头不讲胡适的《尝试集》,而是以汪静之的《蕙的风》作为第一期的代表,就出乎一般人的意料;随后讲徐志摩、闻一多,尚在情理之中,而焦菊隐的《夜哭》被重点讲授,白话诗的元老刘半农排在了第五位,却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事实上,如果细致地研读这部讲义,会发现这样的选择也并非随兴所致,出于个人的偏好,某种内在线索还是贯穿其中。
一般的新诗史叙述,在把握新诗内在演进的线索时,往往着眼于诗体、形式层面的变化,如新诗如何从旧诗中解放,又如何寻找新的形式规范等,这样才有从“破坏”到“建设”,从“尝试”到“成熟”,从“自由”到“格律”等进化的历史想象。直至今天,新诗史研究的重点,仍是如何从诗体形式的内部揭示变化的线索,这似乎构成了新诗历史较之其他文体历史的独立性、完整性所在。对于形式的“线索”,沈从文的讲义也保持一定关注,但他的着眼点一开始就落在了别处:“五四运动的勃兴,问题的核心在‘思想解放’。”(35) 这是新诗讲义的第一句,暗示新诗所体现的社会意识是他关注的重点。不选胡适而以汪静之为第一期代表,恰恰与此相关,因为《蕙的风》中对“情欲”的自由书写,在“男女关系重新估价”上所惹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在后面的几篇诗人论中,新诗对年轻读者情感的动摇、新诗所代表的灵魂不安定状态,构成了他潜在的“问题意识”:谈到徐志摩时,他作出如下判断:“一种奢侈的想象,挖掘出心的深处的苦闷,一种恣纵的,热情的,力的奔驰,作者的诗,最先与读者的友谊,是成立于这样篇章中的。”(36) 焦菊隐的《夜哭》之所以入选他的讲义,不只因为有“三年中有四版”的畅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本雕琢堆砌的诗集“是一本表现青年人欲望最好的诗”,代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情形。(37)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关注新诗与年轻人不安定的、骚动的心理状态的关系,可以看作是沈从文新诗讲义的一条内在线索。
1927年后,沈从文从北京移居上海,生存环境、写作场景的变化,使他对文学的商业化、消费化有了更深的感受。日后对“海派”文学的批判,在30年代初也已埋下了伏笔。在“新诗”以及“新文学”对灵魂或官能之烦恼的表现中,他已发现了一种迎合年轻读者趣味的可能。(38) 历史的描述与判断,在这里实际上已服务于一种个人观念的表达。沈从文新诗讲义的内在线索,因而从单纯的“历史的兴趣”中剥离出来,卷入了当下文学生活的复杂网罗中。
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里讲授新诗以及新文艺,废名应该是较晚的一个。据说,他曾向胡适请教如何讲好这门课,胡告诉他照《中国新文学大系》讲就好,而废名“大有不以为然的意味”(39)。在新文学历史叙述的形成中,《中国新文学大系》无疑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五四新文学的“创世”神话,在这部大书中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在朱自清所谓的“历史的兴趣”中,其实也包含着对这一“神话”的前提性认同。废名拒绝《大系》的讲法,在某种意义上,已表明他讲授的起点,并不在“历史的兴趣”上,借历史讲授来重构新诗的想象,才是他的目的所在。1936年11月,在为林庚诗集《冬眠曲及其他》所做的序言中,这一点已被废名道破:“不了解诗而闹新诗,无异作了新诗的障碍。私心尝觉得这件事可恨,故常想一脚踢翻那个诗坛,踢翻那个无非是要建设这个,即是说要把新诗的真面目揭发出来。”(40) 随着新一代前线诗人的崛起,重建一个诗坛的愿望在30年代中期,并非废名一人独有,新老两代诗人之间的冲突也势成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大学课堂也可以看作是新诗坛的另一种延伸。
所谓新诗的“真面目”,也即是《谈新诗》中废名提出的著名论断:“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这一论断的具体内涵以及废名对晚唐资源的援引、乃至由此形成的与胡适文学史观的对话关系,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这里不再缕述。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他具体的讲授方式。与其他几部讲义相比,废名在《谈新诗》中随讲随编、随编随讲,似乎没有预想的整体框架。譬如,胡适的《尝试集》他一共讲了四次,在展开的方式上也纵横开阖、思路跳荡。然而,这种“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讲述,并非没有内在的章法,在某种意义上,这前面的四讲类似于总论,主要是为了解答开篇提出的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新诗?这个标准在我心里依然是假定着。”(41) 确立了标准,方可剪裁新诗的图谱,废名的逻辑实际上十分清晰。
至于新诗的“标准”为何物,“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一语仍过于笼统。但细读废名的具体讲述,还是有迹可寻的:一种瞬间情感统一、完整的当下表现,或许就是他对于诗的理想期待。(42) 有了“标准”之后,更有意味的是废名的讲法:在“总论”之后,每谈一个部诗集,必选出合乎“标准”的作品,完整抄录,他与其是在“讲”诗,毋宁是在“选”诗。所选诗作的多寡,因人而异,关键是“总论”之后,废名的讲授近乎于完全的作品举隅。有时,他还作相关的分析和评点;有时,他干脆不着一字,只是一首接一首地抄录。(43) 通过作品的展现,让学生获取对新诗的直接感受,这是废名的授课风格,(44) 但换一个角度,《谈新诗》也就不单是一部讲义而已了,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看作是一部特殊的新诗选本。
在新诗的历史展开中,通过“选诗”来确立一种标准、一种“经典”的秩序,对于新诗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正统”的维系,是极其重要的手段。胡适当年为了反驳守旧的批评家,就亲自站出来,在《〈尝试集〉再版序》中指点出十四首“真正的白话新诗”;后来,他邀请一批友人为《尝试集》“删诗”,也无非是要打造一部真正的“经典”(《尝试集》第四版),而从最早的《新诗集》(1920年),《分类白话诗选》(1920年),《新诗年选》(1922年)、一直到后来的《初期白话诗稿》、《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不同的“选本”也一直参与着新诗的历史叙述。而废名工作的特殊性在于,为了树立一个新的“标准”,“踢翻”并重建一个诗坛,在理论阐述之外,他也无形中提供了另一个“经典”的序列。
这一“经典”的序列,当然不同于胡适确立的“正统”。譬如,《尝试集》第四版里被删去的《四月二十五夜》,废名认为写得很好,推为《尝试集》里新诗的范本;而胡适自己颇为得意的《应该》一诗,在废名看来却是失败之作。同时,“历史的兴趣”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徐志摩的冷落。出于新诗自由化的理念,将徐志摩等人的格律化实践当成“一条岔路”,在废名那里并不奇怪,但不讲新月派,新诗的历史线索显然不会完整。有趣的是,废名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我遗漏了一些好诗,因为我记得我还读过许多好诗,但我的工作可以无遗憾了,我所遗漏的诗也正是说明我的工作。”(45)“我所遗漏的诗也正是说明我的工作”,自信的表白恰好说明废名“讲诗”(或“选诗”)的内在完整性。“历史的兴趣”本不是他的出发点,通过历史的检讨,来呈现一种价值、一种标准,才是他的目的所在。
为了重建诗坛,新老两代诗人的冲突,已涉及“经典”秩序的流变问题。1937年,更为年轻的诗人吴兴华就发表文章,指摘当时“选本”上出现的都是从胡适到新月派的老面孔,没有呈现《现代》之后更新的一代诗人。(46) 在“看不懂”的争论中,为卞之琳等打抱不平的废名,似乎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他的讲授却没有特意为年轻的诗人们张目,而是完全出于一片公心。在他的论述中,那种代际之间的“进化”链条,并没有被暗中设定,在他的标准之前,新诗的历史实际上被“共时”化了。
30年代,新诗进入了大学课堂,在重重争议中成为“研究的对象”,在新诗“经典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诚如上文所指出的,“经典化”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化,即将正在发生的、流变的历史,安排在某种线性的叙述里。废名的讲述,在发明出“个人经典”的同时,他也发明了另一种谈论新诗的方式,即在历史的描述之外确立一个标准,以此将历时的演进拉成一个“共时”的平面,去拣选他所谓“标准的新诗”。作为一种个人“深湛的偏见”的表达,价值的诉求虽然超越于“历史的兴趣”,但一般“系统”研究中以“知识”名义出现的“开端”、“完成”、“入轨”等线性叙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新诗历史想象的“固化”,也随之以另一种方式,被有效地闪避了。
五、结语
不论是满足“历史兴趣”,还是旨在“诗坛的重建”,朱自清、沈从文、废名等人的课堂讲述,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新诗历史想象的生成,对后来的新诗史写作也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课堂讲授,可以看作是新诗进入学院研究的起点,那么80年代,伴随着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复兴,有关新诗历史的梳理与检讨,在学院研究中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展开。在历史的挖掘之外,从审美、形式的角度,勾勒新诗内在的演进线索,展开“分期”的历史想象,仍然是新诗史讨论的重点。其实,不仅是新诗研究如此,即便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对“线索”、“规律”、“演进”的关注,也被看成是现代文学学科获得学科品质的标志。(47) 在这一要求的背后,除了有对学科自主性的期待,学院知识生产方式的潜在规约,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然而,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历史图景,在获得完整勾勒,逐步被系统化、常识化的同时,也日趋封闭、固化。如何打破“系统研究”内在的限制,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开放问题的空间,已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在这个意义上,谈论30年代大学课堂上新诗历史的早期讲述,不仅具有学科史回顾的性质,对文学史研究可能性的思考,也就包含在起点的追溯中。一方面,比起确立标准、设定范式,“历史的兴趣”或许会溢出一般的线性叙述,但更有助于扩张对繁复、多样之“过程”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将活泼的文学实践知识化、对象化的同时,如何在与现实境遇的紧张中,提炼出独特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从而摆脱学院知识生产的成规,获取一种具有穿透性的眼光,仍然是释放新的研究视野、激活新的历史想象的前提。
注释:
① 沈从文:《关于看不懂》,《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07—04。
② 适之:《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07—04。
③ 温儒敏:《30年代前期的文学史写作热》,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二章第一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④ 沈从文1930年在中国公学曾讲授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新文学课程”,该课程讲义后以《新文学研究》为名由武汉大学印行,后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⑤ 废名在北大讲新诗,大概在1937年上半年,见《十年诗草》中的叙述:“我的新诗讲义讲到郭沫若,学年便完了,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接着七七事变我离开了北京大学,再也没有写这个讲义的机会了,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未完的工作。”(《论新诗及其他》,第15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⑥ 《新文学的将来》,发表于1928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校刊增刊之一《文学》第一期。关于杨振声到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的情况,见萧乾《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代序),《杨振声选集》,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⑦ 王瑶:《从一个角落来看中国文学系》,原载1936年9月6日《清华暑期周刊》第11卷7、8合期,署名李钦;引自《王瑶文集》第7卷,第41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⑧ 后来,王瑶在谈到朱自清为何停止“新文学研究”时,也只轻描淡写的一句:“他无疑受到了压力。”(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⑨ 在1930年9月制订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已列出“新文艺试作”一课,但具体的学分未定,只说“由周作人、胡适诸教授担任组织,俟有规定后,再行发表”,大概只是一个构想(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BD 1930014);在1932年制订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对“新文艺试作”的学分、选课数量、考核方式都作了规定,并列出具体的教员,此课应该正式开设。(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9,案卷号:BD 1932012)
⑩ 这一点可以从课程的说明中见出:“凡有意于文艺创作者,每若无练习之机会及指导之专家。本系此科之设,拟请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凡从事于试作者,庶能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就正。”(见1930年9月《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第11页,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BD 1930014)
(11) 以上叙述参考1930—1935年间《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及《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
(12) 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4,案卷号:BD 1935008。
(13)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张中行,在回忆废名时就说:“其时我正对故纸有兴趣,没有听他的课,好像连人也没见过。”(张中行:《废名》,见《负暄琐话》,第6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4) 陈国球在讨论《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立科之关联时,就谈到“文学”的现代学科地位确立,并不是由思想前卫的梁启超来推动,反而是思想保守的张之洞成了“文学”的护法,因为“文学”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可以要在西潮主导下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见《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 朱光潜:《文学院》,原载《教育通讯》,第3卷第27、28期合刊,1940年7月,引自《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6)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17) 杨振声:《新文学的将来》,《杨振声选集》,第272页。
(18) 沈从文:《复王际真——在中国公学》(1930年1月3日),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3页。
(19) 废名:《尝试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页。
(20)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还引用了余冠英《论新诗》(清华大学毕业论文)的观点,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3页,注释13,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1935。
(21) 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苏雪林文集》,第2卷,第88—8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即便是身为新文学的圈内之人的朱自清,也会在课堂中遭遇尴尬的场面,在1932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他写下这一条:“学生问对高长虹诗意见如何,因未读过,无以对。”(《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2) 1929年6月沈从文致胡适信,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6页。
(23) 陆侃如:《中国文学系课程说明书》,见《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中国公学大学部办,1929年夏出版。
(24) 缪天华:《吴淞江畔的追忆》,见《私立中国公学》,第279页,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25)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73—2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6) 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现代学生》第1卷1期,1930年10月;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57—463页。
(27) 譬如,朱湘在30年代也写下了一系列新诗方面的评论,每谈一个诗人或一部诗集,一般都聚焦具体作品的评价、解说,并不太多顾及发展线索和历史定位,这些文章收入《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
(28) 关于此次演讲的报道,见1927年11月4日《时事新报》;可参见王锦厚编《(饶孟侃)简谱》,《饶孟侃诗文集》,第42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29) 余冠英:《新诗的前后两期》,原载1932年2月29日《文学月刊》,见《中国现代诗论》(上卷),第155—16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30) 废名:《冰心诗集》,《论新诗及其他》,第113页。
(31) 孙作云:《论“现代派”诗》,原载1935年5月15日《清华周刊》43卷1期;见《中国现代诗论》(上卷),第224页。
(32) 朱自清:《新诗的进步》,见《新诗杂话》,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3) 温儒敏:《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三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4) 朱自清:《选诗杂记》,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17页。
(35) 沈从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84页。
(36) 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99页。
(37) 沈从文:《论焦菊隐的〈夜哭〉》,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17页。
(38) 沈从文:“由作品显示一个人的灵魂的苦闷与纠纷,是中国十年来文学其所以为青年热烈欢迎的理由。只要作者所表现的是自己那一面,总可以得到若干青年读者最衷心的接受。”(《论朱湘的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40页)
(39) 鹤西:《怀废名》,载《新文学史料》,1987(3)。
(40) 废名:《〈冬眠曲及其他〉序》,见《废名佚文小辑》,载《新文学史料》,2001(1)。
(41) 废名:《尝试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页。
(42) 如以下几种表述中:“旧诗五七言绝句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引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的”(《尝试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5页);“这里确有一个严厉的界限,新诗要写得好,一定要有当下完全的诗”(《冰心诗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17页);“诗人的感情与所接触的东西好像恰好应该碰作一首诗,于是这一首诗的普遍性与个性具有了。”(《沫若诗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39页)
(43) 譬如,废名讲周作人《过去的生命》,抄出其中的十首诗,没有另外的文字,最后坦言:“我抄写这十首诗,每篇都禁不住要写一点我自己的读后感,拿了另外的纸写,写了又团掉了。我觉得写得不好,写的反而是空虚的话。”(《〈小河〉及其他》,《论新诗及其他》,第79页)
(44) 据废名的侄子冯健男回忆,叔父为他讲新诗时,也只是一首首地诵出或写出,并不多加讲解(冯健男:《我的叔父废名》,第139—141页,南宁,接力出版社,1995)。
(45) 废名:《十年诗草》,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53页。
(46) 吴兴华:《谈诗选》,载《新诗》2卷1期。
(47) 王瑶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中,就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第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标签:沈从文论文; 大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胡适论文; 文艺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尝试集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朱自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