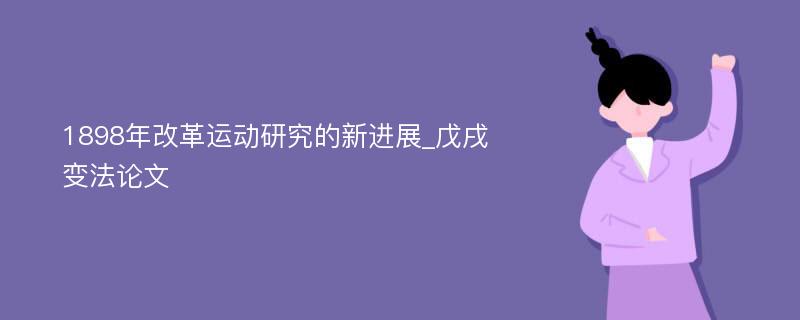
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新进展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4-0057-09
1998年,在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戊戌维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围绕戊戌维新的性质、历史意义,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关系,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以及文化思想、社会与区域变迁、教育改革、外交和中外关系、戊戌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关系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是此后十年戊戌变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
2008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纪念。自戊戌维新100周年纪念以来十年中,戊戌变法研究仍呈现多领域、多角度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呈现突出重点、集中讨论的可喜现象,戊戌变法研究逐步掀起一个新的热潮,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而如以往一样,这一研究热潮的内容,充满了对戊戌变法相关问题不同观点之间针锋相对的辩难。
一、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史料发掘上的新进展
史学研究重在材料发掘,没有材料、证据,一切观点、新说都是空中楼阁,站不住脚。近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在系统运用史料方式的新总结、史料发掘新途径的开辟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国内档案史料发掘和运用方式上的突破
在国内档案史料运用方式的突破上,茅海建等学者通过系统运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材料,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的研究,显然是其中的代表①。这些档案史料运用的成果证明,近年的研究,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所藏故宫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主体档案材料看似已被学者搜罗穷尽后,研究者却又能在档案材料的挖掘、利用上另辟蹊径,通过《穿戴档》等侧面的档案材料来辨析主体材料的真伪、可靠性,推动研究的深化。
(二)国内外新史料发掘的新进展
目前,戊戌变法研究在国内史料发掘方面要获得重大突破,存在较大难度。但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在发掘国内外相关官私史料上获得诸多新进展。
第一,对以日本为重点的国外官私档案文献的系统发掘。
戊戌变法的开展与失败,固然与当时国内各政治势力改革与守成、权力与利益之争有密切关系,也与甲午战后东亚国际环境、维新派与日本关系演变等因素密切相关。运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研究戊戌变法,学者们多年前已有尝试但不系统。当前,系统发掘日方材料及其他国家的材料,与中国的材料互证,可以开戊戌变法研究之新路。
日本方面有关戊戌变法的官私档案文献数量巨大,主要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48 000余册,每册又包含几件甚至几百件不等的原始史料,其馆藏档案文书经整理出版为《日本外交文书》②,其中有大量涉及戊戌变法前后清国朝野和中日交涉的史料,此外,日本外交史料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史料,也包含大量有关戊戌变法的内容;防卫厅档案则是一个尚待深入挖掘的新材料来源③。东亚同文会编辑出版的《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以及《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近卫笃麿日记》、《井上雅二关系文书》、《宗方小太郎文书》等公私档案、私人文集的进一步发掘,显然具有重要价值④。而近代以来日文报刊,如《太阳报》、《东京日日新闻》、《东洋自由新闻》等,有大量关于清政府的材料可供发掘。中日学者联合开发、利用这些材料,与中国史料参互运用,以打开戊戌变法研究的新局面,已成趋势。近年来,将日本有关戊戌变法的资料译介到中国,郑匡民和茅海建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在2005、2006年联合翻译了从日本外交史料馆发掘出的部分关于戊戌变法的史料。[1]其他国家的材料,近年引入的《英国外交机密档案》等官方档案,以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私人档案,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一批与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官私档案文献的发掘。
康有为文献的新发掘和完整搜集,一直以来都是大陆、港台和海外的戊戌变法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出版,集目前海内外已发现的康有为文献为一辑,使戊戌变法研究在康有为这一人物材料方面拥有了目前较为完备的版本。
梁启超文献,虽然已经有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但显然相关文献的搜求并未完备。《〈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出版,在前述两集之外为戊戌变法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一个较好的汇辑本。
晚清重臣翁同龢私人档案文献的发掘是一项重要工作。由翁同龢后人、旅美学者翁万戈家藏,并与旅美学者孔祥吉联合整理的翁同龢私人档案内容丰富,收录了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88-1898年)十余年间大批活跃在朝野的中下级官员向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户部等清政府机构呈递的奏折、条陈,包括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抄录本,以及翁同龢的批注等。这批文献中另一具有重要价值的材料,就是当事人、包括上述奏折、条陈的作者,写给翁同龢的信函、禀帖、文电等,以及翁同龢本人对各类文书归纳提炼的随手记,对于包括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批文献,已由台北艺文印书馆陆续刊出,第一编主题为“新政变法”(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辑录与戊戌维新关系密切的文献资料。谢俊美编辑的《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也为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
此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张荫桓日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等的整理出版,为深入研究戊戌变法,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持。
二、十年来戊戌政变及其原因研究的新进展
戊戌政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而关于戊戌政变的研究,学者们的焦点集中在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和直接原因上。
(一)戊戌政变发生时间认识上的变化
关于戊戌政变发生时间,以前有三种观点:一是八月初四日政变说,李剑农首先提出,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向慈禧递训政密折,八月初四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发动政变。[2](P18)二是八月初五日政变说,萧一山提出,慈禧担心光绪八月初五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因此,初五日一早她从颐和园回到皇宫,发动政变。[3]三是八月初六日政变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等论著都采用此说。可见,戊戌政变发生时间上的意见分歧,在于这一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变原因、政变期间各政治派别的活动密切相关。
目前,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考察有重大推进,即从八月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这几个时间点,推进到八月初三日至初六日这样一个时间段,拓展了我们对政变发生时间的认识⑤。
(二)戊戌政变过程和直接原因研究的新进展
戊戌政变的研究中,政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学界没有什么分歧,基本认定是在维新与守旧、权力利益之争的范围内。而关于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导火线,则意见歧出,众说纷纭。
目前,戊戌政变直接原因的论争,主要集中于袁世凯告密说、伊藤博文来华说⑥、杨崇伊密折说三种观点上。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说,自康、梁提出之后,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丁文江、赵丰田在20世纪30年代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提出疑问:“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⑦从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学者黄彰健质疑并证其伪开始,袁世凯告密引发政变说到今天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50年代台湾学者吴相湘提出杨崇伊呈递给慈禧太后密折引发政变一说,经80、90年代延续至今,房德邻、孔祥吉、林克光、骆宝善、茅海建等大陆学者研究考订,认为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因御史杨崇伊呈慈禧太后的密折,慈禧一派已经开始行动。
围绕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问题,研究者关注的内容有新的扩展。1999年,骆宝善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一文,针对赵立人的观点,认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2006年,赵立人撰文对黄彰健、房德邻、骆宝善等学者以慈禧“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和游说袁世凯“围园”的谭嗣同为据来推断戊戌政变非袁世凯告密所致的说法,提出商榷,指出“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9月26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9月21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他在政变发生的当天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4]2002年,郭卫东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提出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并推测袁世凯告密地点不在天津而是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袁世凯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的对象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5]
对戊戌政变直接原因和过程的认识获得重要推进。2000年,房德邻发表《戊戌政变之真相》,提出对戊戌政变原因和过程认识的一个重要思维,即“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是八月初三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八月初四日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再次是八月初六日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消息到京后,光绪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荣禄到京后,光绪的处境才有所改变。[6]2001年,蔡乐苏等合著的《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一书,对戊戌政变原因的观点虽然是综合前说,但提出政变近因当从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军机四章京,逐李鸿章、敬信出总理衙门算起,袁世凯、伊藤博文先后来京,加速了政变进程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戊戌政变直接原因构成因素的思维同样是一个推进。[7](P783-881)2002年,茅海建发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核定,并做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细化了戊戌政变全过程,[8]对戊戌政变的研究做出重要推动,为更深入地探讨政变原因打下基础。
三、十年来“公车上书”研究中的几次重要论争
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史上的重大事件。自1998年以来,国绕“公车上书”的真伪等问题,发生了数次大辩论。
1999年7月,《光明日报·书评周刊》根据姜鸣《被调整的目光》一书中《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一文,刊出了《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根据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等质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问题的研究成果⑧,指出当时反对《马关条约》的主要是官员,而举人们的上书也未受到阻碍。康有为写此上书的目的,很可能一开始就准备在上海发表,由此而制造了一个大骗局。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众多议论。12月,汤志钧针对姜鸣的观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公车上书答客问》,引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天津《直报》等材料,指出当时确有“公车上书”一事。[9]2003年,汤志钧出版《戊戌变法史》(修订本),对于“公车上书”,坚持自己在初版本中的意见:“康有为这一次上书,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10](P149)2006年,姜鸣也再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改名为《天公不语对枯棋》,坚持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不同意汤志钧的意见。[11](P139-157)这是近十年来关于公车上书的一次重要论辩。
2001年,蔡乐苏等合著的《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对“公车上书”问题,坚持采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观点。[7](P283-293)同年,刘高《北京戊戌变法史》一书部分采用康有为的说法,认为公车上书是“在主和派的干扰下夭折了”。[12](P42-49)2002年,欧阳跃峰发表《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根据孔祥吉、汪叔子等的观点,再次提出“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制造的大骗局的观点。[13]虽然没有不同观点之间针锋相对的辩难,但不同观点的发表,也略可视为近十年中关于“公车上书”的一次论辩。
2005年,茅海建在同意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观点的基础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认为所谓“公车上书”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是康有为作伪的结果。2007年,房德邻对此作出有针对性的辩驳。一场令近代史学界瞩目的学术论争产生了。他们辩难的主要内容如下:(1)谁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茅文认为,从军机大臣翁同龢等“政治高层”有利用“公车上书”的需要和动机来看,翁同龢等“政治高层”是“公车上书”的真正策动者,目的是利用下层舆论来迫使光绪改变同意割地议和的主意。而房文认为:茅文“主要利用《翁同龢日记》,对之作逐日解读,不过多有误读,所以其结论难以成立”,“在批准条约之前的这几天的《日记》中,翁未说过一句妥协的话,也未说过一句主战的话,甚至未出过一策,可以概之以‘无作为’。……他对于自己当初主战已经后悔。……在犹犹豫豫中与主和派同流合污了;……他说‘此等情形,直同已死’,倒是既形象又准确。一个‘直同已死’之人,他还能够与皇帝斗法,暗中鼓动舆论,毁约再战吗?”茅文从翁同龢有利用舆论的动机推测出政治高层“决定于二十一日对外透露”的论点,并从三月二十一日以后的上书内容中做出同样的推断。房文则认为:“翁同龢等截止到三月二十一日并没有利用舆论来反对光绪皇帝的签约电旨的意图,因为翁同龢等也是同意这道电旨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二十一日向外泄漏过《马关条约》的内容,而且乙未年大规模的上书浪潮也不是因为二十一日传出《马关条约》的内容引起的,而是李鸿章二十六日成约归来这个公开的消息引起的。所以不能说乙未年的上书是由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发动的”。(2)“公车上书”是否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和组织?茅文认为,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只是向外泄露消息,但他们并不具体策动举人上书,具体策动者是文廷式等级别较低的京官。房文认为,“从茅海建先生举出的文廷式暗中策动的例子和5例京官与举人联名上书的例子来看,除江南举人联名上书外,其他31次举人上书都与京官无关,既无京官公开参与其中,也无京官在背后策动。而江南这次也不是由文廷式策动的,他只是点窜过上书的文稿而已。所以32起举人上书,没有一起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3)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茅文认为:“汪叔子先生、王凡先生1987年的论文即已对此提出‘三阶段’,以说明此中的变化层次。康氏‘公车上书’的事实,被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色彩越来越靓丽,情节越来越戏剧化,也越来越容易引起治史者的兴味”;“康有为《我史》中关于‘公车上书’的记录,多处有误,很不可靠。如从政治高层的决策过程去观察细部,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其牵强与张扬,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似为其想象。叙史者若加引用,需得处处小心。”房文则从“康有为是不是乙未年‘公车上书’的第一发动者”、“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否分托朝士鼓动”、“康有为是不是18省举人联名上书的领袖”、“康有为是否到都察院上书”等方面作出分析论证,认为“上书的基本过程是清楚的,康有为的作用也是清楚的:康有为鼓动起乙未年第一批举人上书,其时间比京官的大规模上书略早,他又组织了规模最大的18省举人联名上书,他起草的上书乃是维新派的变法纲领,因此他是公车上书的当之无愧的领袖。”针对房德邻等的观点,2007年,茅海建发表《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一文》作出回应,该文引用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等材料,并解读《直报》的报道,进一步说明自己在《“公车上书”考证补》中的观点⑨。这是近年来关于“公车上书”的又一次重要论战。
四、研究戊戌变法时期日本等外国力量在中国活动的新成果
戊戌变法前后日本各派势力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情况,在1998年纪念戊戌维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几位日本和旅日学者就上海亚细亚协会、戊戌变法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对张之洞的游说工作及其效果、戊戌维新前后中日两国关于招聘日本顾问的谈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揭示出运用日方材料来研究戊戌变法的新趋势⑩。
2004年,茅海建和郑匡民合作发表《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对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关注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长,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等情况做出深入探讨。认为当时的改革派,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还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张之洞等官员,思想上都有很大变化,大多倾向于联日。戊戌变法期间,日本政府表露出对中国维新运动的赞许和同情,但援助甚少;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则公开或私下救援维新党人,阻止废除光绪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并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使清军撤离的联合行动。戊戌变法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为增强。不管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还是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14]
孔祥吉和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著的《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运用中日材料,对戊戌期间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确立情况,翁同龢被罢官,戊戌前后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演变等问题,作出深入探讨。[15]
关于中日结盟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桑兵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和《“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一文中,对上海亚细亚协会、东亚会、同文会活动中体现出的中国维新人士与日本“兴亚”力量之间谋求联合的活动,作出深入研究。[16]探讨戊戌时期日本各派政治力量介入中国内政,在中国展开结盟活动,必然要研究日本“振亚”、“兴亚”思想、亚细亚主义。盛邦和与戚其章在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的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兴亚主义、兴亚会等问题上的探讨和辩难,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探讨戊戌时期日本各派政治力量以“兴亚”名义与中国结盟等活动。[17]
五、研究戊戌时期变革政治体制和政治改革运作的新探索
关于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体制设计,马洪林《略谈戊戌变法的“保守”与“激进”》一文提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开国会、定宪法、兴民权的主张,突破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束缚,开启了政治近代化的闸门,没有戊戌时期近代化思潮的传播与影响,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化的展开,也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8]徐怀东、张茂泽撰文指出,在宪政体制和宪政思想的引进方面,与西方以人权抗衡神权不同,维新派采取了以民权对抗君权的特殊形式,但是,其左右两翼的思想主张又有所不同,即使同为维新派的左翼也有分歧。左翼的谭嗣同激烈反君权,但对民权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而左翼的梁启超、严复则主张在君权和民权之间折中调和,主张君主立宪。作为维新派的右翼,康有为侧重于尊君权兴绅权。[19]
在国家学说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中,维新人物往往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地,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都是其中的代表。李华兴认为,从甲午至戊戌,严复以自由、平等为武器,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参照,以民族危亡为背景,以谋求国家富强为目标,是后来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开路先锋;考察严复国家学说的政治实践,他由维新派中的稳健派变为民主革命的反对派,再变为袁世凯帝制的帮手,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使他深陷矛盾泥沼不能自拔,最终无法找到中国富强之路。[20]
关于戊戌变法期间具体的政治变革实践,2004、2005年,茅海建连续发表《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和《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两文,认为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地向皇帝上书,是戊戌变法期间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变法期间,大约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是一次历史上少见的来自中下层的无指挥多声部政治大合唱。他又认为,司员士民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诸策,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21]2006年,茅海建发表《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一文,指出甲午战后光绪皇帝下诏求贤所面临的迷茫局面,使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期间改变方法,督抚廷臣保举人才开始成为光绪帝择用小臣的特殊方法。“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书保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各地督抚和京内大臣也先后出奏,保举的人才超过百人,光绪几乎全部下令召见,到政变发生前共召见26人。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促动了变法的展开,并体现出清朝政治的若干特点。[22]
六、戊戌思潮和重要人物研究的新进展
戊戌变法时期思潮和人物研究,成果丰硕。限于篇幅,不可能对每一篇(部)相关思潮和人物研究的论著做出评述,在此仅择要评介。
(一)戊戌思潮研究现状
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成果丰硕。潘光哲在《〈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一文中,对《时务报》这一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报刊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的状况,对晚清思想解放多层面的反应作出探讨。[23]梁景和则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站在资产阶级文化高度批判中国传统婚姻陋俗的角度,肯定了维新派对中国19世纪进步婚姻观的重要推动。[24]
关于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的探讨论著颇丰。何一民针对学界对康有为大同学说的否定,认为康有为在批判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将大同学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本质区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25]张彩玲、王延涛、张守君、贾孔会等撰文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提出在中国实行大机器生产,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股份制经济产生的必然性(11)。
戊戌时期文化学术革新方面,学者们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新学”,维新派运用孔教、经学、西学作为变法理论资源,以及维新派在传播西学、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的演进等方面,做出了多样丰富的探讨(12)。
(二)戊戌人物研究现状
1.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十年来,研究康有为的论著很多,其中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康有为自编年谱》(又称《我史》)的可靠程度、是否作伪问题的讨论。马忠文在《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康有为自己所说从乙未年(1895年)开始撰写《自编年谱》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此后康有为对年谱不断有修订和增删,定稿于康有为逝世前,可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有为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26]茅海建在对康有为《我史》手稿本进行笺注的基础上,发表《“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一文,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确定其写作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通过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修改手迹的辨认,发现《我史》已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27]
2.关于光绪皇帝的研究。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包振远根据公安部门通过中子活化实验方法、法医病理毒化检测等现代科学手段检测的结果,撰文指出光绪是大剂量、急性砷中毒而死。[28]茅海建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一文中指出,光绪在自己狭小的权力空间中,通过觐见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亲笔书写与日本国书、召见伊藤博文等对当时和后来影响细小的实践,表现出摆脱传统外交束缚、拓展自己权力空间的努力。[29](P413-462)
3.关于梁启超的研究。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对戊戌变法期间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接受东学,并反哺中国和日本社会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30]
4.关于荣禄的研究。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学界一般都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荣禄反对变法、是镇压维新派帮凶的评断。冯永亮通过对戊戌变法前后荣禄的奏稿、函电、文牍等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并考察政变后荣禄主持枢垣时采取的积极举措,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荣禄看作顽固守旧人物,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是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遵循的是另一条缓和而渐进的变法道路。[31]
5.关于汪康年的研究。江浙维新派的首脑人物汪康年,无论在戊戌时期主办《时务报》,还是在庚子勤王运动中都占据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论述。[32]
6.关于翁同龢的研究。翁同龢罢官问题,为学者共同兴趣之所在。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一文同意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在《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一文中的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最初同意变法,不会在维新伊始就处心积虑地加以反对,而积极变政的光绪皇帝觉得翁同龢过于持重、苦于被翁掣肘,故突然罢免翁同龢,并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的本意。[33]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的研究并未因十年前戊戌维新100周年纪念的高潮而出现相对沉寂的状态,相反,近年来的研究高潮迭起,成果丰硕,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新进展。
[收稿日期]2008-12-20
注释:
①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这些文章收入茅海建所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05。
②《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协会,昭和二十九年版。
③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1-14页,成都,巴蜀书社,2004;汤志钧:《乘桴新获》“前言”,第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④《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原书房,1981年版。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编:《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刊行,1980年东京版;《近卫笃麿日记》,鹿岛研究所昭和四十三年版;《井上雅二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藏件;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原书房,昭和五十年版。
⑤房德邻和茅海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为代表。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二)》,《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⑥参见萧一山:《戊戌政变的真相》,《大陆杂志》(台湾),第27卷第7期,1963;汤志钧:《伊藤博文来华与戊戌政变发生》,《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油印本,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本改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43、1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⑧黄彰健:《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87-59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75-8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汪叔子:《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王凡:《〈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⑨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⑩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陶德民:《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参见《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90-402页、第403-4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王晓秋:《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1)张彩玲:《康有为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王延涛:《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张守君:《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贾孔会:《梁启超股份制经济思想浅析》,《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
(12)王先明:《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形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刘学照:《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陈其泰:《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等。
标签:戊戌变法论文; 康有为论文; 翁同龢论文; 茅海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清朝论文; 袁世凯论文; 光绪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马关条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