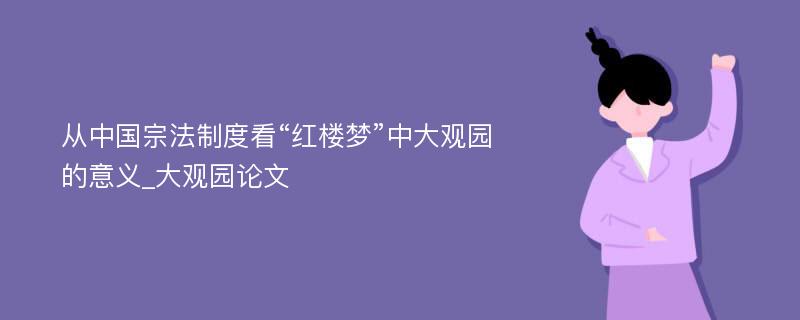
从中国父权制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观园论文,父权制论文,红楼梦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楼梦》作为一部被丰富诠释的文本(text)〔1〕, 吾人常可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角度,来一窥其中隐而未现的多样面貌,历来亦常被视为是最足以体现中国文化(如思想、社会、生活、情感等)的小说之一。从性别(gender)〔2〕的角度来看, 书中乃立基于“女清男浊”的观念,以女子及歌颂女儿文化的男子(贾宝玉)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在此小说舞台上,能任其一显才情、展现生命风华之自由天地,便是“衔山抱水建来精”“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了。
关于大观园的研究,前人已在地点、布局及园林艺术的研究上,展现了相当丰富的成果,除此,还有强调与探究大观园“理想”特质的论著〔3〕,以为大观园的诠释上,注入更多的生命。 近来由于受到西方性别理论的影响,亦有学者自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大观园〔4〕, 使得大观园作为一个女性空间(female space)的论述,有了一更新视野的呈现。在女性主义角度的观照下,父权制常是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被批判的核心与焦点。而当我们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所常强调的:女性在行之已久的父权制之压迫下,必得去反抗、批判或颠覆这一套以男性利益为考量的价值体系,才能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存活空间这样的观点时,却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虽说父权制的存在,具有跨越文化的成立基础,但在中国文化中,却可能有着不同的进行方式与面貌,自然,女性在此中的因应方式,亦将与西方女性主义所述有所不同。
《红楼梦》作为一部体现中国文化以及提高女性被论述之价值之小说,若从中国父权制此一视角来作探究,或许,可一窥大观园之所以能出现、成立,甚或导致后来衰败的深层文化意义。
一、孝悌与名位——中国父权制特色
父权制(patriarchy)这个概念,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指的是:以“父视权力”为原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体制,或者是由群体内年长的男性独掌家庭和公共政治权威的社会体制。对于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父权制与母权制孰先孰后,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学术界一致认为,在人类家庭发展史上,父权制是一普遍存在的事实。
多数研究西方古代文明的学者(如H.Maine、F.de Coulanges、 G.Jellinek)均大抵同意:我们最原初的父系权威的类型,则可追溯到罗马人的“父权”〔5〕。著名的社会学者韦伯(M.Weber)则曾进一步指出,罗马法中保存了最完整的父权权力法条。韦伯认为:父权制确实是“截至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传统支配的类型’,而中国与罗马帝国正是父权制与世袭支配的原型〔6〕。韦伯将此意义扩大并系统化后, 便认为:儒家将“孝顺”此一道德原则,从家中孩童对父权权威的孝顺,扩及于官员对统治者、低阶官员对高阶官员,及一般人对官员和统治者的依顺,故而将此观念修润得更具一致性〔7〕。因此, 在中国的家族中,父祖是统治的领袖,而且也可说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
西方学者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父权制所带来的“压制”性时,往往会得出:女性及年幼的男性是其中的被压迫者的结论。诚如米勒(Kate Milletts)所言:“性支配主权(sexual dominion)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普遍的意识形态(ideology),而且,它可谓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权力观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就像所有其他之历史文明一样是父权制(patriarchy)的缘故。〔8〕”因此, 女性做为一个群体,唯有正视这个问题,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威顿( Chris Weedon)在“女性主义与理论”(Feminism and Theory)一文中,便直言不讳地宣称:“身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起点是社会的父权结构。‘父权的’(Patriarchal)这个词, 指涉女人的利益从属于男人利益的权力关系。……女人的性质与社会角色乃是相应于男性的规范而界定的。〔9〕”在如此具权力从属结构的思考里, 父权制便是一个造成女性被压迫的最本质性(essential)的要素。
观察中国的父权制,我们可发现:强调权力/从属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压迫/被压迫的解释,并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父权制的特色。笔者以为,只有从孝悌与名位所形成的序列结构,才能得见中国父权制中,男性与女性间微妙的权力流转以及女性在此结构中的生存策略(politics)〔10〕。
“父”在字义上确实有首领、领导的意思〔11〕,事实上,在中国重宗族伦理的社会中,“父家长”的色彩更为浓厚〔12〕。但中国人并不从父家长的“权力”来著眼,而是从“孝悌”与“名位”之规定中,来见出角色扮演与顺从要求之后的权力义务关系。若比较中西的不同,此倒可以以詹密笙(George Jamieson)所说的为准则:“在罗马法中强调父亲的主权,这隐含着在儿子一方的义务与顺从。而在中国的法律中,则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待:它强调儿子的义务与顺从,于其间则隐含着在父亲一方可施行的权力。〔13〕”以儒家传统下的中国社会而言,齐家与治国的发展是平行而对应的,家族中的父长便如同一国之君一般,子女与臣子必须要对其绝对的服从,为了家族与国的秩序与和谐,“孝”“悌”此一根本的道德原则便会被强烈地要求着,并且循此德行,扩而为“忠”的基本内容(所谓“移孝作忠”“忠孝难两全”之类的讲法,均可见“孝”与“忠”在中国人思考上的平行对应关系)。如《论语·学而篇》即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儒家学说的着重孝悌,使得父权制的父长权力核心更为稳固〔14〕。
“孝悌”的道德原则还必须与“名位”的概念相结合,方能使“孝悌”能够长久以来,成为鉴别中国人个人道德人格的重要准则。
“名位”的概念在先秦时即已萌芽,孔子所言之“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篇》)等,即为中国人的正名观念确立基础〔15〕。正名的观念使得子或臣的角色扮演有了一明确的要求与依据,这一方面代表了身份的差序,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当其位者应循的礼节内容,在此序列的结构中,家族里的人子、幼辈便理所当然的接受了孝悌所规定的内容〔16〕,当此内容被规定的同时,亦即暗示了父祖所隐然被赋予的权力。事实上、中国的家族、经济、政治早已混融为一体系,所以,由家到国,可谓已全面地笼罩在父权制之中。
而在此情形下,女性的处境又是如何呢?这可就两个方向来谈:
一、虽然,在中国父权制下,女性的“顺从”早已被规定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但,当女性的角色从女儿转变成母亲时,中国父权制对儿子应遵行的孝道的强制力,便会在身为儿子的男性身上展现,而《礼记》中的“夫死从子”与此却并不冲突。因为,中国人在此本就不从“权力”着眼来思考,而是从“名位”的意义及其所具有的道德原则来作思考。因此,当孝道成为中国社会中的重要道德要求时,身为母亲的女性,便在儿子“侍亲”“顺从”的相对性中,获取了权力。当然,在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中,“夫为妻纲”仍是不变的指导原则。因此,当我们看《红楼梦》中的贾母时,便可见其隐然仿佛是贾府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大家长,但事实上,这是源于两个先决条件——同辈的男性(夫、叔伯)已死(或出家)以及成为深受儒家道德洗礼的儿子的母亲。因此,贾母的尊权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成立。而女性可能的被压迫命运亦就此改观。
二、由于中国强调名位的序列特色,为了达到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正名”),“名”的神圣性和正当性便需要经由先圣先王、以及由来已久的传统(如“礼”)来确立与保证,但当传统“名”的系统实际运作时,它的现实性便会增强,也因此,在“名”的形式之下,“实”的呈现便有了因时因地制宜地、属于中国人式的“拿捏分寸”的转化〔17〕。因此,在名实之间,便存在了一些可能的空隙,而这也提供了女性在中国父权制下,另一个可能存活的空间。《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出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中国父权制下,女性虽有一定的局限,但却并不必然被全面地压制着,这实乃源于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对于“权力”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态度与看法,西方强调的是一种权力意志的精神,而中国则着重在位置角色扮演的意义,由于位置的可能转换,使得权力亦在其中产生了自然的变化。当然,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所引致的特殊社会文化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父权制名实空隙下的大观园之成立
如前所述,中国父权制在着重“孝悌”与“名位”的特殊文化下,产生了一些女性在孝道伦理下之翻转的机会;同时亦在名与实中间,提供了一些的可能空隙。事实上,这也诚如莫伊(Toril Moi)所言:“只有意识形态概念,当其以分歧、滑动及不协调来标示出其矛盾结构时,便会令女性主义解释,何以即使是最严历的意识形态压力,亦会产生他们自己的空隙了。”〔18〕
大观园的出现,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中,初始完全是因为“元妃省亲”的缘故〔19〕。这个如御苑般的园子能够被建造起来,而后又能让一些姊姊妹妹们住进来,俨然如女儿国一般,实是由于它能在父权制的“空隙”中成立的缘故。
元妃是贾政的长女,回贾府来省亲。若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回来探望父母,贾府原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的。但由于她的角色位置——元妃,标示了背后的“君王皇室”,在父权制的序列结构中,这可说是最高的位阶了。贾府历来是深被皇恩,袭官封爵的;因此,对荣宁二府而言,“元妃省亲”便是一桩共同的大事了。是以,大观园之筹建,便完全是贾府站在“君/臣”的臣子的立场,以相应于皇室的排场规模来做考量的,但其实也真是“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十六回赵嬷嬷语)。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贾元春所处的这个名位,让她可以在形式上如被接圣驾般地对待着,这种因皇妃之名而有的形式意义,亦展现在她与贾政的对话中;当元春强忍心中幽处深宫的伤悲(诚如元春向贾母、王夫人言“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十七至十八回语),向其父感慨“骨肉各方,终无意趣”时,贾政却以一派冠冕堂皇的臣子口吻来感念皇恩,所谓:
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愿我君万寿千秋……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待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便可见出,随着元妃回贾府而看似为元妃所建的“省亲别院”大观园,事实上的重点,乃完全是为了成就君/臣之义,而烘染出富丽堂皇(即连元妃都“默默叹息奢华过费”)的形式上的虚名罢了!
说大观园乃为“形式上的虚名”而建,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的。首先,就其讲究的规模气势而言,它并不是针对元妃个人性情和她实际需要来着眼的(“贵妃崇节尚俭,天性恶繁悦朴”“且说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十七至十八回),它乃纯就符应社会上大家都如此行的“迎皇室之排场”之必要准备(如十六回贾琏所言:“现今周贵人的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修盖省亲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在这过程中的面子和排场方是贾府所不敢轻忽的,而这对于身为女性的元春而言,奢华之排场却只不过是父权制文明所堆积出来的价值罢了。除此,就贾府的实际情况而言,本身实原已有供休憩、赏玩的园子(如宁国府后边的会芳园,及荣国府东北——贾赦院之后的园子),故是不必要为修砌庭园再大费周章的。是以,大观园的立意设计确实是为了元妃省亲当下的豪华气势及游乐赏景的考量,因此便在园内设计了许多供休憩的楼亭房舍。就“颂扬皇恩”而言,大观园确实在形式上,于元妃幸此园时,展现了它的功能。
我们可以说,大观园以“如实的建造”来颂扬了“父权之名”,但矛盾之处也在这里:当省亲结束后,这当下的“崇高的”“父权之名”功能亦同时完成而消失,然而,此“实际的”“如实的建造”却仍依然矗立在那里,它原初看似的神圣之名和供游赏遣玩的园子的实用价值之间,有了一段差距,而这确也突显出转眼即逝的“父权之名”本身所带有的一种虚妄特性。对此,贾元春有深切地了解:“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廿三回)
在这因“崇高之名”而有的“现实之实”二者之间,所造成的可能空隙,提供了元妃以“父权之名”来行成立“女儿国”之实的机会。此能实现的最大关键乃在于,元妃是个“拥有权力的女儿”。
由于元妃是在父权制下的最高父权——皇权的依附者,因此,对于父权的结构而言,她可说超越了家族的父祖权力核心,而径至了国的父祖权力核心,因此,趁这父权之名所形成之虚妄空隙,元妃运用了皇权,将贾府中的姊妹及认同女性价值之宝玉均移置进了园内,让他们在空间上得以暂时离开了与父权制过于密切的关系(如父权制所带来的价值体系,所给予女性的定位所造成的限制;甚且后来那些女儿们便在园内吃饭,连到园外吃饭请安之礼亦都免了——五十一回),诚如元妃所以为的:“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廿三回)。因此,大观园便在这样的前提下,成为了女儿们的王国,而取代了初始建园的目的。这其中的转换,就女性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成功的“策略”(politics)运用。脂批有言:“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捻。”〔20〕脂批之言,实可再解为“借元春背后的父权之名而起,再用为女性考量的女儿用心来安置诸艳”,此中,女性在父权制下所运用的“偷龙转凤”策略,确实使得女儿们觅得了属于自己的存在空间。
大观园成为女儿国的事实,亦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相映成辉的例证。首先,由园内的客观环境而言,园内乃是以象征女儿的“水”(第二回宝玉即尝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为主景设计〔21〕,其次,当姊妹们移进园内后,小说更强调以“花”来象征女性的有别于父权制下男性文明的“洁净与纯粹”(如廿三回黛玉葬花,即是为了避免撂在水里的花,“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六十三回的占花签,便以女子形象和花相辉映,以及四十回贾母向薛姨妈笑道:“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另外,这些姊妹们还拥有了为园内景物命名的“命名权”〔22〕(七十六回当湘云赞“凹晶馆”此名取得新鲜、不落窠臼时,黛玉言:“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也有存的,也有删改的,也有尚未疑的。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也都拟出来了…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是以,女儿命名权的展现,更标示了大观园是女儿国的事实,因为,女儿们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情性和想法,以命名的符号表征方式来初步地构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三、隐匿与逃避——父权制下大观园女儿国的存在之道
在姊妹们和宝玉都搬进了大观园后,宝玉是“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廿三回);而女儿们则更是“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熳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廿三回)。在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属于女儿(文化)的“桃花源”内,女儿们所进行的活动意味着什么?而这与父权制的关系又是如何?在西方面对父权压迫而有的“反制与解构”的思考下,大观园相对于中国父权制,却展现了另外一番“隐匿与逃避”的思考与因应策略。
有别于中国父权制之讲求“名位”与“孝悌”之序列结构,大观园内乃以“情”来作为女儿们间重要的联系要素(相关于“情”的论著已很多,此便不再赘述),在这宛如没有父权制干扰的世界中,园内的女儿们,置身在如诗如画的景致中,便以成立诗社(海棠社与桃花社),以做诗(偶而填词)的方式,托物寄“情”地呈现他们自己,展现他们的“感情”“性情”与“才情”,而这也可说是他们最美妙的审美活动。
大观园的女儿们透过“诗”的表述形式,建立了有别于园外的世界,由与大观园平行叙述的情节中可知:园外的男子行酒令、放纵性欲、或者缺乏活泼的诗心,而园外的女子则忙于家族事务。在此大观园的世界中,女儿们的鲜活的主体特质逐渐地被建立起来,而她们的诗作也都表征了她们的性格与形象。以诗作为表述形式,看似全盘模拟重复了父权制文明下的形式与标准,就如探春初发起成立诗社,邀请众姊妹来共襄盛举时的动机即是:“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勤之雅会,让余脂粉”。(卅七回),此中女儿们意不在论述上建立一套颠覆主流论述形式的“阴性书写”(ceriture feminine)〔23〕, 而是借用了男性文明由来已久的“言志”形式来呈现他们的主体性。诚如伊莉葛来(Luce Irigaray)的分析,可知女性在父权制下, 是没有本身之语言的,而只能模仿男性论述,故连作品也无可避免会是如此〔24〕。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展现了在父权制下,女儿不被角色规定的生命风采,就这点而言,从香菱(薛蟠妾)的由园外移置园内后,方能开始学做诗(四十八回),更可清楚见出大观园已成为女儿耀动生命光华的主要空间了。而这也可说是大观园所具的较积极性的功能。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表征他们主体的诗作,和园外世界的关系是如何?就这点而言,宝玉和探春黛玉的对话极堪玩味。在四十八回中,便有这么一段描写:
宝玉道:“…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傻酿懈纭薄w煊裉酱禾担嫉溃骸澳阏嬲婧郑*
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
由探春黛玉的反应可知,虽有作品为人所欣赏的欣喜,但她们却不愿自己的诗作往园外流传,而与男性的论述相结合。六十四回的宝钗亦是此种态度,虽宝钗向来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但仍认为诗作“传扬开了,反为不美。”她们不愿诗作外传,事实上,我们可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解读。首先,女性在以男性为主的父权制中,往往是群被视作“客体物”(object)的存在,而在严男女之防的礼法社会中,女性更是一被撩拨起极大好奇的“偷窥”的对象。故而,凡与女性相关的事物或者是其书写的创作,便往往是以男性为主的主流论述所欲窥论品评的对象〔25〕。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借由诗作来展现他们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他们在其中相互品评,玩笑取乐,但一旦诗作外传时,他们原来自足性的主体存在,便会在转瞬间成为了客体,而且是他们并不认同的父权制下的男性标准的客体。诚如黛玉曾针对宝玉说道:“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六十四回,宝玉而后也同意了:“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这样的心态,倒也和她自比为花,乃“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心境不谋而合。
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借由诗展现了他们的生命力和创作力(七十六回的黛玉与湘云联诗,真可谓是女儿们创发力的极致表现),并为他们的天地,点染出更多的色彩。但这些与园外的父权制的男性文明是不相关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隐匿”在父权制中,在不教人窥视的女儿们的共识中,存全了他们的主体性,当然,这仍拜于大观园为他们区隔出来这样一个有效的空间。那么,当家族中象征父权的贾政、贾赦入园时,情况又是如何?我们可见女儿们的才情和主体性,则更是自然地“隐匿”了起来,七十五中即描写到贾赦、贾政一同与贾母及众人在“凸碧山庄”上赏月,不仅宝玉“踧踖不安”, 甚且一干有才情的女儿也都安静消音了,唯待贾政等人离了园子,女儿们才又重获了发言的机会,而女儿们的诗情诗才亦方才有了跃动的可能(黛玉与湘云精采的联诗,即是一例)。
就父权制的序列结构而言,大观园的这种“隐匿”性,更是展现在尤二姐的未被收编前的安置上。
在六十八回中,贾琏背着凤姐在外偷娶了尤二姐,凤姐得知后,便趁着贾琏不在,假作好人地对尤二姐说道:“你我姊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谏劝二爷……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谏丈夫……”,使得尤二姐便放心地随凤姐进了贾府,但因此事乃在贾琏服孝中所做,不合“孝悌”道德原则之要求,再加以此事又尚未禀明贾母(贾府女眷中位阶最高者),故而,大观园便在此时展现了它的作用。
凤姐即对尤二姐说道:“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姊妹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园里住两天,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时再见方妥”,由于尤二姐尚未被“明媒正娶”,自然便在不被公开(凤姐一一的吩咐的众人:“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的情形下,住进了大观园,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还未被“正式”收编入此父权制“名”的序列结构中之前,大观园相对说来扮演了一“隐藏”的功能,由于在空间上的一种隔绝性,使得园内也暂时成为了绝佳的隐匿之所。果然,直待尤二姐见过贾母,首肯之后,尤二姐才“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住居”。
大观园此一女儿国,不论是面对父权制文明、父权制结构或者是面对家族中的父权象征,它都以隐匿的方式来因应、而这也可说是它的一种生存之道。因此,它有别于西方的压迫/反抗的对应父权制方式,而展现了属于“中国式”的因应策略。
大观园除了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外,它还为女儿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空间。大观园的“逃避”性,主要可在以下几段事件情节中得到说明:
(一)平儿避居大观园
在四十四回中,贾琏趁著凤姐在贾母处乐和着过生日,便和鲍二家的在房里私通,凤姐得知消息,带着几分酒意走至窗前,正巧听到他们咒自己赞平儿,气不过地便“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之后,便边骂边打人。贾琏也因吃多了酒,便上来踢骂(平儿)。凤姐又把气转架给平儿,“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最后闹到贾母那儿,还是尤氏等人说了公道话:“……平儿没有不是,是凤丫头拿着人家出气。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平儿委曲的什么似的呢,……”在这场混战中,因着贾琏的婚外偷腥,而使得平儿无故遭此飞来横祸,但因着自己妾的身份,且又正当是凤姐的生日,且看平儿如何自处?
此处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描写,让平儿避开了这个平白受冤,教自己有口难辩的场面,——“原来平儿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情节描写中,平儿受到了宝钗、袭人的好言安慰,更且得到了宝玉尽心的温慰与照顾——“好姐姐,别伤心,我替他两个赔不是罢。”“‘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换了下来,拿些烧酒喷了熨一熨。把头也另梳一梳,洗洗脸’一面说,一面便吩咐了小丫头子们舀洗脸水,烧熨斗来……,‘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宝玉忙走至妆台前,将一个宣窑瓷盒揭开,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簪花棒,拈了一根递与平儿。……宝玉又将盆内的一枝并蒂秋蕙用竹剪刀撷了下来,与他簪在鬓上”。后来,李纨打发丫头来唤他,当晚,“平儿就在李纨处歇了一夜”。
受了委曲的平儿避居到了大观园,得到了身心的全面照顾与尊贵的对待,在这事件中,大观园完全展现了它的“逃避”功能,使得女儿们可以逃进园中,得到暂时的安顿。
(二)鸳鸯心烦逃至园中
在四十六回中,因贾赦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头鸳鸯,“禀性愚强,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的邢夫人,便支使着凤姐一同到贾母处来,先来探问探问鸳鸯,鸳鸯虽获贾母欢心,但毕竟只是个丫头,当着邢夫人面,不知如何拒绝,只能用“低了头不动身”“只管低了头,仍是不语”的沉默来传达他的不愿意,邢夫人以没有人会“放着主子奶奶不作,倒愿意作丫头”的心理来揣度鸳鸯,便一头热的,径自进行着。且看此时的鸳鸯如何抒解情绪——“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必在凤姐儿房里商议去了,必定有人来问他的,不如躲了这里”。
就这样,鸳鸯心烦气闷地“躲”进了大观园。
平儿(早先已进园)和“将来都是做姨娘”的袭人,先是和她取笑,而后才在对话中,引得鸳鸯道出了她的心声:“我只不去就完了”“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作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而后,鸳鸯的嫂子寻至园中相劝,不仅被鸳鸯讥讽,而且平儿、袭人也帮着抢白一顿。这三人后来便一同随宝玉回怡红院来。“宝玉将方才的话俱已听见,心中自然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
鸳鸯的怨、鸳鸯的怒、以及她的不顺从,都在躲进这个园子后,得到了暂时的舒解,而那纷扰且充满了令人气闷无处发的世界,也都暂时地被隔开了,大观园可说是在鸳鸯不知所从、强大压力逼临时,所最先想到的去处。
(三)迎春嫁人后的重返逃避之处
由于贾赦的作主,大观园内的女儿迎春便嫁给了所谓的世交孙家。在七十九回中,描写到邢夫人等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宝玉“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倏然,……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由于迎春的出嫁,引得宝玉大为感伤,园内之景物亦增添悲凄的气氛,诚如宝玉跌足自叹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另陪嫁四个丫头过去),女子的命运只有宝玉能感同身受了。
到了八十回,描写迎春回贾府,方哭啼地诉着委曲,原来孙绍祖是“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又说老爷曾收着他五千银子,不该使了他的。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脸说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迎春“被安排”嫁给孙绍祖的原因,以及他后来悲惨的生活,都在这里得到了说明,他的婚姻可以说就是:自己的父亲为了私利而和自己的丈夫所定订的买卖与交换。虽然,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从小儿没了娘,…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但这一切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事实,面对着强大的父权制的威逼以及自己无力改变的悲惨命运,迎春此时所想的,便是亲近的姊姊妹妹和大观园了。
且看迎春说道:“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记挂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还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由她的自白中可知,迎春于回贾府时的最大心愿,其实便是重回大观园了,因为那儿有她“过了几年心净日子”(迎春语)的痕迹,而那也实代表着众女儿们的曾经快乐无忧的自在天地,在迎春遭受痛苦折磨时,大观园隐然也成为,她可以暂时逃开平日丈夫所加诸在她身上桎梏与魔咒的地方。
以上的叙述都在说明大观园女儿国所展现的存在特色,它的重点不在于与父权制做“正面的”、“公开的”对抗,而是默默地采行了一种“非公开”的“潜藏”之道。事实上,大观园以“隐匿”与“逃避”作为它因应父权制种种的策略,实不能维持长久,因为,当隐匿“被揭开”,逃避“被发现”时,大观园相对于父权制的存在基础,便容易产生了动摇,而当女儿国的存在精神不复往日时,便也同时暗示着大观园可能瓦解与衰败的命运。
四、大观园暴露公开后的走向衰亡
大观园作为一个“清净”、“理想”的女儿国而言,走向衰亡似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命运,诚如余英时所以为的:“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26〕但是,若从父权制的角度来看,大观园的衰亡尚还有其他的必然因素。
大观园因为有了姊妹的进入,方才构建了一个有别于园外的世界,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有别于父权制的世界。在其中没有以父权标准所建立的位阶关系,一切都以女儿的活动、女儿的谈笑、女儿的论述为主,所充满的一个女儿文化的世界。而唯一能加入其中的男子宝玉,亦就是奠定在能强烈认同于此,甚至,强烈视此为尊的基础之上,方能成为其中一员的。是以,大观园乃能成为一个独具女性色彩的地方。然而,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大观园的成立,却原就有它依附父权制的基础,亦就是说,在父权制的一定条件下,方才有了所谓女儿国的出现。而事实上,吊诡之处也在这里,因为,没有一个结构能真正彻底独立于支配结构以外〔27〕。因此,大观园虽展现了它的独特性与主体性,但在父权制的体系底下,大观园仍不可免的受到了它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我们可以说它是既独立于其外,而又内含于其中的。因此,观察大观园的衰亡,便要由此入手,方能进一步突显出“被发现”“被公开”之后,对大观园带来的杀伤力。
首先,就园内的女儿而言,诚如宝玉所以为的:清净洁白的女儿一旦沾染了男子的浊气(指女儿出嫁),或者一旦认同了父权制文明的价值标准,入了国贼禄蠹之流,那么,女儿的纯净便容易消失了〔28〕。姑且暂不论女儿失去纯净本质的说法,是否会瓦解了女儿国,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宝玉的说法确实暗示了,若女儿被收编在父权制的序列结构中时,他便失去了女儿们共处一地时,所享有的主体自由与自在,亦就是,他开始要为了他的角色位置尽责任与服膺父权的义务;这也饶堪玩味,为何园内的女儿若不是特殊如丈夫已死的李纨,便多的是父亲不在的身份了,如黛玉、湘云、宝钗、惜春、妙玉、香菱、袭人、晴雯等,以及尔后加入的邢岫烟、李纹、李绮、薛宝琴等人,亦都是如此。这些女儿们只有在父亲过世,父权暂被稀释的情形下,方有机会寻得自己片刻的自由,亦方才有可能加入这女儿国的行列。即便是有贾政此父在上的宝玉、探春,他们在大观园内做诗行乐、诗社达至巅峰状态时,亦是贾政离开贾府的这段时间;贾政自卅七回钦点学差出远门时,便正是探春发起成立诗社之时。
但女儿们终须面对父权制网络的再次收编,从大观园的隐匿与逃避中再次进入,因着“嫁人”此被命定的选择,女儿国的四散而去,便是可以预见的结局。在前八十回中,即以迎春的出嫁来标示着身为女性,在父权制底下的永难摆脱的命运。此不是仅如宝玉所言的,出了嫁便是颗没有光彩的死珠子(五十九回)的情形而已,而是女儿被收编在父权之下后,他原有的生命光华所散发的主体特质,便愈见消失,而转而成为一从属的、为扮演在夫家家族中的被规定的角色而存在。
而若当女儿们倾向于认同父权制的结构和标准时,自然也易自女儿国中出走。大观园中,明显有此倾向的,便是“随分从时”的薛宝钗了,是以,当大观园被抄、出现了颓象与不祥时,隔天,他便轻易地即刻搬离。宝钗的说辞是:“只因今日我们奶奶身上不自在……我今儿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儿。……等好了我横竖进来的……”(七十五回),自然,这番表面上的说辞,让当场的李纨、尤氏皆了然于胸“李纨听说,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只看着李纨笑”,而宝钗确也从此再没进了园子。他的离开大观园,不再与其他女儿为伍的作法,实可由此来做另一角度的理解。
而残酷的事也在于,七十四回中,王夫人的下令抄检大观园,确实标示着大观园女儿国的走向衰亡。因为经此一抄后,宝钗搬出、晴雯(宝玉的大丫鬟,没多久便病死)、四儿(宝玉的小丫鬟)、司棋、入画(迎春与异春的大丫鬟一辈)被逐、及一干原各姊妹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亦一概被发配出去。如此一“整治”后的大观园,失去了往日欢乐、热闹的情景,且看宝玉来到宝钗住的蘅芜苑的描写:“只见寂静无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宝玉默默出来后“又见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各处房中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悲感一番,……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七十八回)。
而在这一片女儿国的凋零声中,我们不禁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会面临被抄检的命运?抄检的行动对大观园而言,意味着什么?又,大观园的存在策略在此次行动中,为何无法奏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以了解在“女儿出嫁”此不得不让女儿国最终散了的命运到来之前,何以抄检一事,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它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又是什么?
大观园的被抄检,它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在七十一回中,因为司棋和表弟潘又安于园中厮会,不小心遗下了上有春宫图的“绣春囊”而引起的。因这“绣春囊”为痴丫头傻大姐所拾,而后又遇着邢夫人,邢夫人将其转交给王夫人,故便由王夫人下令,凤姐领命,和王善保家的及周瑞家的来趁夜抄检大观园。
这个事件有人以为,乃因此囊污了这女儿国的“清净”之地,所以才遭致此运,或者是否因司棋与人在“清净”之地,意欲干下男女之事,引此“浊气”,方才导致女儿国的衰亡,又或者,从四十九回平儿的镯子于园内被偷,而断言大观园的衰败,自此已露征象。以上的这些说法都有他看似合理之处,却也极为片面,因事实上,我们从大观园的成立、它的存在特质(隐匿与逃避)、以及它与父权制的关系来思考的话,便知道,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绣春囊”的“遗落”于大观园,或者是是否发生了男女之事,以及园内是否发生了不合于道德、不好(如偷窃)的事。而是,经过了“绣春囊”的“被发现”“被公开”,使得这种“揭开”与“暴露”的行动,再次严重地挫伤了大观园原本的存在状态。
就“绣春囊”这类带有春意、低俗的东西而言,它并非是不能拥有之物。早在王夫人获此物时,便原猜测可能是凤姐所有,关键不在于是否能“有”此物的问题,而是如王夫人所质问的:“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甚且,如果是“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七十四回),因此,一切的顾虑,关键都在于,这个东西若已“曝光”“为人所见”“为人所知”时,该怎么办?是以,在这种标准下,“绣春囊”的被发现,自然便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在中国父权制下,与“性”相关的东西,除了在夫妇伦常之名外,原就未被赋予一正当性价值,而在宋元以后,更由于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念甚嚣尘上且深入人心,使得被视为“人欲”的“性”,无法获有在正式、公开场合中被谈论的合法社会基础。是以,痴傻单纯的傻大姐,拾获此囊时,只觉得可爱有趣,不仅不识此囊之春意,更不知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禁忌,唯有在此父权制中,深深了解其运作规则的邢夫人、王夫人,才会有“严重”的反应:邢夫人是“接来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握住”(七十三回),而王夫人是“气色更变……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和凤姐说:“你婆婆(邢夫人)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说是前日从傻大姐手里得的,把我气了个死”(七十四回)。由于担心这个禁忌的公开会扩大,更且会再接二连三出现,因此才促使了抄检行动的产生。
王夫人带着父权制下的认训标准,为一劳永逸地解决此禁忌公开后的后果,便寻思要暗暗查出此囊背后的主人,逐了出去。因此,方才会采用了王善保家的之提议:“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七十四回)这趁着夜晚,神不知鬼不觉的抄检行动,“猛不防”地给向来“隐匿”在父权制中的大观园一个致命的一击。园内的女儿们由于空间上的区隔,自来便与园外父权制种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采行了隐匿与逃避的因应策略,而能在其中自由的活动。但这次的抄检行动,挟带着父权制标准的余威而来,是以,凡是不合此标准的人事物,便一并在此株连之内。
前文已提及,在中国父权制中,由于讲求孝悌与名位,女性可以因为成为母亲,随着儿子对孝道的依循而相对地获取了权力,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儿子也可说是母亲希望与权力来源之所系。对于王夫人而言,原就死了一个儿子(贾珠)在先,因此,宝玉对于王夫人之意义,自是又加深了一层,三十三回贾政痛打宝玉时,王夫人便伤心地哭道:“……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见宝玉被打重了,则更是“儿”一声,“肉”一声地:“……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个!”王夫人在这种现实情况和心理的前提下,他对宝玉的“保护”可说是更为严密了。因此,父权制象征的王夫人也才会在“金钏儿事件”的阴影下,趁着抄检之便,一并逐走了长得标致,有“勾引”之嫌的晴雯,以及长得“有几分水秀”与宝玉同一日生的四儿,而因“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王夫人语,七十七回),故也将原唱戏的女孩逐了出去。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宝玉平日与女儿们无伤大雅的玩话,由于旁人的私传告状,都成了“有一点分外之事”嫌疑的把柄,王夫人的提醒:“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七十七回),在在强烈地标示着:父权制所代表的标准,会不时地察鉴着大观园,让一切都无所遁逃。而这也是“抄检”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在这一连串的“揭开”之后,大观园此女儿国隐匿与逃避的存在策略,至此终于失去了它的效力。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趁父权制之名来行动的元妃,乃是以“女儿用心”来真正“让女儿自由”,而今王夫人却因母亲之私,顶着父权制之价值标准来摧残这个女儿国,不仅惊动了女儿,更是让原本保卫、呵护着女儿的宝玉,唯有“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真正失去了保护女儿的能力!
五、结语
大观园在所处的中国父权制下,原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原就不是为了姊姊妹妹们的女儿国所建的,因此,若没有中国父权制下名实的可能空隙,大观园女儿国根本很难产生。在这种情形下,它的相对于父权制,可说即是一个边缘与主流的关系,在此关系中,它并无意对男性主流文化与论述进行颠覆与对抗,它采行了一个隐匿与逃避的方式,来使自己得到抒展与自由,而这也是它对女儿们的最重要的意义。
而事实上,隐匿与逃避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个陌生的传统,历代凡是被排拒于社会权力中心之外,不为主流价值(如儒家)所容的男性文人,通常便会以这种方式来存全自己,而这些边缘,处弱势的男性文人,亦极易将自身处境,投射在同是边缘存在的女性身上〔29〕。例如“美人香草”之喻,以及以女性“画眉”之象征自喻的文学作品都可由此得到理解。而我们由这种现象,也可见到,在历史上常常消音了的女性,他的存在样态与心思,似也常透过社会边缘的男性文人之笔,巧妙地再现(represent)了出来。
在《红楼梦》这部文本中,我们即看到了,作者如何站在一个非主流的论述立场〔30〕,来细细描摹了一个女性的世界,在其中,也透显了作者对边缘存在的一种深刻的同情与了解。当然,在文本中所构作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一回)的真假、虚实之论述策略,亦或者乃再次提醒阅者眼目,大观园女儿国的看似真实的存在,事实上,亦不过只是社会边缘论述的一个虚幻的投射罢了!?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再深入探究的课题。
注释:
〔1〕为确保文本解读的完整性, 以避免由于出自不同的作者(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续之作者不同),在叙述脉络上的不同,而可能带来的不必要文本解读上的争议,因此,本论文的研究范围锁定在前八十回,用的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校注》,台北里仁书局,一九八四年。
〔2〕性别(gender)主要乃有别于性(sex),性(sex)是指从生物学上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指从文化上的所获得的对性的同一性认知。
〔3〕早在一九五四年, 俞平伯就曾强调了大观园的理想成分(俞平伯著《俞平伯论红楼梦》页六五一至六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而后一九七二年,宋淇发表了一篇“论大观园”,进一步说明了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收录于《大观园论集》)而余英时于一九七三年秋天,则以宋淇之文做为讨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起点,发表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强调了大观园所代表的一个理想世界的意义,及其与肮脏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密切的动态的关系,该文收于氏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近年来则另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周汝昌便以《红楼梦》中的实际描写来批驳“理想世界”立论之可议,可参见“大观园的情思”,《国文天地》七卷七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4〕较著名的例如朱崇仪的“大观园作为女性空间的兴衰”(《中外文学》廿二卷二期,一九九三年七月,该文精彩地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莉葛来(Luce Irigaray)的理论观点来分析大观园。
〔5〕参考自韩格理(Gary G.Hamilton)著,翟本瑞译“传统中国与西欧的父权制:韦伯支配社会学的重估”一文注十五,该文收入《中国社会与经济》一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
〔6〕此乃韦伯于《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一书中之重要观点,参同注⑤,页十八至十九。
〔7〕同注〔6〕。
〔8〕引自米勒(Kate Milletts)著《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P33.First Canadian Printing:July 1978。 此书乃六○年代以来,美国妇女运动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构成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发展之基础。
〔9〕该文乃Weedon的“Feminist Practice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的第一章,收录于王志弘编译《性别,身体与文化译文选》 ,页八,自印一九九五。另外,白晓红将其译为“克莉丝·维登”著《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一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四。本引文采自前者。
〔10〕策略(politics)用于此处, 主要乃从性政治策略(sexual politics)之角度而言,米勒(Kate Milletts)即从此角度强调了politics乃是一种“权力结构”(powerstructured)的关系, 是由于权力的配置(arrangement),方才导致一群人被另一群人控制。同注 ⑧,P31。
〔11〕《说文解字,又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方言》卷六:“艾,长老也…南楚谓之父。”
〔12〕车传鼎于《中国古代氏族分合与父权保存之关系》一文的研究:“在图腾社会的初期,多半以女子为首领,等到父系化以后,各阶层的首领就变成了男子,在中国称为父,父掌握着团体的一切职权。”由于中国乃一重宗族的社会,故而籍贯仍以其祖先的居住地为标准;而父家长的权威,就一家来讲,则展现在管理家产、管理妻妾、儿女婚姻、及儿女的惩罚上。《中兴大学文史学报》十八期,一九八八年三月。
〔13〕同注〔9〕,页廿五至廿六。
〔14〕儒家政治整体常被女性主义者辩为“父权共同体”(United Patriarchs),事实上,关于中国传统妇女的处境,女性主义者和当代新儒家便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向,前者是以儒家的道德体系,意识形态为维护父权社会的“势”而开出的“理”,而新儒家则以为男女不同的礼仪规范,夫妇有别等,乃道德主体据“理”而造成的“势”,关于此,可参见文洁华“儒家道德主体在父权社会中的理势问题”,《鹅湖月刊》十九卷八期,一九九四年二月。
〔15〕中国人的正名观念,自先秦孔子奠定了基础,到了荀子时,则赋与更丰富的内容,从对社会秩序产生的作用来看,名是“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荀子·正名》),到了汉董仲舒则提出“深察名号”之法,并以为名号的基础乃来自于天地,“治天下之大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6〕《说文解子·老部》:“孝,善事父母者”,《尔雅·释训》:“善父母为孝”,《墨子·经上》:“孝,利亲也”《说文新附·心部》:“悌,善兄弟也”,《墨子·兼爱》:“为人弟必悌”。《论语·学而》:“孝弟(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考与悌是中国宗法制度下的一根本性的道德,孝悌的强调亦可说是维护家族私有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根本。总括说来,孝乃善事父母,所以利亲,而悌乃善事兄长,所以和顺。
〔17〕“拿捏分寸”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的是个人以心思度量来操持、调节自己身、心与外在对象或环境的合宜关系。名的拿捏分寸化,使得名的系统可在不需变动的情形下,而能对名的实际运用有一更具弹性的空间。有关“拿捏分寸”的研究,可参见蔡锦昌《从中国古代思考方式论较荀子思想之特色》第一章,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八九。以及邹川雄《拿捏分寸与阳奉阴违——一个传统中国社会行事逻辑的初步探索》第一章及第二章,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一九九五年六月。
〔18〕莫伊(Toril Moi)《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26,19 85,New York:Methuen.
〔19〕贾元春和大观园在早期稿本中是尚未出现的,很可能最晚在第四次增删稿时方才出现,相关资料和论证参见朱淡文《红楼梦研究》,页一○一至一○四,台北贯雅文化公司,一九九一。
〔20〕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齐评语辑校》页四五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六。
〔21〕参见戴志昂《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艺术”一文,收于《大观园论集》。除此,《红楼梦》十七至十八回写至贾政等人游园时,即多有泉、河、池、水等的相关描述,甲戌、庚辰本之脂批亦云:“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同注〔20〕,页二九七)
〔22〕女性主义者在语言性别歧视的研究中,常有的一个议题便是“命名”的问题,他们甚至认为“有权力命名世界的人就有权力影响现实”(Kramarae Cheris "Women and Men Speaking.Frameworks forAnalysis"p165,Rowley,Mass.:Newbury House 1981)
〔23〕《阴性书写》主要是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Helene Cixous)的主张,他强调在父权制二元性系统中(如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父亲/母亲、男性/女性),男性永远是较高层级,因此,唯有不停的动摇传统阳物中心主义,打开封闭的二元对立关系,才能真正欢愉在开放式文本书写中,西苏主要在打破所谓传统父权制语言,而展现一种流动式的,带有阴性之欲流(libidinal femininty)的书写形式, 此中,重要的并非作者性别,而是书写所展现之性别。参同注〔18〕,p102—126。另参黄逸民“法国女性主义的贡献与盲点”, 《中外文学》二十一卷九期,一九九三年二月。
〔24〕同注〔18〕,p140。
〔25〕明清时期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大量女作家的记录,他们从事的创作,如诗词,戏曲,或者是弹词小说,近年来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与研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在文学史的论述中,没有被编写进来,除了作品的质与量值得重新考虑以外,似乎也意味着,他们无法成为满足被男性窥视青睐的标准与内容。在文学典律(canon)形成的过程中, 由于男性掌控了论述权,使得女性往往不容易成为“有效”的发言主体。
〔26〕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六十一。
〔27〕此亦正如同美国女性主义者修华特(Elaine Showalter)对“女性写作史”及“女性的写作”所反省的:“没有真正能彻底独立于支配结构之外的写作或批评,没有能完全独立于支配结构之外的写作或批评,没有能完全独立于男性支配社会经济与政治压力外的出版物”。就相对于父权制结构而言,女性之存在确是如此。修华特(Elaine Showalter)著,张小虹译“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外文学》十四卷十期,一九八六年三月。
〔28〕宝玉于宝钗劝诫时,便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卅六回),宝玉又曾云:“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七十七回),或者由丫鬟春燕转述了宝玉说的:“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了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五十九回)以上均可见出宝玉对清净女儿的可能改变而有的慨叹。
〔29〕《周易·坤·文言》:“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此地道、妻道、臣道,便是“坤”的具体化表现,此乃相对于“乾”卦所言之“天、夫、君”而有的思考,其中自然便隐含着,一个见弃于君的臣子,往往将自己比作一“弃妇”的心理基础。事实上,战国时期,被放逐的屈原于“离骚”中以弃妇来自比,便是在天/地、君/臣、夫/妻的对比关系中来立说的,因此,于文学作品中,男性文人藉由深入女性的角色和心理,来代言己志,可说於先秦时便已奠定下基础。
〔30〕作者非主流的论述立场,从第一回的“作者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绮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以及他透过书中主角贾宝玉之口批驳“仕途经济”“文死谏”“武死战”此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人生价值之所在,均可知作者隐然呈现了一种非传统主流价值的论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