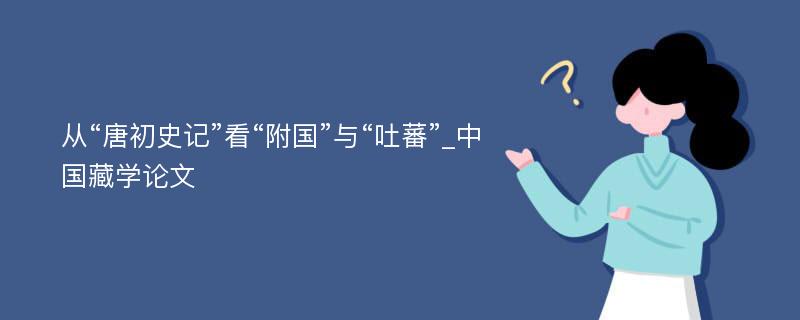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46年岑仲勉先生发表《〈隋书〉之吐蕃——附国》一文,提出“附国即吐蕃”观点并引发“附国是否为吐蕃”的争论以来,(注:解放前该问题的争论主要在岑仲勉与任乃强两人之间展开。参见岑仲勉:《〈隋书〉之吐蕃——附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任乃强:《附国非吐蕃——质岑仲勉先生》,《康藏研究》第4期,1947年,岑仲勉;《从女国地位再讨论附国即吐蕃》(附任乃强答案),《康藏研究》第10期,1947年。)
迄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中,学术界有关附国的研究虽取得不少进展,但在“附国是否为吐蕃”问题上却仍存在不同看法。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再趋活跃,发表的较重要论文有汤开建“隋书>之附国非吐蕃》、(注:载《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
孙尔康、唐景福《〈隋书〉之附国即早期吐蕃(悉勃野)》、(注: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杨嘉铭《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注: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等,另在其他一些相关论著中也都涉及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
(注:涉及附国问题的其他论著还有: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其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敬洵:《七至九世纪川西高原部族考》,《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唐嘉弘:《吐蕃族源及相关问题》,《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田晓岫:《吐蕃王族族源新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等等。)
从目前看,虽多数学者主张“附国非吐蕃”,但也仍有一部分学者持“附国即早期吐蕃”的观点。(注:目前主张“附国即吐蕃”的学者主要有孙尔康、唐景福、田晓岫等。马长寿先生虽未具体论述附国问题,但倾向于岑仲勉的观点(参见《氐与羌》,第29页)。格勒在《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其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一书中主张“附国即吐瞢”’但在后来的论文中则放弃了此观点,认为附国非吐蕃。参见格勒:《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笔者以为,该问题所以长期悬而未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有关附国的原始记载仅见于《隋书》、《北史》两书,两书的记载基本雷同且较为简约、模糊,更重要的是两书对附国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人唐以后的情况均未作任何记载,这是“附国即吐蕃”之说得以立足的关键;二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附国是否为吐蕃”的争论主要是围绕《隋书》、《北史》两书《附国传》所述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的比较来进行。由于附国、吐蕃同处青藏高原范围,两者的地理与人文特征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就造成了争论双方长期各执一词、彼此难以说服对方的局面。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澄清“附国是否为吐蕃”这一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视野,即跳出以往以附国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进行比较的讨论范式,着重从“附国即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记载附国的史料产生之背景来审视此问题,也就是说主要从观点及史料的发生学角度来进行一番探讨,这或许可使我们对此问题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拟依循这一途径,试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作一讨论。
从根本上说,岑仲勉当初之所以产生“隋之附国,即唐之吐蕃”的看法,诚如其所言,主要是基于“吐蕃”一名在唐初“突然而起,隋人尚无所知,颇令人大惑不解”,故以为“隋之附国,即唐之吐蕃”,“如是,则《隋书》传与两《唐书》传可大致相接,吐蕃之出现于唐初,无突如其来之异”。而对“附国”一名在入唐以后全无踪影,岑仲勉作了这样的解释:“奈唐人自始即不知凭何族(吐谷浑?)言语,繙为吐蕃,后此更不追寻其本国之土名。夫吐蕃为患,几与唐朝相始终,以关系如是之深,竟不知其初以附国名著。”(注:均引自岑仲勉:《〈隋书〉之吐番——附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显然,岑仲勉认为在入唐以后“附国”一名被转换成了“吐蕃”,转换原因是唐人依据别族(岑疑为吐谷浑)的浯言将原来的“附国”叫成了“吐蕃”。当然,这只是岑仲勉为求证其观点所作的一个逻辑推测,并未给出具体证据。但此推测从发生学上看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预设:即唐人只知“吐蕃”而不知有“附国”,因为在唐人那里“附国”已转换成了“吐蕃”。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先来看记载附国的史料形成之背景。我们知道,《隋书》的修撰始于唐贞观三年(629),是年唐太宗诏魏徵等人修隋史,贞观十年修成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共五十五卷。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又修成梁、陈、齐、周、隋之《十志》三十卷,其后将《十志》编入《隋书》,共为八十五卷,(注:参见(唐)刘知几:《史通》卷12《古今正史》;《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隋书》。由此可知,《隋书》的传(包括其中的《附国传》)是在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期间修成的。而据新、旧《唐书》和《通鉴》的记载,吐蕃首次向唐朝贡的时间是贞观八年。《通鉴》载:“贞观八年十一月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注:《遇鉴》卷194《唐纪》10。)这是唐、蕃通使之始,(注:《旧唐书·吐蕃传》记此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新唐书·吐蕃传》也作“始遣使朝贡”,与《通鉴》的记载一致。惟所记月份有差异,《唐会要·吐蕃》卷97作“贞观八年九月,朝贡使至”,《通鉴》记“贞观八年十一月甲申”,《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使三》卷970作“贞观八年十一月,吐蕃……并遣使朝贡”。苏晋仁认为:“三书所记月份虽有不同,应是同一件事。九月是使者来到的日期,十一月则是朝见的日期。《通鉴》的甲申日是根据《太宗实录》来的,应确实可信。”参见苏晋仁:《唐蕃使者之研究》,《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苏晋仁认为此记载中的甲申日,当是据《太宗实录》而来,(注:苏晋仁:《唐蕃使者之研究》,《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第2页。)而且在吐蕃首次遣使朝贡之时记录吐蕃之基本情况也符合《实录》的惯例,所以此记载依据《太宗实录》写成当无问题。从这段记载看,至少在贞观八年,唐朝对吐蕃的地理位置、疆域、兵力乃至其日渐崛起的势头显然已有所了解,并特别提到吐蕃“未尝通中国”,这当然是指贞观八年以前的情况。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贞观八年《隋书》的修撰正在进行之中,《隋书》中既然有《附国传》,那么唐朝史官对“附国”的情况显然是了解的。而且可以肯定,记录“贞观八年十一月甲申,吐蕃赞晋弃宗弄赞遣使入贡”一事的最初蓝本——《太宗实录》同样出自唐朝史官之手。这就意味着在贞观八年之时,唐朝史官显然既知“附国”,也知有“吐蕃”,并不存在岑仲勉所说已将附国“繙为吐蕃”的情况。唐初史官既然是在完全知晓有“附国”的情况下来记录“吐蕃”使臣朝贡及吐蕃之基本情况的,其将“附国”与“吐蕃”相混淆的可能性就极小。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贞观八年当吐蕃首次遣使朝贡时,唐朝史官对吐蕃基本情况的记载与《隋书·附国传》的记载相去甚远:第一,附国是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吐蕃则“在吐谷浑西南”。第二,附国在“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入朝”;吐蕃则“未尝通中国”(这里用“中国”而不用“我朝”或“唐”,清楚地表明这里的“中国”应包括唐以前的中原王朝)。第三,附国“国有二万余家”;吐蕃则“胜兵数十万”。以上第二、三点尤能说明问题。唐初的史官既然是在修撰《隋书》(包括其中的《附国传》)过程中记录下吐蕃使臣来访一事的,并称吐蕃在贞观八年以前“未尝通中国”,这就说明唐初史官心中清楚地知道“附国”不是“吐蕃”。因为《隋书·附国传》明确记载附国在隋“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对这一点唐初史官十分清楚。此外,《隋书·附国传》还记载:“(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说明隋时已将附国纳入其管辖范围。虽从“遥管之”的记载看,这种管辖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既然将其归于“西南边诸道总管”管辖之下,说明附国的地域当在西南的范围。而据《通鉴》记载贞观八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未尝通中国”;《隋书·吐谷浑》云,吐谷浑的位置是“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故吐谷浑的位置应在今甘肃洮河之西、以青海湖为中心的“数千里之地”。吐蕃既在吐谷浑的西南,那么这一位置显然已远超出西南的范围。《旧唐书·吐蕃传》云:“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也说明吐蕃的位置在更遥远的西方,而不在西南。贞观八年去隋仅17年,附国在隋既已置于“西南边渚道总管”的管辖之下并有明确的朝贡记录,若“附国”为“吐蕃”,那么贞观八年吐蕃使臣来朝之时,唐朝史官就绝不会有“未尝通中国”的记载。关于吐蕃在贞观八年以前未曾与中原隋、唐王朝发生直接关系这一点,我们从现有的汉文或藏文史料(包括吐蕃敦煌藏文写卷和后弘期的藏文史料)中完全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也可获得间接印证。(注:在现有的汉文和藏文史料中,目前笔者未找到贞观八年以前吐蕃曾与隋、唐王朝发生直接联系的记录。
)《隋书·西域传》中共列有23国的传记,其中包括了吐蕃外围的吐谷浑、女国、党项、附国、于阗等诸国,但所有这些列传诸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有向隋朝贡的记录。(注:参见《隋书》卷83《西域传》中所列诸国之记载。
)因此可以肯定,《隋书》对周边诸国列传的标准乃取决于它们是否与隋有朝贡关系。从敦煌藏文写卷的记载看,吐蕃向外扩展势力虽始于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色(stag-ri-gnyan-gzigs)在位之时,(注: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1页。)时间大体应与隋相当,但其时吐蕃的中心还主要限于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河谷一带,它的北面有苏毗、吐谷浑两个大国的阻隔,东面及东北方向则有附国和党项的阻隔,所以吐蕃未能与隋朝发生直接关系并不奇怪。就隋朝方面来说,由于吐蕃没有使臣入隋,隋对吐蕃的情况不详,没有原始记录,故《隋书》不立吐蕃传。贞观八年,正值修撰《隋书》的唐初史官对此情况当然甚为详悉,这也是吐蕃遣使入朝之时唐朝史官能断言吐蕃“未尝通中国”的原因。此外,从前面的第三点看,《隋书·附国传》记附国“国有二万余家”,《通鉴》所记贞观八年吐蕃则是“胜兵数十万”,我们姑将“国有二万余家”看做是大业四年(608)隋朝从附国朝贡使臣那里获得的数据,但大业四年距贞观八年仅相去26年,若附国即是吐蕃,那么就很难解释其何以在短短26年间由“国有两万余家”忽然变为“胜兵数十万”?我们难以否认后者数字可能有夸大成分,但关于当时吐蕃军队数量尚有一个重要参照:若把“胜兵数十万”视为贞观八年吐蕃使臣入贡时唐朝史官对吐蕃军力的一个粗略估计,但仅四年后即贞观十二年吐蕃出兵攻松州是“率众二十余万”,(注:《通鉴》卷195《唐纪》11。)可见吐蕃“胜兵数十万”估计并不是太离谱。即便再将附国扩张的因素考虑在内,也断难在如此短时间内形成如此巨大的悬殊,这只能说明“附国”不是“吐蕃”。
或许有人会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贞观八年吐蕃始遣使入贡时,因为是首次,唐人对“吐蕃”的具体内涵并不十分清楚,所以仍存在将“附国”与“吐蕃”相混淆的可能。假如说,在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修撰《隋书》(包括《附国传》)过程中吐蕃使臣来朝确系唐朝初识“吐蕃”,尚有这种可能,那么,从《北史》(内有《附国传》,与《隋书·附国传》基本相同)的成书时间则可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北史》为唐初李延寿撰,李延寿在唐太宗时曾受诏先后参与《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修,后在其父旧稿基础上,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北史》完成于高宗显庆初年,显庆四年由朝廷批准流传。(注:参见《北史》卷100《序传》;《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李延寿既参与《隋书》的编修,又撰《北史》,故两书之《附国传》应有承袭关系,即《北史·附国传》当以《隋书·附国传》为蓝本,这是两书《附国传》基本相同的原因。但《北史》成书时间较《隋书》晚25年,这25年中唐朝与吐蕃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交往:贞观十二年吐蕃以唐朝不许婚,出兵二十万进攻松州,唐蕃交战于松州;贞观十五年唐朝嫁文成公主于吐蕃;贞观二十一年唐朝出兵攻龟兹,吐蕃受命连兵进讨;(注:参见《通鉴》卷198《唐纪》14。)贞观二十二年唐使臣王玄策出使中天竺被掠,吐蕃发精兵与王玄策击天竺,大破之,吐蕃遣使献捷;(注:参见《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贞观二十三年唐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封“西海郡王”。(注:参见《通鉴》卷199《唐纪》15。)永徽元年(650)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薨,唐高宗“举哀于光化门,遣右武侯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往吊祭之”。(注:《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一》卷974。)另外从唐蕃交聘记录看,贞观十年到永徽元年的15年中,吐蕃使臣入唐有18次,唐使入蕃有5次。(注:参见谭立仁、周原孙:《唐蕃交聘表》,《中国藏学》1990年第2-3期。)在显庆四年颁行《北史》以前,唐蕃之间的交往既然已达到如此频繁、深入的程度,那么唐朝史官将“附国”与“吐蕃”相混淆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从曾参加《隋书》修撰工作的李延寿在其后撰写《北史·附国传》时仍沿袭《隋书·附国传》之旧貌而未作改动这一点可以证明,即便在唐与吐蕃有了深入的交往接触和唐对吐蕃有充分了解之后,唐朝方面也仍明确地将“附国”与“吐蕃”区分开来。由此可见,不论是贞观十年修定的《隋书》还是显庆四年颁行的《北史》,在唐初史官心目中始终一以贯之地知晓“附国”与“吐蕃”并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绝不存在将两者混淆或所谓将附国“繙为吐蕃”的情况。所以,从唐初的史料来看,“附国”是附国,“吐蕃”是吐蕃,这一点在唐初史官笔下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在记载中两者的差别也非常明显。换言之,将《隋书》中的“附国”说成是唐之“吐蕃”的观点,我们在唐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
事实上关于附国非吐蕃,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附国问题的讨论中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汤开建在《〈隋书〉之附国非吐蕃》一文中曾提及他新发现的有关唐初“附国”的两条重要史料:其一,保存在《广川画跋》中关于唐初由阎立本画成的《王会图》的一段文字记录:“鸿胪导客,次序而列,凡国之异,各依其方。东首三韩……西首以吐蕃……其南首以交趾……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国、筰等次之……”,(注:(宋)董逌:《广川画跋》卷2《上〈王会图〉叙录》。)对阎立本作《王会图》的时间,《图画见闻志》卷五载事在贞观二年,《广川画跋》卷二载为贞观十七年,但其为贞观时所画可以肯定。既然在贞观年间“吐蕃”与“附国”均作为向唐进贡之国出现于同一幅图画中,这就清楚地说明附国不是吐蕃,其二,贞观时由阎立本所作另一幅画《西域图》中也列有附国,并有关于附国服饰的文字记录,该文字保存于《剡源文集》中。(注:参见(元)戴元表:《剡源文集》卷4《唐画〈西域图〉记》。)这也说明附国在贞观初年仍然存在。以上两条尤其是第一条,已可充分说明附国并不是吐蕃。(注:参见汤开建:《〈隋书〉之附国非吐蕃》,《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此后李敬洵的《七至九世纪川西高原部族考》(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一文也引证以上材料来说明附国非吐蕃。)以上两条史料虽存于宋元人的文集中,但真实性却可由《新唐书》得到印证。我们知道,后晋刘眗所修旧《唐书》中未立附国传,而北宋欧阳修重修的新《唐书》中却立有附国传。这表明在北宋欧阳修重修《唐书》时其所依据或参考的史料尚能清楚地表明附国不是吐蕃。否则《新唐书》中既列有吐蕃传,又立附国传,就成为不必要的叠床架屋,逻辑上也断难成立,这也同,样清楚地表明在《新唐书》的作者乃至宋代文人眼中附国绝非吐蕃。而对《旧唐书》不立附国传惟《新唐书》立附国传,汤开建作了这样的阐释:“《新唐书》既立吐蕃传,又立附国传,是因为太宗时,吐蕃与附国都与唐有政治上、外交上的联系,也都曾入贡于唐,虽然附国后已亡于吐蕃,如要全面反映唐之外交关系,则附国也应列传,其他如苏毗、羊同、东女莫不如此。《旧唐书》对这类‘亡国’多不立传,实为其疏,此亦见新书之见地较旧书为高。”(注:汤开建:《〈隋书〉之附国非吐蕃》,《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此分析颇为精当而具说服力。综上所述,附国非吐蕃,已可为定论矣。
标签:中国藏学论文; 吐蕃论文; 唐朝疆域论文; 唐朝论文; 吐谷浑论文; 旧唐书论文; 新唐书论文; 太宗实录论文; 隋书论文; 思想战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