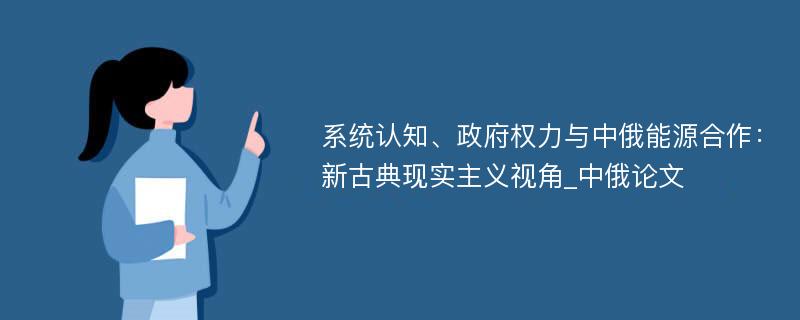
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中俄论文,视角论文,认知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能源合作,学术界向来存在经济或政治两种分析路径。“经济路径”突出能源的自身特性和市场属性,对能源贸易进行定量分析,但其“供给—需求”模式无法解释能源合作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学”的内容。“政治路径”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中。在当前的俄罗斯能源外交研究中,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是主要的分析框架,该理论把能源资源的获取视为一种冲突来源,把能源贸易视为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倾向于对管道地缘政治进行零和分析,能源安全被视为国家外交决策大博弈中的重要考量因素。①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欧俄、中俄油气合作研究中,国外学术界甚至为中石油的公司行为贴上“能源驱动的重商主义”标签。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沙德瑞纳(Shadrina)认为,由于俄罗斯在国际能源舞台上同时扮演着生产国、消费国、出口国、进口国和过境国的多重角色,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其能源政策在时间上的灵活性和空间上的多样性。②目前,俄罗斯能源研究中出现了更加注重政治、经济要素的趋势,并对国家和市场的角色进行了重新评估。③ 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指出:“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④本文认为,俄罗斯能源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外交政策,并深受俄罗斯国际地位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安大线”的夭折和2014年亚信会议上4000亿天然气大单的签订都深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但是,国际因素并不构成中俄能源合作时紧时慢的唯一解释,政府首脑尤其是普京总统的判断和决策,以及俄中央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俄能源管理制度都对中俄能源合作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本文试图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中俄能源合作问题。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与中俄能源合作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国家对外战略与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体系因素与特定的外交决策之间加入了国内变量。与沃尔兹(Kenni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视为独立变量,认同“一个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当首先问询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有概括力的特征就是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⑤但是,体系因素并不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还需要引进“国内对体系的认知”和“政府动员国内资源的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即外交政策不仅仅是由权力和体系压力塑造的,也受到认知、价值和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它们构成了“次要但直接的原因”。⑥该理论将权力理解为“国家彼此影响的能力和资源”,⑦将外交政策利益视作驱动国家对外行为的目标。唐世平将战略行为分为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强调外交决策人的重要性,后两个阶段强调了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⑧ 首先,由于具体的外交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不仅受到国家相对实力的影响,也受到领导人对这种实力的认知的影响。“即使承认结构存在并非常重要,也仍然存在着领导人如何看待它的问题。”⑨也就是说,国家的外交政策在短期和中期内未必会随着相对力量的变化而变化,重要的是领导人的看法和相应的反应,“行为的快速变化与对权力分配认知的变化有关”。⑩新现实主义擅长解释国际政治的长期结果,但难以解释中短期的政策变化,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其次,即使国家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本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权力的相对变化,但未必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其能够提取和调动足够的资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有必要将政府力量和国内资源动员能力视为中介变量。国际体系地位类似但国内结构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外交政策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其政府决定的,政府的权力更重要,这种权力表现为政府为实现其目标而提取资源,以保证实现其核心领导者意图的能力。”(11)也就是说,即使国际地位类似、领导人认识类似,但政府能力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反应。沃尔夫斯(William C.Wohlforth)在针对俄罗斯扩张倾向的研究中指出,不是均势中的客观地位,而是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和国家所能提供的资源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俄罗斯扩张的倾向。(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最终是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其物质力量决定的,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则是间接而复杂的,因为体系压力必须通过单元层面的中介变量才得以转化”。(13)正是单元层面的干预性变量(即国内进程)决定了面对体系压力所应采取的外交政策。 本文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非常适合分析中俄能源合作问题。1992年以来,尽管中俄两国关系日趋紧密,双方领导人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为何合作之路却一波三折?多年来国内外学界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探讨。(14)一般认为,有利于中俄油气合作的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俄罗斯生产而中国需求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2)双方都有战略多元化的需求,即俄罗斯希望出口多元化而中国希望进口多元化;(3)地理上的临近性,即不需要第三国作为过境国,尤其是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希望得到不经第三国过境的陆路进口途径。妨碍中俄油气合作的因素主要包括:(1)缺乏重要的基础设施。在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ESPO)开通前主要由铁路运输,而油价的波动往往改变双方的利益;(2)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变动、俄罗斯企业的内斗延缓了合作的进展;(3)俄罗斯能源部门投资不足难以提高产量,能源贸易产品单一且过于集中在石油方面;(4)缺乏互信和理解,对承诺有一定的恐惧心理。俄罗斯认为,中国利用其地位对俄提出的价格优惠是不合理的,因而尽可能多方寻求客户,并担心因此成为纯粹的原料供应商。中国则不满莫斯科挑动中日间竞争、限制中国公司收购俄罗斯上游部门股份,并且由于俄罗斯能源外交政策波动较大,也影响了中国对俄方的信任等。(15) 新古典现实主义所提供的分析路径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们并不否认、回避或希望取代这些实际存在的主客观因素,而是对其进行控制与干预,目的是将影响中俄油气合作的上述因素放在一个便于理解的框架内,明确各类因素在油气合作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同其他理论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的影响上。 首先回顾一下中俄能源合作的历史。1991~1993年,中俄经济规模大致相仿,俄罗斯自视为世界强国,政府能力充沛,对华能源合作不积极;1994~1998年,俄罗斯认识到自身国际地位的大幅下降,但政府动员能力受到限制,对华能源合作意愿虽然有所增强但进展依然缓慢;1999~2008年,俄罗斯国际地位上升,政府能力趋强,对华能源合作再度迟疑;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经济备受打击,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俄罗斯3.5倍。(16)俄罗斯深感国际地位下降,普京政府加大力度强化政府能力,对华能源合作步伐大大加快。综上可见,当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感到满意时,政府权力的充沛或不足都不会加强对华能源合作的意愿;而当其对国际地位不满时,如果政府权力不足,则对华能源合作意愿就不强,而如果政府权力充沛则对华合作意愿强烈。以下将首先概述从苏联解体到2000年的中俄能源合作,然后重点讨论普京担任总统以后俄罗斯的体系认知,尤其是其政府权力和能源管理制度改革对中俄油气合作的影响。 二、从苏联解体到普京上任前的中俄油气合作 (一)体系认知与政府力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决策者对其国际地位的认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91~1993年,俄罗斯认为苏联的瓦解并未对其军事实力造成巨大影响,俄罗斯与美国的国际地位仍不相上下。俄罗斯领导人,尤其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奉行亲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与美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但这种思路未能成为现实。面对北约的东扩,俄罗斯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其国际地位的下降,于是从1993年起逐渐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1996年普利马科夫的上台标志着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的认识有了重大的改变,他们更加强调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反对美国指使下的单极世界,并大力推进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希望构建多极世界抗衡美国的单极霸权。 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力量也经历了一个由强变弱又变强的发展轨迹。苏联瓦解之初,政府对大多数国民经济部门的控制依然很强,从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可以看出政府的权力。例如,1991年,俄税收占 GDP的20%以上,此后一直呈下降态势,直到2004年才重新达到这一水平。其中,1993~1996年,税收降至GDP的14.5%左右,1997年为10.8%,1998年更是降到9.2%,标志着政府力量迅速下降,直到1999年才回升至12.8%。(17) 俄罗斯能源部门自苏联解体之初就实行了市场化改革。虽然起初天然气行业依然保持了苏联时代受政府管辖的传统,天然气工业公司直接继承了原主管机关苏联天然气工业部的职能,但后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实行了部分私有化,于1993年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公有制份额下降到38%。由于俄罗斯政府对石油业解除了价格管制,引入了自由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大量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取代了前苏联的石油工业部,经过一系列的收购,到90年代中期仅剩下14家大型公司,到2003年则仅有10家。到21世纪初,俄罗斯国有企业的产油量不到总产油量的20%。(18) (二)中俄油气合作 俄罗斯领导人对体系地位的认知及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影响了中俄油气合作。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上向西方“一边倒”,与中国关系趋冷,直到1994年才开始主动和中国商谈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问题。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开始寻求海外能源。这一阶段叶利钦政府与中国石油合作的愿望迫切但成果并不显著,双方石油部门刚刚开始接触,俄政府对私有化后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缺少控制能力。 面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下降,1996年叶利钦总统加快了与中国开展油气合作的力度,两国达成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并签订了天然气协议。俄罗斯还推行了“新东方政策”,积极开展同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合作协定,如《1996~2005年远东与外贝加尔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和《1996~2005年西伯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相继出台。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成为俄罗斯“新东方政策”的重点对象。(19) 1998年,两国就铺设“安大线”问题正式磋商。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俄,中石油和尤科斯公司(YuKos)、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签署了《关于开展中俄原油管道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的协议》。由于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私有化运动中,俄政府不具有实际影响力,该阶段中石油的合作对象主要是以尤科斯公司为代表的私人油气公司。与俄罗斯私有油气公司的合作成为当时中俄石油合作的主导形式,双方合作的实际进展较为缓慢。 三、俄罗斯的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油气合作:2000~2008年 这段时期,俄罗斯的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大幅上升,政府权力不断加强,但以2004年为界,中俄能源合作有所差异。2004年以前,由于俄罗斯加强政府权力,大打地缘政治牌,中俄油气合作受到一定影响;2004年以后,北约东扩带来的压力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一)体系认知 1999年国际原油价格开始上涨,俄罗斯联邦延续多年的预算赤字变成了连续8年的盈余。石油产量的增长超过了50%,从叶利钦时代的每天平均600万桶达到普京时代的每天950万桶,(20)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石油美元的流入。1999~2008年,俄罗斯经常项目余额达到5874亿美元,央行持有的国际储备也在2008年8月达到了5966亿美元的最高峰。(21) 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也有所变化。2000年普京上任伊始就对当时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为不满,其第一任期的主要外交目标是利用实力的上升实质性地加强国际影响力,甚至不惜为捍卫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做出暂时的妥协,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应当成为伙伴而不是敌人。2002年7月,普京总统宣称“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内经济利益”,经济联系尤其是与欧盟的能源联系:是重中之重。他还要求俄罗斯外交官帮助商人开拓海外市场。外交部长普利马科夫坦言,能源外交正在成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的新方向。(22)普京也将俄罗斯国有天然气股份公司(Gazprom)(以下简称“俄气”)视为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工具。 自2004年起,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继续增长,但国际安全环境却日益恶化。赵华胜指出,俄罗斯的体系认知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俄罗斯开始宣称支持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二是2005年普京政府借油气价格上涨、俄经济增长的强劲之势高调反对西方入侵伊拉克。(23)2004年,一些前苏联国家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欧盟和北约,欧盟内部反俄情绪加强,影响了俄欧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橙色革命”使俄乌疏远,直接造成俄乌关系恶化,并在能源运输问题上引发了2006年俄乌天然气之争,严重削弱了欧洲对俄罗斯的信赖。此外,美国也酝酿着在波兰和捷克境内部署反导基地。俄罗斯对当时的均势格局再度表现出不满。普京表示,俄罗斯将致力于建立平衡的多极化世界,自主决定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24)俄罗斯领导人意识到,追随西方并未给俄带来实质性的利好,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俄需要并开始着手加强中俄纽带。 (二)政府权力 2000年普京上任后,通过国有化运动加强了政府对油气产业的直接控制。俄气重新控制了天然气工业,国有成分达到公司股份的50.002%。(25)税收、出口体制、石油管线以及油气田拍卖与招标等,都成为中小型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进入壁垒,国有企业因而获得了资源的优先开发权。 首先,许可证制度(26)明显偏向国有企业,禁止国内中小企业和外国公司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资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对非本地油气产业投资者的态度几经变化,既有欢迎外资参与的生产分成计划,又有禁止外国投资的政策。在天然气行业,俄气控制了管道运输系统,享有唯一的出口权,有权勘探新的大型油气田并得到“战略性油气田”条款的保证。此后,私有公司逐渐丧失了投资新油气田的机会。在石油业,虽然国有企业产量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许可证制度阻止了中小型企业对具有战略价值的未开发地区进行投资,从而确保了国有企业的地位。 其次,外资企业受到排挤,不得不在条件苛刻的情况下寻求与国有企业的合作。投资“萨哈林—2”油气项目的外国公司把控制权过渡给俄气;英国石油公司(BP)也被迫把科维克金气田(Kovytka)的控制权出售给了俄气。上述做法限制了油气行业对外国企业和国内中小型企业的开放,使后者无法自由地投资地质勘探和技术现代化,成为长期困扰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难题。 最后,普京任命了总统地区代表以辖制州长的权力,并打击寡头势力。2003年,各自由派政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失利,寡头势力被排挤出国家杜马,并解散了尤科斯公司。这一切都表明,俄政府支持忠于政府的企业,同时惩罚那些反对政府干预的企业。 2004~2008年,俄政府权力继续加强。2005~2006年国家税收达到GDP的24%,出口收入使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增加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政府拥有大量预算盈余,卢布稳定并对美元稳步升值。(27) (三)中俄油气合作 普京在第一任期内基本延续了叶利钦时期的对华石油合作政策,并没有拿出实质性的项目给中国,《俄罗斯2020年前油气战略》和《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油气综合体发展的基本方针》也只是一种战略筹划。普京上任后,中俄油气合作问题不少、摩擦不断、进展缓慢。发生在这段时期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即中石油竞购斯拉夫石油公司(Slavneft)的失败和“安大线”计划的搁浅,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前者与俄罗斯政府的权力重组有关,后者则受其体系认知的影响。 2002年12月,俄罗斯第九大石油公司斯拉夫石油公司举行私有化拍卖,中石油作为唯一的外国公司向其递交了竞标申请。中石油的竞标在俄罗斯引起了不小的震荡。俄罗斯政要对竞标背后的政治目的也表示了担忧。12月16日,俄罗斯杜马通过一项决议案,反对俄罗斯将实行私有化的国有公司股出售给外国公司。此举意味着俄罗斯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控股的实体参与竞拍斯拉夫石油公司的股权。中石油当晚即决定退出竞拍。 在“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建设方面,中俄双方于2001年同意建造一条到2005年运输能力达到2000万吨/年,到2010年达到3000万吨/年的石油管道。2002年12月初,中俄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中俄石油管道项目将按期实施。2003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飞抵莫斯科提交了修建“安纳线”的建议,同年3月,俄提出折中方案,分别建设通往中日的两条支线,但“安大线”将优先建设。然而日本却提出,如果俄同意优先修建“安纳线”,日将提供75亿美元的资金以协助俄开发东西伯利亚新油田。由于日本的条件优厚,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宣布否决“安大线”。同年10月,“安大线”的支持者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k Hodorkovsky)因偷逃巨额税款被捕,“安大线”计划彻底搁浅。“安大线”一案虽然表面看是由于日本的介入,但本质上还是源于俄罗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俄罗斯不会轻易让中国成为唯一垄断俄罗斯油气出口的国家,俄必须在能源输出问题上占据主控权,并以远东输油管道项目来带动整个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上述事件与普京实施的“能源超级大国”战略有关。这一时期,普京握有战略主动权,中国更需要俄罗斯。普京的能源战略是不想让中国垄断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开发,希望能在中、日、韩三国间寻求平衡。如果说“安大线”的最终夭折明确反映了这种战略考虑的话,那么打击石油寡头尤科斯和中石油竞购斯拉夫石油公司的失败这两起案例的背后则是普京政府重建“政府权力”的主要举措,这些举措严重影响了中俄油气的合作。虽然中方领导人对此非常不满,认为俄罗斯不可信赖,但中俄双方的制度建设却取得了更快的进展。(28)关于该时期的中俄油气合作,俄罗斯最重要的中国研究智库远东研究所(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主任米哈伊尔·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认为,两国间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超过20年的疏离和敌意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29)积累了几十年的不满、偏见和不信任还在不知不觉中妨碍着两国关系。俄罗斯担心成为中国的“能源附庸”,普京敦促中国进口更多的机械和技术,但中国对此并不感兴趣,而是希望俄罗斯成为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由于双方目标不一,两国能源合作要比预期的更慢。(30) 自普京的第二任期(2006年)开始,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和政府能力的增强,中俄能源合作较前期加快了步伐。北约东扩迫使普京强化“新东方政策”,计划10年后对亚太国家的石油出口从3%上升到30%以上。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以下简称“俄油”)计划在2020年前对亚洲的石油出口量从6%增加到20%。(31)中国的巨额贷款使俄罗斯看到了中国强大的资本实力,中石油、中石化与Rosneft和Gazprom建立了战略联盟,副总理级别谈判机制也得以建立。2006年,中俄石油合作取得全面突破,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原油1597万吨,比2005年增长约25%,占原油进口总量的11%左右。重大油气开发项目和运输项目得到切实推进,政府间能源合作机制常态化,公司层面上形成了战略联盟,远东石油管道“泰纳线”一期工程和中国支线破土动工,中石化收购乌德穆尔特(Udmurtneft)石油公司和中石油购买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股份,中石化和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企业在两国成立合资公司等。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俄罗斯的能源政策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即俄政府把攫取外部油气市场带来的租金机会视为重点,普京第二任期的能源政策是短期的被动反应式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恰恰表明,中俄能源关系此时已进入了“正常化”阶段,体现出平等、去意识形态化和以利益为驱动的实用主义。(32) 四、2008年金融危机与俄罗斯能源管理体制的调整 (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体系认知 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经济。随着油价大幅下挫,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和出口量急剧下降,导致俄罗斯税收减少、赤字高企和资本外流。2009年,俄GDP萎缩了7.8%,工业生产下降了9.3%,出口减少了35.8%,进口减少了34.4%,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50.1%。(33) 为了给能源行业寻求出路,俄政府为国有企业聚集了大量资金,帮助其清理与外国银行的短期债务,还适度调整税收和关税政策以刺激投资(包括外国投资),并支持长期大型的、具有风险的陆上和离岸未开发区域的油气项目。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20年俄联邦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中指出,要确定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34)2009年6月俄总统明确表示,要在五大核心领域加速科技突破,这些领域包括能源效率、节能(包括新能源开发)和核科技发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迫使俄政府修改了2009年11月13日通过的《2030年能源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并在其中设定了四个主要目标:实现能源安全、提高国内经济的能效、提高燃料和能源综合体(FEC)的经济运行效率和保障生态安全。对于能源发展和出口的多样性,《战略》强调对东西伯利亚、远东、亚马尔半岛(西西伯利亚)和北极大陆架等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据此,油气资源出口将更多地转向东方。Gazprom进一步细化了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天然气生产目标,并以亚洲导向的项目为主,如建设连接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海参崴液化天然气厂等。2011年,Gazprom也对《2030年俄罗斯联邦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进行了修订,库页岛、堪察加半岛和马加丹州的离岸油气田成为计划开发的主要新油气田。 普京总统第三任期高度重视亚太。在2012年12月12日对联邦议会的报告中,普京强调“21世纪俄罗斯的发展是向东发展”,希望“在亚太这一全球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占有一席之地”。(35)2013年2月发布的《外交政策构想》再次确认了俄罗斯加强与亚洲合作的意图。2013年3月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参与金砖五国事务的构想》进一步强调了与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是重中之重。普京认为,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不仅具有双边意义,也具有全球意义。(36)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民间的亲华情绪也在不断增长。虽然俄民众十分重视主权,但他们同时认为,与中国而不是与西方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纽带将更好地捍卫俄罗斯主权。俄国防部、外交部和军工复合体的领导人希望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相抗衡,因而热衷加快推动中俄合作。(37) (二)俄罗斯能源管理体制的调整 2008年以后,经过多年的努力,俄中央政府对油气行业的控制已经基本完成。政府权力的加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有权结构调整 在勘探、开发、加工、运输分配以及经销等所有部门中,国有企业都上升到突出的地位。天然气领域的政策明显有利于国有公司,但私营公司如诺瓦特克天然气公司(Novatek)、石油生产商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Surgutneftegaz)和卢克公司(Lukoil)等也取得了重大进步,2012年产量达到石油提炼总量的27%。过去几年,诺瓦特克天然气公司为争取天然气出口权积极游说。在2013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总统宣布会逐渐削弱俄气的出口垄断,允许Novatek下属的亚马尔(Yamal)液化天然气公司和俄气—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萨哈林1号项目组建自己的液化天然气工厂并用于出口。然而,Gazprom仍然继续垄断管道出口。 20世纪90年代初,Rosneft只占俄石油总产量的4%,而在2005年通过购买尤科斯公司的资产后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2013年又以540亿美元购得秋明石油公司(Turmin Oil),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与天然气工业中的Gazprom地位相当。 在油气运输部门中,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是一家国有垄断公司,2010年以前是对华出口石油的主力。管道运输则分别由Gazprom和俄罗斯石油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垄断。私营输油管道数量极少,只有卢克公司、萨哈林能源投资公司和秋明石油公司拥有,但后两者现已被Gazprom控制。 2.决策机制 俄政府在大油气公司的董事会中安插了官方代表,使国家能够直接参与能源企业的决策。2012年普京继任总统以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决策实体——“燃料、能源部门及环境安全战略发展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普京本人任主席,Rosneft首席执行官谢钦任副主席。该委员会拥有决策权威,实际上剥夺了现有的燃料及能源复合体政府委员会和许多其他相关部门的权力,目的是集中总统对于能源部门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尤其是Rosneft的权力。 3.税收制度 2008年石油部门生产不景气,政府略微减税,并放松了价格监管,将税收滞后从两个月调整到一个月。但国内石油工业仍然要求更大幅度的减税。 由于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减税并不容易。从2011年10月1日起,俄采用了新的出口税体系(所谓“60-66”体系),对原油征收的边际出口税从65%降低至60%、石油醚制品和重质石油产品一律按66%征税、汽油按原油税率的90%计税,目的是抑制粗加工产品出口,促使炼油厂升级换代。到2012年,俄成功地改善了税收行政管理质量,国际排名从第94位上升到64位。(38) 4.投资政策 能源投资对摆脱经济危机至关重要。2008年俄能源部预计,到2020年,俄罗斯的投资需求将达到24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30年俄罗斯需要4000亿美元。(39)2008年7月,一系列关于大陆架、天然气供应和底层土资源的联邦法律修正案使Gazprom和Rosneft在油气领域充当起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也使外国商人发现受到严格管制,除了接受国有企业的条件并与之合作之外别无选择。而且2008年批准的《战略部门法》列出了41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物资清单,投资这些领域的外国公司要么必须完全受到限制,要么必须按照个案进行审批。该法设计了一个被称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底层土资源”的门类,构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许可证程序,涉及大量机构,包括联邦安全部、国防部、经济发展部和能源部。 5.关税制度 政府通过国有公司控制着运输服务价格和关税,以及分配油气管道系统(包括出口设施)的使用权。俄罗斯联邦关税系统(FTS)是唯一决定对天然气、原油和石油制品征收关税的行政机构,但是政治动机也往往造成负面影响。例如,为了重启亚洲能源战略,俄政府决定建设ESPO。由于地质和气候条件恶劣,不具备任何前期的基础设施,该项目的建设成本极大。俄石油运输公司估计该管线的实际运输成本大约在130美元/吨,对石油生产者来说过高。但是最终关税还是被定为50美元/吨,留下了较大的价格缺口。(40) 总之,俄气和俄油的特权地位无法帮助俄罗斯顺利实现现代化和变革的目标,技术变革也缺乏竞争环境。俄罗斯的勘探和开发活动即使能吸引到大量外资,但要想取得成功也需要商业环境的重大改革。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了俄罗斯油气部门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致使俄罗斯政府大幅加强对油气资源的控制和战略干预,因而在中俄油气合作中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 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中俄油气合作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俄罗斯在油价高企时代对华管线项目合作中的拖沓做法,成为中俄油气合作的“转折点”。(41) 2009年斯科沃罗季诺—漠河段顺利动工,Rosneft和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分别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5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的贷款,每年向中国供应9000万吨和6000万吨的石油,为期20年。但此时双方在价格,尤其是运输关税上发生了分歧。中方认为,俄方对ESPO的运输成本每吨高估了将近30美元,而俄方则认为,石油的运费应该根据ESPO全程管道来计算,中方的价格只包括了斯科沃罗季诺段的运输成本。最后,凭借着俄政府强大的管控协调能力,2012年4月28日俄方同意将每桶石油的运费降低1.5美元。(42) 2009年底东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完工之后,2012年12月,从斯科沃罗季诺到科济米诺的东西伯利亚石油管道二期也投入运营。到2015年,东西伯利亚石油管道的运输能力预计将增长到100万桶/天,其中30万桶/天供给大庆,60万桶/天供给亚太其他地区。ESPO对东北亚出口量急剧增长。根据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的统计,2012年东西伯利亚石油出口总量中,日本占31%,中国占24%,韩国占5%。(43)ESPO二期的完成显著提高了俄罗斯对东北亚的石油出口量。 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支持俄罗斯向东北亚国家出口天然气,2006年3月,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从2011年开始俄罗斯每年向中方出口8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由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东段和西段两条管线输送。但由于中国对天然气价格持有异议,在随后的几年里该计划没有进展。2009年10月,Gazprom和中石油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规定从2014年到2015年间每年向中国供应680亿立方米天然气,并再次提到了两条管线的问题。西西伯利亚每年通过西段线供应300亿立方米,东西伯利亚通过东段管线提供约380亿立方米,并连接了科维克塔(Kovykta)气田和在萨哈—雅库特(Sakha-Yakutia)地区的恰扬达气田(Chayanda)以及萨哈林近海的气田。(44) 2009年12月,俄气旗下的天然气出口公司和中石油旗下的中石油国际签署了一项关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主要条款和条件的协议,并于2010年9月签订了延伸条款和条件的协议,对通过西段管线向中国交付天然气设置了关键的商业限定,即供应量和出口的时间框架、照付不议的标准、供应期以及担保支付的标准。然而直到2013年习近平访俄之前,两条管线的选择仍不明朗。俄气支持西线,原因是西线开发早、基础设施配套完备且成本较低,同时,西线气田也可以供应欧洲,而东线只能供应亚洲市场。而中国更青睐东线,因为东北地区比西部内陆地区更急需。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能源合作领域发布了许多官方正式公告,并与俄罗斯签署了大量商业合同。2013年6月,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一次发言中,普京总统建议逐步减少液化天然气(LNG)出口的限制,并批准埃克森美孚国家公司—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项目和诺瓦泰克—道达尔—中石油亚马尔项目。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与中石油公司签订了新的供应协议,邀请中国公司合作开发和勘探Rosneft在巴伦支海(the Barents)和伯朝拉海(Pechora)的位于北极勘探区的3块海上油田。Rosneft将在未来25年内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20亿美元的贷款,该公司计划将这笔资金用于东西伯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的天然气开采计划。(45) 2013年6月,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Rosneft与中石油签署了一项新协议,在未来25年内每年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总金额达2700亿美元,并得到中国700亿美元的预付款。(46)这样,Rosneft每天将向中国供应30万桶(约363吨)的石油,是过去十年供应中国石油量的2倍以上。预付款将帮助Rosneft解决因用550亿美元收购秋明英国石油公司(TNKBP)而急速增长的债务问题,俄罗斯依靠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来解决其国有公司债务的倾向明显加强。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的合并以及随后的西方联合制裁大大恶化了俄罗斯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速了中俄能源合作的进程。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亚信峰会上,Gazprom与中石油最终签署了为期30年、总额约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成为截至目前中俄两国签署金额最大的天然气供气合约。(47) 俄罗斯之所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除了西方的制裁之外,还有其他体系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市场上,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北美及东非等潜在供应商都存在竞争关系。新建的中亚—中国管道价格相对低廉,最终将达到每年1000亿立方米的供应量。缅甸的天然气也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运作,每年可以提供120亿立方米。此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预计到2020年,中国国内产量将达到每年约400亿立方米。(48)北美页岩气开发也使美国从液化天然气进口大国转变成出口国。这使得俄罗斯在世界油气体系中的地位面临威胁。为了锁定中国这一巨大的需求市场,俄罗斯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天然气出口价格,而俄罗斯强大的政府权力也使普京表示为供应中国的气田免除一项矿物开采税,中国也停止了对俄天然气征收进口关税以示让步。 六、结论 综上所述,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对中俄能源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历史上看,凡是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满意且政府权力充沛时,对中俄能源合作的意愿就会下降,行动就会迟缓,如1991~1993年、2000~2008年。而当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不满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政府权力不足时,对华能源合作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乏意愿但缺少行动,如1994~1999年;二是对体系地位不满但政府权力充沛时,对华能源合作便会热情迫切且行动迅速,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4年西方对俄经济制裁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也有助于我们得出上述结论。 就中俄能源合作而言,2003年俄杜马通过的《2020年能源战略前景》中首次将亚洲作为政策分析和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仍将是俄能源外交的主导因素,亚洲只起到辅助作用,主要目标之一是振兴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加强俄罗斯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地位。2009年发表的《2030能源战略前景》标志着俄罗斯开始建立以亚洲为主要目标的能源出口政策,并以远东开发为名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工作。尤其是目前俄罗斯在欧洲市场上困难重重,加之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的合并以及西方的制裁,这些都加速了俄罗斯实现油气出口多元化的迫切性。 一方面,俄罗斯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欧洲天然气市场需求正在萎缩,同时西方会继续加剧对俄制裁,俄罗斯不能保证可以继续维持现有的能源出口量。这些因素都成为其转向东方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也加入了西方对俄制裁,因而中国市场对俄意义重大。当然,也不排除一旦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得到改善,其领导人的体系认知发生变化,可能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俄油气合作。但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应该充分抓住机遇获取主动,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强化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Carlos Pascual and Jonathan Elkind,Energy Security:Economic,Politics,Strategies,and Implication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0,p.28. ②Elena Shadrina,“Russia's Foreign Energy Policy:Paradigm Shifts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Europe,Central Eurasia and Northeast Asia”,IFS Insights Oslo: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November 2010,http://brage.bibsys.no/xmlui/bitstream/handle/11250/99341/1/Shadrina_nov_2010.pdf. ③Sadek Boussena and Catherine Locatelli,“Energy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al Changes in EU and Russia:Revisiting Gas Relations”,Energy Policy,Vol.55,No.1,2013,pp.180-189. ④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版,第1页。 ⑤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1992,p.197. ⑥Jennifer Sterling-Folker,“Realist Environment,Liberal Process,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1,1997,p.22. ⑦William C.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Com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4. ⑧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78~202页。 ⑨Aaron L.Friedberg,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1895-190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8. ⑩William C.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p.294. (11)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9. (12)William C.Wohlforth,“The Russian-Soviet Empire:A Test of Neorealis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2001,pp.213-216. (13)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160. (14)中俄能源合作涉及众多层次和内容。世界经济结构,金融期货市场的变动,大国力量的兴衰,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的关系,大国或集团的外交和战略博弈,以及反映各类力量对比变化的国际能源治理体制、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相关利益集团博弈、各类油气公司间、政商间的关系、互信、商业利益的追求、乃至各国内部的法律条例和地理、地缘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5)Erica S.Downs,“Sino-Russian Energy Relations:An Uncertain Courtship”,in James Bellacqua,ed.,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2010,pp.146-175; Mikkal Herberg,“Fuelling the Dragon:China's Energy Prospects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in Andreas Wenger,ed.,Ener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 a New Producer-Consumer Framew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69-297; Bobo Lo,Axis of Convenience:Moscow,Beijing,and the New Geopolitics,London:Chatham House,2008; Nina Poussenkova,“Russia's Future Customers:Asia and Beyond”,in Jeronim Perovic,ed.,Russian Energy Power and Foreign Relations: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p.132-154. (16)Thomas Graham,“The Sources of Russia's Insecurity”,Survival,Vol.52,No,1,2010,pp.55-74. (17)转引自Anita Orban,Power,Energy and the New Russian Imperialism,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 Security Press,2008,p.27,http://www.quandl.com/WORLDBANK/RUS_GC_TAX_TOTL_GD_ZS-Russian-Federation-Tax-revenue-of-GDP。 (18)Elena Shadrinaa and Michael Bradshaw,“Russia's Energy Governance Transi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Japan,and South Korea”,Post-Soviet Affairs,Vol.29,No.6,2013,p.465. (19)周京奎:《中俄石油产业合作的基础、契机及模式》,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第85页。 (20)Clifford G.Gaddy and Barry W.Ickes,“Russia's Declining Oil Production:Managing Price Risk and Rent Addiction”,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0,No.1,2009,pp.2-3. (21)参见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credit_statistics/。 (22)Mark A.Smith,Russi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Shrivenham,Oxfordshire,UK: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er,2003,p.2. (23)赵华胜:《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16-22页。 (24)《俄罗斯主张建立平衡的多极化世界》,新华网,2007年1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24/content_5644401.htm。 (25)Jonathan Stern,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Oxford:O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8. (26)许可证制度的目的是:(1)调节代理人数量并控制其质量状况;(2)开发新油气田以维持/扩大生产;(3)平衡资源发展和生产的地区结构;(4)通过出售许可证获得收入。 (27)Clifford G.Gaddy and Barry W.Ickes,“Rus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1,No.3,2010,pp.281-311. (28)Vitaly Kozyrev,“China's Continental Energy Strategy:Russia and Central Asia”,in Gabrielle B.Collins,ed.,China's Energy Strategy: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8,pp.210-211,212-213. (29)Mikhail Titarenko,“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Far Eastern Affairs,Vol.38,No.1,2010,p.5. (30)Erica Downs,“Sino-Russian Energy Relations:An Uncertain Courtship”,in J.Bellacqua,ed.,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0,p.164. (31)Rosneft总裁谢尔盖·博格丹奇科夫在罗马世界能源大会上的表态。参见《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向亚洲大幅增加石油供应》,人民网,2007年11月1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59942/59955/6524065.html。 (32)Yu Bin,“In Search for a Normal Relationship:China and Russia Into the 21st Century”,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5,No.4,2007,pp.79-80. (33)Shadrina Elena and Lu'cio Vinhas de Souza,“Russia and the ‘Great Recession’”,International Affairs,No.2,2010,pp.112-127. (34)Dmitry Medvedev,“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November 12,2009,http://eng.kremlin.ru/speeches/2009/11/12/1321_type70029type82912_222702.shtml. (35)普京:《普京文选》,贝文力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36)普京:《普京文选》,第296页。 (37)Andrei Tsygankov,“Russia's Tilt Toward China”,The Moscow Times,2009,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russias-tilt-toward-china/387633.html. (38)普京:《普京文选》,第332页。 (39)《戈尔德托认为能源并未成为莫斯科手中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中国工程技术信息网,2008年3月,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344374。 (40)Yury Shcherbanin,“Russia's Crude Oil Pipelines and Their Tariff System”,Northeast Asia Energy Focus,Winter 2009,pp.48-53. (41)杨雷:《中亚局势的现状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第32~37页。 (42)《俄罗斯石油公司同意对华出口石油每桶优惠1.5美元》,新华网,2012年4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16/c_111788099.htm。 (43)Tabata Shinichiro and Xiang Liu,“Russia's Energy Policy in the Far East and East Siberia”,in Pami Aalta,ed.,Russia's Energy Policy:National,Interregional,and Global Dimensions,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2,pp.161-163. (44)《俄罗斯Gazprom与中石油签署天然气协议》,新浪财经网,2014年5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ronews/20140521/191719182771.shtml。 (45)《俄油对两类合作伙伴各有所求》,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3年6月19日,http://news.cnpc.com.cn/epaper/sysb/20130619/0084464004.htm。 (46)普京:《普京文选》,第329页。 (47)魏峰:《中俄天然气十年谈判 双方在最后角力上实际旗鼓相当》,和讯网,2014年5月26日,http://opinion.hexun.com/2014-05-26/165118346.html。 (48)《2012年非常规天然气现状分析探讨》,中国行业研究网,2012年11月9日,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21109/823436.html。标签:中俄论文; 能源论文; 俄罗斯石油公司论文; 中俄原油管道论文; 中石油重组论文; 中石油改革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西方石油公司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