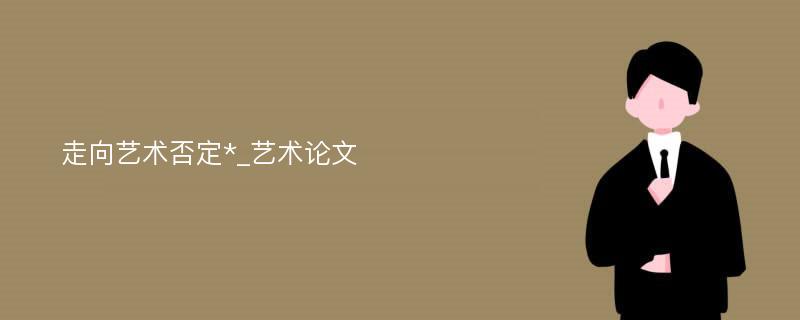
走向艺术否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论论文,走向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显在标志是:在文化救亡、启蒙和建设这一“现代性”主导需求的背景下,从王国维之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鲁迅之于国民性批判,毛泽东之于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新时期对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本思潮的推波助澜,文学承担的是由各种观念形态制约着的“载道”和“言志”的重任。作为传统文学生存形态的一种趋于衰落性的延续,也作为转型时期的文化对于文学的直接性需求,这种从属性的文学既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应,也制造出大量注定会过时的作品——囿于这种社会效应,人们容易将从属性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去理解,从而舍去了褒贬之意,但由于效应的背后总是带有各种急功尽利性和非文学性内容的侵染,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进入更为深邃、纯粹的艺术世界,这种“特质”也无疑到了需要改变的时期。正是在此意义上,1985年兴起的新潮文学运动以及她所倡导的“形式本体论”观念,可以视为对这种从属性文学的改变性努力。只是,当新潮文学家宣称文学形式自身即是目的的时候,由于文学否定现实能力的匮乏,他们只能将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和现代派作品的形式作为新的现实、新的上帝去从属,产生摹仿大于创造的问题,这就重新蹈入文学的“载道”性窠臼,只不过大写的乐观之“人”换成了小写的悲观之人,容易雷同的故事转化为容易重复的形式,致使其努力结果和努力初衷相违背。新潮文学和前期从属性文学的共同症结在于:由于文学创作必须通过充分个人化的状态去实现,所以共同的、群体认同的观念(无论这观念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这类文学难以消除的顽症,又由于文学创作的形态必须通过充分个人化的“表现”去实现,所以观念性内容的直接流露造成作品内含过于明显、浅显,是导致这类作品难以成为一个丰富的体验世界的缘由。文学作品当然可以而且需要展现当下的现实社会内容,但文学如果只把这种展现作为目的,而不能超越这些内容,一旦这些现实社会内容过去,文学自然也就有过时乏味之感。这就是《小二黑结婚》、《青春之歌》、《伤痕》太为“从属”现实及其观念性内容之所在,也是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狂人日记》)因过于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使其艺术性逊于《野草》等散文的缘由所在。
这就容易使得当下学者更感兴趣于百年文学史的另一条线索:由传统的“缘情说”、“性灵说”而延续下来的为艺术而艺术,产生了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个人色彩较为明显的承接性创作风格。表面上看来,这类作家均站在文化启蒙和批判的边缘,对“现代化”“革命”等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或回避或超越的姿态,通过显山露水和春风沉醉般的抒情描绘,或构筑出一个个没有硝烟风雨的世外桃源,或传达出一种小桥流水的闲情逸致。这些曾被为人生派作家指责为脱离社会现实的作品,由于处在当下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文化背景之下,反而获得了一种坚持个人化写作,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审慎的间距的肯定性评价。从中西方成功的艺术创作实践来看,曹雪芹、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作家,均可以视为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文学思潮之外,其作品才有效地保持一种独立的品性的,这样,在所谓的重写文学史中,一些学者将赞成票投给过去遭贬低的一方,才显得情有可原。只不过,在这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重写”之中,我们可能会忽略文化从来是整体性的——在一种类型文学身上暴露的问题,会不会通过表面上的冲突,传染给另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从而消弥了两类文学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对立?比如,在“为人生”派那里的观念的群体化,是否必须会造成“为艺术”派作家风格上的雷同化或类型化?如果沈从文与汪曾祺在风格上的差异性弱于其共同性,那么风格——这个应最能显示作家创作个性的领域,其症结是否同样应该追溯到这类作家也不具备自己对世界的独到理解、体验?如果作家的个人性只是主要体现在他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逆反性地构筑或挖掘一个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民间天地,那么我想说,作为一个作家,这种个人性实现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更不用说《棋王》这部表面上极富个性的写作,在根柢上还是衔接上了古老的道家遗风,从而给作家这个“个体”,打上了一个不小的折扣。更为重要的是:真正个体化的写作,既不会用回避现实的方式丧失直面现实的能力与勇气,也不会在情感抒发中将闲情推向极致从而丧失激情——通过回避现实而流露出的闲情逸致,正好说明了这类作家将自己灵魂和思想放逐后,只剩下一个孱弱的自我在民间散步,从而失去了一个健全的、丰富的个体穿越现实的否定性精神张力。也正因为此,我们在首肯沈从文、林语堂这类心地宁静的作家个性相对突出时,总会觉得他们身上缺少一些重要的素质,当然是和西方精典性作家相比较。
也正因为此,在这两条文学发展线索间做或此或彼的取舍,进而在“表现性”和“写实性”文学观之间做价值褒贬,就已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还是在于建立一种新的思路,分析出上述两类文学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进而从中提炼出共同的艺术特质和品性,为转型期和跨世纪的中国文学开辟新的价值取向。其结果,是通过对中西方既定理论进行双重超越,来建立新的理论雏型。
这意味着,将文化使命直接作为文学的使命,无论这使命多么重大,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文学的文学本体性。但文学本体性在此不是指形象形式,也不是指情感表现和抒发性灵,而是指她在多大程度上能完成“对文化现实的否定”。这种“否定”首先是指:由于文化总是具有集群性(文化可以使个人思想变为群体思想,如马克思、尼采),对文化否定便体现为在对集群性的思想观念的否定中产生作家个体化的理解——完成这样的“否定”,便可在从属性文学中产生相对优秀的作品。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如胡适、茅盾、巴金、曹禺等,都属于为中国现代化推波助澜的作家。但鲁迅的高人一筹之处,不在于他早期追随进化论思潮,也不在于用西方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观念来反对封建束缚,而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的症结,通过《阿Q正传》等作品,做了独到的发现和揭示,使得鲁迅在现代思想史上,成为一个不用西方现成思想诉说的独立思考者。尽管独立思考本身不是文学的终极目的,但却是文学能“自成一个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等经典作家共同的思想特征。这样,说鲁迅为现代化唱赞歌,或鲁迅的思想成就大于文学成就,散文成就大于小说成就,就多少失之浮光掠影。由于任何艺术形式均派生于作家独到的对世界的理解(如卡夫卡的《城堡》),我们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一个作家能否有自己的对世界的理解(思想),是他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关键——独特的思想产生之际,就构成了对既定的文化性思想的否定;其次,由于文化现实总是以“观念”形态显现的,因此“否定”在此还应体现为对观念化的世界的否定,并通过这种否定,进入独到的形式和形象世界之中。不能完成这一层面上的“否定”,一个有独到思想的作家,也同样不能被保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至少,这会造成作家作品质量上的参差不齐。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鲁迅的《阿Q正传》在艺术质量上超过了他的《狂人日记》,而鲁迅的杂文有时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在于总体上鲁迅的思想阐述欲望大于其艺术表现欲望。《狂人日记》通过对传统文化“吃人”的呐喊,起到的是社会效应和文化批判效应,但《阿Q正传》通过对国民精神形态的淋满尽致的表现,起到的却是类似果戈理《死魂灵》的艺术效果,并由此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在此,生命意志说,苦闷象征说,摹仿与表现说,乃至社会意识形态说和文化批判说,作为理论形态,也许都可以切入鲁迅作品的某一方面内容,但却难以揭示出鲁迅的伟大,在于既能摆脱既定思想的束缚,又能在文学意义上摆脱个体化思想束缚的连续性否定过程。对于所有喜欢“听将令”的作家来说,鲁迅的成功在于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艺术否定,而鲁迅的局限又在于他没能彻底地、始终坚持这样的艺术否定。这种不彻底性甚至也体现在《阿Q正传》这样的力作中。一部好的作品,其“否定性”不仅应该体现为对政治现实的否定进入文化现实空间,而且也应能在对文化现实空间的否定中进入形而上的人类性空间,这会使作品意蕴空间更为深邃、丰富和言说不尽。比较起来,昆德拉通过政治批判走向人类批判,使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获得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而鲁迅的严峻由于缺乏走向形而上的张力,就使《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在获得文化批判的力度感时,也同时堵塞了作品意蕴的进一步的开掘。
反之,如果将艺术对文化现实的否定,仅仅理解为站在“现代化”思潮的边缘或之外,保持一个作家相对独立的视角,为艺术而艺术的“性灵派”作家在现象上,确实好象更接近我所说的艺术本体。但“否定”的更深刻的意义,不是指站在边缘回避对现代文化现实的直面,而是指站在边缘穿越现代文化现实,用自己的结构构筑一个独特的世界,这样,文化现实内容就成为材料和魂灵,形成这“世界”的有机组织。《西游记》和《边城》的产生都具有自娱性,但《西游记》是用一个虚幻的世界直面现实世界,虚幻世界中的故事就成为现实性文化内容的缩影和隐喻,而《边城》用一个偏僻的清纯世界来回避喧嚣污染的现实性文化世界,以体现作家的价值选择——在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世界这一点上,《边城》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个世界缺乏面对现代文化现实的勇气和能力,又在某种程度上衔接了道家“出”的生存意识上,我们又可以说作家没有真正完成对文化现实的否定——联系到当代知识分子丧失了把握现实的思想能力,只能以资料搜集和考证为自己的生存选择,其“自己的世界”的虚弱性,不正好说明这种个体贫困的传统,是一脉相传的吗?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个体,是否就是这样的?中国知识界的个体,是否只能这样?文化转型对个体的要求,又是什么?
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这种性灵派的创作者常常以面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写作为理由,来或对西方意义上的“生命”进行中国式曲解,或者就暴露出“文学生命说”本身在理论上的局限。这就是:生命本身就是本体,还是生命应该有一个本体支撑与限定?如果选择前者,那么性情、感受、闲情就都有在写生命的理由,如果选择后者,那么生命的所有生长、舒展和敞开形态中,就应该有一个核心形态发挥类似心脏的功能,而感受和闲情,就都只能成为生命的血肉。这个核心形态在作家这里,就表现为在“对现实的否定”中产生的对所描写对象的独到体验和理解,也表现为在对一切既定的体验和理解的怀疑对那个未诞生的“自己”的渴望。在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里,观赏的闲情之所以被一种惊人的朴素美产生的敬慕所笼罩,是因为作者对托尔斯泰的伟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验和理解;而林语堂的《余所欲者》尽管闲适飘逸,但由于对生活的愉悦渴望大于理解渴望,也就落入了人皆有之的情绪之中,不能内含启迪使作为生命的作品丰富而有质地。所以一个优秀的抒情派作家,不是听凭自我的生命状态写作而是依赖生命的本体——对现实的否定冲动,来带动生命的所有组织进入激发状态。当代人听凭生命的任意筹划产生无聊和空虚之感,摆脱时代使命后的个人化写作之所以在郁达夫时代和今天新生代作家这里常有欲望呈现后的琐屑之感,文学生命说在本世纪初和本世纪末之所以两次兴起而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在我看来,均在于对生命本身缺乏新的,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价值限定,而艺术否定论,强调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限定的可能。
艺术否定论是针对百年来我们只能在从属性文学和性灵性文学之间进行选择和徘徊这一状况提出的,因此它意图消弥两类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的分野,在两类艺术共同的好作品(尽管不多)中提炼出艺术共同的对现实的否定本性,作为对当代文学摆脱上述两种文学的阈限、将视线投注在艺术实现自身程度的一种理论设计——正如小说模式今天已走到尽头,作家只能通过对现实化的小说进行否定以完成新的整合一样,小说模式不再重要,而昆德拉所说的小说本性将更为关键一样,文学从此后的提问方式不再是“写什么”,也不再是“怎么写”,而是写得“怎么样”。其次,艺术否定论通过强调对共识性的观念的否定完成自己的观念的诞生,通过对自己的观念形态的否定完成自己形式的诞生,通过对表层的政治和文化内容的否定进入人类性层面,通过将现实内容材料重新整合完成自己对现实的直面和超越,进而对自己的生命状态提炼完成自己的丰富的艺术世界的诞生——每一次否定都可以视为对对象性质的改变,每一次否定也都是一个新的世界内含的拓展,从而既完成对传统哲学将“否定”与批判、破坏、解构、取消的区别,也有别于20世纪在中国文坛盛行过的任何西方文学理论。艺术否定论认为,文学是生命也好,文学是表现和摹仿也好,文学是工具抑或人学也好,文学是结构和解构也好,均是在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模式上对文学的规定,从而忽略了各种内容各种模式的文学区别于现实、也区别于文化所达到的程度。因此艺术否定论是一种艺术本体论和艺术存在论,以区别于以往的艺术本质论(即只问艺术是什么,而不问艺术敞开自己实现程度如何的理论)。关键是,艺术否定论的上述五点内含,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说,强调艺术充当新感性(马尔库塞)生长的工具、强调对由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的克服等各种现实性需要的文学理论有所区别。严格说来,艺术否定论不是某一文化某一阶段的理论,而是在各种文学史和文学史各阶段都可以找到说明的理论。因此可以说,是否只有通过艺术否定论,才能真正甄别文学作品的质量高低,也才能真正建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从而使文学理论的跨世纪建设真正有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 可参阅作者《否定本体论》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标签: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边城论文; 作家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