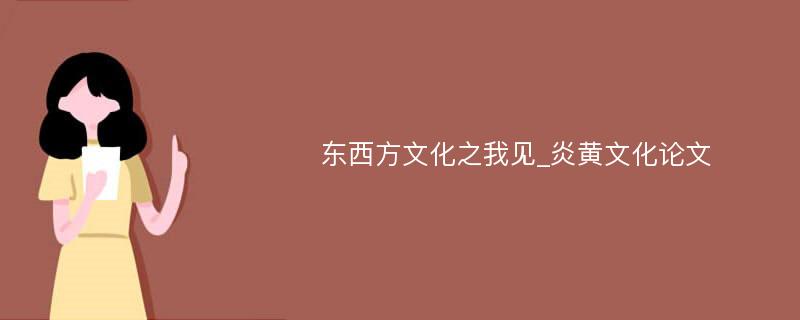
东西方文化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我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葛剑雄先生《我看东西方文化》一文中详细说明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对于澄清目前文化讨论中的概念极有贡献。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以为补充,并与葛先生商榷。
一、到底什么是西方,什么是东方?
我历来反对随意使用东方文化这个名词,西方文化因为有一个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还不妨囫囵谈论。东方文化则至少有东亚文化(姑且以中国的儒教文化为代表)、南亚文化(姑且以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为代表)、西亚—中亚—北非文化(姑且以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为代表)。三者大不相同,其差别实不亚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别。自古以来中国与三者的接触也远不如19世纪以来与西方的交流。在今天的中国,博通这三种文化的人,即使不能说没有,也是少之又少。因此我认为无法把三种文化捆在一起当作东方文化来谈。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以梵文专家的身份一再合三为一把东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而且以为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进而按照据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断定:既然最近几个世纪是西方文化主导世界,那么下个世纪必然是东方文化主导世界,而且即使东西方文化汇合为一种世界文化也一定是东方文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我对此论不敢苟同。三年前曾撰《辨同异,合东西》一文,就是为说明我的这个观点。虽然如此,东西文化之说仍然日见流行。
抛开文化不说,当代所应用的东西方概念事实上是冷战引起的。50年代初,著名的苏联作家爱伦堡就曾在《真理报》上尖锐地讽刺西方的政治家与政论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不顾地理常识而把苏联和中欧国家妄称为东方,又把日本妄称为西方。我还亲自听到过他到中国访问时发表过这番宏论。所以,葛先生对近50年来东西方概念的划分完全正确。当然,近年的形势大有变化。今年的新闻是俄罗斯已参加“西方”七国集团使之成为八国集团,捷、波、匈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东方与西方的概念看来又要变动了。
另外一种把世界笼统分为东西方的人应当说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们心目中,西方就是先进的文明国家的总称,东方就是落后的野蛮国家的总称。鼎鼎大名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就如此把世界两分而说过:“East is East/West is West/Nowhere the twain shall meet。”欧洲人把东方分为近东、中东、远东,我怀疑是以伦敦为中心命名的,很值得考一考。不过,以早于英国称霸世界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坐标,近东、中东、远东的概念还是一样,中国目前还颇有人牢守这样的东方观,同时又努力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未免有些顾此失彼了。
二、文化是可以变化与移动的
虽然比起意识形态来文化的稳定性要大得多,但是却同样不是不能变更的。南北美洲本来是印第安人的文化,即所谓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但是五百年前西方人入侵以后,其主体已成了基督教文化。今天的中亚(包括中国的新疆在内)本来是“西天佛国”,但是现在已统统成了伊斯兰世界,那里的居民甚至不愿承认自己的祖先曾是虔诚的佛教徒。“远东”的印尼也是一样。这两年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即波黑战争中的所谓穆、塞两族,其实其人种、语言、历史都相同,是土耳其五百年的统治使双方的宗教发生了差别的结果,更不用提印巴分治了。我们历来总是说以力服人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而历史上却又有大量的反证,到底为什么?伊斯兰教的吸引力为什么这样大?军事、政治对文化有多大影响?人们研究得很少,所知并不多,看来还值得深究。
有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到近代以来才大大加速,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才不但更加加速而且已开始引起一部分人的惊恐,这就是由于移民而引起的文化移动。历史上有过许多因族群移动而融合的现象,但今天的移动来得太快,简直不容有融合的时间。比如上面谈到的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本来都是历史经过千百年的时间所形成的。到20世纪上半叶应该说还算稳定,但是从下半叶开始,法国增加了许多阿尔及利亚人(且不说还有别的非洲人),英国增加了许多巴基斯坦人(且不说印度人和西印度人),德国增加了许多土耳其人(且不说南斯拉夫人和其他外国人)。在这些本来只有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国家,现在都出现了许多清真寺,成为一种新景观。在所谓民族大熔炉的美国,原先以奴隶身份带着锁链到新大陆来的黑人本来无所谓文化传统,因此几乎全都随着自己的奴隶主信奉基督教,而且连姓名都是由奴隶主给的,因此美国虽然历来有种族问题却并没有文化问题。可是战后50年来,越来越多的黑人改宗伊斯兰教,自己给自己起了阿拉伯式的名字,前几年到过中国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现在黑人穆斯林的领袖法拉罕公开宣布成立伊斯兰国,一开起会来据说有百万之众,而且势力还在扩张。多元文化已成为所谓现代社会的常规。这种文化随种族而渗透的现象在发达世界的西欧北美特别显著,因为按照“人往高处走”的定理,生活水平低的地方的人总是要往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移民。正是这种趋势,今天已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内容,使亨廷顿这样的人不但忧心忡忡而且恐惧已极。他提出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敲起警钟,而且提出,西方只有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才能自保。其实敏感如亨廷顿之流不可能不预见到随着世界人口增长与移动的大趋势,用不了一二百年世界文化就会出现百衲衣式的情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不是可以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民族国家的组合可以划地为牢以自保的。只是有碍于所谓政治正确性—“PC”(Polical Correctness)而不敢说出来罢了。这样的前景可能导致人类历来视之为理想的文化融合,也可能导致许多人已经预言的文明冲突的悲剧。历史是无法预言的,今天谁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三、东西之分果然只是古今之异吗?
葛先生提出东方文化(我想葛先生这里的东方文化指的是一切落后于时代的文化的总称,与地域无关)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时代差异而不是本质差异。这倒不是新论点。至少就中国来说,自本世纪初有文化讨论以来就有了。冯友兰先生很早就提出的“东西之分即时代之异”之说,可能是最著名的一家。他甚至比喻西方人为城里人,东方人为乡下人,说中国人要求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力求从乡下人变为城里人〔1 〕。此话不但正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而且大旨也符合相信并且主张全人类都要进步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文化问题讨论了几十年,讨论来,讨论去,人们也发现各种族、各民族之间确有若干根深蒂固难于融和统一的东西在,也确有不能以社会发展阶段解释的差异在。葛先生以父母莫不爱其子女,子女莫不爱其父母,来说明文化的普遍性,这当然是事实,然而一旦制度化为一种文化,如中国的儒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其差别就不能算小了。耶稣确实讲过“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2〕。这与儒教教义完全对立。 利玛窦在中国本来想蒙混过关,容忍中国人既拜天主,又拜君父,以利传教,但是被人打了小报告,罗马教皇因此明令不能妥协,使其在中国传统的事业归于失败,西方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出发而养成了所谓个人主义,其好处是独立自强,其末流是利己主义。中国从“君父至上”出发,养成了所谓集体主义,其好处是可以为公利而牺牲自己,其末流是奴隶主义。两者的不同与冲突都是十分明显的。亨廷顿说:在可见的将来,世界上还不会出现一种统一的文化。迄今未见有人提出异议。所谓可见的将来大概一二百年也不算长。虽然人人都认为世界历史的运动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再快也不像能使一二百亿的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50年内就能达到此数)在一二百年内来一个“混一车书”。正因为如此,亨廷顿说西方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这话并不像中国有些论者斥责他的那样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他实际上已完全不相信西方文化有“化”掉人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民族的能力了。
四、文化果然没有优劣之分吗?
我在这里要向葛先生提出异议的是他提出的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应该说,这个观点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统一观点。我在50年代曾参加过一些外交文书的起草工作,就常常写到国家民族无分大小对人类文化宝库各有贡献、一律平等这样的话。最初是当作一种高尚的思想学来的,后来就深信不疑。但是久而久之,见识渐广,到现在已很怀疑这个论断了。十多年前,我在埃及开罗参观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刚好有几个台湾人同我一起参观,他们大概觉察到我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于是就来问我“咱们中国古代的东西要比这高明得多了罢?”老实说,我在中国虽然算不得一个好古敏求的学者,自问也见过一些世面,然而面对着埃及五千年(这可是不折不扣的五千年,不是我们那种含糊笼统的五千年)至六千年前的文物,我实在想不起当时的中国有什么可以相比的东西。然而这正是葛先生说的中埃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农耕社会或奴隶社会的时候。二十多年前,西安发现了秦俑,现在已成了中国人的“骄傲”,许多人竟不惜拾西洋人的牙慧称之为世界“第八奇迹”(他们不知道“第八奇迹”是可以任人排队的,比如吴哥就早被人称为“第八奇迹”了),但是,秦俑除了数量多而外,质量能与希腊、罗马的雕像相比吗?再看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初游西欧的,几乎无不对其艺术惊叹。文化(culture),就其最窄的定义来讲,本来就是指艺术, 我们不妨从石器时代西班牙和法国山洞里的岩画起,比较各地各时代各民族的绘画、雕刻、陶器、音乐、舞蹈、建筑,可以说优劣是确实存在的。至于在器物以上之各个层次如制度,如哲学,也不是不可比较,例如博学多识的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中国哲学美术“远逊泰西”的话。当然优劣的标准比较难于确定,但是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标准,当然决不是全部标准。情况确是比较复杂,极可能优劣互见,或优中有劣,或劣中有优;或优而可以变劣,或劣而可以变优;或优于此而劣于彼,或劣于此而优于彼,但是总而言之,是有优有劣的,否则各文明即无学习之可言,亦无交流之必要。至于为什么有优劣,有人以为人类各族群自有自己的语言起,即走上了开创各自不同文化的道路,再难一致。有人则因此而有所谓文化基因论,正如各民族的体质基因尽管是大同仍不无小异。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则认为各民族文化从起源时起,即有“不可共量性”。我则以为孟夫子所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句话也就可以说明白了,事物的本性本来就如此。如果要说民族文化基因有什么差别,那么最好(优)的基因就是最善于向人学习的基因,最坏(劣)的基因就是固步自封不肯见贤思齐的基因。
我自知这个思想如果在今天的“西方文明世界”发表,是违反所谓PC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两年以前我介绍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与美国《外交》季刊扎卡里亚谈亚洲价值的谈话。他说“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No.They are not.”我并不同意他的许多观点,但是很佩服他的勇气。他当时的话特指几万年前由亚洲跨过白令海峡到美洲去的印第安人。他的意思是说印第安人本来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亚洲人,但是在美洲的环境中生活了几万年以后变懒了,不那么优秀了。李光耀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自我嘲讽了一下,认为自己政治上不正确。可是实际上是十分自鸣得意的。奇妙的是我们今天有不少留洋学生却与他们的先辈不大一样,看不到人家的优点,而经常有一种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的情绪。这也许正反映了中国的进步,然而却缺少了孙中山、康有为、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那一辈人“知耻近乎勇”的态度。这是我心所谓危,深为忧惧的。
这是我要向葛先生提出商榷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很知道这是一些犯禁的话。然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还是要说出来向葛先生请教。我发现葛先生在文章中常有“优秀的”这样的说法。这样,按逻辑推理,似乎即不能没有“低劣的”以为反衬。所以我假设葛先生实际上也是承认文化有优劣的,不知是否唐突。不过我也赞成葛先生说的各民族文化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本质上”这个词太小了。人既然在生物学上属于一个种(specie),就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不能没有“质”的差别,则是经验事实可以证明的。
五、中国落后于西方多少年?
葛先生在文章中屡次谈到中国落后于西方“二三百年”。不知是否是葛先生的一个定论。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上升,关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年代不断在缩短,这大概是葛先生也注意到了的。我看到的最新的说法是,1840年中国败于英国不得不被迫割让香港,但是仅仅二十年前(即182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一。我起初甚为不解,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指的是中国的GNP数世界第一。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 (不仅指人口言,俄国与美国的疆域当时也还并未伸足),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GNP占世界第一确实不应该有问题,就像中国粮食产量一直是世界第一一样。但是当时世界有无各国的GNP统计,我不甚了了。总 之是听到以后不觉哑然失笑,觉得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要是都能这样认识问题,大可不必奔走呼号白忙乎了。当代中国人之虚骄之气一至于此,可发浩叹。
然而,我心里真正赞成的是葛先生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说的一句话“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五百年”。我还记得这是他死前不久在一个什么会议上力排众议,拍案而起,慨乎言之的。我的理解与他一样。五百年前,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1492年),亦即西方文明席卷(说裹挟或侵略亦无不可)世界的起点。中国文化从此有了一个大参考系,无论是凭目测,凭研究,说“至少”从那时开始落后,应当不会有问题。季龙先生学贯中西,他立说必有根据,不像我只是大而化之远远一望。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他的这一个论断,我特别希望葛先生作为他传衣弟子,能够表而出之,光大其说,一杀今日学界少年浮薄之气,反于求真崇实之正,功莫大焉。
注释:
〔1〕见冯友兰《新事论》。
〔2〕《马太福音》第10:34~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