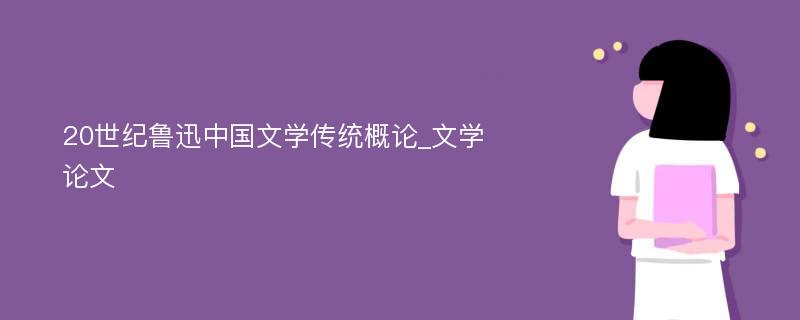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鲁迅传统》导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导论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传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传统”这个词儿被用来指称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应为后人所珍视的主要特点,指称鲁迅的文化路向、宝贵精神、创作成功的要素和文学活动的价值指向,似乎最早是1933年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语"revolutionary tradition"译为“革命传统”,用在鲁迅身上:“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他把鲁迅的“宝贵”的“传统”概括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接着是1937年冯雪峰说:“要以他(指鲁迅。——引者注)的全部著作当作我们文学工作的经典……要承接和发展这一种武器和这一个独特地诗的传统。”(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引者)[1]在他们之前,好像没有人把“传统”这个词儿用在鲁迅身上;后来很长时间,类似的用法也不多,只是偶尔有“进一步继承鲁迅杂文艺术的优秀传统”[2]等说法;到七、八十年代,“鲁迅传统”“鲁迅文化传统”“鲁迅文学传统”等才成为常见的说法。不过,这时,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许多人的笔下和唇齿间,“传统”二字用于“五四”运动起直至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点、文学运动主流、文化行为规范时,那意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指称这些的时候所用的“传统的观点”“传统的提法”“传统的做法”等说法,大抵不含“宝贵”的意思了,而多是表示“旧的”“过时”“保守”“偏狭”“错误”的意思,用来作为“最新观点”“最新潮流”“最新文化态势”“现代最新……”的反衬、对立物、要推倒要取代的东西。鲁迅和鲁学已被称为“古堡”。所以,当“鲁迅传统”“鲁迅的……传统”被提到时,在人们头脑里唤起的概念、意味、情感倾向都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分歧,都更复杂了。片面的、较全面的、贬的、以为“宝贵”的、以为“就那么回事”而一般化对待的都有。
先说情感倾向、意味方面。“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主流方面(或者说较多的人),在每个阶段都珍视鲁迅传统,他们许多人没有使用“传统”这个词,可是都大致像瞿秋白、冯雪峰那样,以为“非常宝贵”,都有继承和发扬的意向或激情。试看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说法:
蔡元培说:“综观鲁迅先生全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鲁迅先生全集序》,1938年。)
陈独秀说:“鲁迅先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我对于鲁迅的认识》,1937年12月。)
胡适说:“五年以来的白话文学……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差不多没有不好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3月。)
林语堂说:“我们对于鲁迅的成熟的艺术必得另眼相看,以别于那班‘萌芽’的作者。如果鲁迅,这位叛逆的思想家,是戴上了‘青年叛徒们的领袖’的头衔,那就是因为…充分的成熟性和‘独到处’,充分的气魄和足以给他们仰望的巍然的力量。”(《鲁迅》1929年1月。)
茅盾说:“比他(指鲁迅。——引者注)年轻十六岁的我,不消说,是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食粮……每读一次鲁迅的作品,便欣然有得,再读,三读乃至数读以后,依然感到一次比一次有更多更大的收获……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精深与博大,就因为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的缘故。”(《精神的食粮》,1937年3月。)
郁达夫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鲁迅的伟大》,1937年3月。)
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在文艺上成就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要学习鲁迅的精神。”(《论鲁迅》,1937年10月。)
巴金说:“我站在……鲁迅先生的灵前……心情很激动,我不相信他会死……的确,他怎么会死呢?二十多年来,我每想到他,我就感到他那强烈的爱……他给了我多少的勇气,给了我多少的温暖!”(《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56年7月。)
周扬说:“鲁迅所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伟大高峰,包含了极为广博的学识、哲理和智慧。他的独特而热烈的文风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1979年5月。)
以上所举几个时期、几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所说的有代表性的话,足以证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主流方面是珍视鲁迅传统的。至今还是如此。当代有深刻丰富的思想、有较大成就的作家、文学理论家中多数的老、中、青年还是觉得鲁迅传统“宝贵”,觉得当今社会、当今文化、当今文学仍然很需要鲁迅,感到鲁迅仍然活在他们心中,活在当代,而且走在“前面”,认为他的古代、近代文学传统与我们更切近,属于“现代化了的文学”,更值得重视和发扬。
2
现在,对“鲁迅传统”反感的,基本上或完全否定和弃置的人,还和以前一样是少数,处于劣势。但是,在要“继承和发扬”的人们中,有“遥远”感的,觉得已成“古典”并感到生疏而不亲近的、觉得不必特别视为“超级”宝物而只须当作“过去时代”的一种文学(和那个时代其他众多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一样)对待的,等等,已经存在,并且占了不很小的比例。此外,有些人虽不表示否定鲁迅,却觉得不如别的某些文学更合口味。其中某些人被某些文学引入了心理畸变状态之后,逐渐不自知地离鲁迅越来越远,以至于非常冷淡了。同时,他们却像有了瘾似地热衷于鲁迅所不为的隐逸闲适文学、恬淡空灵文学、“卿卿我我,哀哀唧唧……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的文学、沉溺秘闻琐屑的文学,以至热衷于鲁迅所唾弃所反对的“瞒和骗”文学、“二丑”文学、“流尸”文学、昏瞀在“△”里的文学,甚或热衷于逗弄肉欲、吹拍权贵富豪、艳羡强暴凶横的文学。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的确发生了更多的分歧,更复杂化了。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
有人自述对鲁迅的“认识”和“感情”说是“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读者》1996.4.第16页)这大约是35岁左右到45岁以下的许多人的心理历程,他们年少时的“信奉”、“热爱”不是较全面地自读鲁迅而得的深刻体认,而是带着少年难免的盲从性质的。那位自述者说,那时候是“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到了80年代有许许多多“新鲜第三者打进来”了,他对本来“信奉”“热爱”的鲁迅就“怀疑”“疏离”“厌烦”了;80年代最后一年起,又向鲁迅“回归”,一是因为意识到尚未走出“鲁迅的年代”,二是感到“只有读鲁迅”才能“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而不敢“在云端舞蹈”;三是觉得鲁迅几乎是出自文人却“唯一”没有那股令人“厌恶”的“中国文人”气味的人,这“值得惊奇”,然而“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看来,自述者是似乎想要做“继承”者的。不过,他同时认为,“鲁迅留下了缺憾”,而对于这“缺憾”,他不满意于“智识界”用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来“平衡鲁迅”,认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座标”的是胡适和钱穆,说鲁、胡、钱三人虽是“已经逝去的钱三角”,却应该成为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
从这种述说和见解,我们也可以看出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鲁迅传统的情感和认识的变化及其复杂性。类似这位自述者的人们,最早所“信奉”和“热爱”的是不是真实的鲁迅就成问题。当时热烈地接受了那种“包办”的,似乎并非完全因为“别无选择”,大约倒是因为更热烈地选择了别的什么——正是那种“别的什么”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个按那种方式造出来的另一个“鲁迅”,那个“鲁迅”与实在的鲁迅相去甚远,却得到了被“包办”者的接受,而且“热爱”了起来。当80年代到来,真实的鲁迅渐渐露面,原来的“包办”者和被“包办”者倒以为不是他们所喜欢的而“厌烦”“疏离”了,那确乎是同“第三者”大有关系的。“第三者”也未必真是“新鲜”的,有许多是数十年前甚至数百数千年前就存在并且很有些丑陋之处的,只是没见过、不熟悉他们的人觉得“新鲜”罢了;自然也有真正新鲜的,也有虽是曾被某些人胡乱丑化的老熟人却因卸了丑装,也很可爱的。不过,有许多被称为“第三者”的,他们自己并不是取代鲁迅,赶走鲁迅,倒是那些见异思迁者见了自以为“新鲜”的就拥抱,既“厌烦”了原来选择和热爱的假鲁迅,也没有和真鲁迅好好交流交流思想感情,甚至连真面的鲁迅什么样还不知道,就拒之门外了。对某位“第三者”的热恋期过后,发现了他(她)的丑、他(她)的心理缺陷,或者发现并不适合自己想借以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就再去拥抱别的“第三者”。随着自身要名、要位、要钱、要刺激的变化——并不是说每一个拥抱“第三者”的都如此,他们之中有一些是有对文化、对社会的正当美好追求的,那位打“包办婚姻”比喻的自述者,也许就是一位对做怎样的“知识分子”有高尚追求的——环境和人自身的诸因素导致目的和需要的转换,也就换着一个又一个的“第三者”,好久好久,他们没想到要亲近鲁迅了。近些年,确实看到了“回归”现象。然而这“回归”也各种各样。有的,又觉得原来所“信奉”的那个“鲁迅”比自己拥抱过的“第三者”们更适合目前的“兴趣”,于是,“回归”到那个片面的、被政治实用主义用为敲门砖和棍棒的“鲁迅”(稍稍改换了些服饰);有的“回归”,带了一个甚或几个“第三者”,而且自己曾经“疏离”的那位“鲁迅”虽然从真鲁迅那里捡来了点儿什么,却仍然不是鲁迅,带回来的“第三者”又原是鲁迅的对头或者是妖冶畸变、好逞恶性的“新”角色,那局面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回归”,一方面是向真鲁迅的回归,在切实深入的研究中逐渐接近鲁迅,有了自觉而诚挚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和“第三者”交往之后有所回顾,对于曾发生的昏瞀之恋有所检点,却并不作简单化的处理,也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知道其中一些人的特有之义和特有之美,正常地继续处为朋友,戒其过失,另一些沉滓、秽物才是要完全抛弃的。
无论看现在35岁上下到45岁左右的作家们对青少年时代情况的自述,还是当时接触青少年的时候所熟知的情况,都远不单是服从“包办婚姻”那么一种情况。他们有些人是没有服从“包办”,没有去“信奉”“热爱”那个被抬来推到面前的假鲁迅的,而是去接近真鲁迅的,尽管由于太年少,较难深入地了解,可是他们感觉到别人要“包办”给他们的那一位是个替身。真鲁迅要亲切得多,也博大得多,只要用心读了他的最容易接触到的作品如《一件小事》《祝福》《故乡》《孔乙己》《药》《风波》《社戏》《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理水》《自题小像》《自嘲》等,只要把课本上的这些作品印入了心灵,少年们就实际上不那么信从那个替身。况且,至少有一部分少年是自己用心读了些鲁迅的其他作品的。当时,也并非“别无选择”。那时候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其弊害多端,却也在客观上有点“积极效果”:给了少年们“自由活动”的“可乘之隙”。现在的中青年作家们,有许多就是当时在那“可乘之隙”里读了别的好作品的。当时的要“包办”者虽然不许,但在“乱哄哄”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他们也不那么容易“包办”得了少年们那么多事。从作家们的自述和当时我周围的大、中学生、知青们读书情况看,他们当时从长辈亲人那里得到书,从老师那里借到书,从图书馆里“偷”出书,从“缴获”的“四旧”里暗暗藏起了许多好书,如《水浒》《三国》《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新文学大系》,史汉文选及韩柳欧阳修的文,屈原陶潜三曹李杜苏辛的诗词,甚至有被宣判为“反动”的一些书;外国的有《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简爱》《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包法利夫人》《人间喜剧》《神曲》《堂吉诃德》等等。他们当时的这些“选择”,不仅不妨碍而且有助于他们接近和爱上鲁迅。我当时是青年教师,记得我周围的同事们,多数是没有反对而且支持青少年们读这些书的,自然也是在那种“无政府状态”下乘着“缝隙”支持。因而,当时青年中被“包办”得“信奉”假鲁迅的,只是一部分,另有既乘隙接近真的鲁迅又接触中外其他优秀文学的青少年们在。
在“第三者”纷纭复杂的80年代和现在,有昏瞀的也有清醒的。“回归”有先后,有各种情况,同时又有尚未“回归”和说不上是“回归”还是一直赶时髦翻筋头,或一直远离鲁迅,或一直嫌恶鲁迅的。与此相联系,对于“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有乐观而不重视阻力的存在的,(二)有因社会心理和文界状况的不良方面而忧虑的,(三)有“任其自然”的;(四)有压根儿没有纳入思考范围的,(五)有反对的。其中,第(一)(二)种人对于“继承和发扬鲁迅文学传统”有难度感的不同;后三种没有这种难度意识,但他们自身就是“难度”问题的一个方面。
3
心理反应、情感倾向、难度感的复杂多样和人们之间的参差、冲突,都与对“鲁迅文学传统”的不同理解联系着,都与对“继承和发扬”的不同理解联系着。
文学作品,文学家,与一般人相比,总带有某种复杂性;鲁迅和他的作品,他的文学观、创作历程和各种文学活动所呈现所蕴含的,则又特别丰富、复杂。他处在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式”向“近现代式”转捩的过程中,处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现代巨变的当儿。作为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产儿,他既在历史的联系上必然地承受传统,又必然地受近现代新物新潮的触动和冲淘。传统的良性方面,不良方面,优劣夹缠而一时难以理清的方面,他都不可能不多少有所承;他感应和选择的新物新潮,也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掺和着的。在同社会实际、政治风云、文化冲突相交流融会的联系中,在对古今中外文学的研究、取纳、融合的过程中,都形成和增强其丰富复杂性。生活史的曲折多变,所深味的各种痛苦、枯寂、忧愤和喜乐,心理历程的剧烈起伏回荡和多种矛盾,文化素质多方面的发展及其不平衡状况,思路、理论和观念的多源、多面、多层及多次自我超越,使得他在精神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留下了追求、探索、抗争和革新的足迹,使得他的文学观、文学活动和作品具有异乎寻常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丰富复杂性是人们在解读中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面。
另一方面是解读者群的复杂性。他们所处的时代、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和环境,他们的生活历程和经验,他们的文化素养、心理结构、文学兴趣、审美品位和倾向,等等,有种种差别。种种差别都导致解读的分歧。任何一种文学都会被解读成各种各样;鲁迅那么丰富复杂的文豪,对他的作品的解读必然更加多有分歧。
鲁迅论及人们对《红楼梦》的解读时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人们对于鲁迅的解读也许比对《红楼梦》的“命意”之解还要多种多样。单是阿Q,读者的不同看法就多得难以说准了:有些读者在不知作者与他们并不相识、不可能详知其事时,曾以为作者是揭他们的隐私,予以嘲笑的;稍后则有写“国民劣根性”说,写“人性弱点”(“人类缺陷”)说;接着有“精神典型”说,“辛亥革命批判”说,“旧社会批判”说,“文化批判”说,“农民”说,“民族性”说,“游民无产者”说,“生命现象解析”说,等等;至今仍然异说纷然,各不相让。对于鲁迅的总体性、倾向性特点的看法就更加歧见百出。“爱国主义者”和“汉奸”。“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不得志的法西斯”。“有革命倾向的知识者”“革命先锋”和“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人民文豪”和“堕落文人”“小官僚”。“青年叛徒的领袖”和“落伍者”。“西化”“断裂中国文化传统”和“承接和发扬了中国民族的战斗传统”、“师法”了几千年中“老”“儒”“墨”“佛”中的积极合理成份并与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博大精深”和“偏狭”。“伟人”和“小人”。有的说他晚年大量创作“诗和政论凝结”的杂文是“艺术的深刻”“艺术的高迈”;有的则说是“江郎才尽”。有的说他只是在中国文学荒芜中才显得有些创作,与外国的大文学家却是不能相比的;有的则说他不仅与高尔基在“对于劳动者大众的关系”上是“相似的”,而且尽了“别林斯基的历史的任务”,“在文学建立上又尽了果戈理的任务”,有的说在中国可与曹雪芹相提并论,在世界上也决不逊于歌德、司汤达、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易卜生、德莱塞等等。有的说他是“先知”,“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说他有“独立”的“高远深邃”的思想,是“导师”;有的却说他“浅薄”、不过是“政治工具”。有的说他的文学是深、广、清醒的现实主义,有人说又是“理想主义”“浪漫(积极)主义”的。有些人强调他的文学的“多种形式”的创造、“审美”的“高品位”和“独特深刻凝炼的风格”;有些人强调“社会镜子”“精神文化底蕴的丰富性”和改造社会的激情和改进人类的“终极关怀”。有的更强调思想和艺术都最强烈最决绝地“反传统”;有的更强调其在中国文化环境形成的、与中国优良传统“不可分离”的“中国民族性”和“独特的中国气派”。有的说他是“大众主义”“大众化”文学的先行者;有的说:有多少“大众”能读懂他的书?有的说“寂寞”“彷徨”“虚无”“无奈”“悲凉”“阴冷”是他作品的主色调;有的则说他总有“热切”的“希望”。一直有“前进”“革命”“抗拒”“战斗”的“坚定性”“韧”和“内在热力”,表面的冷是“火的冰凝”,从另一角度看,他也并不“枯寂”。总之,解读中的分歧太多了,要不要继承,继承和发扬什么,各有所执。
4
究竟什么是“鲁迅文学传统”?人们所感知、所认识、所概括的,有广有狭,有深有浅,有确切程度的差异——这是与客观存在的文学家鲁迅及其作品相比照而言的;人们所重视、所选择、所接受并且承而传之、发扬而光大之的,又相参差——这虽是解读者主观因素所致,但却是客在的鲁迅文学现象、底蕴、路向、特质及形成创作新形式、新技法、新风格的规律性等等得以承传和发扬光大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尽管人们的理解、继承和发扬都互相差异,参参差差,甚至误读错认,以偏概全,轻重倒置,真假混淆,割裂错位,以枝节摹写为继承,以方向相左而谬至千里的“理论”和作品为发扬,尽管这些现象往往令人眼花缭乱或令人心情不悦,但必须正视,必须去研究,辨别,排除谬误偏敝,杂乱里寻规律,砂砾中淘金子。在这样的过程中,经过努力也许可以逐步逼近鲁迅之真实,不断发现其新价值,逐步从解读者群中发现积极的正确的东西,从各种不同的“继承和发扬”中发现和综合出真正可贵的东西,逐步在越来越大的幅面上既取得共识,又各显神通,以使得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当今及今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形成相激共进的动态过程。
那些完全否定鲁迅文学传统,反对继承和发扬的暂置不论,其实那也是不值得多花笔墨反驳的,在明了鲁迅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后,自然可以明白否定和反对者们的荒谬。单从认同鲁迅文学传统、要继承和发扬却存在分歧的各种意见来看,问题常出在“摸象”式的偏弊上。丰富复杂的鲁迅文学现象和内质不仅其总体是多方面的整合,而且每个方面也多是貌似相反或不同特点的统一:
暴露和讽刺“国民劣根性”与爱“大众”、“为大众”的“大众主义”,及中国社会“病态”与爱国,人们就会各讲一点,其实鲁迅那里是整合融一的,启蒙、改造国民精神和中国病态社会就是爱国、爱大众、为大众。以歌颂工农兵为理由而舍弃“病”的“疗救”,或因民与国有病而不爱、不“为”,都和鲁迅不是一路。
爱国主义文学与“世界”(人类)性文学在鲁迅那里也是整合着的,各执一面的人们也是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片面性理解。
文学的鲜明社会斗争倾向,对于社会政治斗争,总是倾向于革命、进步的一面,在鲁迅那里是与他的“人”学精义、文化目的等密切联系而自然融一。爱人类、讲人道与改变现有人类的精神状态、克服缺陷相联属,因此就倾向于对于人类社会、世界现状的革命性改造。这与庸俗的政治工具实用不是一路,也与满足或听任自然人性的“人道主义”有异。
鲁迅的“写实”主义是有其“理想”的光照耀着的,他的“理想”、“浪漫”主义又是足踏在大地上的、与“执着现在”不相离的。一般地讲“写实”和悬离实人生的“浪漫”,都没有明白鲁迅文学传统的真谛。
民族特色(风格等)与融合域外新艺,往往被一些人各相孤立起来。讲文学的民族艺术风采就有意无意地排外,讲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新文艺的重要,就不自知地忘了民族性文艺的发扬。呈显新的民族特色与在“拿来”域外新艺基础上的独创相得相长、整合统一才是鲁迅传统。
“鲁迅式”审美也是多方面的。具有战斗者的雄厉勇猛,也有“回眸时看小於菟“的慈爱温暖美;有严正美也有幽默美;喜宏放却并非不仔细;辛辣尖锐极明显,对闰土、祥林嫂的描写中却更多的是亲切和厚道。他阳刚美突出,却并不排斥柔和美。要消灭苏州话,那是事出有因的一时偏激的言辞;总体上的鲁迅还是能和别的多种审美相容、共存、相长的。此外,丑中见美(丑得像阿Q,在与假洋鬼子、赵秀才等的比照中却见其可爱之处)、美丑关系的深沉审度等也要注意。如果把鲁迅的尖锐凌厉激愤孤立化、极端化,或把鲁迅的“艺术美上的宽容”说无界限,连兽性“文学”也被说成发扬鲁迅文学传统者应该认可的,那就是荒谬的了。
继承和发扬鲁迅文学传统,单强调某种艺术形式,片面张扬某种趣味,也会生偏弊。鲁迅是多向度的艺术独创的大师。多种形式的创造,多种风格及其整合性,艺术趣味之强及其多向性,文体有长项而更显多样风采,这是鲁迅传统。
有些人有继承鲁迅之态,却忘记了鲁迅在文学创作过程上是厚积而发的,忘记了他艺术创造上的“韧”,忘掉了他在作品酝酿、熔铸、表达上的精益求精。例如有些杂文政治观点鲜明、批判火力猛烈,只看到一点就写、粗糙生硬,既无厚积而发的智慧光芒,更无诗味儿,那就还是离鲁迅传统甚远的。
以上各个大方面,在鲁迅那里是集于一身的,整合着的。继承和发扬者既须分别研究,又须作为整体来学习。不然,既难免“摸象”之讥,又可能走入歧途而不自知。
1996年5月草于南京,8月改定
注释:
[1]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第2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2]刘半溪、孙昌熙、韩长经《鲁迅杂文的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见《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第56页。
[3]《鲁迅全集》卷8第145页,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