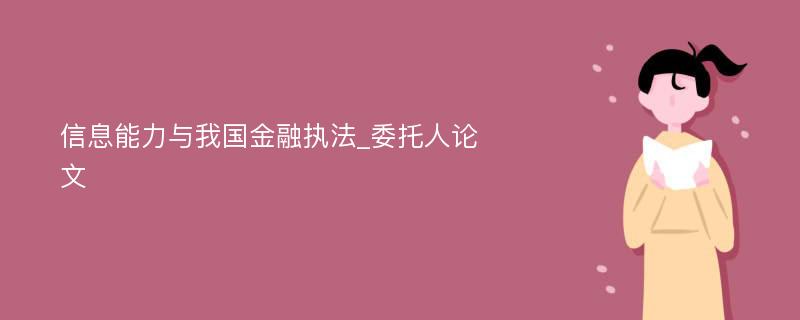
信息能力与我国财政执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能力论文,我国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1)11-0101-08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塑以及对地方政府竞争激励的影响已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学界讨论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的积极效果方面,例如可以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沈立人、戴园晨,1990;Montinola et al.,1995; Qian and Roland,1998)、政治晋升激励(Edin,2003; Tsui and Wang,2004; Li & Zhou,2005;周黎安,2007)等,以实现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张军、周黎安,2008)。但此种分析路径的有效性、解释力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王永钦和丁菊红,2007)。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我国财政分权的另一特征即“政治集权”,指出这是我国区别于西方分权模式的典型特征(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杨其静,2010),也是地方政府激励效应产生的前提(Qian and Weingast,1997)。应当说,对我国财政分权不同特征的讨论有助于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厘清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之谜”等问题的深入分析。但无论是分权下的地方竞争激励,还是集权下的中央调控,所有制度安排与运行绩效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共同前提,即中央能够掌握地方政府行动与绩效的准确信息。对此,既有研究多数都假定中央政府直接通过地方政府“行动”或地方政府“诚实”汇报就自动获得充分信息。很明显,此种假设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那么,中央政府如何获取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与绩效的真实信息呢?是中央政府直接调查还是依赖地方政府或掌握信息的第三方主动汇报?前种方式自然得到了中央政府执法资源、调查能力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而后种方式下,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及第三方汇报的信息是真实的?对于这些问题,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但分析对象仅仅是某些非正式制度,例如媒体监督(Egorov et al.,2007;蒲丹琳、王善平,2011)、民众抗议(Lorentzen,2008)、上访制度(杨瑞龙、尹振东、桂林,2010)等,但仍然缺乏制度性、体系性的研究。
我国财政制度运行与监督也存在同样问题。依据现行财政监督体制,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审计制度来掌握并监督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财政预算及相关政策执行等具体情况,并通过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保障纳税人知情权并让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活动,[1]但从现状来看,不仅各项审计成本很高,同时政策实施效果也并不理想,诸如政府审计“屡审屡犯”、[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不断出现。目前理论界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如何提高我国审计质量、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较少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信息的有效获取这一视角来研究。
如果依照McCubbins等人(1984,1994a)的分类标准,中央通过政府审计掌握地方财政信息的方式主要属于“警察巡逻式”(police patrol),而通过诸如媒体监督、审计结果公开的社会监督获取相关信息则属于“火险警报式”(fire alarm)。从理论上说,两种信息获取模式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但二者的适用环境、相关制度设计与运行成本并不相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对比两种信息获取模式的适用环境和制度效率,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执法行动与绩效信息最优获取模型,得出两种信息获取模式替代或综合适用的最优解。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当前中央政府应当依据具体制度环境,综合运用两种信息获取模式。最后,文章也对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警察巡逻”与“火险警报”:地方财政信息获取一般模型
在我国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同时拥有关于政策执行实际情况的“私人信息”,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获取地方财政制度运行效果的准确信息。具体来说,中央政府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要求地方政府主动向其汇报相关情况;第二,中央政府直接调查,包括常规性政府审计、特定时期“集中整治”,以及特定事项专项调查;第三,鼓励掌握真实信息的第三方主动汇报或曝光,比如媒体监督、民众举报、申诉控告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般常规性信息或可以显示其政绩的“利好信息”自然愿意汇报,但对于某些“不利信息”可能会隐瞒或虚假汇报,但中央政府或许更想真实掌握这部分信息,因而更注重第二、第三种信息获取模式。McCubbins and Schwartz(1984)将委托人直接调查代理人信息模式称为“警察巡逻式”(police patrol),而将掌握信息的第三方向委托人汇报模式称为“火险警报式”(fire alarm)。[3]
(一)两种信息获取模式的效率比较
“警察巡逻式”与真实的警察巡逻有些类似,主要是指委托人主动、直接调查代理人的行动信息,例如委托人可以通过审计制度、直接调查、监督讯问等;“火险警报式”则是指委托人采取被动、间接的方式,主要通过建立一套规则和程序,使得掌握代理人相关信息的第三方(个人或利益团体)可以向委托人进行报告,或者向委托人提出控诉、寻求救济等。委托人为第三方报告提供便利程序、负担部分报告成本、为第三方的质疑或控诉提供支持,以及组织相关第三方采取集体行动以对抗代理人。
尽管两种模式都可以使委托人充分获取代理人的行动信息,但二者在调查成本、行动激励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在“警察巡逻式”下,委托人需要投入大量的经济、时间等资源才能充分准确掌握代理人的信息,因而许多学者认为警察巡逻式的适用非常有限(Dodd and Schott,1979; Theodore J.Lowi,1979)。相比之下,“火险警报式”具有如下优势:(1)由于“警察巡逻式”事先无法确定监督的结果,委托人可能花费巨大成本却发现代理人并无违法或不当行为;“火险警报式”事先有相对人或利益集团的报告,因而发现代理人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概率更高;(2)“火险警报式”是事后调查机制,此时代理人行为可能已经引发第三方的抱怨或不满;“警察巡逻式”主要属于事前调查机制,不利后果可能尚未发生或并不严重。因此,在“火险警报式”下,委托人的调查处理可以获得更多外界支持,进而可能获得政治声誉;(3)在“警察巡逻”模式下,相关调查成本基本都由委托人自行承担;而在“火险警报”模式下,诸如不法行为的调查及相关证据收集等成本可能由信息第三方承担,因此“火险警报式”可以大量节约委托人的调查成本。
当然,“火险警报式”也并非必然地优于“警察巡逻式”。“火险警报式”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掌握代理人行动信息的第三方可能因为自身利益不提供警报或启动虚假警报,比如第三方已经从代理人的行动中获得不法收益,或者第三方与代理人串谋。因此,在“火险警报”模式下,如果委托人无法获得“警报信息”或无法保证“警报信息”是真实的,该模式就不能适用,只能转而选择成本更高的“警察巡逻式”以获取代理人的真实信息。那么,委托人如何才能保证第三方的“警报信息”是真实的呢?或者说,警报人提供真实“警报信息”的条件是什么?
(二)真实“警报信息”的供给机制
Lupia and McCubbins(1994a;1994b)提出了警报人向委托人提供真实信息的激励机制。[4]他们认为,委托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安排以激励警报人向其提供真实的信息:第一,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会受到处罚,也就是通过提高警报人的撒谎代价来遏制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但这一点并不必然保证警报人提供真实的信息,因为代理人可以用更高的价格买通警报人(如果可以事先确定警报人),使得警报人谎报信息仍然可以获得净收益;第二,委托人与信息提供者具有偏好一致性。如果警报者与委托人对共同结果(代理人的真实信息)的偏好保持一致,即警报人与委托人共享全部或部分的目标结果,此时警报人就会向委托人提供关于代理人的真实信息;第三,信息的可验证性。如果警报人知道委托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验证“警报信息”,警报人自然会选择提供真实信息。如果再结合虚假信息的处罚机制,这对提供虚假警报的威慑效果会更强。
因此,委托人与信息提供者的偏好一致性可以给警报人主动汇报提供正向激励,而“警报信息”的可验证性以及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进行处罚可以有效威慑虚假警报行为。此三项条件可以有效激励掌握代理人信息的第三方向委托人提供真实的警报信息。同时,如果警报人对其提供虚假“警报”的预期处罚越高,警报信息的可验证性越强,以及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共同偏好程度越高,其就越有可能向委托人提供真实的警报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委托人越有可能选择“火险警报”式而舍弃“警察巡逻”式。
三、我国地方财政信息获取模式最优选择
以上主要对比代理人信息获取两种模式及其效率比较。一般来说,相比较于“警察巡逻式”,“火险警报式”在成本分担、信息获取效率、民众支持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由于警报人可能会提供虚假警报,“火险警报式”也并非必然优于“警察巡逻式”,尽管委托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为警报人提供“激励相容”条件,但这也需要制度成本。因此委托人应该综合权衡两种模式的成本收益,从而选择最优的信息获取模式。
(一)制度运行成本与信息获取模式选择
依据我国现行财政监督机制,中央主要通过财政审计制度来获取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执行相关信息,即中央财政机关、审计机关以及驻地方专员(特派员)办事处等部门通过定期财政审计或不定期专项审计等制度来调查、监督地方财政资金使用以及财政制度执行情况。此种信息获取方式基本属于“警察巡逻式”,而依据上文分析,“警察巡逻式”在审查目标选择、审查成本与收益、民众支持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事实上,这些不足之处在当前财政审计制度已经有所体现,例如我国财政审计效率问题已经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5]而在“火险警报”模式下,上述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甚至避免。因此,在目前我国财政执法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摆脱过度依赖财政审计制度获取地方信息的做法,适当考虑采纳“火险警报”模式,即通过相关制度设计来激励第三方向其提供“警报信息”,以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最近理论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媒体监督在提高我国政府审计效率中的作用,例如陈红艳(2005)从2004“审计风暴”报道看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指出在这场风暴中媒体的监督力量空前加强,有深度的调查报道和有力度的评论使事件的真相显露无遗;[6]华金秋(2009)认为,政府审计与媒体监督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在抗震救灾资金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应协调政府审计与媒体监督的关系;[7]蒲丹琳和王善平(2011)进一步指出媒体报道在审计前期、中期和后期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审计质量,因此审计部门应尊重新闻自由,重视媒体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权力,借助媒体减少审计工作中的阻力。[8]此外,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事实上也会形成“火险警报”效果,这一点也逐渐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9]
但是,考虑警报激励制度的运行成本,中央政府也不能完全依赖“警察巡逻”模式,而是通过权衡两种模式在不同条件下的综合效果。具体来说,如果地方财政信息不易直接获取(即财政审计制度成本较高),中央政府应该更多地选择“火险警报式”;反之,如果真实警报信息供给机制的运行成本很高,或者中央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直接获得地方政府财政信息,例如可以比较方便地观测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执行活动,或者通过控制和调整授权内容(如授权可以观测的事项),或者地方政府谎报信息的情况并不严重,此时中央政府应该选择“警察巡逻式”直接获取地方财政信息。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应当根据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的重要程度、地方政府谎报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以及授权内容(信息类型)等因素,综合考虑两种信息获取模式以达到最优效果。
(二)信息类型、重要程度与信息获取模式选择
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不同类型、不同重要程度的财政信息也会影响到其获取模式的选择。首先,地方政府不同财政信息类型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模式选择。具体来说,如果地方财政信息或政策执行活动不容易观测,或者相关“警报信息”不能有效获得,以及警报人竞争市场非常不发达,此时中央政府只能选择“警察巡逻式”直接调查信息;反之,如果地方财政信息属可观测信息,或者警报竞争市场比较发达,中央政府就可以选择“火险警报式”。不仅如此,在“警察巡逻式”下,中央政府为有效降低相关信息的调查成本,可以通过调整授权内容与事项,例如授权地方从事更容易观测的行为,或者替换具体执行人员,以便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活动。其次,地方财政信息重要程度不同也会影响中央信息获取模式的选择。如果部分财政信息并非属于重要事项,那么对中央政府而言,虚假警报信息造成的影响并不严重,因而也就无须运用警报激励机制,直接依赖“警察巡逻式”就可以获得所需信息。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相关财政政策执行信息属于重要事项,中央政府直接调查成本可能很高,因而需要选择“火险警报式”。同时,随着中央政府掌握地方财政信息的“边际收益”不断增加,或虚假信息造成的“边际损失”越严重,其选择“火险警报式”的净收益也越大(投入的边际成本为零)。
因此,如果将地方政府财政信息重要程度视为连续变量,随着信息重要性的不断增加,中央政府信息获取的最优模式应该符合分段函数的形式:当地方财政信息并非十分重要时,中央应该选择“警察巡逻式”;而当地方财政信息逐渐变得重要时,委托人应该选择“火险警报式”。在连续函数的某一点上,委托人选择“警察巡逻式”与“火险警报式”的效用相等。
四、我国地方财政信息获取相关制度建设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依据地方财政信息的获取成本、信息类型及重要程度的不同,中央政府应当综合运用“警察巡逻”与“火险警报”模式,以获得最有效财政执法效果。鉴于我国财政审计制度(属于“警察巡逻式”)已经相对成熟,同时考虑到“火险警报式”在节约执法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我们认为在当前财政执法监督形势下,中央政府政应当更多采取“火险警报”模式,即通过警报信息激励机制的完善,鼓励更多警报人主动提供警报信息,以便更加充分、真实地掌握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执行与绩效信息。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可以建立下列制度:
(一)对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机制
在“火险警报”模式下,增加对警报人提供虚假警报的处罚意味着提高了其虚假信息成本,因而中央政府可以规定,如果警报人(包括新闻媒体)故意提供虚假警报信息将会受到一定处罚,以此来威慑第三方的虚假警报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说,对虚假警报的处罚越高,相应的威慑效果也越明显,但过高的处罚可能会抑制警报人提供信息的激励。因此,对于并不具有法定或约定警报义务的第三方而言,对其的处罚额度不能过高,即应当更多地通过奖励机制而非处罚机制。同时,为保障激励的有效性,对第三方提供警报信息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过高,原则上只要警报人不是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就不应该给予处罚,否则会抑制警报人提供信息的积极性。
(二)设定真实警报信息的奖励制度
如果警报人认为他们与委托人(中央政府)的偏好存在显著一致性,他们也就有更多的激励去追求与中央政府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警报人对其与委托人共同偏好的认知程度影响着其警报行为程度。因此,为更好地激励警报人提供真实的信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增强警报人对共同偏好的认知程度。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可以设定真实警报奖励制度,以分享真实警报信息带来的成果。如果警报人向中央政府提供警报信息,并经中央政府查证属实,就可以获得相应物质奖励,如此就可以增强警报人与中央政府对共同结果的偏好,进而激励警报人提供更多真实的信息。当然,如何科学设定物质奖励的幅度还需要进一步权衡。
(三)减少警报成本并建立警报人竞争市场
警报成本直接影响警报人的行为激励。如果中央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为警报人提供警报信息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程序,例如公布二十四小时热线、增加接受警报信息地点、扩大警报宣传、保护警报人的隐私等,不仅可以给警报人提供更多的便利,从而减少警报人的行为成本。同时在警报奖励制度综合激励下,警报人提供真实信息的激励进一步增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间接地形成了警报人之间的竞争机制:在虚假警报处罚和真实警报奖励机制下,任何掌握地方财政信息的第三方都有向中央政府提供代理人真实信息的激励,从而在警报人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竞争市场。同时非常便利的警报条件与程序,以及不断扩大的警报宣传等机制,使得警报人竞争市场不断扩大。警报人为在竞争市场中获胜(获得警报奖励),都会极力向中央政府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从而便于中央政府更好地掌握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此外,随着竞争市场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试图与警报人串谋或隐瞒信息也变得更加困难。[10]
五、结语
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绩效信息的获取是实现地方竞争激励的前提。中央可以选择“警察巡逻”和“火险警报”两种模式有效获取地方政府的真实信息。两种模式的选择依赖于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的重要程度、警报人谎报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以及授权内容(信息类型)的区别而定。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国家财政政策的信息主要是通过财政审计模式获得,此种“警察巡逻”模式的调查成本非常高。因此可以考虑适当引入“火险警报式”,除要求地方政府更详细地汇报相关信息外,还可以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更多鼓励信息第三方如媒体、利益第三方等警报人主动向中央汇报财政政策执行的相关信息。
收稿日期:201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