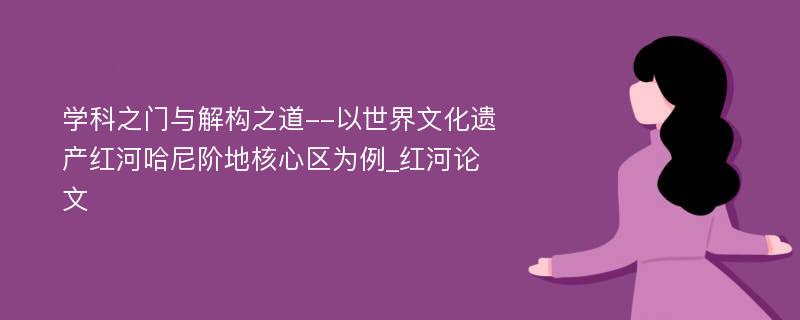
规训之门与解构之道: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核心区的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河论文,核心区论文,梯田论文,之道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5)06-0010-06 2013年6月,中国红河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5项世界文化遗产。在十余年漫长的申遗过程中,处于哈尼梯田核心区的哈尼族村寨箐口村也在经历着如何呈现真实传统文化及如何改造村落以吸引游客的纠葛。本真性或曰原真性是国际公认的文化遗产评估、保护和监控的基本因素[1],为了体现乃至强化哈尼梯田文化的本真性,当地政府在开展保护工作的同时,以“恢复历史”、“体现民族特色”为目的开展了许多针对梯田文化景观的规划及改造工作。从理论上讲,人们对文化本真性的认识已经出现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向,本真的文化“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2]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实的问题却是在认可了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时候,本土文化持有者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常常被忽视,由此也导致了以民族文化作为资源的开发活动事实上总是由外力主导的结果。这就大大地改变了现实的村落格局以及村寨内社会结构、文化逻辑的各种规划及方案的实施,而且还常常在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凸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名义下进行。从那些大手笔地改变传统村落的行动者的逻辑来看,要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露出当地身形之一角,要在现代性的众声喧哗中哪怕只是发出微弱的声音,都要按照外部的要求来改变村落中不符合这些要求的诸多方面。这就经常使得那些村落布局和许多文化事项都会被置于怪异的古希腊神话人物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上:身高者身体长出的部分要被去掉,身矮者的躯体则要拉长到与床的长度相等。 令人困惑之处则在于许多村民在这类要求他们削足适履的行动中常常是服从的,似乎这类切掉或者拉长身躯的行动与己无关。如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第二年即2014年的夏天,政府相关部门以凸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名义,把箐口村的许多人家的门更换成这个部门带来的新门,理由是这些哈尼人家的门不像他们带来的门那样具有哈尼文化特色。奇怪的是身为哈尼族的村民对于这个非常奇怪的理由并不感到奇怪,并不去问为什么哈尼人自己家的门没有哈尼特色,而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门反而是有哈尼特色的。这个明显给村民增加了不少麻烦的事居然在两周左右时间里顺利完工了。似乎门在哈尼族生活中已经单单只是遮风挡雨的物质意义的门,其原本具有的重要文化意义已经丧失,因而可以随意更换。然而,当我们对箐口村哈尼人家的门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意义及其变迁做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分析之后却发现,在面对此类行动时,当地文化拥有者并非只是一味服从,村民们事实上总是以自己的文化逻辑解构着此类外来的文化意义建构。对发生在村内的建寨门、更换宅门之类的静水微澜般的事件做出深入的分析,就有可能发现这些将外在于社区的文化意义硬性嵌入村寨中的行为到底对村寨内部产生了怎样影响,村民又是以何种逻辑在解构这些意义的。 一、换门或者规训门 2014年7月,箐口村全村232户村民中,居住在村寨主干道两旁的51户村民的宅门被政府相关部门用产自其他县的门替换掉,理由是这种门更能体现哈尼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而村民们说,他们过去从没有使用过这种式样的门,也从没有在附近其他的哈尼村寨中见到过这样的门。 如果对十余年来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及箐口村开发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就能够理解箐口村村民的宅门为什么会如此顺利地被替换掉。箐口村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位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域内,集中展示了“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四素同构的生态文化景观。箐口村村落格局建立在传统的社会和宗教结构基础之上,既兼顾了村民日常生活的便利,又体现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许多哈尼族村落的传统风貌依然保留着,具有传统民居特色的哈尼族蘑菇房在元阳县的村落中随处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打工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村民建盖新式住房而使蘑菇房逐步减少,平顶砖房日渐增多。元阳县在2001年提出旅游发展战略之后,便首先选择了哈尼族传统蘑菇房存留较多、交通较为便利的箐口村作为哈尼民俗旅游村来进行打造。在被纳入当地政府的旅游开发规划之后,箐口村的景观格局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变化。时至今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了近千万元用于修筑新的寨门,拆迁部分村民住房,恢复传统式样的蘑菇房,安装消防设施,修建生活用水池,安装路灯,修建两个村寨广场,建盖哈尼文化陈列馆,修建巨大的图腾柱,硬化村内道路等。2004年,箐口村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8年被云南省旅游局列为首批旅游特色村。2008年,元阳县政府引进云南世博集团,共同参与开发梯田旅游,组建世博元阳公司,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对哈尼梯田进行旅游开发。2013年红河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正是因为箐口村处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域内,所以申遗的成功更是引发了政府对箐口村新一轮的“打造”热潮。 在十余年的打造过程中,整个村寨从森林、田地、村落到屋舍,甚至人们的日常起居都成了遗产景观,也成了旅游者眼中的审美景观,村民们也被动地逐渐习惯了成为景观本身。承载着箐口村哈尼人传统信仰观念的家院之门,甚至守护村寨的寨门,都变成了一个个展示的物体。箐口村的村落格局、建筑式样等在十余年间有了诸多的改变,但这些改变很少充分考虑过村民的意见。 对箐口村民来说,建门和换门都是关系到家宅安定的重大事项。按照传统,换门是要请摩批选日子并要举行复杂的仪式才可以进行的大事。但是因为此次换门是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传统文化名义推进的,很少有村民敢于提出异议。绝大多数村民并不真正理解世界遗产是什么,他们只是迷糊地等待着相关宣传的承诺的兑现——申遗成功后,旅游业会腾飞,村民们都可以获益。很少有人敢为了自己的一些无法实证的小禁忌去冒破坏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之大不韪的。 外来者以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名义进行的更换新门的做法当然会使箐口村的景观发生变化。这类并没有经过合理性论证的行动是否就真的会让游客们欣赏,甚至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本真性是否真的能够让未来要来检查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专家们满意都还是问题。但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的行动其实是代替村民对门这一文化符号进行了选择,从而使村民们自己的选择权力被取消而成为一种规训。由相关部门统一规划门的式样的做法正是规训的“规范化裁决”[3](P.201)的具体表现。当然,这些规训从总体上讲都是以体现民族文化本真性及为了当地的发展的名义进行的。 二、作为文化符号的门 在哈尼族的现实生活中,门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无论是寨门还是宅门,都因其在空间上具有分离与联合内部与外部的作用,门的安装与装饰等都具有诸多的文化意义而使门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箐口村哈尼族的寨门和宅门仍然会作为多层次的隐喻在当下箐口村民的人生礼仪、节庆习俗中反复出现。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箐口村人也“借用户或门的符号意义,与其他符号搭配组合,表达一种顺应自然又引导自然的愿望”[4](P.88)。 哈尼族对寨门极为崇敬,他们建寨子的一件大事便是立寨门。哈尼族的祖先在选定寨址后,宗教人士摩批要杀狗,然后用狗血划定寨子边界,同时还要在村寨入口处选择道路两旁的两棵树,用一条稻草搓成的绳索横挂其间,上吊木刀、木枪、木槌等辟邪物,以此作为寨门。此后每年举行的“昂玛突”(祭寨神)仪式都要由摩批做仪式把村内不干净的东西扫出去,然后新建寨门并进行祭祀。“昂玛突”节日之后,有形的寨门撤下,无形的门却留在人们的心中。寨门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新娘被迎进男方村寨的寨门,就表明新娘被夫家村寨的寨神和集体接纳;只有本村的人才可以在村内生育;非正常死亡者必先由摩批在寨门外做了相应的仪式之后才能被抬入村内等等。 宅门对于箐口村哈尼人家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村民家门框上基本都挂有黄泡刺和蒿草,这是辟邪的。串着九个小糯米团的细竹签会别在门上方的墙缝里,这是祈福的。在门这一内外界线上,[5]村民们以辟邪与祈福二元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他们对内与外、熟悉与陌生、吉祥与危险等等关系的观念。 人生礼仪大都与宅门发生关系。如婴儿落地后,家人便立即在宅门的门楣之上悬挂黄泡刺杆避邪,还会通过在门外悬挂一把木弓或者一个鱼篓的方式来宣示所生孩子的性别为男性或者女性。新生儿出生后的第13天,家人会抱着孩子出门。在这之前,忌讳外人进入家门。因为不速之客可能踩断奶水,或者可能带人不祥之物。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进家门要用一对公鸡母鸡引路,公鸡是男方家的,母鸡必须是女方家带来的。新人进入家门之前,门的两边分别插着金竹和刺竹。新郎和新娘只有分别把金竹和刺竹拔起放在大门两边后,才能一起跨进家门。新人跨进家门时是不能碰到门的,其寓意是婚后生活不磕磕碰碰。 门对于箐口村哈尼族人家的意义也体现在传统节庆习俗之中。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扎勒特”一般从农历十月的第一个龙日起,至猴日止,历时6天。箐口村现在的“扎勒特”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隆重,但节日期间,妇女依然会制作糯米粑粑。一家老少齐聚家门之内,进行祭祖。之后男主人用一根细长的竹签串上9个糯米团,别在自家宅门的门楣之上的墙缝里。这是祈福。 家门之内是灵魂的安处之地。箐口村民大都相信人有十二个魂。丢魂的话,轻则生病,重则无药可救。丢魂的原因多种多样,丢魂的地方也千奇百怪。但从来没有谁会说在自己家门里丢了魂的。为丢魂的人叫魂时,也就只需把魂叫回家中。箐口村的“苦扎扎”节大致在每年农历六月中旬举行。在完成磨秋祭祀、秋千祭祀以及磨秋房祭祀等仪式环节之后,仪式主持人咪古会宣布祭祀结束。此时,远远地等在村中小巷中的妇女们都会每人端着一碗饭菜,叫着她们去参加祭祀活动的丈夫、儿子的名字往家里跑。刚刚结束仪式活动的男人们也都在“回来咯,回来咯”的呼喊声中往家里跑去。参加这些祭祀活动,也是有可能会丢魂的。守在家里的妇女也就必须在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赶快把参加祭祀活动的丈夫和儿子的灵魂叫进门来。[5]村民们从村外走夜路回来的时候,一般都要在家门外等几分钟才能进去,这是为了防止把一些不洁的东西带进家门,同时担心走夜路时因为匆忙而使魂跟不上。只有在家门前稍歇一会儿,等所有的魂都归体了,这个人才可安然跨进门,回到洁净的家中。 确实如道格拉斯所说:“穿过一道门的这种平常的经历能够表达很多种不同意义的‘进入’。”[6](P.44)从文化上看,正是因为箐口村的门有诸多的意义附着而成为能够表达民族文化特色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在生活的积累中汲取的象征,各种文化意义的存在也是由他们日常的文化实践而得到了保证的。 三、符号的能指变化与所指存续 生活在变,门也在变,与门这个符号相关的能指和所指及其关系也都在变。符号对于人的生活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拉康所说,由于符号的出现,自然才得以否定,文化生活才得以确立。[7](P.47)而作为“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的符号[8](P.102)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构成表达层面的能指和构成内容层面的所指及其关系的变化上。是生活的变化和要求使拉康所谓的“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从而表现了生活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生活的变化。箐口村的门以及与门相关的各种文化符号也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些文化符号的变化也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表征,并且也影响着社会生活本身。 随着人们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祈福、消灾功能的符号表达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箐口村宅门上方除了具有辟邪意义的黄泡刺和蒿草之外,往往还增加了废旧的剪刀或者断锯片。近十余年间,门神和春联也开始在村寨中出现并不断增多。村民对贴门神和春联原因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出外打工会平平安安;生病的牲畜会很快痊愈等都可能是理由。贴上这些东西可以使家人健康,事事顺利是大部分人的理由。 然而,大部分村民对于门神是什么基本都不甚了了。画上的人物是尉迟敬德、秦叔宝还是关羽或张飞,一概不清楚,但清楚的是这些好汉手里拿着的鞭、锏、刀、矛之类的武器是可以起到和黄泡刺一样的辟邪作用的。那些春联和福字则是可以和门上挂的汤圆串一样保证纳福和丰衣足食的。虽然村民过去还比较避讳红色,但现在开始相信这些物件是可以招财进宝的,是可以给家人带来各种各样的福气的,于是也就接受了。 用这些新的符号表达传统的消灾及祈福意义的村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村里当过干部的,包括原来的老村支书等;二是家中有年轻人在外地打工的;三是摩批和咪古等哈尼族社会的传统文化人。当过村干部的村民家里贴门神、春联和福字是容易理解的。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与村外的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对于汉文化也容易接受。出外打工的人将这些东西带回来,可以说是文化接触的结果。这些具有纳福意味的春联,具有防御作用的门神贴画等被带回家也是很自然的。最有意思的是作为哈尼传统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摩批与咪古这些人也在门上贴这些显然是其他民族的符号。新世纪以来,政府对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保护传承的力度越来越大。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宗教也以民族民间习俗的名义得到了政府的承认甚至尊重,哈尼族的摩批和咪古也因其对传统文化的掌握而成为政府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所倚重的对象。他们的文化身份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尊重。如箐口村的摩批李正林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哈尼哈巴”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人也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表演、传承等工作。这些文化交往使他们较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 当然,新的符号能指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符号能指的必然消失。2000年之后,政府要求那些新建的红砖墙都要涂上与传统土坯房颜色近似的涂层,以便不破坏作为旅游审美对象的村落景观。墙上的砖缝被抹平,其结果就是没有办法把串着九个糯米团的竹签别在墙上,于是许多人家就由男主人用指头沾上糯米浆在门楣上划9道印子,以此代表九个糯米团。尽管这些符号的能指发生了变化,但门作为内外的一个分野以及对内祈求家人健康、丰衣足食,对外以锋利之物对外在的邪性之物进行抵抗和避邪的所指意义依然延存。 从箐口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来看,传统的文化观念大都保留着。大多数村民的门楣之上的糯米的痕迹以及黄泡刺等符号都在那里,而这并不与新贴上去的门神、春联等新的符号形成张力。如果符号的本质就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是所有能够达到同一目的的符号共有的东西。”[9](P.39)那么,这些符号的本质即是辟邪与祈福。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一些更加新奇的符号也是可能出现并允许的。如箐口村前任咪古李小生家的门楣上居然钉了一个破旧的鞋底。他的解释是:亮起鞋底,可以把任何邪灵蹬掉,使之不能进入家中。也如特纳所说,“每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其实都与现实经历中的某种经验性事物相联系。”[10](P.41)可以用脚把东西蹬开这一生活经验最终凝结出了可以用鞋底把邪灵蹬掉这一认识。 四、规训的解构 对于村民来说,门当然要有遮风挡雨的作用,此外,村民们只要还可以在门这个空间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运用传统的符号或者新的外来的符号去表达驱邪及祈福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门是木门还是铁门,是光板的还是雕花的都不重要。政府部门要求换门,那就请便,只要那钱是政府出的。政府部门要换民族特色的门,那也无须向村民解释,因为所谓的“文化本真性”及“民族特色”是展示给外人看的。 无论是之前为了满足游客消费需要而鼓励当地村民自己开小商铺或是引进外地的小商贩进村开小商铺而进行的改装铁门的事情,还是现在为了体现民族特色而进行的换门的事情,都像修建新寨门,拆迁部分村民住房,修建村寨广场,建盖哈尼文化陈列馆,修建巨大的图腾柱,硬化村内道路等等工程一样,其推动力都是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发展经济,体现文化本真性、保护传统文化等目的。作为村寨主体的村民是否需要这样的改变,他们对发展的目的诉求是什么,以及他们在诸多行动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都没有得到考虑。由于在几乎所有的保护或者发展行动中都被置于事外,其结果就是本应作为发展主体的村民没有能够成为这些行动的成员。村民们也很难去接受这些新建造的物质实体及外来者新建构的各种文化意义。 由外力驱动的箐口村开发或者保护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村落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裂变为了两个部分:一是属于箐口村的,一是属于村外的。比如,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进村的那条土路没有像那些不搞开发的村寨那样把路修成水泥路面的或者是柏油路面的,而是修建成了弹石路面的,据说这可以让游客马上知道是进入新奇的民族村了。弹石路面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这条路主要不是为村民修的。这也就不奇怪原先是以修路补桥为善事而人人愿意出力的村民现在只会在路塌方的时候给这条路的主人打电话报告一声,却不会再去修路。进村道路旁的高大的图腾柱除了个别村干部知道那是什么以外,几乎没有村民会多瞟一眼。因为要体现民族文化旅游村的特色,所以政府实施的通水工程就要与别处不同,水管就不能修到村民家里,而是在村里修建几个水池,让村民的洗漱、浆洗、挑水都成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更加令村民不安的是那些村寨的仪式中的神圣意义也在发展的名义下受损。有时,领导带着外面更大的领导或者专家来到村里,要求摩批和咪古来表演一些祭祀活动。尽管有着诸多的不情愿,甚至在表演之后又另外做了禳解仪式,但他们还是表演了。但这些表演会使仪式的神圣性向娱乐性转移,村民对这类表演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忧虑不安,同时也抱怨宗教人士只管自己赚钱而不顾及村寨的利益,摩批和咪古这些宗教人士的威望受到损害。政府相关部门也不断地在村内进行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尼哈巴”传承中心就建在村内,相关部门每年也会组织县域内有名的摩批来中心开展交流活动,但村民基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不关心。确实,“新的文化符号建构的结果如何,要看不同的文化图式之间是否能够达成彼此接受的协议。如果当地人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经常处于一种失语状态,那么,这样的协议就很难达成。”[11] 毋庸置疑,各种发展规划在村寨内的实施也客观上改善了村寨的交通、卫生等情况,不能说村民没有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受益,实施许多发展项目带来的“涓滴效应”也是有的。但是,由于村民们并没有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发展项目的实施中成为真正的主体甚至很少成为参与者。对他们而言,得到的一些好处只是附带的。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他们也仅仅只是这些发展项目实施的正外部性的受益者。 该换的门都顺利换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意义建构的完成,也不意味着村民总是只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消解这种意义而平安无事。2010年,旅游部门在寨神林旁修建了一条颇具“曲径通幽”意境的观光石板小道。这条小道似乎也会像其他被硬性嵌入的其他东西一样,再次在村民“与我无关”的漠视中被游客所欣赏。然而,2011年7月的一天,村民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将这条小道堵了起来,修建的挡墙上粗粝的玻璃碴形象地表达着村民的不满。村民的理由是,这条道挡住了寨神的脚,小道边新修的栏杆挡住了寨神的眼睛。于是寨神很难保佑村民,而这就是修建这条小道之后有村民接二连三死亡的原因。尽管从研究者的角度看,修建旅游观光石板小道之后,村寨中的死亡率并没有增高,但村民的看法却无法用这些抽象的数据去改变。旅游部门对此无能为力,村干部和村内的宗教人士都在村民集体砌墙堵路这一天十分凑巧地外出了。此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解构外来者规训的效果十分明显。有村民已经说了,这次换门到底会不会在以后给主人家带来不好的东西还真说不好。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还不好说,但村民们另外的议论就真的是站得住的。他们说,如果真的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什么就只是给有游客走过的这两条街道的五十几户村民家换门,其他深巷中的更多人家的门为什么不换呢?村民们还会因此就前些年政府拿钱出来帮助改造危房的时候就总是先安排路边的人家而不是优先安排真正贫困的人家建房来说事。“他们爱做面子工程”,这就是村民的一般看法。 其实,村民对政府的权威是信服的。比方说,有不少村民认为村里的公章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尽管新农合等政策的实施已经改善了村民的就医条件,村民们也知道了科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遇到一些病痛的时候还是经常会在就医的同时去让摩批做一些驱邪的仪式。一些村民还会去找张白纸,请村干部盖上村民小组或者村委会的公章,然后把这张纸贴在门上,据说驱邪效果很好。还有一些村民说,这个方法在生产队时期就有了,而且效果也很好。效果如何,这不是本文要关注的。这里想关注的倒是这些行为会不会只是表现为政府怀着良好意愿去从事发展工作,却由于很少考虑村民对发展目的和手段的看法而使这些行动成为事实上的规训。政府的权威在规训被不断解构的过程中被弱化也是可能的。 毫无疑问,当地政府的各种发展行动的愿望都是为了当地百姓的发展。然而,为了体现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为了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当然也为了开展旅游、发展经济,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些由他们主导呈现的文化能否合乎外来者,如游客、世界遗产专家等等对民族文化的想象,而村民诉求的表达途径则没有被考虑。其结果就是,实施发展者在不断地规训着一切,而作为发展主体的村民却会因被规训而对发展本身进行意义的解构。解构之道就是将这一切视为与己无关的东西或至少不按规训者的愿望去接受这些意义。由于没有村民的真正参与,这样的发展在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能真正使村寨在发展中得到新的整合。村民在被不断进行的规训中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性,也由于主动性的缺乏而使文化创新的能力不断减弱。由此也使本可以在发展中不断加深的文化融合以及在融合中进行新的创造失去了可能。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般也会扩展人的生产力”[12](P.89),发展是与发展主体的能力增强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能够使村民的发展能力得到提高,这些发展项目的意义将会大大减弱。 收稿日期201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