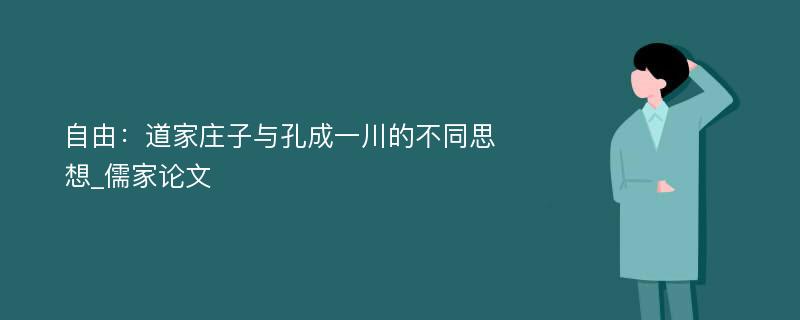
自由:道家庄子与儒家程伊川的不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川论文,儒家论文,道家论文,庄子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B24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4-0027-15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4.004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观念史家所梳理的“自由”一词的定义不下“两百多种”,“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1](P.170)缘此,以赛亚·伯林提出切不可用“惟一的尺度”裁评世界各种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自由思想与传统。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自由思想源远流长,恰如“儒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沛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精神”。[2](PP.284-285)曾经与徐复观笔战得“天昏地暗”的殷海光,时至晚年也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内在自由”[3](P.2)。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自由思想,是一座有待于学人进一步去挖掘与评估的精神“富矿”。本文以道家庄子和儒家程伊川为例,对道家和儒家自由思想的内在哲学蕴涵、生命旨归与境界形上学,作一些新的考辨与阐释,力图证明在中国思想史上,自由是超越学术派别之争而客观存在的天赋的自然权利。 一、人性是“道”之“德”:庄子逍遥自由的哲学论证 徐复观将庄子定位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4](P.252)。庄子之“伟大”,不仅在于揭明逍遥自由是人本性的澄现,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权利,是生命永恒、绝对的价值观与生命理想境界,更深刻的还在于从形上学高度论证逍遥自由何以可能。在庄子思想体系中,道既是宇宙本体,又是生命哲学层面的核心范畴。庄子一以贯之地表述一个核心观点:人人生而平等,人权是人本性的要素,逍遥自由是人性的朗现,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在本质上逍遥自由。庄子的自由,哲学性质上属于殷海光晚年所界说的“内心自由”、“开放心灵的自由”[5](PP.1175-1180),与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也有几分近似之处。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人逍遥自由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其实这是研究庄子哲学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可惜学界对这一深层次的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有一个哲学前提:“人有道德行为能力是否可能?”如果没有道德行为能力,就没有意志自由;如果没有意志自由,也就无所谓道德选择。因此,亚里士多德进而从人性论角度证明人有道德行为能力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两相比较,东西方古典哲学在问题意识和逻辑思维上,存在着一些相通性。就今本《庄子》33篇本而言,庄子及其后学对“人逍遥自由何以可能”有一个深入而全面的证明过程。庄子将逍遥自由哲学建基于哲学本体论与人性论基石之上。在人性论上,庄子有一个基本观点:人有现象自我与本体自我之分,在本体自我意义上,人性善且自足。正因为人性善且自足,逍遥自由生命理想境界的实现得以可能。那么,人性善且自足的形上学根据又何在?庄子的回答是“道”,“道”既是哲学本体,也是一德性本体。“道”决定了人性的本质,“道”是“臧”,道先验至善!道分化在人而为“德”,因为道善,所以性善,“道”因此也暴露了人逍遥自由的形而上根基。在人性论、逍遥自由生命理想境界与道论三者的关系上,庄子的证明过程井然有序:“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在小强盗与大盗跖的对话中,表面上是在讨论仁、义、智、圣、勇等伦理价值观是否具有普适性。大盗跖立场坚定地认为“盗亦有道”,仁、义、智、圣、勇不惟善人信奉,强盗对这一“圣人之道”的尊奉较之善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庄子及其后学于此提出了一个质疑:世俗社会中的仁、义、智、圣、勇伦理价值观存在的正当性何在?缺乏正当性证明的伦理价值体系,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人文精神往往缺位。人文精神缺位的伦理价值体系又何以能为人们所普遍信仰?如果说在《胠箧》篇还只是提出了一个疑问,那么在《天道》篇中,庄子及其后学开始从人性论高度探讨仁义与人性的关系:“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在老聃与孔子的对话中,已开始论证仁义与人性的内在关系:仁义是否源自人性?这一探讨极具理论价值,所达到的哲学深度令人欣慰。在儒学史上,孔子“仁者安仁”命题已初步从道德形上学高度说明仁出自普遍本性,仁内在于生命本然。孟子继而揭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性所固有,“四端”源自天,落实于心为人性之“端”。因为人性与“天”相牵扯,所以仁义是“命”,命意味着普遍性与绝对性。孟子与庄子的人性学说在逻辑思维上,存在着相通之处。在《庄子·天道》篇中,尽管孔子(当然这只是庄子寓言意义上的孔子)已从人性论高度证明仁义的正当性,但是,老聃仍然批评孔子是“乱人之性”,其缘由在于孔子没有从本体论(道论)高度证明仁义与人性的内在关系。这种没有“放德而行,遁道而趋”的人性学说,其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然可疑,“兼爱无私”实际上只是“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子·齐物论》)层面上的偏曲私爱。在反驳与批判的同时,庄子及其后学继而从正面论证道与人性、仁义的关系。在《齐物论》中反复出现“真君”、“真宰”概念,类似概念在《荀子·天论》和《管子·心术上》篇也出现过。“真君”、“真宰”意味着统摄、主宰与支撑,释德清说:“天真之性为之主宰。”[6](P.27)“天真之性”有别于世俗社会的人性,“天真之性”源自道,“天真之性”在《庄子》各篇章中称之为“常性”、“真性”:“夫道,渊乎其居也,渗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故金石有声,不考不鸣。万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广,其心之出,有物采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此谓王德之人。”(《庄子·天地》)“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一句非常重要,道、德与生(性)三者的关系已挑明。成玄英《疏》云:“德者,得也。”道得之于人心为“德”为“性”,所以“立德”的目的在于“明道”。据徐复观先生考证,《庄子》诸篇中的“道德”就是“德”,“德”即“性”[7](P.228),这一结论持之有故,予人启迪。“因之,性即是道。道是无,是无为,是无分别相的一;所以性也是无,也是无为,也是无分别相的一。更切就人身上说,即是虚,即是静。换言之,即是在形体之中,保持道的精神状态。凡是后天滋多蕃衍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性,或者是性发展的障碍。”[7](P.228)性源于道,性就是德,有道性才有人性,“合乎人性以合乎天性为其实质的内涵”。[8](P.223)庄子及其后学的这一观点,已从哲学形上学高度证明人性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朱熹曾经考证孟子与庄子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孟子从天论,庄子从道论,两人不约而同地从哲学形上学高度论证人性本质与存在正当性,先秦时代所达到的哲学成就令人骄傲!“真性”是“道德”,源自道,以道为哲学形上学依托,性作为道之德,自然而然禀受了道性。道自身先验性具有仁义属性,“道德明而仁义次之”(《庄子·天道》),“吾师乎,吾师乎!虀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庄子·天道》)仁义是道固有的本质属性,所以道至善。《齐物论》中的“无己”、“无功”、“无名”,表面上是赞颂真人之德,实际上是表述道之品性,因为真人、圣人、至人都是道之人格化形象。道至善,在《骈拇》篇中直接表述为“臧”:“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兄,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臧”即善,成玄英《疏》云:“臧,善也”。德源出于道,德“臧”自然以道“臧”为前提。“臧于其德”和“任其性命之情”,都是指道在人性之彰显。道善决定了人性善,人性(“真性”)中的仁义是“道德不废”意义上的仁义,这种仁义是“大仁”、“至仁”。在庄子所建构的诸多寓言中,“浑沌之死”发人深思:“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吕惠卿认为“浑沌之死”意味着“丧其素朴”[9](P.167),释德清认为“浑沌之死”象征“丧其天真”[6](P.149),“视听食息”代表人的感性欲望,七窍开而浑沌死。真性一旦死亡,“人之性”就随之而生。因此,在庄子人性学说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人性概念。 其一,“人之性”。“人之性”属于现象自我,是情与欲层面人类本性。“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真性”与“人之性”不可混同。毁坏白玉而成珪璋,毁坏道德而成仁义。“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人之性”已经与“道”和“德”相割离。当年孟子与告子为“仁义内在”还是“仁义外在”辩论不休,庄子所言“人之性”,近似于告子所主张的“仁义外在”之性。仁义是人类社会自黄帝、尧舜以来的矫情伪性之作,属于“人伪”(《庄子·渔父》)。“出乎性”、“侈于德”(《庄子·骈拇》),人性与道与德相割离,所以这种仁义犹如“附赘县疣”,不仅对人性无益,反而“残生损性”(《庄子·马蹄》)。世俗社会中的仁义不是“大仁不仁”意义上的“大仁”,而是“虎狼,仁也”意义上的小仁小义,是“道德”已废前提下的仁义,这种仁义价值观散发出世俗社会的功利、自私与邪曲的“气味”。“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凡成美,恶器也。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庄子·徐无鬼》)假仁义之名,行蝇营狗苟之事,“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不过是为了“养吾私”(《庄子·徐无鬼》)。人类社会自黄帝、尧舜就开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庄子·在宥》),人类由此进入了“大惑易性”时期,“自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庄子·骈拇》)因为圣王明君“制造”出来的仁义外在于人性,并且与“道”相悬隔,千百年来芸芸众生一直陷于“大惑”生命境地。《骈拇》篇多次发出的“意仁义其非人情乎”的呼吁,既是智者的觉醒,也是智者的痛苦。 其二,“真性”。在庄子人性学说中,既然性就是“道德”,性就是“道”在人之德,道德之性就不可等同于世俗社会中的“人之性”:“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庄子·天地》),“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庄子·山木》)仁义忠信内在于人性,源自道,得之于人心而为“德”。所以这种先在性蕴涵仁义的人性是“道德之正”(《庄子·骈拇》),属于本质自我。多次出现“不知”,旨在说明仁义忠信不是尧舜等帝王发明的,也不是世俗社会从外在强加于我。仁义忠信礼内在于生命,不假外求,犹如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道性至善,所以人性(道德)至善完满。人性完满自足的这一理想境界,庄子称之为“愚而朴”(《庄子·山木》)。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人性论史上,庄子才是第一个真正提出并系统证明“人性善”的思想家。孟子只是反复阐明人性有“四端”,“四端”来自“天”,得之于人心为性。孟子“遇人便道性善”[10](P.199),意在启发人人皆先在性禀有善端,当护守并扩充之。但是,孟子从来就没有全面否定自然人性是否也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关键在于是“从其大体”还是从其“小体”。孟子有“君子所性”与“人之性”之分,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立足于自由意志“应然”层面,呼吁人人应自觉以“四端”为性。孟子所倡言人性有“善端”与庄子之人性至善完满相比,显然不可混同为一。庄子立足于道论证明人性善,其哲学意义在于——人性平等。真正的自由必须建基于平等的文化基石之上,否则所谓的自由只是王公贵族少数人的自由。无论你出身于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德性皆来自道性,德性的光芒无尊卑贵贱之分。庄子“德性源起于道性”的观点,有别于西方中世纪神学家宣扬的人之德性是“神的直接启示”,道不是上帝人格神,道只是形而上学本体。逍遥自由是人性的实现,人生而逍遥自由,逍遥自由体现在精神与道德层面,具体表现为德性平等与自由选择。在《庄子》文本中,“得道”、“体道”者大多数是社会地位卑微如庖丁阶层。庄子思想的这种反复陈述,绝非随意为之,而是蕴含深刻哲学义旨。因为人性平等,“注定”了逍遥自由具有平等性。平等是庄子自由理论最大特点之一,平等意味着人人实现生命内在超越存在可能性,意味着道家主体性的确立。 在庄子思想逻辑框架中,道性至善,德是道分化而内在于人性,道即是德。正因为道至善,所以人性善、人性平等。徐复观先生点明,庄子经常以“天”代替道,道即是天[7](PP.224-225)。“法天贵真”命题的提出,合符庄子思想的内在逻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庄子·渔父》)“真”指“真性”,成玄英《疏》云:“谨慎形体,修守真性。”真与礼有别,“礼者,世俗之所为也。”(《庄子·渔父》)“礼”指称自尧舜以来“制造”的仁义价值体系,人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礼”充满了功利性与片面性,所以庄子斥之为“人伪”(《庄子·渔父》);“真”是《齐物论》所言“道德之正”,“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真性源出于“天”,也就是源出于“大道”,道与天在这里是同义词,天主要强调其自然性、平等性和内在性。“法天贵真”一方面表明真性是人类生命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慧所在;另一方面,“法天贵真”以真为贵为美,指明了人类实现生命理想境界——自由——的路标与责任。“道之所在,圣人则之。”(《庄子·渔父》)庄子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哲学。不仅如此,庄子的逍遥自由生命哲学又是自由选择理论。庄子学派不仅阐释了逍遥自由生命哲学的基本内涵,证明了逍遥自由是否可能、何以可能,而且也指明了实现生命理想境界的路向与责任。“夫体道者,天下君子所系焉。”(《庄子·知北游》)《齐物论》与《逍遥游》中的理想人格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但始终没有解释理想人格何以能臻至如此超越自由无碍境界?《达生》篇对此作出了解答:“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实现生命内在超越,有赖于两大条件:其一,“养其气”,这是工夫论意义上的概念,心斋、坐忘、去欲等等,皆是其中内容;其二,“壹其性”、“合其德”,这既是认识论层面范畴,又是道德践履层面范畴。人性之德在本体上源自于道,是道在人心之澄现。因此,人在后天的经验世界中,应始终如一“守性”。“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悟道、体道、“反真”、逍遥,尽性成德,是“天下君子所系”,是人人实现生命内在超越之唯一正确方向。逍遥自由,并非后天世俗社会的制度、习俗或道德体系所认定的主张,而是人人生而具有的正当理由。 二、从天理“元善”到仁善:程伊川自由思想的哲学证明 徐复观尝言:儒家仁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这是“儒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非常重要的一大学术观点,时至今日,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儒家仁学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伦理基础是否可能?自由思想的政治指向与愿景何在?凡此种种,这是学界需从理论高度深入探讨的一大课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程伊川无疑是一位公认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正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所言:“在新儒学复兴儒学的运动中,真正有创见的人物是程伊川。如果衡量一位哲学家伟大的尺度是他的贡献的独创性和他的影响大小的话,毫无疑义,程伊川是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11](P.32)这位“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最伟大之处”,在于构建以“天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虽然《庄子》《韩非子》《礼记》等典籍已出现“天理”一词,“能指”虽同,但“所指”与哲学意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程明道颇为自豪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2](P.424)“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在哲学性质上,无生无灭,犹如华严宗所言“涅槃无生无出故。若法无生无出,则无有灭。”[13](P.82)既然天理不可以“生灭”界说,自然没有空间的特性,“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则可以由辞而观象”[14](P.1205),“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15](P.21)“理无形”的表述在程伊川文章中多次出现,“有方所,则有限量。”[16](P.913)天理无方所,不存在具体存在所具有的空间特性。此外,天理有时间特性吗?换言之,天理有时间起始吗?程伊川的答案是:天理不可以用时间界说。程伊川是否受到庄子与华严宗、禅宗的哲学影响,尚有待于细究。庄子明确点明“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庄子·秋水》)道与物截然相分,形上层面的“道”,不可以“终始”来界说。道没有具象那种度量时间属性,具体之物才有度量时间属性,因为时间与空间只是具体存在才具有的存在方式。天理无形,天理无终始,甚至“天理”这一概念本身之“能指”与“所指”,也“只是道得如此,更难为名状”。[15](P.38)天理在逻辑上“难为名状”,使用“天理”这一概念也不过是“强为之名”(《老子》),这一观点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如果将天理界定为大乘空宗意义上的“空”,无疑也是大错特错。“和靖尝以《易传序》请问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莫太泄露天机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12](P.430)天理是“至微”,是无形无象的“实”,不是绝对性的精神本体,也不是大乘空宗绝对之“空”。张载曾经说:“太虚者,气之体。”《正蒙·乾称》太虚即气,“清虚一大”的太虚是气之本然状态。张载批评“虚生气”,因为这一命题将太虚与气相隔断,甚至将太虚论证为位列气之上的宇宙本体,太虚成为位格最高的宇宙本体。程伊川也多次谈太虚,但对“太虚”这一范畴作了全新的哲学界定:“又语及太虚,曰:‘亦无太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15](P.66) “又语及太虚,先生曰:‘亦无太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或谓‘许大太虚’,先生谓:‘此语便不是。这里论甚大与小!’”[17](P.610) 《河南程氏遗书》和《宋元学案》记录的这一段语录基本相同,只是《宋元学案》多出了后面一段对话而已。程伊川把太虚“置换”为理,“旧瓶装新酒”,含义与哲学意义焕然一新。天理不可以“大与小”界说,但是,天理是“实”,不是绝对之空。因为有“实”的哲学特性,天理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本体。“问:‘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这里只是点头。’”[17](P.610)面对大千世界的山川树木、鸟语花香,只能“点头”,不可用语言表述,甚至也不能用范畴、概念界说,因为人类能说与所说的只是哲学本体的一偏,而非其全体。“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①天理是自在的存在,不是人的创造物。不会因为尧是圣人而有所增加,也不会因为夏桀暴虐而减损。“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14](P.1272)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天理作为宇宙的“所以然”始终存在。“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15](P.215)这句话前半截源出于《孟子》,在“尽心—知性—知天”逻辑结构中,孟子力图证明“四端”之德性具备普遍性与绝对性,所以人人需“立命”。程伊川巧妙移植过来,旨在说明作为天地间“所以然”的天理,其存在与作用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天理也是“命”。 但是,需特别指出的是,二程兄弟精心建构的以天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其最终的哲学追求并不是对纯粹自然世界的本质与奥秘进行探索。“醉翁之意不在酒”,二程天理哲学真正兴趣与最高目标关注的是人,即人自身如何尽性成德,“止于至善”,在人生“此岸”实现内在超越。换言之,二程兄弟天理哲学的真正兴趣在于证明“止于至善”何以可能以及“仁义”等儒家伦理观念存在的正当性与普遍性,而非矻矻探寻自然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在儒家道统上,程颐是对孔孟思想与逻辑的“接着讲”,标志性的命题就是“性即理”: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15](P.292) 伯温又问:“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15](PP.296-297) 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② “性即理”之“即”不是谓词“是”,而是“若即若离”之“即”,含有“融和”之义。从人与本体关系视域立论,性是天理在人之彰显与落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人作为认识与实践主体,理“夯实”为性理,理才具有活泼泼的意义。由此而来,“性即理”层面的“性”自然而然具有“善”的品格:“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15](P.274) “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15](PP.296-297)“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18](P.17) 程颐、朱熹皆认为性是天理在人之实现,“性者,浑然天理而已”。[19](P.2427)这是儒家主体性的挺立。在程朱哲学逻辑结构中,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理之性”先验蕴涵“健顺五常之德”。具体而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都是性之固有内涵。“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16](P.968)“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15](P.14)“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0](P.1885)天理浑然不可分,天理与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关系不是本体与派生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本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仁义礼智并非由理“旋次生出”,理是人伦道德的“总名”,仁义礼智信则是天理之“件数”。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兄友弟悌,各有所止,当止其所止则安,失其所止则乱。在社会伦理诸德目中,仁的地位最高,仁是“体”或“全体”,义、礼、智是“支”:“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15](P.14)在社会伦理体系层面,仁是集合概念,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是仁之精神在各个社会关系准则中的具体表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15](PP.16-17)“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义礼智一般。”[19](P.107)程朱哲学中之“仁”,犹如周敦颐哲学思想中之“诚”。诚是太极之德,贯通天人上下。仁是“理之性”之德,因此,仁有“公”之品格,“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15](P.285)“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15](P.153)“公”是仁内含之天理,仁是“公”之具体实现。朱熹对此诠释说:“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19](P.111)天地之理是“公道”,“公道”在人心彰显为仁。朱熹所说的“公道”,在程伊川思想中等同于“道心”:“‘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15](P.256)公与私相对,私是人欲、“客气”,公的基本特点是“克尽己私”,也就是中正、公平、公正、普遍,克尽己私方能彰显天理之中正公平特性。既然“仁者公也”[15](P.105),仁是“公”,自然意味着仁是善,仁善的形而上根据来自“至善之源”[19](P.1388)的性:“盖本然之性,只是至善。”[19](PP.1387-1388)仁是至善,意味着这种善类似于托马斯·格林哲学意义上的“共同之善”(common good),“共同之善”适合于天地间每一个人。 由此而来,“性善何以可能”已是程伊川势必应当回答的哲学问题。葛瑞汉指出,程伊川在论证“性善何以可能”思路上,其问题意识与逻辑路向可梳理为:从天理落实到性,性善因为天理善。“至于二程,伊川毫不犹豫地把善归于理,因而也归于性。”[11](P.209)葛瑞汉这一诠释应当是“原样理解”,从天理至善落实到性善、仁善,确实是程伊川一以贯之的运思路向:“如天理底意思,诚只是诚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别有一个诚,更有一个敬也。”[15](P.31)天理是天地万物“所以阴阳者”,是“事物之所由成为事物者”。[21](PP.88-89)既是天地自然存在之最终依据,又是人类社会应然法则,所以称之为“百里具备”。不仅如此,天理还是性善何以可能之形而上学根据:“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15](P.292),“盖天道运行,赋与万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则所谓天命者也。”[22](P.641)天理“至善”!程颐、朱熹这一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在儒家谱系中,寻找并证明“至善”,是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矻矻以求的哲学使命。《大学》“止于至善”,还停留在生活伦理的视域论证,尚未上升到形上学的本体论高度证明。周敦颐以“诚”论太极之德,太极本体已蕴涵“纯粹至善”的超越德性,但尚处于发轫时期。一直到程明道、程伊川和朱晦庵,才系统、深入地从哲学形上学高度证明“至善”何以可能。 缘此,程朱是如何从形上学层面证明“天理”至善的呢?粗略分析,似乎可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从天理“生生之德”意义上立论。在程颐、朱熹思想逻辑结构中,对“天理至善”何以可能的证明,首先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中寻求理论资源。“‘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15](P.29)“造化所以发育万物者,为‘继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为‘成之者性’。”[19](P.1897)《易传》作者所言“生生”之德,是从宇宙生成论视域立论,“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本原化生万物,宇宙之间一片春意盎然。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每一种物体都按照其本性自由自在生长。但宇宙本原从不居功自傲,宇宙本原有“生生”之德,“生生”之德即是善。在传统思想资源意义上,除了《易传》之外,程颐、朱熹思想与老子“道”论有几分相通之处。老子“道法自然”即“道不违自然”。道生成万物,但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十章),道并不居功自傲,也不干预天下万物,而是遵循万物之本性(自然),让天地万物自身如其自身的存在与变化。道不仅是宇宙本原,而且道有大德。换言之,道是价值本源与根据。严灵峰认为老子之道有四重义项,其中之一就是道乃人生修身养性之应然法则。[23](P.378)唐君毅也认为,老子之道蕴涵“同于德之义”:“道之义亦未尝不可同于德之义。盖谓物有得于道者为德,则此德之内容,亦只是其所得于道者;此其所得于道者,固亦只是道而已。”[24](P.230)道是“德性”的最高存在,程伊川的天理也先验性具有德性。 其二,进一步从超越的意义层面立论。周敦颐《通书》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周敦颐以“诚”贯通天人,以形上本体之诚,论证人之心性之诚何以可能。价值本体已蕴涵“纯粹至善”的先在德性。二程思想中“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应当是对周敦颐思想的“接着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如一阖一辟谓之变。”[15](P.67)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15](P.162) “理则一而已,其形者则谓之器,其不形者则谓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盖阴阳亦器也,而所以阴阳者道也。是以一阴一阳,往来不息,而圣人指是以明道之全体也。”[20](P.2147) 程颐、朱熹在运思路向与观点上,显然与《易传》作者大异其趣:一是以“天理”范畴取代了阴阳气论,理是“所以阴阳者”;二是不再局限于从宇宙生成论角度立论,而是从价值本体论高度证明。作为非对象性存在的天理,其自身之善天然具有“元”的特性:“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天理之善是“元善”,“元善”之善属于至善,“元善”不是与恶对立的善,而是超越了善恶对立的善。天地万物“无独必有对”,皆是对象性存在。但是,天理是“独”,“独”也就是“元”,“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14](P.1268)如果说“未有不善”还属于正言反说,以否定句形式表述天理至善(元善)的正面含义,那么以下师生之间的问答已跨越伦理学高度,直接从本体论视域讨论天理何以至善:“或曰:‘《大学》在止于至善,敢问何谓至善?’子曰:‘理义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识可也。’”[14](P.1208)《大学》中盼“止于至善”还只是伦理学层面的概念,与生命理想境界相牵连。但是,二程于此所回答的显然已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至善”,而是本体世界层面的“至善”。天理至善不可以概念、范畴界定,也不可以语言表述与界说,只可以“目之”与“默识”。或许这正是东西方形而上学共同面临的一道哲学之“坎”,所以康德会为人类理性划定一范围。人类虽不能认识与证明,但可以信仰。信仰虽不能证明,但可以相信。“目之”与“默识”,既有求诸普遍证明的特点,也蕴含信仰的成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天理至善(元善)也是“命”。“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15](P.274)理是“命”,天理元善也是“命”,这是程朱哲学上接孟子思想的一大命题。此处之“命”,蕴涵两层义旨。 其一,命意味着普遍性、平等性。“人之于性,犹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动之物。”[15](P.67)“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于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圆不移,其光一也。”[15](P.312)天、理、性、命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环环相扣、相互说明。“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19](P.82)分而言之,各各不同,在天为命,理落实于人心为性,已发为情。因此,命强调的是天理“流行”。儒家自孔子“仁者安仁”、孟子“四端之心”肇始,就开启了人性平等之先河。程颐、朱熹起而踵之,从天理高度论证人性源出于天理,因此天地万物和人类皆在性理层面存有共同的性,“‘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15](P.313)自尧舜以至平民百姓,皆本来就具有共同的性理,皆拥有生命的尊严,皆具备内在自我超越的道德生命。 其二,“命”意味着无条件性、绝对性。“天之赋与谓之命,禀之在我谓之性,见于事业谓之理。”[17](P.630)“在天曰命,在人曰性。”[25](P.606)“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19](P.82)程颐、朱熹用性沟通天人,贯通形而上、形而下。在性理意义上,性源自天理,所以又称之为性命。性命观念表明:作为“天之赋与”的性命,在本体层面与天理无二,只是在实践理性领域有本与用的区分。天理与性理恒常自存而遍在,先天地而独立,即使天地山河塌陷,理、性、命仍然“颠扑不破”。理善不与恶对,善是超越性的、独立的、固有的、先在性的“元善”。 程朱道德形上学中预设天理至善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天理至善的无条件存在,“性善”、“仁善”等观念的存在才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天理至善,在整个程朱理学体系中,无疑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拱心石”的作用。程颐关于天理至善(元善)的思想,后来对胡宏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宏闻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独出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请曰:‘何谓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26](P.333)胡宏认为,孟子性善的含义并非指谓“人性善”或“性是善的”,“善”只是一形容词,赞叹“性无限美好”,“善”已不能对“性”作任何限定,也非与“恶”相对之“善”。“或问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则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欤?’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26](P.333)“性”作为天理在人之落实,善不足以概括、描述性之特质,恶更无从表征与形容之。性理层面的性已超越善恶对立,因为善恶只能评判后天的“已发”,发而中节则为善,发而不中节则为恶。但本然之性属于“未发”层面,远远超出了善恶能够评判的畛域。胡宏的善恶“不足以言”性论,通过对孟子人性论的阐发,对程颐天理至善思想有所体悟。 缘此,我们不禁要问:恶有独立的形上来源吗?程明道与程伊川对此观点有歧义。程颐、朱熹的回答是:恶不存在形上学的根据,恶与天理本体无关,恶与性命无涉,恶只与“形化”层面之气有关。“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15](P.274)“寿夭乃是善恶之气所致。仁则善气也,所感者亦善。善气所生,安得不寿?鄙则恶气也,所感者亦恶。恶气所生,安得不夭?”[15](P.224)在程颐思想体系中,因为气有“气化”与“形化”之分,气禀之气已不是张载哲学意义上的“气本”。天理是至善无恶,“形化”之气有善有恶。恶不存在一个超越经验世界的形上根源,天理无需对恶负责。“恶专是气禀,不干性事。”[19](P.2429)恶“不干性事”,自然更“不干”天理事。理与气已经截然相分,“形化”之气需对恶负责,恶源自恶气。纯善无恶之天理与有善有恶之“形化”之气,成为程颐哲学一大主题。 三、“内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庄子与程伊川自由思想的不同追求 庄子的自由学说与程伊川相比较,在内涵、愿景与价值追求上,皆有所不同,现分别加以论述。 (一)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在庄子思想体系中,逍遥自由思想与形上学层面的道论相“挂搭”,从形上学高度证明逍遥自由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在梳理“道”观念基本内涵与特点基础上,庄子进而“以道观之”,道是人类生命理想境界,真人、全人、至人都是“道”之人格化形象,或者说是“道”之隐喻。道不离人,逍遥自由不离人的日常之“在”。逍遥自由的文化根基在于“道”,人性是“道”之“德”。道外在化为真人、神人,内在化为人性之德。“道德”先在性“注定”了人生而自由。逍遥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之实现,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可能生存状态与理想境界。徐复观认为,庄子的自由属于“自作主宰”意义上的“内在自由”。 具体就理想人格而论,庄子思想框架中的理想人格是“真人”、“至人”、“神人”。“真人”、“至人”、“神人”是自由的拟人化。尤其需要点明的是,这些理想人格,究其实质无一不是道之隐喻、道之人格化澄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 庄子自由思想学说中的理想人格有四大特点。 其一,理想人格的名号繁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全人”、“大人”、“圣人”、“德人”、“天人”等概念,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为何《庄子》没有“仙人”、“仙”、“神仙”等名号?甚至在《庄子》内外杂各篇中,根本就没有“仙”这一概念。我们知道,在《楚辞》与《列子》中,存在着大量与《庄子》有关理想人格近似的记载。内容虽然相近,名号却不一样。燕国、齐国和南方楚国是方仙道播扬地区,庄子故里位居中间位置,按说庄子理应对方仙道有所耳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庄子所阐述的理想人格立足于生命哲学的层面,与原始宗教无涉,有意与方仙道划清界限。方仙道后来或许受到了《庄子》哲学的影响,在“真人”观念基础上,建构神仙崇拜学说。犹如东汉道教徒以《老子》思想为蓝本,建构天师道与五斗米道理论体系。 其二,“死生无变于己”。何谓生?何谓死?生死本质以及惧怕死亡衍生的情感变化,是东西方哲学永恒的主题。在庄子思想逻辑中,感性生命的死亡对芸芸众生而言,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生命困境。但是,对真人、神人而言,死亡的困境已不复存在,生与死所带来的情感差异也荡然无存。“死生无变于己”,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读。 首先,在哲学认识论畛域,“以道观之”(《庄子·秋水》)。“以道观之”是对“以人观之”的超越,意味着哲学立场与视域的彻底转变。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气则是宇宙生成论层面的范畴。在道与气关系上,道是逻辑上在先。“以道观之”具体落实在生命哲学领域,就是应在“通天下一气也”(《庄子·知北游》)基础上看待生死本质。生与死是气之聚散方式之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如果人们能从道、气哲学高度认识到死亡犹如幼年流落他乡的游子,晚年回到神往已久的故乡,何尝又不是人生之乐?所以面对妻子的死亡,庄子选择的是“鼓盆而歌”。好友惠施之所以对庄子“鼓盆而歌”不解甚至愤愤不平,就在于惠施与其他普通大众一样对生死本质的认识充满了“惑”(《庄子·齐物论》),对生与死滋生的情感状态也是执迷不悟。臻至理想人格境界的真人“有真知”(《庄子·大宗师》),“真知”意味着“以道观之”,所以“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生带来的欣喜、死带来的悲伤与恐惧,早已在精神层面化解。“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从“外天下”到“外物”,而后到“外生”,最后到“见独”,表面上是工夫论意义上递进递佳的几大层次,其实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哲学认识论层面的跨越。之所以“见独”才能体悟到“无古今”,因为时间只是具体物质存在与运动的属性,道是“独”,道不是对象性存在,道无所谓始终、生死与古今,“度量时间”的特性对于道而言是不存在的。人们如果有朝一日像“朝彻”一样豁然大悟,领悟生与死不过是气化运行的环节与过程,“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知北游》)。在气化的宇宙中,生与死循环往复,不曾停息。明乎此,就能明白“死生存亡之一体”的本质,从而进入“撄宁”的生命理想境界。所以,在庄子思想体系中,对生死困境的认识与超越,主要还是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解决的。 其次,在生命哲学与工夫论畛域,庄子相信芸芸众生皆具有超越生死困境的可能性。在《逍遥游》《齐物论》等多篇文章中反复出现的“真人”、“至人”、“神人”,绝非与尘世众生毫无关系。“真人”并非遥不可及。通过哲学形上学层面的“悟”和工夫论层面的“去欲”、“坐忘”修行,人人有望成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真人,超越生死困境,达到“与造物者为人”(《庄子·大宗师》)之自由境界。但是,庄子所主张的只是精神层面的“超越”,“游心”于方外、“游身”于方内皆有可能实现,但这一切都是限于“游”。“游”是精神层面的“无待”之游。“游”的实现有赖于以德养身与心,“澡雪精神”,身心与德合一,方能臻于“无待”之游。“凡庄子所谓游心,即神游之意。故其乘云气,御飞龙之说,皆喻其心之所之,神之所经,非若后世神仙家言,真能乘云气御龙也。”[27](P.183)王叔珉先生的这一观点切中肯綮,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只是“道”之隐喻,犹如蝴蝶只是“道”的艺术化符号一样。庄子并未主张人在感性生命层面可以长生不死,“长生久视”只是庄子后学和今本《老子》的观点。关于庄子是否主张过人可以在感性生命层面超越生死困境、长生不死,在学术史上一直有争论,而且这一争论从庄子后学就已经展开了。“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大宗师》)在《大宗师》这一段表述中,“登假于道”一句值得仔细玩味,因为类似文句又出现于《德充符》篇:“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登假于道”与“择日而登假”,含义相同,庄子后学言之凿凿地认为,庄子是赞同长生不死的,他们只是在“学着讲”意义上“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在庄子后学看来,如果意识不到“神人”客观存在、长生不死是庄子本义,属于人生之“芒”,是聋子与瞎子。只不过这种“聋者”、“盲者”属于心智上的,而非形体上的缺陷(《庄子·逍遥游》)。吕惠卿赞同庄子后学的观点,认为长生不死是“人心之所同有”[9](P.10),“彼且择日而等假,去而上仙,则其于往来容与如此其至也,则人安得不从之乎!”[9](PP.93-94)释德清进而诠释说:“谓彼人且将择日而登遐,远升仙界,而超出尘凡也。”[6](P.96)宋代与清代学者皆以道教神仙学说解释“登假于道”,这一论证思路及其表述的观点,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成分。在这一问题上,钱穆先生的观点犹如醍醐灌顶:“凡《庄子》书言长生,皆晚起,非诚庄生言。”③与此同时,庄子在明确否定感性生命长生不死的同时,又反复阐明一个非常的观点:德性生命“不死”。“心未尝死”(《庄子·德充符》),人之心是道之精,所以人之精神在本体上与天之精神同出一源。道内在于人心为“德”,德即性。人之德性源自道,所以庄子既有“形骸之内”与“形骸之外”(《庄子·德充符》)的区分,又有“德有所长”与“形有所忘”不同(《庄子·德充符》)。人的形体可以死亡,如同槁木。但人之德性与精神却不会死亡,如同“死灰”一般。人死只是指躯体死亡,人的德性生命作为从道分化出来的精神最终又将回到未分化的道,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大归”(《庄子·知北游》)。“旧国故都,望之畅然。”(《庄子·则阳》)单纯从字面上分析,好像是游子思恋遥远的家乡,实际上比喻人的德性生命的最终归宿是大道。大道“不死”,德性生命由此获得永恒。因为德性生命“复阳”,所以内心“畅然”。 其三,“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人世间的名利权势、富贵爵禄,是天下凡人的奋斗目标,但在理想人格看来,这一切都是“尘垢粃糠”(《庄子·逍遥游》)。尧是历史上的圣明君王,是人之翘楚。以“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而洋洋自得的尧,一旦见到藐姑射之山的真人,“窅然丧其天下焉”(《庄子·逍遥游》)。所有的自得与骄傲,在“无己”、“无功”、“无名”的生命领悟与理想人格形象面前,显得如此的浅陋与猥琐。在《应帝王》篇中,面对“请问为天下”的提问,得道之士无名人直接斥责提问者是“鄙人”。因为对这种充满名利诉求的问题,得道之士首先是嗤之以鼻,其次明确告诉对方:天下本不可“为”!“为天下”既违忤自然本性,也有违于人之天性。犹如太阳已照耀四方,圣明君王还在自以为是“爝火不息”(《庄子·逍遥游》)。在庄子生命哲学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尧舜与真人。为何尧舜所代表的名利权势、富贵爵禄皆是“尘垢粃糠”?庄子的回答很明确:人有“方外”与“方内”之分,“方外”与“方内”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区别,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与价值观上的差距(《庄子·大宗师》)。“游方之内者”醉心于“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庄子·逍遥游》),而“游方之外者”“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庄子·大宗师》)“游”是庄子哲学核心范畴之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游乎万物所终始”。“游”意味着这一世俗世界需要超越,意味着功名富贵都是实现生命理想境界的束缚。尘世众生可以通过游身于世、游心于道,升华到“游乎尘垢之外”。《庄子》文本中超然世外的真人形象,到葛洪《抱朴子》中,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葛洪所描绘的神仙其实已是“活神仙”,对人间之事充满了兴趣:“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28](P.52)因为止家不死,还可以不离妻子,享尽尘世荣华富贵。此外,神仙并非意味着断绝一切尘缘,恰恰相反,“欲求仙者”以仁义为修身之本,救危扶难、“立功为上,除过次之”。[28](P.53)葛洪强调的是在人间“积善事”、“行功德”,与庄子所追求的“以天下为沉浊”(《庄子·天下》),前后已有云泥之别。 其四,“栩栩然蝴蝶也”。无待而游、逍遥自适、追求精神自由,是庄子理想人格最大特点。《逍遥游》与《齐物论》为我们展现了鲲鹏、天籁和庄周梦蝶等三幅逍遥自由图景。三幅图景内容有所不一,但哲学宗旨与生命理想却惊人一致——逍遥自由。何谓“逍遥”?成玄英罗列了学术史上三种阐释:“所言逍遥游者,古今解释不同。今泛举紘纲,略为三释。所言三者:第一,顾桐柏云:‘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第三,穆夜云:‘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29](PP.6-7)三人解释虽然有异,但都指出“游”是庄子逍遥自由思想的本质所在,这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游”是庄子思想架构中非常有特点的概念,“游”在《庄子》一书中出现106次。“游”是摆脱了生死、名利等生命困境之后展现的自在自由生命状态,这种自在自由是生命“自作主宰”(徐复观语)意义上的“内在自由”、“积极自由”,而非外在的“外部自由”、“消极自由”。“游”意味着若即若离,“若即”是指芸芸众生无法完全彻底地脱离这一世俗的物的世界,只能游身于世而无法与世俗的世界彻底决裂;“若离”意味着这个物的世界需要超越,人是目的本身,人的精神完全可以自作主宰,彻底从“浊沉”的世界中超拔出来,游心于道。“遥者,引而远也。”[30](P.81)“逍遥游”本质上在于揭明一种崭新的生命哲学或价值观:消解以人为本位的文化中心主义自我意识,“以道观之”(《庄子·秋水》),尊重并因循自然本性,挺立人的主体性,抗拒工具理性价值观对自然本性的戕害,在有限的生命“此岸”追求精神生命内在超越。逍遥自由的文化根基在于“道”,人性是“道”之“德”。因此逍遥自由是人的正当理由,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可能生存状态与理想境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庄子的逍遥自由思想是否与“命”相抵牾?因为在《大宗师》《德充符》多篇文章中反复提到“命”是人生“大戒”,不仅死生富贵是命,而且贤或不肖也是命。缘此,在学术史上有些学者小心翼翼地论证庄子之“命”与逍遥、德、性之间的关系,竭力弥合庄子思想体系内在可能出现的大裂缝、大漏洞。[4]其实,《齐物论》与《逍遥游》两篇文章中根本就没有出现“命”这一概念!这是一偶然现象吗?绝非如此。因为“命”与以《齐物论》与《逍遥游》为代表的庄子核心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如果承认命,而且“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德充符》),对逍遥自由的论证与向往,在哲学形上学层面将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在实践上丧失行动的可能性。甚至庄子道学思想体系“大厦”,因为“命”的存在与作用而轰然坍塌。在此必须郑重指出:庄子本人否定与反对“命”,《大宗师》《德充符》多篇文章中出现的“命”只是庄子后学的观点。辨明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只有立足于《齐物论》与《逍遥游》来认识庄子思想基本逻辑架构与特点,才能正确认识庄子内心世界。理解了《齐物论》与《逍遥游》两篇文章都不谈“命”,我们才能茅塞顿开地理解庄子为何证明社会地位低微如庖丁,也能在其有限的生命历程中获得体道、悟道的幸福、快乐与自由:“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马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的庖丁已超越了“技”的层面,进入了“得道”、“体道”的逍遥自由生命理想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获得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体道者不是王公贵族,而是卑微如庖丁阶层。庄子于此实际上是想阐释一个哲学观点:逍遥自由是人之本质,人人皆可能逍遥自由。自由具有平等性、普遍性特点,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亦即是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31](P.55)庄子道论虽然富于哲学形上学性格,但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始终与现实人生相联结。逍遥自由具有平等性、普适性特点,犹如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道不离人,逍遥自由不离人的日常之“在”。“得道”、“体道”在本质上已不属于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与实践理性和工夫论有关。由此可见,庄子的逍遥自由哲学蕴含自由意志。康德认为有自由意志的善,才是真正的善。证诸庄子自由哲学,确乎不谬! (二)程伊川:“格君心之非”与理性自由 与庄子“内在自由”相比较,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在内涵、特点与最终追求上,皆有所不一。概而论之,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可高度提炼为理性自由。因为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并未单纯停留于“内圣”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外王”领域。自由不仅是一种思想,更重要的是也是一种主义。自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权利的表达与实现,也是法律、制度与人伦道德等等正当理由的实现。换言之,程伊川的自由已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古典表达。程伊川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大特点与哲学指向在于:为天下立法。“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盖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25](P.452)“为治之大原”或许可以从两大向度解读。 其一,“为治之大原”源出于天理,是天理在人类社会的彰显与落实。扬雄曾经说通晓天道、地道和人道,方可称得上真正的“儒”;只贯通天道和地道,但不通晓人道,充其量只是一个“伎”。程伊川对扬雄的观点予以批评,认为扬雄“不知道”:“岂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焉?如止云通天之文与地之理,虽不能此,何害于儒?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15](P.182)天道、地道与人道打通为一,都是天理的凸显,理一而分殊。正因为如此,“圣王之法”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15](P.174) 其二,“为治之大原”具体以仁为道德依托。仁是人类普遍的道德理性,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伦理道德规范只有依仗仁这一道德理性建立,才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15](PP.73-74)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是人的本性,道德理性使人能制定社会制度与伦理规则,并使人人遵守这些社会法则与规范。人类遵从基于自身道德理性制定的社会法则与伦理规范,就是自由。恰如康德所言:“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32](P.31) 程伊川的自由可概括为道德理性自由,或简称为理性自由。在社会政治、法律与经济领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法者,道之用”。儒家自孔子以降,一直强调法与法令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虽尚德但从不废弃法与刑。德法并重,犹如大鹏之两翼,互为倚重。“自故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16](P.720)法是孟子所说的“规矩”与“方圆”,因此治国第一步在于“立法”,法具备“先”的特点。此外,法还具有“公”之属性。“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25](P.585)程伊川借司马光之言,阐述法具有“公”之特点,“公”意味着普适性与公正性,法不是为君王一人所制定,也不是为维护少数贵族利益而制定,法是为天下人根本利益所制定。由此实际上引申出程伊川进而想表达的一个观点:何为善法?何为恶法?善与恶评判原则与最高标准何在?当年荀子提出“礼法”思想,合乎礼之法就是善法,违逆礼之法就是恶法。善恶炳彰,不可混淆。儒家为天下立法,善与恶的标准由儒家来制定。儒家这一道统,在程伊川思想中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法者,道之用也。”[14](P.1219)道是体,法是用。道是本,法是末。道是“天地人只一道”之道,具体而言,在社会领域就是“孔子治天下之道”,[25](P.513)也就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王道。王道是天理,法是天理精神在人类社会的彰显,“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14](P.1219)法犹如“网之有纲”,纲举目张。合符“孔子治天下之道”就是善法,反之就是恶法。 其二,“格君心之非”。如何制约最高权力,一直是儒家矻矻以求的政治使命。孔孟以“王天下”作为诱饵,从伦理道德角度劝谏君王以三代圣王自任,德治仁政,“君子之德风”,天下百姓归之如流水。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理论出发,以“谴告”威慑君王,以“祥瑞”奖励君王,制约最高权力的理论与手段已有所变化。迨至程子,制约最高权力的思路与孔孟有些近似。“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5](P.165)君心正,朝廷风气正,天下风气正;德政之德指向的是统治者,而非平民百姓。缘此,君心是与非评判标准何在?由谁制定是非对错准则?程伊川的回答是:“讲论道义。”[25](P.447)以儒家道义作为判断是非功过的最高依据,“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25](P.447)是非标帜已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格”?除了法律层面的制约之外,程伊川提出了两点措施:一是“学”,“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无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人,道义之言难进”。[25](P.550)学“道义之言”,才能通晓儒家“大道”;二是立志,以道自任。“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25](P.521)君王“以道自任”之“道”,就是以“圣人之训”为内涵,以“王道”王天下为最终社会政治愿景。 其三,“顺民心为本”。强调“民心”,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孟子尝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儒家道统在董仲舒思想中有新的表述:“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此处之“天”不是人格神,而是民心,是“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思想的赓续。张载认为民心“至公”,“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33](P.256)民心实质上就是天心,天道在民直接彰显为民心。程伊川起而踵之,提出“三本”思想:“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25](P.531)“顺民心”在经济上的体现是“厚民生”,“厚民生”的具体措施是“因民所利而利之”。何为儒家之“利”?张载有一颇具代表性界定:“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34](P.375)“利于民”与“利于国”、“利于身”相对,“利于民”才是真正的“利”。财产权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善恶与否的首要道德标准,“有恒产者有恒心”,所以程伊川在“视民如伤”精神指引下,提出“轻财”、“财散”主张:“颐欲公以爱民为先,力言百姓饥且死,丐朝廷哀怜,因惧将为寇乱可也。不惟告君之体当如是,事势亦宜尔。公方求财以活人,祈之以仁爱,则当轻财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则恃财以自保。古之时得丘民则得天下,财散则人聚。”[25](P.600)二程兄弟在经济政策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双方所据立场不同,观点自然迥然有别。王安石立足于事功权变,千方百计为政府敛财;二程兄弟立足于儒家性命道德之学,力主“爱民为先”,反对“青苗法”等盘剥平民百姓措施。二程兄弟在政治舞台上郁郁不得志,与其说是个性才智原因,不如说是因坚守的思想信仰所导致。哈耶克认为,财产权和法治是自由得以存在与延续的两大社会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二程兄弟的经济思想与政治主张,与其自由主义表达紧密相连。 庄子与程伊川的自由思想代表了古代中国自由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样态:庄子的自由思想可高度概括为“内在自由”、“精神自由”。庄子自由思想的逻辑为:“道”落实于人性为“德”,尽性成德,“道德”的完整澄现就是逍遥自由,逍遥自由才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然权利。具有权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本质,也可以说是人之“命”,人命中注定生而自由。徐复观评价庄子的自由思想是“要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一方面要自己决定自己,同时要自己不与外物相对立,以得到彻底的谐和”。[4](P.238)庄子“对精神自由的祈向”与以赛亚·伯林所言“积极自由”有几分近似之处,因为“积极自由”的基本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1](P.179)因此,徐复观先生高度评价庄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自由主义者”[4](P.252),可谓公允确当。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学说与庄子相比较,在问题意识、运思路向和价值目标上有同有异。相同相通之处在于:皆从价值本体论高度论证自由何以是权利的实现。程伊川从天理“元善”出发,继而论证“性即理”。不同之处在于:程伊川证明仁涵摄其它诸德,仁有“公”之特性。“讲论道义”,仁即儒家的“道义”。仁是人类道德理性,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伦理道德规范只有符合仁这一道德理性与正当理由,才具备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天下立法,是儒家义不容辞的担当与理想。因此,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可高度概括为理性自由。因为程伊川的自由学说并未单纯停留在“内圣”层面,而是积极地扩充到了“外王”领域。对自由作为一种权利的诉求与实现,在程伊川思想中已有展现。因此,程伊川的自由思想既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主义。 四、结语 在词源学意义上,西方自由主义(liberalism)源发于19世纪初西班牙一个政党的名称,但其思想渊源一直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与信仰。与此相对应,自由思想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自成一格,彰显出自由意志以及独创性、普遍性特点。道家与儒家思想中蕴涵着丰厚的自由思想资源,换言之,儒家与道家的最高哲学指向就是自由。在庄子思想体系中,逍遥自由思想与形而上学层面的道论相“挂搭”,从形而上学高度证明逍遥自由是人之自然权利,这是庄子自由哲学最大特点,也是庄子自由思想所达到的哲学最高峰。与此相对,儒家程伊川从天理高度证明“仁”善,人类遵从基于“仁”这一道德理性制定的社会制度、法则与伦理规范,就是自由。为天下立法者不是君王贵族,而是儒家。程伊川思想中的自由,已超越了观念学说视域,扩充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外王”领域。因此,在程伊川思想体系中,自由不仅是一种思想,也并未单纯停留于自然权利畛域。更重要还在于,自由已是超越自然权利的社会诉求与理想社会秩序设计。在这一意义上,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古典表达。 哈耶克尝言:“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35](P.71)自由离不开“传统”的支援。在中华文明史上,此处特定意义上的“传统”可解读为道德理性。缺乏道德理性支撑的自由与自由主义,将会沦落为人类社会一切罪恶中最大的恶。庄子思想中的“道”既是哲学本体,也是一德性本体。“道”决定了人性的本质,“道”是“臧”,道是至善。道落实在人而为“德”,因为道善,所以性善;因为性善,所以人逍遥自由显现德性的光辉。与庄子思想相映成趣的是,程伊川说“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天理之善属于绝对性的“元善”,“元善”意味着无条件性、先在性。“人伦者,天理也。”理善,所以“理之性”善;性善,所以仁善。仁在普遍的人性中是无条件的命令,无条件意味着自由,仁是儒家自由意志视域中的自由。无论是道家庄子,抑或儒家程伊川,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道德理性在自由学说中的重要意义,因此都从哲学形上学高度证明道至善或天理至善,道德理性之善源出于道或天理,自由只不过是道德理性的彰显与发挥。道德理性的善,又捍卫了自由与自由主义,不会沦落为人类之恶。 收稿日期:2016-01-12 注释: ①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1页。这一段话虽是程明道所言,但也代表程伊川思想。二程兄弟哲学思想有同有异,这一段话当是异中之同。 ②对于程子“性即理”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朱熹的评价比较确当:“如‘性即理也’一语,直是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是个公共底物事。”参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六《伊川学案》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650页。 ③钱穆《庄老通辨》中卷之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4页。徐复观先生也说:“此处之神,即是道,即是德,即是性。而其所谓长生,‘乃终其天年’,‘尽其所受于天’,不可与后来神仙家之所谓长生相混淆。”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十二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庄子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道家论文; 伊川论文; 孟子论文; 齐物论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