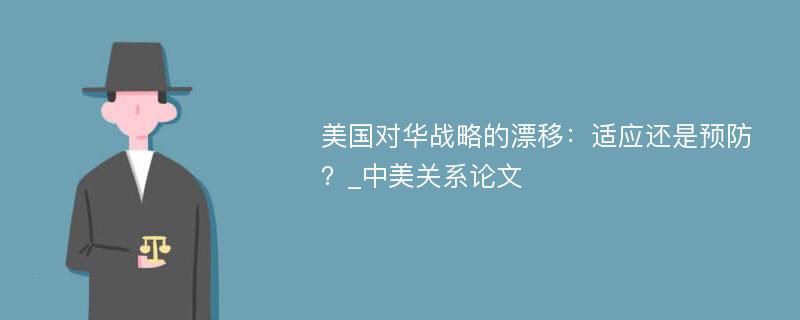
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走过的历程类似于乔治·沃克·布什执政的第一年,不过颠倒了顺序:一个是“高开低走”,一个是“低开高走”。布什竞选期间曾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当选后又发布协防台湾的言论,加之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对台军售,曾经令人极为担忧中美关系的走向。然而,到布什任期结束的时候,他最大的外交遗产之一却是维持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奥巴马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凯歌高奏,令人充满期待。然而,到奥巴马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中美关系的战略互疑增加,①两国国内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也随之上升。中美似乎在过去四年中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本文将简要回顾过去四年来奥巴马政府对华外交、安全战略的变化,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前景。
美国对华战略的“威尔逊时刻”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奥巴马入主白宫到2010年上半年,是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定位中美战略关系、期待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时期;2010年下半年至今,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渐从属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或者“再平衡”战略,重新回归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并且溢于言表。
奥巴马就任总统时,美国的反恐战争已经进行数年,地区防扩散挑战日益严峻,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因此,他执政之初的当务之急是拯救经济,调整反恐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挽回软实力受损的局面,并构建更广泛的“联盟”来应对地区防扩散挑战。在奥巴马的对外政策日程上,中美关系显然是核心内容之一。从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对华政策来看,美国显然致力于“口头上”尝试定位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刻意经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两国关系没有经历磨合期。冷战结束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布什都在就任后经历了中美关系的磨合过程,克林顿总统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布什总统则发表协防台湾的言论和对台售武。奥巴马执政后避免了这一点,特别是避免了发生在南海的“无瑕号”事件的升级发酵。
第二,虽然希拉里·克林顿主政国务院,但美国决策部门中的中国问题团队阵容强大,多由中国问题专家组成。这体现了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通常情况下,负责中国政策的三位关键人物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政策资深主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奥巴马执政初期,担任这三个职务的分别是贝德、坎贝尔和格里格森。②贝德外交履历丰富,且多与中国事务相关,曾数次任职台湾、香港和北京,担任过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坎贝尔曾经担任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也曾任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亚洲问题上,坎贝尔倾向于重视美日关系而非中美关系,但他的上司、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存在限制了他的作为空间,因为斯坦伯格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谙熟外交事务。③格里格森亦曾深度接触亚太安全事务,曾在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亚太事务主任,并出任过中央情报局长的军事事务执行助理。另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此人是摩门教徒,曾经在台湾传道,也曾在美国政府从事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至于内阁成员,任职商务部的骆家辉和任职能源部的朱棣文都是美籍华人。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政策团队,而且其成员在中美关系上拥有基本共识。
第三,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避免采取刺激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策略。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后,将首次出访活动安排在亚洲,彰显了美国对亚洲国家的重视。希拉里·克林顿向来在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上直言不讳。1995年来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她曾大肆批评中国人权;美国大选期间,她也多次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呼吁布什总统不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然而此次访问期间,她降低了身段。她在谈到人权问题时表示,美国仍然会在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她不希望这些施压影响到中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和安全危机。④在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即宣布了大宗对台军售计划,但希拉里·克林顿出访亚洲期间则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发生转变。⑤这意味着美国将延续布什第二任期内与中国达成的共识,反对台独势力挑战现状。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避免在访华之前会见达赖,并努力说服达赖接受这个安排。⑥
第四,中美建立了新的沟通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布什执政时期,中美建立了战略对话(Senior Dialogue)和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期间首次会晤,宣布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机制。该机制取代了此前的两个对话,旨在为两国高层官员提供有效渠道,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与两国利益相关的双边、地区及全球的机遇和挑战。从对话的层级、议题和两国政府赋予对话的重要性来看,中美均对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寄予厚望。克林顿国务卿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联合撰文,称“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单凭一己之力予以解决,也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实力、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⑦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式上,克林顿国务卿盛赞对话是有史以来中美高层官员最大规模的聚会,“覆盖的议题范围无与伦比”,“为面向21世纪的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奠定了基础”。⑧这个对话机制也催生了有关“两国集团”和“中美共治”的期待。
第五,美国尝试摸索中美“战略稳定”和“战略再保证”。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这也成为中美关系维持稳定的基本理念。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演讲时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表示美国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其内涵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而中国则应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其发展和全球作用的扩大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⑨这个构想提出之后,美国国内的反应比较复杂,其中颇多批评声音。⑩有批评意见认为该构想含混不清,似乎在“绥靖”中国。据称这个构想的提出更多地基于斯坦伯格个人的思路,并不代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共识。这与佐立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区别明显。(11)因此,斯坦伯格发表演讲之后,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并没有讨论与此构想相关的问题,之后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也未提及。
虽然“战略再保证”的构想没能走多远,但随后美国官方文献中出现的“战略稳定”概念应该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定位中美关系的重要尝试。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相继发布了若干政策评估报告,特别是《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对本届政府而言,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与维持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稳定一样重要”,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展开“实质性的、持续的对话”,以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并减少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12)《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再度援引了《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措辞,称美国将致力于维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稳定。(13)“战略稳定”的概念在两个报告中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多数美国官员和学者倾向于模糊地解释“战略稳定”的内涵,即:既包括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也包括中美在特定的战略力量领域的稳定。也有美国学者称,因为这个概念出现在一份有关核态势的报告中,其内涵就相当于认可中国对美核威慑的有效性。(14)无论美国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战略稳定”是“现在时”还是“将来式”(致力于构建战略稳定),两份文件都表明美国在尝试重新定位中美关系。
第六,奥巴马总统访华并发表联合声明。克林顿国务卿首次出访选择亚洲(包括中国),奥巴马总统也在上任后第一年访问中国,这都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十分重视。2009年11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中美两国对未来的预期落实为文字。声明以积极的基调评价了中美关系,涵盖了中美关系中的所有议题,并将双边合作延伸到地区和全球挑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议题。从如下措辞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各自的期许:“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极端重要。”“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15)
总的来看,奥巴马总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尝试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发展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将中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七届美国政府”,“积极的一面是对中国的定位很高,消极的一面是美国将会把很多责任推卸给中国,给中国笑脸,但让中国买单”。(16)奥巴马总统在对华政策上所展示的一系列“新政”姿态,恰好回应了他在总统竞选中打出的口号——“变革”。其实,奥巴马执政初期的外交新政不仅体现在对华政策上,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他在就职演说中向所有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发出呼吁:“只要你们愿意松开攥紧的拳头,我们将伸出手。”(17)他在开罗发表了题为《新的开端》的演讲,以重塑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在布拉格呼吁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在莫斯科呼吁“重启”美俄关系。凡此种种,莫不是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方面的“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18)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曾撰文指出,“奥巴马外交的核心点是:美国突然不一样了。美国变了,变好了。因此,到了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的时候了。”(19)美国的利益没有改变,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姿态和调门变了。于是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
回归现实主义政策:两面下注
奥巴马采取的威尔逊式的对华政策包含了对中国诸多不现实的期待。这种期待并非寻求利益互换或达成共识,弥合分歧,而是要求中国在多个方面照顾美国的利益关切,具体表现为: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用意,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中国加强防扩散领域合作的目的,是期待中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的议程保持同步,向朝鲜和伊朗施压;推进两军关系持续、可靠地发展,旨在通过航天、外空、核与网络空间领域的对话缓解美国的关切,增进中国单方面的“透明度”;妥善处理军事安全和海上安全问题,是为了保障美国军舰在中国经济专属区的行动不受阻碍,美国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抵近侦察不受影响;一方面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希望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要求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希望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不受影响;希望降低预算赤字,鼓励私人储蓄,但继续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承认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表示反对保护主义,但只希望中国市场对美国开放,拒绝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和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希望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做出努力,但自己仍然原地踏步。
美国罗列了长长的愿望清单,但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因为它无视或刻意淡化中国在诸多议题上的国家利益和轻重缓急。不仅如此,中美双边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但并没有消除,良好的双边关系气氛只是由于双方集中关注多边议题而造成的假象。因此,在随后的半年内,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国际问题上对中国“深感失望”。
中美关系从高歌猛进向麻烦迭出的转变,始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合作空间,但分歧同样巨大。中国在多边场合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与77国集团和“基础四国”中的其他三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站在一起。中美激战哥本哈根,美国媒体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表现得“强硬”、“傲慢”,哥本哈根气候峰会遂成为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随后发生的与中美两国密切相关的事态导致两国关系的气氛急速改变。2010年1月,克林顿国务卿在谷歌问题上发表有关互联网自由的讲话,(20)批评中国;美国推迟作出对台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但仍宣布了价值60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21)2月,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3月,美国指责中国对天安舰事件的处理态度消极,担当了所谓朝鲜“恶行”的“保护伞”,(22)随后美韩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更导致中美分歧的加剧;5月,美国在联合国推动对伊朗的严厉制裁,认为中国从中阻挠,迫使美国不得不弱化制裁的内容;(23)2010年上半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屡次对中国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
中美之间的上述紧张态势引发了双方的关注,中美均意识到了稳定关系的重要性,曾尝试修补双边关系,包括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于2010年3月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于同年4月参加美国倡导的核安全峰会并会晤奥巴马总统,中美首脑在多伦多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等,但中美关系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调整迹象。
2010年7月23日,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后会见记者,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强调在南海实行“航行自由”、维护“国际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敦促中国与相关各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24)如果说奥巴马执政初期的亚洲政策以中美关系为中心的话,现在美国正对其亚洲政策做出明显的调整。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调整的核心内容:一是以传统的五个条约盟友为核心;二是与本地区的新兴力量建立联系,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三是建设多边机制。斯坦伯格称,这是探讨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的基本背景。(25)自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重回现实主义,“两面下注”的战略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奥巴马政府最初的中国问题团队的多名政府官员相继离任。2011年3月30日,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斯坦伯格副国务卿宣布离任,(26)中东、南亚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伯恩斯取而代之。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宣布离任,取代他的是日本和韩国问题专家拉塞尔。4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原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移任驻华大使;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格里格森也离任,取代他的是利伯特。同期,格里格森的主要助手、精通中国问题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米德伟也离开五角大楼,被任命为缅甸特使。(27)自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协调,而多尼隆并不熟悉中国问题。坎贝尔和拉塞尔成为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声音,二人都更为强调美国亚洲政策中美日、美韩同盟的重要性,而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主管官员的变化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受到许多不熟悉中国问题或不重视中美关系的官员的影响,而这势必显著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28)
美国在降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同时,着力加强同中国周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29)在政治上,美国高调宣示其“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和定位,频繁派出政府高官访问亚太各国。截至2012年5月,克林顿国务卿已经访问过96个国家,共计有320天在访问途中,飞行里程高达77.8万英里,(30)其中对亚太国家的访问占了很大的比例。奥巴马总统也曾数次访问亚洲,国防部长盖茨则访问亚洲10余次。这些访问凸显了亚太国家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亚洲多边机制——无论是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还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美国官员访问了以前从不造访的蒙古和太平洋岛国等,还积极改善同缅甸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致力于强化与传统条约盟国的关系,努力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关系,积极创设或加强新的多边协调机制,包括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和其他三边关系,尝试“建造一个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结构”。(31)美国并非简单地参与到这些地区安排中来,而是要主导这些地区结构,直言不讳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经济领域,美国强调亚太地区是增加国内就业、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关键,为此推动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批准,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并着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
在军事领域,美国积极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军事关系,努力构建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准军事关系。这些措施并非都是显著的“增量”,也借助于一些言论和行动,如美国同多个国家进行的“2+2”会谈(外长加国防部长)、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倡导的联合军事演习等,都让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存量”更加引人注目。美国激活亚太军事存在“存量”的思路在其官方文献中体现得非常清楚。报告《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11:重新界定美国的军事领导》提出,重新定义美国的军事领袖作用,让美军扮演四种角色:协调者(facilitator),即协调美国政府各机构和其他机构,以促进国家利益;赋能者(enabler),即协助增强其他国家的能力,以促进共同利益;召集者(convener),即协调和加强与各国的军事关系,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保证者(guarantor),即如果必要,美国将单独或者协同盟友和伙伴共同威慑并击败侵略行为。(32)概言之,美国要扮演领军角色,在不增加美国军事存量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其他国家或者协调盟友关系来增加美国军事的总量。此即美国军事领导地位的内涵。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防务要务》基本沿袭了同样的思路,这也是美国军事战略东移的公开宣言。(33)两份关键的军事战略文件均强调“领导”(leadership)地位并非巧合,这恰恰是美国军事战略东移的主旨。在具体的战略执行层面,美国强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增进两军的协调;美韩军事关系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之后也得以加强;美日韩三边防务协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美菲军事关系的改善也显而易见,这不仅包括美国向菲律宾出售军事装备,还体现在美国海军在退出苏比克湾近30年后,再度以轮换部署的方式重返苏比克湾。美澳军事关系显著加强,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将在澳大利亚部署2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并逐步将这个数量增加到2500名。(34)美国还计划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并增加美国与新加坡军队的协同训练。美军自身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加强也比较明显,特别是美国着力经营关岛军事基地,未来关岛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枢纽、海空军基地。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2012年6月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宣布,未来将有60%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争议问题上,美国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国的争议方,诸如在黄岩岛问题上有限度地支持菲律宾,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支持日本。如果美国的军事计划如期实现,那么其未来的军事中心明显转向亚太。(35)
克林顿国务卿于2011年11月在东西方中心发表讲话,暗示美国“必须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将与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内”。(36)这种政策框架的目的在于敦促中国“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遵守一套从知识产权到基本自由等各个方面的行路规则”;当中国“不承担影响力扩大带来的责任时”,美国将“尽力鼓励”中国“改变路线”。(37)美国的新亚太政策淡化了中美关系,其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对中国形成约束和牵制。这几乎可以称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规制主义”,(38)即通过双边对话敦促中国军事透明,解决双边分歧;在地区或全球领域内敦促中国遵守美国认可的规则。而如果中国遵守美国认可的规则,中国的作为空间必将受到限制。
适应与防范: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
奥巴马执政两年后,美国国内开始讨论奥巴马政府是否有一个大战略。多篇评论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认为奥巴马政府缺少战略或者战略家,称所谓的“奥巴马主义”就是“没有主义”(No Doctrine)。(39)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有大战略,而且是两个:一是多边收缩(multilateral retrenchment)战略,包括减少美国的海外承诺、恢复美国的形象、将美国的负担转嫁给全球伙伴;二是重拳反击(counterpunching)战略,即在全球防止其影响和理念受到挑战,安抚盟友,向竞争对手展示对抗意志。(40)
奥巴马政府是否有一套对外大战略姑且不论,过去四年来中美关系经历的波折起伏和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足以说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形成于三个基本背景之下。其一,美国经历了多年的反恐战争,软硬实力受损,金融危机更导致美国经济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不仅需要削减财政赤字,还需要振兴经济。其二,国际力量转移,新兴经济体崛起。奥巴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并且“面临局势转变的时刻”;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影响中心,包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美国“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论这个国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独自迎接全球挑战”;(41)“国际秩序中相对权力的持续转移和日益增强的联系意味着一个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的出现”,日益变化的权力分配预示着世界正朝向一个“多节点”(Multi-nodal)的方向发展。这个世界不再表现为对立集团间僵化的安全竞争,而是基于外交、军事和经济权力而达成的受利益驱动的联盟。(42)美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力量转移的态势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和战略指南中均对此有所强调。(43)其三,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的崛起是近几年国际社会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指标分别是:美欧相继受到金融危机重创,而中国基本独善其身,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幅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认为全球和亚太地区不断演变的战略图景中最具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的崛起将继续重塑国际体系。(44)
塑造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三个基本背景均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也是奥巴马执政初期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之一。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不可能单独应对包括全球变暖、国际经济复苏、地区安全挑战在内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诸多挑战,中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在国际力量的转移过程中,中国显然也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最主要力量之一,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互动模式将随之产生变化。中国迅速崛起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中美双边领域的互动也将产生变化。在奥巴马执政的四年中,这三个基本背景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动,而美国对华外交和安全战略却经历了重大调整,从最初探索中美战略稳定转变为对华采取“两面下注”战略。
美国“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首先,美国很难平衡“适应”和“防范”之间的关系。由于逐渐淡出反恐战争,美国开始进入一个缺少主要“敌人”的时期,而美国当前面临经济复苏缓慢和削减赤字的压力,国内利益集团仍然存在较强的寻找敌人的冲动。最近几年,美国部分政治力量大肆宣扬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45)和中国在外交方面的“过分自信”,炒作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言论面对的是美国国内的公众。其目的是降低削减财政赤字对美国军队的影响。近来美国提出的“海空一体战”很难说是为了其他目的、针对中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友敌”(Frienemy)定位,很可能最终将中国塑造成潜在的“竞争者”、“对手”,而不是可以合作的“朋友”。
其次,美国在对中国进行防范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合作,亦很难实现。中国对于美国经济复苏、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需要进行合作是美国政府内部达成的基本共识。当然,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所言,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即使出现分歧也不致破裂,并能够继续合作”。(46)但“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动态的管理”。(47)中国当然也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并实现中美合作,但面对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姿态和“防范”政策,中国难以达到美国所期待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再次,“两面下注”只会增大中美双方的“互疑”,而无助于增进互信。从过去两三年来中美两国学界和媒体的评论来看,中美“互疑”呈上升态势,(48)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引发了中国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深度疑虑。中美双方都关注对方的战略意图,但各自作出的解释和保证却未必能被对方所接纳。例如,美国一方面在实质上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将重返亚太解释成主要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让中国无法理解。美国担忧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尽管中国在高层互访和官方文献中明确表示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美国仍然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够透明。
又次,美国对华“两面下注”还制造了亚洲各国的混乱。中国崛起必然对周边国家产生各种影响,由于其中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历史问题或领土争议,这些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中国形成一种力量平衡,但它们绝不期待中美形成对抗态势,因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最符合它们的利益。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两国中间选边站队。
最后,美国对华“两面下注”将导致未来的危机管理难度增大,而这些潜在的危机并非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很有可能也存在于第三国,包括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争议问题上立场模糊,一方面表示在主权问题上不采取立场,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甚至宣称争议海疆属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条约覆盖范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骑墙姿态从地区紧张局势中“渔利”,这不仅会增加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还可能导致周边国家误用美国的“有限承诺”,并且有可能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争议转化为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始终存在“遏制”与“接触”的论争和摇摆,与之对应的“中国威胁论”也起起落落。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美国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略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而19世纪欧洲的均势战略同样不适用,(49)“遏制”显然是一个过时的战略。同样,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接触”战略也不能管理中美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战略既非“遏制”,亦非“接触”,而是“两面下注”。这种战略并没有解决“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而是部分地“适应”中国的崛起,以争取中国在美国关注的议题上提供支持;同时部分地“防范”中国的崛起,以避免或约束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简言之,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友敌”。(50)这种战略更像是权宜之计,口头上宣称适应中国的崛起,但行动上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而这显然无法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对华战略似乎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
中美战略不稳定的前景?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其政策的延续性将大于变化,不少官员甚至对当前的对华战略自鸣得意,认为重拳反击(counterpunching)战略不仅有利于改善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而且能够有效地防范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空间的挤压和主导地位的挑战。然而,美国这种部分“适应”中国崛起、部分“防范”中国挑战的战略不仅包含如前所述的诸般内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已经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正在动摇。虽然中美高层互动频密,官方交流渠道畅通,虽然美国一再重申重返亚太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但两国学界研究和媒体评论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上升。对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美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视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包括经贸和意识形态等挑战。膨胀的“中国威胁论”不仅唱和了美国战略重返亚太的大背景,而且突出了中美利益冲突的一面,“防范”有可能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调。同样,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动作,更多中国学者认为随着美国淡出反恐战争,缺少敌人的美国正致力于遏阻中国崛起,而非致力于促进中美战略稳定。
中美在亚太地区面临危机的几率上升。奥巴马政府新亚太政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安抚盟友,消除其对华“焦虑”和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另一方面约束盟友的外交和军事行为,防止在涉及与中国利益冲突的领域走得太远,“误用”或者“放大”美国的“有限承诺”,伤害美国利益。美国既希望其盟友保持与中国关系的适度紧张,又要竭力避免局势失控,这似乎是“鱼”与“熊掌”得兼的艰难任务。美国与其盟友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叠,在某些对华政策上其利益甚至显著冲突。美国能否有效地平衡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能否实现对盟友的精细管理与约束?未来的形势发展未必乐观,因为此种形势下,驱动中美关系变化或者调整的未必是美国或者中国,而可能是与美国利益部分重叠、与中国利益根本冲突的中国周边国家。在中菲黄岩岛领土争议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受了挑战,并比较幸运地防止了局势失控,未来在中日钓鱼岛争议问题上,美国是否还能有效约束日本而不是给日本提供错误信号,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结论。未来同样的麻烦还有可能出现在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
中美在双边议题上也潜含危机。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展,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发和试验,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和空中抵近侦察有增无减,中国持续的反对和抗议并没有促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引起了中国的激烈反对。另外,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中国将逐步走出“近海”,中美两国海军在海上“不期而遇”的几率亦相应增加,而双方对于如何管理两国海军的互动并无共识。过去十余年间,中美已经遭遇EP-3南海撞机、“无瑕号”事件,所幸两次危机均在中美良性合作的大背景下得以合理解决,未来此种危机再次出现的可能并没有减少,反而可能增加。不仅如此,奥巴马总统刚进入第二任期,已经有美国议员高调宣布要推动对台大宗军售,这将挑动中美之间最敏感的议题。随着中美各自国民心态的变化,以及中美相对实力的消长,美国既往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的政策在将来未必还行得通。美国在中国人权、民主、网络、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居高临下姿态同样更容易引发中国更激烈的反应。
双边关系可能潜含诸多直接和间接危机,而未来的危机管理难度已经显著增加。导致危机管理难度增加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一是双方国民心态的显著变化,这不仅包括美国日益增强的对华“防御”心态,还包括中国渐增的对美“自信”。虽然审慎和妥协是国际政治的美德,但国民心态的显著变化将使得中美决策层腾挪空间受限。其二,互联网让影响决策的民意获得了新的释放渠道,并有能力放大其政策影响。互联网的普及理论上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获取即时信息的渠道,微博等社交媒体则为表达诉求、传递情绪的意愿“插上了翅膀”,而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则是“网民”热议且具有相当政治正确性的话题。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中国,网络培育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外交决策因素,而它让危机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
当然,在看到中美未来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还应意识到两国同样面临着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重大机遇。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节点,中美已经具备了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两国意识形态对抗的可能性极小;容易诱发中美对抗的台湾问题也因为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而大为改观;中美之间建立的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也有助于缓解两国面临的各种分歧。中美建交30多年来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此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对手好。”(51)美国也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没有几个外交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52)
建立中美战略稳定需要美国做出重大努力。如前所述,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漂流导致诸多内在矛盾和风险,如不善加管理和调整,中美滑向非蓄意对抗的风险并非没有可能。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经提出的“战略再保证”、官方政策报告提出的“维持战略稳定”等概念未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调,也许现在是美国认真思考如何构建或者重建中美战略稳定的时候了。2012年11月中旬,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中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努力”,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53)事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实际行动的支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以往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只要求中国照顾其利益关切,而不试图照顾中国利益关切的互动模式可能已经成为历史。美国需要在诸多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关切的领域让渡空间,妥善解决双方的利益诉求,包括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应该在战略军事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即两国的军备竞赛和潜在的军事对抗只会造成双输的结果。冷战时期,美苏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才真正意识到维持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当前中美之间的互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中美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一场危机来证实战略稳定的重要性。当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和疑虑非短期内能够解决,战略互信非短期内能够达成,但这不应该妨碍两国拓展在政治上不太敏感而中美利益重叠较多领域的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航道安全、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等,通过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来增进了解,累积互信,培育共识。惟其如此,“稳定而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才可期待。
注释:
①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
②贝德、坎贝尔和格里格森的履历分别见:http://www.brookings.edu/experts/baderj? view=bio; http://www.state.gov/r/pa/ei/biog/125594.htm; http://www.cna.org/about/staff/wallace-gregson。
③斯坦伯格的履历请见:http://www.maxwell.syr.edu/deans.aspx? id=77309418030。
④Hillary Rodham Clinton,"Working toward Change in Perceptions of U.S.Engagement around the World",February 20,2009,Seoul,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9430.htm.
⑤"Clinton:Chinese Human Rights Can't Interfere with Other Crises",http://www.cnn.com/2009/POLITICS/02/21/clinton.china.asia.
⑥John Pomfret,"Obama's Meeting with the Dalai Lama Is Delayed",Washington Post,October 5,2009.
⑦Hillary Rodham Clinton,Timothy Geithner,"A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7,2009.
⑧Hillary Rodham Clinton,"Closing Remarks for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Washington,DC,July 28,2009,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599.htm.
⑨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
⑩Kelly Currie,"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Reassurance'",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2,2009; Daniel Blumenthal,"Not so Reassuring...",http://www.defensestudies.org/cds/steinberg-in-china-not-so-reassuring/.相关分析亦见[美]白永辉:《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保证”》,《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第108—109页。
(11)Josh Rogin,"The End of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reassurance'?" 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11/06/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strategic_reassurance.
(12)Department of Defense,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10,pp.34—35.
(13)Department of Defense,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April 2010,pp.28—29.
(14)笔者曾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就此问题访谈美国官员和学者。
(15)《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目。
(16)吴荻、金灿荣:《金灿荣点评前后“对话”之不同》,《世界知识》,2009年第16期,第22—23页。
(17)"President 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2009,http://www.whitehouse.gov/blog/inaugural-address.
(18)John Milton Cooper,Jr.,"Obama's Wilsonian Moment",December 8,2009,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09/12/09/obamas-wilsonian-moment.html.
(19)Robert Kagan,"Barack Obama as Woodrow Wilson's Foreign Policy Heir",Washington Post,June 7,2009.
(20)Hillary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Washington,DC,January 21,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21)Helene Cooper."U.S.Approval of Taiwan Arms Sales Angers China",New York Times,January 30,2010.
(22)"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G-20 Press Conference in Toronto,Canada",June 27,2010,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obama-g-20-press-conference-toronto-canada.
(23)David Sanger,Mark Landler,"Major Powers Have Deal on Sanctions for Iran",New York Times,May 19,2010; David Crawford,Richard Boudreaux,Joe Lauria,and Jay Solomon,"U.S.Softens Sanctions Plan against Ir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5,2010.
(24)Hillary Clinton,"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Hanoi,Vietnam,July 23,2010.
(25)斯坦伯格讲话的题目为“美国对中美伙伴关系的期望”(America's Vision for a China Partnership)。James B.Steinberg,"Remarks at Nixon Center",Washington,DC,July 27,2010.
(26)斯坦伯格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参见:Josh Rogin,"Steinberg Leaving State,Burns Moves up",March 30,2011,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3/30/steinberg_leaving_state_burns_moves_up。
(27)Josh Rogin,"It's Official:Mitchell Named Burma Envoy,Bader Leaving White House",April 14,2011,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4/14/it_s_official_mitchell_named_burma_envoy.
(28)Mark Landler,"Shake-up Could Affect Tone of U.S.Policy on China",New York Times,April 9,201l1.
(29)详细内容参见樊吉社:《美国“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载于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美国全球及亚洲战略调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本文部分分析参考该文。
(30)Susan B.Glasser,"Head of State",Foreign Policy,July/August 2012,p.84.
(31)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September 8,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17.htm.
(32)Joint Chiefs of Staff,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February 2011,p.1.
(33)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nse,January 2012.
(34)"Up to 2500 Marines Could Be Based in Australia",http://www.marinecorpstimes.com/news/2011/11/ap-up-to-2500-marines-could-be-based-in-australia-111611/.
(35)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指的亚太与太平洋司令部覆盖的区域是一样的,而耐人寻味的是,国防部长帕内塔为“战略指南”撰写的前言以及他在国会的作证中,他所提到的美国战略重点是亚太和中东,而不仅仅是亚太地区。见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 2011: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Defense Budget Request-Written Submitted Statement to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February 14,2012。
(36)Hillary Rodham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Honolulu,Hawaii,November 10,2011.
(37)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September 8,2010.
(38)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将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概括为三个基础:一是承认并尊重中国的崛起及其合法利益,二是坚持中国的崛起应该合乎国际规范和国际法,三是加强同盟与伙伴关系,确保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是稳定的。杰弗里·贝德:《当前中美关系不处于紧张阶段》,《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66期,2012年4月24日,第2页。
(39)Jackson Diehl,"Obama's Foreign Policy Needs an Update",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1,2010; Michael Hirsh,"Obama:The No-Doctrine President",National Journal,March 29,2011.
(40)Daniel W.Drezner,"Does Obama Have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11,Vol.90,Issue 4.
(41)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1.
(42)Joint Chiefs of Staff,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February 2011,pp.1—2.
(43)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nse,January 2012,p.1.
(44)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10,pp.7,60.
(45)Stephen M.Walt,"Inflating the China Threat",August 27,2012,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8/27/inflating_the_china_threat.
(46)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September 8,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17.htm.
(47)Hillary Rodham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Honolulu,Hawaii,November 10,2011.
(48)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
(49)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
(50)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期间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三场辩论中将中国称为“对手”(Adversary)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并不讳言美国“pivot to Asia”。参见“Transcript of the Third Presidential Debate”,http://www.nytimes.com/2012/10/22/us/politics/transcript-of-the-third-presidential-debate-in-boca-raton-fla.html? pagewanted=all。
(51)“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2010年3月14日,http://www.mfa.gov.cn/chn/gxh/tyb/zyxw/t663856.htm。
(52)"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lon",November 15,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15/remarks-national-security-adviser-tom-donilon-prepared-delivery.
(53)Ibid.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奥巴马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奥巴马访华论文; 中美关系正常化论文; 美国国务卿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经济学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