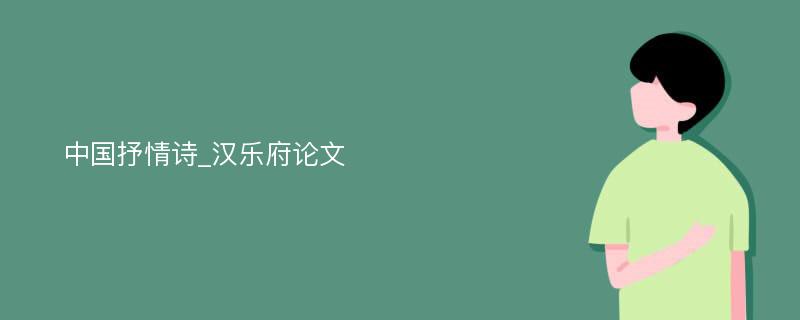
中国的歌词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歌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传统诗词,与音乐联系密切,无论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体式上的变化和诗体名称上的差异,但从古至今,把它作为乐曲中的一部分歌词,却是很少改变的。
中国最早的一部歌词诗集是《诗经》,也就是被称为“不学诗无以言”的三百篇,这是周朝政府从民间收集到的三千多首歌词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乐歌以供专门乐舞机构使用。为显示周王朝的尊严,起着“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作用。这些被后人尊为“经”的歌词诗在当时都能配上音乐曲调而演奏,只因时代的变更,可供宫庭演唱的音乐大都散失,三百篇乃脱离歌词的性质而独立成为徒诗,它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歌词诗。
这一部歌词诗集,经过孔夫子到宋代朱熹对其的推崇及不断的雅化和曲解,掩盖了作为民歌的淳朴原貌,按照当时礼乐制度的需要而包装成为宣扬等级制度及王道尊严的“圣诗”,而作为中国最早的歌词集的《诗经》,反而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淡漠了。
《诗经》之后的另一伟大诗集为《楚辞》,诗的特征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事,名楚物”,可见是楚人结合了楚地的语音语言之特点化而为楚辞的,说明楚地有着特殊的地方方言语词语法及音调。加上受到楚国音乐和巫风的影响,使楚辞有着浓厚的巫术色彩。《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佞巫鬼,重淫祀。”由重巫术而兴起的巫风和地方音乐,形成了“巫音”,《吕氏春秋·知音》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这种巫风巫音对《楚辞》自然有很深的影响,造成《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重要篇章,都带有浓厚的巫歌色彩,配以楚地特有的巫术音乐,像《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它们可能即是提供巫人演唱的歌词。其中另一些篇章如《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其特色很有“乱”、“少歌”、“倡”等乐曲含意,出现于被庄严化的《诗经》歌词诗之后,成为独立的体式即“骚”体,屈原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留下姓名的歌词诗作者。
然而,在中国诗史上,占领歌词诗这一领域时间最长、阵地最广者,当属乐府诗。正是由于历代封建王朝需要乐府来炫耀其威严与尊崇,并在封建典章制度的要求下,以音乐和诗歌相辉映的乐府诗,遂应运而生了。
乐府诗肇始于秦,大兴于汉,其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宋元直至衰落。但无论乐府诗如何变易,但其配乐演唱的歌词性质,则一直不变地延续了很长时间。正如郑樵《通志·乐乐第一》所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凡律其词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可知早期乐府诗,无不是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词,它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由于乐府要配上歌词,遂使歌词借历代乐府机构而流传下来。
秦设乐府,只是开创时代。汉承秦代之制,设立了太乐、乐府二署。汉武帝时,乐府形成规模,大量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填写歌词,编配乐器以进行演唱。汉武帝对乐府制度进行了大量改革,兼采文人之诗来作歌辞。据《汉书·礼乐志》载:“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于此可见汉武帝时的乐府征集歌词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大致是,从民间采录来的叫“歌诗”,从贵族文人那里采录来的叫“歌”,音乐的歌谱则名之为“声曲折”,歌谱与歌诗双双对应,如“河南周歌诗”七十五篇,则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十五篇,这里所说的“歌诗”就是“歌辞”,“声曲折”为歌谱,而曲折则表示音乐之旋律音拍。这里有个界分,即乐府所能采纳收用的歌诗是有限的,后来就把曾被乐府机构采录过的称为“乐府”,未曾配乐使用过的则称为徒诗。
汉乐府中有用之于祭祀的《郊祀歌》,有融合少数民族音乐的“鼓吹曲”、“横吹曲”等。在乐府风气的影响下,汉代文人桓谭、马融、蔡邕等也很喜欢音律,有的文人把民歌改造加工后作为歌曲演唱。汉代乐府歌曲的名称繁多,如《相和引》、《相和曲》、《四弦曲》、《五调曲》等,其中《五调曲》可能是由于五调性质相近,作为轮番演唱的不同调式之转换。著名歌词诗像《饮马长城窟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流传最为普遍,也成为被喜爱的乐府歌词流传开来。
在诗经产生数百年后,汉代重又采集民歌,以丰富乐府的歌词演唱。歌词诗被冷落了一个时期之后,重又振兴起来。
曹操父子继承、学习汉代民歌的抒情特性,转向了抒情乐府的创作,从曹操的《薤露行》、曹植的《白马篇》看,已具有了“慷慨多气”的建安诗歌的特征。由魏向晋过渡的乐府歌词家当以傅玄、张华为代表。从被广泛传诵的《秋胡行》,可以看出傅玄歌诗是受汉魏乐府影响的。
西晋张华的乐府诗,《诗品》评之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而从其为宫廷乐舞机关所作的《晋中宫所歌》、《轻薄篇》等可以看出,他之歌辞受到赋的侧重铺陈的影响,显得绮丽而繁缛,缺乏歌词所需要的形象感受,因而《诗品》说他的歌词“其体华艳,兴托不寄”。陶渊明的乐府诗作受当时玄学风气的影响,流露出自然化的倾向,艺术成就不如他的徒诗。
在南朝,采自江南民歌的歌曲叫“吴声”,梁武帝曾设有吴声、西曲女乐部。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民歌兴盛,采之以为歌辞是很自然的事。著名的《子夜歌》就是歌唱男女爱情的歌词,其中有很多男女赠答的对歌,如:
男唱:落日出前门,暗瞻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女答: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
这有点像现代少数民族所谓的“花儿”。
鲍照是刘宋时乐府歌诗的重要作者,他既能继承汉魏古曲,又能采用民间新曲,为唐代的杜甫所称赞。随着宋齐时代音律的兴起,不仅文赋中重视音律,当时的歌词也注重奇偶音组的相配,宫商之音的协调。这时,沈约倡导的诗歌声律说,从音韵上丰富着新体乐府,而沈约本人就长于乐府诗。他写的《明君词》即刻意于对仗、音律之运用,《青青河畔草》虽用古题,经过换韵与和谐的音调安排,感到音节完美,出现了另一种新歌诗的气象,影响到齐梁时代的新体乐府不断涌现。
北齐乐府流传最广的为《敕勒歌》和《木兰诗》,慷慨豪迈、粗犷雄壮。
借乐府而存在并发展的歌词,到了唐代,可谓到了最鼎盛的时期。秦王李世民,征伐刘武周获胜,士兵与百姓合作了《秦王破阵曲》,李世民即位后,就把这支曲子带回宫廷演奏。文治武功兼备的李世民,革除南北朝乐府的浮艳华丽之词,力求声律、风骨兼备。那时的歌词,多为三、四、五、六言的古体诗雅音,但其格调当属新体。初唐四杰的乐府歌诗,既注意采摘民歌之精华,又注意骈偶、谐律之运用,从而开拓、发展了歌诗之体制,为盛唐歌诗的兴盛开创了新的格局。
唐明皇是个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的君王,曾设立太乐署和鼓吹署,又设梨园两处、教坊五所,人数多至几万人。由于盛唐采取选词配乐的办法,使得唐代大诗人如李白、杜甫、李益、李贺等的诗作得到了更好的传播。盛唐时用律诗、绝句配乐作为歌辞,已经相当普遍,所以盛唐诗人之作品,在当时既是诗的,也是歌词的,只要觉得适合,他们的作品即可被采之入乐。
盛唐流传最广的两首歌词诗是刘希夷的《白头吟》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两首歌词诗,既有和谐的音律,又形成了新的乐府格调。李白的《清平调》三章,是唐玄宗因原有歌词陈旧,命李白创新作以进,再命梨园配曲、李龟年演唱的新歌。李白的乐府诗,“即事命题,无复依傍”,为以后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打开了局面。杜甫的乐府诗创作也是感时事而另创新题,不依古人之成声,比李白更进了一步,如他的《兵车行》虽用“行”字,为古乐府的一种体裁,但属自创的新题。
元、白的新乐府,来自于杜甫的新题乐府。新乐府着重表现民间疾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白居易的新乐府歌诗志在关心民瘼,针砭时弊,提出诗歌应为民为事而咏。其新乐府的命题,实际是采自流传于民间的曲调。白居易新乐府的代表作有《卖炭翁》与《新丰折臂翁》。而元稹的所谓新题,更多的是已在宫廷演唱的乐曲题。元稹乐府有的是唱和李绅的,可见李绅也是同属重视政治现实的歌词家。这样,“乐府新题”的首创者应该是李绅。晚唐至五代时,宫廷乐府的歌词已呈颓势,宋代宫廷音乐,只保留下唐代部分乐府。
总括唐代的乐府来源,首先是改造利用少数民族的乐曲和歌词,有的则是用古乐调制腔填词或自创新曲新歌词来完成,如此才造成了唐代乐曲歌词无限丰富和多样的宏伟局面。
宋词由乐府演化而来,也是可以入乐歌唱的,不仅受少数民族乐歌的影响,也受六朝杂言乐府的影响,如梁武帝的《江南弄》、侯夫人的《看梅曲》等,已有从诗的齐言体到词的杂言体的发展痕迹。两宋词的创作,更适应于应歌合舞之需要。经五代至宋长期的发展变化,使词成为两宋的合乐歌词。
根据《宋史》记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使宫廷、教坊燕乐新声的创作十分兴盛。欧阳修在诗文创作中保持着庄严气象,而其歌词创作就相当开放,如他的《浪淘沙》词:“好妓好歌喉,不醉不休。”他与晏殊所作的小歌词,承袭着“民间词”的格调而被认为是词之正宗。与“花间”词相对应的,有苏轼、辛弃疾的“壮词”。苏轼填词很讲究字声,长于配合乐曲之音律,其歌词一旦入乐便合于歌法,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能入律可歌,且唱法十分讲究。同为“壮词”的辛弃疾,在声律上虽不及姜夔严密,但注重音乐效果,岳珂曾说:“稼轩以词名,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桯史》)
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是“倚声填词”,这就要求填词要合于声律,所以北宋著名的词家如柳永、周邦彦多妙解音律。柳永为举子时就喜欢与教坊乐工合作,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陈师道《后山诗话》称:“柳三变(永)作新乐府,天下咏之。”但他所作的歌词,更多的是为酒楼妓馆的歌妓所传唱,达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普及程度。
周邦彦是又一能歌词且工音乐者,曾为音乐机关的太乐正,提举大晟府,《藏一话腴》赞扬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即是周邦彦词广为传唱的证明。他所填制的词,严于平仄,而又妙解节拍,音节清妍和雅;所创声调很多,有人讥他创调之才多而创意之才少。
南宋词家精于音律、制曲、填词的当推姜白石,他是少数能够自制乐谱并由伶工按拍演唱的歌词家。姜白石留传下来有十七首注工尺旁谱的词。他的倚声,有截取唐代法曲、大曲的,有从当时乐工曲子中译取的,也有用琴曲改为词曲的。他还特别喜欢“自度曲”,方法是:“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也就是说,自己随便写下一个歌词,然后再配上乐曲。后人学习周邦彦的常常是字字依填四声,以致歌词写好后文理欠通,而白石自创为新调,就没有这样的缺点,因此,他在制曲填词后,马上可以交给乐工歌妓演奏歌唱,而有的作者的词作却只是供别人阅读而不能被之管弦的徒诗。
到了金、元、明、清,虽也有演唱近体诗的记载,但不再有重大的革新与创意,能够领时代之风骚的,是南曲与北曲,及吴越间的民间歌唱,文人士大夫反而唱不出这些歌词的曲调了。
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白话文和白话诗,同时也就出现了白话歌词。独立的新诗是有的,但无论是新月派诗还是散文诗,都没有像歌词诗的流传那样普遍,不少白话诗,发表过后也就被人淡忘了,于是就有人提倡作旧体诗,但旧体诗的格律严谨,束缚人的手脚,于是又有诗人提出宽限韵律和恢复入声字,但也没有被普遍地接受。我们不难从中国诗歌史上得到这样一些经验:一、中国的诗、骚、律绝、词无不是从采风及吸收民歌中得来后,再加上文人的加工参与;二、中国诗词的大部分,是通过音乐配歌词的方式而后广为流传的;三、中国的诗歌体式无论经过多大的转折和变迁,而其在作为歌词这一点上,却具有着时代的穿透力,就像前面提过的《诗经》三百篇,就是周代宫廷的雅乐,逐渐离乐而独立,由歌词转变为徒诗,再由徒诗变为《诗经》的。
由这一经验的总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轻视当代歌词之创作,如具有革命铿锵之音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解放前的抒情歌曲《渔光曲》,现在广泛传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施光南创作的《打起手鼓唱起歌》,以及西部歌王王洛宾收集编写的新疆歌曲,它们既是现时代最优美的歌词,也是当代的歌词诗或徒诗。而在我们的观念未曾转换之前,容易把目光放在格律的探讨上,而感到当代诗作的贫乏。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收集整理现代歌词诗,我们就不会感到当代诗作的贫乏,而是感到其中有无限的生命创造力。因为它们既是来源于民间的,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又是与音乐结合后而流传方便的体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其中的精华部分选出而当作现代的徒诗呢?这样,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没有被广泛传诵的诗之困感了。至于由此而发展的新诗体,是会自然形成的。我相信,经由时代催生的诗体、时代创造的格律,必将会在大量美声、民歌、流行歌曲中涌现。在大量歌词诗中,产生出既不是新诗,也不是旧体诗词这样一种新诗体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寻求,将会比重新研讨、编辑诗韵、诗律,更有益于当代新体诗的诞生。
标签:汉乐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