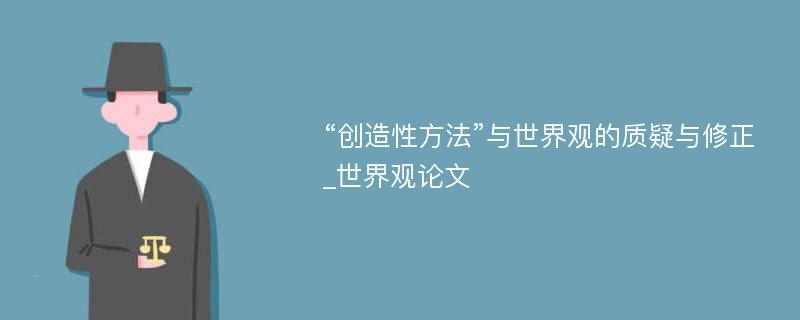
“创作方法”与世界观问题质疑与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观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作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吗?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等术语,在19世纪的艺术批评中早就有了。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把它们叫做“创作方法”,而是把它们看作思潮、倾向、流派或创作原则。本世纪20年代,苏联的拉普派首先提出“拥护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口号。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是基于对艺术现象的认识论理解。人们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与之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拉普派看来,艺术既然是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形式,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那么,只消一步推理,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艺术的创作方法”的结论来,所以他们提出了“拥护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口号。
后来,拉普派在苏联受到了批判,他们提出的这一口号也同时受到了批判。批判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的创作方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于是,在30年代初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批判拉普派的“拥护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口号时,本来应当发现艺术并不仅仅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或者说主要不是一种认识形式。如果仅仅是一种认识形式的话,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理所当然地也适合于艺术这一特殊的认识世界的形式,“拥护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提法也就没有什么错误了。然而实际上,艺术并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所以,直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作为艺术的创作方法,才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实践中,总是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拥护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这一错误口号的被废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苏联人在废止“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之后,仍然长期坚持艺术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的观点。这表明他们对于废止“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这一口号的艺术哲学根据还是模糊不清的。这当然也难以责怪他们。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价值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那时的苏联人只知道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还不知道人与周围世界存在着价值关系。把艺术仅仅当作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形式,带有当时那个历史时代的痕迹,我们无法苛求于前人,应取宽容的态度。
我国的文艺理论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极深。50年代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艺理论课程的讲稿《文艺学引论》(后由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这样界定“艺术方法”的:“对待艺术和文学上的认识和再现现实现象的方法叫做艺术方法。”这段文字翻译得疙疙瘩瘩,不过意思还是可以弄懂的。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说得就更清楚了:“文学的创作过程既是对生活的认识并表现的过程,就它对生活的认识来说,也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前面说过,文学的创作过程就是作家艺术认识并表现社会生活的过程,文学的创作方法也就是艺术认识并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220页、第238页)。这里解释艺术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都是从认识论着眼的。仔细推究起来,存在很多问题。
艺术家之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还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无疑都是要认识社会生活的。认识社会生活也都要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这些方面,即在认识社会生活上,他们并没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规则、途径、过程。如果有的话,那么艺术理论家们早就会写出诸如《现实主义艺术认识论》、《浪漫主义艺术认识论》或《象征主义艺术认识论》之类的大部头著作了。至今还没有人写出这样的著作,说明在认识社会生活上可有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分,而不会因为所采取的创作原则不同便各有一套不同的认识论。如果说我们以上的分析和推理没有什么漏洞的话——我看不出有什么漏洞——那么我们便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创作原则归创作原则,认识论归认识论,这是两股道上的车,不应当混淆不清。之所以造成上面所引几段文字中出现的那种混淆,就是因为对艺术的本质发生了错误的理解,把艺术当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单纯的认识形式。既然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秉持者并无各自不同的一套认识论,那么,就不应当把认识论的哲学内容概论到“创作方法”中去。也就是说,文艺创作的方法不应当包括哲学认识的方法,艺术毕竟不同于哲学,这是显而易见的。
创作原则是艺术家在从事艺术创作时所依从的一些基本原则。在苏联人把“方法”与“文学、艺术”关联起来以前,西方艺术理论文献中所使用的便是“艺术创作原则”的概念。有人说,1850年法国画家库尔贝首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标明当时文艺创作的新倾向,杜朗等人创办的《现实主义》刊物(1856—1857)首次刊载了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宣言:如实地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参阅杨成寅主编:《美学范畴概论》,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20页)。但据波兰美学史家符·塔达基维奇的考证,“现实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21年的一篇题为《十九世纪的墨丘利》的文章中,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荣誉的不断增长,表现在文学的原则上便是忠实地摹仿现实所提供的原型。”这一原则“可以称作现实主义”(符·塔达基维奇著《西方美学概念史》,学苑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83页)。“现实主义”这一名称一出现,就被叫做“原则”,而不是叫做“方法”。“创作方法”的概念自1928年在苏联出现以来,沿用既久,在我国也已成了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今后大约还会继续沿用下去。名相与实义的关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去掉苏联人当初创立这一术语时的不科学的认识论内容,这一术语继续使用下去自然也无甚不可;不过应当看到,用这一术语指创作原则,容易产生误解。其一,容易使人仅仅理解为艺术创作的纯技术手法,这是“方法”二字与“创作”联系起来之后的字面意义引起的。我们读书时初接触到“创作方法”这一术语就产生过误解,后来在大学教书,每次讲到“创作方法”都要反复向学生交代不要仅仅理解为创作手法。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学生把它仅仅理解为写作手法。而实际上它的意思固然包含艺术表现的某些手法特征,但主要不是指表现手法,更不是技法,音乐、美术中的许多基本技法是各个流派共同使用的;而是指艺术创作所遵循的某些原则。若改称“创作原则”,就不会造成这些误解。其二,由“哲学方法”类推出“艺术方法”,使它们并列对称,而多年来我们所理解的“哲学方法”实际上又是认识方法,因为几十年来我们从苏联引进的哲学学科体系是大认识论的学科体系,并无价值论的位置。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艺术并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而是人们对于益、善、美或害、恶、丑诸种正的或负的价值事物与价值理想的感情体验的升华与结晶(参阅拙著《艺术价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6—241页),那么,使用“艺术方法”或“创作方法”这样的术语来指谓创作原则的内容,又往往与“艺术认识”这样的概念相联系,必然带上哲学认识论的色彩,因此,不如把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方法”或“创作方法”的内容,恢复到拉普派之前的通常叫法,仍叫做“艺术原则”或“创作原则”。这样也许更科学、更符合它的本义,而且不易引起误解。若再考虑到与国际艺术科学接轨,学术交流需要名词术语的统一,也是以把现在我们所概括的“创作方法”的内容改称“创作原则”为好。当然,“创作方法”一语仍可使用,不过,不应当再让它涵括“创作原则”的核心内容,而让它只指艺术创作时所使用的手法。这样它的内容和名相也就相符了,不会再造成误解,也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被译成多种语文,几十年来屡次再版的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是这样使用“创作方法”一语的:“我们可以说惠特曼诗歌创作方法的特点之一是一种分析式的展开法,……他首先逐项摆出他的项目,然后大量地解析它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3页)这里的“创作方法”完全是指写作手法,与我们几十年来所说的“创作方法”大不一样。这才是“创作方法”一语的本义。由于拉普派的误导所造成的一个大弯子,今天应当转过来。提出这点意见供学界参考。
浪漫主义艺术家是倾向于描写理想的生活,塑造理想的人物,往往采取幻想的非人间形式表现人间的内容,喜欢采用历史题材、神话传说,善于采取夸张的手法、充满激情的笔调,等等。现实主义艺术则多半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描写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的典型。席勒虽然没有使用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术语,但在其《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对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已作过生动的描述和理论的概括,此后许多理论家都指出过它们的区别。这显然是两种有重大不同特点的创作原则。但是,却不能说这是两种对立的认识生活的方法。理论家们经常引用乔治·桑对巴尔扎克说的两句话:“你既有能力而且也愿意去描绘人类如你所眼见的。好的,反之,我,总觉得有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的来描绘它。”(参阅勃兰兑斯:《法国作家评传》,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年版,第2页)人们总是以这两句话作为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原则的最简洁、最准确的概括。那么,现在让我们对这两句话进行分析,看是不是巴尔扎克和乔治·桑操着对现实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方法。十分明显,乔治·桑在这里说的是她同巴尔扎克在“描绘”什么和怎样“描绘”上所遵循的原则不同,而不是说她和巴尔扎克在“认识”世界的原则、方法上有什么分歧。“描绘”是艺术创作上的术语,“认识”是哲学认识论上的术语。“描绘”什么和怎样“描绘”属于创作原则,怎样“认识”世界则属于哲学认识论上的方法。尽管每一位艺术家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要认识世界的,而认识世界也总是遵循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原则或方法的,例如唯物论或唯心论,辩证法或形而上学;但是,这并不直接就是“创作方法”。把它作为创作原则或创作原则的一部分内容,必然导致混淆艺术创作和哲学认识的界限。乔治·桑所说的“我,总觉得有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的来描绘它”,这里面“我希望于人类的”、“我相信人类所应当的”,都是她关于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身的价值理想,而不是她认识生活的一种方法,她用这种通过艺术描绘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理想,来提高人类关于自然生活和自身品质的价值观念,激发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望和追求自身完善的感情,并使这种感情成为行为的动力。这不是说乔治·桑对人类社会生活没有认识,也不是说她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对于她的创作实践没有影响,不是这个意思。应当说乔治·桑和巴尔扎克一样,对于法国的社会生活都是有认识的,因为她的理想都是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缺乏认识,也就不可能产生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的理想。我们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认识论的方法和创作原则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认识论方法并不直接就是创作原则或创作原则的一个部分。唯其如此,认识论原则或方法作为世界观的高层次内容,才能指导、影响艺术家选择何种创作原则,并影响他的创作活动。如果论识论原则或方法就是艺术创作的原则本身,或者是艺术创作原则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它怎么能指导、影响创作原则的选择?那不变成它自己指导、影响它自己了吗?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说得通呢?
毕达可夫所说的“对待艺术和文学上的认识和再现现实现象的方法叫做艺术方法”,即使不说它译文上的语句不通,从内容实质上看也是完全没说到点子上的,经不住分析和推敲。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把“认识方法”归入创作原则,作为创作原则的一部分内容是不对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他所说的“再现现实现象的方法”,能否作为创作原则的普遍定义呢?事实上也是不行的。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再现现实生活,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原则的中心内容,对于浪漫主义或其他一些创作原则来说,“再现现实现象”的说法就未必适合了,在陶渊明所生活的封建社会里,本来到处是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但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却描绘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黄发垂髫,并怡在自乐”的美好世界。这能叫做“再现现实现象”吗?这作品所体现的创作原则能说是“再现现实现象的方法”吗?显然不能。但是你又没有理由说它不是文学作品。它是公认的传世文学作品中的名篇。你也没有理由说它未体现任何种类的创作原则。它显然属于那种按照作者所“希望于人类的”、“相信人类所应当的”样子来描绘生活的作品之列,体现着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作为艺术创作原则的普遍性定义,应当适合于各种不同的创作原则。毕达可夫的“艺术方法”定义就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把一种创作原则的某些信条说成是一切创作原则的规范,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的理论既然没有普遍适用性,当然也就不会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毕达可夫等人之所以这样界定“创作方法”,完全是由于他们对艺术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是他们把艺术仅仅当作人们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形式的荒谬艺术观念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观”涵义探究
数十年来,在我国和前苏联文艺理论界,没有比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产生过更大的分歧意见和引起过更多的争论的了。然而,这个问题虽然讨论了数十年,始终还是没有讨论清楚,没有在理论上给以真正的解决,最后竟成了文艺上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那种认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有时存在着某种矛盾、“创作方法”有时可以突破落后世界观的局限而使作家写出具有真实性的好作品的观点,被认为可以导向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的结论而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观点的帽子,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于是不了了之了。
实在说来,在当流行的那个理论框架内,这个问题也的确无法解决,因为当时在人们的头脑中“世界观”一直是一个模糊概念。连“什么是世界观”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会搞清楚它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呢?对于文坛上的这一老公案给以新的审视,不是没有意义的。
“世界观”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世界观”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宇宙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它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即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历史是发展的还是循环的?如此等等。第二个方面是价值论方面的内容,它回答“世界应如何”的问题,即世界万物对人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益的、善的、美的?什么是害的、恶的、丑的?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秩序?人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如此等等。
狄尔泰在其所著《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各种世界观都包含着同样的结构,即以概念语言来把握本体,同时又暗中赋予其意义和价值,含蓄地表达制约于生命的某种道德愿望。从狄尔泰对“世界观”的概括,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世界观”一词所包含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俗称“老《辞海》”)对“世界观”一词的界说,十分清楚地区分了广狭二义:“[世界观]对于此世界所怀抱之意见也。与人生观相对举,有时亦兼括宇宙观及人生观而言。在哲学上派别甚繁,解释亦至不一律:认识论方面有实在论、观念论、唯象论、不可知论;本体论方面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平行论、目的论、机械论;价值论方面有乐观说、厌世说、改善说等。”这里所说的“与人生观相对”的“世界观”,即“宇宙观”则“兼括宇宙观及人生观”,即兼含上面我们所说的第一、第二两个方面的内容。
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在这种体系中,没有价值论的位置,认为价值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一讲到世界观,价值论主面的内容也就被排除掉了,只剩下本体论和认识论,“世界观”与“宇宙观”成了同义词,人生观不再讲了(近几年有所改变),只讲“世界观的改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或“宇宙观”。
1980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俗称“新《辞海》”)是这样解释“世界观”的;“世界观亦称‘宇宙观’。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处地位不同,特别是阶级地位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各种世界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先进阶级和进步势力的世界观,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反动阶级和保守势力的世界观,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方法。”几十年来国内编著出版的各种《哲学辞典》、《自然辩证法辞典》以及翻译出版的前苏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等,对“世界观”一词的注释都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式。对“世界观”的这一注释有显著的缺点:第一,它没有区分“世界观”一词的广、狭二义,把狭义的或者说价值哲学产生以前人们对“世界观”的偏狭理解,当作了“世界观”的完满定义,排除了包括人生观在内的价值论方面的内容;第二,就狭义的“世界观”(“宇宙观”)而言,它只讲到了不同阶级的人们的阶级地位对形成不同世界观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发展程度对形成人们的世界观的巨大作用。在原始时代,并没有阶级,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手段粗陋,因此普遍迷信鬼神,对世界万物给以神秘主义的解释,宇宙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宇宙观的并不是只有阶级地位这一因素,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意义。
尽管在理论上从世界观中排除了价值论内涵,但几十年来在我国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却以其他的名义处处强调了实质上是属于价值论内容的方面。例如当讲到世界观的转变时,总是强调立场、感情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们知道,“立场”在价值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具有相对性,益害、善恶、美丑诸种正负价值,并不是像物体的大小、形状、运动速度那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坐标内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同样一个物体,决不会在张三眼里大而方,运动不止,在李四眼里小而圆,静止不动。价值就不同了。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作为价值主体与价值物的关系不同,同一事物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对张三有益的事物,有可能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李四有害。同样,善恶、美丑也有这种情况。由于价值物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价值,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事物就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评价。立场的转变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就是作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移位,从作为价值主体的此一社会集团的立场上,移到作为对立价值主体的彼一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人们的感情总是与价值和价值理想相对应的,感情要么为某种正的或负的价值(包括价值的象征物、摹拟物在内)所引起,要么为追求某种价值理想而产生。价值主体移位之后,价值关系变了,当然感情也就变了。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原来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土地改革对于他所属的作为价值主体的社会集团有害,因而他认为土地改革“糟得很”,给以否定性的评价,并在感情上深恶而痛绝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参加了革命,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转到贫苦农民一方来了,也就是完成了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移位,他便会对土地改革作出肯定性评价,认为土地改革“好得很”了。“好得很”既是评价,又是感情态度。对于这种立场和感情的变化,通常说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当然“世界观”作为观点、概念、观念的体系是属于理性世界的,它不直接包含感情世界。但是它与感情世界有联系,因为世界观中的价值观、人生观无不与人们的感情相联系,价值观与人生观常常是在对社会人生中的诸种正的或负的价值事物的长期的感情体验中升华为理性观念体系的。理性的价值观念又反转过来影响人们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价值观与人生观作为观念体系,与人们的感情呈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这与从前苏联来的关于“世界观”的定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它既不关系于宇宙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联系不上物质和精神究竟何者是第一性的。这反映了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实践的脱节,反映了不讲价值论只讲认识论的哲学学科体系的严重缺陷。这一缺陷在对“世界观”的定义中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使“世界观”的涵义残缺不全,丧失了它一半的内容。
宗教界人士信上帝,信神佛。依照前苏联和我国流行的关于“世界观”的定义,宗教界人士在宇宙本体论上和人们的认识论上,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又被认为是反动的世界观,所以在“文革”时期宗教界人士成了打倒的对象。然而全面的“世界观”涵义除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之外,应当包括价值论的内容。“反动”不“反动”是政治概念,政治处理的是社会利益问题,利益是价值范畴。宗教界人士世界观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这也是他们的世界观的一部分。祖国和人民对于我们来讲有最高的价值。从价值取向上看,就不能说这些爱祖国、爱人民的宗教界人士是“反动”的了,而是和广大人民一致的,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应当讲团结。由此可见,理论上的片面性会导致政策上和行动上的偏差,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终究会纠正理论上的片面性的。
当我们一般地讲“世界观”时,应当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诸方面的内容。由于多年来流行的“世界观”定义缺少价值论方面的内容,造成了很多理论混乱。应当在学理上加以探究,使指导实践的理论更加精确有序。
以上,我们对所谓“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分别进行了质疑和辨正,这样,二者的关系就好研究了。以前在这方面出现过很多简单化的毛病。世界观本身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它怎样影响创作原则和创作实践,需要进行系统的层次分析。限于篇幅,只好另文论述了。
标签:世界观论文; 认识论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艺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辞海论文; 宇宙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