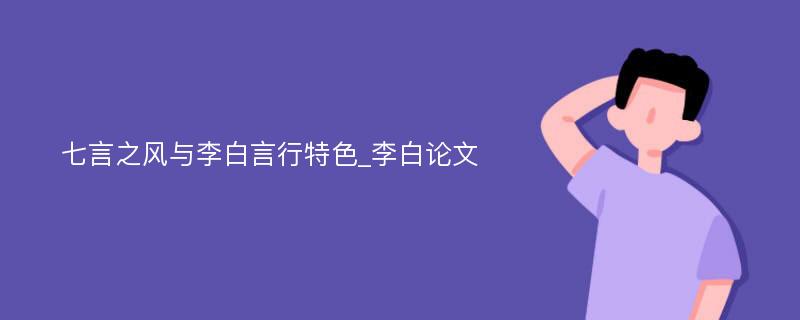
七言歌行的体式与李白歌行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行论文,体式论文,李白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5-0133-06
关于李白歌行的特征,学者们的论述有不少精辟见解,但总的来说,在全面性和准确性上都有些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对歌行这个概念认识模糊,将它界定过窄,认定为齐梁后具有乐府体调特征的七言古诗而不包括乐府及别的诗体。依照这样的界定,李白集中乐府卷60多首七言乐府不属于歌行,属于歌行的只有歌吟卷中那30余首七言古诗。以这样的范围、这样少的作品来分析李白歌行的特征,自然会造成差误。
句式、韵式、修辞手法(指字法、句法、章法)是构成歌行体裁的三个基本要素,加上后出的声律,歌行的体裁特征即体现在这些要素上。这些体裁要素在歌行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形态,它们的结合形式也多种多样,形成了多种体式。李白的歌行吸收了之前各种歌行体式的特征,接受了各种体式的深刻影响,研究其特征应特别重视与以往各种体式的比较对照,通过比较对照看其如何在吸收、接受中形成有别于前人及时人的体式特征。
一、七言歌行的五种体式
从七言歌行发展史考察,唐代之前的歌行体式可以确定为古七言体、骚体、乐府杂言体、齐梁体、赋体等五种。
(一)古七言体。这里所说古七言体是指齐梁前七言诗的体式,它在句式、韵式上的总体特征是:通篇七言,句句入韵。这样的七言诗汉代即已产生,除诗外,镜铭和别的七言韵语采用的也是这样的句式、韵式。
古七言体分转韵、不转韵两类。不转韵一类以汉武帝时《柏梁诗》篇幅较长、出现较早,后人即以其为句句入韵、一韵到底七言诗体体式的代称。柏梁体还有两个附带特征,一是押平声韵,二是有奇数句,汉魏时柏梁体皆具这两个特征,晋宋后有所改变。转韵一类出现也较早,转韵句子多少不等,有两句、三句、四句及四句以上的。两句、三句转韵又称短韵或促句转韵,这样的转韵以二句较多见,东汉张衡《思玄赋系辞》全篇12句,二句一转,以后一些乐府题诗如《乌栖曲》、《东飞伯劳西飞燕》皆通篇如此。三句转韵最奇特,较少见,东汉王逸《琴思楚歌》(见《古诗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未收)是较早的一篇,全篇15句,三句一转,略早于王逸的崔骃有一首三句一韵七言诗被《太平御览》采辑,可能是三句一转的古七言体的残篇。在各种转韵形式中以一篇混用多种转韵句数的较常见,如宋鲍照《代白纻曲二首》之二,全诗7句,三次转韵,其句数分别是二、二、三,《代鸣雁行》全篇6句,两次转韵,其句数是四、二。转韵的古七言体与柏梁体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有学者称其为柏梁变体。[1]
齐梁前七言齐言诗基本形式就是柏梁体、柏梁变体,上述七言乐府是这样,民间歌谣如晋《陇上为陈安歌》、《军中为汲桑谣》亦是,连佛教七言偈颂、道教七言歌曲也是如此。这种句式、韵式用于咏唱、吟诵几百年,是歌行体的早期体式之一,对后来歌行的创作有长久的影响。齐梁后纯粹这样体式的并不多,但部分采用如王力所称“部分的柏梁体”[2] 或部分的柏梁变体则较多见。古七言体由于句句入韵显得音韵比较谐和,又由于多用平声,声调也显得较为悠扬,但用韵过密,又一律七言句,易给人单调之感,语言也显得比较质实,作为早期歌行的一种体式,艺术表现是不太完善的,但后人为了调节诗句的韵律、节奏,追求风格的古拗、劲峭,还时常采用、模仿这样的句式、韵式。
(二)骚体。骚体是汉代以后仿效楚地民歌和楚辞而产生的。骚体的基本句式为七言,也是较早出现的古代七言诗的一种体式,汉代以后这样体式的作品产生很多,其数量远多于古七言体,既有数句的短歌,也有较长的篇章。汉代许多帝王都有骚体诗,汉武帝名下就有7首,《瓠子歌》二首共22句,以后蔡琰骚体《悲愤诗》38句,晋嵇康《思亲诗》30句,都是比较长的作品。
骚体在句式上显著的特征是句中或句末常有一“兮”字,兮字是语助词,常用来表示停顿和感叹,有调节句子节奏、增强情感表达的特别作用。句中的兮字还能充当介词、连词、结构助词,有相当于“以”、“于”、“而”、“之”的作用,往往能与前面二字组合成三字节拍,从而改变七言诗惯常的二二三音顿,使七言诗的节奏更为丰富。有些骚体诗和骚体辞赋句上不用“兮”字而用“以”、“于”、“而”、“之”,可以看作与“兮”字同样的句式特征。骚体句子长短组合比较灵活,多于七言、少于七言的都有,往往有长句出现,尤其是中间带“兮”字的句子,“兮”字上下能连带缀加较多的字,分开则为两短句,合之则为一长句。骚体的韵式齐梁前与古七言体大致相同,差不多是句句入韵,转韵的方式亦同古七言体,汉武帝《瓠子歌》两句一转,嵇康《思亲诗》三句一转,张衡《四愁诗》混用二、三、四句转。齐梁后骚体的韵式渐与齐梁体趋同。晋宋后骚体中还出现了含有较多杂言成分的类似辞赋的作品,如宋谢庄《怀园引》等三首、齐江淹《杂三言五首》、梁沈约《八咏诗》,都是长达三四十句的组诗,这些作品也可以称为辞赋体。
骚体在句式上较古七言体灵活多样,节奏明快,修辞手法如重叠、蝉联、铺排也多见使用,词采也较华茂,艺术表现力显然胜过古七言体。它还能与时更新,一直到唐代还有一定的适应性、生命力,不仅以这样体式的作品汇入唐代歌行作品之林,还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其它体式歌行乃至其它诗体的创作。
(三)乐府杂言体。乐府杂言体乃区别于齐言乐府而言。相对于齐七言乐府,杂言出现最早,作品数量最多,而又独具特征,故以一体名之。汉魏乐府中杂有七言句的作品不少,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等类中多见。《乐府诗集》杂歌谣辞还收有一些汉魏以来民间歌谣,乐府杂言体其实也就是民间歌谣体。
早期乐府杂言体七言句所占比例较少,至鲍照多数杂言皆以七言为主。鲍照前杂言的句式较杂,从一言到九言、十言都有,还有散文句式,鲍照作品七言外主要是三言、五言与七言搭配,多见三三七、五五七、五七七、五五七七这样的组合,在节奏上既具有民谣风味,又有规律性。在韵式上早期的杂言一般是隔句押韵,有多句七言相连时也句句入韵,类似古七言体。鲍照的乐府杂言无论七言及七言外句子,绝大多数是隔句押韵且转韵。杂言体语句一般都显得比较活泼、流畅,重叠、蝉联、句子的复沓较为常见,鲍照还经常使用排比、对偶,在篇首、句首他还创造性地使用“君不见”这样的呼告语,18首《行路难》“君不见”出现了10次,这是十分引人注意的创造,齐梁后出现的《行路难》多有这样的呼告语,并且扩展至其它题目,这就为用于抒情、议论的杂言歌行提供了一个十分富于情感力度的表达方式。鲍照是先唐今存乐府杂言创作量最大的作家,共22首,特别是其中15首杂言《行路难》,在许多方面为以后乐府杂言体七言歌行创作提供了范式。乐府杂言体对唐代特别是盛唐以后七言歌行的发展影响巨大。
(四)齐梁体。齐梁体指齐梁后出现的七言诗新体式,相对于七言古体来说是隔句押韵并有规律地转韵,同时自觉地引入了声律要素,注意调配一句和两句间声调的平仄。王运熙说:“齐代永明声律论兴起后,七言诗也跟着重视声律,出现了七言的齐梁体。”[3] 王力称此七言体为“入律的古风”或“新式古风”,并界定说:“典型的新式古风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平仄多数入律;(二)四句一换韵;(三)平仄递用。”[2] 说这是“典型的”,自然那些大致具备这些条件的也属于齐梁体,特别是在齐梁之初。齐梁间这种体式最先见于七言乐府,以后扩及其它七言诗。比如《燕歌行》,齐梁之前皆为古七言体,自齐梁之间萧子显后则一律演变为齐梁体,梁元帝萧绎的《燕歌行》比较典型,基本上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越到后来,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作品越多,陈代徐伯阳、傅縡、徐陵、江总都有全篇基本入律、四句一转、平仄递用的作品。当然非典型的齐梁体作品还是不少,显见的是换韵的句数有二、六、八句,但超过八句的长韵很少。
齐梁体除王力概括的三个特征外,还有一些特征:1.在韵式上除隔句押韵、有规律转韵外,篇首及转韵首句一般皆入韵;2.以通体七言为主,也有篇首、篇末及其它位置偶尔用杂言者;3.大量使用对偶句,除篇首、篇末及转韵起首二句外,一般皆对偶,对偶句一般也是律化程度较高的句子;4.在修辞上集以上各体修辞手法之大成,尤以蝉联、铺排为多见,还特别注意使用关联词以绾接、照应句子间、章节间语意、声情。
齐梁体全面整合句式、韵式、修辞、声律七言歌行四要素,形成了有别于以上各体的新的体调特征,句式整齐,声韵铿锵,脉络分明,情词婉畅,十分富于情感和气势。这样的体式最适宜游观、咏物、闺情、叙事诸种题材内容的抒写,也宜于词藻典故的撷取、篇幅的扩充。齐梁体起于齐梁,在诗歌律化大趋势的作用下,陈隋后越来越得到诗人的认可和喜爱,成为歌行体、七言诗体中最突出的一体,初唐达至最繁盛的阶段,四杰最为突出,因而后人又称之为初唐体、四杰体。因为这一体在齐梁后是歌行体中最时新、最活跃的一体,作品量也较多,所以历代的诗论家以及今人多径直将它作为歌行的唯一体式对待。
(五)赋体。在前面介绍骚体时已提到一种辞赋体,那是由骚体衍生的一种体式,其基本特征同于骚体。这里所讲的赋体是指在齐梁体出现后产生并以齐梁体为基本形式特征的一种七言赋体。这种赋体的来源一是齐梁体的放大,前面已讲到齐梁体的转韵、铺排十分适宜于长篇的写作,若写作的内容有明显的时间、空间、性状的展开和铺叙,即成赋体,如萧绎、王褒、庾信的《燕歌行》。七言赋体另一来源是骈赋。齐梁后兴起的骈赋多夹用五七言诗句,夹用的句子都是偶数,二、四、六、八都有,一节一节夹用,每一节都换韵,以七言为主,一般也都有五言,如果将这些诗句抽取出来,往往就是一首完整的五七言交替成章的长诗。梁代的萧纲和戴暠就有几首这样形式的作品。萧纲有一首《伤离新体诗》,全诗40句,七次换韵,五七言交替成章。由诗题知写的是伤离别,全诗以时间、空间为序,层层描述伤别的情状,十分近似一篇《伤离赋》。诗题上又标为“新体诗”,看来作者是有意在尝试创造这种新诗体、新写法。他和戴暠的《度关山》也是这种形式。还有一些题目上有“篇”字的新题歌行形式也是这样,如陈张正见《神仙篇》、北齐颜之推、卢思道《听鸣蝉篇》,以及初唐骆宾王《帝京篇》、《畴昔篇》,都是典型的具有骈赋特征的赋体歌行。关于骈赋与七言歌行发展的关系,赵昌平《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有较充分的论述。[4]
二、李白歌行的五点特征
以上是李白之前曾先后出现的几种歌行体式,将李白歌行与之对照,其特征就比较清晰地显现出来了。若以此为范围,则李白的歌行作品共119首,包括乐府诗64首、骚体诗6首、其它歌辞题七古49首。① 这就比那30几首多出许多,研究李白歌行应以这119首为对象。
(一)诸体皆备。李白歌行具备了先前出现的古七言体、骚体、乐府杂言体、齐梁体、赋体全部五种体式。最多的是乐府杂言体,83首,其次是齐梁体,32首(与前类有重复),前者是李白在歌行体式取向上有别于时人的最突出的方面,后者是时风影响的产物。李白对古七言体、骚体也有很大兴趣。他的古七言体作品有8首,是入唐以来作品量最多的,这种体式的作品在李白前很少,其侪辈只有王昌龄、李颀很少的几首。李白歌行中“部分的古七言体”(仿王力语,合柏梁体、柏梁变体而言)就更多了,可以说遍布各歌行体式,总数达50首,接近他全部歌行的一半。李白的骚体有6首,题目是《远别离》、《幽涧泉》、《鸣皋歌送岑征君》、《临路歌》、《寄远》之十二、《代寄情人楚词体》,“部分的骚体”还有《蜀道难》、《胡无人》、《梦游天姥吟留别》、《万愤词投魏郎中》,共10首。宋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入唐以后骚体诗也有一些,如卢照邻、陈子昂、宋之问,分别都有五六首,王维最多,9首,但基本都是一些抒情短章。杜甫有两题8首“部分的骚体”,《同谷七歌》各首只有最后两句是骚句,《桃竹杖引》后半部分是骚体,论结构立意,论篇制,李白自然为第一。李白的赋体近20首,这些作品多是大篇,又多与以上各类相重,如《蜀道难》、《猛虎行》、《西岳云台歌》、《梁园吟》、《庐山谣》、《天姥吟》、《鸣皋歌》。李白的歌行赋体特征最为突出,采用赋体手法比比皆是,定为赋体的这近20首,是其特征最明显、篇制最大者。
在李白之前所有的歌行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做到诸体皆备。李白之前的唐代歌行作家约60余人,其作品主要体式是齐梁体,而一般作品的量又都不大,难以兼及诸体,只有盛唐的王维、李颀、高适、岑参作品较多,各20首左右,但也未能诸体皆备,最多具备四体,如王维缺古七言体,高适、岑参缺骚体,李颀缺骚体、赋体。李白之后杜甫作品最多,其数量仅少于李白,为111首,古七言体、齐梁体多于李白,赋体相当,乐府杂言体比例较少,骚体基本是个缺项,如果算上“部分的骚体”,只能勉强算是诸体皆备。
(二)融合众体。诸体皆备是从总体上对李白歌行所作的体式分析,这里是就其单篇作品所作的特征分析,就是说李白的许多七言歌行作品并不只是具备一种歌行体式特征,而是同时具备两种、三种甚至是四种、五种体式特征,李白在创作七言歌行时往往将各体式特征融合到一篇作品中。这样的意思古人、今人也曾有所表述,清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梁陈流丽亦时时间出,谲辞云构,奇文郁起,后世作者,无以加矣。歌行变格,自此定也。”除了古七言体,这段话算是都概括到了。但在他的意识里歌行体起于齐梁,对鲍明远之前他并不以歌行体式目之。也就是说他这里是谈李白歌行创作所受前代诗歌艺术的影响,而不是谈各歌行体式的融合。葛晓音曾明确地揭示李白歌行融合其它“歌行形制”的特点,[5] 但是由于她对歌行概念界定过窄,对这种特点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关于李白歌行融合众体的情况,笔者作了仔细比对,李白全部119首歌行中有65首融合了两种以上体式特征,超过了一半,其中融合两种体式的46首,融合三种体式的13首,四种5首,五种1首。融合三种的如《庐山谣》,属乐府杂言体,它又采取铺叙手法,依庐山景点空间位置层层铺叙,而成赋体,又在“庐山秀出南斗傍”下连用9句句句押韵的柏梁体韵式。融合四种的如《天姥吟》也是乐府杂言体,它在“熊咆龙吟殷岩泉”下使用了18句骚体句,又在最后七句中改用古七言体,在全篇结构上采用层层铺叙的赋体方式。五种体式交融一体的是《蜀道难》,它原本乐府杂言,句子极为参差,但又有许多骚体句式,开篇的惊呼像楚辞《九辩》的开篇,下面的“之”字句、四字句仿效的是楚辞句式,明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认为此诗“实与屈子互相照映”,在后半部又使用了不少古七言句式、韵式。《蜀道难》在李白歌行中算是较长的大篇,所写景观极为雄峻壮阔,在材料的组织、层次的安排上又运用了赋体手法,明陆时雍就认为“近赋体”,詹锳通过比较认为此诗与其所作《剑阁赋》“极为近似”。[6] 一诗而具五种体式实前所未有,所以时人殷璠赞其“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融合众体是李白歌行区别其它众多歌行的一大特征,以前的歌行作家真是“鲜有此体调”。融合二体者还能发现一些,融合三体以上的则极为少见,盛唐的王、李体式很单纯,少有合二体者,高、岑合两体者有一些,但无合三体者,杜甫合三体的有六、七首,无合四、五体者。这是李白在歌行创作中具有创造性的整合,前人认为这是“歌行变格”,并不准确,因为李白是意在综合发挥七言歌行发展以来所具有的一切体调特征,全面承继一切好的艺术经验,这不是“变”,而是充实、匡正,应称其为“正格”才是。
(三)杂言独多。李白歌行中杂言最多,乐府杂言加上其它各体杂言共92首,占其全部歌行近80%。王、李、高、岑、杜除王外,齐言皆占大多数,杜甫齐言70余首,占其歌行63%,杂言近40,只占37%,王维的杂言约占一半。在整个初盛唐以李白杂言所占比例最高,数量独多,白朝晖统计初唐至安史之乱前杂言七古共247首,李白有90余首,超过三分之一。[7] 或许这里统计的杂言七古这两项数字不太精确,但包含在七古内李白杂言歌行超过这个时段杂言歌行总数三分之一是没有问题的。
李白歌行杂言句式主要来自杂言乐府体和骚体,其句式、长短十分纷繁参差,自二言、三言、五言至八、九、十以上,“兮”字句、“之”“而”结构的句子,关联词连接的句子都有。上面所提到的几位作家作品中杂言主要是三言句、五言句,偶尔有“兮”字句,其它类型很少。在各种杂言类型中,李白最特出的是四言句、长句以及“之”“而”结构及关联词连接的句子,有的论者将这些句型称为“古文句”,或者追溯到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似乎不太正确,其实这些句型在楚辞中、汉魏乐府中是大量存在的,这正是李白歌行熔铸骚体、乐府杂言体所带来的特征。王运熙《李白七言歌行的体式渊源》[8] 正是从楚辞和汉魏乐府而没有从其它文体来考论李白歌行句式的渊源,是十分正确的。王先生在文章中特别考论了长句,列举了18篇包含长句的例子,其实还有15篇,总数为33篇,这大概也是古今所无。杜甫有长句的篇数只有12篇。这些长句是李白歌行具有特别豪迈奔放气势的一种体现,元稹称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大约是就这样的歌行而言,以致后人多叹为“不可及”(谢榛评《蜀道难》长句)。
李白的杂言多不是一般的两种句式混用,而是在一篇作品中错综使用多种句式,有的甚至达十数种,如《鸣皋歌》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十五言、“兮”字句、“之”字句,四言、六言各16句,穿插于各层长句之间,极尽长短之妙。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论七古长短句之妙说:“七言古或杂以两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杂以八九言、十余言,皆伸以长句,而故欲振荡其势、迴旋其姿也。其间忽疾忽徐,忽翕忽张,忽停潆,忽转掣,乍阴乍阳,屡迁光景,莫不有浩气鼓荡其机,如吹万之不穷,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长篇之能事极矣。”这段话评的就是李白歌行句法。
(四)韵式丰富。李白歌行用韵方式在荟萃各体式特征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基本的韵式是隔句押韵,数句一转。李白歌行除15首乐府杂言体、3首柏梁体、其它2首齐言七言诗外,都有转韵,转韵比例达83%。歌行至盛唐一韵到底的增多,王维、高、岑比例加大,杜甫一韵到底的作品共38首,占其全部歌行三分之一强,反过来说其转韵比例为66%,低于李白很多。特别是杜甫歌行中的齐言七言诗不转韵的多达22首,李白只有2首,差别更大。清叶燮在《原诗·外篇下》中说:“七古终篇一韵,唐初绝少,盛唐间有之,杜则十有二三,韩则十居八九。”此言虽是谈七古,也包括其中歌行,可见在转韵上盛唐风气已转,歌行正走“调失流转”(何景明《明月篇序》评杜甫歌行语)变格,在这方面李白仍恪守先前做法,是正确的。
至于李白歌行转韵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多数齐梁体包括部分乐府杂言体、赋体转韵比较有规则,大抵四句、六句一转,平仄互换,而总数占多数的作品则规则性不强,或者多长韵,或者多短韵,或者长短交替使用。如《襄阳歌》换韵句数是六、二十二、五,《乌栖曲》二、二、三,《夜坐吟》二、二、四、二、四。虽然规则不强,但都显得很是自然流畅,正如叶燮在前引数句下所言:“大约七古转韵,多寡长短,须行所不得不行,转所不得不转,方是匠心经营处。”李白这样的转韵正体现了他的匠心独运。
李白歌行在用韵上还有一大特点,即喜用古七言体韵式。李白有8首古七言体,即句句押韵,包括转韵与不转韵的柏梁体和柏梁变体,此外还有50首非古七言体引入了“部分的柏梁体”、部分的柏梁变体,即或一连几句七言句句入韵不转韵,或一连几句七言句句入韵又转韵,这样的用韵能造成在和谐中求变化,在顺适中见奇崛的声情效果。此种用韵方式入唐后不多见,同时人岑参稍多,杜甫为29首,但都少于李白。由于大量地引入这样的韵式,因此李白歌行中奇数句也很多,有23例,杜甫则为15例。人们多认为李白歌行多古调,除了句式等其它因素外,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白歌行在韵式使用上正如句式使用一样表现了很强的综合性,即在同一篇作品中采用多种用韵方式,其大部分作品用韵都不是单一的,众多的韵式配合在一起,真可谓五音繁会,跌宕生姿,如《公无渡河》头二句一韵;再八句转韵,此八句前六句句句入韵,后二句隔句韵;再七句转韵,此七句前四句句句入韵,五六两三字句不入韵,第七句入韵;最后三句转韵,句句入韵。长韵、短韵,偶句、奇句,隔句、句句,多种韵式就这样交汇在一起。
(五)修辞二长。李白歌行在修辞上也是荟萃了以往歌行的诸多修辞手法,无论是骚体、乐府杂言体还是齐梁后新的歌行体,其修辞方式在李白歌行中都有鲜明的映现,但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排比的使用,二是“君不见”的用语。
李白歌行排比句的使用也许是歌行作家中频率最高的,约略检视一下,其有排比句的作品有40余首,超过其全部歌行的三分之一,王、李、高、岑比例远低于此,杜甫有排比句作品20首左右,不足其全部歌行的五分之一。李白歌行多排比句首先与其歌行体式的构成有关,杂言体较宜使用排比而不太适宜对偶,骚体中的骈句也多为排比,赋体的铺排也常与排比相关;其次也与他对声律、偶对的态度有关,他不大喜用格律精严的对偶句,往往在可以用对偶的地方用上排比。当然更重要的这是一种积极修辞的做法。使用排比和对偶一样可以起到调节节奏、声韵的作用,但又比对偶显得自然、流畅,读李白歌行会有这样的感受。李白歌行中的排比不仅有两句排比,还有多句、多层排比,这样又可以起连接章句、贯通文气的作用,比如《蜀道难》“但见”、“又闻”的排比连接了四句,《梁甫吟》开篇两个“君不见”的排比各连接了八句。李白许多歌行气势壮盛,激情澎湃,不少也是由排比造成。用在首句,声势夺人,如《将进酒》起首两“君不见”排句,极为豪壮,前人多以“豪”字评之,《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即《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亦以排句起,前人也多赞评,王尧衢《唐诗合解》赞曰:“起势豪迈,如风雨之骤至。”用在篇中,上下振荡,如《行路难》其一“欲渡”下四句、其三“子胥”下六句连续排比,将其徬徨四顾、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何等激切。许多论者都谈到李白歌行章句、意象的跳跃性,其跳跃性的造成在一些方面也是由多用排比造成的。
前面已谈到“君不见”这一呼告语的来历及表达作用,它也有加强气势、连接章句的修辞作用。鲍照以后这个短语时见歌行及其它七言古诗中,但不太多,唐代李白前七古中用“君不见”大约有40余例,李白在七古中使用了16次,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12次用在歌行中,有的用在首句,所谓“破空而来”,有的用在充分陈述之后,一吐为快。“君不见”又往往与排比句结合为一,如《梁甫吟》、《将进酒》,既增加了力度,又强化了所连结句子的语脉、语势。还多与长句相连,往往领起多个长句,即使与一短句接也成了长句。排比、“君不见”、长句这些句式相互作用,对形成李白歌行宕荡奔放的语言风格起到重要作用。这里所谈“修辞二长”及其它方面所表现的特征也见出李白对鲍照的追摹。
注释:
①参见汤华泉《唐人的歌行概念与李白的七言歌行范围》(《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原文数字统计有小误,作品微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