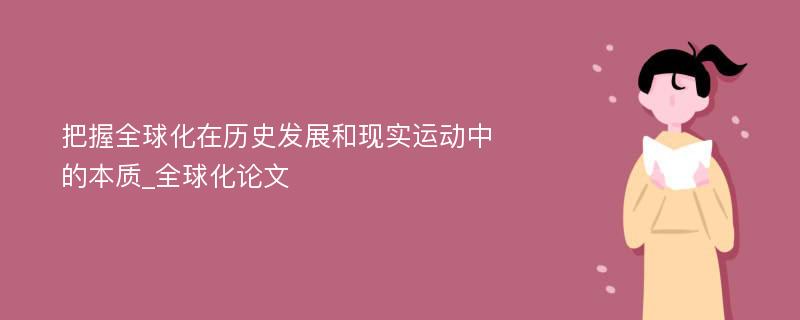
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动中把握全球化的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可否认,全球化的确给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并推进了全球经济的全新整合,但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导致了全球范围的雇佣状况不稳定、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福利削减、恐怖袭击甚至战争等诸多负面问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复杂状况,如何以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清问题的本质,就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而从资本主义的体制、机制出发,分析这些问题就是揭示全球化本质的重要途径。此外,全球化引发的国际领域的诸多问题,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引发的历史事实也极为相似,这又启发我们联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去思考这一问题。本文将通过介绍和分析一些反全球化理论,阐明笔者对全球化实质问题的理解。 一、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其实并非人类的新历程。有位记者曾这样说过:“全球化一词在表述上也许是全新的,但它却是很早之前就有的过程,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就确实有过这样的过程。在殖民地时代,欧洲各国在全球所到之处推行他们的规则……即开拓市场和进行掠夺,结果是从1600年到1800年期间从拉丁美洲等殖民地攫取了无尽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主要财源。”① 如果觉得将现在的全球化像这样追溯到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主义时代难以接受,我们不妨再将视野稍微限定一下。世界银行在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中,通过对“贸易、人口移动、资本流动等”的研究,总结出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全球化进程:第一次是1870年-1914年,第二次是1945年-1980年,第三次是1980年至今②。支撑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的包括从帆船到蒸汽机的运输技术的改变,英国自由贸易体制的确立,从欧洲到北美、澳大利亚的移民等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和保护主义、移民限制以及封闭式经济、信息管制、计划经济等原因则抑制了全球化的发展(这也说明全球化并非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球化再次兴起,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形成了第二次全球化进程。第二次全球化虽然促进了海上贸易的恢复,一部分贸易壁垒也被打破,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些国际规则限制了资本、商品、服务的流动以及人员的移动等,使当时的资本流动和人口移动都没有恢复到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的水平。而且在这些规则下,由于南北之间的贸易是以南方的初级产品与北方的工业产品进行贸易这样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结构形式展开的,南北之间的差距由此而被固定下来。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世界迎来了殖民地解放、争取国家独立的时代,但很快从旧殖民地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便跌落为旧宗主国经济霸权下的从属国。联合国10年的开发努力以“受挫的10年”而告终,新经济秩序的梦想也不足10年即告破灭。人们意识到,第二次全球化实际上不过是新殖民主义取代旧殖民主义的过程。 第三次全球化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南北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推动已经固化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条件是世界格局在质上、量上发生变化:经济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政治上冷战体制的结束、文化上美国化的倾向,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方式发生了改变,出口中制造业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25%上升至1998年的80%,服务贸易的比例从9%扩大到17%③,然而,如今这种融入这股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和被这一浪潮排除在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被卷入全球化的各国之间的或是各自国内的差距扩大及其固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差距、不平等、压制和异化等,都已经严重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现状是:曾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经历过的历史过程再次以全球化的形式显现。虽然人类有着较为丰富的纠正市场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灾祸的历史经验,但那些多是区域性的,若将这些经验用于全球的话,就显得很不够了。 二、恐怖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报应 如果将全球化置于历史长河中的话,就不难发现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关联。“9·11”事件以及之后的同时性、多发性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都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Ashby,Johnson)曾在他的著作《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果》(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将“19世纪称作帝国主义的东西换成了看似更为合理的词汇”罢了,由它引起的问题的所有责任都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国家政策以及外交政策,“这场世纪末发生的经济危机起源于美国打开和控制东亚卫星国经济的计划,其目的在于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并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④。 查莫斯在全面分析了全球化导致的20世纪末的经济危机爆发、恐怖主义出现等意外后果之后,又作出了这样的预言:“典型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以袭击无辜者来引起世人关注不可战胜者们的原罪。21世纪的无辜者们将由于帝国主义在近几十年中的冒险行为而遭到报复。虽然大部分美国人不大在意有人以他们的名义过去和现在都干了什么,但他们作为个人和集体都将为了他们的国家继续控制世界的企图而付出高昂的代价。”⑤ 这是纽约世贸中心发生“9·11”恐怖爆炸事件前一年的预言。这种预言和批评不禁让我们想起大约150年前、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对于一些事件,马克思曾作出的批评。当时在英国的非正统殖民地印度爆发了东印度公司雇佣兵的反英大起义及英国对此进行的武力镇压,英国的首都伦敦不断传来印度当地居民施行的残暴行为,以及对居住在印度的英国妇女及孩子采取无差别恐怖主义行为的报道,当时生活在伦敦的马克思对这些报道给予了批评。他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指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英国对殖民地统治过程中日常使用的暴力,因为英国的报纸(《泰晤士报》)故意只夸大地报道了当地居民的残暴行为。“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行,的确是骇人听闻的,可怕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是只有在武装暴动的战争中,在民族战争、种族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的暴行。”可是,这难道不是“报应”吗?马克思接着这样说道:“西帕依的行为尽管声名狼藉,也只不过是集中反映了英国本身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不仅包括其建立东方帝国时期,甚至包括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十年。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要指出刑讯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⑥ 因此,“即使就目前这次灾难来说,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的,英国人则体现了人类的一切善良天性,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还特别深刻地揭露了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⑦的暴行,以及镇压“西帕依叛乱”时,英国军人实施的无数杀戮和残暴行为“总被说成是军人的尚武行为,往往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不讲令人作呕的细节,而土著人的暴行,本身已令人震惊,又往往被故意渲染夸大”⑧的真相。 可以说,约翰逊的预言和150多年前的马克思的揭露都准确地预测了帝国主义的全球支配将会导致的历史报应。因此,不论发生怎样的无差别恐怖事件,将残酷的一面全部归咎于恐怖分子一方,而对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一味地给予同情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需要冷静地质询问题的本质,这才是根本。当然,笔者并不是要为恐怖分子辩护或是支持恐怖主义行为,正如马克思虽然提到那是“历史报应”,却并非支持“土著居民的残暴行为”一样。 三、全球化的体制原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要了解当今全球化的本质,还需要关注几个主要的反全球化思潮。而产生这些思潮背景的正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一系列的反全球化运动,这里不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些运动的过程⑨。 1.20世纪末开始的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通常被认为开始于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确,西雅图的游行是针对“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而掀起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一潮流真正的开始实际上是在此之前的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缔结。虽然反对这一协定的运动并没有成功,但却使之后多国间投资协定(MAI)的秘密交涉以失败告终,为西雅图的抗议行动作了准备。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同时,墨西哥的原住民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武装斗争正风起云涌,在墨西哥爆发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武装斗争也可以说是对反全球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促进了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受到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统治阶层出现裂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几位大经济学家开始公然批评“华盛顿共识”,这些都对反全球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5年,法国公共部门的大规模罢工导致政府想要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受挫,社会舆论转向左翼,涌现出诸多反全球化的活动家。从2000年开始,华盛顿、布拉格、魁北克、热那亚相继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就是世界社会论坛(WSF)中的反全球化能量形成的过程。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反全球化运动的特征的话,那就是组织起来的工人与非政府组织活动家们的联合,也被称作“卡车司机·海龟同盟”⑩。工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在之后的魁北克、热那亚、巴塞罗那运动中也有所表现,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特征。 另一个特征是,从2001年热那亚罢工起,这些运动表现出明确的反战意识。在热那亚,人们呼吁反对阿富汗战争,这一呼声与欧洲各地的反对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运动一道迅速传播。可以说,到2002年3月16日,欧盟巴塞罗那首脑会议期间爆发的“反对资本和战争的欧洲”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将这一特征推向最高潮。这期间虽然因为“9·11”事件的爆发出现过短暂的退潮,但在2002年2月的巴西阿雷格里世界社会论坛上,却再次掀起热潮。反对美英出兵伊拉克的呼声从伦敦、罗马、马德里、柏林,甚至跨越大洋,传播到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上千万人走上了街头。此后,在西班牙,追随布什的阿斯纳尔政权在大选中遭到国民的抛弃,最终实现了从伊拉克的撤军。不过,反全球化运动现在正日益面临着“武装起来的全球化”的危险局面,运动的参与者们似乎已经对此有所警觉。 2.反全球化运动中涌现的主要思潮 从反全球化运动并非统一的行动可以看出,其实这些运动中包含着多种思潮。 第一种思潮是虽然不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反对全球化。像英国的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等人和一些保守的非政府组织就是持这一立场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坏,只是企业拥有了过大的权力,只要再多考虑一些政治与经济的平衡,督促企业自律就可以了。 第二种思潮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在不反对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点上,虽然与第一种思潮相同,但在要改变什么这一点上却是与第一种思潮不同的。而根据要改变的对象的不同,这一思潮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该恢复全球化导致的被削弱了的民族国家的权力,从而回到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受到制约的阶段(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那些主张引入托宾税的,就可以说是持这一立场的人。另一派则主张对市场经济加以限制,那些谋求公平贸易的运动以及经济上的区域化的人就属于这一立场。 第三种思潮是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的自主运动的延续。从运动本身来看,有“白上衣”派和“不服从”派(11);从思想家来看,有著有《帝国》的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从战术上看,以去集权化的组织等为特征。 第四种思潮是社会主义的反全球化立场,这是一种始终追求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立场。当然,这种立场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追求更具弹性的计划经济为特征,这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持这一立场的人现在也只是少数派而已,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理论指导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卡利尼科斯理论(12)通过分析反全球化运动的世界性潮流,针对“谁是真正的敌人”“打倒敌人所需要的战略是什么”以及“胜利之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三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他在《反资本主义宣言》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与整个星球对立”,反全球化运动应采取多样的策略,主张将追求正义、效率、民主主义、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价值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问题进行研究。 上述对抗理论提示我们:全球化的本质实际上与所谓的资本主义体制理论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为了纠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才会出现一些是否必须限制资本、对资本主义原理作出某些调整或修正的提法。然而仅以此来回答全球化的本质问题显然还是很不够的。 四、全球化的国际原理:帝国主义的全球化 1.一种新帝国主义论 要揭示全球化的内在机理,还需要了解另外一个理论——加拿大政治学家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 Gindin)的帝国主义理论(13)。他们试图将现代的全球化与美国帝国主义论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以下是他们的主要观点:第一,所谓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第二,为了对上述观点作出正确的理解,需要重新明确帝国主义的概念。第三,新帝国主义(进行“国际协调”的帝国主义)的特征有三点,即以非正式帝国面貌(以自由贸易作为手段的霸权国家)出现的美国、将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网络、通过直接投资的相互渗透。第四,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具有其自身的矛盾。由于美帝国只需通过控制其他国家就可以进行支配活动,即各国在拥有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情况下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对美帝国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会主动脱离帝国权力的控制,从而使其丧失作为帝国存在的正当性,而这一正当性又取决于其国内社会势力的平衡关系。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一方面现在的左翼势力已经丢掉帝国主义概念、处于混沌状态中很久了,另一方面全球化越是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野心越是暴露无遗。而这一理论的独到之处正在于,一方面他们主张恢复帝国主义的一般概念,另一方面主张阐明美帝国的特殊性,这一做法正好回应了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同时,这一理论一方面接受了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加拉格(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提出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观点(14),并明确表示放弃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另一方面又从W.A.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门户开放的立场”(15)出发,将美国描绘成自建国以来就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说,这些观点展示了方法论的创新,具有独到的理论意义。 2.传统帝国主义论的不足 可以说,现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如此明白不过的结论,为什么现代左翼却认识不到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受到列宁等人传统帝国主义阶段论理论的束缚,即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自由竞争、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这种阶段性的历史理解,这或多或少也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识,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左翼世界的常识。然而事实上,早在50多年前,加拉格和罗宾逊就已经打破这种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帝国主义),提出了新的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解[“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论,以及为了理解这一理论提出的“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概念上的区别]。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或是左翼学界对此却完全无视,依然执着地坚守着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理解。实际上,自由主义阶段也有帝国主义,以垄断阶段的特征来定义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是很难解释通的。因此,当世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后,在通过全球化找到活路时,执着于阶段论的帝国主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下子陷入无法解释的境地,反倒是“从属论”“世界体系论”勉强给予了解答。可见,如果不接受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概念,则对于并没有殖民地的美国为何是帝国主义国家这样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也很难给出理论上的解答了。为此,要将全球化的现实当作美国帝国主义的问题去理解,则必须回到加拉格和罗宾逊提出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这一问题上。 帝国主义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近代帝国主义的概念是在对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的冒险主义的政治态势进行评价时开始使用的(16),马克思的用法也源于此(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章)。之后,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7)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为人们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经典概念。这一概念包含如下几个特征:第一,是包含其中的特定的历史性解释,其支撑理论是独特的发展阶段论。例如,不论是列宁还是霍布森,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19世纪70年代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帝国主义。而将这之前的19世纪40年代-60年代(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时期视为帝国主义尚未形成,更没有将更早的西班牙、葡萄牙的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作为研究对象(18)。这是一种将19世纪70年代视为自由主义向帝国主义转换的时代而将历史割裂开来的观点。第二,是向资本主义本身寻求帝国主义本质的倾向。例如,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的列宁的定义,以及试图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建立健全的帝国主义的霍布森的立场曾经广泛流行,而试图将帝国主义还原为资本主义去理解的本质还原论也曾出现过。与这一倾向紧密相连的是第三个特征,即通过资本输出和国内消费不足来说明帝国主义形成的经济中心论,这种观点认为,特别是海外直接投资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帝国主义的形成。 不过,随着帝国主义概念的广泛流行,这些特征逐渐显现出重大缺陷,并日益与事实相背离。第一,即使是在自由竞争的时代(1840年-1860年),法国也曾相继将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南太平洋诸岛、西贡等地划归为殖民地,而且已经将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的英国也相继把新西兰、香港、纳塔尔、缅甸、拉各斯划归殖民地,甚至在这一时期还将印度全部吞并。整个19世纪,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显现出帝国主义的连续性。第二,帝国主义虽然曾在世界各地抢占战略基地(包括贮碳港),但却常常被证实并非完全是出于经济动机。即便是将被纳粹煽动起来的抢占领土的欲望以及纯粹出于政治动机的强权政治的表现还原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因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媒介,在国家理论中得以概括,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国际贸易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的。帕尼奇和金丁也指出,帝国主义不是能够从经济阶段论或危机论中直接推导出来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如果无视这种方法论的过程,使帝国主义理论跨越国家理论,直接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相连接的话,则是一种太过武断的想法,这甚至会导致“国家的行政能力”失去对于帝国主义应有状态的重要影响。为什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领土扩张要求比以前更加高涨呢?真正的原因在于英国已无法通过自由贸易这种非正式手段来维系帝国了,在于英国力量不足了,而不在于自由主义时代突然转变为帝国主义时代了。第三,不论是消费过少,还是资本输出,将帝国主义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原因直接联系,都是有说不通之处的。例如,帝国主义时代曾是全面的消费热的时代(19)。帕尼奇和金丁曾指出,从“半饥饿状态的消费水平”起,帝国主义各国的“大众生活”“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都能感受到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从资本输出的角度看,也无法将其看成是帝国主义建立的主要原因。到1913年为止,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额的1/4以上投到了非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包括这一事实在内,英国资本输出的大部分被投到了能够帮助英国扩大原材料生产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而非帝国主义时代被吞并的非洲和亚洲。可见,为了寻找过剩资本的投放地而向海外寻求殖民地的说法,作为事实认识也是无法成立的。 产生上述难点的最大原因是,按照一般的理解,帝国主义与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是无法同时存在的,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一对对立的概念这样一种思维,或者说,是只将武力夺取(吞并)领土作为帝国主义的特征这样一种印象所致。如果将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经济控制这一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考虑进来的话,实际上自由主义时期已经有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之前提到的加拉格和罗宾逊,他们提出,19世纪的英国帝国主义一直试图“可能的话通过非正式手段,必要时与正式手段并用,以确保维系其最高控制权”。拉丁美洲是前者的例子,印度是后者的例子。究竟采取怎样的手段是依据当时的状况而定的,即“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上有不同”罢了。因此,虽然印度是以非正式的英帝国开始的,但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1877年)被编入正式的英帝国,战后独立后又回到英国的非正式帝国中。不去触及政治方面的国家主权、经济上通过自由贸易实行帝国主义支配的可能性,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通过这种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扩充和更新,可以很好地把握过去那种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通过自由贸易的国际标准强行实行支配的帝国主义以及不想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等多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新本质。 3.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 展示上述新本质的正是美国帝国主义。众所周知,该帝国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对他国的领土要求(20),在思想意识上持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正式的帝国主义)的立场,自认为是“自由”的守护神。另一方面,美国又在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的自由贸易规则(从门户开放到华盛顿共识),并为此在控制地区建立独立的主权(傀儡政权)。为了强调这些要求与帝国主义无关,在美国历史解释(美国史的神话(21))上进行掩盖自己的扩张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粉饰。 事实上,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推行的扩张主义的诸多事例早已被很多研究所证明。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就明确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代表农业利益的领土扩张主义的传统和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贸易扩张主义的传统息息相通,前者从反联邦派的杰斐逊开始,后由民主党继承;后者则由联邦派一辉格党开始,后由共和党继承(22)。将比尔德的这种公式化的观点理解为扩张主义的历史一贯性,将是有帮助的。另外,支撑这种扩张主义理念的现实美国帝国主义(到1890年宣布消除边界为止),主要专注于国内的殖民地——西部的“开拓”,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得以一直成为与欧洲不同的、没有必要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独特的帝国主义国家。输入且受到剥削的黑人奴隶,被以武力虐杀、围捕、抢夺土地的美国原住民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最早的牺牲品(23)。伴随着西进运动、西部殖民地化的结束,美国帝国主义开始了真正的海外扩张(海洋帝国的构想),肩负这一时期的扩张主义使命而出现的是大企业。19世纪90年代,是海外扩张主义的承担者发生改变的时期。19世纪90年代之前,受到北部和东部资本压迫的农业利益的受益者(农民及农作物加工者)向海外市场寻求活路,90年代之后则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金融—工商业者掌握了海外扩张的主导权”,主角变为“投资家、出口业者、船主—海运业者、海军相关者等”(24)。从此,非正式帝国的美国帝国主义全新的历史开始了。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非正式帝国或者称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美国版”(25),之后的“关于贸易的罗斯福新政的思想不仅维持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或非正式的帝国,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它”(26)。将加拉格和罗宾逊提出的问题适用于美国帝国史的是美国史学家威廉姆斯和包含他在内的美国新左翼的史学研究者们,他们身处帝国主义的美国,威廉姆斯接下来的这一段很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看到的“悲剧”:“说是要援助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美国人道主义冲动,在努力要帮助他们时,所使用的方法却是没有内容的,甚至是损害性的。可以想见,其他国家因为美国的政策丧失了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心理上的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与其说是得到了救助,不如说是受到了伤害。结果是,他们萌生出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报复的心理,进一步将这一开始时就已非常复杂的问题扩大化,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这对于理解美国政策的内在矛盾是怎样加深的,非常重要。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时,也许才能够离美国的理想更进一步,或是才能够建立起更有效地援助其他国家人民的构想吧。”(27) 越是将自己的理念或理想高高举起的人,越是容易被现实所欺骗。理想和现实之间令人恐惧的背离扎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中,这无法永久地自我欺瞒下去。威廉姆斯对美国政策的精英们疾呼:“你们错了!”将帝国主义的矛盾理解为美国政策的内在矛盾时,就可以探寻到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因为问题已不是美帝国,而是美国帝国主义。美国的“人道主义冲动”在日益唤起“政治的、经济的报复”或是心理报复的现实面前,上述将国际原理为基础的全球化作为焦点展开的近几年的研究已经很明确地表明:全球化的国际原理就是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全球化的本质与两方面的原理密切相关:一是以阶级社会为媒介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体制原理,另一个则是以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机制为媒介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国际原理。只是,如果将全球化视为直接引发、暴露不平等的运动,与其相对的,则是试图纠正这种不平等、实现平等的反抗的活动或运动的存在。这一点,只要考虑一下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越是阐明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原理或是倾向,人类就越会通过限制或者修正资本主义、实现市民社会(或福利国家)去努力修正过度的不平等,实现可容忍的平等。或者,帝国主义越是显露出大国控制或是引发悲惨的战争,人类就越会通过国际共同体的实现,努力避免差距或纷争,实现和平和协调。这些对抗性的努力和运动是人类近代史的真实写照。 因此,相对于引发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会对抗性地产生出谋求平等的另一种全球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草根一族的反全球化活动就是这种必然性的产物。这一运动将如何与迄今为止的人类史的发展相联系,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予以解答。 为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的理论课题:第一,为了克服全球性的不平等以实现平等,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实现全球性的市民社会,限制资本主义,抑制帝国主义。第二,为此,需要从历史性、整体性、结构性、批判性、原理性等方面阐明全球化的本质。第三,需要全球化的社会科学(不仅限于单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狭隘的专业视角)的研究以及相应的综合性视野和理论性框架。 注释: ①ウェイン·ェルウツド:『グ口一バリゼ一ションとはなにか』、渡辺雅男·姉歯暁訳、東京:こぶし書房、2003年、17-8頁。 ②世界銀行:『グ口一バリゼ一ションと経済開発』、新井敬夫訳、東京:シュプリンガ一.フェアラ一ク東京、2004年、第1章。 ③世界銀行:『グ口一バリゼ一ションと経済開発』、新井敬夫訳、東京:シュプリンガ一.フェアラ一ク東京、2004年、36-7頁。 ④[美]查莫斯·约翰逊:《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果》,罗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9-200页。 ⑤[美]查莫斯·约翰逊:《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果》,罗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6页。 ⑨渡辺雅男:「「 反グ口一バリズム」ってどんな運動なのですか?」,『自然と人間』2004年3月号。 ⑩这一称谓源于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WTO的活动中,参加的团体中既有呼吁保护海龟的环境保护团体——海龟修复组(Sea Turtle Restoration Group),也有很早就为人所知的战斗性工会——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这一称谓形象地反映出这种联合的特征。 (11)20世纪70年代欧洲曾爆发以意大利为中心,在学校、工厂、街头以建立自治权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在遭受镇压的过程中,曾出现身穿纯白衣服、或不穿以示抗议的人们。 (12)[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罗汉、孙宁、黄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13)レオ·パニツチ、サム·ギンディン:『アメリカ帝国主義とはなにか』、渡辺雅男訳、東京:こぶし書房、2004年。 (14)ジョン·ギャラハ一、口ナルド·口ビンソン:「自由貿易帝国主義」、ジョ一ジ·ネ一デル、ペリ一·カ一ティズ編:『帝国主義と植民地主義』、川上肇ほか訳、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3年。 (15)ウィリアム·A·ウィリアムズ:『アメリカ外交の悲劇』、高橋章ほか訳、東京:御茶ノ水書房、1986年。原著于1959年出版。 (16)Richard Koebner and H.D.Schmidt,Imper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 (17)ホブスン『帝国主義論』上下、矢内原忠雄訳、東京:岩波文庫、1951-2年。原著于1902年出版。 (18)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承认这种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存在。 (19)Niall Ferguson,Empire,Londen:Allen Lane,2002. (20)从这一主张来看,曾经侵犯夏威夷、古巴、菲律宾主权并将它们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史实,已经从美国历史中消失了。 (21)关于美国史的神话,可参考ジェ一ムズ·W·ロ一ウェン:『アメリカの歴史教科書問題』、富田虎男訳、東京:明石書店、2004年。 (22)チャ一ルズ·ビア一ドほか(松本重治ほか訳)『アメリカ合衆国史』,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同『アメリカ精神の歴史』、東京:岩波書店、1954年、同『共和国』社会思想研究会出版部、1950年。 (23)Gareth Stedman Jones,The Specificity of US Imperialism,New Left Review,No.60,1970. (24)高橋章:『アメリカ帝国主義成立史の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11頁。 (25)ウィリアム·A·ウィリアムズ:『アメリカ外交の悲劇』、高橋章ほか訳、東京:御茶ノ水書房、1986年、137頁。 (26)ウィリアス·A·ウィリアムズ:『アメリカ外交の悲劇』、高橋章ほか訳、東京:御茶ノ水書房、1986年、254頁。 (27)ウィリアス·A·ウィリアムズ:『アメリカ外交の悲劇』、高橋章ほか訳、東京:御茶ノ水書房、1986年、26页。标签:全球化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非正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