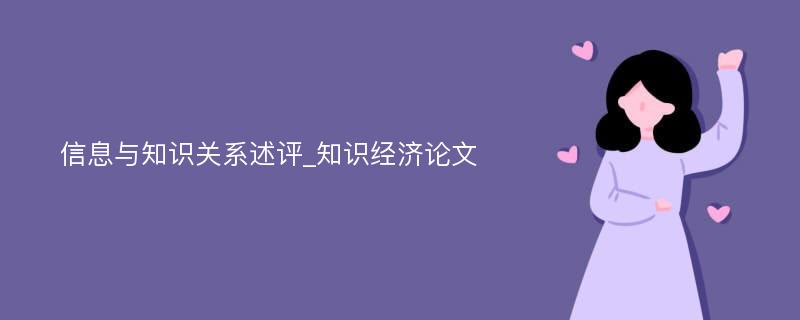
信息与知识的关系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关系论文,知识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半年多来,在国内“知识经济热”的讨论中,不仅引起人们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关系的关注,而且促使人们考虑信息与知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鉴于前一个问题我已写过《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关系述评》[1]一文,这里想就讨论中出现的有关信息与知识间关系的种种认识再进行一番评论。
评论前,需讲讲必要的预备知识。根据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K·Popper)“三个世界”的理论,信息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在这个分类中,我们把人类以外其他生物界包括在客观的物理世界内。因此,其他生物作为主体对外部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形成的信息,也就列入了第一类信息的范围)。这三类信息都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才能成为知识。但有时第二类和第三类信息也可能直接表现为知识。所以,一些世界著名的字典如《韦氏大字典》等往往把知识视作数据、新闻一样包括在信息的释义中。
讲完上述预备知识后,我们综观知识经济讨论中所产生的关于信息与知识间的关系的认识,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五种:
(1)并列关系
为了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把知识从信息中分离出来而与信息相并列。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定义知识经济时说:“这种经济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2]
这种并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把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包括隐性的和显性的)即知识同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区分开来加以强调,其经济学依据是新增长理论对知识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新认识。按照该理论,源于研究开发、教育培训的技术进步不是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变量,即由经济系统本身来说明;技术不同于竞争性商品而具有非竞争性,又不同于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而具有部分排他性;技术有“创造性的破坏效应”,技术的这类特征与作用同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即知识有关,知识及其积累有“溢出效应”,能使边际报酬递增。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上述知识新作用的发挥,同信息及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息息相关;而且基于信息的知识固然重要,基于知识的智能或智力更为重要,知识向生产力的转化,关键在于运用知识的能力,而非任何知识的简单集合,智能的培养、提高比知识的灌输、接受更重要。
(2)转化关系
信息经过加工转化为知识,自不待言。因为绝大多数书文都承认,知识是加工过的信息。加工到何种程度,信息才转化为知识,则是一个动态的深化过程。
至于知识向信息的转化,显然是信息技术作用的结果。知识依其获取时是否通过实践产生经验,又区分为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即主观知识、编码型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即客观知识,这两类知识分别与预备知识中讲的第二类、第三类信息相对应。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影响,不仅编码型知识迅速转化为“信息世界”的成员,易于从语法信息的角度加以度量,而且越来越多的意会型知识由于外化和物化通过编码型知识而转化为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特别是因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或知识工程发展使意会型知识与编码型知识的界限日趋模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论述知识经济的趋势和涵义时,也不得不承认“知识经济的特征是既需要不断地学习编码化信息又要具备利用这种信息的能力[3]”,“正是由于知识的一些可编码成份的不断增加,使得现在的时代具有‘信息社会’的特征”[4]。
信息与知识的相互转化,既存在于客观的概念世界,也存在于主观的精神世界,即人脑的感知和思维过程中,更存在于这两个世界之间以及客观的物理世界与主观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中。
(3)包含关系
“有趣的是,研究知识经济的将信息定义为知识的子集,研究信息经济的则反之,视知识为信息的子集。”[5]个别同志以此来“证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是“同根”的。且不说这样证明的同根关系能否成立,信息与知识之间究竟谁包含谁是含糊不得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根据前述波普三个世界的理论,知识只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虽作用于但并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而信息则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且反映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又是形成知识所必不可少的。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是成立的,反之则不成立。
认为信息包含于知识,是由于这种观点把信息局限于编码型知识,而把意会型知识因其“难于编码化和度量”排除在信息之外[6](这种观点源于Lundvall和Johnson,为我国部分学者所接受和传播)。实际上,意会型知识也只是认识论意义上隐性信息中的一个部分。当然,知识包含情报,然而情报虽是信息,但不能等同于信息。应当说,情报是知识的子集,而知识是信息的子集。这在信息学中已成了常识。
(4)分立关系
有人主张把知识从信息中分立出来,认为信息仅仅是知识的“原料”或“燃料”,以突出知识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否认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并看不到知识可以转化为信息,还与第一种并列关系不同,力图压低信息的作用以抬高知识的作用。
(5)替代关系
由于信息与知识有不少共同的属性,如分布非对称性、使用无排他性等,两者在一定场合相互替代是可能的。在知识经济的讨论中自然不会出现用信息替代知识的现象,但用知识替代信息则相当普遍。问题是信息与知识各自所处的层次不同,如信息偏重技术但处于全局层面,而知识偏重内容但处于专门层面,有些替代出于强调知识而无视信息的需要,忽视了知识与信息的差别,就显得不尽合适或过度轻率。例如,把明显属于信息产业的软件产业的超常发展视作知识经济的首要特征时,不考虑软件的技术产品属性,把软件产业改称为知识产业。孰不知科研、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业。又如用知识网络替代信息网络,用知识基础设施替代信息基础设施等等,这样的任意更改只会引起混乱、造成误导。尽管信息网络可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目的并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但信息网络的用途十分广泛,远非以此为限,还可用于政府管理、远程医疗、公众娱乐等等,而最大的应用领域则首推电子商务。至于信息基础设施是知识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石,把它改称为知识基础设施后就不知其所指为何物了。
以上关于信息与知识间五种关系的认识,我认为第一、二种关系和第三种关系中的前一半是可以接受的、正确的,而第三种关系中的后一半和第四、五种关系则是错误的、不能苟同的。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虽然与不同人士的不同用意有关,例如迎合风向未经研究就信手写来、企图突出自身行业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但是也确有共同的根源,例如,把知识等同于科学、技术的泛化现象,使知识脱离开反映实践状况的信息而认为它来源于头脑且存在于头脑[7](如说“人脑创造出知识”、“它(指人脑—引者注)是生产知识的唯一源泉”等等)的虚幻化倾向,以及有意无意地贬低知识在工业经济以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适当地夸大知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又未能指明其与以往相比的实质性不同,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