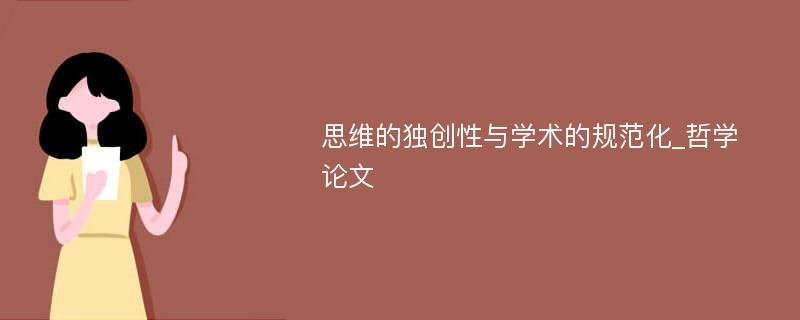
思想的原创性与学术的规范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范性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以及如何对立
倪梁康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于学术与思想之关系的讨论已有时日。常常可以听到有“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这 一类说法。它们大多不言自明地把“学术”与“思想”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这总 会使我感到有些茫然。首先是不明白“学术”在这里究竟是指什么?然后是不明白“思 想”又是指什么?因此自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学术与思想之间会有对立?以及为什么 要对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做如此强调?我从一开始便把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看作是 一个汉语语境中的特有议题。或许是孤陋寡闻,但我确实不知道在其他文化中是否有过 相关问题的讨论。当然上述困惑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明。很难确定“ 学术”与“思想”这两个表述在其他语言中的对应概念是什么,尤其是当它们是在对立 的意义上被使用时。困惑多了,我甚至还产生怀疑,即怀疑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究竟 是否能够成为问题。
我并不想说,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一个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分析哲 学、胡塞尔与现象学哲学都主张排斥的那种虚假命题。因为我相信,既然问题被如此引 人注目地提出来,必定也就存在着它被提出的理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黑格尔所说 的“现实”与“合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假问题也应当有其作为假问题出 现和存在的理由。
因此,如果不想消极地回避这个问题,那么出于一个偏好现象学风格的研究者之习性 ,我在这里所能做的就只有对“学术”与“思想”这两个概念的现实含义与可能含义做 一大致的描述和清理,然后才尝试着去把握它们之所以在对峙的状态下出现的原因。
我们先来试着确定“学术”概念的大致内涵。而后我们或许便可以把排斥在“学术” 之外的所有较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活动都称作是“思想”,并以此方式来把握一个“学术 —思想”的概念对子。
我们首先假定:当人们把“学术”与“思想”当作对立的概念来使用时,“学术”一 词主要是指“学问”,用较为西学化的术语来说,大多是指“科学研究”,亦即在学院 的范围内进行的精神工作,姑且不论这里说的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自然科 学。而且这也与我们今天在较为国学化的语境中以及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中所使用的“学 术”概念基本吻合。在此概念的语义分析上我赞同许苏民先生对“学术”的定义,即它 不是梁启超、严复等在“学主知、术主行”意义上的“学术”,而是指“学问”、“知 识”①。
这个意义上的“学术”,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pisteme”较为相似。在《形而上学 》的中译本中,吴寿彭便将它译作“学术”,而苗力田也译作“科学”②。当亚里士多 德说“哲学的智慧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时,他显然是把哲学这种学术看作 是一种静观的知识,即不具有功利性质的知识。因此他也说,“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 自属确当。因为理论—静观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而实践—行动知识之目的则在于其功 用。”③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学”与“术”是有分别的,甚至是有对立的 。他所说的“episteme”概念更应当是指“学问”而非“学—术”。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所有理论的或静观的“学问”或“科学”,或“为学术的学 术”,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学术”;而在这个科学范围以外的思考,即那些以功用为 目的、以实践活动为特征的精神活动,都是“思想”的事情?
似乎行不通。因为一旦将“学”与“术”的分离等同于“学术”与“思想”的分离, 棘手的问题就会出现。就学问意义上的理论性“知识”概念而言:既然它的源头一直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那么在宽泛意义上的“科学”或“学问”显然就不能撇开例如自古希 腊以来便在思想史上自成一脉的那种论证风格。我们在那里已经可以发现哲学(当时的 哲学尚未与科学分家)与诗学的某种对立,或者是“logos”(逻各斯)与“ethos”(习俗 )的对立,或者是“logos”(逻各斯)与“muthos”(神话)的对立,如此等等。而“学” 与“术”的概念与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学术与思想”这对概念是否可以意指这里提及的哲学与诗学、理性与神话、 论理与伦理等等不同学科、方法、风格之间的差异与分离呢?显然也不行。试想,如果 去除了苏格拉底的睿智、柏拉图的透彻、亚里士多德的缜密,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逻各 斯的灵魂,残留下来的思想领域将会显得如何贫瘠?我想大多数人在思考思想史时,都 不会同意把这种代表着希腊特有精神的东西排斥在外。
因此,对这里的“学问”或“科学”概念,我们似乎还应再做进一步的限定。“科学 ”在这里既不应当是指古希腊的“知识”(episteme)或“静观”(theoria)——与它相 对立的是“意见”(doxa)或“行动”(praxis),也不应当是中世纪的“学识”(doctrin a)——与它相对立的是“无知”(ignorantia)。或许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 必须始终在近代的意义上理解‘科学’(wissenschaft)。”④“科学”在这里主要是指 那种自近代以来得到充分弘扬的、在很大程度上已数学化了的、精确的和实证的学术活 动(wissenschaft)。这个意义上的“科学”,应当是与“艺术”和“哲学”界限分明的 精神活动。将此意义上的“科学”转用到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那么例如考古学 中对某个墓葬的年代的确认,历史学中对某个记载史实的辨伪,社会学中对某个地区人 口增长率的统计,人类学中对某个原始部落的观察描述,以及诸如此类,它们都可以不 被纳入“思想”的范畴。换一种说法,一个人可以博古通今,或者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但由此并不能得出他的精神活动一定会与思想有关。学问家不是思想家。——这样, 我们似乎便在问题的解决方面前进了一步。
----------------------------------------
注释:
①参见《开放时代》1999年7、8月号许苏民文。
②③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993b。
④《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145页。
----------------------------------------
然而且慢!细究起来,这种用限定学科类型的方式进行的划分仍然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一旦把近代科学划出思想的范围以外,那么它的始作俑者如伽利略、推动和完善者如牛 顿、爱因斯坦等一大批人都会被关在思想的门外。这恐怕是大多数运用“学术”与“思 想”这对概念的人所不能赞同的。我们自己也将会在许多公认的“科学思想家”面前无 法自圆其说。
如此说来,“学术”与“思想”的划分与其说是与学科的划界相关,不如说是取决于 精神活动的不同性质。“思想”的特征看来主要在于它的原创性。而它在哪一个领域发 生,则可以说是一个非本质的因素。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思考问题了:我们先把握“思想”概念的 内涵,然后把所有不具有这种特殊内涵的高级精神活动都称之为“学术”?
这种思考取向显然会把“思想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最终引向我前不久刚论述过的对“ 原创与积累”问题的分析。我认为在它们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是相互依存。这应当也适 用于“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自有它的一定道理。例如在孔 子那里便已经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①的说法。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从“积 累与原创”的角度对“学术与思想”关系的最早论证。而在一篇至此还是写给自己读的 文字中,我曾将学术思想领域中的活动者大致分为三类:学者、思者和贩者。他们在历 史上的各自代表分别是玄奘、惠能和支敏度。撇开支敏度不论,学者如玄奘,思者如慧 能,分别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中的学术与思想之两极。这可以算是在问题的解决上前进 了一步吗?
但还是要慎重些!因为把“思想”等同于原创性精神活动的做法仍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比“学术”更难以把握的概念。如果思想是原创 ,那么学术又是什么?难道学术仅仅是单纯的复制吗?举例来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算得上是思想典范。但他的《哲学史演讲录》又算什么?在其中究竟是复制多于原创 ,还是恰恰相反?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 技术史》,它们究竟属于学术还是属于思想?福柯的《规训与惩戒》或《疯癜与文明》 ,它们是学术著作还是思想论述?
再回过来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史,这里多有以史代论的先例,困难就更大了:徐复观的 《中国人性论史》属于学术还是思想?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是学术还是思想? 学者如玄奘真的是完全无思想的吗?思者如惠能真的是完全无学术的吗?再看原创的典型 熊十力。他的基本为学风格可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为:“根柢无易其故,裁断必出于几。 ”②前者涉及他对旧唯识学之研究的态度,后者则表明他的新唯识学立场。熊十力毕生 之努力究竟应当被归为学术还是归为思想?即使是具有纯粹重构和再现意向的历史学研 究,也不可能不带有原创的因素。就像目前较受注目的古代史断代工程,它能否说是完 全排斥原创思想的纯学术研究?
解释学已经向我们阐述过一个见解:精神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形式是理解。而理解并不 是简单再造的(reproduktiv)行为,而且始终也是原造的(produktiv)行为③。按照这种 看法,在任何学术活动中都必定含有原创的因素。因而所谓学术性与思想性之间的关系 ,也就可以用伽达默尔所说的“熟悉性与陌生性”或埃柏林所说的“同一性与可变性” 来描述。原创与复制因而永远处在对话的间域之中。常常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六经注 我”与“我注六经”,归根结底只是理论的夸张而已。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只能以相互作 用的方式存在和发生。否则,“学术”和“思想”都是无稽之谈。换言之,既然原创无 法凭空而起,既然复制不可能达到同一,那么“思想”与“学术”的截然对立也就无法 具体而现实地成立。
----------------------------------------
注释:
①《论语·为政篇》。
②《佛家名相通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③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81页。
----------------------------------------
设果如此,那么孤立地谈论学术或思想便是不合适的。对学术与思想的确定划分之所 以困难,说到底乃是因为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必定会含有原创性的因素;而真正的思想 创造也绝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所谓学术与思想,都是在严肃的限度中进行的精神 活动。一旦脱出这个限度,学术和思想就要加上引号。也就是说,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是 完全无学术的;真正的学术也不可能是完全无思想的。
看上去很遗憾,我最终也没有能够给出“学术”和“思想”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和 明晰界线。这里所做的一切,似乎始终只是在围绕这两个概念兜圈子。但若换个角度考 虑,这些圈子很可能就是构成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基本视域。它们纵使没有可确定的界线 ,却仍然是环绕“学术”与“思想”的光晕。
我觉得至此为止大致可以弄清楚一件事:说穿了,当我们一再地谈及“学术与思想” 的关系时,当我们开始习惯于把“学术”与“思想”的概念加以对立地使用时,我们是 在有意无意地指出当前学术思想领域中的一个弊端:学术与思想之间纽带的断裂状态。 强调学术与思想之对立的人,往往是在表露对某个现状的遗憾或不满,或者是对所谓的 “学术”,或者是对所谓的“思想”。“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是一个论战性 的问题。
因而是否应当说:唯当我们不再发现思想与学术之间的鸿沟,唯当我们不再遭遇无思 想的“学术”或无学术的“思想”,我们才会不再去特别关注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 我们才拥有一个成熟的学术思想界,我们才可以在学术思想领域有所指望?
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
吴炫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应该说,从晚近“义理、词章、考据”三分天下以来,学术与思想之关系,就不断地 被学界所议论。虽然时有将“学术与思想”截然对立的观点出现,但“学术与思想”的 相互渗透,可能是今天更多学者容易接受的看法。只是,由于这个命题先天的思维方式 之局限——即将学术看作是与历史、材料、研究打交道的学问,将思想看作是头脑里产 生的想法、观点及其思辨形态,这就不仅将创造性的思想与学术混同于依附性的思想与 学术,而且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摆脱对西学的阐释状态、创造我们自己的 思想和学术的时代原创要求。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忽略,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凸显” ,就存在着思想的异己化问题,而90年代的“学术凸显”,也存在着以西方的学术规范 为学术规范这一新的异己化问题。这两个异己化,不仅使得我们的思想不具备独立性, 也使得我们的学术同样不具备独立性,从而共同呈现为对中国当下文化现实问题解释的 无力性、影响的有限性。
这就将问题转化为对“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的追问上来。如果说思想有依附既 定思想与创造自己的思想之别,学术有依据成见研究、阐释对象与依据己见研究、阐释 对象之别,那么,在我的否定主义理论中,这个问题就转化为生存性、依附性思想学术 与存在性、创造性思想学术之别,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使“思想与学术”之关系 成为一个空洞的命题。
就思想而言,问题首先来自我们容易将哲学性的思想与学术性的思想之混淆。当我们 说80年代是“思想凸显”的时候,显然与我们在80年代引进西方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等 哲学思潮相关。这使得我们在说思想与学术这对范畴时,主要是说哲学性的思想而不是 学术性的思想。这意味着,一个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但在 哲学上,则很可能是依附的、认同的,因此也是没有思想的。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在文艺理论上提出“境界”说,应该说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境界”说 在哲学上与道家和禅宗思想存在着血统上的关系,并融进了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思想,所 以我们就不能说王国维在哲学上有自己的思想。一旦一个文艺理论家在哲学上没有自己 的思想,也就必然会影响其文艺理论的独立品格。所谓王国维对哲学“可爱不可信”的 疑惑,在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那里是不存在的。即一个哲学家可能有困惑,但对自己的思 想则应该是确认的。王国维的这种困惑,其实也就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 的普遍困惑。这正好说明了在不同程度上有学术性思想的中国学者,为什么在哲学上一 下子就没有了思想,或者在哲学上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是双重的:一 方面它使得我们在西方人面前底气不足,于是我们只好靠中国传统哲学来显示我们先前 是有底气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真正把握住我们自己的问题,反而用西方哲学制造出 许多伪问题(如对现代性的反思)。所谓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所谓中国学人为什么众多 而思想家几近于无,所谓我们的作品、刊物为什么数量众多,但中国作家面对世界为什 么还找不到优越感,原因也概在于此。同样,90年代思想为什么会“淡出”,原因也概 在于80年代我们只有对西方哲学进行阐释的学术性思想,而没有真正的哲学原创性思想 ,以致形成了一谈理论创新就要将视线投向西方的思维定势。又由于西方哲学不同程度 上脱离中国现实问题的特性(比如西方的“彼岸”、“崇高”、“神性”文化精神就不 一定适合中国),所以这个原本就价值有限的哲学思想之失落,可能就是正常的。
于是,这就将问题引向我们将思想认同、承传与思想生产、创造之混淆。当中西方既 定思想作为一个已然的对象被我们加以讨论时,思想要么成了知识和学术让我们去接受 ,要么就成了对已经知识化了的思想进行的“思想活动”,从而远离了思想就是创造一 个新的世界观的本真之义。我当然不否认思想具有承传的性质,并且这种承传构成了人 类文化性循环生活的重要方面,但20世纪前后中国学界的思想文化热,显然不是在承传 的意义上接受西方思想的,也不是在承传的意义上对待中国传统思想的,而是在中国文 化衰落引发的一系列让人困惑之问题(比如中国人的优越感丧失)上产生的。这实际上是 一个要求我们进行思想生产的时代,也是要求我们用生产的思想建立新的文明的时代— —一如中国古代文明与儒道释思想休戚与共,也一如西方不同的文明生产出不同的思想 和主义一样。然而,当思想生产与思想选择被混同时,我们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中 国文化的衰落归结为传统思想,而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出我们当代的思想——如 果中国传统思想曾经催生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如果一种思想的功能不是永恒的话;于是 ,激烈的反传统必然导致对文化自然生态的破坏,从而造成了一个今天同样很人为化的 宏扬传统之问题。二是对西方思想采取了很功利化的“拿来主义”态度,在远离本应该 很自然的文化交流状态之后,对西方人的思想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审视,从而既遮掩了胡 适、冯友兰、金岳霖这些依附于西方思想的哲学家的现实影响的或缺问题,也造成了王 国维用叔本华哲学牵强地解释中国文学的生搬硬套之情况,更忽略了西方人的思想主要 是针对西方的问题而来的这一思想有限性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贯穿20世纪中国思想文 化界之始终,那么,所谓学界的“失语症”,正好反衬出认同来的思想之不稳定性以及 最终的虚空性。
学术问题也同样如此。“什么学术”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来,一是因为同样是研究、阐 释西方哲学史,中国学者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与西方学者罗素的《西方哲学 史》,在价值上就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不完全属于学术个性问题,也不完全属于 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问题,而是依托成见与依托己见之性质不同的问题。二是如果 说中国学术在80年代存在着浮躁之毛病,那么问题其实也不主要在于缺乏学术规范,更 不在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规范,而在于中国学者缺乏求精求深求创见的探究精神— —这种精神在先秦知识分子身上应该说闪现过,并构成已被后人遗忘了的中国创造性学 术文化传统。
就前者而言,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应该说在摆脱 极左思潮影响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在对西方哲学史料的描述与把握方面,至今 依然值得重视,也就是说依然有学术价值。然而由于本书尚未脱离当时“唯物与唯心” 论的思维模式,并带着这种模式去把握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演变,这就使得该书的学术 含金量十分有限。而这种依托成见写成的各种历史,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 如将阶级斗争的视线改为人道主义的视角,将有判断的历史改为判断隐匿的历史,但其 依托成见和共识的思维模式没有得以改变,也就使我们在学术上始终处在需要反省的状 态,并因此对反省对象的学术价值打上折扣。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之所以值得一提 ,主要不在于这是哲学家写就的历史,也不在于这部哲学史主观性较强,而在于这是一 部对西方哲学进行独特阐释的历史,并因此可以穿越时代的变化、成见的束缚而不断给 人启发。如果一部学术著作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仍熠熠生辉,那么它的学术性在于它的 独特性,便成为自然的推论。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还在于:我们今天如果用所谓“ 全球化”的眼光来写一部历史,其实并不比用“唯物唯心”的眼光来写一部历史的学术 价值要高。重要的在于史家如何用“个体化理解”来穿越共性的内容。否则,我们再过 几十年来看“全球化”,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唯物唯心”论的感觉一样的了。
这就说到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学术性”了。将学术与学术规范混淆,尤其将学术与西 方意义上的学术规范混淆,我以为是我们在学术性问题上的另一个误解。90年代以来之 所以有“学院派”之说,而“学院派”之所以倡导言必有据,据必有释,释必有注,显 然与纠正80年代的信口开河、浮光掠影之文风有关。这自然也没错。但且不说尼采的思 想性著作与这种学术无关,即便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 ,恐怕也经不起这样的检验。当然,学术性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这是正常的。 但这种要求是定位在西方的学术文化上,还是定位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当代需求上,我 以为意义是不一样的。正如80年代的“思想凸显”问题不在于“非学术化”,而在于我 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支撑一样,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依我看也只能接轨在学术规则 上,而不可能触及中国学术的批量复制乃至变相抄袭等平庸化问题。当然,这也不是说 回到乾嘉学派就算中国的学术了——同样致力于考证,其中也以是否能够“发现”作为 学术性的试金石。如果说真正的思想不等于对既定思想的阐释,真正的学术也不等于随 时代而调整的学术规范,那么,要理论形态意义上的思想,还是西方学术规范意义上的 学术,其意义可能都是有限的。这就将问题的关键揭示了出来:有学术性的研究不在于 引文、出处、关键词这些表面的学术规范,而在于你是否能在前人之说与西人之说面前 提出新说,有学术性的研究也不仅在于你对前人与西人的学说取尊重的研究态度,而在 于你是被这种尊重所束缚,还是能穿越这种尊重建立起自己的阐释。而这种要求,自然 就将学术的严谨、认真、扎实等要求衬托出来了。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学术与非学术 ,而是依附性学术还是创造性学术。如果是依附性学术,那也可能并不优于非学术,也 不优于依附性的思想。
而且依附性学术,也不一定就能导向创造性学术,正如依附性的思想,不一定就能导 向创造性的思想一样。因为这不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而且后者还是对前者的“离 开”。在否定主义哲学中,“离开”就是“本体性否定”,而“本体性否定”,就是对 既定学术与思想的“局限发现”,而“局限发现”,则来自于研究者以特定问题对既有 学术与思想缺陷的揭示,宛如海德格尔发现所有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局限一样,也宛如陈 寅恪以“以诗证史”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一样。这意味着,“本体性否定”其实是有价值 的思想与学术的共同特征,也意味着,丧失“本体性否定”的思想与学术,已经构成了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化的一个难以治愈的症结。在此意义上,学界和思想界所谓有思想 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只是注意到思想与学术结合的生存特性,但并未注意到思想与 学术结合的存在特性。生存特性可以将现成的思想与现成的学术结合,而存在特性则要 求以发明的思想与发现性的学术结合。至少,后者是我们一下子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 境界,也是我们讨论思想与学术关系的最终目的。
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
邓晓芒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 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我感到 有些吃惊,并且颇不以为然,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 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不能否认,80年代的“思想”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人 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自由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西学的大量引进和“美 学热”、“人学热”、“文化热”的兴起,文艺领域中各种“禁区”的逐步突破,固然 反映了时代的躁动,但由于很少进入到深层次的学理层面,基本上是“水过地皮湿”式 地在中国思想界下了几场雷阵雨,除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不断在刺激着人们的兴奋 点之外,思想上总的说来只不过是旧话重提,并没有超出“五四”以来所厘定的“启蒙 ”的范围。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都是“五四”时期早已有人说过了的,甚至还不如 那时说得透彻。人们顾不上去清理历史旧账,相互之间也来不及进行理论上的认真的交 锋,唯一急于追求的是形成“热点”,成为大众关注的中心。学理的浅薄限制了思想的 深化。那个时代许多人惯用的口头禅是“要建立一门××学”,他们忙于发现新领域, 填补旧空白,争当开创者,却并不耐烦为任何一门什么“学”而埋头苦干个十年八年。 进入90年代,知识界面临信仰危机,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只不过是依附 于政治使命或政治前途这张“皮”上的“毛”而已,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 是靠“学术”能够撑得起来的。一大批文化人开始“渴望堕落”,在玩世不恭和游戏人 生中寻求补偿;另外有的人则以“纯学术”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和信仰的丧失,满足 于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到陈寅恪、吴宓、钱锺书等人的书斋生活中去寻求“学术独 立”和“人格自由”的楷模。随着“人文精神”讨论的滥觞和“国学热”的兴起,90年 代的思想和学术都呈现出一种向内龟缩的趋势,与其说是思想和学术,还不如说是意气 和文章。理论兴趣的消解使学者越来越“文人化”,甚至连作家、艺术家也纷纷疏离了 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群又一群靠时令散文、小品文逢场作秀的文人了。
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思想和严肃的学问了。深刻的思想和学问是不分 家的。思想和学问的分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学者不敢表露自己 的思想,只能以学术的方式来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如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 的乾嘉朴学。另一种是思想的狂躁和学术的浅薄导致的分裂,这种例子在中国现代思想 史上特别多,如胡适的口号“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梁漱溟认为自己不是个“ 学问家”,但却是个“思想家”,90年代的轻思想而重学术也属于此列。近年来要求“ 学术规范”的呼吁对治理国内学术界的“假大空”、“脏乱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 多文章的引文出处大大增加了,“学术打假”也造成了一阵接一阵的风波,但这些都还 只是表层次的。我以为,真正的学术规范应当是思想的规范,即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 辨析从理论上清除思想界的陈腐之见,在具有基本思维能力的学者中形成某些共识。这 就要求一方面尊重事实,包括尊重历史事实和尊重当代生活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尊重 逻辑,要努力从历史和当代现实中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并且要能自圆其说。没有相 当的思想穿透力,这两点都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是对单纯事实的接受,也需要有健全的 思想。如“文革”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沉渣泛起”,不同的人对同样 的事实就有不同的说法;又如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究竟是由于“现代化”所导致的,还 是由于不够“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们也是各执己见。这些问题没有学理上的分析和逻 辑上的推断,单凭个人感觉甚至情绪倾向来体会,是绝对解决不了的。
由此观之,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 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就是说,这种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 ”,而只是传统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与西方历来把道德政治思想建立在学术之上 (典型的如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不同,中国传统只有在预先设定了道德政治 立场之后才谈得上学问(“天德良知”)。而中国传统道德又是立足于情感(或“情理”) 之上、以“诚”“信”为本的,更是不容学理和逻辑有自由施展的余地。因此,一方面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只是道德(及道德情感)的附庸,而由于道德的政治化,也不能不是 政治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正由于这一点,这种学术哪怕表面上“独立”了,实质上也 只不过是对其依附对象的暂时的悬置,而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如西方 对形式逻辑的尊重实际上含有对“神圣逻各斯”即普遍理性的信仰的成分)。人们在学 术上所关心的,还是传统儒家经典的训诂正义(如朴学)。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学人眼里 ,一谈“学术凸现”就是“国学凸现”的缘故。研究老古董既可避开现实敏感问题,又 可曲折地标榜自己对待现实的道德态度,凸现自己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 ”,这对于传统型的中国文人的确不失为在现实理想受挫的情况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至于作为纯粹思想探索的学术研究,以及动用纯学术来进行思想上的开拓和突破,则 是中国传统学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所以“思想和学术分裂”一说只不过表明了中国学 人在90年代的一种主观心态,而事实上,道德政治化的思想和依附于其上的学术从来都 没有什么“分裂”,而只有“隐显”之别。这真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悲哀。
我以为,当代中国学人的要务并不是如何(及是否应当)把学术和思想分开的问题,而 是如何(及是否应当)超越旧的学术思想而开拓新的学术思想的问题。所谓“新的学术思 想”,不仅仅指它的内容,而且也包括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不再单纯把学 术看作思想(道德政治思想)的附庸,而是将严格的学术作为思想本身内在的风骨,它引 领思想的灵魂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成为立足于自 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学术是思想的自律,只有自律 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有超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首 先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它当然也包含有道德政治的内容,但又不止于这些内容,而是对 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和审视;因而它是超功利的,但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的,它直接关系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前理解结构”。从历史上看,人类一 切曾经有过的思想在学者眼里都已经成为了“学术”;就当下来说,没有一种学术不是 同时也在表达着一种思想。学术对现实的超越其实是对现实的深化,即深入到了人心和 人性的普遍现实、深入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即“时代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 神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它的前面充满了未知数,是根本不可能用一种 封闭的、内部一片混沌的思维框架(天人合一、天道有常、五德终始等等)来把握的,而 必须精炼我们的思想武器,用一种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锐利而轻灵的逻辑理性来刺穿 现实的表层,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趋向。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范。
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的学术思想,就会迫使我们克服中国人历来健忘的毛病, 而认真研究和冷静分析我们的传统和历史,包括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被动挨打遭受屈辱的 历史,不是停留于义愤和仇恨,而是找寻出规律和原因,不是沉浸于“要是当初不…… ,那将会……”的可笑假设(如同祥林嫂的口头禅:“我真傻,……”),而是力求不要 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样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思想的探讨和成长。黑格尔曾提出哲学史就 是哲学,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我以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 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因为这些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而历史科学根本说来是隶属于哲学的 。 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历史和哲学的关系。只有在哲学的眼光中,历史 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因为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说法,所谓历史并不仅仅是编年史和史料史 ,而是历史的意义的历史,不是外在器物的历史,而是赋予这些器物以意义的人的发展 史,而这些单凭自然科学的实证眼光(通常所理解的“学术”,即客观定量化的“死学 问”)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反过来,也只有在对历史发展的思索中,哲学和深刻的思想 才有可能形成起来,并对历史具有超越性,才能产生真正的“新”思想。所以恩格斯说 ,一个人要想获得哲学的修养,除了学习哲学史以外别无他法。那种自以为不读前人的 著作,只凭一个晚上的冥思苦想就能构造出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说 梦。从智力上来说,今天的人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你能想到的,前人在数千年间必定 也有人会想得到。今人之所以能超越古人,并不在于个体天才的超常发挥,而主要在于 今人有条件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更远、更全面、更深刻。所以,那种天马 行空、师心任性、玄妙高蹈而不留痕迹的“原创性”思想,我总觉得不像是真正有学术 价值的思想。真正站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 起来的。哲学家就是那种善于站在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其他哲学家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 看世界的人,一个人只有达到了这种境界,才有可能提出自己原创性的哲学思想。
学术非思想及思想泛学术
邵建
(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
学术与思想是什么关系?当两者日益成为一个合成词,比如“学术思想”,并同时又成 为学界习用的称谓时,我想,是应该强调一下它们的不同了。
这个不同,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李泽厚先生对90年代的知识界曾表述过这样的 看法: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在客观上已经把学术与思想分作两途。王元化先生许是 感觉到了这种分离状况的非理想,提出了一个主张:学术思想化,思想学术化。尽管王 元化先生希望两者能“化”到一起,水乳交融,但在未化之前,似乎水是水、乳是乳, 思想是思想,学术是学术。
的确,在初始意义上,思想与学术是两样东西,并非一物。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学 术可以是一种职业,思想则不是。所谓学术就是吃知识饭,马克斯·韦伯临终前有两个 著名的讲演,第一个“以学术为业”,这个“业”就是可以吃饭的职业。所以讲演一开 头就从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谈学术与生计的关系。那么一个人是否可以以思想为业呢? 一般不可以。思想只管脑袋不管胃(不但管不了胃,有时还会妨碍之)。申言之,现代教 育体制下的大学,大多按照术业专攻形成相应的系别(以满足不同兴趣的人以后捧上不 同的饭碗),如文学系、哲学系、史学系……,但听说过思想系吗?当然,大学里可以开 设思想史或××思想研究之类的课程并成立相应的机构,如英国的伊赛亚·伯林吃的就 是这碗饭,他是牛津著名的思想史方面的教授但不是什么思想教授,思想也无以教授。 两者不同在于,思想史是把思想作为一个学术对象来研究,它本身属于可以当饭吃的学 术而不属于吃不上饭的思想。因此,学术与思想的一个外在区别,如果从大学建制来看 ,我以为是学术有系,思想无系。
系者,系统也。学术分系,是要求一个人系统地掌握他所研究的这门学科的知识,哲 学系便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知识层面上的系统化,它注重的是知识自身的演化和秩序 ,并且要遵守一定的规范。比如90年代学术凸显的一个标志,就是知识界对学术规范的 强调。思想呢?思想无系也许首先就在于思想不需要什么系统,也没有什么规范。一句 话便足以是一个思想,而学术很难是一句话。并且思想是个动词,具有当下性,不像作 为名词的学术,在时间上已然是一个后于思想的知识对象物了。因此,即时性的思想并 不需要学术上的演进和秩序,它为什么不可以是突发的、跳跃的、单刀直入的、游蛇见 首不见尾的呢?当学术必然遵守循序渐进、孤证不证、文有出处等一系列形式规范时, 思想更多像决堤之水,不择地而流,且随物赋形。因此,学术有“系”,在其规范意义 上其实就是《说文》里的“约束”之意。系统即约束,不约束无以成系统。可以想象取 消知识边界后的各门学科会是什么样的吗?当然,学科的互化与融合是另一层面的话题 。但思想是无所约束和规范的,一旦有之,即使是学术意义上的,思想也告窒息。
如果再行比较一下“学”与“思”在造字上的不同,或许更能看出两者的区别。“學”字构体为三,上部为两手持“爻”(即八卦)状,中部的宝盖即家,下面的子 指孩子。合而谓之,“学”的古义是孩子在家识八卦。那么,“思”呢,这是个上下合 体的会意字。上面的“田”是“囟”即脑门的象形,与下面的心会意,“思”即心脑之 运作。造字之异显示了两者重心不同。学是有外在对象的,如“爻”,其任务就在于识 得它,因此它用力于外。思则不然,它是人在对象缺省状态下的考虑,其用力侧重于内 。当然,侧重于内并非不要对象,只是不以对象为务。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学术是 一种有关外在对象的知识,思想乃出于主体个人所形成的识见?根据这一分殊,今天的 学术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即你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它可以是一个人(如 康德)、一本书(如《存在与时间》)、一个学派(如“法兰克福”)、一种现象或思潮(如 “后现代”),你就它们写出了论文,达到一定水平,便能获得发表。但你假如不以它 们为依凭对象,或者把它们作为泛对象来言说自己,抑或干脆如蒙田“我所研究的就是 我自己”,那么,对不起,你的文章恐怕就不易在学术刊物上发出,至少你的文章在学 科分类上就麻烦。其实这类文字的非学术性是因为作者在文本中陈述的是自己而非对象 ,或者说对象只是个借体。因此,学术与思想的分野,如果就主客对待之不同(学术研 究更多融己于他,思想运作更多融他为己),那么我就有理由认为:“我注六经”是 道问学,“六经注我”是尊思想。
现在,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把思想与学术视为两途,难道学术就不要思想、也没 有思想了吗?非也。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两者应当是 合一的。那么,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不。为什么?如题,学术非思想。什么意思?我的意 思是,学术当然要思想,也有思想,但那是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专业思想,而非人们 通常所说的那种外在于任何专业的思想。所以,在本题语境里,学术思想非思想。是否 可以示例?可以。比如,当年水木清华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他们各自在国学、文学、史学、语言学领域内,哪一个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但 你能因此而称他们为思想家吗?反过来的例子是鲁迅,就以上四个领域而言,鲁迅在学 术思想上的造诣分别不如他们(王国维似除外),但谁又能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如果把学 术思想和思想等同,那么,爱因斯坦因为他的相对论也可号称思想家了。但,如果他被 人称为思想家,却肯定不是因为相对论。
既然学术非思想,那么,人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到底又是什么?这里的计较是,学术及其 思想如果是一种“知识关怀”的话,那么,通常意义上的思想主要是出于“社会关怀” 。相应地,学术及其思想乃是对学术本身或学术对象发言;思想不同,它的发言对象则 是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文化、宗教等,或者说思想是对它们所形成的具有穿透力 的识见。鲁迅是一个思想家,正是因为他在上述有关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辟的见解。比 如历史,又有谁能够像鲁迅那样把一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仅仅读为两种时代的交替 ,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比较一下与鲁迅同时代 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吧,“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古史辨”思想在当时的史学界造 成了多大的影响。但,蕴含在这两种思想背后的文化关怀能是相同的吗?顾颉刚是从史 料层面切入中国历史,他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目的在于弄清中国历史的真相,这无 疑是一种知识关怀。鲁迅关心的显然不是知识,他关心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思想 具有当下性一样,社会关怀也永远是当下的。尽管思想的触须可以伸至空间与时间上的 无限远,果然如它能够的话,但它瞄准的却是当下的社会与人生,是对当下社会人生的 发言与启示。就刚才的鲁迅思想言,问题显然更在于,我们今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因此,什么是思想,什么是学术(思想),在鲁迅和顾颉刚那里分解得清清楚楚。
或曰:既然思想出于社会关怀,但社会科学关注的本来就是分类意义上的各种社会现 实,那么是否可以说,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有关对象的见解就不仅是知识,同时也是 思想呢,比如,政治哲学中对民主的看法。我的解释,它们依然不是一回事。学术、学 术,学得有“术”,作为经验形态的社会科学,这个“术”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所恪守的一个原则,用马克斯·韦伯 的概念来表示,即“价值无涉”。思想呢,思想非但无术(并非不学),而且,在其倾向 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而必然是价值分明的。即以刚才的民主为例,19 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所谈 论的内容显然就不属学术而是思想,其价值倾向甚至在题目上就一览无余。但如果是转 至学术层面上谈民主,按照韦伯,就应当尽可能去做到“价值无涉”了。也就是说,应 当尽可能具体地研究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作方式,包括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 件所能产生的结果,并且还要将它与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总之,一切都是 技术的。技术地分析各种可能性,而并不在各种可能之间寓其褒贬,这就是所谓的“价 值无涉”。因此,价值无涉,还是价值分明,也就形成了学术(思想)和思想这两者互动 的不同区间。当然,“价值无涉”不能绝对化也难以绝对化,因为更多的人习惯于把学 术问题和思想倾向融到一起。于是,学术和思想互相靠拢了,与此同时也带来因错综而 产生的某种不便。比如前段时间有关经济学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争执,其所以说不到一 起,就隐含了说话者是学术维度还是价值维度的分歧。这个问题假如放在我这里,我想 我会这样权宜:经济学是不道德的——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但出于某种社会选择 的经济思想则肯定是道德的,且不管是什么道德。
以上的陈述大致表明了我对“学术非思想”的看法,下面说说标题的另一半“思想泛 学术”。王元化先生提倡“思想学术化”,我有一个看法,一旦“思想学术化”,即化 为学术,那么,思想则不复为思想,而是学术了。因此,思想、还是学术?虽然不是什 么哈姆莱特式的生死抉择,倒也的确是一种选择。我个人如果愿意保持思想原来形状的 话,那么,我的选择可能就不是学术化,而是泛学术。
思想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我上面是以鲁迅为例,属于这一谱系的,大致有法国 的蒙田、德国的尼采、美国的爱默生、俄罗斯的赫尔岑等,他们大抵可称为文人思想家 ,是不把思想往学术上做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相反,他们有意识地把思想做成了学问, 并形成相应的思辨体系,从而使自己成为思想家族中的哲学家类型。这一点,在以善于 思辨而著称的德意志民族尤为突出,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是一流的显 例(大致说来,德意志思想家以思辨型见多,而法兰西思想家以文人型不寡)。两种类型 的思想家本无也不应有地位上的高下,若有,那也在于思想家本人对问题思考的力度与 深度,而不在于他采用了什么形式,比如文的还是哲的、体系的还是碎片的。我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思想的学术化或泛学术其实也就是思想的形式化选择。选择固然是自由的 ,但,不同的选择却会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不同分流。
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是哲学家、还是思想家?如果我这样问自己,那么 ,我的第一感觉,恐怕以前者居多。原因即在于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最终变成了一个自洽 的、圆融的、也是概念林立的学术体系。尤其黑格尔,“绝对观念”是他的思想核心, 围绕它所外化的三部曲,运演周密,体大虑精。但这个体系完全是学术上“做”的结果 。做当然是头尾俱全、逻辑贯通的功夫,虽然黑格尔不难以在形式上做得功德圆满,问 题是,思想不是圆的,做圆了反而会失去思想本有的锐角与紧张。因此黑格尔的理念论 最终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对象而非思想启示的对象。这一点不知是否可以部分地说明海德 格尔为什么后来放弃《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而直接以无学术遮蔽的方式亦即以诗的方 式敞开自己的“思”。比较一下翻阅《存在与时间》与《林中路》的感觉吧,读前者是 问学,读后者则像是在倾听。和黑格尔相比,海德格尔是不是更像一个思想家,同时也 更接近思想的天性呢。
思想泛学术不是不要学术,而是不要使思想化为学术。不要学术,一个村头老叟也能 根据经验冒出一两句睿智的思想,但人们并不以思想视之,原因就在于他的经验形态尚 缺乏相应的知识内蕴和背景。而泛学术不脱离的就是这个背景和内蕴,并且也不企图超 越之。也就是说,以知识为其内蕴的思想,尽管具有一定的学术意味,但却不刻意往学 术上做。这种比较可以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伯林和哈耶克那里展开,伯林 的《两种自由概念》是泛学术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则是学术化的。就哈著而 言,它与其是自由主义本身在思想上的发微,毋宁是一本有关自由主义论证的学术大著 。而思想学术化,很大一部分功夫就是花在对思想的学术阐明上。思想原本是一个锐角 的点,但论证的展开使它扩展为一个面。其利弊在于,思想因其学术化可以显得细密而 周备,但它由一个点变成了面,本身力量也就相对地稀释了。因此,思想之为思想,也 许并不需要在学术上深文周纳,而保持泛学术,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度”。泛者,浮也 。思想之舟以学术之水为依托,它浮于水上,却不吃入水中。因为思想作为当下跃动着 的精神生命,有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最适合它的状态往往是思无定质、言无定形、 文无定体。
进而言,思想既出于社会关怀,它面对社会发言,其倾听者就是整个社会,功能也在 于对社会有所发挥。如果一味转向学术,思想变成了知识,它便从社会退踞学院,成了 学人讨研的对象。当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劲旅的“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以批判为务 的思想流派,60年代欧美学生运动和它(主要是马尔库塞的思想)有不解之缘。可是这个 流派在今天发生了某种转型,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它越来越学院化了。哈氏的“交往理 性”讨论的是社会问题,完成的是学院作业,因而它是一本供学者们在案头作专门研 究的书,其影响力是不太容易穿透学院的围墙而成为一种渗透到时代和社会中去的精神 氛围(当然,所谓社会影响往往有时效性,而学院的影响则更久远)。
如果再比较一下学术转型前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前为社会批判和后为交往理论),在学 术与思想的分野上,我似乎倾向于一种很个人的看法:思想的本质在批不在立。也就是 说,思想的任务就是说破一种被遮蔽的真相。而形成此种遮蔽的往往是长期的积习、历 史的惯性、流行的见解、社会主流的趋同或体制的威权。这就要求思想家敢于以挑战这 一切的姿态把他所认为的真实说出来。学术转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这样,鲁迅是这样 ,鲁迅思想资源中的尼采也是这样。因而后两者之作为思想家,我以为,比蒙田、帕思 卡这类温和睿智而又不乏深邃的思想家显然更具思想本有的锋芒。马克斯·韦伯作为一 个力倡“价值无涉”的学者,当论及思想家的责任时,也认为一个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 责,就是对盛行的观念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并且必要时“反潮流而动”。因此,当思 想对思想本身和思想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相应的要求时,这些要求对学术来说既无可能 ,也无必要。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也就存在着不同的“游戏规则”。
最后,把话说回来,学术与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纯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其可能性 不止一途。你想它们成为什么关系,它们就可以是什么关系。不同的人在它们之间建立 了不同的关系模型。当然,每一种模型都是一种选择。而我所以选择它们的不同做文章 ,实乃出于我个人对既是学术主体又是思想主体的“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体认,本来 应该诉诸文字的,用以支持我上面的分析,可惜给定的篇幅用完了,只好暂付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