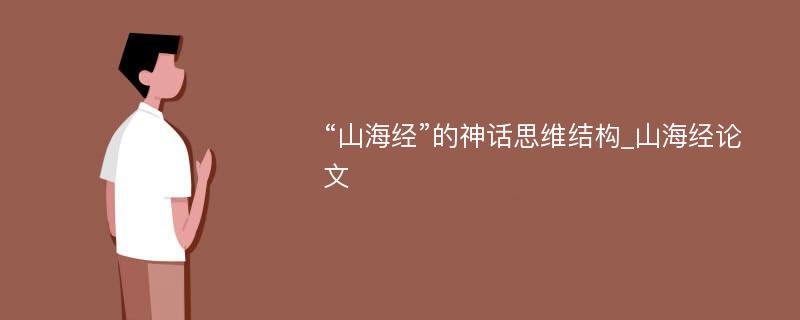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海经论文,思维论文,神话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蕴含着远古文化奥秘的古代典籍《山海经》,以特殊的话语形式、结构形式记录了原始初民朴野的生存状态和智慧真实。本文从神话思维结构的破解入手,对《山海经》独特的表述系统、隐喻结构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基质、特性,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尝试性探索。
关键词 神话思维 生命主体 价值追求 神话风格
中图法分类号 K203
一、引言
人类文明时代的精神创造,是在自由自觉的理性控御下而把思维的矢向伸展到各个领域的。如今,任何一块古化石的剖现,都能引发不尽的话题。但是,面对遥远而古朴的古代神话,现代人的解说总显得隔靴搔痒,掠及皮毛,因为原始神话不独以令人很难理会的语音、词语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而且也以繁复而神异的想象创造了属于他们的独有的精神世界。这仿佛是对今人不无嘲弄的智慧封锁,尽管许多的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对此惊讶不已,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在确信对古神话魅力有所发现的同时,也发现另外存在着一种铁的事实,即原始初民所运用的那种特殊的神话思维方式,阻挡了我们对洪荒年代神奇世界的进入。因此,对我们来说,若要破解远古文化的奥秘,首先必须破解原始初民以神话编码所呈示的奇异的思维结构。
中国的古代神话也毫不例外地把不尽的奥秘封存在这种难以开启的“黑箱”之中。就今所见,散在于中国各类典籍中的神话资料,以《山海经》保存得最为丰富和完整。然而,自汉代以来,虽注家、考释者屡出不绝,却直停留在名物考定、史实比附阶段止步不前。直到近现代,鲁迅、茅盾、顾颉刚、袁珂等人的解说出现,方就《山海经》一书的神话性质、神话轶事资料多所掘发和揭示,然而仍未就其神话思维结构形成系统的论述。与此同时,从近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山海经》的探讨,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愈演愈烈的倾向。有的学者着力否定《山海经》的神话性质,如英山徐显之所著《山海经探原》一书,以“其物非怪”、“其人非怪”、“其地非怪”、“其事非怪”、“其文非怪”等为题,将独特神异的《山海经》实解为一部古代氏族社会的方志,有意消解或否定《山海经》的神话文化价值,令人很难持赞同意见。再就是有的学者抓住神话的一端玄想臆测,如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一文,对《山海经》神话意象的隐喻所指,以近似离奇荒诞的结论,试图印证古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生的奥秘:轩辕之国,即现在的匈牙利;英格兰西部的巨石阵,从《大荒西经》能找到何人、何时建造的答案;古罗马人源于东方来的一个民族,而且极可能是黄帝家族;该文甚至引证古希腊文明的缔造者正是启,是启建成了辉煌的克里(启)特(代)文化……[①]笔者认为,对《山海经》的研究,还是应该本着文化科学的态度,以神话为突破口,通过切合原始先民神话思维方式的文化阐释,才能做出科学而准确的言说。
以神话思维结构的揭示为破启《山海经》文化奥秘的入口,其深在的意义在于从根本性质上认定《山海经》是一以神话思维方式完成的古文化文本。而神话思维方式对于初始民族文化创生的意义,又在于以看似悖离文明的非逻辑的话语形式表达了该民族朴野的科研成果与文化,并由此而反映该民族真实朴野的生存状态。思斯特·卡西尔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没有功夫虚构编造,没有功夫人为地作假或误解。谁若了解到他的神话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这神话对那个民族所施加的内在力量,以及其中表达着什么样的内在性,他就不会说神话是由个人虚构的,正如语言也不是个人虚构的。”[②]《山海经》作为神话思维形式的产物,恰恰因为这种神话思维的本真性质,才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中华民族远古年代生存、命运、生活情态和精神搏动的真实。这种真实绝非机械地、僵硬地从地理学、历史学或什么方物志学之类考定出来的,又难以确切验证的所谓与史事、民族或当今某地名形成对应的真实。而是说,《山海经》通过神话思维形式所能记述、保存的真实,是真正把远古种族、早期人类的生命整体——他们有声有息的希望、恐惧、呐喊及其涌动着欲望、情感的活动史——给予淋漓尽致地呈现的真实。因此,如果说,要想真正揭开蕴藏在《山海经》中早期人类文化之谜,就必须深入到其神话思维结构的深层进行探测,而且也只有进行这样的探测,才算是以最切合《山海经》的方式在研究它,阐释它。
二、《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显层结构
《山海经》作为文化文本,其最明显的特征是神话思维形式贯穿了全书的各个部分。这并非说此书所有的内容都是神话,而是指先民与其生命存在最实质性的内容隐匿在这种神话眼光、神话表达的结构之中。
综观全书,以《五藏山经》最为朴野。它大约反映的是由狩猎、捕捞业向农耕业过渡时期的先民生活。因之,对山地形势、动植物性状,初民们颇能具说,且赋以浓郁的想象色彩,使触及到的一切朴朔迷离、奇幻难测,而对农耕生活本身,则因尚不稔熟或觉平而无奇而甚少寄情,只是在后来涉及到人事才人格化地予以敷衍,演释。[③]总计《山经》所叙5370座名山中,最令先民精神上振奋欣悦、恐惧不安、疑念丛生的是那些尚难把捉而寄以灵性的神怪之物。《南山经之首》这样叙述道:
南山经之首曰雀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谜。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猩猩,食之善走。丽麘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在这段一百余字的行文中,备述了山招山的位置、矿藏、植物、动物和水流。其文字简洁,结构组织严密。显然,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期之后才能写出的手笔。《周礼》云:“惟王建国,辨正方位”,“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泽、丘、陵、衍、原、隰之名物。”可见,此段文字之方位辨识,名物所记,与周朝设官巡察、记录风俗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极可能是在这种政策、情势推动下形成的文体。但即便是官方搜集、记录,虽不无加工,也基本是按述而录,以存遗风。所以,我们可以从对祝余草、迷谷树、以及猩猩的描述,窥探到原始初民的观察、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生存心理。每一种动植物的名称,在先民那里最初都包含着生动的神话想象。“祝余”草奇异的抵饿功能、“迷谷”树虽枝干是黑色的,却又能光照四方。朴实的自然物被神奇地赋予了超自然的性征。在这些记述中,现实的动物、植物成为非现实的主体本质力量的客体化存在。主体实际上以能动的创造否定了现实的环境、具体的感知对象,以为生存的困窘、难堪谋求出路。“神话所叙述的故事,终竟是遥远的洪荒年代发生过的事件。神话的否定,就意味着现在的否定,也就是说,现存的秩序是神话描述事件的必然发展,否定它,就等于否定了现存秩序最原始的基础和前提。”[④]于是,所有的希望、恐惧和想象真实而具体地得到了表达,并且并不存在与“肉体感知”无关联的所谓浪漫想象或所谓抽象的永恒的生命本质。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素朴的神话形态了。《山海经》大量的篇幅就记录了这样的神话。如果说,这种神话将人类早期祖先情感、体验和想象力实现了不自觉的投射,那么,由自然的描述进而到人事的描述,也就在不自觉中实现了古华夏神话系统绚丽而多姿的独特建构。
古华夏神话系统在《山海经》中得到典型的保存。在《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中,自然神和人格神谐和并存。它们不像希腊神话那样,神灵们像熟透的果实,秉赋着文明进化充分的水分,不但与人同形同性,而且还理性化地生存在抽象的空间——奥林匹斯圣山上,成为与人世真正隔离的天神。而《山海经》中的诸神,多寄寓于山水,拥金抱玉,或寄身秃岭荒野,他们一方面形容可怖,另一方面总是在大地上表演种种作为。其中,作为最高的神祗,如太皞伏羲、炎帝、黄帝、蚩尤等,也一应在大地上发挥他们的威力。《西次三经》写道:黄帝以昆仑山为都邑,里面充满能吃人的野兽。每当天下发生大事,黄帝就从这里派诸神出战。著名的黄帝与炎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进行的: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令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龙。
——(《大荒北经》)
魃是极少有的一位天神。在这次战争中,叙事主角是参与战争的诸神,不像希腊神话中那次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是神操纵着人进行战争。
马克思曾指出,处于野蛮时期的人类,已发展起来许多高级的特性,如个人尊严、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勇敢等“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点,但和它们一同出现的还有残酷、诡诈和狂热。在宗教领域里发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对人格化的神灵和伟大的主宰的模糊观念。”[⑤]马克思所阐明的这类原始神话观念,在《山海经》中可以说一应俱有。
神话观念的演化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山海经》或由于记录者从地理方位切入杂糅一体的缘故,使得这种演化过程被表述得非常模糊,以至当行文进入人格化的神话叙事时,起先的自然神,包括那些刻板的名物记录,似乎陡然增添了灵气,成为烘托、强化人格神性和作为的氛围、环境因素。《中次十二经》的片断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鸡鼓。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湖,出入有光。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祖梨、桔摇系,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气韵何其饱满的词句,烟笼雾罩般将神灵的怪异给淡化了。至此,《山海经》的神话表述似乎又别添一层诗意的描摹,从而深化了神话的隐喻色彩。如“神灵操蛇”,据有关学者的考证、阐释,蛇在原始文化中是极具妖魅风情之物,在神话中它们往往成为性或性欲望的指代。这样,当神话通过其表述,能将原始先人的生命本能也情意化地予以展示时,则原始先人的生命性情就获得了真正完满而真切地表达。
透过《山海经》朴野的记述,可以窥测到原始神话的原初面貌及其演化形态。当我们面对这样一部古老而珍贵的神话典籍,似乎不需要更多的推想,也不需要什么附会,就能够感受到进入到神话思维固有逻辑里去。在以神话的固有逻辑去释读《山海经》时,一切摇曳多姿的神话意象会自动勾连起来,荡成一曲美丽而奇幻的古文化乐章。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对那种认为中国神话不具有完整系统的观点做一讨论。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神话结构特色,不能用他民族的神话体系来硬套此民族的神话,比如希腊神话,马克思称为人类童年期发展得最完美的神话。肯定希腊神话的成熟只是肯定了某种神话体系类型,也并不等于否认了中国神话的系统性和体系性。其次,曾经有人以中国神话生存土壤的贫瘠而认定中国神话不具备美丽而富足的色彩,其实,中国神话是以主体性情的充分展示而呈现其诗意般的绚丽多姿的。并且不同的构成因素在中国神话中往往是在互衬互补中并存谐和起来的。这些从《山海经》的表述就可得到明证。因此,可以说,中国神话就其想象力度,情感色彩以及时空跨度等方面,比之希腊神话、埃及神话等毫不逊色。只不过由于后人辑录时修饰或加工、改窜,令我们无从辨识神话符号系统原初的能指和隐喻所在罢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要加深对《山海经》这一典型神话文本的开掘与研究,以求能够真正揭示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隐喻、象征意义。
三、《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深层结构
作为古华夏文本,《山海经》不仅具有独特的神话思维表述系统,而且其神话话语的深层所指也是独特的。我们把隐藏在《山海经》表述结构之后,关切到神话思维之价值本体、审美本体的内在构成及其组合关系,称为《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深层结构。
一个民族神话思维的深层结构,乃是该民族原始形态的哲学、宗教、道德、美学观念的最初的自主性建构。因此,有关深层结构的构成因素与组合方式,就不仅共时性地反映在该神话的神灵性质、神话意象、图腾和禁忌的表述当中,而且历时性地反映在该神话演变进程中的风格、气质和韵味等方面。对于《山海经》这部神话文本而言,细致地掘发上述每一种因素都是必要的,但本文限于篇幅,只想着重就规定《山海经》神话思维深层本质的两个基本特征做一阐述,即《山海经》的价值追求的精神性问题和神话风格的悲剧性问题。
1.精神性的价值追求
《山海经》通过其神话思维方式运作的独特创造,强烈而饱满地表达了华夏先民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尽管真、善、美的观念,在他们的期待和意向中多表现为混沌性的主体感觉,但借助于想象力媒介的外化作用,便使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生动地具体到有生命的神话细节和轶事中了。综括言之,《山海经》主要以神话形象的辩证创造,凸现了主体生命的精神性超越,又以神话经验结构的伦理性、道德性,把原始民族崇高的精神本质充分地渲泄了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山海经》对生命主体的神话塑造隐含着鲜明的善恶价值判断。并且,这种判断不是孤立于某一方面、某一特质,而是融聚了生命体验的辩证的判断。从贯穿于《山海经》各部分的思维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感知主体,能够确切辨识方位,识察名物的性状、功能的认识主体。对此,如前所述,大概与进入文明期后后人的思维、意识渗入有关,再就是先民思维本来就具有倾向于科学认识的一面也未可知,因为对此颇有一些学者是持积极态度的,列维—斯特劳斯就说:“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作有用或有益的,正是因为它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种思维主体,即以神话方式创造的生命主体。在《山海经》中,不同的生命主体被在或肯定或否定的辩证处理中,显示其或善或恶的本体存在价值。“精卫填海”神话通过炎帝之女的“游于东海,溺而不返”隐喻了一层外在自然对生命本体的否定,但女娃又化而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丁石,以堙于东海”,又通过精神志向的外化肯定,使生命本体得到精神性的价值超越。“夸父逐日”则是主体精神外张的另一典型实例。对于这一则神话,《大荒北经》和《淮南子》都有批判其不自量力、乘情悖理的口吻,但《海外北经》则以诗意般的情志转化,肯定了夸父的顽强意志和真挚热情: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邓林”即桃林,足以解渴之林。这里夸父逐日似乎并非不可,只是因为所饮不足解渴,才致半道而死。而夸父变形为桃林,则将未遂之志寄望于后来者,表现了对其行为价值的充分自信,此外,“鲧腹生禹”、“刑天舞戚”,都含有表面上肉体死亡,实质上其志未泯的底蕴。而且这些神的死去,都是精神再生的必要环节,是生命新生的必要前奏。因而,当述及禹从鲧腹跑出来,帝也为之坚强不屈的斗志所感动,“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与这些追求积极的精神力量的神不同的,是那些凶残、阴毒、图谋私利的恶神、丑神,对于他们,《山海经》是以帝的惩罚为终局而间接地否定了其存在的价值。对丑与恶的否定也就是对美与善的肯定。在丑恶一类的神中,相柳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本是共工的大臣,长着九颗脑袋,分别在九座山上吃东西。凡是相柳经过的地方,便成为沼泽和溪谷。后来禹受命杀死了他。相柳的血流出来,遍地腥臭都不能栽种五谷。另如鼓的被斩也说明丑恶的神只能给人类带来祸害:鼓被杀后仍不甘其灭,化成鵕鸟,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大旱灾。创造神话的先民把世界上发生的灾难、病患都归罪于这些丑恶的神。从而,那些并没有直接述其由来的、却给人世带来不幸和灾难的怪异之物,都是一些丑神、恶神的化身。如蛊雕,穷奇,都是吃人的动物;熟湖、毕方、合窳等,不是给天下带来大旱、火灾,就是带来瘟疫。几乎天下可能出现的病患、灾难,如水肿、痔疮、梦魇、饥饿、火灾、涝灾、旱灾……无不与丑恶之物的侵扰密切相关。《山海经》以神话形态的人格神降而为动植物神的转化,强烈地否定了丑恶的力量,愈加衬托了善良而美好的动植物(自然神)和人格化的神的精神威力。
其次,对于神话经验结构的伦理性、道德性,我们也应予以揭示。无疑,神话所显示的伦理、道德品性是强化神话精神性价值的重要因素。在《山海经》中,朦胧的伦理、道德标准是和排斥享受、谋取私利以及性欲望的隐晦、回避直接相关的。由于原始生存环境的险恶,决定了神话创作中对那些为天下人民奔走、辛劳的神,倍加褒扬,甚至神话伦理的标准也渗透到心理气度的衡量方面,越是有气魄、有肚量、胆量者越受推崇,胆小、心胸狭窄则甚受鄙夷。如刑天虽然被帝砍下头,仍然“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再如“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前者是对大无畏气魄的礼赞,后者是对胸怀博大者的称美。从上述释例,显然可见原始神话中的伦理、道德标准与文明时代的大有差异,但也可看出维系某种普遍的善与美的端倪。至于性欲望的避忌,似乎在中国神话中是一突出的特征。虽然生殖崇拜是原始崇拜中最普遍的一种文化形态,但华夏古神话都以隐晦的意象暗示这一点。或者索性以其他意象巧妙避开性接触、性过程的问题。前述操蛇之神,当是生殖崇拜的隐喻。但在述及人类由来时,却连这样一种暗示也避开了。如女娲是传说中造人之神。《说文》解为:“娲,古之神圣也,化育万物者也。”《山海经》提到女娲,只说有十位神是她的肠子化成的。并无女娲为伏羲之妹及后来兄妹结为夫妇之说。后来《风俗通》将女娲造人的过程,完全变成巫术性的仪式:“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及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至此,似乎性欲望的避忌也成了伦理性的自在组成部分了。而在希腊神话中,诸神风流多情,欲壑难填。由此可见,《山海经》神话思维甚至在经验、心理的深层构成方面,也突出了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尽管这种追求颇带有意识朦胧的生存禁忌、体验性,却也是格外鲜明而撼动人心的。
2.悲剧性的神话风格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呈现,这种风格呈现是由内在质的规定而影响、渗及到外在的表述层面的。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对神话最敏感的接受方面,恐怕就是由神话内容和形式之统一所达到的这种风格影响力了。我们今天在谈论中国文化的特性和风格时,常常为何以形成某些稳定的特性而苦思不解,例如,中国文化何以既富有浓郁的主观性,又具有伦理、功利的现实性?中国文化何以既重视生命价值的超越性实现,又在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上愈来愈脱离感性生命,而趋向于普遍的、规范化的情感和追寻玄虚飘缈的哲理呢?这些悖论性的文化存在,固然与现实、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深切相关,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忽略中国早期人类神话风格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在我们对《山海经》神话思维所显示的精神性价值追求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还必须对其风格构成的悲剧性韵调有深入的省察,因为这一点也是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希腊神话中只是包容有某些悲剧性的片断——如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被罚以及宙斯、赫拉等出于怨怒、忌妒而对其他的神或人进行的惩罚性举动——不同,中国神话的悲剧性风格,反映在《山海经》中不是局部的,而是总体的。似乎可以说,《山海经》就是一种悲剧性神话。对此,我们可以从主体存在的悲剧性、生存体验的悲剧性和生命过程的悲剧性这几方面分别做一阐述。
(1)主体存在的悲剧性。
《山海经》神话思维所表述的生命主体所面对的是真正属于远古洪荒年代的大自然。无穷无尽的自然灾难对于萌发了混沌性生存意识的原始人来说,实在是过于强大而难以抵御了,因此,我们的祖先不得不把外在的自然以及自身的存在,都交付给异常怪异的想象创造。这样,生命主体似乎在怪异的想象中赢得其自身的存在地位,但这种存在却是以崇拜神灵为前提的,因而只能是被动性的、悲剧性的。譬如作为百神之主的黄帝,似乎具有操纵生杀之权的主体性,但他居住的都邑本身就是食人鸟兽肆虐之地,甚至连他自身的形貌也是混沌莫明的:
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
——《西次三经》
“帝江”,毕沅云:“江读如鸿”。《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曰:“帝鸿,黄帝”。这说明古华夏神话朦胧的主宰观念,也是依存于自然而略具形貌的混沌性主体存在,连最高的神都不能免掉为自然所限制的悲剧性角色,其他神就可想而知了。
(2)生存体验的悲剧性。
最令原始人刻骨铭心的是他们对生存的悲剧性体验。一方面,不仅物质现实环境充满了威胁和灾难;另一方面,他们的想象也制造着形成威慑的神灵。对他们来说,任何能够感觉到的自然物都可能对肉体造成直接的影响和危害。因而,虽然他们以崇高的气魄试图改变这种现实,创造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每一种想象创造都饱含着悲苦无奈的体验。日光的暴晒,飓风的袭击,毒蛇猛兽的扑咬,饥饿和病患……这些接踵而来的生存考验,使他们的想象不得不过分地夸张丑恶的力量。以致尽管有代表善良意愿的神为他们驱赶旱魔、杀死毒蛇猛兽,但这些善良的神似乎并不能够改变大自然的整体威胁。在这样的体验中,原始人以对死的祈求作为最大的生存代价,渴望能够死后幻化成像精卫鸟、天狗、狡、类(自身具备两性器官的一种动物)、鹿蜀(一种佩其皮毛宜于繁殖子孙的动物)、猩猩……等那样。抵御凶灾、生死顺利、有使不完的力气。然而,这毕竟是想象性的寄托,是对象性的、自欺性的一种虚幻存在。当先民们愈是走向文明,就愈是能清醒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就愈是饱尝悲剧性的体验。这样,在我们对《山海经》解读时,也就很好理解,何以丑、恶、怪、凶一类的动植物神和人格化神,在数量上,甚至形状、阵势上似乎一点也不比善良的神弱小。这种悲剧性体验发展到后期神话,就不能不以抽象的善的观念来替代具体的神,《南次三经》云:
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德”、“义”、“礼”、“仁”、“信”这些抽象观念,显然是人类进入文明期的产物。辑录神话者把它们掺杂在原始神话中,以求扭转神怪、丑恶逼压、威慑善良心愿的氛围。但因为这种描述是抽象的,在具体而充满活力的原始想象中,显得十分单薄而无力。因此,《山海经》中这种漫延的悲剧性生存体验必然作为一种文化基质而积淀到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以致宋代苏过撰文《记交趾进异兽》这样悲叹曰:“麒麟凤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凤矣,必复生虎豹蛇蝎,苍苍者或自有说。然天之生麟凤也不数,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于深山大泽间,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凤凰,高飞远引,不一游于世也。”(《斜川集》)这可以说是文明时代的人对原始人悲剧性生存体验的一种延伸,但后世文明人尚可以寄望于有道明君,原始人只能靠自己的搏击来赢得生存,由此更反衬出《山海经》中生命悲剧体验的深刻性与强烈性。
(3)生命过程的悲剧性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创造了一种生命过程的悲剧性轮回。轮回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浸染颇深,但文明时代的轮回以人投胎再生为主要形式。《山海经》中,生命的轮回体现为由植物神升华为动物神,进而人格化神。当人格化神经历了“死”的过程之后,又复现为动物或植物。或许由于《山海经》记录整理者的疏漏,我们难以看清植物神到动物神的演化痕迹,但原始人赋以植物、动物的功能、灵性,却是被人格化神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在这样一种神话式的轮回圈里,真善美的毁灭体现为生命过程的暂时终结。只有极特殊的情形,是人格神死后复转生为人格神,如鲧之生禹。但众所周知,禹乃是非常切近于文明时代的最后一位人格神。神的毁灭及轮回性动植物的幻化再生,表明了原始人对生命的悲剧性意识已达到超越肉体存在并对精神性存在有所醒觉的层次。但正如刑天断首不忘抗争,共工怒触不周山以求拚死一搏,都是珍重肉体性生命存在的一种反映一样,原始人对幻化了的动植物神,寄以人格神的灵性延伸,使得在描述这样一种生命过程的转化时,传示于人的悲剧性氛围、情调也更加浓重了。如果我们由此说,原始人尚不知道这种幻化性的再生正是一种永恒性的追寻,那么,他们对神性再生的愉悦,与其说是一种主体本质力量的想象性投射,不如说是主体本质力量对悲剧性境遇拥有深彻感悟后的一种缠绵而无奈、恐惧而压抑的状态中所反弹、跃动的又一种精神奔泻。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为推崇《山海经》神话思维所传达的那种崇高的内在品格。这种内在品格赋予了中国神话以悲壮、绚烂又不无忧郁的复杂情调。而最终作为悲剧性风格的总体归结,是令我们认识到古华夏神话在人类远古文化之林中所具有的鲜明主体性、伟大的生命力度和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意义。《山海经》作为这样一种精神文化创造的典范文本,无疑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格外珍贵的瑰宝。
注释:
①参见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发表于《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该文引述很多资料,对《山海经》进行实证性研究。本文认为《山海经》的主要价值仍是其独特的神话文化价值,故对实证性研究持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意见。
②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6-7页。
③对《山海经》各部分的神话真实性问题,笔者赞同刘大杰的观点,认为《五藏山经》出现最早,较为朴野可信,故作为主要的论述资料凭据;另外,也综合袁珂认为《荒经》以下五篇保存了许多原始神话资料的观点,把《荒经》作为重要的神话资料依据;而对《海外经》《海内经》则慎重择取而用,尤其对有关域外种族神话,则视其文为后人的补辑,一般不予引证。
④(日)祖父江孝男等:《文化人类学事典》(乔继堂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59页。
⑤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⑥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版,第13页。
标签:山海经论文; 神话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神话体系论文; 山海经异兽论文; 神话创造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黄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