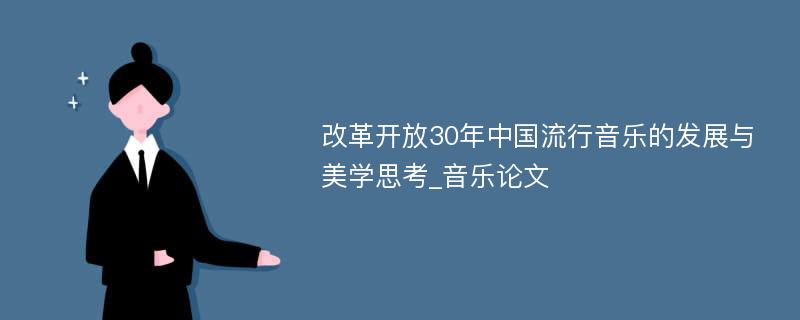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及美学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发展状况论文,流行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行音乐有着独特的美学主张和美学品质、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它不仅给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理念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不仅使中国的音乐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使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现出中国音乐自我更新的活力和张力。当然,作为一种最具实验性、争议性的先锋音乐,流行音乐的确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行音乐经历了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流行音乐和大量流行音乐作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流行音乐的发展更为成熟且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为我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和繁荣
(1)改革开放初期抒情歌曲的复兴。首先获得群众推许的作品为《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它们继承了50-60年代抒情民歌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旋律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代表了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由“十五首抒情歌曲”奠定的写作风格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主要流派,并于80年代前期居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活跃的作曲家既有“文革”前期及中期已蜚声乐坛的唐诃、吕远等,又有“文革”中崭露头角的王酩、王立平、施光南等。其中,王酩的歌曲创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到以后的《知音》,都显现了处理抒情题材的能力。他的旋律委婉动人、一波三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王立平在《太阳岛上》的创作中已带上了流行音乐的节奏因素,此曲的演唱也使郑绪岚一举成名。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创作的《乡恋》,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嗣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此时的抒情歌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而是处于“文革”之前的群众抒情歌曲与80年代中期的流行歌曲之间的一种过渡体裁。与抒情歌曲复兴相对的是进行曲创作的衰退,除1981年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贺东久、任红举词,朱南溪曲)外,直至80年代末几无其他成功之作。
(2)港台歌曲的传入和内地流行音乐的兴起。随着改革开放,外面的东西开始不断涌进国内。音乐上人们最先接受的便是港、台的流行歌曲。伴着录音机、卡式磁带的大量进口,这些歌曲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它们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校园歌曲作为台湾年青一代流行乐创作向现代过渡的成就也影响到内地校园歌曲的产生。如《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韩先杰词、谷建芬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等。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1980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广州茶座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为流行音乐演出之先行者。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郑绪岚、远征、苏小明、吴国松、任雁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王洁实、谢莉斯二人则以演唱校园歌曲而成名。
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流行音乐也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84年始,当时活跃的流行乐坛上的新秀有郭峰、陈哲、甲丁、雷蕾、温中甲、徐沛东、伍嘉翼、董兴东、张伟进、刘小林、士心、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何建东、徐东蔚、陈小奇等,中年一代则有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傅林、孟广征、王积福、张丕基等,一时间可谓人才济济,显现出巨大的创作实力。与此同时,朱逢博在上海、李谷一在北京分别组建了轻音乐团,谷建芬则组建了“声乐培训中心”,东方歌舞团也多方罗致流行音乐歌手。这些活动均刺激了内地流行音乐界,使得流行音乐成为具有控制市场实力的音乐文化,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多方位的尝试和走向繁荣。“港台风”持续了较长的一个时期后,人们变得冷静了,听久了港台歌星的嗲声嗲气,洋腔洋调,已不满足歌曲中的风花雪月,柔情蜜意,于是开始寻找自己的通俗音乐创作的出路。这样“西北风”便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我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心愿》、《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以及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曲》等。“西北风”代表了自邓丽君以来的阴柔的演唱风格的转变,在音乐观念上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南方及中原音调为主的我国音乐创作现状以及前几年流行音乐界“阴盛阳衰”现象的一种逆反。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泄色彩;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
继“西北风”之后,一批知青歌曲纷纷制作出版。这些歌曲多表现思念亲人、惆怅、失意和怀旧的情绪,具有浓重的俚俗风格,且大多出于业余作者之手,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作为赶浪潮、抢销售的盒带产品,商业化的粗制滥造又抹掉了这些作品本身所可能具备的特点。接着,苏芮和齐秦跨海而来,占领的是中学生市场,同时也得到很多青年的喜爱。其风行的原因除去明星崇拜外,还在于其摆脱了早期港台流行音乐的模式,更多吸收了欧美现代摇滚乐的因素,音乐制作更加精细,也更贴切地表达了青少年的文化心态,因而受到年青一代的欢迎。
此外,1989年间,“卡拉OK”这一新的娱乐形式由日本引入我国,并迅速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发展。这时,许多作者已沉下心来做不同的尝试、摸索,作品风格渐趋多样化。歌手中刘欢、毛阿敏、韦唯到了鼎盛时期;范琳琳、那英、张可、朱哲琴、谢津等知名度渐高。听众的喜好也逐步分化而形成不同的欣赏群。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界新民歌、摇滚乐、流行乐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流行音乐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2.20世纪9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新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徘徊,从90年代起,由于著作权法的实施,国家对引进港台音带的数量作了限制,这就影响了那些靠做引进版生意的音像公司的生计。客观环境的变化,使得内地各音像企业不得不重新规划各自的生产流程,开始重视创作、重视培养自己的歌手和制作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如广州的杨钰莹、周艳泓、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上海的王焱、甄凌、石云岚等。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在开掘的深入、描摹的精细上还未达到港台歌坛鼎盛时期同类作品的水准,但已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费市场的局面。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艾敬、朱桦、田震、屠洪刚等一批在8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又以新的面貌重登歌坛。歌坛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各界知名人士跻入其间。
90年代流行音乐的表现题材虽仍以情歌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更大的拓展的作品。艾敬的《我的1997》、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和何勇的《钟鼓楼》等城市民谣真实贴切地表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张楚的《姐姐》、腾格尔的《父亲》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社会底层。《弯弯的月亮》在赞颂家乡的美丽的同时,也表达了“今天的故乡还唱着昨天的歌谣”的惆怅。《同桌的你》、《露天电影》等冠以“校园民谣”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怀旧情绪直接反映出作者对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社会的思考,是内地流行乐坛中出现的新潮流。《涛声依旧》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韵。黑豹《别去糟蹋》表达了反对暴力、呼唤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想。
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也推动了音乐体裁及表现手法的发展与创新。《纤夫的爱》等以传统民间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继承了80年代的新民歌的传统,并在歌曲的流行化方面进行了新的处理。9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传统戏曲唱法演唱流行歌曲的所谓“戏歌”的热潮,比80年代中期流行的那种戏曲民歌加上电声乐队伴奏和迪斯科节奏处理的“大联唱”又进了一步。“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将京剧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中。郑钧的《回到拉萨》吸收了西藏民间音乐的因素。小柯、章鹏、姜昕等人的专辑试图融合多种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严肃音乐及民间音乐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还出现了流行摇滚(《黑豹》)、重金属摇滚(《唐朝》)、庞克摇滚(《解决》)等摇滚乐专集。
随着流行音乐被社会各界的广泛接受,舆论界对流行音乐的关注焦点也转向了对流行音乐行业的发展趋向和具体作品的评论上。如对流行音乐的“包装”问题和歌曲《小芳》所反映的道德伦理观念的讨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流行音乐的文章,反映出专业音乐理论工作者对流行音乐的关注。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流行音乐作曲专业,其他的高等音乐院校也相继开设电子音乐和音响导演专业,培养流行音乐的高级专门人才。各种传播媒介对流行音乐的扶植也有所加强。张宏光、三宝、赵光等由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的青年作曲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勇、郑钧、“指南针”、“轮回”等新一代摇滚乐手和摇滚乐队显示出了巨大的创作潜力。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高晓松、洛兵、沈庆等从校园歌手中成长起来的创作者日益引人瞩目,成为内地流行音乐创作队伍中的一支新军。
90年代的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唱片公司对流行音乐的商业化属性的认识及相应的操作程序的掌握有了很大的提升,创作人员对流行音乐的探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流行音乐在强调娱乐功能的同时,对表现当代生活和社会心态、反映人民心声方面有所忽视,在强调专业化的“包装”、“制作”的同时,对于流行音乐的民间根基的重视和开掘上更是普遍滞后。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运行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完善,急功近利的心态依然表现得较为突出。
3.21世纪初——网络歌曲异军突起
21世纪,随着电脑的普及和手机彩铃下载业务的兴起,网络歌曲开始异军突起,流行音乐的制作也更加商业化、世俗化。2000年,雪村的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网络上热了起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网络传播对音乐的帮助。2004年,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唐磊的《丁香花》、庞龙的《两只蝴蝶》,也在网络上火起来。其中杨臣刚《老鼠爱大米》更是一夜走红,直至走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红地毯。此后,以通俗、轻松、幽默为特点的网络歌曲在国内乐坛风起云涌,大量平民歌手通过网络,把自己和其所创作的歌曲推向社会。
从2005年开始,又有不少网络歌曲脱颖而出。《老婆老婆我爱你》、《你到底爱谁》、《月亮之上》、《秋天不回来》、《香水有毒》等歌曲先后成为生活中的热门歌曲。它们虽不是经典的,但却是优美的,它们就像美丽的蝴蝶一样,短暂而美丽。很多网络歌手也频频出现在各大颁奖典礼上。
网络歌曲在内容上与传统的流行音乐并无区别,只是由于通过网络传播,所以不需经过唱片公司、经纪人、音乐人、编辑等。它们的成败全由网民的点击率决定,具有反精英化、本土化的特点,代表了平民的审美观,具有源于民间的生命力。但由于网络歌曲的门槛很低,网友原创、翻唱、改唱的歌曲都可以传到网络上去,从而产生了另一产业链:翻唱音乐网。网络歌手大批涌入翻唱网寻找属于自己的成名机会。事实上大批网络歌手的涌入并未让网络歌曲繁荣。令人遗憾的是,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网络歌曲却迅速滑向了令人不安的低俗之中。
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网络歌曲就从备受欢迎的“大米”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流于低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网络歌手的“一夜成名”刺激了很多人,于是泥沙俱下,低俗之风泛滥。同时,互联网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实现音乐梦想的机会。但是,这些网络歌曲往往倾向表面化的个性标榜,而缺乏对生活内涵的发掘。更糟糕的是,为了哗众取宠,一些歌曲还采用侮辱人格和打情色擦边球等“出位”的做法,导致格调低下之风在网络歌坛蔓延。有些歌手为了达到一夜成名的目的,把恶搞当幽默,毫无道德感和艺术责任心;一些专业网站和手机彩铃制作商则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道德,传播劣质作品。上述种种恶行导致网络歌曲的集体名誉受到损害。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流行音乐的美学考量
1.中国流行音乐的美学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音乐已走过30年的坎坷风雨路。在这个时段中,它以大众娱乐文化的姿态和极为张扬的个性颠覆了“文革”中概念化、符号化的畸形的音乐创作理念和表演理念,瓦解和摧毁了以往的音乐流派的界限及创作与表演的原则,改变了人们的音乐审美理念和审美习惯,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品质及形式的音乐流派。
(1)审美形式的多样化。同其他音乐流派相比,流行音乐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多样性。在它的领域内,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式样的音乐并存:既有原创音乐又有改创音乐,既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又有外来音乐与本土音乐的融合,既有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融合,又有不同门类音乐的融合,使得以往相对单调的音乐变得丰富多样。关于这些,我们从歌唱家杨鸿基用美声唱法演绎通俗歌曲《再回首》、成方圆用通俗唱法诠释美声经典作品《月亮颂》、刘欢用京剧的韵味去演唱《情怨》以及崔健的摇滚民歌中便能感受到。此外,诸如“唐朝”、“花儿”等风格各异的摇滚乐队和音乐组合;“港台风”、“校园民谣”、“西北风”等此起彼落的声音;藏族的“高原红”、朝鲜族的“阿里郎”等少数民族的音乐组合及腾格尔、容中尔甲等少数民族歌手,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流行音乐的多样化。
(2)审美内容的人性化。流行音乐改变了以往的音乐审美立场,淡化了音乐的教育功能,走上一条人性化的路线。从平民百姓的内心焦虑、信仰困惑到对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对自我的重新审视等,它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人性的每一个层面,尤其是那些多如牛毛的爱情歌曲,虽说有些泛滥,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行音乐的确在贴近人性。
流行音乐在许多时候表现的是更重大的人性问题,显现出它对音乐的崇高性和神圣性的理解与实践。从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等,都在流行音乐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不仅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及意识形态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而且还体现了对自身生存状态及生存环境的审视与思考,使得流行音乐有了更宽泛的人性色彩和文化价值。可以说,流行音乐的人性化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转型期的时代特性,它音乐化地表达出商业社会中的人们不再以集体的目标或信仰来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转而关注当前的自我价值和自我生存,代之以更多的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我行动及自我实现。
(3)审美对象的大众化。随着电台、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流行音乐覆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流行音乐的这种空前的大众化,既是其存在的基础也是其生存的方式,它最终的结果之一就是摧毁了由文化地域不同、文化内容不同及音乐审美观念不同所造成的障碍,使其成为大众化的音乐形式,进而使大众成为真正的音乐审美主体。
流行音乐的大众化还体现在:由纯粹的“听觉音乐审美”变为某种程度上的“行动审美”。关于这一点,在大众钟情的卡拉OK热中便可领略到,而由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大赛,则更是由明星娱乐走向平民娱乐、大众娱乐的经典版本。
在大众成为音乐审美主体这一事实面前,各种形式的音乐尽可能地流行音乐化,甚至表现出某种时尚或时髦来满足大众音乐审美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在这个过程中,将经典世俗化、将高雅通俗化、将传统现代化,从而使得流行音乐具备了雅俗共赏的美学品质,成为大众化的平民音乐。
2.中国流行音乐的审美意义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具有商业色彩的大众文化,虽然有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方向一致,但它最主要的价值定位是更多地强调娱乐功能而不是教化功能,以满足个体的情感要求和音乐审美需求,本质上属于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影响从其他层面实现它的音乐价值、社会价值及对审美对象的塑造作用。
(1)为音乐的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艺术通道。流行音乐不固守某种成型音乐流派的风格或原则,也不固守某种权威的理论和主张,而是藐视一切旧有的、现有的规范,将古典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音乐统统招到自己的麾下,用新的创意、新的手法、新的形式进行艺术的搅拌,以构筑自己的鲜活音乐:用沙哑的嗓音打破了圆润甜美嗓音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强调节奏打破了以旋律为主的创作理念,震耳甚至是刺耳的声音打破音乐必须是悦乐的原则……在流行音乐面前,音乐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门类间的界限不存在了,任何新形式的音乐的出现都变为可能。对流行音乐来说,所有的音乐都是构筑自己的音乐个性、音乐逻辑的参照。
流行音乐这种大胆创新,既是对传统音乐的反叛与颠覆,又是对传统音乐的反哺与重构,不仅为当今的音乐带来蓬勃的活力,也为未来的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多样性打开了更为宽阔的艺术通道,让人感到音乐艺术创造空间无穷无尽。
(2)改变了人们的音乐审美观念和审美习惯。由于流行音乐格外讲究标新立异,所以它总能用新鲜的音乐让人不断地惊讶:原来嘶哑沙哑的歌声也如此有魅力,原来势不两立的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竟可以融合得天衣无缝……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原来如此”的惊讶中,传统音乐文化遭到全方位的消解,旧的音乐审美习惯和审美观念发生断裂乃至崩溃,使人们在新旧音乐的对比中不得不重新审视音乐,重新调整自己的音乐审美规范,从而提升了人们的音乐审美能力。
在以往的音乐审美活动中,大众在音乐活动中总是规规矩矩地当听众,如今,随着流行音乐的市场化、互动化,人们在音乐审美活动中不仅仅要获取听觉和视觉的欣赏与享受,而且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抒发和表达他们的情感,由单纯的被动的音乐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某种意义上的音乐表现者,并由此对音乐有了更直接、更个人化的感受和理解。
(3)大面积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讲,以审美价值为最根本价值的音乐,是以审美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它对人的改变作用是人们在对它的主动的审美体验中获得而不是靠外力强制实现的。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它对人的作用当然具有以上特点,再加上它的大众化是空前的,因此相对其他形式的音乐而言,它对人的影响更为广泛。比如,《好人一生平安》等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已成为流行的时髦语汇;那些追星族不仅模仿歌星的行为举止,甚至还要整形整容成为歌星的模样;许多手机、电话的铃声也变成流行音乐的某段旋律或某段歌唱……这些看来习以为常的事,其实就是流行音乐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从这个角度看,流行音乐使音乐大众化了,也使大众不同程度地音乐化了,而这个音乐化的过程就是大众在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过程。
3.中国流行音乐存在的问题
的确,流行音乐在多个层面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以及音乐本身,其产生积极的深远作用已远远超过目前的理论阐述,但是作为最具实验性和时尚性的流行音乐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是反审美、反文化、反人类的东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流行音乐的主流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和美学意义,又要看到它的不足和缺憾。
(1)商业与艺术的失衡。在社会市场化的今天,流行音乐已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有着其他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所没有的巨大的商业市场,因此流行音乐离不开商业的运作与合作。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不愿错过挣钱的机会而放弃了对艺术的精雕细刻,丢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比如,靠“身体艺术”和低俗的挑逗寻找票房价值、用过度的商业包装和一些花边新闻炒作卖点、那些被商业游戏规则操纵的音乐排行榜……这些,不仅使音乐丧失了起码的艺术尊严和独立性,也给流行音乐蒙上厚厚的阴影,给社会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
(2)通俗与庸俗的错位。的确,流行音乐通过通俗的手法和技法打击了古典音乐和所谓的高雅音乐高高在上的傲慢与孤芳自赏,使音乐最大限度地通俗化和大众化。但是,作为流行音乐审美主体的大众,其审美需求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有些甚至是阴暗和颓废的。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囚歌”,一些嗲声嗲气的“爱情歌曲”,一些粗制滥造的网络歌曲等,它们都将通俗演变成了庸俗、媚俗,甚至是低俗。结果是讨好了大众却践踏了音乐,满足了大众的某些肤浅需求而缺失了对大众的精神世界及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深层关怀。
(3)娱乐与教化的断裂。流行音乐走着大众娱乐文化的路线,满足着大众的娱乐需求,这既是音乐的属性使然,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为了娱乐就可以放弃对人的精神塑造的艺术使命。然而,一些流行音乐却与此背道而驰,恰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出现了偏差。比如《人民币》中的拜金主义、《垃圾场》中的颓废堕落、《借了你一夜》中的低级下流等。其狂放不羁的演唱,丧失理性的反叛精神,毁灭他人也毁灭自己的音乐姿态,用“荡妇”、“弑杀”等命名的乐队名称等。这些由人性和审美的双重变态制造出的亵渎人类尊严和神圣的东西却成功地锁定了为数不少的年轻人,使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与扭曲。
无论是作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还是作为审美活动的需要;无论作为一种娱乐形式还是一种表达自我、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流行音乐应该是:注重原创性和本土化及个性化,注重娱乐功能也注重教化功能,既与商业联姻又能保持艺术的尊严,更好地表达和诠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及审美需求和审美理念,使之成为具有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审美特点的音乐艺术。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对生活的深入学习和了解,创作出既有强烈个性,又有鲜明时代气息,并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和喜爱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流行音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