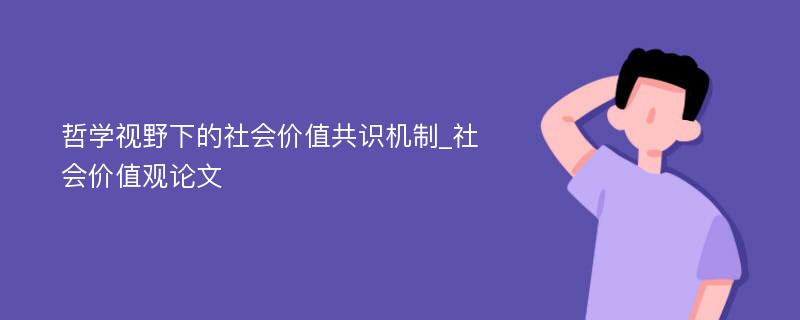
哲学视域中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共识论文,价值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生活结合的研究中,共识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然而,有些学者把认同与共识予以混同,把共识与差异予以割裂,混淆共识与社会主体意志表达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从哲学视域中研究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机制。 一 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共识 黑格尔把多样理解为知性所坚持的“相关事物的不同而已”,把差别理解为“乃基于它的固有的规定性”;“差别自在地就是本质的差别”;“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但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于这两个范畴,时常是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这样科学的兴趣总是这一次仅仅在当前的差别中去追溯同一,另一次则又以同样的片面方式在同一中去寻求新的差别”①。这对于我们论题中的共识研究有两个方法论启示: 其一,社会价值观念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多元的。 就多样而言,各社会价值观念表现不同,“按照它们的原样,各自独立”;就多元而言,各社会价值观念的主体不同、利益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不同,“自在地就是本质的差别”。社会价值观念上的独断论承认“多样”,但否认“多元”,力求用“一元”来达到一统。宗教神学用它的神学价值观念来整合其他社会价值观念,于是就出现了中世纪的“黑暗”的宗教裁判所;当代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用它们的原教旨价值观念来对待不同文化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9·11”式的恐怖主义。 对于只看到多样而不能进一步揭示多元的观念,黑格尔从思想方式的角度举了一个颇有意味的例子:“据说莱布尼茨当初提出他的相异律时,宫廷中的卫士和宫女们纷纷走入御园,四处去寻找两片完全没有差别的树叶,想要借以推翻这位哲学家所提出的相异律。”黑格尔的评语是:“这是对付形而上学的一个方便法门,而且即在今天也还是相当受人欢迎的方便法门。”②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大有人在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仍然有一些人总是想用一元社会价值观念来替代多元社会价值观念,这就是黑格尔所讽刺的“对付形而上学的一个方便法门”。 其二,对于社会价值观念的研究需要在“同中之异”中看出“异中之同”。 如果说,“用‘多样’来否定‘多元’”是与否认“同中之异”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彻底多元主义则与否定“异中之同”联系在一起。持彻底多元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人认为,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划归为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念。伯林就断言:“既然有些价值可能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那么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这种观念,便是建立在关于世界同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③也如有论者所言,否认“异中之同”的实质在于:“以往在民族、国家、宗教界限内的最高价值在全球化的场域中被相对化、矮化,成为众多坚硬的差异价值中的一种,使得超越性的最高价值付之阙如——宰制一切的‘上帝’真的死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在使个人自由意志与权利得到伸展的同时,也使得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世俗意识形态蔓延全球,具有超越指向的价值、意义在现实生活中逐渐逊位”④。人类没有共同追求的东西,因而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独断论的反动。马克斯·韦伯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世界被祛魅”,于是价值世界就会出现“诸神斗争”的局面,“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无休止斗争之中”⑤。这种价值世界中“不间断的祛魅”既是马克斯·韦伯所处时代的“我们文化的命运”,也是现时代的“我们文化的命运”。 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价值的多元和一元永远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不仅不断地形成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在追求价值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地形成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共识。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理解,共识就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而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到一致意见”。⑥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⑦的社会形态交织在一起,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冲突日益尖锐。这是对独断论的反动,然而人们的价值取向由“祛魅”而趋混乱,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寻求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共识,从而构建共同追求的信仰,就成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务之急,因此尤其需要研究和提炼“异中之同”。 恩格斯在批判葛德文“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的观点时指出:“它不是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而是赋予粗野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⑧这个“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的活动必然指向这样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由此就造成了历史中“那种消灭现成状况的现实运动”。正是在“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历史运动中,“每个新阶级赖以实现统治的基础,总比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宽广一些”⑩,“现实的”而不是“现存的”——“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而仅仅属于“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的东西(11)——统治阶级赖以实现统治的基础不断拓展,就构成了价值共识主体的范围历史地扩大的社会根据。“承认价值的共同性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不到价值领域存在共同性,就无法解释人类文明纵向上的继承关系和横向上的借鉴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12)当然,从量变到质变的角度来理解,“随着价值共识范围的扩大,价值共识的形式和性质就可能产生质的变化”(13)。 为了与独断论划清界限,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必须把差异包含在内。差异与共识本来就是相互包含着的。黑格尔指出,对于“预先假定了单纯的同一或抽象的同一是某种本身自存之物”的人,必然“同时也假定了差别是另一种同样地独立自存之物”,于是“同一”与“差别”就不能相互转化,于是事物的运动就不存在了(14)。离开了差别的同一是不存在的,离开了同一的差别也是不存在的;离开了差别与同一的相互包含,就不能理解事物在变化中的运动。从我们的论题来说,共识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共识源于差异。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不是对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的简单否定或替代,而是对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的补充和完善。以差异为基础的共识的本体论根据就在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然而不同利益诉求的价值主体又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的,而作为现实社会基础的共同体在历史的进展中则不断地扩张。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必然从自己的角度来进行评价活动,由个体认同差异所带来的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态度,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共识的丰富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对社会价值观念“差异”的肯定,构成了关于社会价值观念共识的理论基础。虽然从表面看,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了“共识”形成过程中的困难和紧张;但“差异”绝不意味着只是对抗和冲突,它更多地蕴含着一种思想张力。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多元性竞争和理性对话,就能够使不同主体在理解对方或他者的社会价值观念立场中扩展自己的理解、丰富自己的内容,从而可以寻找到某种共享的价值理念。因此,对于差异的共识是共享与互利关系的协调和体现。“共识不是直接裸露的、某种现成的存在,它是需要人们去积极澄清或追求而‘形成’、‘达致’的结果”(15)。正是在“对人自身和他者关系的反思和领悟”过程中,“才有可能自觉地意识到与他者共在的事实或至少体验到一种与他者的共在感”(16)。 二 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及其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论》“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17)。在此书中,他以“秩序良好的社会”作为立论的基本前提,指出人们对于构成优良生活的因素存在着广泛的共识。然而,后来罗尔斯对此书内容进行反思后指出:“在《正义论》中我所使用的公平正义之秩序良好社会的理念是不现实的”(18)。社会中存在着不相容却合理的各类综合学说,尽管其中没有一个学说是公民普遍认可的,然而人们仍然能够和谐地共存,“这是何以可能的?”(19) 《政治自由主义》的出版表明了罗尔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思索:“社会统一的本性是通过一种稳定的诸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重叠共识所给定的”,由此就能达到“多元条件下的有正当理由的稳定”。(20)为了保证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必须在各种不同学说之间寻求相互间“重叠”的共识面,使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能就此达成一致即形成“重叠共识”。(21)从我们的论题出发,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其一,全体公民是“重叠共识”的主体。罗尔斯认为,这种共识体现了“公民参与和支持民主政体的意志基础”,构成了“确保民主政体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理念基础”。(22)由此,在这种共识基础上所构建的政体就能“得到该社会在政治上持积极态度的公民的实质性多数人支持”(23)。罗尔斯实际上把“重叠共识”的主体是“全体公民”作为其立论的根据。 其二,公平正义是“重叠共识”的核心内容。罗尔斯认为公民不可能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达成共识,共识作为“在排除了各种分歧和对立之后的共同认识”,只能是“独立于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之外的观念”,然而“其核心是一种具体的政治正义观念,而公平正义即是其标准范例”。(24)公平正义包括“立宪民主”、“平等、公平”、“良心的自由和普遍的思想自由,而不仅仅是政治自由和政治思想自由”、“结社的自由和移居自由”。(25) 其三,公共理性的运作是“重叠共识”形成的基本方法。罗尔斯认为,不能依靠某一种普遍完备性学说来达到“重叠共识”,因为它得不到多元民主社会中全体公民的认同;也不能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行一种“重叠共识”,因为“要求利用国家权力的制裁来纠正或惩罚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左的人,是不合乎理性的”。(26)因此,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公共理性的运作来达到对政治正义观念的共同认可。 由此,他分析了“重叠共识”形成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达成一种宪法共识而告终,第二阶段则以一种重叠共识而告终”(27),公共理性的运作就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对于“独立于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之外”的某些自由主义正义原则,“许多公民会感激这些原则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们所关心的那些人以及对社会所带来的普遍好处,然后便会在这一基础上来认肯这些原则”(28)。正是在此基础上,“最终固定某些政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内容,并赋予它们以特殊的优先性”(29),“宪法共识即可达成”(30)。在第二阶段,“重叠共识的焦点乃是一类自由主义的观念,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在某种多少较为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着变动”。这就要求各政治集团“必须进入政治讨论的公共论坛”,并要求他们在政治讨论中“超出自己观点的狭小圈子并发展各种他们可以依此面对更广阔的公共世界来解释和正当化其所偏好的政策,以便构筑一个大多数”,这就形成了“重叠共识”(31)。通过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宪法共识”和“重叠共识”的“公共理性的运作方式”,就可以理解罗尔斯的一个很有寓意的命题:“理论多元性的事实并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不幸状态”(32)。 西方社会并非如罗尔斯所说的是一个在“重叠共识”的支配下,体现不同集团利益的各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和平共处”,从而使人们能够和谐地共存于其中的稳定社会,而是充满了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然而,罗尔斯关于“重叠共识”的阐述,对于在当前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社会价值观念中的共识,仍然具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其一,一个社会价值观念要成为“共识”,其主体必须与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化,但要使一个社会价值观念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就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使大多数人成为这个社会价值观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作为“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3),其所依赖的基础必然会不断地拓展,这就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在大多数社会成员中形成共识提供了本体性基础。然而,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必须体现在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现实的展开之中,由此就为人民主体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提供了空间。这就要求,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必须提高自觉性,不断地意识并努力拓展其所依赖的主体基础,不断地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社会现实的展开中使大多数人乃至“全体公民”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真实的主体。 其二,一个社会价值观念要成为“共识”,其内容必须与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罗尔斯把“公平正义”作为“重叠共识”的“标准范例”,其实“公平正义”总是与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既不公平也不正义。“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世界的精神体现着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34)马克思把人的生命过程理解为在“个体的自我实现”(35)过程中所特有“自由的活动”(36)。由此就决定了人文精神的展开体现为对自由的追求。这正是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终极追求,从而作为终极关怀在本质上必然与大多数人追求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人文精神在与“超人性的神性”、“反人性的兽性”和“非人性的物性”的对立统一中展现其具体形态,从而体现出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同样,与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公平正义,在时代的变迁中也体现出时代特征。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要在大多数社会成员中形成“共识”,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具体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并具体体现与人文精神时代特征密切相联系的公平正义的时代特征。只有这样,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才能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识。 其三,一个社会价值观念要成为“共识”,其方法必须与“公共理性”的运作相联系。罗尔斯把“公共理性”与强行推行“一种完备性学说”和“国家权力的制裁”相对立,而与“对社会带来的普遍好感”即与对社会带来普遍利益和“超出自己观点的狭小圈子”而“进入政治讨论的公共论坛”相联系。在这个世界上,一种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感到普遍的好感”;必须通过“公共论坛”的讨论,在讨论中“超出自己观点的狭小圈子并发展各种他们可以依此面对更广阔的公共世界来解释和正当化其所偏好的政策”,从而使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形成“共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尔斯“重叠共识”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如何于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中寻求“共识”提供了启示,而且也在于为如何克服“消除文化多样性、导致不同地区文化同质化的现实危险”提供了启示。20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现实危险:“不对这个过程进行自觉的调节,各个地区各种文化物质生活方式的趋同化不仅会成为跨文化社会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客观根据’,而且会成为用这些规范的普遍性来压抑和取消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的‘客观根据’。”(37)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问题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决不能用“共识”来消除多元,共识必须把差异包含在内,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否则意识形态就不会丰富多彩、绚丽多姿。这是罗尔斯“重叠共识”所提供的与上述意义不同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 三 在个体主体认同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共识 群体的共识离不开个体的认同,为此就要理解认同概念。认同是一个很有歧义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使这个概念“既不明确,又不能不用”,但“有一个中心主题是彼此吻合的,这就是‘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38)循此方向,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把认同理解为“主体同化、吸收其他人或事,以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39)。这就决定了作为自我认同的认同必然要把一定社会价值观念内化为主要内容,由此就使个体在“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中形成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从而使个体“焦虑”的灵魂能在“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获得安顿(40)。在认同活动中,一方面“让个体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分离关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让个体成为社团的一员”;由此就把认同理解为“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从而是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41)。因此,尽管“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心理社会学中形成了多种相应”的关于认同的理论,但“都强调作为社会建构自我的社会属性,并且都回避将自我视为独立于或前在于社会的观点”。(4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同”(identity)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等同,把认同与社会认同理解为两个范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认同作为个体自我认识的活动,顾名思义是个体指向自身的意识活动,由此就决定了“内省”是其独特的方式,然而“内省”并不意味着就是“私人”的。以“内省”方式进行的个体认同活动总要通过个体的某种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否则认同就没有必要进行,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存在或者根本就无法存在。泰克·J.柏克认为:“认同是一种行动,尽管这种行动的参照是他人的期望”(43)。杜威说:“经验变成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生物经历和感受它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这个行动和感受(或经历)的密切关系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经验。”(44)个体的认同必然与行为联系在一起形成经验,然后被人们所感受。以内省方式所进行的个体认同,总会通过行动以可以被观察的经验形式呈现出来。 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个体不能离开价值形态的世界,而社会价值观念作为精神价值成为价值形态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社会的动物,群体是个体存在的普遍形式,离群索居式的“鲁滨逊一类的故事”,“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45)人不能离群索居,不仅意味着人不能离开社会的物质生活,而且意味着人不能离开社会的精神生活。个体必然地不是与这种就是与那种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认同关系。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总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它们像“精神的太阳”(46)那样照耀着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对一些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决定着社会成员能否过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 既然对社会价值观念的个体认同不是“私人”的,既然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总会对个体发生影响,那么个体对这些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状况就必然会在个体之间发生作用,从而相互影响。就微观层面来说,个体对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状况必然会受到其他人的评价,“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47)从而相互发生影响;从宏观层面来说,个体之间对于社会价值观念认同状况的相互影响,必然会在社会层面形成对于一定社会价值观念的某种共识,即“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而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到一致意见”(48),尽管这种共识可能是“重叠共识”。 黑格尔从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来阐述“个体认同的相互作用形成共识”。“个体所享受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49),因而众多个体主体的认同作为个体意见总是林林总总,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偶然性内隐藏的必然即众多认同个体的共识“作为绝对的普遍性、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50)就体现了出来。 埃弗雷特·罗杰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阐述个体认同相互作用中共识的形成。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是重要的,“因为与其说信息传播是信息简单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还不如说是授受关系的产物。传播能使意义逐渐趋向一致,即意义并合。新思想的产生,正是意义并合过程的产物。”(51)由此就能理解埃利斯·劳纳·伍曼概括的一条传播原理:“交流者总要将相互作用融入有意义的模式之中。”(52)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每个认同个体都发挥了作用,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53),于是共识就在其中形成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不同个体主体通过多元竞争和理性对话,从而可以寻找到某种相互共享的价值理念,形成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念方面的共识,这是一个不断地建构和解构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要注意一定社会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共识是一个动态过程,对此不能采用一劳永逸的态度。 认同主体之间如何进行相互作用,对于形成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共识并且深化共识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罗尔斯的理论所得到的启示,不能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行。还是罗尔斯说得深刻:政治权力之不能被滥用,在终极意义上,政治权力“乃是公共的权力,即是说,它是作为集体性拥有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权力”(54)。对此,哈贝马斯赞同地指出:“共识必须从一种由传统确定的共识转变为一种通过交往或商谈而获得的共识”(55),即通过“公共理性”的运作,使交往中个体意见之间能充分地相互作用。 如何正确地进行认同个体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可以把哈贝马斯相关思想概括为:“交往对话应确定所有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参与,畅所欲言,表达自己所主张的规则、欲望或需求,同时也要允许每个人对他人的主张提问、质疑。为避免对话因误解产生分歧,对话者在使用语言时应遵循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与正确性的有效性原则。”(56)我们把它概括为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言论自由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如果连言论都不自由,那么“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57)在言论自由的气氛中,认同个体能自由地把自己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体会交流出来,能自由地对他人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体会进行评价。于是,在认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中不仅能形成对于一定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共识,而且能深化这种共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意识形态上要放弃将特定社会价值观念转变为社会共识的努力。但必须要把特定社会价值观念通过宣传的组织环节,“进入到形成社会舆论的公众意见互动的传播中介之中,以内在的方式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以平等的身份进入认同个体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之中,从而“在公众意见的双向和多向的互动传播中发生影响”(58)。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世界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教导文明”应当被“对话文明”取而代之,如果一味地居高临下,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回顾这些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思想体系的历程,我们是有经验也有教训的。 四 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是社会主体的意志表达 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要“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59),从而自觉地构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努力使之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凸显出来,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一种社会价值观念能够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凸显出来,必须具有两个品格: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赢得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认同(60)。对于由统治阶级自觉构建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一种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能够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凸显出来,则说明了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为时代所认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能够自觉地构建出这种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统治阶级,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着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体现出来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及其价值追求,这样的阶级其要求和权利便“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61),从而必然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62)。 历史是人的劳动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3)。人在构建“为我而存在”(64)的关系中创造价值世界,既创造物质形态的价值世界,也创造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的精神形态的价值世界。正是创造价值世界的活动及价值世界自身构成了历史以及在其中展开的社会形态。人民创造历史,是历史的社会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然而,在一般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体不具有直接表达自己意志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而必须通过某种现实的“无机”方式,使体现其意志的“绝对的普遍性、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65)表达出来。 前面我们多次用了“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前者是由统治阶级自觉构建的,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发生作用,其主体是统治阶级;后者是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中形成,从而在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发或自觉地发生作用的,其主体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一个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能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说得准确些,能否在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凸显出来(在历史上一个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转化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与个体主体对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认同状况及在社会层面上对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共识状况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时强调:“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6)。我们可以断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地使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人认同一种社会价值观念。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标准,因而是绝对的。在某种环境下,个体主体可以违心地同意某一个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但这并不能算是内心的认同。个体主体对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认同状况,体现了该个体主体的意志;社会层面对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共识状况,体现了在众多个体主体认同的相互作用中社会主体的意志。 我们知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7)。这就决定了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认同个体的复杂性。利益的多样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样化价值取向导致了主体的多层次性。人的经济地位和财富占有状况不同,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力占有状况有别,人的接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实践活动经历不同,等等,这些方面的不同又交织在一起,从而就使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体价值取向极其复杂。在一般社会情况下,这种个体价值取向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层面的共识,必然呈现为如上面所分析的“异中之同”或“重叠共识”。这种“异中之同”或“重叠共识”是正常的,它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共识形成中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供了空间,也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共识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动力。然而,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在社会层面上的共识必须是广泛的“异中之同”或“重叠共识”,否则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就不能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凸显出来。 如果一个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广泛的共识,那么就说明了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不能赢得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认同。这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体对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一种意志表达。从根本上说,之所以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缺少这一品格,就在于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不能体现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那么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在根本上就不能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从而也就说明了必然缺少另一个品格。这样缺失一个或两个品格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即使由于上层建筑中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而能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着,那么必然是“现存”的,而不是“现实”的——在历史哲学中,“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而仅仅属于“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的东西(68);“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69),而仅仅是“现存”。这样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乃至自觉构建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统治阶级,迟早要被其他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和自觉构建其他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阶级所替代,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应该从社会主体意志表达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问题。共产党人必须创造条件,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基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不断凸显。否则,“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0)这种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注释: ①②(14)(6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51-254页;第254页;第250页;第296页。 ③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49页。 ④沈湘平:《反思价值共识的前提》,《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 ⑤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8页。 ⑥(48)汪信砚:《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当前我国价值论研究的三个重要概念辨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⑧⑨⑩(33)(59)(62)(64)(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页;第294页;第87、100页;第87页;第99页;第13页;第81页;第60页。 (11)(53)(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5页;第697页;第215页。 (12)文平:《“普世价值”辨析》,《红旗文稿》2009年第10期。 (13)(16)王玉萍、黄明理:《价值共识及其当代意义》,《求实》2012年第5期。 (15)沈湘平:《价值共识是否及如何可能》,《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7)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译者前言”第2页。 (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54)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导论第4页;第38页;第45页;第582页;第584页;第39页;第175页;第177-178页;第146页;第168页;第170-171页;第171页;第174页;第175页;第38页;第144页。 (34)陈新汉:《哲学视域中的文化、文化功能及文化自觉》,《哲学动态》2012年第8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16页。 (36)(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96页;第131页。 (37)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8)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20页。 (39)(4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01页;第102页。 (40)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8页。 (42)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43)Peter J.Burke,"Identities and Social Structure",Social Psychology,2004,Vol.67,No.1,p.215. (44)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97,第4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46)(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1页;第179、201页。 (47)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第118页。 (49)(50)(6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31-332页;第332页;第332页。 (51)Everett Rogers,Communication Yearbook,3,The Free Press,1981,p.67. (52)Elisabegh Noelle-Neumann,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ki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238. (55)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44页。 (56)韩东屏:《如何达成价值共识》,《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 (58)陈新汉:《权威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38-339页。 (60)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1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26-42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35页。标签:社会价值观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普遍联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