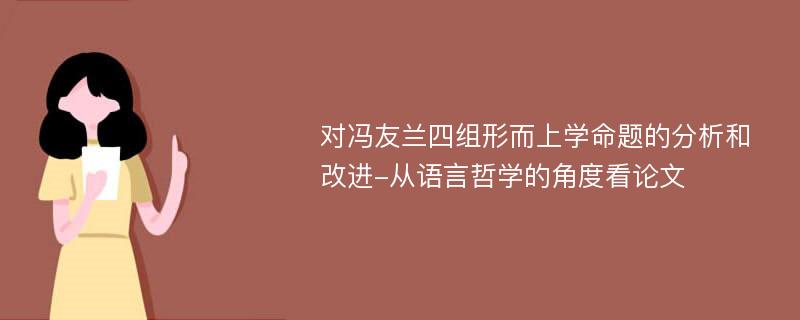
·哲学传统研究·
对冯友兰四组形而上学命题的分析和改进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
陈晓平
摘 要: 冯友兰赞成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摈弃,但不赞成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摈弃。为此,他提出一种逻辑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四组命题和相应的四个观念,即理、气、道体和大全。冯友兰开创的这一语言分析的形而上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其论证尚有一些缺陷,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冯友兰的四组命题及其论证改进的关键措施是区分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让理、气、道体和大全存在于语言世界,从而把仅仅涉及语言世界的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隔离开来,实现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 向”。
关键词: 冯友兰;形而上学;逻辑经验主义;语言学转向;本体论承诺
一、冯友兰的语言分析的形而上学
冯友兰(1895—1990)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新理学”。“新理学”由六部书组成,统称为“贞元六书”,其中包括《新理学》 (1939年)、《新事论》 (1940年)、《新世训》 (1940年)、《新原人》 (1943年)、《新原道》 (1945年)和《新知言》 (1946年)。其形而上学部分主要在《新理学》中阐述,后来又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 (1943年)等论文中加以引申,并在《新原道》和《新知言》中加以改进。冯友兰明确宣称,他的“新理学”受到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影响,是在其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
逻辑经验主义也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30—50年代对西方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包括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以及柏林学派的莱辛巴赫等人。逻辑经验主义将一切命题分为两类:一为综合命题,一为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对实际事物有所断言,其真假必须经受经验的检验,因此综合命题必须在原则上具有可检验性,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与之不同,分析命题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不涉及实际事物,其真假无需经受经验的检验。如果一个命题不是分析命题,那么它必是综合命题;如果一个命题是综合命题但却是不可检验的,那它必定是无意义的。在逻辑经验主义者们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用这种无意义的命题组成的,故而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 号。
冯友兰曾将“新理学”与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处理进行比较。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他说:“维也纳学派说它们是无意义的,是有理由的。传统的形上学中的命题,大部分是这一类的命题,所以维也纳学派说形上学是无意义的。……坏的形上学,是可以以维也纳学派的方法取消的。取消此等所谓形上学,是维也纳学派的贡献。但真正的形上学中,并没有如上所举的命题,并不对实际有所肯定,有所建立。真正形上学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在引文中把虚词“底”一律改为“的”。后面的引文一律如此。
在这里,冯友兰区分了坏的形而上学和好的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属于坏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属于好的或真正的形而上学;因为“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命题不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这便产生一个问题:逻辑学和数学也是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那么,“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与逻辑学和数学有什么不同?对此,冯友兰回答说:“逻辑算学不仅对于实际无所肯定,亦无所建立,而且不说到实际。形上学说到实际,但只形式地说,所以虽说而无所说。”② 同上。 换言之,逻辑数学压根儿不提实际,形而上学则提及实际,但仅此而已,并无具体地肯定和 述 说。
对于形而上学命题的应有特征,冯友兰后来给出更为形象的表述:“形上学的命题是空而且灵的。形上学的命题对于一切事实作形式的解释。其解释是形式的,所以是空的。其命题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所以是灵的。”③ 同上书,第501页。 换言之,形而上学命题是“空灵”的,空即不着实际,灵即普遍适用,而且正因为它们不着实际,所以它们才是普遍适用的,正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们才是灵 的。
二、冯友兰的四组形而上学命题
现在我们集中讨论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本节将给出冯友兰形而上学的四组命题,随后各节将对这四组命题逐一地加以讨论,并给以澄清和改进。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命题具体如 下。
“第一组主要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的话说:‘有物必有则’。”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03页。
“第二组主要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的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以能存在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有理必有气’。”② 同上书,第508页。
“第三组主要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一切流行涵蕴动。一切流行所涵蕴的动,谓之乾元。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无极而太极’。又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③ 同上书,第511页。
“不要急,先听我说完。在现实里,男主人公不是带着两个疑问黯然离去吗?在现实结束的地方正是小说的开端,这也是小说家的用武之地。S返回果城,跟踪监控那个情敌。有大半年,他一无所获,他看到的全是其夫唱妇随的恩爱镜头。S涌起了对前妻的刻骨思念,又为她被‘霸占’而火冒三丈。功夫不负有心人,S终于拍摄到了情敌出轨的镜头,S激动得浑身颤栗,想起了昔日看着那个女人掏出那个大牛皮信封的情景。就要一报还一报了。S曾猜想那沓照片肯定跟那个男人有关,只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也没有蛛丝马迹。”
“第四组主要命题是: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④ 同上书,第512页。
近年来,靖远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资金扶持等方法相继建成了金杞福源、鼎鑫、同益药业、陇草堂等10多家中药材龙头企业和以金田野、雪山、高原宏、福唐为代表的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160多家,其中3家通过了中药材GAP认证,研发了中药材保健养生等中药材系列产品。中药材产业的迅速发展,为靖远县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了就业渠道,也带动了全县运输、餐饮、包装、农资经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兴电灌区和贫困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
冯友兰总结说:“以上四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亦可以说是形式命题。此四组形式命题,予我们四个形式的观念。即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及大全之观念。真正的形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提出这几个观念,并说明这几个观念。”⑤ 同上书,第514页。
不过,在笔者看来,冯友兰的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较为复杂,其分析性也差一些。其中的一些命题似乎有些武断,缺乏语言的分析性,并且命题之间似有逻辑跳跃和不协调之处。如,“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这句话对实际有所断定,似乎违反了冯友兰形而上学“不着实际”的特征。当然,是否真的违反还取决于这句话是否分析性的,而这又取决于冯友兰对“流行”的解 释。
冯友兰解释说:“存在是一流行。因为存在是一动,是一建立。动必继续动,然后才不至于不动。存在必须继续存在,然后才不至于不存在。继续就是流行。”⑥ 同上书,第511页。 我们看到,冯友兰首先把“流行”解释为“动的继续”,然后又概括为“继续就是流行”。按此概括,流行也应当包括静的继续,进而使得“存在是一流行”与“存在是动的继续”之间不够协调,除非有分析性的理由把“存在是静的继续”给予否定。但是,冯友兰并未给出这样的理由,事实上也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理由。因为动的事物可以存在,静的事物也可以存在;动的事物可以继续动,静的事物也可以继续静。存在着的事物并非只有动的,也有静的,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可能把静止事物的存在性排除 掉。
在这组命题中,冯友兰对“道体”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定义,即“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一切流行涵蕴动”。因此,道体也具有动的特征。但是,以上分析表明,由于流行不能排除“静的继续”,道体也不能排除静的特征。这使冯友兰作为流行之总体的具有动之特征的“道体”缺乏分析性,因而失去“不着实际”和“空灵”的特征。既然对实际有所断定,那就需要从经验上加以验证;仅从逻辑上不能阻止我们做出相反的断定,即道体是静的,或者静和动兼而有 之。
进而言之,在冯友兰那里,道体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无极是气,太极是理;相应地,无极而太极就是由气实现理的动态过程。这些论述是否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取决于冯友兰对理、气和道体之表述的分析性。应该说,在这方面冯友兰的表述是有缺憾的,其症结在于没有把真际和理安置在语言层面上。为此,笔者将从语言哲学角度重新审视冯友兰的四组形而上学命题,并加以修正、补充和完 善。
①落实管护人员,明确管护责任。北京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建立本市农村水务建设与管理机制意见的通知》。全市成立3927个农民用水协会,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每人每月500元补助)组建了10800名农民管水员队伍,负责农村水土保持、机井管理、用水计量、水资源费征收、河道管护等工作,实现了源头管理。北京市政府建立了水源涵养林管护机制,出台了山区移民搬迁政策 (每人每月400元补助)组建了4万多名生态林管护员队伍,使全市61万hm2水源涵养林实现了管护全覆盖。
三、对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的改进
既然旧命题中的“有某种事物”断定了某种事物存在于时空中,即断定某种事物是实际存在的,而新命题中的“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却于实际毫无断定,这意味着,冯友兰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所谓“由知实际而知真际”③ 冯友兰:《新理学》,载《三松堂全集》 (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变成“由知如是的真际而知理的真际”。稍后将表明,由真际到真际只是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的特征,其他三组命题的特征是由真际到道际。这里的“道际”是指既可说又不可说的领 域。
蒙特卡罗(Monte-Carlo)方法是一种应用随机数进行模拟试验的方法。该方法对研究系统进行随机观察抽样,通过对样本值的观察统计,实现对研究系统的模拟。本文将站点逐日降水作为一个随机变量来处理,根据过去的资料提取降水量所具有的统计规律性,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站点逐日降水量的本质特征。把这些统计规律应用到未来降水量的预报中,提高降水预报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该方法确保每个降水量样本值在未来预报系列发生的频率与其在过去发生的频率相同,并使预报系列多年的均值与过去资料多年的均值相等(韦庆等,2004)。
冯友兰解释道:“有山则有山之理,有水则有水之理,有某种事物,则有某种事物之理。”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05—506页。 这些话对于实际无所断定,因为它并未断定世界上有山,只断定“如果有山则有山之理”,因而这个命题是“空的”。不过,形而上学毕竟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存在的,因而事物之理与经验实际有所关联,尽管理的存在不依赖实际事物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空灵的形而上学命题也多少谈及事实,但只是点到为止;仅以此为出发点,做逻辑的演绎或形式的扩展,而对此出发点并不进行详述,更不加以证明。冯友兰指出:“形上学是自事实出发的,认为事实存在,是‘共许’的,所以并不拟证明事实的存在,而只拟对于已存在的事实,作形式的解释。”② 同上书,第505页。
笔者曾于1989年给冯友兰去信,对其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的分析性提出质疑:“有某种事物”和“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涵义?若不是,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前者涵蕴后者是分析命 题?
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指出,相对而言,冯友兰的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较为复杂,其分析性也差一些。这组命题是关于形而上学观念“道体”的,“道体”被定义为流行之总体。流行被定义为“动的继续”,同时又被定义为“存在的继续”,但这两种说法是不协调的,因为存在也可以是静的继续。若断言存在只是动的继续,那么这是一个综合命题而不是分析命题。相应地,把道体的动看作“无极而太极”的程序,这也是一个综合命题而非分析命 题。
冯友兰的这一解释对于笔者理解他的学说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我意识到,他所说的‘某种事物’并不是经验世界的某种事物,而是语言世界的某种事物,即由一个名词表示的某种事物,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名词的外延。因此,他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是语言层面而非经验层面的。我的这一看法在《新知言》中得到进一步的印 证。
在《新知言》中,冯友兰把“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② 冯友兰:《新知言》,载《三松堂全集》 (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其中的“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显然是一逻辑命题,相当于逻辑学的同一律“A是A”。由此理应得出一个结论:作为形上学的出发点的“实际”并不是经验的实际,而是语言的实际;或者说,并不是经验世界,而是语言世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冯友兰并没有明确地得出这一结论,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是从经验出发”的说法 上。
后两个命题涉及“狭理”和“广理”,这是冯友兰理论的应有之义。按照冯友兰的说法,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是一个词的内涵;在逻辑学中,一个词的内涵就是它的定义,而定义的一种普遍方法是“种差加属”。种和属是相对而言的,种是一个小类,属是一个大类,并且属包含种。对一个种名的定义是所属的属名加上该种与同属的其他种之间的差别即种差。例如,对于“人”这一种名的定义可以是“有理性的动物”,其中“有理性的”是种差,“动物”是属。由此,我们得到命题:“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必有某物之种差和属。”
冯友兰把“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简称为“如是”。他说:“山如山的是,水如水的是,这座山如这座山的是,这条水如这条水的是,一切事物各如其是,是谓如是。一切的如是,就是实际。形上学就是从如是如是的实际出发,对之作形式的释义。”③ 同上书,第194—195页。 上面谈到,“如是如是的实际”是语言实际而不是经验实际,可是冯友兰却接着说:“此种分析及总括,都是对于实际作形式的释义,也就是对于经验作形式的释义。”④ 同上书,第195页。 这样,冯友兰就把“如是如是的实际”归结于经验的实际,从而使他的新提法回到原点,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重大意义。为什么冯友兰在给出新说法之后又退回到旧说法呢?对此我们加以分 析。
冯友兰把旧命题“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改为新命题“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之后,以“山是山”作为“如是如是”的例子谈道:“现在我们说:山是山,必有山之所以为山者。这个命题,并不肯定某些山的存在。……因为如果‘山是山’是有意义的一句话,所谓山者,必不只是一个空名,它必有其所指。其所指就是其对象。其对象就是山之所以为山者。”① 冯友兰:《新知言》,载《三松堂全集》 (第五卷),第196—197页。
为了达到水利工程的节能目的,可以从用电设备的使用出发,如提高水泵的整体性能。为了提高水泵的使用性能,需要对水泵的进水效率进行调整。为了实现水泵的节能使用,需要不断加强水泵的改造升级工作,从而减少用电负荷,实现绿色施工。
请注意,“山是山”这句话有意义的前提是“山”这个语词有意义。在这里,冯友兰实际上是从“山”这个词有意义推出“山”的指称对象是存在的,即山之所以为山者是存在的。请问,“山”这个词的意义存在于哪里?显然,不存在于经验世界中,而存在于语言世界中,因为“山”的意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语言而被理解,这个被理解的东西就是山之所以为山者,它也存在于语言世界之 中。
在语言世界,各种事物是由语词表达的,与经验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孙悟空”这个词在《西游记》中是有意义的,于是它便有指称,其指称对象就是《西游记》所描述的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而无论经验世界中是否存在那样一只猴子。换言之,孙悟空存在于语言世界中,而不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用现代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术语来说:孙悟空存在于某个可能世界之中,这个可能世界并非现实世界,它只能被语言所描述,但不能被人们所经 验。
从图6可以看出,裂隙位于坡中时膨胀土边坡的安全系数明显小于裂隙位于坡顶时膨胀土边坡的安全系数。在坡顶裂隙中,雨水大多沿着裂隙发展方向做垂直入渗;而在坡中裂隙中,降雨饱和后往往还会出现平行于坡面的顺坡渗流[19],产生渗流力,不利于边坡稳定,这也导致一些降雨诱导型滑坡往往会出现破坏面与原坡面大致平行的情况。因此,膨胀土边坡滑坡后缘多发生在坡中,而极少出现在坡顶[20]。
为什么“孙悟空”在《西游记》的语言世界中会有所指呢?因为孙悟空具有孙悟空之所以为孙悟空者,即“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根据冯友兰给笔者的复信,“孙悟空之所以为孙悟空者”就是“孙悟空”的内涵;有外延必有内涵,所以,有孙悟空必有孙悟空之所以为孙悟空者。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上讲,此话是对的,因为一个词如“孙悟空”如果没有内涵或定义,那它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语词,因而不能被有效地使用。在一个语言系统(语言世界)中,一个词能被有效地使用,就是它具有外延的标志。从一个词能被有效地使用推出它具有指称对象,相当于从一个词的外延推出它的内 涵。
冯友兰修改后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在此,“某物为某物”相当于:关于某物的那个语词是有意义的,即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能被有效地使用因而具有外延。“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相当于:该词的指称对象是存在的,因而具有内涵。显然,这种意义的“存在”不是相对于经验世界而言的,而是相对于语言世界而言的;相应地,这个命题具有冯友兰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即“形式的”或“不着实际的”或“不拖泥带水的”。② 同上书,第126页。
在《新知言》之前,冯友兰所提出和讨论的旧命题是: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其中“有某种事物”是指某种事物在经验世界即实际中存在,而“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则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领域即真际中。用冯友兰的话来讲:“有某种事物之有,是我们于《新理学》中所谓实际的有,是于时空存在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是我们于《新理学》中所谓真际的有,是虽不实在于时空,而亦不能说是无者。”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06页。 由于该命题面临逻辑上的困难,冯友兰在《新知言》中对之加以替换,将其中的“有某种事物”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② 冯友兰的这一修改受到沈有鼎先生的提示[参见《三松堂全集》 (第五卷),第196页],笔者于1989年给冯友兰的信中也指出类似的问题。
在这组命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是:“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此话相当于“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理”,在此,“某种事物之理”被解释为“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 者”。
然而,冯友兰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改变的重大意义,仍然坚持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是经验实际,而不是语言实际即真际。他说:“从如是如是的实际出发,形上学对于实际所作的第一肯定,也是唯一的肯定,就是:事物存在。”④ 冯友兰:《新知言》,载《三松堂全集》 (第五卷),第195页。 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山是山”这一如是如是的命题并不断定某山实际存在着,而只断定“山”这个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种真际的存 在。
进而言之,如果把“某山存在”理解为在语言世界中存在,而非冯友兰所说的在经验世界中存在,那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如果“山是山”是有意义的一句话,“山”在该语言系统中便有外延,即有某山,亦即在该语言世界中某山存在;但这并不意味某山在经验世界中存在。这样,我们便得到一个语言分析的命题: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 反之亦然,如果在一个语言世界中有某山,即某山存在,那么“山是山”是有意义的一句话。这便得出另一个语言分析的命题:有某物,必使某物为某 物。
冯友兰的失误在于,把“某物为某物”所蕴涵的语言世界的“有某物”混淆为经验世界的“有某物”,从而把形而上学的出发点看作于时空中存在的实际,而不是超时空的真际。当我们纠正了冯友兰的这种失误之后,便可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内做进一步的推导,充分展示形上学体系“不着实际”“超乎形象”或“不拖泥带水”的特征。下面我们给出修正后的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的完整表 述。
修正后的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狭理。有某物之狭理必有某物之广理。
需要说明,以上第二个命题“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是由“有某物,必使某物为某物”和“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联合推出的。相对而言,后两个命题不太重要,故不放在第一组命题之中,但放进去也未尝不 可。
(3)标准库到调查库。调查库是在标准库的基础上,参照城镇地籍调查的实际情况,将内容和结构进行扩充和完善的基础数据库。标准库建立后,参照实际业务需求,再通过SuperMap提供的标准转换模型,在标准库基础上完善结构并扩展内容,将数据转入到调查库中。在转换过程中,会因连接字段值或字段值长度出错而会出现中止转换的状态,此时需进行手动修改,完全正确之后才能完成最终数据的转换。建立调查库之后,必须重新更新宗地关联属性、生成接图表以及批量更新界址线边长。
冯友兰谈道:“所谓某之类,究极言之,即是某之理。例如方之类,极究言之,即是方之理。”① 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2—23页。 这就是说,类和理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尽管如此,二者在用法上是有差别的,类是从外延上讲的,而理是从内涵上讲的。当说“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时,前半句中的“某物”是指某物的外延,后半句中的“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是指某物的内涵,即某物之 理。
受众分层要求推广者根据不同的特征和爱好对受众进行细分,在正确的定位原则指导下确定核心受众群。但是老约翰绘本馆并没有将目标受众进行很好的分层。在前期的公益性宣传中,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中低端人群,但事实上真正对绘本感兴趣并且有能力长期对孩子进行绘本教育的是社会上的中高端人群。
前面谈到,某物的内涵即定义必须涉及一个大类即属,而属也是一理。例如,对于“人”而言,“有理性的动物”是它的理,“动物”也是它的理。为避免混淆,我们把前者即“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叫做“某物之狭理 ”,把后者即“某物之属”叫做“某物之广理 ”。由于某物之狭理(种差加属)包含了它的广理(属),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命题:“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狭理”和“有某物之狭理必有某物之广理”。例如,有人必有人之狭理即有理性的动物,有人之狭理必有人之广理即动物。不难看出,“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狭理”是从“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和“狭理”的定义联合得出的;“有某物之狭理,必有某物之广理”是从狭理的定义和广理的定义联合得出的。② 对冯友兰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的改进,初见于拙文《关于冯友兰先生的形上学体系的出发点及其改进》 (《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在此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由此可见,以上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中的所有命题都是通过语言分析而逻辑地得出的,完全没有涉及于时空存在的经验事 实。
第三,基础设施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促进双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根据回归结果,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平均来看有一定的比例是通过作用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但用于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更容易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由前文影响机制分析可知,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于完善东道国自身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道国贸易便利化、增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通过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通过促进双边经贸往来和吸引中国OFDI促进投资母国经济增长。
四、对第二组形而上学命题的改进
蒯因指出:“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而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② 蒯因:《论何物存在》,载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 15页。 在此,蒯因把“何物存在”的问题区分为两种:一为语言之内的,即人们说什么东西存在;另一为语言之外的。蒯因着重讨论语言之内的存在问题,而对语言之外的存在问题只是点到为 止,存而不论。
冯友兰解释说:“第一组主要命题,是就某种事物著思。此一组主要命题,是就一个一个的事物著思。……一个一个的事物是存在的。我们从一个一个的事物著思,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作形式的解释,即得如上述诸命题。”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08页。 这就是说,第一组命题着重谈事物之理,而事物之理属于真际,而不是实际。与之不同,第二组命题是着重谈实际的,即一个一个的事物,它们都是存在的,即“于时空存在者”(对于理,冯友兰只说“有”而不说“存在”)。我们立刻发现,这样的命题与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不着实际”的宗旨是不符的。如果说,冯友兰的第一组命题已经对此宗旨有所背离,那么这第二组命题则背离得更远,因而有必要加以纠 正。
其实,在我们纠正第一组命题的基础上,对第二组命题的纠正要容易一些。既然第一组命题只是相对于语言世界即真际而言的,那么第二组命题的出发点也是真际的,并且是接着第一组命题而展开 的。
修正后的第二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有某物必有某物之广理。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极广理。有物必有气。有理必有气。
[37]布赖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刘艳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显然,以上第一个命题“有某物必有某物之广理”是从第一组命题中的最后两个命题联合推出的。需要指出,某物的狭理和广理是相对而言的,如“动物”对于“人”来说是广理,但是,动物本身也是一个物种;根据第一组命题中的“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狭理”,“动物”也有其狭理(即内涵或定义),即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自由移动的生物。又根据第一组命题中的“有某物之狭理必有某物之广理”,“动物”也其广理即“生物”。同样地,“生物”也有其狭理和广理。以此类推,直至所有物种都属于其中的“极广理”,极广理似可叫做“事物”或“东西”。显然,万事万物都属于事物,因此,有某物必有事物,这也就是“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极广 理”。
需要强调,极广理除了是最大的属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特征,否则它就不能成为最大的属或极广理。这种没有任何具体特征的极广理,我们称之为“气” 。据此,由“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极广理”可得“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气”。又因为气没有任何具体特征,某物之气和他物之气是同一种气,并且所有物都有气,因而不必强调“某物”和“某气”,进而可得“有物必有气”。相对于语言世界,某物和某狭理是一一对应的,因为狭理就是某物的内涵或定义。根据这种对应关系,由“有物必有气”可得“有理必有 气”。
冯友兰的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中有断言:“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而事物是“于时空存在者”,因此,这里所谈的存在是经验世界的存在,而不是语言世界的存在。我们在对前两组命题的改进中,已经把事物的存在变为语词的外延与内涵的存在(根据冯友兰给笔者的信),而这种存在是相对于语言世界而言的;气作为极广理是各种物或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相对于语言世界而言的。笔者接受冯友兰的这一说法:道体是气实现理的过程,即“无极而太极”的程序;不过,我们要追问,这一过程或程序的机制是什么?须强调,这里所说的是语言学机制,而非经验的机制。为此,我们有必要提及当代西方哲学家蒯因的有关观 点。
虽然“有物必有气”和“有理必有气”,但是气本身不是一物,也不是一狭理。因为根据第一组命题中的“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狭理”和“有某物之狭理必有某物之广理”,作为极广理的气再无广理,因而不是某物之狭理,进而不是某物。既然气不是某物,即气这种物是不存在的,根据第一组命题的“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我们不能说“气是气”,亦即“气是气”这句话是无意义的,进而“气”这个词是无意义的;所以,气是不可说的。但是,当我说“气是不可说的”,我们正在说气,并把气定义为极广理,气又是可说的。由此得出结论:气是既可说又不可说 的。
气不是一物,气也不是一理,气是既可说又不可说的,这也是冯友兰的结论。他说:“气所以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我们不能以名名之。如以公名名之,则即是说它是一种什么事物,说它依照某理。但它不是任何事物,不依照任何理。”② 同上书,第515页。 当冯友兰说气是不可说的时候,他便对气说了什么,并且把气定义为事物的“所以能存在 者”。
与气相比,理是可说的,物也是可说的,“某物为某物”是有意义的,因为某物有确定的涵义,即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冯友兰把理的世界称为“真际”,并把另外三个形而上学观念即气、道体和大全也归入真际。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后三个观念都是既可说又不可说的,与可说的理有着根本性的差别。用冯友兰的话说:“在此四个观念中,有三个观念(即气、道体和大全——引者注)所拟代表者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③ 同上。
为了加以区分,笔者把既可说又不可说的三个观念即气、道体和大全归入道际。所谓“道际”,就是既可说又不可说的世界, 亦即《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层面。显然,道际像真际一样属于语言世界,只不过二者分属语言世界的不同层次。当我们由理推出气、道体和大全的时候,便从真际进入道际,而非仍然停留在真际。然而,冯友兰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提出“道际”或类似的概念,这是他的一个失 误。
由以上分析可见,第二组形而上学命题也是通过语言分析而逻辑地得出的,与经验实际完全无关。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组和第四组形而上学命 题。
五、对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的改进
冯先生在回信中说:“你所提的问题很好。我的那篇文章的提法,确实有问题。‘某种事物’和‘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的意义并不相等。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一个名,有外延,必有内涵;有内涵不必有外延。所以,可以从其有外延推知其有内涵。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详载《新原道》第十章和《新知言》第六章。”① 陈晓平:《冯友兰先生与陈晓平同志的一次通信》,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
这里的“无极”是气,“太极”是理,“无极而太极”就是由气实现理的过程。按照冯友兰的说法,由气实现理,就是真际中的理通过气而变为实际中的物。他说:“实际就是事物的全体。太极就是理的全体。所以,实际的存在就是无极而太极的流行。总一切的流行,谓之道体。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11—512页。 请注意,这种流行就是实际的存在,这样一来,作为流行之总体的道体便成为实际存在的总体了,这与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不着实际”的宗旨相违背,因而有必要加以修正。我们对前两组命题加以改进的关键措施是立足于语言世界而非经验世界,对第三组和第四组命题的改进同样如 此。
“腐蚀防护是镁合金行业的核心课题之一。尽管现有技术可以制备出抗蚀性良好的防护膜层,但这类膜层往往比较脆,容易在服役过程中破碎和脱落。”研究团队负责人说,“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从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出发,研发可在镁合金表面长出致密、强韧和牢固的防腐层的新技术。”
由“有物必有气”和“有理必有气”可知,气是各种物或理存在的必要条件,即若无气,那也无物、无理。在这种意义上,冯友兰把气看作各种物的“所以能存在者”是未尝不可的。重要的是,气是语言意义上的,而非物理意义上的。对此,冯友兰谈到:“气就是一切事物所以能存在者。此不可与科学中所谓‘能’相混,更不可与‘空气’‘电气’等气相混……我们所谓气,并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亦名无极。”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10页。 在这里,气或无极不是什么,只是一个名字而 已。
蒯因(W.V.O.Quine)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起了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把“何物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从而成为语言系统之内的问题。具体地说,对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何物存在往往是不同的,取决于该系统的约束变项的值域即论域是什 么。
冯友兰的第二组形而上学命题所涉及的概念是“气”,其内容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的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以能存在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有理必有气”。在这里,气被定义为某物的“所以能存在 者”。
在笔者看来,语言之外的存在问题相当于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问题,我们只知它是存在的,至于它如何存在,具有什么特征,我们一概不知。这就是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既然不可知,那我们对自在之物的存在问题就不必多谈,而把重点放在语言之内的存在问题,此问题大致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现象界的存在问题。按照蒯因的说法,对语言之内的存在问题给出回答,就是做出某种“本体论承 诺”。
一个语言系统的本体论承诺,体现于该系统把其论域规定为什么;论域也就是约束变项的值域,即代词的指称范围。例如,自然数论把自然数的集合作为论域,约束变项的取值范围就是自然数;相对于此论域,任何一个自然数都是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自然数都可作为约束变项的值。再如,人类学把人的集合作为论域;相对于此论域,任何一个人都是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作为约束变项的 值。
当蒯因把约束变项的值域即论域作为何物存在的判别标准,他便超越各种本体论之间的争论,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宽容态度对待何物存在的问题。他谈到:“我提出一个明显的标准,根据它来判定一个理论在本体论上做出什么许诺。但实际上要采取什么本体论的问题仍未解决,我所提出的明显的忠告就是宽容和实验精神。”① 蒯因:《论何物存在》,载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8页。 所谓“宽容和实验精神”也就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多元本体论,其基本精神是:从理论上可以同时承认各种不同的本体论,因为相对于不同的语言系统,论域可以是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因此而不同。但在实践上,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需要,人们采取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从而给出某一特定的本体论承诺。这可说是理论上的多元论和实践上的一元论的统 一。
实用主义(pragmaticism)是相对于实践目的而言的。在语言哲学上,实用主义被称为语用主义,语用主义集中体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语境主义强调语境对语义的决定性作用。语境 (context)即言语环境,它不仅包括语言因素,而且包括非语言因素;不仅包括客观因素,也包括主观因素。例如,说话的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说话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等,这些都是语境的构成要素。可以说,语境就是语言实践 的代名 词。
在诸多语境要素中,论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它决定了讨论的对象范围。按照蒯因的说法,对论域的确定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承诺,论域中的所有对象都是存在的;当然,这种存在是相对于语言系统或语言世界而言的。在语言哲学中,一个语言系统就是一个语言世界,该系统的论域就是该世界的物的总体,也是最大的类。按照冯友兰的说法,类和理是彼此对应的;因此,最大的类对应最大的理。我们在关于第二组命题的讨论中,把物的最大类定义为“极广理”,又把极广理叫做“气”。现在我们可以说:气就是论域。
接下来的问题是,论域是如何产生的?按照蒯因的说法,论域只是本体论承诺,是人为规定的;但并非随意规定的,而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即出于语言实践的目的。语言实践也可叫做“语境”,因此我们说,论域是由语境而产生,并且是语境的构成要素。再根据命题“气是论域”可得:气由语境而生,并且是语境的构成要素。相应地,语境也可被看作产生气的气场,而气又是气场的构成要素;这意味着,气和气场是相互依存的,正如论域和语境是相互依存 的。
论域中的成员都是存在的,即一个一个的物;并且论域中的成员可以构成各种子类。按照冯友兰的说法,每一个子类对应一个理,所以,子类的总体对应理的总体即太极。既然论域就是气亦即无极,故而可把论域产生所有的物及其子类看作“无极而太极”。相应地,产生论域的语境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即道体。由此我们得出:道体就是语境; 也可说:道体就是语言实践。
语境相当于气场,而气和气场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气和道体是相互依存的 。由于语境就是语言实践,而语言实践是动态的,因而,道体是动的, 而不是静的。正因为道体是动的,它才能成为“无极而太极”的过程或程序。至此,我们得到第三组形而上学命 题。
修正后的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气就是论域。道体就是语境(语言实践)。气和道体是相互依存的。道体是动的。道体是“无极而太极”的过程。
需指出,道体是既可说又不可说的。道体是语境,说道体就是说一个语境,那需要在另一个语境中来说;而另一语境也是道体,要说它需要借助第三个语境,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因此,道体是不可说的。然而,当我们说道体是不可说,已经对它说了些什么,并且还能列举语境的一些构成要素,其中包括论域。可见,道体是既可说又不可说的,属于道际,而不是真际,也不是实 际。
另需强调,所谓“道际”就是语言的边际,我们说道体属于道际,是指处于语言边际的语境,即那个无限追溯的语境,而不是日常的语境。日常语境对于语言哲学也很重要,对此,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阐述。① 参见陈晓平:《对冯友兰形而上学体系的改进和补充——增加一组“形而中学”命题》 (《学术研究》, 待发)。
六、对第四组形而上学命题的改进
第四组命题在表述上相对简单,即“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②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12页。 。这是关于“大全”这个语词的定义,当然属于语言层面上的。并且,冯友兰对“大全”做了很好的语义分析,从中得出大全悖论。此分析如 下。
“大全既不可思议,亦不可言说。因为言说中所言说之大全,不包括此言说。不包括此言说,则此言说所言说之大全为有外,有外即不是大全。”① 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载《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第514—515页。 当我们说大全不可说的时候,已对大全说了些什么,包括给大全下定义。大全既可思议,又不可思议;大全既可言说,又不可言说。这就是“大全悖 论”。
需求情况:今年秋季用肥较往年延后。受经销商提货缓慢影响,部分复合肥企业库存压力略增,对钾肥采购量下降;受钾肥大合同尚未签订、现货价格较高等影响,经销商观望为主,钾肥市场整体需求支撑仍较弱。
如果我们明确了弗雷格所说的“语句”与自然语句形同而实不同,那么自然不会对判断杠“|”的使用产生误解,也不会认为他把自然语言中的语句和单独词项混为一谈。为了使弗雷格的“语句”与自然语句的区别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为弗雷格逻辑系统中的“语句”加上标注:▲f,而具有判断力的表达式则为:|—▲f。那么,与自然语句“2+2=4”相当的并不是“(2+2=4)f”,也不是“—(2+2=4)f”,而是“|—(2+2=4)f”。
对于大全悖论,冯友兰还给出更为清晰的表述:“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思的本身。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可是他仍需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载《三松堂全集》 (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这里的“宇宙”就是“大全”。既然大全既可思又不可思,既可言说又不可言说,显然,大全属于道际,而不是真际,也不是实际。大全悖论揭示了哲学的真谛。冯友兰意味深长地谈道:“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③ 同上书,第283页。
大全悖论由“大全”的定义所引起,是一种思想的或语言的悖论,而与经验无关。推导大全悖论所凭借的逻辑方法是集合式概括,即数学中构造集合的方法,因而是逻辑的。其实,大全悖论类似于罗素提出的集合论悖论。如所周知,从逻辑上讲,悖论是可憎的,因为从悖论这样的矛盾命题可以推出任何命题,致使整个系统成为无意义的。正因为此,集合论悖论动摇了整个数学大厦的根基,成为必须清除的对 象。
然而,与之不同,对于哲学这门特殊的学科,悖论不是怪物而是福音,有人甚至把哲学看作受悖论激发而专门处理悖论的学问。这是为什么?因为哲学可以把必然推导 出来的悖论看作思维的界限,在与悖论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思考;换言之,哲学是把注意力放在对这个界限的思考上,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这更高的层次上,悖论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推理的前提,因而不存在从悖论推出任何命题的问题,也就不会使哲学推论成为无意义 的。
正如康德对“二律背反”的处理,康德称之为“批判哲学”,其方法相当于对思维界限的反思。反思与一般的对象性思考不在一个层面上,它不是思考对象,而是思考思想。相应地,由反思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哲学命题,而不是关于具体对象的命题。因此,反思悖论不但可以摆脱悖论的恶性纠缠,而且可以在哲学的层面上结出硕果。冯友兰正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大全悖论”的,可以说,在其方法上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继承和发 展。
大全悖论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语言实践的界限,一旦达到这个界限便陷入语义悖论,此悖论呈现为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过程:从大全可以思议(言说),推得大全不可思议(言说);从大全不可思议(言说),推得大全可以思议(言说);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对于这一无穷往返的过程,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可被描述为“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亦即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或物极必反就是语言实践(语境)即道体的终极规律,不妨称之为“道律”。我们说道律是道体的终极规律,那是因为,道律是既可说又不可说的,属于道际,即语言世界的边 际。
经过修正或补充的第四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呈现为既可言说又不可言说的逻辑悖论。大全悖论展示了道体的终极规律即道律。道律的基本内容是:反者道之动。
至此,我们对冯友兰的四组形而上学命题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形而上学“形式的”和“不着实际”的宗旨。不过,在笔者看来,事情还没完。正如冯友兰所说,我们研究形而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对实际经验做形式的释义,最终是为生活实践服务的,因而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世界或语言实践的层面上。为此,我们有必要增加一组“形而中学”的命题,以为这四组形而上学命题与经验实际的联系提供桥梁或纽带。① 参见陈晓平:《对冯友兰形而上学体系的改进和补充——增加一组“形而中学”命题》 (《学术研究》, 待发)。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9)01-0053-15
作者简介: 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教 授。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境主义反怀疑论方案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8BZX040)、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基于先验论证的语境主义知识论研究”(项目编号:GD17CZX01)、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规范的自然化研究”(项目编号:18JYA720017)资助。
(责任编辑:肖志 珂)
标签:冯友兰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逻辑经验主义论文; 语言学转向论文; 本体论承诺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