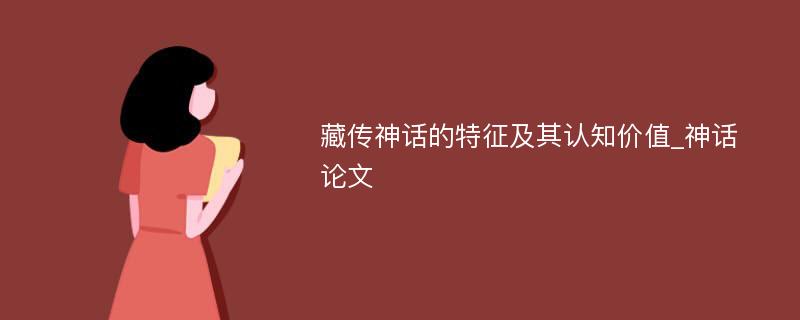
藏族神话的特点与认识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神话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藏族神话,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高原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就藏族神话的特点与认识价值作一粗浅探讨。
一、多姿多态的创世神话
藏族的创世神话,形式多样,有的是散文,有的以创世古歌的形式出现。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
第一种,肢体化生说。如《斯巴宰牛歌》中唱道:
问:“斯巴宰杀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割下牛尾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剥下牛皮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答:“斯巴宰杀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山上,
所以山峰高耸耸;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割下牛尾放路上,
所以道路弯曲曲;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剥下牛皮铺大地,
所以大地平坦坦。”[1]
而流传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创世神话却说:“一只脸面就象人的大鸟,名叫马世杰,它把左边的翅膀一摇,成了天空,它把右边的翅膀一摇,成了大地;它的右眼叫住月亮,左眼移为太阳;它的骨骼成了地上的石头,筋络化做了山脉,血液变成了江河;它身上的肌肉成了地上的泥巴,毛发成了大地的森林、禾苗和花草。”[2]
第二种,大海变陆地说。这类神话在藏文《柱下遗教》、《贤者喜宴》等历史典籍中都有记载。不过最为生动的,要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流传的《大海变陆地》的神话。神话讲:在很久以前,大地原是一片海洋,后来天天刮风,尘土被吹到海面,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现在的大地。当时太阳和月亮从海里升出来,两姐妹商量着分工轮流升起照亮世界,不让海水老往上涨。月亮让太阳先出来,太阳说:“白天出来我害羞。”“那么你就晚上出来吧!”月亮谦让姐姐说。太阳又说:“夜里出来我害怕。”月亮问:“那怎么办呢?”她想了一想,对姐姐说:“你还是白天出来吧!不必害羞,我给你一把针,谁要看你,你就用针扎他!”所以直到现在,人们要是在烈日下瞧她,总是那么扎眼。月亮轮到晚上出来,心里也有些害怕,因此便带着一只兔子做陪伴。
第三种,卵生说。这类神话,主要记载于本教的经典中。神话讲:世界形成之时,有位叫南喀东丹却松的国王,拥有“五种本原物质”。法师赤曲巴把它们搜集起来,放入他的体内,轻轻地“哈”了一声,就吹起了风,当风以光轮的形式旋转起来时,就出现了火,火越烧越旺,火的热气和带有凉意的风相接触,产生了露水,在露珠上出现了微粒。这些微粒被风吹落,堆积成了山。法师又从“五种本原物质”中生出一个发亮的呈牦牛状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呈锥形的卵。然后,用一个光轮去敲发亮的卵,产生了火光。雨和雾又从“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来,形成了海。于是天、地、海出现,世界就这样造出来了。
第四种,天地混合说。也有一首歌唱道:
问:“最初世界形成时,
天地混合在一起,
请问谁把天地分?
最初世界形成时,
阴阳混合在一起,
请问谁把阴阳分?
……”
答:“最初世界形成时,
天地混合在一起,
分开天地是大鹏,
大鹏头上有什么?
最初世界形成时,
阴阳混合在一起,
分开阴阳是太阳,
太阳顶上有什么?
……”[3]
第五种,大神开天辟地说。这类神话多流传在具有白石崇拜的四川藏区。神话说:远古时候,有两位大神,决心开天辟地,让万物和人类都发展起来。开始时,屡遭失败,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想出了用白石支天的办法,将天地分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白石具有如此巨大的神威,所以被视为“灵物”,专门用来镇屋、镇基,以保护生者和死者的安宁。[4]
第六种,绷天绷地说。这一神话流传在四川白马藏区。神话讲:“……老母虫木日扎该忙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钻过去,正看见罗拉甲伍在绷天。天绷好了,是圆拱形的,在上方。后来杀拉甲伍又绷地。地是圆球形的,在天底下。可是一比,天绷小了,地绷大了,怎么也盖不严。罗拉甲伍报怨杀拉甲伍说:‘你看!叫你先绷你不听,这下子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只好使劲挤地,把地挤小一点。这下,天和地终于扣严了。在挤的时候,地面上有些地方鼓了出来,有的地方陷了下去,鼓出来的地方成了山坡、高地;凹下去的地方就形成了沟壑、海子。”[5]
就一般情况而论,一个民族有一个创世神话,而藏族创世神话如此之多,这与藏族居住的地域辽阔,族源众多不无关系。远古时期,青藏高原上居住着众多的氏族、部落。在很多的藏文史书中,都有四十小邦、十二大邦的记述。到了公元六世纪,尚有苏毗、白兰、羊同(向雄)、附国、党项、突厥、吐谷浑等部落、部族存在。后来,经过部落之间频繁的征战和密切的交往,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藏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大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流传,这就构成了藏族创世神话的多样性。再加上藏族居住的地域辽阔,除西藏外,还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交错杂处。长期而又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的创世神话受到了其他民族创世神话的影响;有的甚至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创世神话,经过加工、消化而成为自己的神话。如上面介绍的木里自治县的大鸟肢体化生型神话,就与彝族的创世神话极为近似。彝族神话讲:天神取下虎的二膀化为日月,眼睛化为星星,肠胃化为江河,皮毛化为草木。所以,这些多姿多态的神话,又成了我们认识和研究藏族族源、藏族形成过程,以及与其他兄弟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
与此同时,上述创世神话,还告诉了我们藏族先民的原始图腾。同是一个肢体化生型神话,北欧神话说,万物是冰巨人伊密尔的大尸体化成:肌肉形成大地,眉毛形成山,齿成崖石,发成树木与百草。这与我国盘古神话描述的基本相同。盘古垂死时:“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6]两则神话都说巨人肢体化生为世界万物,而彝族、藏族神话则说世界万物是由巨兽肢体化生而成。彝族的巨兽为虎,藏族的巨兽为鸟,更多的是牛。确切地说,是青藏高原特产的牦牛。这反映了彝族的原始先民崇拜虎,藏族的原始先民崇拜牦牛。至今山南穷结一带,还流传着雅拉香波山神是一头牦牛,从牦牛的口、鼻不断喷出风暴的神话,在藏文史书中,更把雅隆部落的祖先与牦牛联系在一起,说吐蕃历史上的七贤臣中的第一位贤臣——茹勒杰,就是止贡赞普的妃子,被罗昂达孜赶到山上放牧羊群,熟睡后,与一头白牦牛山神化成的白衣人交欢所生下的孩子。是他帮助止贡赞普的儿子打败罗昂达孜,重新获得王位的。这就让我们联想到雅隆部落图腾的对象是牦牛。他们在部落联盟的大会上,或者在与其他部落作战时,均以牦牛作为部落的标记。随着雅隆部落与其他部落交往联系与相互融合,雅隆部落自身也发展壮大起来,在部落战争中,一直处于优胜地位。最后,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他们的图腾,成了众多部落或部族的崇拜对象。而个别的部落或部族仍保留着过去氏族、部落的图腾,如在神话中出现的大鸟、白石图腾等。
二、丰富无比的山神神话
藏族神话中,以山神神话最为丰富。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山高水险,地势高寒,人们常在山崩、地震、泥石流、冰雪、风暴威胁下生存,生活条件较之其他民族严峻,因此对山神的崇拜特别普遍,几乎是每座山峰都有一位山神,每一位山神几乎又有一个动人的神话。在西藏,比较有名的,有雅拉香波山神神话、念青唐古拉山神神话、纳木娜尼峰山神神话、珠穆郎玛峰山神神话和长寿五姐妹神话;在青海,有阿尼玛乡山神神话和年保玉载匝山神神话;在甘肃,有阿米年青山神神话;在四川,有斯古拉山神神话、木尔多山神神话、格聂山神神话、卡罗日山神神话;在云南,有纳格拉山神神话;等等。而且山神神话往往与江河湖泊的神话交织在一起,山神大多为男性,江河湖泊的神灵多为女性。他们之间,有的是兄妹,更多的是夫妻或情人,这不仅反映了青藏高原的山多为雪山,溶化的雪水即在山脚汇集成江河湖泊的自然特点,还演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里程。如流传在珠峰地区的《长寿五姐妹》神话里讲:珠峰地区,有五座山峰,他们原来是五位女神。大姐扎西次仁玛,长得年轻漂亮,全身素装,一脸温和的笑容,骑一头白色狮子,左手持一支占卜神箭,披着孔雀毛制成的披风,头戴华冠,主管人间的福禄寿辰,奉献给人类的是聪明和智慧。二姐婷吉希桑玛,身着绿装,手持魔镜和一根系有彩带的木棍,骑一匹野马,主管星算,奉献给人类的是预知未来的智慧。三姐米玉洛桑玛,身着黄色衣服,右手持装满粮食的盘子,骑一头金黄色老虎,主管农田,奉献给人类的是食物丰富的福禄。四妹决班震桑玛,一身红装,手持一个装满宝物的盘子,骑一头红色雌鹿,主管宝库,奉献给人类的是宝物增多的智慧。小妹妹名叫达嘎卓桑玛,全身碧绿,容貌秀丽,身穿轻柔天衣,手持占卜神箭,骑一条遨游天空的玉龙,主管畜牧,奉献给人类的是生畜繁荣的智慧。在珠峰脚下,有五个冰雪湖,每个湖有不同的颜色,与五位女神的身色一致,看来这一神话,比其它的神话较为古老,它是母权制氏族社♂的反映。当时“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丹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重的地位。”[7]这是由于在生产上处于采集经济时期,采摘野果,分配果实,以及养老育幼等方面,妇女均比男子擅长;在氏族上,当时处于群婚制阶段,子女只知其母,不识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而一群男配偶却象过客一样,并不重要。因此,在氏族中,母系血缘是唯一的;在智力上,妇女遥遥领先,处于被神化的优越地位。因为原始时代的生产劳动、分配管理等社会实践,培育和锻炼了妇女的聪明和领导才能。正如拉法格所说:“妇女对于不会操心和没有预见的野蛮人是神明,她,聪明而有预见的人,支配他的命运从摇篮到坟墓。男人是在智力的收获和自己日常生活事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一开始必将妇女神话。”[8]
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男子在谋取生产资料方面起了决定作用,他们在狩猎、捕鱼、农耕、放牧、运输,乃至掠夺性的战争等方面,都超过了妇女,担当了重任,在家庭、氏族和整个社会中,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便由野蛮走向文明,婚姻也由群婚制经过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发展。正如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所讲:“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与一夫多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9]这色彩斑斓的婚姻形式,在神话中都有体现。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纳格拉山神神话《神奇的女山神》中就讲:岗拉山神和翁水山神原来是一对好朋友,后来岗拉山神被多情、风流的女神巴丹拉姆的美貌所迷住,便借口去到女山神居住的纳格拉赤土仙洞游玩,久而久之,与女神产生了爱情,时常留在巴丹拉姆处过夜。巴丹拉姆女神经常去格姆仙洞玩耍,必须经过翁水山神的住处。不知不觉翁水山神也对巴丹拉姆产生了爱情,时不时也挽留她在自己的住处过夜。这事被岗拉山神知道后,他怒火燃烧,举起乌朵[10]狠命一击,恰恰打在翁水山神的脚下。翁水山神也不示弱,他绷紧弓弦,一箭射去,击中了岗位山神的左眼。巴丹拉姆女神听说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也不去理采两位山神。这则神话是一妻多夫制下男女关系、地位的再现,那时整个社会处于对偶婚阶段,妇女还有极大的独立性,至少在婚姻问题上,她们还可以自由地选择丈夫或情人,如同神话中所讲的巴丹拉姆仙女一样。但男子独占女子的欲望已经萌生。到了后来,不知经过了多少世纪,母权制被推翻,女性遭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惨败,母系氏族时代“至高的母系”地位,被宇宙的合法主宰“至高的父系”所取代。于是在神话中又出现了一夫多妻制的现象。如《纳木娜尼峰》的神话讲:纳木娜尼峰是喜玛拉雅山系中一位美丽出众的女神。一天,她赶着羊群在巴嘎尔大草原上放牧,在回家的路上,远远传来悠扬的笛声和小伙子的歌声,她寻着歌声和笛声找去,原来是住在她附近的山神——冈仁布钦。两人便相爱了,第二年结成了夫妻。但在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上,冈仁布钦又迷上了另外一位美丽妖艳的姑娘,她就是玛旁雍措仙女,她是特提斯海王的女儿。一次纳大娜尼峰女神因寻找丢失的牛羊,来到湖边,无意中发现了丈夫和一个女人鬼混,本想大闹一场,但又不想给丈夫制造难堪,强忍悲痛,回到家中,不但没有埋怨丈夫,反而对他更加体贴温存。但冈仁布钦堕入了玛旁雍措的情网不能自拔,不时向妻子撒谎、遮掩。纳木娜尼峰女神见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不能使丈夫回心转意,便痛苦地决定回到喜玛拉雅山系的大家族中去。一个漆黑的深夜,她离开丈夫,走在巴嗄尔大草原上的时候,东方出现了曙光,她四肢僵硬,又还原成了一座冰雪覆盖的雪山。冈仁布钦第二天起床寻找妻子的时候,也还原成了一座雪山。那妖艳的玛旁雍措仙女被化成了一个湖泊。她就在冈仁布钦与纳木娜尼山之间,仍然用媚眼来挑逗冈仁布钦。但醒悟过来的冈仁布钦再也不理她了。
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父系制代替了母系制,世系和财产的继承,都按父系计算,人类便产生了祖先崇拜。山神神话也由描写单个的神进而成为描写以地域为中心的山神神系。如神话中记述阿尼玛乡山神共有三百六十个“玛”系兄弟,他们各自骑着虎、马、豺、狗等野兽在山野嬉戏。山神与他的妻子有九个儿子和九个女儿。九个儿子骑虎,九个女儿皆骑杜鹃鸟。而阿尼玛乡山神,在另一则神话中则讲,他是沃德巩甲山神的第四个儿子。沃德巩甲山神原是藏区称为“世界形成之九神”中的第一位,他有八个儿子,他们是雅拉香波、念青唐拉、蛟乡顿日、阿尼玛乡、岗巴拉杰、雪拉居保、觉沃月甲、西乌卡日等山神。他们以狩猎、游牧为生。一日老人外出狩猎,碰到了一大群逃难者,说朵康出了妖魔,请求老人降妖。老人把自己的儿子都分派到各处去降伏妖魔。老四去的地方是安多,降伏妖魔后,他在那儿建立了一座九层水晶宫。后来,四儿子与父亲沃德巩甲山神相会时,水晶宫变成了一座大雪山,它就是阿尼玛乡山。
从神话中,我们还隐隐看到了青藏高原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直到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历史进程。在斯古拉山神神话中,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王朝组织的内部结构。斯古拉山神便是神王,他的仙妃是措曼杰姆湖女,他供养的上师是普聂班丹山神,他的大臣是亚里西勒与贡日山神,扎隅郭松山神是他的大将,提普多协尔山神是他的勇士,扎夏、扎聂、扎当、玛滚青等山神则是他的兵卒。除此,仙妃措曼杰姆还有众多小山神作她的女婢,也有许多小山神是斯古拉山神的奴仆。神话中的神系世界,俨然就是吐蕃时期的现实社会。所以通过我们对藏族神话的剖析,对藏族社会,特别是藏族原始社会,将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三、浓郁的宗教色彩
藏族神话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藏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如同孪生姐妹一般,同源于人类处于童年时代,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诸如天、地、山、川的形成,风、雨、雷、电的产生,鸟、兽、虫、鱼的出现,日、月、星、辰的升落,春、夏、秋、冬的变化等等,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神在控制着,神能给人类带来吉凶祸福,于是对神产生一种敬畏情绪,便向神献祭祈祷,以求免灾得福,从而出现了最初的原始的多神教——笃本。另一方面人们对大自然的种种奥秘,根据自己的认识能力,加以猜测和解释,并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不断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而且在此基础上,渴望取得更大的胜利,由此便出现了神话。神话中出现的主人公,如天神、风神、火神、山神、水神、树神、崖神、自在神、星宿神等等,也是原始笃本崇拜的神灵。他们开始大多是以天体、山脉、河流、湖泊、星宿的自然面目出现。后来与动物崇拜相融合,自然的形体由动物取代,例如羊、鹿、野马、牦牛、蛇、龙等。最后,随着外来辛饶氏的本教教义的传入,神灵形体逐渐又由动物形体向人的形体过渡,原来动物形体的神灵,变成了伴属神,或者成了人体神灵的坐骑。如本教所讲的世间四大本原神祇之一的火神,他的形象是:右手握念珠,左手捧火的祭品,骑一只山羊,身着天衣,头戴宝冠,下身穿五彩丝裙。主管水、火、土、风四大本原物质中的火。风神则是头戴宝冠,项戴珍宝项链,上身披柔美天衣,下身穿丝制彩裙,双手挚风旗,骑一头无鞍牡鹿,在和风中奔走四方。而水神却头戴宝冠,两身垂挂珍宝耳环,手戴珍宝手镯,脚戴珍宝足钏,双手握水蛇,骑一条硕大无比的巨龙,行走在碧波之中。念青唐古拉山神,全身白色,骑一匹四蹄雪白骏马,右手持藤条,左手握水晶剑。如果说藏族神话与原始的笃本都同源于万物有灵的信仰,两者互为胚基,是当时原始人类心灵中开出的两朵并蒂莲花的话,那么,藏族神话与后来吸取了外来辛氏本教发展起来的本教之间,则是彼此依存,互相补充,相荣相长的关系。本教的焚香祭祀经或祈祷颂文,以及祭祀仪书中,保存了不少的神话,如上面介绍的《斯古拉山神神话》和《年保玉载匝山神神话》。本教的巫师,往往又是神话的传说者与演唱者,他们在向众多神灵供献牛、羊等祭品时,也用传说和演唱神话来愉神、颂神,达到禳灾、祈福的目的。神话的内容成了本教宗教心理和观念的集中体现,是其宗教思想核心的组成部分。而本教的焚香祭祀等宗教活动又是神话观念的集中表现形式。神话促进了本教的发展和延续,以及强化其宗教崇拜的情感。相反,本教的存在又在不断丰富、弘扬神话的内容,使其感召力与感染性、艺术魅力更加提高,成为藏族艺术的珍品。
到了公元七世纪,当佛教传入西藏以后,本教虽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神话并没有因此而毁灭,而是逐渐打上了人为宗教的烙印。如流传在广大藏区和搜集在各种历史典籍中的《猕猴繁衍为人类》的神话就讲:观音菩萨点化的一只神猴,到山南穷结地方的崖洞修行,一罗刹女来到他跟前,要求与他结为夫妻。神猴说:“我是观音菩萨跟前的持戒弟子,若娶你为妻,便破了戒律。”罗刹女回答说:“若不答应,我便自杀。”神猴想:我若不答应她,将造极大罪业。于是前往观音菩萨跟前,说明原由。由观音菩萨和度母加以指点后,神猴便与罗刹女结合,生下六个儿子,没毛没尾,以野果为生。后来繁衍的后代众多,果食吃尽,饥饿之状,老神猴不忍目睹,遂又去求观音菩萨,赐以不种自收的谷种,诸猴饱食其谷,能作人语。他们吃野谷,穿树叶,遂变为了人类。神话中将佛教的神灵观音菩萨说成是藏族人类繁衍的主宰者,自然是在流传过程中佛教徒的加工变异而形成的。另外,还有一些神话,由于神话中的神祇被莲花生大师所征服,变成了佛教的护法神。神话也因此由主要叙述神的世界而转为叙述人神相混,以人为主的世界,神话也就演变成了传说,如流传在西藏的一则传说讲:一个名叫玉纳金的国王,为墨竹工卡龙女墨竹色金的美色所动,常跑去与她幽会,尽管龙女长着一条尾巴,他也毫不忌讳。但是,终于有一天,国王的咒师发现了这个秘密,不让国王与龙女来往。无论龙女如何哀求,咒师都不肯答有让他颜见面。最后,墨竹色金只好决定与咒师斗法。咒师自知不是她的对手,算向莲花生大叔求救。莲花生来到墨竹公卡,接受了龙女的挑战。双方开始斗法,只见祷条巨龙腾空而起,一只大鹏鸟紧跟在后,刹那间,天昏地暗,地动山摇,突然又云开日现,晴空万里,但见成千上万条红蛇从天而降,原来巨龙就是墨竹色金,那只大鹏乃是莲花生的化身。墨竹色金战败后,对莲花生言道:“今日做了大师手下的败将,愿听凭处治。”莲花生就让她去协助修建桑耶寺。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问她有什么愿望。墨竹色金念念不忘她的情人玉纳金,只要求给予她一个人的躯体。莲花生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变成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女子,遗憾的是,由于她修炼未到家,莲花生未能将她的龙尾巴变成双腿,因此,至今人们在龙王庙中看见的龙女墨竹色金的塑像,仍然是人身龙尾模样,不过她已成为受人尊敬的佛教护法神了。这一变化,反映了西藏宗教史上,佛教与本教之间,相互斗争,彼此吸收,互相融合的社会现实。据藏文史书记载,吐蕃赤松德赞以前,“王以本治理邦国”,到了赤松德赞作赞普时,信奉本教的贵族与王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赤松德赞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暗中支持佛教,派遣大臣巴·赛囊从印度请来大乘佛教显宗的佛教徒寂护入藏传教,不幸被反佛教的势力所赶走。寂护回去后,又将密宗大师莲花生请来。莲花生搞的那套咒法,与吐蕃的传统观念较寂护所传播的印度佛教大乘显宗的教法更为接近,因此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将本教的神灵吸收为佛教的护法神,更减少了崇信本教的贵族的抵触情绪,故而才使佛教在吐蕃立住了脚跟,建立了桑耶寺作为据点传播佛法。但佛教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这阻力不仅来自贵族,也来自王室的个别成员,如赤松德赞的王妃蔡邦萨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莲花生不得不离开吐蕃,而象遍照护等吐蕃本地的佛教徒则被流放,但终因佛教的教义、仪轨等各方面比本教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又得到赞普的鼎力支持和苦心经营,佛教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达到了足以与本教抗衡的程度。赤松德赞见打击本教的时机成熟,便提出让佛教和本教的代表人物进行一场大辩论。辩论以本教徒的失败而告终。赤松德赞趁机宣布了三条命令:一、所有本教徒均改信佛教;二、本教徒必须放弃宗教职业,做一般的纳税百姓;三、如果既不改信佛教,又不愿当平民百姓,就流放到边荒地方去。这一命令颁发以后,本教徒中的一些人迫于形势改信了佛教,另外有许多人则选择了流放的出路。传说中,关于莲花生大师征服妖魔鬼怪和墨竹色金龙女,以及众山神为佛教护法神的故事,就是这场佛本斗争的艺术再现。
四、幻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在藏族的神话世界里,没有抽象的概念和议论,只有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以及原始初民淳朴的感情奔放的想象。它是那样的天真可爱,生动感人。如在一首古歌里讲到太阳的时候,这样唱道:
“太阳有父有母也有儿,
太阳的父亲是谁?
太阳的父亲是朝晖;
太阳的母亲是谁?
太阳的母亲是夕照;
太阳的儿子是谁?
太阳的儿子是中午的烈焰。
……
太阳早晨吃的是什么?
太阳早晨吃的是高山的花草。
太阳中午吃的是什么?
太阳中午吃的是它普照的东西。
太阳黄昏吃的是什么?
太阳黄昏吃的是重重青山。”[11]
歌中把太阳完全人格化了,把它当成有生命,有亲属,要吃东西,会走路,要睡觉等和人没有两样,幻想瑰丽多姿。
藏族神话中的幻想,绝不是描神画鬼毫无根据的空想,而是以客观现实作为基础,与丰厚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自然和社会现象在藏族先民头脑中的曲折反映。如有关羊八井地区的一则神话中讲:相传很久以前,旭格拉山的山神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每当热水湖上薄雾弥漫,宛如轻纱白帐笼罩的时候,母女二人便相伴来到湖中,沐浴戏水。人们还说:女神有盏金灯,每当她们高兴的时候,便把金灯高举在湖上,金光四射,照亮了湖水和雪山,照得周围一带鲜花盛开,百鸟齐鸣,成了人间的仙境。这则神话,如果没有羊八井众多的地热田,没有地热田中无数的高温泉眼整天散发着热气,使那里云雾缭绕,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现实美景,也就没有人间仙境的奇特幻想。又如,据近代科学考察,在远古时代,西藏高原一带,原来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才渐渐升高成为高原,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增高。我们在上面介绍的《大海变陆地》的神话,很可能就是这一自然现象的遥远、曲折的艺术反映。而关于《猕猴繁衍为人类》的神话,又与人类由古猿中的一种进化为人类的科学论断完全巧合。而山南河谷一带,气候温和,水草丰茂,适合于农耕开发。神话把它作为藏人种族繁衍之地,确实让人迷惑,它到底是神话还是科学。
除此,还有许多物种神话和生产生活。如《驯虎青年》,是以藏族原始先民狩猎时代的生活现实作为基础的;《狗找朋友》、《马和野马》等神话,则与青藏高原的原始先民由单纯狩猎阶段开始走向畜牧业喂养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种籽的来源》、《狗皮王子》、《青稞种籽的来历》等神话,也是以藏族先民由单独的畜牧业饲养迈向农业耕种作为前题的。这些神话,反映了藏族原始先民在改造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如《种籽的来源》就讲:从前,当天地开辟以后,地上没有种籽,人们都住在岩洞里,靠着出外打猎维持生活。然而,大自然给人间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空中陆续升起了九个太阳,万物烧为灰烬,大地成了焦土。这时,有一个青年,根据喜鹊报告的消息,准备了应付的措施,他历经千辛万苦,为寻找生命的所在——天泉,翻山越岭,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天的尽头。在这儿他不仅看到了美丽的山山水水,还得到了真正的爱情。在情人的帮助下,青年机智地排除了天神一次次的刁难,完成了“火耕地”的开垦等等。最后,和天女结为良缘,瞒着天神,巧妙地带上青稞、小麦、葫豆、豌豆等种籽来到人间,辛勤耕耘,不断繁殖,从此人间开始有了粮食的种籽。神话中赞美的青年,他既是一个为了群体的利益,不怕困难,敢于同大自然作斗争,将种籽取回人间的英雄,又是一个辛勤耕耘,为人类的生存,繁殖出多种粮食谷物的劳动能手。热爱劳动、勇敢、维护氏族或部落的群体利益,乃是受人崇敬的美德。实际上,神话中歌颂的青年,已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藏族先民与大自然抗争,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群体的集中代表和典型的艺术形象,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真善美的化身。
综上所述,藏族神话,是藏族原始先民创造的融历史、宗教、哲学、道德、科学和文学艺术于一体的艺术画卷,具有多学科的认识价值。同时,藏族神话奇妙的幻想,丰富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对后世的民间传说、故事、童话、歌谣、史诗和作家文学的小说,戏剧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藏族神话,是藏族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认真探讨与深入研究。
审稿人 陈立明
收稿日期1996-02-20
注释:
[1][3] 引自《藏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第10页。
[2][4] 转引自《藏族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第53页、第35页。
[5] 引自《四川白玛藏族民族文学资料集》第80页。
[6] 转引自《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吴蓉章著,四川大学出版社,第80页。
[7][8] 转引自《民间文学导论》,刘守华等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第208页。
[9] 引自《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1页。
[10] 乌朵:又称投石带。毛绳中腰成一小兜,放入石子,双折轮舞,乘势松其一端,将石抛出的工具,牧人用以驱赶牛羊。
[11] 转引自佟锦华教授文《简析藏族神话》,《西南民院学院》1985年3期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