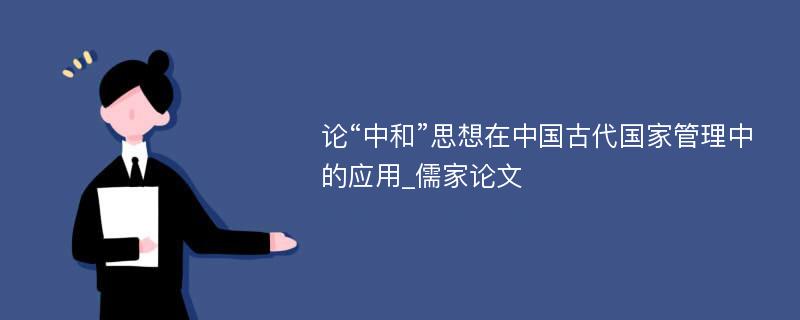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思维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源远流长,其精义主要包容在“两”、“中”、“权”这三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中。中国历代统治者将“中和”思维运用于战略管理,处理国家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统一,改善政治状况,促进经济发展等。这种思维模式所蕴含的辩证法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国家管理仍不乏启迪作用。
一、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
尚中思想在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在孔子之前这种思想大抵是被作为道德规范或某个方面的要求使用的。如,《尚书·盘庚》中记载盘庚对奴隶的训词中有“各设中于乃心”(每人心中都要有一个中正的标准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话,《尚书·酒诰》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说:“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你要经常反省自己,以实践中正之德);《孟子·离娄》下记载商汤用人“执中,立贤无方”(坚持中正原则,举立贤才,不拘一格)等。他们所讲的这些“中”是就道德规范、执法依据、用人标准等某个具体方面讲的,尚未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已体现出尚中、执中的思维倾向。
孔子总结了前人关于“中”的认识,对之进行了深刻论述,提出了“中庸”理论。孔子的中庸虽仍多用于论述道德修养问题,但已具有方法论的内容。他总结舜的统治经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提出了“两端”和“用中”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范畴;《论语·子罕》中也记载他讲到过“叩其两端”的思维方法。《论语·尧曰》记载尧对舜说的话:“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谓允当地把握“中”,就能由近及远,穷尽四海,永保政权的稳定。在这里,“中”已被看成是国家统治术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其关于“中”的认识无疑已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一些早期儒家经典性著作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如“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等,也都体现了“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思想。
历代学者从孔子的中庸理论及自身体验中,不断挖掘、丰富其哲学内涵,使之成为系统的儒家辩证思维理论。据古文《尚书·大禹谟》(学界考其为魏晋时人所作)记载,舜对禹也曾讲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话,宋人称之为“十六字心传”。汉徐干著《中论》,传为隋王通撰的《中说》,从更大理论范围和实践性上对中庸之道进行论述。到了宋代,中庸的哲学含义被理学家们阐发得更加丰富,“中和”理论臻于完备。其精义主要体现在“两”、“中”、“权”这三个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中。
“两”。孔子所说的“两端”是指过与不及。至东汉郑玄时,仍作如是注。这一解释是从程度上讲的。唐初孔颖达疏“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的“两端”为“终始”,使这一范畴不但具有了空间的含义,而且也有了时间的内涵,即认为每一过程的开始和终结亦包含在孔子所说的“两端”之中。这一解释较前人的注解有了新的进步。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已把“两端”解释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对立统一现象了。张载的“一物两体”,二程的“万物莫不有对”,朱熹的“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等,都体现了对矛盾普遍存在的感知,从而使儒家的“两”与道家的“二”这两个概念内涵趋于一致。老子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二”,即是指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即阴阳)。朱熹讲“一分为二”,论述中常常将“二”、“两”互代。这说明,儒、道在对对立统一规律认识方面虽表述有异,但实质已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了。
“中”。过去人们多把儒家的“中”解释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与辩证法毫不相干。这种认识至少是片面的。儒家的“中”并不仅仅是指中间状态,而是讲处理矛盾的适度性问题,大致可将其理解为适中、适宜、适度、恰到好处。其要义是使对立物达成和谐的统一。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反对“同而不和”(《论语·子罕》),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和是指内部的和谐,同则是表面的同一,二者有质的区别。《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才能繁荣昌盛,“同”则只会使事业断绝。可见,儒家的执中思想中虽包含有折中、调和的内容,但绝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儒家认为,要执中,就必须开展反对过和不及两种倾向的斗争,是很讲原则的。这一思想超越了道德修养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犹不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路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1 〕他用量质互变规律考察了中庸思想,认为“中”是指“相对安定的质”,这个质有“过”和“不及”两个方面,通常表现为量,当这种“过”和“不及”的量没有超过一定的度时,事物仍保持原来“相对安定的质”,但当其超过一定的度,事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他据此提出“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是对中庸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的科学的哲学分析和概括。
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中”必须定位准确;否则,就会把反倾向的斗争搞错。孔子把“中”最终定位在奴隶制社会的“礼”上,“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记·仲尼燕居》),这就使他的中庸思想在政治上具有了保守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甚至会滑向反动,以此为标准反对过和不及,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可见,把“中”的位置定错了,其反对倾向的斗争也必然随之错,持之者曰“中”,实际上是“过”或“不及”;反之者曰“过”或“不及”,实际上恰恰是“中”。那么,应把“中”的座标定在什么位置呢?答案只能是客观规律,换言之,人们应使自己的认识唯客观规律是从,以此为准,开展的反对“过”和“不及”两种倾向的斗争,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否则,从狭隘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出发,从唯心主义、实用主义、长官意志出发,就会将“中”的位置定偏,出现欲“正”何曾“正”,云“中”未必“中”的后果。二是开展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个“和”字,即所谓“致中和”,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这一点非常重要。儒家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认为只有达到“中和”状态(高度和谐),才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发育,这与《老子》的“三生万物”的“三”含义相通,所谓“三”,亦是指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和合状态。这种“和”不是不同质事物的物理性混合,而是有机的化合,它和谐、有序、浑然一体。那么,“和”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古人认为,“不学乐,无以知和”(《中说·立命篇》),只有音乐所表现的那种“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意境才能使人真正理解“和”的含义。古人认为,只有这种“和”才能事业兴盛。否则,只强调斗争,或只强调同一,都背离了“中”,都会产生相反的后果。
“权”。即权变,其要义是因时因势制宜。儒家认为,“执中”并非固守一点而不知变化,认为那样,实际上不是“执中”,而是执偏,不仅不合道,而且还有害于道。《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害百也。”同书《离娄上》举例释“权”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者,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是封建礼教之经(亦即中),但嫂子掉入水中,做弟弟的应该用手把她救上来,这是权宜之变,同样是符合经的。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也主张实行权变,他说:“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伸),非强暴也。义以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荀子·不苟》)他在《议兵篇》中甚至具体地提出了君、将必须具备“五权”的要求。王弼注《易·系辞下》“巽以行权”中的“权”为“反经合道”,即“权”看似违反经,实则合于道,精譬地讲出了“权”与“中”的辩证关系。朱熹提出:“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孟子集注·尽心上》)这些论述都揭示了“权”与“中”的辩证关系。但同时他们又指出,“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可暂用而不可常用;用权要有度,不可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化等。否则,他们就要坚决反对了。
对“权”与“中”辩证关系认识比较深刻的应属兵家。《司马法·仁本》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孙子将“权”发挥到极致,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命题,为一些儒家学者所不容。从荀子到董仲舒,直到宋、明、清的一些儒家学者对此都提出过尖锐的批判。但亦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宋朝的黄震就说,孙子的“诡道”、“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黄氏日钞·读诸子·孙子》)。郑友贤也说:“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则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无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孙子遗说》)较深刻地揭示了“权”与“中”的辩证关系。
总之,“执两”、“用中”、“行权”是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主体内容,三者密切相联。“执两”是基础,只有“执两”才能“用中”,但只有“用中”,也才能真正做到“执两”。“执中”不是“执一”,而必须因时因势“行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中和”的目的。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专门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专门系统的“权”的理论。兵家的权谋理论与儒家的执中理论相结合,用老子的话概括,就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经国治军胜敌的理论利器。
二、“中和”思维在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国家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推进社会进步而进行的管理国家和军队的具有全局性、长远性、高层性特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将“中和”思维运用于这种研究和管理活动中,主要体现在对一些重大关系问题的处理上,诸如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宽与用严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强调用“中和”思维处理这些关系,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一)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
中国古代国家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国君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君主为了对整个国家实行有效管理,必须将部分权力分割给不同部门和地方。这种权力分割中出现的“过”和“不及”都会对中央集权造成损害。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到“执两”、“用中”。
中国历代君主实行权力分割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条型权力分割,即把国家大权用由上而下切割的办法分割成许多条型权力,交由不同的部门去掌握。如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即是如此。三公九卿制由丞相总理朝政,太尉主兵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九卿(各部门长官)各司其权。三省六部制又对宰相之权进行分割,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长官分掌其权,“中书主受命”(按皇帝意图起草文件)、“门下主封驳”(驳回不当或有误的文件),“尚书主奉行”(贯彻确认无误的文件)。尚书省下设六部、二十四司及九寺、五监,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地方政权中也有相对应的机构,从而构成由上而下的条型权力系统。二是块型权力分割,即把国家权力分成许多等级,每级各掌握一部分权力,形成块状宝塔形权力结构。中国古代一般实行郡县制,即由中央统郡、郡辖县,郡县主官由中央直接任免,中央的号令可逐级传达和贯彻。也有的朝代在郡上再设一级行政区划,如西汉初期分封的诸侯王,东汉末年在郡上设州,唐中后期在州(郡)上设节度使等。由于其行政区划过大,都不同程度地给国家的统一造成了危害。三是权力的时间分割,即将同一权力在不同时期交由不同的人去掌管,不使地方高级官员久任一职,久驻一地,到了一定时候就将其调离,把权力移交给别人。这种条、块、时相结合的权力分割方式形成了经纬交错的权力网络,有利于国君统掌国家大权,维护国家的统一。
中国古代有见地的政治家十分重视权力分割的适度性问题,强调既要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又能发挥各级权力机构的能动性。既防止皇权过分集中,又防止部门、地区官员权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中国历史上看,各王朝建立初期,一般皇权力量比较强,容易出现过分集中的倾向,有见地的政治家在此时多强调适度制约皇权,防止其走向极端;到了一个朝代的中后期,中央集权能力大都减弱,地方势力膨胀,政治家们多强调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强化中央力量。对于某些中央王朝用割让中央权力以换取地方豪强势力支持自己的作法持批评态度,认为是饮鸩止渴,剜“心”补疮。如东汉窦氏政权将本属于国家的盐铁大利割让给地方豪强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即属此例。在行政区划上,古人也主张大小适中,认为行政区划过小,虽可避免形成与中央抗衡之势,但因全国行政区过多,中央难以对之实行直接有效的领导;行政区过大,则易出现割据局面。宋元以来实行的路、行省、省等行政区划制是比较适中的制度。古人从历史经验中得出,地方和军队的高级长官不宜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不宜久驻一地,但亦不可使之权力过轻,或调换过于频繁。宋朝就因此出现过“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因而屡打败仗的情况。这里都有“执两”、“用中”以求适度的问题。
(二)用“中和”思维处理变革与稳定的关系
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认识到变革与稳定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因而强调在对国家的管理上应以“小变”求“不变”,即以变革调节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发展国民经济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易经》的精义说到底就是以“变易”、“简易”求“不易”,这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朱熹强调“经”是不能变的,他称之为“体”。为了坚持“体”不变,就必须适时适度地进行权宜之变,他称之为“用”。“用”之变是为了保持“体”的不变,而“体”的不变必须要以“用”之变来维持,“论其体则终是恒。然体之常,所以为用之变;用之变,乃所以为体之恒”(《朱子语类》卷七十二《恒》)。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历代有成就的君主都实行过程度不同的变革。变革常会引起某些波动,这是为建立新的秩序,求得新的稳定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处理得好,这种波动是局部的、短暂的、低幅的,最终实现大范围的、长久的、健康的稳定和强大。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即是如此。但变革也有很大风险,操之过急,甚至会造成“翻车”。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的失败,也说明了变革的难度和风险。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变革,才能求得发展和稳定,怕不稳定而不变革,这种稳定是表面的,会掩盖、潜伏更为严重的危机。“小变”才能保持“不变”;“不变”往往会酿成巨变。所以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尽管看到变革的风险,但仍坚持以变革求发展,以发展求稳定,只不过在对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的把握上注意掌握适宜原则罢了。
变革往往会遇到分配均衡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孔子认为,治国理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一观点常为后人误解或曲解。其实,孔子绝对不是平均主义者,这里的“不均”是指分配过于不公,造成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因为这样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会酿成动乱。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之争、南北之分、农民造反、民族起义等,大都与这种“不均”有关。孔子正是从维护和改善已有的统治秩序、防止出现动乱出发,才要求对此适当限制的。中国王朝在建国初期一般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等,都曾以严厉的手段抑制土地兼并,秦始皇曾一次“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剥夺了他们在中原兼并的土地,秦汉政府推行“授田”制、“自实田”制等,也是为了防止土地过度兼并。隋、唐两代将“均田制”推行到全国,同土地兼并现象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最后均田制还是遭到破坏,出现了大量无业游民,为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如西汉初期,允许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富冠天下,吴王刘濞遂成为吴楚七王之乱的罪魁祸首。明末和清末,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朝廷不是取“有余”以补“不足”,而是对“不足”地区的民众也同样横征暴敛,致使民不堪命,因此造成了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大都从贫困地区始。唐李績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旧唐书·李績传》)此话极为朴素,然而却是真理。
变革就要进行利益调整。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处理好满与损的关系,以损求益,以亏求满,立足长远,支持变革。古人从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的大量极则反、满则倾,盈则损的现象中得出教训,从而提出了以损求益的“持满”之道。《荀子·宥坐》载孔子之言:“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抑而损之之道也。”儒家的这一思想与道家的贵柔守雌思想是相通的。在一些政兵书中亦有类似论述,如《六韬》提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武韬·发启》)就体现了这一认识。
中国历史证明,在利益分配上,要求社会实现绝对的均衡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严重不均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统治者必须不断用变革的手段调整“均”与“不均”这对矛盾,使过和不及的量变幅度不超过质变的界限,从而使整个社会保持“中和”的状态。
(三)用“中和”思维处理用宽和用严的关系
在对国家管理方法上,儒家主张恩威并举,宽严相济,张弛结合。认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2〕;“张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法家、兵家和一些有见地的政治家很多论述与儒家这一观点相通,但其论述的法治色彩多于儒家的伦理说教。
首先,古人主张确立法制。“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凌),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司马法·天子之义》)。“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汉书·刑法志》)。在制定法律法令时,必须把握两端,“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旧五代史·选举志》),防止出现过和不及两个极端。曹操的儿子曹丕就犯过因不先立法制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错误。他即位不久,社会上对他不满的言论甚多,曹丕对之深恶痛绝,下令说:有妖言惑众者杀,有告发妖言惑众者赏。导致互相诬告的事件越来越多。曹丕又下诏书说:“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这样一来,即使想实事求是揭发问题的人也都望而却步。曹丕在鼓励人们揭发问题时,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倾向:诬告。当他纠正这种倾向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他政治上犯有幼稚病,不先立法制,在思维方式上违反了“执中”原则。历史上类似现象屡见不鲜,原因盖在于此。
其次,古人主张在执行法律时要赏罚适中,既反对过严,又反对过宽;既反对过密,又反对过疏。所谓“师多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司马法·天子之义》);“赏罚不可以疏,亦不可数。数则所及者多,疏则所漏者多。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民不劝,罚轻则民亡惧;赏重则民徼幸,罚重则民无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徐干《中论·赏罚》)。这些论述都体现了“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
再次,宽严因势而权。政失之于严,则济之以宽;政失之于宽,则纠之以猛。秦末,政失之于暴,故汉高祖以宽得之;汉末,政失之于宽,有见地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等,都主张以严纠宽。王猛治理前秦时,主张治乱世施以重刑;西魏大臣苏绰治国实行“非平世法”,其子苏威则在隋初反其道而以宽得人。民国蔡锷提出,在“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3〕。这些言论和做法都体现了审时度势、因势而权、 以权获正的思维特点。
(四)用“中和”思维处理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
军队是国家机器中的重要成份。国家最高统治者管理军队与管理地方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但贯彻“执两”、“用中”原则却是一致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处理控御军队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矛盾,谨防顾此失彼,出现过或不及的失误。
为了达到对军队控御的目的,历代王朝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大都实行发兵权、统兵权、指挥权三权分离的制度,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掌握。其次,在全国武装力量部署上,实行“居重驭轻”原则。如汉、唐都以强大的军队驻守京师。唐太宗时设立的折冲府有600多个, 总兵力约60万人,分布在全国10道7府77州之中, 其中首都长安所在地的关内道就有280多府,兵力约20余万,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 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明清时,也是按“居重驭轻”原则布署兵力。再次,实行各部队互相制约原则,使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相互制约,内外维系。汉代的中央部队中,南军与北军互相制约,北军各校之间互相制约,南军内部郎卫与卫尉之间也相互制约。唐前期南衙府兵与北衙禁军互相制约;府兵中,十六卫互相制约,十六卫又与地方军、边防军互相制约等。外军难于专擅军权而割据一方,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机关的将领也不易利用本系统的军队发动变乱。所谓“下分争,则上安”(《战国策·楚一》)。
但任何事物无不包含其相应的反面。宋代把相互制约的兵力部署原则推向了极端,实行“将从中御”,甚至要求领兵将帅必须按朝廷事先制定的阵图布兵打仗,使军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历史经验证明,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必须适度,既要注重控制,又要提高其战斗力;既要使之相互制约,又要防止其互相掣肘;既要居重驭轻,又要防止削弱边防力量;既要控御将权,又要对之充分信任。中国历史上在关于对将帅“御”与“不御”问题上曾发生过长期争论。孙子主张将能而君不御。后世有赞同者,也有激烈反对者,宋朝的苏轼就对此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应诏集·孙武论》)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个问题一直没处理好,非偏于此,则偏于彼,总的看,他们更注重于对部队的控制而轻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受到严重制约和削弱。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键是要完善国家体制;其次是找到控御军队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使二者都能发挥出积极的效能;再次,对将领要知而后任,任而不疑,同时建立适当的监督机制,既防止过,也防止不及。
(五)用“中和”思维处理怀柔与威服的关系
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古代王朝的统治者主张用怀柔和威服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管理,以达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所谓怀柔,主要是指“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其中包括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如树立“胡汉一家”、“华夷并重”的民族观念;实行“同服”、“不同制”的国家制度;选派良吏充任边关;实行和亲政策等。将宗教做为“驭藩之具”〔4〕,利用宗教以“助王化之遐宣”〔5〕;给影响较大的宗教领袖以适当的特权和厚赐,使宗教领袖以中央的册封和赏赐来提高、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央则利用他们的名份和权力为维护国家统一服务,二者相互为用,以达到互利的一致性;同时建立制约和管理宗教领袖的制度和措施,如朝廷掌握对宗教领袖册封、赏罚、升黜之权,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建立定期朝贡制度,作为宗教势力对朝廷臣服的表示;在管理制度上,由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过渡,限制宗教领袖的活动范围等。总之,对他们是既限制又利用,两种手段,在时上或兼而用之,或交相使用;在度上恰当把握,适可而止。
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者对割据势力和叛乱活动,主张首先“抚以恩信”,不“轻动干戈”〔6〕,尽量采用德化手段解决; 如达不到目的,就使用武力威慑和进行政治瓦解,使之畏服,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如对方仍不服从,就使用武力进行镇压。镇压中多采用“明其为贼”、“剿抚并用”、根除乱源、改革弊政,以求久安的策略。
古人强调,处理好怀柔与威服的关系,也必须使二者相济相泄,防止过或不及;做到柔而不弱,威而不欺。怀柔不是姑息,威服防止穷武。“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姑息只会“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杜牧《守论》)。只有恩威兼施,才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7〕。
(六)培养国家管理人员的“中和”思维能力
“中和”决策必须由具备“中和”思维能力的官员施行。因此古人高度重视培养“中和”思维型人才,把这项工作作为管理国家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儒学家者对此提倡尤力。历代统治者则更强调身体力行。古人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有大量“中和”思维的内容,将此做为培养和选拔国家管理人员的标准。如《尚书·皋陶谟》列有“九德”,即:“宽而栗(宽弘而庄敬),柔而立(和柔而自立),愿而恭(诚笃而恭谨),乱而敬(有治理能力而谦敬),扰而毅(顺从而果毅),直而温(正直而温和),简而廉(宽简而廉洁),刚而塞(果断而充实),强而义(强悍而合于义)”。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听《颂》时所讲的话中也包含着对国家管理人员素质的要求:“直而不倨,曲而不诎(挠),近而不逼(侵逼),远而不携(不怀二心),迁而不淫(变迁而不过度),复而不厌(反复而能常新),哀而不愁(有哀伤之心而不愁苦),乐而不荒(乐而有节),用而不匮(有节制),广而不宣(不自显),施而不费(施恩而不浪费),取而不贪(取之以义),处而不厎(守之有道),行而不流。”(《史记·吴太伯世家》)《论语·尧曰》中讲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八佾》中讲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淮南子·人间训》载孔子之言:“丘能仁且忍,辩且纳,勇且怯”等,这些论述中都包含着相济相泄的原理。如,“柔”是一种美德,但过柔就成了软弱,故须以“刚”济之;“强”是有力量的表现,但必须受到“义”的指导,过则泄之,否则就会走向反面;正直应当提倡,但过了就会成为傲慢,故要以“不倨”制约。勇与怯,二者完全相反,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亦可达成完美的统一,这正是“相济”、“相泄”之精义所在。如商鞅主张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刘秀怯于小敌而勇于大战,曹操告诫夏侯渊:“为将当有怯懦时,不可单恃勇尔”,冯道根主张“怯防勇战”等,都较好地体现了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汉代徐干提出的“疾而勿迫,徐而勿失,杂而勿结,放而勿逸”(《中论上·贵言》),《中论》讲的“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礼乐篇》),“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污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魏相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问易篇》),“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事君篇》)等,都体现了思想修养要“执中”的要求。古人认为,只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才能在为人处世、思维决策、处置事务中,保持中正的方向,而不致出现过和不及的倾向。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国家战略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国家战略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而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坚持正确的方向,就必须认识“两”,确立“中”,用好“权”,把握“度”,反对“过”和“不及”两种倾向。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而有益的启示。
注释:
〔1〕《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2〕孔子语,引自《左传》昭公二十年。
〔3〕《曾胡治兵语录序及其按语》。
〔4〕清皇太极语,见《沈阳县志》卷十三。
〔5〕清康熙帝语,见《广仁寺碑文》。
〔6〕唐太宗语,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十二月。
〔7〕《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