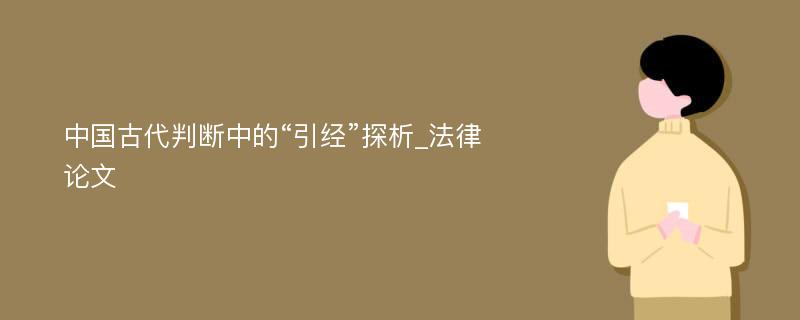
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词论文,引经据典论文,探析论文,中国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502(2012)06-014-08
所谓判词之“引经据典”是指司法官在判词中引用儒家经义、历史、典故等铺陈事实、阐释道理,最后依此作出判决。这种引用“经”、“典”的判决方式可以追溯至汉代的“春秋决狱”和“经义决狱”,它们是依照儒家经义中阐述的道德伦理原则或记述的古老判例、故事等来解决当时的疑难复杂案件。随着法律儒家化的深入发展,“春秋决狱”和“经义决狱”也逐渐发展为判词之“引经据典”。古代中国司法官为了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不仅在疑难复杂案件的判词中“引经据典”,而且在处理简单案件中“引经据典”。这无形中彰显出判词之“引经据典”的诸多特殊功用。
一、一种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
沈宗灵教授曾指出,西方法律中的“衡平”概念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公正、公平、正义;二是在特定情况下,为了避免机械适用某一法律造成不公正的结果,而寻求另一种合理的、公正的标准;三是英国的衡平法和衡平法院。①实际上,这个概括前两层含义是“衡平”的内容,后一层含义只是其在英国的表现形式。我们知道,古罗马关于“衡平”的内容其表现形式为最高裁判官法。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随着不断的对外扩张、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市民法的不平等、狭隘、僵化等缺点日益成为阻碍罗马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最高裁判官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以发布书面告示的形式,提出审判案件的原则和措施。同时,创制了许多在市民法中没有规定、甚至是违背市民法规定的诉权、抗辩权和救济手段。这些由告示、新的权利、新的救济手段等组成的最高裁判官法体系,在“公平”、“正义”的指导下被适用于特定情况,弥补和纠正了市民法的不足,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
鉴于英国和古罗马在“衡平”观念和实践上的共性,一般意义上的“衡平司法”可以理解为,司法官为实现公平、正义,在特定案件中选择适用合理、公正的其他标准的司法裁判。毫无疑问,无论古今中外,在衡平或衡平司法上是共通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古代中国追求个案实质正义的司法实践,本身就是衡平或衡平司法的过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明确指出:“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②可见,“平不夷”、“矫不直”是目标,法只是手段。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一方面,源于社会的法要合人心、通人情,才能治理天下。《慎子》指出:“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韩非子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③这里的“人心”、“人情”既是普遍的、抽象意义的,也是具体案件关系人的人心,相互间的人情;另一方面,法要度俗、宜时,才能有治、有功。商鞅说:“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④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⑤。这里的“时”、“俗”、“务”、“世”指社会情势、风俗习惯、具体案情等因素。这就是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
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模式不是像西人那样在原有法律体系之外创制另一个法律体系来衡平或者补救,而是固有司法官体系内的自我补救或衡平。⑥这种衡平司法模式经历了由“春秋决狱”和“经义决狱”到判词之“引经据典”的发展过程。李鼎楚先生认为,古代中国衡平司法正式始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⑦汉承秦制,有所损益,在司法审判中以《九章律》作为基本依据。⑧但受秦朝之法家重刑主义和“万事皆有法式”治理思想的影响,其在司法上仍带有机械性、教条性等法条主义的弊端。“汉代孔子”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正是在纠正这种司法弊端的情况下产生的。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已佚,仅从散见他书的六例⑨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抛弃了机械的适用法律条文,在深刻把握法律原则与精神的基础上,根据体现法理、情理和常理的《春秋》之义衡平判决案件。此后,汉代司法官员在疑难复杂案件中不仅按照《春秋》决狱,还依据《诗》、《书》等其他儒家经义衡平决狱。随着儒家知识与思想在汉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和官方正统地位的确立,“经义决狱”成为汉代衡平司法的一种风气和常态。
自汉以来,法律儒家化在司法、立法和法律解释领域日益深入,也促使古代中国衡平司法逐渐走向了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形式化和常规化之路,即由原有的“春秋决狱”、“经义决狱”逐渐发展为判词中的“引经据典”。历朝历代的司法官为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在某些简单案件,尤其是疑难复杂案件中,很少直接援引法律条文,而是通过长篇累牍的“经”和“典”书写判词,在综合天理、人情、国法、社会效果等因素后进行衡平司法判决。唐代颜真卿在任抚州刺史时,曾为一件离婚案写了一份简洁的“引经据典”的判词,并作出衡平司法判决。⑩案情很简单,杨志坚的妻子嫌弃丈夫没钱没权没出息,向他讨要休书以便改嫁。杨便给她写了一首诗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于是,其妻拿着这首诗去办理官府的文书。颜真卿判决准改嫁,其判词云:
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帛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这是一件极普通、法律许可的协议离婚案。按《唐律·户婚》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杨志坚夫妻双方也算你情我愿,依法准其离婚即可。但是,作为地方父母官的颜真卿考虑得更为全面和长远。在这份判词中,他先使用前燕人王欢之妻和西汉朱买臣之妻嫌夫贫贱而改嫁的历史典故事实阐说、情理分析和伦理评价,既贴切、富有人情味而又褒贬分明。又考虑到若依法准其离婚客观上会造成“污辱乡间,败伤风俗”的不良影响,而且“若无褒贬,侥幸者多。”因此作为地方父母官,他权衡法律和道德后衡平司法,对杨妻决杖二十后准其改嫁。同时赠杨志坚布、帛、米,便署随军,还要刻意让远近知悉此种表彰行为,以起到惩恶扬善、教化风俗之功效。清代是古代中国衡平司法的成熟期,大清官于成龙当为“引经据典”之衡平司法的典范。如在“婚姻不遂案”(11)中:
罗城人冯汝棠之女冯婉姑,姿容秀丽,擅女红,工诗词,与私塾先生钱万青两情相悦,私订终身,又托媒人说合后得到冯婉姑之父的允诺。然市井无赖吕豹变,目不识丁,贪恋婉姑美色,贿赂婉姑的婢女,挑拨、离间婉姑与万青的关系,又托媒人向冯父游说。冯父贪图吕家钱财,毁弃前约,将女儿许配给吕豹变。迎亲之日,婉姑拒绝上轿,被强行拖去。拜天地时,冯婉姑乘人不备,从衣袖中抽出事先暗藏的剪刀,刺伤了吕豹变。事出意外,众人乱作一团,冯婉姑乘乱逃出吕家,跑到县衙鸣冤,泣求于大人为她做主。此时,钱万青也提出毁婚约之诉。吕豹变经救治后,亦到县衙要求严惩凶手。
对于此案,其判词曰:
《关雎》咏好逑之诗,《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鍼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稳巫山,竞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作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欢谐。谁知孽海无边,风波忽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婿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聩,竟听谗言。遂使彩凤而随鸦,乃至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他。挥劲血以溅凶徒,志凯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得。仍宜复尔前盟,偿尔志愿。明年三五,堪称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者,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儿竟为奇货。须知令甲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滑纨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
于成龙的这份判词,通篇没有直接引用《大清律例》的法律条文,而是引用《诗》、《礼》和诸多历史典故叙述事实、阐情说理,最后做出冯父免责、吕豹变杖责的惩罚决定。事实上,此案件至少有两种情形涉及适用《大清律例》之相关规定。一是冯汝棠悔弃婚约。依据《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对于冯汝棠悔弃婚约的行为,于成龙是知晓法律有关悔婚之惩罚规定的,只是“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作为地方父母官,他不能不考虑孝顺的女儿对父亲的理解和谅解,并要替父亲受罚的泣请。古代法律对于子女替父受罚是许可和提倡的。但是,作为父亲悔婚受害者的女儿本不应该受到惩罚。而且,退一步讲,假如他真要是依法杖责冯父,则是女儿不孝所致,父女关系从此便有隔阂,甚至恩断义绝。鉴于此,在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中,在父亲受罚和女儿替父受罚的二难选择中,于成龙弃法律而顺人情,做出冯婉姑无需替父受罚,冯汝棠暂免杖笞的衡平判决。这既是出于对孝女的嘉奖和父女亲情关系的维护,也是对父亲之家长权威和尊严的维护。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此案件的判决倡导和维护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管辖区域内以“亲亲、尊尊、长长”为核心的道德伦理秩序。
二是冯婉姑刺伤吕豹变。由于后一个婚约是悔弃前一个婚约后形成的无效婚约,结婚更是强娶。因此,冯婉姑和吕豹变不是夫妻关系,冯婉姑的伤害行为应该按照《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上)》的规定:“折人肋……及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但是,于成龙不仅没有惩治冯婉姑,还做出了对吕豹变“应予杖责”的惩罚决定。在判词中,于成龙通过“引经据典”的情理分析和伦理评价,褒扬冯婉姑,斥责吕豹变,基本上对案件做出了事实判决。他指出,吕豹变为社会道德所不齿的“刁滑纨绔,市井淫徒”,其强娶行为“破人骨肉,败人伉俪”,严重破坏了和谐的亲情和爱情,扰乱了社会正常的道德伦理秩序。因此,从情理上讲,完全可以诛杀之,其道德之罪难以赦免。但是,法律却对这种道德败坏者及其行为没有任何相应的惩罚规定。鉴于此,他作为道德风尚的倡导者和维护者,行使地方父母官的自由裁量权做出判决:“应予杖责,做彼冥顽”。与此同时,冯婉姑刺伤吕豹变的伤害行为全因刁徒吕豹变垂涎其美色、恃势依财、逼婚强娶所引起。婉姑之行为不是普通的故意伤害行为,而是出于维护礼教所倡导的女性之忠贞,吕豹变被刺伤是他咎由自取。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于成龙明白,法律的目的是惩恶扬善、禁暴止奸、捍卫礼教。因此,他摈弃教条地适用法律,而是综合权衡法律宗旨与法律规定、情理和法律、案件的起因和结果,最后作出衡平判决:不仅不惩罚冯婉姑,还对其忠贞行为予以表扬,并判令冯婉姑与钱万青明年正月十五结婚。(12)
综上所述,判词之“引经据典”是一种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模式,它是儒家化的司法官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综合天理、人情、国法等因素后的衡平判决。同时,这种衡平司法也是一种和谐司法、民生司法。(13)司法官以“引经据典”的衡平司法判决不仅要实现具体个案的公平、正义,更要力图维护案件关系人之间和谐的亲情、爱情关系,乃至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
二、 一种文学化的司法形式主义
古代中国的司法官历来倾向于把判词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加以制作,即以文学的修辞手法对判词进行包装,追求语言的艺术化。判词之“引经据典”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的修辞形式。这些判词在形式上,大都构思精巧、句式整齐、节奏明显、铿锵有声、顺口悦耳、文采飞扬。在内容上,对案件之事实铺陈和情理阐释,充满温情、合乎人伦、褒贬分明,读来不能不使人拍手称快,赞叹再三。总之,“引经据典”的判词“弃官式语言之呆板、圆滑而以优美、典雅之文风极力阐释自己独特见解,极具浓厚美学韵味,又含深刻法理,兼容极高艺术性之判决不断奉献于世人面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的法律判决之美而倾心研读关注”(14)。
清代是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发展的高峰期。不少名吏即是通过“引经据典”衡平折狱的老吏,如于成龙、袁枚、张船山、陆稼书、樊增祥等。他们的判词均被称为“妙判”,并且风行其时,被文墨官吏奉为楷模,争相模仿。晚清名吏樊增祥经常引用诗、经、历史、成语、典故等制作判词。他的老师,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清代文学家李慈铭在评论樊增祥的判词时说,“别是人间一种文字,可与入官者作前马”。如在“嬲”字成奸案中,官宦门第冯家衰败,又加之母子不和,其婢女与仆役张祖石私通,后又嫁给官吏程福善,而此二男勾结此女将冯家财产败坏殆尽。(15)樊增祥在此案的判词中“引经据典”颇多。他首先以仲子织屦、郑庄公母子“见必及泉”的故事责骂冯景立;以《诗经》之“蔓草”比喻草间野合、露水夫妻。又以“鸠占鹊舍”谓程福善夺占冯家宅院;借用“鲁之雁鼎”(16)表示冯家所藏的古董,而以“狐裘”、“狗盗”的典故暗喻冯、程二人之行为。引述《春秋》舍子立孙之义,“入瓮”(17)的典故,“搂东家之处子”(18)之经义指张祖石私通冯家的婢女。杂用“申公窃妻”(19)和“桑中”(20)的典故指张祖石与毛子私奔,且以大车运走了冯家的财产。以“还珠”(21)的典故指张祖石将所盗窃之财物退还冯家。以“士师入梦”(22)比喻糊里糊涂断案,以“鲁盗还弓”(23)比喻盗窃者来去自如。以“家鸡野骛”谓二淫男一荡女。最后,他判道,虽有郑伯“勿滋他族”(24)和丘迟“无取杂种”(25)的先例,但还是“谕令景立来则收之,不归亦听之”。因为,当念“遗簪”之不弃的故事。(26)末了,还以“不愧李峤之无儿”(27)和“恨独孤之误我乎”(28)的典故感慨冯公会地下有知。
从樊增祥的这个典型判词可以明显地看出,判词之“引经据典”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一种文学化的叙事和修辞,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使得判词摆脱枯燥乏味等缺点,增强判词本身的可读性,读来给当事人以及案外民众以庄重的情感冲击;二是通过“引经据典”将文学中的叙事技巧、修辞艺术、隐喻手法等广泛地应用到法律判词中,从而弥补了法律语言的陌生感和晦涩难懂;三是通过“引经据典”这种文学化形式将司法判决带入情理场域中,判决就经由“经”、“典”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一种人们的情理认同。
人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或者文化构成的意义之网。(29)所以,说服国族人心者莫过于人们心中的情理之类的常识信念。古代中国司法官判词之“引经据典”就是通过饱含着伦理、人情和常理的“经”、“典”权威来说服当事人和案外人。以今人的眼光,这种文学化的修辞往往是一种非逻辑的、非科学的说服,以西人的理解这是非法理的说服。唐德刚就以西人逻辑优越、法理先进的眼光批评道:“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满口革命大道理,事实上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西方就适得其反。西方的律师,诉讼起来,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逻辑上不差,在国法上自有胜诉。因而他们的逻辑,也就愈发细密了。”(30)对于唐先生的评论,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
的确,汉语与其他语言(如西方诸语言)相比较,在司法判决中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性。但它特别长于表达人细腻的情感,“中文也特别适合用来激发情感或情绪,无论动之以义愤,动之以怜悯,或动之以仇恨,以中文为文都是很有效的。”(31)要知道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影响人们信念和行为的因素有多种,除了理性和逻辑,还有人们的心灵结构,思维模式等。(32)古代中国判词中“引经据典”的文学化叙事和修辞,展示出的一连串具有强烈伦理和人情色彩的意象,潜在地进行着常理阐说、人情分析和伦理评价,无形中获得了大众的情感认同,并将司法判决结论权威化、正当化。古人所谓:“明罚峻法,则辞有秋霜之烈”(33)说的正是在判决的事实叙述和修辞中加入伦理评价、人情分析和常理阐说有助于获得公众信念、情感、道德的认同。除此之外,古代中国的司法判词还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判词之“引经据典”更是如此。它不仅是在当事人之间司法判决,更是要通过此判决明确人们对是非曲直、善恶正邪、正义和非正义的信念,从而引导人们的言行,规范社会秩序。
所以,古代中国判词的“引经据典”是将“春秋决狱”、“经义决狱”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以文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文学化形式发展到清代逐渐系统化、惯例化甚至制度化。这种因司法追求实质合理性而重视对判词的文学修辞或“经”、“典”修辞,本身就是一种司法的形式主义,只不过古代中国在司法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化司法形式主义之路。
三、 一种司法权力的正当化策略
韦伯认为,被支配者并非总是从理性算计和功利角度服从支配者,其服从还源于深层的精神因素,即相信统治者有某种“正当性”。而从支配者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正当性’的信仰”(34)。只有结合了对‘正当性’信仰的习俗和利害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统治可靠的基础。司法权力及其判决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也必须编织一张“信念之网”,达致一种正当性以获得受众的信仰,引发其潜意识地、自觉地认可与服从。古代中国司法官就是通过诉诸于人们内心最为接受和有信念共鸣的“引经据典”话语,使得当事人对司法权力产生了“正当性”的信仰。因为“经”、“典”本身就是大众公认的祖先们生活经验的提炼和总结,也是古代圣贤的道德教诲,更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因此,借助判词之“引经据典”,司法权力从历史传统、道德和文化上获得了正当性。
在追求实质正义的个案中,古代中国司法权力的真正有效运作是通过“引经据典”的话语来实现的。这些“经”、“典”所构筑的正当性话语系统网络,不仅使得当事人对判决从情感上加以认同,也为司法官赢得了一种相对于当事人在智识上的优越性和权威性,从而保证了司法权力的顺畅运作和正当性。面对判词中一个个“经”、“典”权威话语对自己行为的定性,败诉方即使“不悦”也不得不“诚服”之,因为其根本无法用自己的生活话语、甚至法律话语与掌握“经”、“典”话语的司法权力争夺话语权。由此,经由民众对“经”、“典”知识权威性的认同和对其正当性的信仰,司法权力为自己赢得了正当性。同时,判词之“引经据典”这种司法权力正当化策略,不仅可以掩盖司法权力操作者之司法官的价值立场,体现出判决的客观与公正,也能起到保护司法官利益的作用。司法官在作出判词前,对案件事实和结论在价值判断上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前见”。但是,如果司法官在判词中明确表示他的个人价值取向,不仅可能面对为什么维护对方的利益这样的诘难,还可能受到上级官员的诘问。因此,在判词中,司法官虽然赞同了某种价值立场和观点,但也要把这种价值立场和观点诉诸社会公认的“经”、“典”权威之中,以图掩盖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点,从而避免公众和上级官吏对于自己操作司法权力及其判决正当性的质疑。
四、古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
在司法官和法律儒家化、伦理化的社会环境下,古代中国普遍存在着以“经学解释”为代表的法律解释传统。衡平司法之“春秋决狱”、“经义决狱”和“引经据典”都是这种法律解释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义解释或衡平司法根据司法官追求个案实质正义的需要,或者发生在简单案件,或者出现在疑难复杂案件。“引经据典”的解释方法一般分为两类: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和对法律判决的解释,对前者的解释是为了道德定罪,对后者的解释目的在于论证法律以道德为价值支撑。前述颜真卿在这件简单的离婚案中的判词完全是对案件事实的“经”、“典”解释,从人情和伦理上说明杨志坚是无罪的,杨妻是有罪的。最后,他弃法律规定而顺风俗人情轻罚杨妻。而在前举之“婚姻不遂案”中,于成龙则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判决都“引经据典”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在判词中,首先,对案件事实予以“经”、“典”的诠释,道德伦理的褒贬,认定冯婉姑无罪,冯父和吕豹变有罪。他总引“《关雎》咏好逑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35)来肯定人世间男欢女爱、夫唱妇随的常理、常情;用典故赞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36)冯婉姑吟工柳絮、(37)夙号鍼神。(38)又以“巫山”、(39)“偷香”(40)的典故来暗喻两人的幽会;分别用“东床快婿”、(41)“情天不老”、(42)“琴瑟欢谐”(43)之典、诗、经来形容二人完美结合的夫妻情义,相亲相爱;而将吕豹变斥为“好色登徒”,以“彩凤涂鸦”、“张冠李戴”的典故指责冯父嫁女之行为。其次,对法律判决的“经”、“典”解释,彰显出在法律与道德相冲突的情况下,法律应服从和服务于道德。此案件中冯父依法应该有罪,但念及“缇萦泣请”的道德故事,暂免对冯父的杖笞。而吕豹变虽然依法无罪,但道德认定有罪,应予惩罚。
实际上,通过“引经据典”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更深层次上实现的是法律及其判决在四个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以形而上的和谐、和善观论证形而下的法律之道的正当性;以体现祖先经验的“经”和“典”的历史传统权威论证当世之法律及其判决的正当性;以“引经据典”论证法律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支撑;以“引经据典”的个案解释之实质正义纠正法律形式正义的不足。
第一,以和谐价值为核心的“仁道精神”决定了古代中国法律解释的“趋善抑真”追求。(44)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整个人类关系的理想”。(45)具体言之,中国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善。这种价值观念反映在法律解释中就是,法律解释不是为了法律而法律,而是为了和谐而法律;寻求道德之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善,而不是法律本身之真。因此,通过“引经据典”这种承载“仁道精神”的法律解释方法,不仅能够实现天理、人情与国法等之间的和谐,也可以促成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与案外人乃至整个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和谐。
第二,以“经”和“典”代表的历史传统来论证现世法律及其判决的正当性。古代中国人不仅自然崇拜,而且祖先崇拜。表现在法律判决中,司法官就是以祖先生活经验总结的“经”和“典”的权威论证当下具体法律判决的正当性,从而获得整个群体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第三,以“引经据典”论证法律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支撑。任何社会的法律规则,都必须以其特定的价值观念为支撑,才能具有生命和效力,才能为大众理解和遵守。吾华夏民族、得益农桑、泽被礼仪。“引经据典”这一形式承载的正是儒家关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蕴含着实质正当性、合理性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在普遍的有法可依的案件中,“引经据典”是论证了依法判决的价值合理性,那么在特殊疑难案件中,“引经据典”判决则是直接以伦理道德自身真正的把握法意、法理。
第四,以“引经据典”个案解释的实质正义纠正法律形式正义的不足。法律的规定是抽象的、普遍的,它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个个案的具体情况,在疑难复杂案件中法律更是无能为力。真正的正义就是实质的正义,法律的正义仅是形式正义。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现出司法官对每一个具体案件都是在用“良心审判”,都在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
五、结语
判词之“引经据典”及其诸多特殊功用从根本上决定于古代中国的司法官制度。详言之,古代中国的司法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司法官,而是司法与行政集于一身的儒者,是儒士共同体、行政官与司法官的三位一体。行政兼理司法必然导致司法官不仅注重个案本身的公平、正义,更关注个案判决对整个管辖区域内道德风尚、和谐秩序等的影响。而司法官儒学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不单寻求判决的合法性,更追求判决的合理性。因此,作为地方父母官,为了维护这种家长式的统治和他的道德君子形象,在具体案件中必然选择“引经据典”这种衡平司法模式、文学化的司法形式、经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来论证司法权力及其判决的正当性。
张伟仁先生曾这样描述作为古代中国司法官的典型代表汪辉祖:他是一个博洽的人,既懂得法理,又熟悉实务,对于传统文化也有深切的体会,因此他对清代社会的价值和导向都有清晰的认识。他并且决心以其才能去提升并匡正这些价值和导向。所以他以追求公平正义为职志,以为民谋福为目标。而且他将这一工作几乎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所以他怀着虔诚谨慎的心情去做,一点也不敢怠慢。因为他有这种奉献的精神,所以他对自己的酬劳看得很轻。他比较重名,但绝不炫才争功。他安于清贫,因为怕非分之财会迫使他做非分之事,改变他寻求正义的初衷;它持正不阿,但是也富有同情心,只要不违背公正的原则,他处处为人着想,事事兼顾情理。所以整体而言,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给我们的印象,决不是一个只会搬弄条文的法匠,而是一个博洽通达,忠恕公正,而又和蔼热忱,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46)
与此同时,判词之“引经据典”书写的是诗化的生活方式,表达的是诗文的社会体验,充满着列祖列宗的人文关怀,蕴含着吾族吾民的常理与常情,追求的是诗性的公道正义。
注释:
①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73页。
②《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③《韩非子·八经》。
④《商君书·六法》。
⑤《韩非子·心度》。
⑥顾元:《中国衡平司法传统论纲》,《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顾元:《中国传统衡平司法与英国衡平法之比较——从“同途殊归”到“殊途同归”》,《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
⑦李鼎楚:《春秋决狱再考》,《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
⑧《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出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戈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攥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⑨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1-162页。
⑩在《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和颜真卿的《文忠集》里,均有这篇著名判词的完整记载。
(11)高潮:《古代判词选》,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12)若是吕豹变被刺死,此案之衡平司法定是不同。
(13)颜真卿在离婚案中对丈夫的物质嘉奖,于成龙在悔婚案中判决钱万青与冯婉姑明年三五结婚就是例证。
(14)洪浩、陈虎:《论判决的修辞》,《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
(15)李永祥、李兴斌:《刀笔精华新译》,石万鹏等译,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6)《韓非子·說林篇》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
(17)事见《资治通鉴·唐则天皇后天授二年》。
(18)《孟子·告子下》:“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19)《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20)《诗经·桑中》。
(21)即“还珠合浦”或“合浦珠还”。典出《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孟尝传》。
(22)典出《列子·周穆王》。
(2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九年。阳虎入鲁盗得宝玉、大弓。后又归还,避难齐、晋。
(24)《左传·隐公十一年》:“无滋他族,实偪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
(25)丘迟:《与陈伯之书》,选自《文选》卷四十三。
(26)典出《北史·韦敻传》。后以不忘旧友叫“不弃遗簪坠屦”。
(27)典出《唐语林》卷三·识鉴。亦可见《全唐诗话》卷一。
(28)《资冶通鉴·隋纪四》卷一八。
(29)露丝·本尼迪克特提出人之本性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而非生物学遗传的天性。[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30)转引自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3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32)吴玉章:《法治的层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1页。
(33)刘勰:《文心雕龙》,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35)《诗经·关雎》乃是歌咏男女相爱的诗篇,《周礼》乃是婚姻嫁娶的礼仪,五经乃是人伦纲常之本。
(36)《世说新语》。以“倚马”比喻文思敏捷。
(37)《世说新语》。称女子能诗文为柳絮才。
(38)《拾遗记》:“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云,帝改名曰夜来。妙于鍼工,虽处深帷之内,不用灯烛,裁制立成,宫中号曰鍼神。”
(39)据宋玉《高唐赋》载,楚王游高唐,梦见一女子,自称是巫山之女并且愿意陪伴他。
(40)典出《世说新语·惑溺》和《晋书·贾充传》。
(41)《晋书·王羲之传》。
(42)唐代李贺诗《金铜仙人辞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宋人张先《千秋岁》中的“天不老,情难绝”,则是翻叠“天若有情天亦老”句。此处即是。
(43)《诗经·召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44)谢晖:《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101页。
(4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46)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