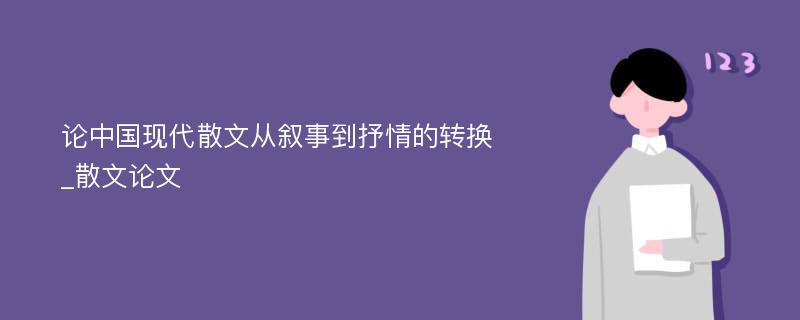
论中国现代散文从叙事向抒情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叙事与抒情的时代转换
4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文学体式也在这些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发生某些变化。一方面,人们过去所熟悉的体式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时代要求,文学需要创造新的文学体式以满足于时代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已有的文学体式也在变革自身内部的构成因素,试图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以适应新的美学原则的要求。旧的散文艺术被批判着,新的散文艺术在4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被作家们强调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散文的新时代也由此开始。
新的时代是一个抒情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叙事时代的开始。在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叙事,不只是一种文体风格,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与延安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话语。这里不仅是对抒情的否定,实际上,抒情艺术方法并未明显地被提出来作为否定的对象,但是,由于它与这个叙事时代话语方式的背离,由于它与当时特定的“抒情”产生了一定距离,因此,它在实际上是被自觉不自觉地否定了,而让位于恢宏的叙事形态的文学。延安文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散文小品,也不是杂文,而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等小说或戏剧作品。作为抒情艺术的诗歌已向叙事功能转化,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而陕北地区的秧歌这时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作为叙事艺术被提倡,也看出人们的良苦用心。发展叙事文学,以文学的叙事建设一种共同的主题,通过一定的对每个个人的“故事”的叙述,重建公共性的社群意识。这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最直接的目的。50年代初期,文学界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一方面是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其抒情情调的批判。50年代初,文学作品中的“小资情调”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文学创作中的各种体式都力避抒情性,尤其不流露个人的感情。
因此,叙事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被尊为至高无上的艺术方式,作家们也需要按照一定的叙事模式将自己的话语系统纳入到这一叙事模式中来,散文艺术也在这里向着叙事艺术倾斜。可以看出,40年代后的现代散文,那种在20、30年代被读者所接受的抒情小品已很难见到,而代之以叙事性的散记,散记也就成为这个时代的可以被接受的艺术形式。而在写法上,也往往将各种文体融为一体,加强叙事的艺术力度。作为抒情诗人的卞之琳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我们都倾向于写散文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论述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象’,但求艺术完整。”(注: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可见叙述艺术在作者心目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也说明在散文创作中,一切可以用来叙事的艺术手段都可以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去。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等作家由抒情诗人散文家而转变为以叙述为主的散记作家,也不能不说明散记对作家们的强大诱惑力。
40年代延安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散文创作中趋向于散记体式的倾向,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到方向性的作用。5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如刘白羽、杨朔、华山、孙犁等进入新中国文坛时,他们已经形成的散文观念也一同带到新中国的文学界,并成为5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流。40年代散文创作的叙事传统在50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散记体式与40年代就已形成的文艺性通讯、速写、特写等新闻纪实类的作品融合,形成了50年代别具特色的纪实性叙事性的特写、通讯等体式,这些体式进入散文创作领域后,已经在相当的层面上替代了散记,更替代了抒情性小品。而当人们从题材的角度看待散文创作时,散文进一步向着散记、速写、特写、通讯式发展,人们一再满足于散文反映生活面的宽阔,认为建国以后的散文几乎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矿山、车间、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的,自然它也走遍了学校、机关、街头巷尾”(注: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散文所取得的这些成绩,也是它的叙事艺术的成绩,是对建国以后火热的社会现实艺术表现的成绩。而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最主要的是采用新的话语体式,通过对新生活的叙事,达到歌颂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艺术水准。从国统区走进新社会的巴金、老舍等老作家,也在50年AI写作出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无名高地有了名》这样的通讯式散文作品。从50年代初开始,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散文集子,也以《散文特写选》出现,其他如《新观察》编辑部选编的1958年《散文特写选》,严文井主编的《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的《散文特写》分册,周立波选编的《散文特写选》(1959~1961年)等,散文与特写已经难以区分,而且大有成为一体的趋势。
应当承认,散文创作体式功能的叙事化,在40年代到50年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颂扬新人新事,为新时代而高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它在体式上也为现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文本,对现代散文的艺术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甚至是积极的意义。在发展中国传统的散记体式方面,尤其是使散记多元化、社会化方面,40、50年代的叙事性散文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是现代散文发展过程中,散文体式与新闻报纸等现代媒体结合的产物,它在借助现代化传播媒体的同时,将新闻通讯的写作和新闻通讯的体式融合进现代散文中来,这应当说是符合现代文学发展的需要的。当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作家的兴奋点过于集中在叙事之中,而忘却了散文的抒情功能,尤其忽视了散文体式的文学化特征,并且过于将散文混同于一般的通讯报道,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味。同时,它在以歌颂为主的体式功能中,也忽视了个人的抒情要求,散文从自我内心的观照转向社会现实的同时,审美观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是淡化、弱化了散文体式的审美要求。
于是,当作家们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叙事已经不能满足于社会的需要时,人们又再一次呼唤散文的抒情功能,要求抒情性诗意化散文的出现。抒情性一直是对作家们创作的一个诱惑,也是作家的创作达到一定阶段的艺术追求,特别是在社会处在一个调整期、相对比较宽松的时期,这一愿望更为强烈。菡子就曾说过:“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注:菡子:《作家自述》,引自佘树森:《中国现代当代散文研究》,第52页。)可以想见,当作家在谈到创作的这一要求时,那是怎样的一种低微的要求,又是怎样的一种可怜。但也可以理解作家们的苦衷,他们处于一个并不太适合于抒情的时代而又要求在创作中抒情,这无疑是太奢侈了。不过,当这一要求与时代的要求相一致时,他们无疑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抒发着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的情感。首先进入抒情状态的是被称为当代散文创作坛上的三大作家:杨朔、刘白羽、秦牧。刘白羽和杨朔都经历了一次由叙事向抒情的转换。50年代初期,刘白羽在散文保留着“战场报道”的记叙性特征,《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横断中原》等作品,以叙述为主,带有通讯报道的性质。1959年刘白羽发表了抒情散文《日出》,从此走向了一条抒情化的散文创作之路,《日出》、《红玛瑙》、《长江三日》、《樱花漫记》等,强烈而鲜明的抒情风格将刘白羽的散文创作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这次艺术转化使刘白羽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获得了自己的定位,使自己的散文很快融入了时代的抒情风格之中。杨朔在50年代初期的散文也多是通讯式的,如《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作品与后来的《海市》、《雪浪花》等作品,其风格特征相差甚大。刘白羽、杨朔的风格转换并不是对自我的简单否定,应当说,他们的艺术特长就是叙述,他们的转换只是一次小的自我调整,通过调整自己的艺术风格,以使抒情的方式更有利于叙述,更合乎新的美学原则。
应当注意的是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当新的国家成立之后,文学的“颂歌”特征被突现到前列,不只一位作家或评论家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唱赞歌,要大抒革命之情,大写社会主义新人。在这样一个文学时代,不仅仅是散文、诗歌这样的抒情体式向“诗化”发展,而且小说创作也出现了一批“诗化”小说,如茹志娟的《百合花》、孙犁的《风云初记》等。这说明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个抒情的诗化的年代,人们在这个时代深切感到了抒情与自我生活的密切关系。正是这样,散文创作的“诗化”倾向并不意味着散文体式的格局有什么总体性的改变,而只是散文在叙事功能的基础上,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变奏而已。在创作方法上,“诗化”散文也并没有从散记的客观写实转移到主观抒情,而仍然是一种表层的抒情性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叙事性,以及对现实的抒情性的表达。50年代末,由于“双百方针”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贯彻执行,也对散文创作的体式变革带来了一定影响,那种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创作思路,明晰地显示着散文作家的政治功利创作目的。散文中的那种虚幻的景象和虚幻中的抒情,也为那个时代的虚幻场景增添了亮色。
下篇:主流话语与“诗意化”散文模式
50、60年代,在散文界流行一个散文理论观点:“形散神不散。”从表层意义上来看,这个观点并无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它之所以在50、60年代甚至70、80年代得到诸多作家理论家的认同,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也说明它的确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形散”,是指的散文作品的外部形式,即它的语言、结构等,而不散的“神”,则是主导散文的命脉的主题,是作家认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主流话语。
现代散文创作中的主流话语,是随着延安文学成长起来的一批散文作家在50、60年代成熟起来并获得成功后而形成的,那些自觉到自己的声音已经不再适合新时代的需要的散文作家,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退隐了,如50、60年代的何其芳只是以一个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学界,30年代那个创作过《画梦录》的抒情作家则不见了。杨朔、刘白羽、秦牧、吴伯箫、袁鹰、魏钢焰、碧野、何为等作家是这种主流话语的创造者,也是50、60年代散文创作中引人注目的作家。他们创作风格不一,成绩大小不一,但在创建共同话语方面,却基本上是向着一个目标努力,而其散文的抒情、叙事也大体是同一个模式的。总体来看,主流话语下的50、60年代散文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个人抒情叙事消融入社会的宏大声音之中。50年代的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比较有力的代表着当时时代的声音,这种声音表达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选择,在一种共同的文化形态中,凸现了它的社会性、阶级性以及政治功利性。
作为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去抒情写意或叙事记述的散文创作,为了将个人的声音融入社会的宏大声音之中,就是“一滴水中见太阳”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所谓“一滴水中见太阳”,就是“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注:刘白羽:《刘白羽散文四集·总序》。),就是要对题材进行高度的抽象和概括,“没有抽象就没有概括,只有通过高度概括才能接近——纯。从沙里淘出金子,用金子铸成金玫瑰,艺术才能璀灿发光”(注:杨朔:《海市·小序》。)。这里的潜台词就是:散文创作只有对自我的感情进行淘洗,消除自我的影子,才能表达出大我的声音,才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本质”。所以,无论是写人写事,或写景抒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托物言志。袁鹰《小站》描写了千里铁道线上的“小站”,这些小站默默无闻,寂寞冷清,但它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仍然是红红火火、一派兴旺,是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颗螺丝钉。《夔州秋兴》借杜甫的《秋兴八首》以抒情,通过古今对比,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今天的盛大变化,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魏钢焰的《船夫曲》以《黄河大合唱》为抒情线索,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的“船夫精神”。作品中的政治热情与当时时代的政治气氛是一致的,而且它们的颂歌体式也是那个时代所流行的。
第二,以明喻为主要修辞手段的显在象征。象征是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的重要的艺术手法,象征主要是通过隐喻的修辞格和关联结构等方式得以实现。但隐喻却并不一定适用于主流话语的创建,因为过于隐晦象征的艺术并不是50、60年代的散文或诗所需要的。而明喻则既可以达到一定的象征的目的,又可以被人们接受,更易于主流话语的表达。一般来说,50、60年代的散文作品都是通过一个人物或一段故事或一处景物的描写、叙事,象征社会变革的新气象、新思想,从而达到歌颂的目的。这种象征是散文创作中的“卒章显其志”的手段,是一般化的显在的象征。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是一篇记事散文,这篇作品以先抑后扬的手法记述了音乐学院复试过程中的一件事情。很具音乐天赋深得音乐教授赏识的陈伊玲,却在复试时失败了。苏林教授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找到了陈伊玲居住的地方,并最终知道陈伊玲是为了帮助安置受灾的民众而影响了嗓子。作品最后揭示出像陈伊玲这样的学生是优秀的学生,苏教授也深为感动,“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溢在他胸口”。峻青的《秋色赋》是以现代语言写的抒情散文。赋,作为古代散文文体,以铺叙事物见长,而以抒情为主的小赋,则在以物或景抒情方面别有特色。《秋色赋》以赋的形式出现,而又超越了赋的限制。作为喻体的秋天丰收的景象所象征的作者眼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气象是在显在的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赋,这一古代文体在这里只是一种称谓,一种散文的说法,已经不再具备赋的体式特点。其它如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猎户》以及郭风的《叶笛》、柯蓝的《早霞短笛》、菡子的《黄山小记》、华山的《童话的时代》等作品,或以“散记”的形式出现,或以短章的形式出现,但其意义明确,象征意义确定,修辞手段往往不那么突出,平铺直叙为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
第三,虚幻的诗意。进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散文创作的诗化倾向成为一时的重要话题。所谓散文的“诗化”,是指散文创作中通过意境的创造的抒情性语言所制造的诗的艺术效果,是主流话语所寻找到的一种外化形式,是作者的政治观点和一定的诗意的结合,或者说是作家的政治热情融入情景之中的艺术表现,也是以抒情的方式抒发政治情怀,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因此,这种诗意是对现实的一种感应,因而也就由某些现实的虚幻特征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虚幻的特点。特别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社会现实的具体情况和政治权力对作家的要求,这种虚幻诗意的发生成为对政治的回应。杨朔在谈到他的散文创作时说,他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它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注: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如果说20、30年代的散文中的诗意来自于作家的中国文人的书卷气和生活味,那么,50、60年代散文创作中的诗意则来自于作家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社会意识,他们对当代中国的参与意识以及政治运动所激发起来的政治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家的散文创作,以抒情的方式歌赞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秩序,以蕴蓄的态度诗意颂扬急剧变化着的社会,这不仅成为作家们的社会使命,而且成为作家政治生涯中一项不可缺少的课题。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来后,这种创作上的诗意化的抒情化倾向更是作家们的自觉追求。1958年大跃进后,新民歌运动的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散文的诗意化,抒情之作较之50年代初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杨朔谈到他的散文创作时说:“我素来喜欢读散文。常觉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于是我也学着写散文。学着运用这种形式来描写人民的斗争、劳动,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注: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这种诗意来自于作者所认同的现实,作者在现实中所得到的启发,所获得的政治激情,经过作者的沉淀,形成感情和诗意。不能不说50、60年代作家们的那种政治热情的真诚与强烈,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认真,但他们却往往缺乏对这些现实和生活的理性把握与认识,而更多地在一种虚幻中和盲从状态之中而无法真正获得创作的诗意。
50、6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流话语,体现着散文的载道品格,这些作品往往通过诗意化的语言和境界,言说社会的意识与政治的意志,是意识形态的形象化。实际化,散文的载道品格并不是50、60年代的散文的独创,它与“五四”时期的散文或者中国古代散文都有若干继承关系。周作人曾对言志散文和载道散文做过区别,他认为,“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这一观点在区别“言志派”散文和“载道派”散文时,注意到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阐述了不同品格的散文的抒情方式与叙事方式。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脱离过载道文学,而言志文学则只是在某些时候的流星闪烁。这一方面与中国作家的使命意识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化体式的功能特征有关。秦牧在谈到散文创作的艺术特征时说:“散文虽‘散’而不乱,全靠思想把那一切材料统一起来,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珍珠才不会遍地乱滚,这才成其为整齐的珠串。”(注:转引自张振全:《秦牧散文选集·序言》。)正是从这一角度理解,当代散文是承继着古代散文传统和五四以来载道散文传统发展起来的,它的载道特征与它的体式特征是一致的。
50、60年代散文的某些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散文的诗化倾向是不应当轻易否定的,也不能将这种缺陷简单地归结到一两个作家身上。实际上,杨朔、刘白羽、秦牧以及其他作家如吴伯箫、魏钢焰、碧野、菡子等,都是以真诚的信念和对艺术的理解进行创作的,他们在创作中也往往表现出了他们自己眼中的现实和艺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散文的出现对于改变40年代到50年代初散文创作的通讯味、叙述化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改变了散文创作中的单一化局面,也带来了散文创作的一些新的写法。即使是已经形成的“杨朔模式”、“刘白羽模式”、“秦牧模式”,也在冲击着散文创作的简单化、毫无诗味和美学风格可言的创作。这些散文模式在对古代散文的继承方面也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尤其那种讲究艺术构思、讲究抒情艺术、讲究在历史与科学知识的叙述中议论抒情的创作方法,并不是散文创作之累,而应当是值得吸收的一种艺术经验。当然,当一种散文艺术模式化、雷同化后,它也就再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各种模式的散文写过了各种题材之后,这些散文也就走过了它们的顶峰期,难以创作出有新意的作品来,甚至会出现倒退现象。
标签:散文论文; 刘白羽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杨朔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