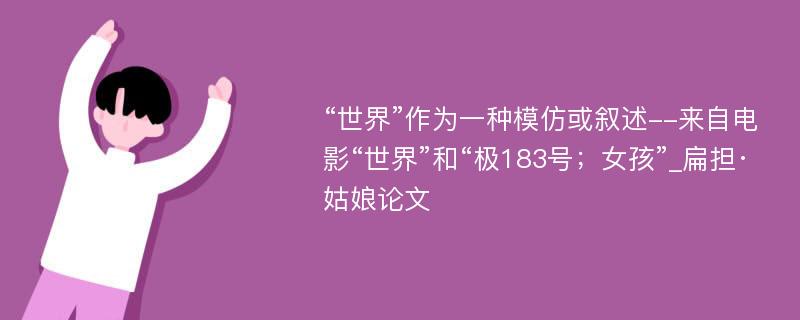
作为仿像或叙述的“世界”——从影片《世界》和《扁担#183;姑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扁担论文,世界论文,姑娘论文,影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仿像
贾樟柯的新片《世界》中,有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细节:第22分钟,世界公园五洲歌舞团宿舍,赵小桃拎着购物袋,沿破败的灰色水泥长廊走来,一路同熟人打招呼。后景靠墙根处几支灭火器是画面中仅有的鲜艳。她顺手把黑色购物袋放在廊柱下,镜头摇,追随她入水房洗手。购物袋在画面一角停留了一两秒,但足以让我们看清上面的Logo:PORTS。
PORTS,中译“宝姿”,1961年诞生于加拿大的成衣品牌,主要面对中国市场,在大陆价位多在千元以上,客户群从职业上讲是高级白领,从“阶层”上分是“得意小资”或中产。它与凋敝的走廊无关,与墙皮斑驳的水房无关,更与赵小桃,一个来自山西、月入数百元的歌舞团女孩子无关。
而这个镜头,甚至与上下文无关。在之前的叙事段落中,赵小桃送别去蒙古的前男友,与现男友成太生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开房,但拒绝了他“以身体证明爱”的要求。插入段落,金碧辉煌的歌舞段落、烟花灿烂的世界公园之夜,叠印字幕:大兴的巴黎;之后的叙事段落,是俄罗斯女人安娜向歌舞团成员兜售手表和望远镜。这个镜头不承担任何叙事功能,它应当只为一个特殊目的存在。
曾经把它当成一个无意的低级错误,但贾樟柯一贯表现“真实”的宣言迫使我思索:“真实”的“底层”生活里为何会出现PORTS?
影片第50分钟,一个与PORTS购物袋呼应的细节被镶嵌在一场情欲戏之中。FLASH段落中,成太生接到温州女人邀请短信,骑马飞奔而去,殷红花瓣从他的每一次呼吸中撒落。一朵红花绽放,花蕊微微探出,这明显是女性性器的象征,浪漫的表象背后是欲望。浙江街,一间杂乱的二层裁缝铺中,杂陈着无上装裸体塑料模特、时装杂志、简易抽油烟机和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身PARTY装扮的温州女人和放在裁缝台上的淡绿色LV(路易维登,法国高级箱包、时装品牌)购物袋。当镜头随着两人的舞步摇移,我们甚至发现那些袋子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之后的对话中,温州女人解释:“客人喜欢哪一套,我就可以把它翻版出来。”“年轻人喜欢牌子嘛。”她是一个复制者,先前不可理喻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解释:女人手中仿BURBERRY的格纹包、“手艺人靠手吃饭”的日文版、乃至30分钟前的PORTS购物袋,都是《世界》复杂混乱的象喻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正生存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仿像世界中。(注:陆绍阳《迷失在“世界”中》,《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
《世界》中数次出现外景地世界公园的霓虹灯广告: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此中的复杂含义是:用一天时间,在40多个国家109个微缩景点中,在饮食、民俗歌舞、动态电影、旅游纪念品之中体验一切。与其说它是“摹本”、“赝品”,倒不如借用让·鲍德里亚的概念,它是一个“仿像”(Simulacra)。仿像概念来自于这个消费时代,鲍德里亚认为:今天的城市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所分析过的19世纪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符号、传媒、符码生产的场所;商品作为一种符号,不再指向“现实”,而表示“概念”,“仿像”文化消费是其本质。
90年代起流行的“世界公园”、“中华民族园”所出售的正是“周游世界”、“梦想变为现实”的概念。如同LV、CHANEL等国际品牌的A货,缩微景观是城市平民的消费品。然而,如果认为世界公园是“真实世界”的模仿,平民阶层是中产消费的跟风,那就错了。作为旅游消费品,世界公园之于“世界”,正如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无非是“异域”的表征符号,只不过针对的客户群不同。
影片中另有一处细节:赵小桃离开火车站外的小旅馆,乘公交车回公园。车窗外是“真实的”的天安门、金水桥。那些讲述“外地人在北京”的影片,如张婉婷的《北京的乐与路》,盛志民独立制片的《心·心》,总会出现天安门的标示。由于拍摄条件的限制,影片无一例外,采取移动摄影的方式,模拟人物的视点,从交通工具中摇过天安门。但这北京的标示却是最“不”北京的地方:它少有常住人口,单属外地游客。在天安门留影,和在公园微缩比萨斜塔前留影含义相同,无非是拍摄一张具有“易读性”的照片,作为“到此一游”的明证。同理,仿冒LV之于温州女人和正品LV之于“成功人士”,含义也基本相同。今日人们消费商品并非其实用功能,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学消费。
二、叙述
在《世界》的首映式上,谈到《世界》的叙述方式,贾樟柯说:“我刻意回避了前因后果的叙事,因为我觉得那样会使人物内在的展现归于平淡,掩盖了影片的深层意境。”(注:参见http://ent.uland.com/detail/3105.html。)他刻意把《世界》呈现为散乱、不相关联的事件,而非叙事。
叙事是我们讲述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习惯于在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加上因果逻辑链,假装它能够被我们用推理思考来把握。而事实上东海岸的风暴与西海岸的蝴蝶振翅没有关系;善行不一定导致长寿;所谓善恶有报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我们害怕,如同一个小孩子害怕外部世界,需要叙事来安慰。
与《世界》取材相似的另一部“新生代”影片《扁担·姑娘》并没有放弃叙事,但对叙事进行了不彻底的结构。王小帅的这部影片中并行着两种叙述声音:农村扁担东子的、官方传媒的。如果说,在《世界》中,消费时代的“仿像”世界对“汾阳来的人”构成一种冰冷的存在,那么,在王小帅的《扁担·姑娘》中,都市利用传媒中的官方叙述,对“乡下人”进行了压榨。
《扁担·姑娘》讲述的是“黄陂人在武汉”的故事。黄陂少年东子来到武汉投奔同乡高平,做了人称“扁担”的挑夫;高平一心想发财,在黑市交易中伙同城里人苏武伏击对方,却被苏武打伤,抢去赃款;阮红梦想成为歌星,却只能在地下歌厅里演唱,做黄陂同乡帮“大头”的情妇。为打听苏武的下落,高平绑架了阮红,并强暴了她,阮红却出人意料地爱上了他。阮红以为命运就此转折,高平却因惧怕“大头”而退缩。
这是一系列幻灭的故事,片中一个细节成为令人心碎的象征:一个名为“龙港舰”的酒吧,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在聚会,阮红和东子就约在此处相见,欢笑一浪一浪袭击着这个不知明天的女人。得知高平杀人潜逃之后,阮红离去。此时,画面中晃动着她颓然的背影,“生日快乐”的歌声先行入画,已经走下楼梯的阮红被一个捧着生日蛋糕的男人顶了上来。蛋糕就在阮红和男人中间,后景中人群围拢,鼓掌祝贺。当阮红露出惊喜的微笑时,男人却转身,走向她身后的一个女孩,人群随之散去,只留下东子一人在她身边。那种不动声色的残忍,正是这部影片的基调。
城市利用传媒机器,却把所有挣扎与幻灭的故事叙述成另外一副样子,他们被塑造成离轨者,供城里人在将其清除的过程中获得归属感;被塑造成堕落者,供窥淫。当阮红被当成卖淫者收容,电视台女记者以“女人”的身份请她谈谈自己的经历,以“教育”市民。聚光灯把阮红的脸色打得惨白,反打,摄像机占据了整个画面,摄影师的面容被虚掉,一束强光从缝隙中射出,是城市大众冷酷窥视的眼睛。
高平被“大头”带人打死后,一段电视新闻插入,标准的普通话播音,与东子的“湖北普通话”形成对比:“公安近日破获一起持械斗殴及斗殴杀人事件……这是一场外地同乡帮之间的斗殴事件,死者是一名20多岁的外地人……公安部门根据农村‘扁担’提供的线索,很快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联系前面出现过的几段有关“民工进城利与弊”的背景广播新闻,这段传媒叙述带着一种历史叙述的强势,一种“邪不胜恶、个别丑恶现象阻挡不了社会进步”的沾沾自喜,如同车轮碾过人物,把生命压成扁平的插图。
这种“压扁”的力量,来自传媒对时间的掌控。贾樟柯在此前的影片,如《站台》、《任逍遥》中,曾酷爱使用“传媒”,如电影、电视来标示时间。《站台》中影院中传出的《流浪者之歌》、大街小巷流传的《渴望》;《任逍遥》中的申奥成功的电视新闻,均成为时间河流上的一处处航标。人们曾以日月来标示时间,东升西落、冬去春来,一日日、一年年就此消失;自从机械钟出现,“时间正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课题。日月的运行也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的后面,不再充当时间创造者的角色”。(注: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页。)而传媒时代到来,媒体记载之中的“大事件”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时间参照系。当传媒以所谓“历史进步”、“社会正义”的宏大叙事向生命碾来,没人能逃脱得了变成插图的命运。
三、所谓真实
谈及《世界》与前几部电影的区别时,贾樟柯这样说:“前3部电影是通过人的遭遇而把现实带出来,那时候人和人之间还有一种信任;但《世界》则是将一个冷的现实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注:贾樟柯访谈《我不想被人忽略》,《长沙晚报》2005年4月19日B1版。)叙事退隐之后,他需要制造一些对立的概念来表意,与“仿像”相对立的,或许是他一直强调的“真实”概念。
但贾樟柯的“真实”又是相对模糊不清的。如果按他的说法:“我一直在追求反映真实的生存”,或者联系他对大部分国产片的指责:“那些片子几乎都是主流的视角,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熟悉的生活,很少有来自个人角度的讲述,很少有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的东西。这种联系因为缺失而显得非常珍贵。”(注:[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78页。)“真实”似乎是一个“题材”的概念。但贾樟柯潜台词中把“反映真实的生存”的影片置于“造梦的、商业娱乐”影片之上,似乎也让人略有不安:毕竟这两种类型的影片承担的是不同功能。
“真实”的另一重含义则是常被影评人称道的摄影风格。但贾樟柯惯用的长镜头的美学风格是制造时空的完整统一感,与“真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贾樟柯用长镜头表达的是对时间、空间本身的尊敬。
在之前的三部影片中,长镜头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性而非戏剧性。摄影机习惯于在大街上游荡,并在“不经意”间发现故事。克拉考尔的一个说法:“街道”一词在这里不仅指街道本身,而且还包括它的各种延伸部分如火车站、舞场、会堂、旅馆、旅馆过厅、飞机场等等。《小武》中,大街就是小武的“工作”及“休闲”场所;《站台》的后半部就是一次“在路上”一般的长旅;而《任逍遥》中彬彬和小济的全部生活无非在街上闲逛,等待随风而来的闲话和从天而降的爱情。与“街道”相比,“路”意味着“寻求”,意义寄托在终点上,而街道的价值却更多在于道边的商店和行人。《站台》中,文工团转了一大圈,却又回不到原地——那个80年代的小镇消失了,成为永远不再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现实的人群。因此这几部影片中,主人公所拥有的只是“街道”而非“路”;只有“闲逛”、“等待”而没有“行走”——等待能为沉闷生活带来些许变化的偶然事件降临。毕竟克拉考尔曾把现代街道称为倏忽即逝的景象的集散地,它引人兴趣的地方在于那里的意外事件要多于注定的事件,而属于偶然事故性质的事件更是司空见惯。(注:[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78页。)
如果说,在贾樟柯的前三部片子中,街道生活还是一条充满不可捉摸的可能性的、切不断的生活流,那么,到了《世界》,街道退隐了。依然有火车站,但火车站只是一个规定场景,上演赵小桃带着新男友对旧男友无味的送别;县城的小街变成了蔓延的京郊高速公路,只见车辆,没有人群。“汾阳来的人”突然不再闲逛。在80年代,闲逛和无所事事尚能意味“反体制”、“艺术气质”;《任逍遥》中的少年,尚能以“青春期的迷茫”为闲逛作辩护;那么,新世纪之后的都市街道上,闲逛的外来者通常被当成潜在的犯罪分子。县城的街道上,陌生的人群形成一种保护,但都市的街道两侧的品牌商店、巨幅广告分明是一种威压,一种无法走进的仿像生活。
因此,《世界》的故事大多发生于封闭空间中。在那个浓缩“世界”的地方,它的主人公没有自己的家。这是莫大的反讽:“一个人假如不能拥有一所房屋,他就不可能参与世界事务,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注:[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63页。)在廉价旅馆的房间、宾馆包房、暂时无人参观的退役飞机,这些临时的私密空间内,赵小桃和成太生难堪地“亲热”着。演员丝毫没有因摄影机的在场而对自己的姿势、动作有所装饰。宾馆包房中,赵小桃向成太生献上初夜那一场,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男演员仅穿红内裤,毫无激情地躺着,女演员呈现在摄影机前的恰恰是她最欠精致的部位。这个镜头丑陋地让人绝望地想起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想起那些自以为诗意、悲情的时刻可能正像这个样子:庸常而平淡。
这是《世界》中少有的几场富有张力的戏。但贾樟柯惯用的固定机位的长镜头,离开街道便失去了生命力。它可能是最有“物质还原性”的,但也有可能是最不电影化的——早期中国电影中多半采用这类固定机位长镜头,但它充当的是“舞台记录”的作用,而且将演员的表演上的做作清晰地暴露出来。《世界》中也有类似的段落:成太生与温州女人调情的两场戏,恰恰在长镜头下呈现为不伦不类的小品表演。
在“真实”的基调之上,贾樟柯插入大量动画段落和电子音乐,目的似乎为制造“时尚”气息,迎合青年观众,但这恰恰被媒体和影评人诟病,认为它造成了切换的突兀,而对商业的妥协削弱了贾樟柯独特的风格。
也许,正如他所批判的“仿像世界”,《世界》也是一个仿像。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之后,“贾樟柯制造”已成为一个品牌,它的关键词如下:非主流、国际声誉、文艺时尚、70年代出生。这几点足以俘获70年代后出生,从城镇/农村进入城市的大部分青年。在他的“盗版碟”时代,那种在隐秘的碟市偷偷摸摸的交易方式本身就成为“非主流”与“反叛”的明证,进入受众的主体意识。当他向商业做出部分妥协后,观众所消费的是他残存的名望和一次次媒体采访中阐释影片时所用的“真实”概念。
也许他的人物就是他的一个隐喻:赵小桃和成太生们并非隔绝在仿像世界之外。以服装为例:将牛仔裤裤角塞进靴子里正是去年的流行,以凸现腰、臀、踝的流畅线条。影片从头到尾,赵小桃一直保持着这身并不适合她的打扮。不适合自己的“流行”只是一个符号,证明自己不是隔绝在都市之外的外地人。她——他们骨子里已被仿像都市同化。
事实上,如同《世界》中无法构成对立关系的“仿像”/“真实”,王小帅的《扁担·姑娘》也有一个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结构:最初我们以为与媒体叙述对立的是“真实”,但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重叙述,来自“东子”。而且,同样进行了事实的简化。东子曾用一句话概括高平的悲剧:钱是大头的钱,阮红是大头的女人,苏武是大头的手下。这是复仇情节通俗剧的概括,不是“真实”。对于两种叙述来说,不存在真/伪的对立,它们只是不同的角度和方式。
行文至此,我却对最初提到的那个PORTS购物袋重新产生了怀疑:毕竟宝姿是一个版型出众,但设计保守的牌子,它的仿制品不像LV、CHANEL一般泛滥;款型也不适合赵小桃的风格。也许它真的只是一个低级错误,来自贾樟柯的仿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