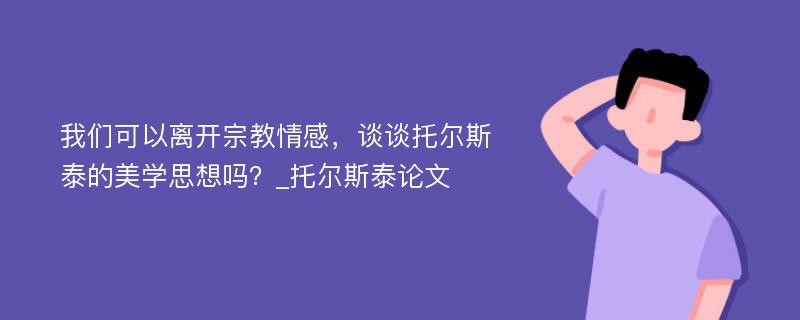
能否离开宗教情怀谈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美学论文,情怀论文,宗教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几乎没有几个美学学者不知道托尔斯泰著名的艺术定义:
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音响和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这个定义就是美学史上著名的“感染说”或“感情传达说”。同样著名的是他的“宗教艺术”或有人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的观点:
艺术,特别是要求有大量准备工作和耗费劳动的戏剧艺术,从来就是宗教的,也就是说它旨在唤起人们认清人对上帝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艺术在其间产生的那个社会的进步人士在某个时候所认识到的。(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国内学界对这两句话采用的是我们所熟知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两点论”的解读方式。认为前者“从感情表现和传达论方面拓展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的美学”,而后者则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成为我们所要警惕的对象。(注: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五卷《十九世纪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432页,第174页,第313页。)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两个论述真的是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我们要学习前者,警惕后者吗?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关于宗教、理性、科学等问题上的几乎是相互矛盾的比比皆是的论点,我们是否就要反思一下我们的“两点论”的解读策略是否有一点简单教条之嫌?我们是不是对宗教两个词有点所谓的神经过敏,以至于我们听到宗教两个词就要免不了要皱一皱眉头?让我们首先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亦即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入手,看看问题到底是怎样的。
二、理性的宗教:两点论的解读策略的困难
托尔斯泰终生在寻找上帝。法国作家莫洛亚(A·Mautois)说:“从童年时代起,托尔斯泰就具有宗教思想,甚至还带有神秘的色彩。”(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托尔斯泰的小女儿说:“信仰上帝,离开这种信念他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是托尔斯泰紧紧抓住不放的根本。”(注:[俄]亚·托尔斯泰娅:《父亲: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启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372页,第479页。)托尔斯泰在1855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关于上帝和信仰的谈话使我产生了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我自信能够以毕生的精力去实现这个思想,即创立一种与人类的发展相适应的新宗教,是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宗教,是不应许来世幸福、却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宗教。我明白,只有若干代人自觉地朝着这个目标去工作,才能使这个思想成为现实。一代人要把这个思想嘱托给下一代人。总有那么一天,狂热或者理性会使它成为现实。自觉地行动,使人们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希望能使我全神贯注的那个思想的基本点。(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
可见,宗教问题至少在他27岁的时候就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而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关于他的前后立场的转变无疑有些夸大。(注:格林伍德(E·B·Greenwood)在《托尔斯泰和宗教》一文中写道:“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写的《忏悔录》(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列文思想下困惑的继续)的第二章中,托尔斯泰想戏剧性地描写他的改宗经历,结果他(并非不自然地)夸大了他当时的观点和早先的立场之间的差异。”文见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92页。)
托尔斯泰终生在寻找上帝。他寻找上帝的结果却是他被驱逐出东正教会。
他之所以被驱逐,是因为他不是以虔敬的教徒式的非理性的信仰的态度寻找上帝,而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理性的态度去寻找上帝。他在1887年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
有人信仰宗教,也有人信仰现代文明,这两种信仰完全相同。(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他在1910年9月15日的日记写下了一段大同小异的话:
认为并且宣称世界是进化产生的,同认为并且宣称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一样愚蠢。前者更蠢些。只有说我不知道,无法知道,而且无须知道,才是聪明的。(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
这样的话对于科学的打击比起对宗教的打击来说不知道要小多少。所以就像当年雅典政府以神的名义审判苏格拉底一样,东正教会以上帝的名义驱逐托尔斯泰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不满意现存的教会,因为他们缺乏理性精神;他也不满意现存的科学和艺术,因为他们缺乏宗教情怀。在他看来,基督徒和科学家之所以对基督教的态度截然相反,是因为他们都误解了真正的基督教,他们都把基督教看作超自然的神圣启示:
据那些宣传教会的信条的人们的观点,基督教教义是一种有关《圣经》提到的一切事物的超自然的神奇启示。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则认为,基督教教义表达的是人类对于超自然的神奇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现今已经过时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这种愿望主要体现在天主教、希腊正教和新教教义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义。(注:[俄]列夫·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孙晓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42页,第43页。)
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不是神圣的启示,基督教是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就是:人,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对幸福充满渴望的人,就应当义无反顾地追求绝对的完善。在追求绝对的完善的道路上,那一只迷途的羔羊和那些在羊圈中的99只羔羊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那只迷途的羔羊比其他的羔羊的地位更高——因为这只羔羊在追求,而其他的羔羊却处在停滞的状态之中:
丢失的那只羊要比羊圈里剩下的九十九只羊更加宝贵;在上帝面前,回头的浪子,重新找回的硬币远比从未丢失的宝贵。(注:[俄]列夫·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孙晓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42页,第43页。)
在这样一种基督教里,教会是没有任何特权的,因为他们最大限度只是那99只羊。真正的天国、真正的上帝的启示也并不在教会之中,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上帝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立即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法规启示给一个人或一群人。上帝总是给一切人,一切正在寻找它的人以启示。上帝的启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上帝的律法不是写在某一本书里,而是存在于生命之中,存在于人的命运之中。(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既然上帝和天国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上帝,我们除了自己孤独而又真诚地去寻找以外,还能依靠谁?除了依靠我们自己的理性以外,我们又能依靠什么?
罗曼·罗兰曾经这样评价托尔斯泰的宗教态度:
没有任何东西能更好地证明,他对最崇敬的基督也保持其独立性。这个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徒,丝毫不象一般的信徒那样,对基督表现得百依百顺。他尽管耗费了部分生命去研究、解释、宣传《福音书》,但他从来没说过:“这是真的,因为《福音书》是这么说的”。但是他说过:“《福音书》是真的,因为它说过这些”。对于这一些,将由您自己,也就是您的自由理智,去判断是否真理……(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
这种自由理智,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自由理智,就是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罪的自由理智;而不是那种盲目自大的理智——以为一旦拥有理智,自己就会无所不知的理智,这种理智恰恰会造成人的无知:
不能以为自己的见解绝对正确,什么都是可能的!……人们获得知识不是通过理智的途径。(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六卷《书信》,周圣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100页。)
这种自由的理智所找到的基督教,也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基督教,而是一种承认自己的有限性、从而向往绝对完善的基督教。1887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说:“灵魂最美好的状态——不是不做有罪之人,而恰恰是深感自己是个有罪之人。”(注:[俄]亚·托尔斯泰娅:《父亲: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启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372页,第479页。)
面对这种既不是迷信的态度也不是科学的态度的独特的宗教探索方式,我们难道还可以用我们的“两点论”的公式去解读吗?显然不能。
如果我们可以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用“两点论”的方法去批评托尔斯泰说他不彻底,既相信理性,又陷入神秘主义,从而把他驱逐出理性的殿堂,那么我们也就不要责怪东正教站在正统宗教的立场上将他逐出教会了,因为他们用的是同样的解读策略。看来成问题的并不是托尔斯泰看似矛盾重重的态度,而是我们的片面立场。片面性正是托尔斯泰所憎恨的:
我渐渐迷上了科学。虽然科学在人的种种癖好当中是最好的一种,我也永远不会让自己单单陷进这一个方面,就是说,完全扼杀感情,不旁顾其他,只一味地注意智育,一味地往脑子里灌东西。片面性是人的诸多不幸的主要原因。(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
这种片面性之所以可恨,就在于它的自大。如果我们站在这样一种片面的科学或宗教的立场用貌似公允的“两点论”去看待托尔斯泰,那肯定找不到真正的托尔斯泰,而只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概念游戏之中。因为他相对于我们所理解的宗教来说,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相对于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来说,他又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
托尔斯泰的宗教,如果非要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那么只能命名为“理性的宗教”,这不无“吊诡”色彩的命名的意义就在于说明我们的“两点论”的解读策略的不可能性。不管对这一命名托尔斯泰是否会同意,但我们坚信它是与托尔斯泰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信仰宗教和信仰科学都是迷信。
也正是在承认自己无知这一点上,作为宗教热情的真诚和作为科学探索的不迷信达到了统一。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和苏格拉底的惊人的一致:
应当使自己处于孩提状态或笛卡儿的状态,对自己这样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我想要做的仅仅是认识生活的真理。因为我必须度过这一生。(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是最愚蠢的人。(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
真奇怪,我知道我有多坏多愚蠢,可人们却把我看做天才。那么其余的人又是什么呢?(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
想永远有理的那种人是可怕的。他们仅仅为了有理就可以去谴责无辜的人,圣人,甚至上帝。(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
所以解读托尔斯泰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先要找到一个什么立场,然后在这个立场上用两点论的眼光看托尔斯泰哪些东西说对了,哪些东西说错了。而是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阅读才是有意义的。
三、对自己的怀疑:宗教情怀与美学探索
托尔斯泰研究美学,不是出于一种学理上的兴趣,而是出于一种深切的宗教关怀。
1881年,托尔斯泰移居莫斯科。莫斯科的贫困使他大吃一惊。出于宗教热诚,他想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帮助的结果是他发现真正的可怜人是自己。他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2—1885)中写道:
我要去帮助可怜的人。谁是可怜的人呢?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人了。要知道我是一个四肢无力的不中用的寄生虫,只能在一些最特殊的条件下生存,在千万个人为维持这个谁也不需要的生命而劳动的时候才能生存。可我,一条吞食树叶的蚜虫,却想有助于这棵树的生长和健康,想为它治病。(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他怀疑自己就是制造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贫穷和灾难的同谋。他本着一种严格的宗教情怀来严格剖析自己:
我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吃,说,听;吃,写或者读(也就是说或者听;)吃,玩,吃,又是说和听,吃,又是睡觉,天天如此,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也不会做。为是使我能够这样做,就需要扫院工、庄稼汉、厨娘、厨师、听差、车夫、洗衣女工从早到晚地干活,且不说为使这些车夫、厨师、听差等等能有他们用来为我干活的工具和对象,如斧子、木桶、刷子、碗碟、家具、玻璃、蜂蜡、鞋油、干草、木柴、牛肉,还需要其他许多人来干活。所有这些人为了使我能够说话,吃饭和睡觉,整天整天不断地干着繁重的活儿。可我,一个虚弱不堪的人,却自以为能帮助别人,而且恰恰是帮助这些养活我的人。(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事业是否道德。这个道德不是这种或那种道德教条,而是作为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道德。站在道德立场上,对艺术进行指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并且贯穿于他的终生。当21岁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1887年写信问托尔斯泰,问他为什么要谴责艺术时,托尔斯泰回答说:
我写一本书,为之我需要排字工人的劳动。我作一首交响曲,为之我需要乐师。我做一些实验,为之我需要制造实验仪器的人进行劳动。我画一幅画,为之我需要别人来创作颜料和画布。所有这些事情可能是于人有益的,但也象多数情况下那样,它们同样可能是完全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可是,当我做着所有这些其益处大可怀疑,而我又迫使别人为之工作的事时,在我的四周却有许许多多需要去做的事,它们无疑是于他人有益的,我也无需任何人帮着我做,例如帮疲乏者搬运重物,替病了的当家人耕田,给人包扎伤口。”(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要在托尔斯泰所揭示的事实面前沉思至少一分钟。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作为脑力劳动者的“我”,究竟有什么资格来享用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他”的劳动果实。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解释成劳动分工的不同,甚至我们可以断章取义地援引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来了结这桩公案,说这个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不用我们的文学大师费心。然后顺手扔给他一本《孟子》,请他拜读,读了之后就安心创作,不要再想这些古里古怪的问题。
然而托尔斯泰并不是不知道分工。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工,而在于我们如何使分工合理。他说:
在人类社会里,分工从来就存在而且将来也会存在;不过,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现在和将来有分工,而在于,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才能使这种分工合理。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当作准绳,那么我们就会因此抛弃了任何准绳;于是,我们会把在人们之间看到的、并觉得合理的任何分工都认作合理的;如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也正导致这种看法。(着重号系引者加)(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如果托翁此言不虚,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考察我们所从事的艺术活动是不是有益的、绝对必要的。因为体力劳动的成果无疑是有益的、绝对必要的。体力劳动者就有权要求我们用来交换他们劳动成果的脑力劳动也必须同样如此。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托尔斯泰问自己,也在问我们:
假如他们向我们提出这样简单而又合理的要求,那么我们脑力劳动者又该怎样回答呢?我们用什么来满足这些要求呢?……又以什么来满足他的艺术方面的要求呢?以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以法国沙龙和画裸体女人、绫罗、天鹅绒、风景和风习的我国艺术家的绘画,以瓦格纳或者晚近音乐家们的音乐吗?这些都毫无用处,也不可能有用处,因为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用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着重号系引者加)”(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注意,这并不是什么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托尔斯泰是极端反对功利主义的。(注:托尔斯泰既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在1894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些人认为艺术的理想是美,另一些人认为是功利,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游戏。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想继续把已经是现实的、不再是理想的东西当作理想。那就是功利和美。艺术是一种塑造应有的事物、塑造一切人都应该追求的、给人以最安定幸福的东西的本领。要塑造这种东西只能通过形象。人类已经为两种艺术理想生活过,现在正为第三种理想活着。第一种理想是功利,即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艺术作品,过去是这样看的。后来是美的东西,现在是善良的、好的、有道德的东西。认识上产生混乱是由于人们想把过去的东西重新奉为理想,正如强迫成人去玩洋娃娃和骑木马。”)托尔斯泰只不过是想替沉默的体力劳动者讨个公道,假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交换还有公道可言的话。
如果“我们甚至不知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语言,甚至忘掉了劳动人民本身,我们忘掉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当作某种民族学奇珍或新发现的美洲来加以研究”(着重号系引者加)(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那么这种分工和交换就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谈什么分工,无疑是给一种欺骗披上一层经济学的科学外衣。
在这时,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论证角度说,如果没有分工,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到达现在这个高度。其实,这也同样没有回答问题。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托尔斯泰并不否认分工,而在于托尔斯泰要求我们提供和体力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等值的劳动。这才符合等价交换这一经济学原则。而只有符合等价交换这一经济学原则,艺术活动才是道德的。
毋庸讳言,托尔斯泰是一个“道德至上”论者(注:这里用的是张耀南先生的术语。张先生在2000年9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诗性启示〉:托尔斯泰非一流作家》一文,说托尔斯泰不是一流的作家,原因很简单,因为托尔斯泰是一个“道德至上”论者。张先生的结论是从阅读邱运华先生的著作《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得出来的。张先生从邱运华先生的著作中得出托尔斯泰是一个他所谓的“道德至上”论者的结论,进而由这一结论得出托尔斯泰不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因为作者说他“是很看不起‘道德至上论’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这个推论过程看似有情有理,只是笔者怀疑他是否阅读过托尔斯泰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否认真地阅读过。)。但托尔斯泰并不是要以道德的名义来禁止艺术,因为他认为禁止艺术和袒护艺术都是愚蠢的。(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他只要求艺术家出席道德法庭,为自己的活动申辩。
假如我们的艺术果真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是给有钱阶级取乐,不仅象娼妓,而且正是娼妓”(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3—64、第364页,第2页,第364页,第364页,第260页,第254页,第226页。),那么艺术毫无疑问就是不道德的社会的帮凶。因为“画家为了绘制自己的伟大作品一定得有那么大的画室,它至少容纳得下四十个细木工或鞋匠的劳动组合做工,而这些工匠目前在贫民窟里正冻得发僵、闷得要死”。(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认为艺术首先是追求美。他在《在俄国文学爱好协会上的讲话》(1859年)中就公开承认他是一个美文学的偏爱者。(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对美的偏爱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在《战争与和平》尾声(1869)还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是在寻找美。”(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而且他还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艺术至上论”者——即只有艺术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是人类的先知。他在《忏悔录》(1882)中这样阐述了他1855年刚进入创作界时,他和他的作家同事们的人生观: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怀疑的他,现在则完全脱离了他年轻时候对艺术和美的迷信。他认为,那是一种欺骗,不真诚。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根本就不知道拿什么来教别人;而且是因为我们表面上声称我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作,但“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套在艺术头上的神圣的光圈被去掉了,艺术成了赤裸裸的存在。难道要把艺术活活冻死在道德的法庭上吗?艺术又该怎样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呢?
四、艺术如何才是道德的:感染说和宗教艺术
艺术如何才是道德的,托尔斯泰花了15年的时间探讨这一问题,探讨的结果就是《什么是艺术》(1897)。
艺术如何才是道德的,换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2—1885)一书中的说法,就是艺术怎样才是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就像体力劳动者给我们提供的食粮一样。也正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2—1885)一书提出的这个简单而朴实的问题,引发了托尔斯泰一系列的美学思考。学界研究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大多重视《什么是艺术》等等专论文艺的文章,而忽略了一系列政论的或宗教的文章,真是咄咄怪事。(注:罗曼·罗兰这样评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和《什么是艺术》之间的差别:“莫斯科的贫困景象使他直接产生痛苦的印象,于是他确信科学和艺术是充满社会不平等和虚伪的暴力的同谋,因而他从此没有放弃过。但他初次接触到世间的贫困产生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伤不再流血了;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再找不到这本书中的痛苦和要复仇的忿怒的战栗。再也找不到用自己的鲜血来创作的这种崇高的艺术家宣言,找不到这种对牺牲和痛苦、即所谓“思想家的命运”的赞颂,找不到这种对歌德式的高雅艺术家的深恶痛绝了。后来写出的艺术批评著作则已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考虑,而不限于纯宗教的议论了;艺术问题和人类贫困的内容分开了;托尔斯泰一想到人类贫困内心就起波澜,就象那天访问夜店,痛苦地哭泣叫喊一样。”(《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68页。))
艺术如何才是道德的,托尔斯泰得出的答案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引用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既是对同一问题的回答,那么它们在内在精神上肯定是相通的,而不能以“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话语去分析。我们现在就从第一句话入手,谈谈这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是从“应然”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所以对它的回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使这个价值判断以事实判断的面目出现,那也说的是托尔斯泰所说的“真正的艺术”,而不包括“虚假的艺术”。托尔斯泰著名的艺术定义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如果单单分析这句话,除了说托尔斯泰揭示了艺术的形象性、感情性以及作家要真诚之外,我们似乎再很难说出些什么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而不是什么高论。大多数论者都忘记了托尔斯泰艺术定义后面的这句话:
艺术不象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是某种神秘的观念、美或上帝的表现,不象生理美学者所说的是人们借以消耗过剩体力的游戏,不是情绪通过外在符号的表达,不是使人愉快的事物所产生的结果,主要的——不是享乐,而是生活中以及向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迈进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们相互交际的一种手段,它把人们在同样的感情中结成一体。(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这一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了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将艺术活动定义为一种感情传达活动的原因。在他的信念之中,艺术应当是团结人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不是将人分为懂得艺术的“文明人”和不懂艺术的“野蛮人”的标尺。这种带有明显宗教情怀的对艺术的认识是托尔斯泰的一贯思想:
一切使人们团结的就是善和美,一切使人们分离的就是恶和丑。(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314—315页,第513页,第514页,第315页,第148页,第148—149页,第310页,第8—9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艺术,真正的艺术,如果想要经得住道德的审判,就必须是团结人的,而不是分裂人的。这是艺术的使命。衡量艺术的标准,便是这个使命的完成情况。所以托尔斯泰说:“区分真艺术与伪艺术,有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即艺术的感染力。”(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感染力越大,团结人的使命就完成得越好。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普遍地感染人的,从而起到团结人的作用呢?这里我们将走进托尔斯泰艺术观的核心地带。
在托尔斯泰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感人的,有的甚至是让人厌恶的。只有根源于宗教意识的感情才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的感情、才是万古常新的,才是需要传达的;与此相对的在于享乐的感情总是特殊的、陈旧的、甚至是无聊的。托尔斯泰说:
再也没有比享乐更陈腐的东西,再也没有比一个人从时代的宗教意识产生的感情更新颖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人类的享乐是有止境的(它受到自然界的限制),而人类的向前迈进(这正是宗教意识所表现的)却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只有在宗教意识(他表现着某一时刻的人们对生活的最高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人民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从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是无限多样的,而且这些感情都是新的,因为所谓宗教意识,无非是人类对世界的新的正在形成的态度的一个指示。从享乐的欲望中产生的感情不但是有限的,而且自上古就已知道,并早已被表达过。(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陈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74页、388页,第39页,第41—42页,第42页,第176页,第49页,第9页,第27页,第272页,第197页,第198页。)
根源于宗教意识的感情之所以是万古长青感情,之所以是深厚的、新颖的、普遍的、需传达的和可传达的,就是因为在托尔斯泰的宗教不是教会的宗教,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宗教。这种宗教是人对绝对完满的追求,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会,其中既充满了每一个人独特的体验,又满浸着人类共有的诉求和渴望。这种宗教关涉到的是安身立命之事,而享乐只关涉到个人的祸福利害。
苏珊·朗格说:“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注:[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5页。)这里所说的“人类情感”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根源于宗教意识的感情,这种艺术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宗教的艺术”;而这里所说“自己的真实情感”,就相当于托尔斯泰所说的“从享乐的欲望中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的表现就相当于苏珊·朗格所说的婴儿的大喊大叫。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托尔斯泰的“感染说”和“宗教艺术”的统一性了。
五、一体的托尔斯泰:评价与反思
我们可以用学理的探讨批评他的一些明显的疏漏,他对一流艺术家的盲视,他的宗教思想的不现实。这时我们保证不会说错话,但这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愚蠢的。好多读者都很善意地警告过我们:
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居然能够如此严厉粗暴地谈论音乐、谈论瓦格纳、谈论诗歌和戏剧,——仅此一端就足以使我们思考许多问题。(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
傲慢地议论什么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和宗教思想在我们现实世界里完全象柏拉图的理想国或雅克·卢梭的社会制度一样无法实现,这不过是一些事后的廉价的聪明话罢了;认为他的理论文章只有个别段落才闪烁着光辉和他的艺术作品中那样的说服力,这种发现也同样是令人可笑的。(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
如果浪费时间,以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去证明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不现实的、无法实现的,简言之,是无稽之谈,那将是很愚蠢的。(49)
这种学理上的批评之所以是没有意义的、愚蠢的,是因为托尔斯泰的立论重点并不在这里。
“托尔斯泰是从某种信念的高度发表他的艺术评论的。在这些评论中找不到任何隐瞒的思想。他不把自己作为范例:他对自己的作品同对别人的作品一样毫不留情。”(着重号系引者加)(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罗曼·罗兰的这句话清楚地点明了理解托尔斯泰的关键——如果我们理解到他从“应然”的角度立论,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实然”的角度去对他横加指责了。托尔斯泰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作出了多少实际的对艺术的客观的分析,而是他提出了好多让我们汗颜的问题,并提出了好多让我们望而生畏的要求。
萧伯纳警告我们说:“托尔斯泰十分激烈地向我们挑战”(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这个向我们挑战的托尔斯泰是一体的,而不是分裂的。因为一个分裂的人不可能向我们发出挑战。应对他的挑战需要至少和托尔斯泰一样的品质。
所以我们应当多想的是如何应答他所提出的问题,而不要纠缠于托尔斯泰主义,纠缠于它是没有意义的。况且托尔斯泰明白地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
既没有托尔斯泰教派,也没有托尔斯泰主义。世上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教义,对我自己和一切人来说,在《福音书》内如此完美地表达的那种普遍永恒的教义句句都是真理。它号召人们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努力摆脱世俗影响,成为上帝和天意的仆人,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力去完成解脱,听命于上帝。一旦人理解了《福音书》上的真理,他就可以和上帝自由沟通,无求于任何人。(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
一直纠缠于“托尔斯泰主义”只是说明了我们的不真诚和迷信。因为紧紧地抱着“托尔斯泰主义”不放只能说明我们曾指望托尔斯泰给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的整体。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这样的心灵中,一切都相互支持,一切都相互关联。”(注: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7页,第77页,第107页,第468—469页,第158页,第73页,第158页,第282页,第48页。)他的宗教情怀和美学思想也应当是这样。
我们之所以喜欢用“两点论”的解读策略来分解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阅读不认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产生于我们对宗教的陌生。陌生的东西首先总是令人恐惧的,这种思维惯性就是这种恐惧的一种症状。
潘知常先生在反思中国20世纪美学研究时说:
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三重维度,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上,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唯独在人与自我的维度上,我们摒弃了西方的信仰。这直接造成20世纪中国美学在面对现实时,缺乏更高的超越的价值来给人以精神信仰的支撑。(注: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
信仰的缺席所导致的局限,在我们解读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时可以说得到了再充分不过的体现。
也许我们不习惯于宗教言说。对于我们不习惯的东两尤其不要乱加指责。这是笔者要奉劝谈宗教而色变的“两点论”者的。
标签:托尔斯泰论文;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日记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忏悔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