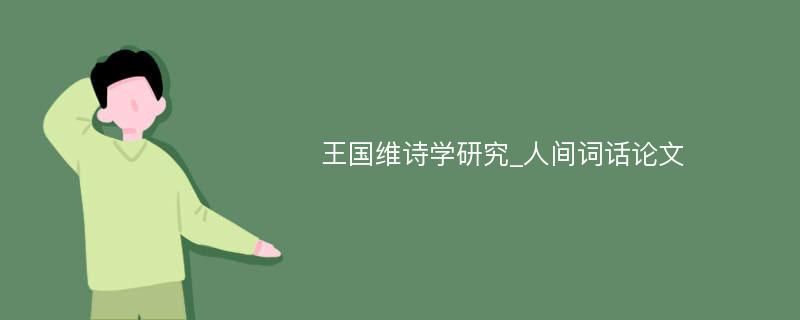
《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90年代前的大陆学界,能潜心于王国维——叔本华关系而作文献学比较者,当推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佛著虽问世于1986年,但其中涉及文献学比较的文字却大体撰于70—80年代初,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先知先觉”。他是心平气和地将王氏诗学看成是20世纪初中西美学“化合”之结晶,①并默默地将王氏生前读过的那本英译叔氏名著找来作重点研读且翻译,对王氏—叔氏关系作了文献学比较之尝试。
佛著比当时大陆同行的同类成果显得有份量。其出色处,我以为,恰在他率先从文献学比较角度提出了王氏《人间词》及其《人间词话》的人本忧思源自叔氏。若就公开披露《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的精神血缘在于“忧生”而言,②或许,陈鸿祥未必比佛氏晚(陈氏《〈人间词话〉三考》发表于70年代);但就方法之自觉,视野之展开,论述之细密,则佛氏又非陈氏可比。这里有两条线索——
一是《人间词》(1904-1907)。佛氏统计出现有115阙中,“人间”一词出现了38次,约每三首即有一个“人间”;而与“人间”形影难离的还有一个“梦”字,“梦”在《人间词》中出现了28次,平均每四首便有一“梦”。③“梦”,忧患之兆也。“梦”与“人间”相随,意谓“忧生”情结之难熬也。对此,佛氏的解释是:因王氏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之深深的浸染”,④于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某些词,特别是那些所谓‘力争第一义’的词,来形象地印证叔氏的某些论点”;⑤由于王氏“将词家的性灵与哲人的‘反思’并融于境中”,故王氏词境“颇涉幽渺惝恍”,即“以骚雅之笔,写‘忧生之嗟’;一面企慕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面又欲与永叔、少游以至纳兰辈相颉颃。其于人生,‘若负之而不胜其重’;于‘尘嚣’,若避之而唯恐其不远。故词中现实成份之稀落,视其诗文尤甚”。⑥极有见地。
二是《人间词话》(1906-1908)。佛氏的观点也颇明朗:虽然王氏曾于1907年撰“三十自序”,说自己近年“疲于哲学”,兴趣已“移于文学”,但翌年脱稿的《人间词话》仍与西方哲学特别是叔氏哲学“关系密切”,“故‘移于文学’,实并未真正放弃哲学,只是将某些哲学—美学原理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词学,曲学领域的研究与独辟而已”。⑦于此,佛氏还借用叔氏关于哲学是人的智慧“眼睛”一语来解释,说王氏对哲学“可以‘疲’,却又绝不可‘无’,”他只是不再直接从事哲学原理研究而已,事实上,其《人间词话》研究“仍不能不时时借用康、叔的‘眼睛’”。⑧鉴于《人间词》的人本哲思本就“极为浓郁”,⑨故,完全可以说《人间词》是对王氏《人间词话》的“一种亲切实践”;⑩而倒过来,也可说王氏《人间词话》是对《人间词》这一不无超前意味的诗艺实验的美学提炼,当然,这一提炼还融铸着他对中国词史的深邃思考。《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就这么与(主要)源自叔氏的人本忧思融为一体。
诚然,确定《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之母题应是“忧生”,其意义绝不限于提供一条新思路,从此可打通王氏诗词与其学术间的心灵渠道,以便更深地洞察王氏治学的直接动因;我觉得,其更大的启示应在于,抓住“忧生”,亦即抓住了青年王氏灵魂演化之焦点。这就是说,“忧生”不仅是他倾心叔氏哲学的内驱力,也是他探索且创立人本—艺术美学的内驱力;或者说,王氏美学研究本是其人生探询的一种分泌物或学理沉积,于是,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忧生”情怀,也就成了他美学整体(包括诗学)赖以建构的起点与内核。为何叶嘉莹看不到王氏美学的内在整体性(即格式塔质)?又为何叶氏仅仅将王氏“境界”归结为“鲜明真切之感受”?我以为,根子仍在叶氏对王氏诗学所蕴涵的“忧生”母题缺乏敏感。而文献学比较恰恰给佛氏注入了这份敏感。于是,叶氏的盲点也就转换为佛氏考察王氏诗学的新视点。此可谓诗学的文献学比较之“得”矣。
二
但文献学比较只是影响比较方法之初阶,它亟待深化,即只是深入到发生学水平,其文献学比较才可能获得坚实的支撑与导向,以免在宏观思路方面陷于迷茫。故,也可说影响比较若发展到发生学水平了,它才真正赢得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成熟与自足。不妨作一对照。我觉得,佛氏所用的文献学比较,其实颇接近王氏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曾说“二重证据法”形态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1)显然,文献学比较是可归入第二形态的,只须将叔氏哲学与“异族之故书”,王氏诗学与“吾国之旧籍”相对应,你就不得不承认,“二重证据法”似也含有文献学比较之因素,只是王氏生前未这么说罢了。但就像当今学界已有人提出应以“三重证据法”来更新“二重证据法”一样,(12)与发生学水平相比,文献学比较也确实流于粗疏,即它只注重比较对象间的互证性考据。譬如读叔氏,它仅埋首搜集似可印证王氏诗学的那些思想、语录或概念,却很少问甚至一点不问王氏为何接受叔氏?怎么接受?接受了什么?接受物与原型对象有何异同?是什么铸成了这一异同?……这就是说,发生学比较不会满足于在文献学水平陈述对象间的形似或沟通,不,它肩负的担子更重,也走得更远,它不仅要深入揭示王氏为何接受叔氏之内在动因,还要循序描述这渐进性接受之过程,更要确诊王氏对叔氏的扬弃度,即王氏在师承叔氏时舍弃了什么,进而辨别王氏美学典籍中的译介与再创……可见,发生学比较委实比文献学比较多一个心眼,它仿佛替后者设置了一个恢宏而精致的逻辑—实证框架,多一份参照,也就少一份随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后者因迂执而迷失。
最能体现佛氏之闪失的,是他发现了《人间词》的“忧生”基调,却未能抓着牛鼻子作追踪式比较,相反,却让思路偏移到叔氏“理念”(王氏译为“实念”),结果,得而复失。大凡细读王氏者(如赵庆麟)皆知,王氏虽有“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一语,但这是在1904年撰《叔本华的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时说的,嗣后,包括《人间词话》在内的王氏美学著述几乎从未引用叔氏“理念”一词。(13)这一史实至少表明如下两点。一,从王氏怎样接受叔氏的过程来看,王氏委实经历了自模拟性学识领悟到再创性学理沉积之转折,前者以《红楼梦评论》(1904)为标记,后者以《人间词话》(1906-1908)为界石,故,他在以前译介时用过的叔氏概念,到后来独立科研时便弃之不引,此即扬弃。二,王氏所以扬弃“理念”,从王氏为何接受叔氏之动力来看,并非偶然。因为,人的存在即生命体验是比哲思更本原的。这就是说,由天才情结与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所激化的灵魂之苦,是直接驱使王氏倾心叔氏之原动力;这就决定了王氏不能也无须将叔氏作为西方哲学史对象来作学究式探讨,相反,他有意无意地撇开叔氏的宇宙图式外壳,而径直把握其人本忧思内核而感奋不已,亦即他对叔氏的人本主义解读大有“六经注我”之意,却无“我注六经”之心。是的,王氏不是叔氏,他富于人本哲学意识,却不是哲学家,也未曾建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宇宙框架,故,也就不必对叔氏“理念”感兴趣。因为“理念”不是别的,正是叔氏用来构筑宇宙图式的逻辑枢纽或脚手架。显然,若提升到发生学水平,则不论着眼于接受动力还是接受过程,皆不会轻易将王氏诗学托付给叔氏“理念”。但佛氏走了另一条路,他不仅疏略了王氏对叔氏的接受动力之探究,不仅漏掉了王氏接受过程中的扬弃与再创,即把王氏平庸化为毫无创意的叔门学子,而且,其文献学比较最后竟因望文生义式的逻辑错位而走向思维内讧。
三
现在我们来看,失却发生学导向的文献学比较,是怎么使佛氏逐步从望文生义式的逻辑错位走向思维内讧的。
毛病仍出在佛氏将王氏—叔氏关系简单化了,以致把王氏诗学“理想”等同于是叔氏“理念”的东方版。
是的,王氏确有“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14)一说,佛氏将此视为王氏诗学“体系的骨架”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能否粗略地在王氏“理想”与“叔本华式的‘人的理念’”(15)之间划等号?这便涉及到怎么看王氏“理想”了。
细读《人间词话》,不难发觉王氏“理想”是个复合型概念,可在两个层面展开。一,当《人间词话》条目(2)提出大诗人“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时,此“理想”当指诗境所凝结的“内美”、意蕴即对人生的遥深感悟,因为王氏历来强调只有对人生怀有价值自觉者才无愧为“天才”,只有诗性地传达出这份文化关怀的作品才算有“境界”,因此,该“理想”实指诗境的高文化品位,饱和着浓郁的人本哲思。二,但当《人间词话》条目(5)论及“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16)——显然,王氏在此主要是从艺术操作层面来谈“理想”的。因为不论该“理想”是否蕴藉王氏所热衷的忧生母题,作为艺术创作,皆亟须对素材原型实施想象操作,使之形变或涵变,以适创作意图之履,这便是王氏所谓“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亦即使原生即“自然”形态的素材经艺术加工而转为能凝结作者创意的诗性载体即题材,于是,“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一语也就不难理解,它无非指,即使是追求状物毕肖之写实风格之诗人,说到底也是为了艺术地传递自己的创意,而为了实现创意,总要裁剪素材,亦即为了“理想”,“自然”务必就范。
综上所述,实已勾勒出了王氏“理想”的复合结构,即它在人本哲思层面是特指诗境之魂在于人生感悟,在艺术操作层面则泛指一般创作皆有的异质于现实的诗性意图。又可称前者为狭义“理想”,后者为广义“理想”。诚然,既曰“理想”是复合型,那么,它在不同条件下必然可分也可合。当王氏用“理想”来解析陶、李、苏、辛的高品位诗境,则此“理想”当是指人生感悟之遥深,同时也是赏其诗作之创意;或者说该创意所以不俗,正在于道出了旷世情怀——这便将狭义“理想”与广义“理想”合二而一了。但也可分,因为诗艺并非巨子之专利,温、韦、冯、周,在王氏眼中虽稍逊风骚,但也有权浅斟低唱,也有清词丽句传世,即使其诗品仅“句秀”,“骨秀”,不及重光“神秀”,还攀不上王氏“境界”,但不排斥其诗作也自有异趣于功利之创意——这又将广义“理想”同狭义“理想”的界限划清了。
其实,王氏“理想”之复合性在《人间词话》曾一再呈示。如条目(60),当王氏直言“美成能入不能出”,(17)显然是以狭义“理想”为参照的,因为在王氏看来,美成虽能入乎其内,“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多生气,“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18);但终究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即未能出乎其外,故欠高致。高致者,“境界”之“第一义”,人生感悟也。但条目(61),当王氏补白:“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时,(19)似又是从广义“理想”着眼的,因为只要诗人想诉诸笔墨了,必有创意躁动于内,不论此意是否王氏“第一义”,诗人对素材(即“风月”)之加工(即“以奴仆命”)则是势在必行的。这儿姑且不论王氏“理想”之复合结构是否易生歧义,我只想说,无论从人本哲思(狭义),还是从艺术操作(广义)角度来看王氏“理想”,它皆不是对叔氏“理念”的简单翻版。
看来,佛氏是从狭义角度让王氏“理想”向叔氏“理念”靠拢的。证据有二。一是擅长哲学体系建构的叔氏无意琢磨艺术美学,他不可能像王氏从艺术操作角度去阐释广义“理想”;二是佛氏确实一再申明王氏狭义“理想”与叔氏“理念”有等价关系,如“王氏的美的‘理想’并未越出叔本华式‘人的理念’的轨则之外”;(20)又如王氏“所谓‘第一义’终不差‘忧生之嗟’,仍略相当于叔氏的在最高等级上的‘意志之恰当的客观化’”,(21)等等。应该说,能发现王氏狭义“理想”与叔氏人生“理念”有思想渊源,这表明佛氏确有眼光,亦即是文献学比较之“得”;但王氏“理想”与叔氏“理念”除了相通处外,是否还有不同点呢?佛氏没说。似乎他还未看到这一点。而这,正是文献学比较之“失”。
王氏“理想”与叔氏“理念”,乍看仅一字之差,其实蕴涵着两种曾有交接的人学观念的不同走向。亦即在人生观上,两者有所同,也有所异。简言之,在承认苦痛为人所与生俱来之本体现象方面,两者同;但在人能否超越这一生存苦痛方面,则叔氏要比王氏悲观得多。叔氏认定人除非走宗教禁欲之路,否则永远不得解脱,至于艺术—审美不过是灵魂的片刻麻痹罢了,故,叔氏坚执以宗教来驱逐艺术—审美;相反,王氏虽也承认艺术—审美是精神鸦片,但同时他又看到沉浸于琴棋书画之古雅,总比一味寻求官能刺激,醉生梦死,更能熏陶或滋润人性,故其坚执以艺术—审美来代替宗教,且提出教育之宗旨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之人格,这比叔氏以人生的自残自毁来换取安魂之阴郁教义,不知要明朗多少倍。
叔氏的人学姿态所以如此阴沉,除了他久陷逆境外,在逻辑上,则是因被其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所累,既然他想把他的个体生命苦痛泛化为宇宙本原,那么,他也就无计走出这永恒之黑洞。这就是说,叔氏意志哲学虽是反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但其宇宙意志自在自为之演化模式却酷似黑氏“绝对理念”,也让人去充当宇宙本原赖以顾盼自身之明镜,于是便借柏拉图之“理念”,作为本原之逐级显现的一般表象(即可供人作审美观照或知性认识的非欲念性个别对象),而人生感悟在叔氏看来,也就成了宇宙意志在人这一最高等级上的客观自省。也正是在这意义上,我承认,佛氏将王氏“理想”“略相当于叔氏的在最高等级上的‘意志之恰当的客观化’”,是很有道理的;但若因此而疏忽这两者之差异,则又转而没道理了,因为这将无法解释王氏诗学为何不引叔氏“理念”,却反而频频引用叔氏“直观”概念这一史实。说白了,无非王氏是将叔氏作人本哲学来读的,故,他只对其体系中的忧生内核感兴趣,而对其僵硬的宇宙图式外壳则不敢恭维,于是,当他穿越外壳、直取内核时,他也就将故作玄虚的“理念”放在一边,而独钟其人本气息馥郁之“直观”了,因为“直观”不是别的,正是指通过自身生命体验来逼近存在之真,这也就是人生感悟本身。这就正中王氏下怀。由此看来,王氏“理想”确跟叔氏“理念”有别:假如说,前者旨在弘扬人对主体生命之价值自觉,崇尚人是目的,是值得艺术去探询且表现的形而上的对象;那么,在后者那儿,人则萎缩成了“原罪”,仅仅是宇宙借以照亮自己的道具或摆设。总之,王氏“理想”虽与叔氏“理念”有关,但并未粘滞于后者,而是再创性地走了出来。也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出于蓝,但已非蓝。若青蓝不辨,当有望文生义之嫌。
四
佛氏的文献学比较,在论及王氏诗学的“自然”概念时,似错位得更明显。
与王氏“理想”相仿,其“自然”的涵义结构也呈复合型,也可在两个层面展开。一,当《人间词话》条目(2)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王氏是就诗境的修能(形式)而言的,即规定“境界”除了其内美(意蕴)应凝结高品位的人生感悟外,其诗语造型还得有清新疏朗之风,犹如豁人眼目的画面能激活读者的再造想象,以便在其心中唤起鲜亮活脱之意象,亦即不像是文字施予的,而是自己切身感受到似的,毛茸茸,水灵灵,“天然去雕饰”。二,但当《人间词话》条目(52)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22)显然,这一前一后两个“自然”指的不是同一意思,假如说,后者当属诗境修能之顺延,那么,前者则是指那种未被功名利禄之“汉人风气”所染的纯审美的“赤子之心”。(23)这就是说,“自然”既可在形式美学层面当作一种诗语风格,也可在本体美学层面用来表征非功利、非粗俗的旷世情怀。诚然,在王氏那儿,“自然”的这两层涵义也是可合又可分的。若无“自然之眼”,当无“自然之舌”,此谓可合;但“自然之眼”毕竟异于“自然之舌”,又谓可分。然而,不论分也罢,合也罢,王氏“自然”皆是在美学领域展开其内涵,则无疑。
但是,王氏“自然”到了佛氏笔下,却从诗学命题演变成了一个反映论(或以反映论为基准的流行文论)命题。我称之为遥辑偏移。这一偏移拟可分如下四步来解析。
第一步,是对王氏“合乎自然”作随意阐释。所谓随意,是指佛氏在界定上述“自然”时,未能恪守语境规则,即不是始终按上下文关系来确定概念本义,而是时而规范,时而豁边。譬如,当他企图以“赋”来注疏“合乎自然”时,(24)他是将此“自然”置于诗艺形式层面的,也是合乎王氏原旨的;但当他在另处将“合乎自然”解释为“摆脱‘意志’的束缚,忘掉自己的个人存在,而‘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之中”时,(25)这就不是在形式风格层面,而是偏到审美本体层面去穿凿“合乎自然”了,这就有违先定语境,而将“自然之舌”等同于“自然之眼”了。事实上,在佛氏心中,“自然之眼”、“自然之舌”本为同义。接着,第二步——既然“自然之舌”与“自然之眼”同义,则,王氏“自然”的复合内涵也就简化为“无我之境”式的审美静观。佛氏以为,“无我之境”之出现须具备内外两种条件:A.“客体的‘美’或‘崇高’的景象(所谓‘天下清景’)足以吸引(甚至强制地)主体,使之一刹摆脱意欲的奴役,而进入‘自由’状态”;B.“此际的诗人业已成为纯客观的直觉的观照者”,“或者照亮事物真正面目的‘一面纯净的镜子’,他的情感进入了一种‘净化状态’。”(26)换言之,“诗人在审美观照中客观重于主观”,亦即使诗人“由现实的‘我’转变为一个‘认识的纯粹主体’。”(27)这里有两个环节亟待澄清:首先,摒弃了世务俗趣的审美心境能否说是“客观”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审美心境近似马斯洛的“生命高峰体验”,在这瞬间,包括生理欲念在内的日常思虑皆被排除在兴奋灶外,灵魂由于充实而弥散宁静的蔚蓝,这与其说是忘了自己,毋宁说是对自身诗性生命的美好实现,它似乎证明,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她)在审美瞬间可使自己的生物性存在净化为某种纯精神的价值存在,这当是情调性的,主观的,非客观的。进而,能否将这一情调性审美静观归结为“认识”?不能。因为审美心境之发生,本就意味着情感圈之放大与认知圈之缩小,这是现代心理学的常识。佛氏所以不顾常识而轻信叔氏,将审美静观等于“客观”“认识”,这除了他对叔氏尚缺辨析力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想为下一步偏移铺路。
第三步,既然审美静观等同于“客观”“认识”,那么,这体现“在艺术创作中”便是“再现重于表现”。(28)佛氏是这么解释上述转换的:当“诗人独自‘观’出并且沉浸于眼前事物之活的意态中,他的自由的想象力,把这一画面跟人生中某些类似表象天然‘凑泊’一起;不是以某种既定概念注入此画面中,使之成为可观照的概念,而是原有画面之自然地扩展与延伸;结果是,通过使人精心选定的此物之某一侧面及其‘生发’,而此‘物’与‘人’的某种内在的本质力量,同时获得了鲜明的呈露。”(29)这段话乍看颇为辩证,既讲主体的情态想象,又讲客体的意态画面,更讲彼此的天然凑泊,仿佛和谐统一得天衣无缝似的。但若细细品味,你又会觉察味道不正,因为按此思路,似乎诗人想象或创作意图总是被动的,非有赖于外界媒触的刺激不可,而且,其诗艺造型也并非匠心之独运,而只是“原有画面之自然地扩展与延伸”,诗写得好不好,仅取决于意—象之间能否对应即“巧于比类”,这在实际上,无异于是将诗人的艺术创造贬为镜像式机械摄录或剪辑了。这当是艺术美学之大忌。譬如,王氏为何推苏轼《水龙吟》咏杨花为咏物之“最工”?难道仅仅是“由‘巧于比类’得之”吗?是否还有比“巧于比类”更深沉、更带决定性的根由才使苏轼成一代词豪呢?否则,为何杨花年年飘零,却只有苏词“最工”呢?看来,苏词之成功绝不取决于“巧于比类”,也不取决于杨花的对象性意态,而是取决于他那饱经沧桑的主体性慧眼,正是那双魂系古今、情归天人的“诗人之眼”,才从那沦落风尘的杨花身上读出了一般球眼读不出的人生真谛。这就是说,苏轼心中的杨花其实已不是自然实在之杨花,而是已内化为既溶杨花表象于内,又被兴衰荣辱之沧桑感所渗透、所泡软的统觉性审美印象了。这也就是说,就像郑板桥将竹分为“眼前之竹”、“胸中之竹”和“笔下之竹”一样,所谓杨花也应有上述三种形态,分属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其中物理性“眼前杨花”属世界1,心理性“胸中杨花”属世界2,艺术性“笔下杨花”属世界3——如此看来,佛氏所强调的那个为诗人提供视觉信息的“眼前杨花”,充其量不过是可能诱发诗人之命运叹喟的外源性媒触罢了,它犹如火柴,火柴自身不会爆炸,直接决定诗兴爆发之规模或力度的是诗人的精神储备本身,亦即诗情郁积若过久过盛,即使一时没有外界媒触,它也会自行引爆的。若这么来看诗人创作,则创作之原动力也就不会源于外在物理—现实空间,而外界物象若想进入艺术世界,也必须先内化为诗人的精神存在即素材,才可能经加工而被组织为题材。这就不是什么“在艺术创造中再现重于表现”,恰恰相反,是诗人欲艺术地“表现”什么了,才去虚构某一“再现”性载体,再现在此是作为手段而从属于表现的;犹如在王氏诗学中,再现性“合乎自然”作为修能,作为某一形式风格,是依附于诗境内美之表现的。故,艺术创作是再现重于表现,还是倒过来,表现重于再现?粗看只是一念之差,其实却贯穿着两种艺术观的对峙:若你把艺术视为不同于认知的审美创造,则你就会坚执艺术确是表现重于再现;相反,若你把艺术当作认识活动之分支,或本是披上形象外衣之认识,则你就会同意艺术是再现重于表现。佛氏当属后者。
第四步,当佛氏默认艺术为认识之变体,这在实际上,离将王氏“合乎自然”之诗境蜕变为一个反映论(或以反映论为基准的流行文论)命题,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值得指出的是,在变前者为后者的过程中,叔氏“理念”起了中介作用。凭据有二。第一,在思辨上,佛氏不仅抓住王氏1904年译介叔氏时所写的“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一语不放,而且还特别钟情于同文中的“个象”一词并反复引用,因为在王氏眼中,“个象”作为足以表征某一物种之一般的个体表象,正是“理念”本身。于是,第二,在诗艺上,也就不难理解佛氏为何要竭力推崇王氏对冯延巳“细雨湿流光”,与周邦彦“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之赞词了?因为当王氏夸冯氏真“能摄春草之魂者”,周氏“真能得荷之神理者”,(30)在佛氏看来,似乎并不是在举例说明诗境风格之清新疏朗,相反,而是在暗示王氏“境界”本是对叔氏“理念”的诗艺注释,用佛氏的话便是:“所谓‘魂’与‘神理’,其实都指以‘春草’与‘荷’的某一侧面,代表各自的全体族类之一种‘恒久的形式’,充分显示各自的内在‘本质力量’之一种‘单一的感性图画’,简言之,就是‘理念’。”(31)再联想到佛氏所说的审美静观之“客观”,“又指审美客体本身之客观的‘内在个性’”,“这在叔氏,也就是对客体的‘理念’之领悟与再现”,(32)如此推导下去,当佛氏道出:“王氏的诗词‘境界’跟叔氏的艺术‘理念’,是平行的美学范畴。离开作为理念之显现的那种‘个象’或者‘图画’,也就不成其为‘境界’了。”(33)你也就无须惊讶了。
重在人生感悟的王氏“境界”于是彻底地被“理念”化了,从此,“境界”之魅力也就不再是诗艺地表现作者的忧生情怀,而仅仅在于它对外物之再现能否蕴有足够的逻辑涵盖面或概括力。那么,怎么才能让诗人抓住足以代表“理念”之“个象”呢?佛氏给出的良方是“典型化”,即“把典型化当作境界的基本特征”。(34)其操作方案如下:为了“使个别‘景物’转化为‘理念’(相当于‘典型’)”,“由不完全的美进到‘完全的美’”,艺术创作“必遗其(自然之物——引者)关系,限制之处”;“所谓‘遗其关系,限制’,一般讲,即‘遗其’物之空间‘并立’与时间的‘相续’,即一刹超乎时空的‘限制’,同时摆脱物物之间的偶然‘关系’,物我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而使“艺术作品中的‘景物’,已不复是某种偶然的特殊的单独的个体,而是‘代表其物之全种’的‘个象’,即充分显示其物之‘内在本性’或‘理念’的个体形象”(35)——这也就是所谓“典型”即“境界”。最终佛氏得出结论:“境界”,“是抒情诗人对生活、自然之美的一种独具只眼的发现与改造,而非诗人意志向外在世界的投影。境界已不同于生活、自然的原型,而是依照客观存在于生活、自然本身的‘美的法则’,而予以艺术加工的创造性产物”,(36)简言之,“境界”是“生活、自然之美”反映在诗人头脑中的观念形态的产物。
诚然,我猜佛氏本意,其动机是想发掘且放大王氏诗学中的所谓“现实主义因素”,(37)以期王氏诗学能朝他心中的那个“现实主义”(实是反映论为基准的流行文论)模式上靠。且不提该模式同经典现实主义差距甚大,我只想说,若王氏“境界”真的被现实主义化了,则“境界”也就不成其为“境界”了。这便涉及到对现实主义的美学界定了。我以为,作为19世纪中叶便风行西方文坛的经典现实主义,是有其独特的美学规定的,它所以苛求艺术应用高度逼真的日常细节来构筑典型性格及其世俗场景,是为了让形式也能凝结或折射作家对现世秩序的批判眼光即清醒理趣。这就是说,现实主义是以鲜明的时代指向性而著称的。这便与王氏“境界”相背,因为“境界”要义是忧生,而非忧世,它重在关注人对生命价值之探询,“而不顾时代与社会之‘兴味’如何”。惹人费解的是,佛氏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如他说过:“试看《词话》举了那么多诗词例句,总的看,其中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与趋向的成份,总是相当的稀薄。他自己的词作也是如此。执着于‘忧生之嗟’的悲观主义……”(38)但疑惑也就接踵而来:既然已经认准王氏《人间词话》的人文主题是人生感悟,既然已经认定忧生甚重的《人间词》本是对王氏诗学的亲切实践,为何佛氏还要从反映论(即认识论)角度去阐释“境界”呢?这不是思维内讧么?
五
明明佛氏自己误入思维内讧,他却倒过来批评王氏诗学有“一个基本矛盾及其重大局限性”,这就是:“唯心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往往限制着,阻碍着诗论中健康的现实主义因素之有力的发挥”,以致“冲淡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自己时代的再现的内容。”(39)具体地说,便是王氏虽“将诗的美之本质放在‘境界’(意境)上,而境界之为境界就在它来自‘自然与人生’”,“但与此同时,他眼里的‘自然及人生’却往往是个脱离具体时代与历史发展的自然人生,其中弥漫着灰暗的悲观的色调”;“这样,他就势必转过来极力限制‘境界’说中具有先进的部分之功能的发挥。例如他的境界说准确地抨击了诗词境界的‘隔’,但其自身却往往从根本上疏远以至隔离了现实社会,疏远以至隔离了狂飙般的时代精神,而导引人们走向‘安得吾丧我’、‘了却人间是与非’的冥漠混沌的境界。”“他一面倡言:‘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一方面又高扬‘以物观物’的‘于静中得之’的‘无我之境’,将那种‘不平’之气削弱到最低限度,甚至不惜将艺术境界拉向某种神秘的宗教境界。诸如此类,都反复表明,王氏的唯心的悲观主义的思想体系,往往冲淡了,缩小了他所提出的某种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艺术观点、原理之巨大启蒙作用。前者成了后者的对立物”。(40)
诚然,作为学术,佛氏怎么看王氏诗学都行,那是他的“一家之言”。我感兴趣的只是:发现“境界”真髓为忧生,本是佛氏文献学比较之实绩,为何到头来又遭佛氏嫌弃了呢?根子可能是佛氏一时消化不了,但又不甘说自己消化力不强,于是便指责对象不易消化,扔了。当然,我所说的消化实为理解或皮亚杰式的同化。胃只能消化它所能消化的食物,每个学者也只能同化与其学养相适宜的那些学术对象,一俟对象逾出其学养范围,主体之局限也就开始露馅。面对忧生甚重的王氏诗学,我以为佛氏在如下两方面尚有欠缺:一曰方法,二曰观念。
先看方法。我说过,文献学比较固然为佛氏带来了新视野,如发现《人间词》、《人间词话》的母题是忧生,但由于缺乏发生学比较的深层导向,便未能进而确认忧生作为整个青年王氏的灵魂聚焦,当然也应是他的诗学建构的思辨根基。这就是说,王氏所以能对思想庞杂的叔氏作扬弃性人本解读,并所以能以忧生主线来再创性地纵贯诗学整体,而不像在1904年时亦步亦趋地模拟叔氏,就是因为他心底蕴有一片远比人本哲思更本原,更幽邃,且日益成熟的价值情怀。这是导致青年王氏建树卓绝的第一能源。但这又必须靠发生学比较的深入发掘才可能勘探到。这就解释了,佛氏的文献学比较虽已绵密到了“史无前例”之境,几乎为王氏《人间词话》的每一重要条目都要找一组相对应(或自以为对应)的叔氏语录,但为何在评判王氏诗学时仍陷于思维内讧呢?要害乃在于:失却发生学导向的文献学比较是无力将它的科学发现贯彻到底的,即光靠文献学比较势必消化不了其实绩。
再看观念。或许有人会问:为何佛氏不从文献学比较走向发生学比较呢?答曰:佛氏为何一定要从前者走向后者呢,若后者与其观念不契的话。这就是说,观念对学者而言,可能是比方法更深邃、更刻骨铭心的东西;当主体以为某对象若靠先在观念便能洞察,他便无意去拓展新视角了。王氏诗学的忧生主题便正是这类对象。因为佛氏早有定见:即像忧生这类精神现象,若仅“限在一个人的内心进行”,“而无涉于社会实践,故全属于唯心论的范围”。(41)这便清楚了,原来,佛氏在哲学观念方面仍坚执基本哲学命题只有一个,即从认识论角度回答人(精神)与世界(物质)的关系,至于人对自身生命的价值关怀(生存哲学)则对不起,因与社会现实隔了一层,故纯属邪道,不屑深究。与此相匹配,假如哲学上只有唯物反映论才是过硬的,那么,落实到美学上,当然也只有再现现实才是“健康”的了。这也就解释了,佛氏为何要将王氏之“合乎自然”夸张为“现实主义因素”之余,又无情揭露王氏忧生为“唯心”了?
不妨让佛氏与李泽厚作一对照。李氏在1957年撰《“意境”杂谈》,其意图也想将王氏诗学“现实主义”化或反映论化,就此而言,也可说佛氏是在80年代重复李氏曾走过的老路。当然佛氏的鞋是新的,这双新鞋叫文献学比较。但耐人寻味的是,李氏至70年代末已悟得此路不通,并接连撰文以示自我超越了。但佛氏却执拗得多,越走越远。
注释:
①③④⑤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9、130、146-147页。
②见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⑥⑦⑧⑨⑩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47、6-7、8、8、146-147页。
(11)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35页。
(12)叶舒宪:《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书城杂志》1994年第1期。
(13)赵庆麟:《融汇中西哲学的王国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14)《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48页。
(15)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89-190页。
(16)《王国维文学论著集》第349页。
(17)(18)(19)《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67、357、367页。
(20)(21)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30-131、189-190页。
(22)(23)《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63、352页。
(24)(25)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64、174页。
(26)(27)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97、195-196页。
(28)(29)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95、184-185页。
(30)《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58页。
(31)(32)(33)(34)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99-200,204,162页。
(35)(36)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82-183、158页。
(37)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62页。
(38)(39)(40)(41)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386-387,386-387,383-385,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