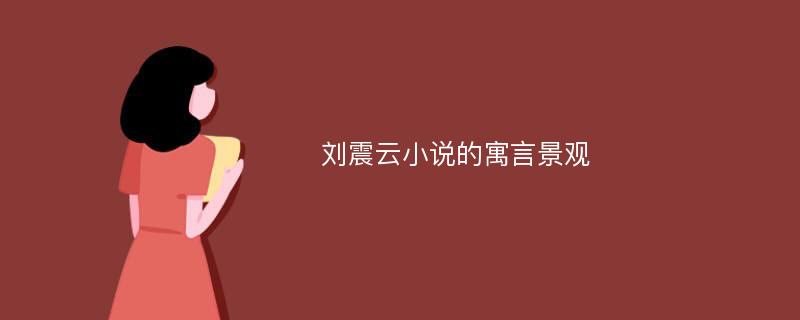
王际兵[1]2002年在《刘震云小说的寓言景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震云小说以寓言景观考察了人生存的虚妄,使存在怵惕于人心。然而,寓言在这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寓意故事,而是本雅明提出的一种审美精神。它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本体论的。 本文在辨析了有关寓言的理论之后,先从艺术形态上揭示了刘震云小说的寓言色彩,其主要表现为废墟的形象世界、戏谑的话语空间和思辨的叙述向度;接着,又分析了刘震云小说的寓言意蕴,从权力、历史、人性等切入点感悟了隐喻其中的存在的荒诞。
刘书怡[2]2014年在《从冷眼写实到喧哗写意》文中研究表明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的实力派作家,自80代末被文坛关注至今,他的作品在创作方式、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主题选择方面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个性鲜明的风格让刘震云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而他的作品也始终体现对时代变化的关注。本文按时间顺序梳理刘震云的小说创作的嬗变过程。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分析探究不同时期刘震云创作嬗变的原因。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刘震云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作为“新写实”小说流派代表这一时期作品进行分析。作品中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注,对权力的讽刺与批判,还原本色的写实风格成就刘震云初入文坛的辉煌。这一时期的创作经历为刘震云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帮助刘震云建立起具有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以个人成长经历作为创作初期的灵感来源使得“零度写作”的背后仍带有对小人物的命运的少许温情。同时刘震云的创作视角也在这一阶段由单一的个体转向群体,由物质层面转向对精神层面的关注。第二部分将90年代刘震云呕心沥血创作完成的“故乡”系列作品作为文本分析的重点,深入探究出90年代刘震云的创作发生变化的原因。时代变革带来的冲击是创作发生转型的外在原因,进入90年代的“新写实”作家们在这一多变的时代中试图寻找新的突破口,尝试去挖掘更丰富的人生意义和更多层面的现实内涵。刘震云以戏谑的形式,对“故乡”和“历史”进行了解构,并构建出自己的精神“故乡”,进行个人化的历史书写。第叁部分从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主要作品入手,从主题,叙事方式等多角度地把握作者新时期的创作转型。刘震云在这一时期积极地与影视合作,充分借助市场和传媒,并打造出在影视界广受赞誉的中国当代的“作家电影”。在“触电”的影响下刘震云的部分作品具有明显的“影像叙事”特征。最后通过多对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嬗变过程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后,认为刘震云自80年代至今的创作中,其多变的叙事模式,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变化都与他的精神层面的困境和力求突围的不断尝试有着紧密联系,在多变的创作形式中实则蕴藏着永恒的精神诉求。
冯庆华[3]2013年在《刘震云小说论》文中研究指明一般对于刘震云的熟知都是从1987年的《塔铺》这篇作品开始的,之后的刘震云以一系列所谓“新写实”引发了一股评论热潮。“新写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传统现实主义视野下从来没人这么写,都像是在做梦,“新写实”是从梦中醒来了,在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的环境中给读者打开了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视角。迄今为止对于刘震云的研究也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但所谓“新写实”固非刘震云创作的重点,也非他的起点。他的写作从发表处女作开始算起可以推到1979年的《瓜地一夜》这个点上,在《塔铺》、《新兵连》这些较为成熟的作品之前,刘震云已经有了将近10年的模仿期。这个时期的写作尽管幼稚,但其关注世界的着力点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感知,并且把刘震云模仿阶段写作与后来写作作整体观,可以感受到他与一般关注风情、风俗、风景、地域、时代的作家不同、也与社会批判型作家不同,刘震云是一个思想型作家,他一直在试图把握世界、人生、时代表象背后的本真。他写作的发展过程恰好反映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考过程,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于时代和个体存在困境的体系性认知,尤其是他没有在解构传统与现代的过程把个体归入到一种虚无之境,而是寻找到一种超越困境的途径。尽管这种超越并非完美,但对于在困境中存在的个体来说,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此外,刘震云这种一直执着于对“理”探求的写作风格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当代文坛也是一副独特的风景。论文试图通过对刘震云写作发展过程的梳理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尽量描绘出他的思想谱系;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当代文学史价值和意义进行评价。第一章是对刘震云至2012年为止的创作过程进行梳理。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模拟期,从1979年的《瓜地一夜》开始至1987年前后。这个过程思想上还在传统的遮蔽之下,试图把握世界而又无能为力;叙事技巧方面则显得有意建构曲折的情节和建构意象的努力,但总体上显得幼稚,做作;第二阶段从1987年的《塔铺》开始,至2002年的《一腔废话》结束。本阶段的刘震云思想上开始挣脱传统的因袭,开始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和世界的认识、开始思考时代背景下个体困境的本质,于是权力、伦理、历史、故乡、宗教、存在等先后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叙事方面则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作了大量形式方面的试验,具体表现在语言狂欢、叙事结构、文体等方面,创作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论;第叁阶段则是从2003年的《手机》开始至今。此时思想上在达到了人存在的困境之后,他认为已经抵达人性的本真,并开始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叙事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形式狂欢重新又回到素朴状态,但第二阶段试验中的成功之处仍然在本阶段延续,其叙事结构的设置常常凸显形式的意味。第二章围绕刘震云作品中的权力书写进行论述,论述了权力引发人追逐的原因、获取权力的过程、权力运作的过程、权力对人的关系。权力成为个体确认自我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这种认识本身便是在权力遮蔽下形成的,这种认识又反过来助推了权力的威力。人性因此在权力遮蔽下被异化,失去了人的完整性,因此这种试图通过权力获得实现自我确认的努力终将归于失败。第叁章论述了刘作品中相关伦理书写。分别概括了作品中呈现的几种伦理,论述了伦理的尴尬与温情。指出伦理尽管最初是本诸于人性的,其中有温情的一面。但伦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被权力改造,成为权力的帮凶,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权力与伦理的合谋中完成的。第四章论述了刘震云的书写“新历史”的努力,其中涵盖了历史的几种向度,重复性、偶然性、真相与表象;人被权力和伦理异化的过程正是在历史这个时间维度中完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种被遮蔽的历史;还论述了刘震云通过戏仿、庸俗化、游戏化等手法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努力;第五章围绕故乡展开。阐述了故乡与怀旧的概念,又围绕时间还是空间、物还是人、想象与真实、故乡与个体四部分论述了故乡作为人个体怀旧的一个精神空间,所有权力的威慑,伦理的训导和温情都发生在其中,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故乡这个空间中完成的。个体的故乡情结不过是一种在对当下不满基础上反顾,一种在想象过去中寻找慰藉的努力。第六章,论文的核心部分,正是在人性的思考中刘震云认为他找到了切入世界的入口。本部分围绕人性的几种进行论述。论述了人性的几种,如懦弱、遗忘,恃强凌弱、习惯当下,从众心理向往公平等等互相共生又彼此矛盾的人性。这是人性的本真,有丑陋凶残的一面,也不乏温情的一面。这是导致个体存在困境的渊薮,也是摆脱这种困境个体必须直面的人性本真。第七章是宗教。本章辨析了宗教的作用及刘震云的宗教观。刘震云对对中西宗教作了思考,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真正起到协调社会关系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家伦理。中国所谓的宗教如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也都是在伦理的隐蔽下求生,共同给人提供生存超越的途径。但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传统伦理的崩溃,宗教的作用也完全消解。现代人陷入一种孤独和焦虑之中。第八章是刘震云近年《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思考的核心,也是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他进入了关于存在的思考,并试图在对存在困境的直面中,依据人性的本然和渴求,探索一条超越困境的途径。结语中对前面几章内容作了一个梳理和归纳,把他思考的这个过程概括为“通向人性本真的途中”。论述了他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对传统权力、伦理、历史、故乡的祛蔽和对个体超越生存困境的探索。其中权力是异化人性的罪魁祸首,伦理则被改造为为权力帮凶,这些人性遮蔽的历时性过程就构成了历史,而其发生的场地便是故乡;权力固然遮蔽了人性,而这种动机却仍然来自人性中欲望的膨胀。个体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孤独、困惑,希望超越,宗教和伦理就是人类找到的关于生存超越的一种途径,但因为其在当下的局限性,刘震云最终把眼光投向了存在的思考。在结语中还指出刘震云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对其创作的成就和特色进行了尽量客观的文学史评价。
杨洁[4]2018年在《论刘震云小说的反讽艺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当代着名作家,刘震云从1982年开始创作,30多年来笔耕不辍,作品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其新写实小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写尽中国社会中小人物生活的琐碎与烦忧;新写实小说之后,其新历史小说又转而言说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新世纪开始,他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用新世纪小说描写人物灵魂深处的孤独特质。纵观其各阶段的小说创作,反讽已成为其作品整体性的文体风格。然而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术研究都只是在文本层面上探究其小说的反讽艺术,对反讽这一历史性概念的界定仅仅是“字面意思与实际意义的悖反”,且甚少涉及对整体小说反讽艺术的深入分析。因此笔者认为,对刘震云各阶段小说的反讽艺术、反讽独特性及反讽意义的研究不得不说是目前学术界需要着重关注且值得系统研究的一点。本论文尝试从反讽层面研究刘震云的整体小说,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涵盖刘震云其人其作、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反讽的历史流变和释义;第二、叁、四章将以刘震云各阶段小说的代表作为中心,从言语、叙事、总体反讽叁个层面细致探究其各阶段小说具体的反讽手法、反讽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在结语部分,本文将对刘震云各阶段小说的反讽艺术进行总结并在反讽的共性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化。通过对刘震云小说反讽艺术比较细致的探究,本论文认为,刘震云不论是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还是新世纪回归小人物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强烈的反讽意味,且各有其独特性。其中,新写实小说以“零度叙述”为代表的语态反讽见长。在冷静客观的自然主义外衣下,运用反讽隐晦且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物异化状态的同情与审视;新历史小说以戏仿反讽见长。在游戏、破坏和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写作下,运用反讽直接且集中地对历史的惯性逻辑进行了批判和讽刺;新世纪小说以荒诞的结构反讽见长,相比前两者,其反讽更为直观、彻底及透悟。总而言之,为了缓解内心愈益凝聚的沉重,反讽叙事是刘震云逃避追逐的最有效手段。综上所述,笔者希望借此论文为刘震云小说研究乃至中外小说反讽的理论和实践做一些较为扎实的基础性工作。
马丽[5]2016年在《论刘震云小说的精神品格》文中研究表明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鲁迅思想的呼应,随着刘震云的小说诸如《一地鸡毛》、《单位》、《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等不断被搬上荧屏,对刘震云作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对其作品的精神品格的分析与解读却存在不足。如果说处在现代夹缝中的鲁迅的思想核心在于立人,那么身处风云变幻的当代的刘震云则在探寻生存困境中人的救赎之路。刘震云从开始创作至今一直笔耕不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刘震云思想的日臻成熟,其创作有着明显的跨时代特征。刘震云作品的思想性、不断开创的新的书写方式在展现着刘震云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的同时,也述说着他一直以来对于人性、孤独、救赎等永恒性话题的不断思考和对救赎之路的探索。本文旨在结合刘震云具体作品,对其作品所表达的对救赎之路的追寻的精神品格进行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既是对刘震云作品精神品格的剖析,也是通过对其创作的梳理,探讨在刘震云跨时代的书写过程中思想不断成熟完善的个人与社会因素。论文分为五个部分:除去绪论和结语共有叁章。绪论主要梳理对刘震云作品研究的现状和问题,阐述其精神品格解读的缘由与意义;第一章通过对刘震云作品中表达的个体生存困境的存在主义解读,来分析刘震云是怎样以冷峻的书写展露人世、人性的;第二章通过作品中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来分析刘震云对个体的关注对真相的追问;第叁章通过对刘震云整个创作历程的跨时代特征的梳理,对作品中内蕴的对信仰与尊严的强调,对理性救赎的呼唤,实现对刘震云作品精神品格的立体化构建;结语主要将刘震云创作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思考其无论在对当代文学中历史书写方式的创新上还是其作品中呈现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徐越[6]2011年在《刘震云“故乡系列”的创作风格研究》文中认为刘震云,当今中国文坛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刘震云创作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叁部以“故乡”为题的作品,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故乡系列”。这一时期的刘震云在创作风格上,较之前的“新写实主义”,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本文将就作家“故乡系列”的创作风格进行探讨,并重点阐释作品中的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后现代等因素。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将刘震云的创作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从主题、叙事、语言等多方面探究“故乡系列”的特殊意义,也就是不同于之前创作的具体表现;二、通过对“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叁个文本之间的内部比较,比如相似和相异之处,来进一步了解作家创作风格的变化和文本的深层意蕴;叁、通过对作品艺术风格的解读,来揭示其中蕴含的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后现代等因素;四、总体评价刘震云“故乡系列”的艺术成就,并说明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张博伊[7]2014年在《多面映像:刘震云小说的乡村书写》文中提出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自他进入文坛以来,他的创作几乎都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手机》、《我叫刘跃进》、《一腔废话》等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其主人公也都是一群来自乡村的城市人。故乡是他创作的园地,是他关注人性、观察社会、思考文化的基点,从而刘震云的作品营造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世界。刘震云的创作风格多样,这与他的思想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当然也与八九十年代,甚至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潮有着紧密联系。在主客观双重因素作用下,刘震云的创作几经转变。本论文则选择其主要转变期内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展开分析,力求全面展现他多面镜像下乡村书写的风貌,重申刘震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对乡村这一主题书写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全文共分为叁大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绪论部分梳理了刘震云故乡情结的生成以及他作品中展现出来多样的乡村世界。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分别选取刘震云四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乡村题材小说,对具体文本展开详细分析,从而揭示出他乡村书写的特性。第一章选取刘震云进入文坛被广泛认可的《塔铺》,在《塔铺》系列中刘震云秉承写实主义传统,构建了一个略带温情诗意的乡村。第二章论述了他以别样的方式呈现乡村世界—《故乡相处流传》。主要选择历史与权力两个视点,论述了刘震云以反讽、戏谑等方式完成对乡村历史的书写。第叁章以刘震云最具争论性的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为切入点,阐述了他以乡村为基点展开的一场精神游走,这部小说无论是文体还是创作方法都是一次革新。第四章以《一句顶一万句》为支点,论述其发现的乡村精神史,完成了由历史向现实回归的路程。最后的结语部分在前文基础上从审美选择的角度来论述刘震云乡村书写转变特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刘震云从乡村走来,他的创作始终以乡村故土为基点,完成他对于整个世界的言说。他的作品受到评论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证明了他的创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通过本论文的梳理,以期挖掘出他对乡村书写的独特性。
赵巍巍[8]2013年在《消解与颠覆—刘震云小说创作思想艺术建构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作家的突出代表,刘震云以其如椽之笔,在洞悉世事与人情的基础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推出了一大批极具哲理、风格鲜明的小说作品。从《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到“故乡”系列、到《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凭借日益成熟的创作技艺和不断推陈出新的作品,实现了人格境界的彻悟与作品思想的重塑与涅盘。其作品深入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人物精神实质当中,借用“微言”与“小事”,进行诗意与哲理的艺术创造,摒弃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典范,开拓并发扬了古今杂糅、纯理性的想象与极度的现实相映成趣的艺术路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刘震云其人及作品应是不可缺席的,这对于我们研判、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意在从创作思维和作品思想内核的角度,对作者的理性创作与作品思想成熟表达双重线索进行新诠释,核心在于挖掘刘震云作品的思想艺术与价值指向,进而探究作者精神追求目标与向往。论文将在回顾刘震云小说创作历程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分析和理解刘震云小说创作思想艺术理路——消解与颠覆,进而通过分析其民间立场、追忆历史真实的目标和小说创作的理性思路与文本特色,探究其为了达到消解与颠覆的目标指向所扎根的基础与实现路径,从而揭示出刘震云为了激起国民觉悟而努力前行的文人情结。
翟春雪[9]2012年在《逃离后的回归》文中提出在80年代后期崛起的青年小说家中,刘震云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日益引人瞩目的青年作家,他写作的朴实厚重和执着的精神探索使理论界的研究评论从未停歇。而作为新写实派的代表,刘震云更是把寻找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出路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不断努力追寻。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故乡”一直是最为耀眼和醒目的核心意象,刘震云试图直面生活的恐惧,质疑历史的理性,他用“故乡”来承载历史,重新构建人类历史和精神的家园。本文分位五部分:导论介绍了故乡情结、对于刘震云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故乡情结源起,探讨刘震云的乡土世界的创作来源和出发点,从历史、想象和消解叁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二章时空体的空间循环,分析作家想象中故乡混乱时空的构成要素和循环规律。第叁章重回故乡,以“从故乡出走”和“朝故乡回归”的顺序解析刘震云回归精神故土的疲惫旅途。
张智韵[10]2012年在《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刘震云小说研究》文中认为存在主义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作为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潮代表,存在主义深刻思考人类的存在问题,它是西方哲学的任务从研究客观世界的存在到追求存在的意义的转折。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有“历史结构的近同性”,因此存在主义在中国新时期广泛传播,同时存在主义文学也在中国文坛掀起热潮。描写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和对社会现实非理性的批评和揭示,以及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关注,是存在主义和中国新时期思潮的重要交汇点。存在主义对我国新时期的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震云作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成就突出的作家,在其小说中表现出对“人的存在”这一主题一如既往地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生荒谬的表现,对历史、世界本体的怀疑和追问,使刘震云成为一名探索“人的存在”的当代作家。仔细研读刘震云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之所以广为人知并获得赞誉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将对“人的存在”的思考贯穿在写作之中,从新写实时期的“小林”系列和以单位、官场为背景的小说,到新历史时期的“故乡”系列等,都揭示了环境对人造成的异化、扭曲。之后进入新媒体批判时期对科技时代人伦关系的思索、批判,直至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始终可以见到刘震云对人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对生存现实的非理性状态的深切体悟、对社会历史的独立思考,深刻诠释了“文学即人学”这一经典命题。在刘震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小说的存在式主题:表现现实的荒诞与历史的轮回,人性的异化、复归以及人的情感与沟通的隔膜。在表现手法和艺术特点上,刘震云小说也大量运用将人物放入荒诞境遇中的方式进行反讽地揭示,同时运用象征化、寓言化批判策略使揭示更具意味和深度。用存在主义视角切入来阐释刘震云小说中所隐含着对寻常个体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探询,和作家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根本性思考,有助于揭示刘震云小说风行时下的原因,也会让我们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境遇进行更深入的思索。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小说的寓言景观[D]. 王际兵.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2]. 从冷眼写实到喧哗写意[D]. 刘书怡.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3]. 刘震云小说论[D]. 冯庆华. 南京大学. 2013
[4]. 论刘震云小说的反讽艺术[D]. 杨洁. 西南交通大学. 2018
[5]. 论刘震云小说的精神品格[D]. 马丽.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6]. 刘震云“故乡系列”的创作风格研究[D]. 徐越. 西南交通大学. 2011
[7]. 多面映像:刘震云小说的乡村书写[D]. 张博伊.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8]. 消解与颠覆—刘震云小说创作思想艺术建构解析[D]. 赵巍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3
[9]. 逃离后的回归[D]. 翟春雪. 四川外语学院. 2012
[10].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刘震云小说研究[D]. 张智韵.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2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刘震云论文; 塔铺论文; 寓言论文; 文学论文; 故乡面和花朵论文; 一句顶一万句论文; 故乡相处流传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故乡论文; 手机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