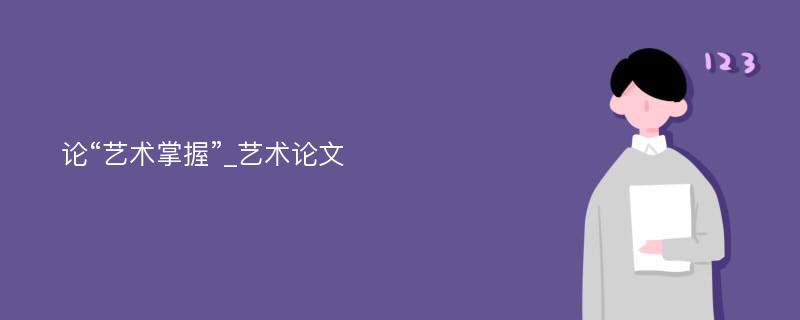
论“艺术掌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是艺术家对世界进行艺术掌握的产物。艺术创造的实践活动,是建立在艺术家头脑对世界进行艺术掌握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艺术家不只在创作的时候,而且在体验、感受生活时,一开始就是运用对世界进行艺术掌握的方式。
因此,认识和研究“艺术掌握”的特点,对于艺术家创造艺术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文艺美学的建立与健全,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艺术掌握”不同于“科学理论掌握”筹方式,这个论点对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都十分重要。但,由于马克思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研究方法时顺便提及这点,而对“艺术掌握”和其他三种掌握方式有何异同,却没有作具体解释,也没有展开论述,因此给我们留下一些理解上的困难。
多年来,很多同志对“艺术掌握”作了一些探索,有一些好的见解,但也有一些见解还需商讨。特别是有一些见解,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我们固然不应该停留于背诵马克思的言词,而应该按其精神去研究新的问题,作出新的阐释,但也不能随意曲解马克思的原意,不在弄清楚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求得新的发展。
本着“对事不对人”,开展同志间友好探讨的态度,下面我冒昧提出一些意见。
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或说法,在美学界中还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有的美学家说:“马克思说(或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查诸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找不到这句话的。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也根本就没有这句话。如果说,有的美学家有这样的看法, 又认为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体会到这个意思,那就必须说出自己的根据,作出科学的论证。否则,一般读者如没有读马克思原著,而信任这些美学家的话,误以为这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那就会谬种流传。例如,有的同志说:“美是什么?这个历来思想家、美学家难以解答的迷人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明白告诉我们:美就是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全面自由。”〔1〕但是,我们翻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找不到马克思有这样一句话,也看不出马克思在哪里早已明白告诉了我们这个意思。如果说,这是作者自己的意思,也还可以商讨。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只简略提一句:“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全面自由”到现在还很难说有谁实现了,那么,岂不是到现在人类还没有美可欣赏吗?这个“全面自由”不知要到哪天人类才能实现,因而也就不知要到哪天人类才能审美。由此可见,这个历来美学家难以解答的迷人的问题,还得研究和探讨,而不宜宣布马克思早已明白解答了。
关于“艺术掌握”,几十年来有些论著中就有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说法,近年来新发表的论文中也仍有这方面的表现。对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展开友好的艺术探讨,目的是想对这些难题的认识能有一些进展。
二
有的同志说:“掌握世界方式是劳动对象、主体的认识和劳动活动、劳动手段和方法以及劳动成果四者有机的结合或总和。缺一都是不能成其为掌握世界的方式的。”〔2〕并且举例说:“宗教掌握世界方式是以如何超脱苦难和罪恶的人生与虚妄的理想的天国或仙境为研究对象,以信奉者的著经和颂经为主要实践活动,以文字宣传经义和定期举行宗教仪式为主要手段和方法,以众多的众生纷纷虔诚信奉和自觉履行宗教职责为宗教掌握世界方式最终标志。”〔3〕
这里所说的劳动对象、劳动活动、劳动方法和劳动成果四者结合的,似乎是在说“劳动”,而不是在说掌握世界的“方式”。举例说的宗教的四要素,似乎在说“宗教”,而不是在说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不是“宗教学”,怎么会有“研究对象’。我认为,一个信徒,面对世界世相,产生宗教的想象,把打雷下雨看成是天公发怒,惩罪子民,是子民前世作孽的报应,这就是“宗教掌握世界方式”,区别于认识打雷下雨的自然原因与规律的“科学理论掌握方式”,也区别于把打雷下雨看成有激动感情的阳刚之气的“艺术掌握世界方式”,也区别于把打雷下雨看成需要在屋内躲避以得平安的“实践精神掌握世界方式”。这里没有“研究对象”,没有著经活动,没有定期的仪式,没有众多的众生履行职责,也仍然是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篇文章提出“四要素”说,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段话:“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它的对象和它的手段。”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对的;但这篇文章把“思维掌握方式”和“劳动过程”混为一谈,就不对了。
这篇文章还说:“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是不能不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的,科学掌握世界方式中的实践活动自然也不例外。”〔4〕显然,这是把“科学掌握世界方式”和“实践活动”混为一谈了。
这篇文章说到“实践精神掌握”时,说这“是具体实践和为实践直接需要的思维或认识”,例如“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军事掌握世界方式等等。可以说,人世间有多少个行业就有多少个掌握世界方式。”〔5〕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掌握方式”的距离就更远了。我认为马克思说的四种掌握方式,是不以行业分的。例如在同一个“农业”内,对待“花朵”这同一个对象;科学掌握方式可以认识它是植物的生殖器官,艺术掌握方式可以感受它是女人的微笑,实践精神掌握方式可以认为它(例如玫瑰花、茉莉花)可泡茶喝,宗教掌握方式可以认为它是禅宗启悟的偈语。
说到“艺术掌握方式”,这篇文章说它必须具备1。艺术思维2。创造活动3。创造手段、方法4。成果—作品。这又是把“艺术掌握方式”与“艺术创造”混为一谈了。“艺术创造”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其中第一项“艺术思维方式”就是“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创造,必须运用“艺术思维掌握世界的方式”,即不同于科学理论、宗教、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作品,则是运用艺术掌握方式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成果与产物,而不是艺术掌握方式本身。因此,怎么能把创造活动、创作手段、成果作品统统包括到艺术掌握方式中去,作为这个方式的四要素呢?
这篇文章谈后面三个要素的篇幅的总和,远远少于谈第一个要素的篇幅,也证明了“掌握方式”实际上就是第一个要素,并不包括后面三个要素。要把后面三要素也当作“掌握方式”去谈,是很困难的,是谈不出多少内容的。
这篇文章说艺术思维是“映象想维”,把“映象”与“形象”作了区分,这是可以的。但说“映象思维”中的“思维”是动词,即以表象进行思维,’而“形象思维”中的“思维”则只能是名词,即以形象表达思维(此处把“思维”等同于“思想感情”,有些勉强)。又把“艺术思维”经艺术创造活动产生“作品形象”说成是“艺术思维”经艺术创造活动转化成“形象思维”〔6〕把“形象思维”等同于“作品形象”也不恰当。硬要把“形象思维”的原有涵意(主要以形象进行思维)否定掉,改成这种新解释(以形象表达思维),也有些勉强。我认为,加一个新的阐释:“形象思维”中的“形象”实指“映在脑中的形象”,它来自“生活中的形象”,最终产物与目标是指向“艺术品中的形象”就可以了。这就把“生活中的形象”、“映在作家脑中的形象”和“物化在作品中的形象”三者区别开来了。而“形象思维”实际上就是以“映在脑中的形象”来进行思维,实即“映象思维”,因为,要用形象来思维,当然只能用外物形象通过感觉映在脑中的表象来思维,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与它的来源(外物形象)与它经艺术创造后物化成的产品(作品形象)当然是有区别的。
三
我们认为,人掌握世界的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实际掌握,即以物质身体四肢去占有对象,通过劳动实践,实际上改变对象,这是人对事物所有掌握关系的基础;二是精神掌握,即在头脑中通过思维、意识去认识、感受对象。精神掌握的可能、内容、范围、深度,都被实践掌握所制约,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掌握的成果(思想、认识、感情、观点)反过去又影响实践。人类不仅要求世界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还要求世界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认识、欣赏、信仰、抒情等),因此,就产生出对世界多种不同的掌握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全面论述“掌握方式”,没有说到人对世界的实际掌握方式,而是在重点说到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时说,这种方式不同于艺术掌握、宗教掌握和实践精神掌握。这里说的四种掌握,都是人的精神意识对世界的掌握方式。
多年来有些论文把这四种掌握方式说成也是实际掌握、实践掌握方式,这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例如,有的文章说:“马克思即使在这里,也不是把掌握方式完全封团在精神活动的领域内,而是看到了精神掌握方式与实践掌握方式的相互联结相互渗透,并且在人类掌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和精神方式的结合中,提出了第三种独立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7〕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掌握方式”的只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8〕在这里,分明说的只是精神掌握方式,根本没提到实践掌握方式,根本没有提到两种掌握方式的相互联结和相互渗透,更没有提出第三种独立的掌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分明是把实践—精神掌握方式与艺术的、宗教的掌握方式并列,说科学理论掌握方式与这三种掌握方式有区别。文章的作者完全可以说自己主张有第三种独立的掌握方式,并陈说理由,却没有必要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我们能这样毫无根据、无中生有地把马克思原文中没有的意思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吗?
马克思在这里,分明认为艺术、宗教、实践精神的和科学理论的四种掌握方式都是精神掌握方式,实践—精神方式,也是精神方式之一,并非第三种独立的掌握方式。但,这篇文章却说:“精神方式主要指理论方式”,而把艺术掌握方式和实践—精神掌握方式都说成不是“精神掌握”;而是第三种独立的掌握方式。这是与马克思这里把艺术掌握、实践—精神掌握都列为人的头脑对世界的精神掌握的原意不相符合的。
这篇文章还说:“马克思……把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看作是人类的物质实践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感性活动方式与理性认识方式的统一,看作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人类‘合规律合目的’的统一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方式,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并塑造自我的方式”〔9〕。我们从马克思在《导言》中的一段话中,能看到这些意思吗?在这段话里,马克思说到了四种精神掌握方式,其中就有宗教掌握方式,这也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难道这种方式也是人类“合规律合目的”的统一的、自由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并塑造自我的方式吗?我们能因此认为在这里“在人类历史上,是马克思第一次达到人类自我意识的最自觉的高峰,最科学地提出和解决了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这一命题”〔10〕吗?显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马克思的那段话里是没有这些内容的。表面上,文章作者在这里抬高了马克思,实际上却是消解了马克思区分四种掌握方式的功绩。
马克思在那段话里并没有提出“关于人类掌握世界方式的多展次的深刻内涵”。因此,文章作者根据自己设想的“马克思”的“深刻内涵”认为:“艺术是一种介于人类物质实践与科学认识、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之间的,综合了实践活动的感性、具体、物质性与科学认识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特点的、独立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掌握方式即艺术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11〕这些话都是还需探讨的。
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这是马克思的意思,那就需要提供马克思的原话作证明。如果说,这是文章作者自己的意思,那也需要论证。特别是艺术综合了“科学认识的理性和抽象”这一点,更需要论证。特别是例如《西游记》和《聊斋》这些艺术品又在哪里综合了“科学认识的理性和抽象”?更需要论证。
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理解,不但不能说是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的原意,而且还是和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的原意正好相反。因为,马克思在《导言》中说的正是科学理论掌握方式不同于艺术掌握方式,怎么会认为艺术(掌握方式)里综合着科学认识(掌握方式)呢?
在我看来,艺术家当然也可能有科学认识,这对艺术创作也可能有帮助,但这是间接的,而且必须转化为审美情感,服从审美情感的表现。艺术中表现审美情感,常常是不符合科学认识的。不综合科学认识,与科学认识不同,这才是艺术的特点。科学理论与艺术的掌握方式,各有所长。只有掌握了它们各自的特点,才能发挥它们的长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要抬高艺术掌握,而把它说成是包罗一切、包罗科学认识的理性抽象在内的最完备的掌握方式。因为,这样的艺术掌握是不存在的。要求艺术掌握具备这样的“大杂烩”特征,也是不正确的。这只会导致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产生,失去艺术特点,也失去真正的“艺术掌握方式”。
至于说到艺术“改造世界”的作用,似也不可简单化。艺术不能直接改造世界。它也不同于科学理论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是要影响人们的审美情感,间接作用于改造世界这也需要辩明。
这篇文章说:“马克思在论述艺术生产与其他精神生产的关系时,显然又把艺术生产从纯粹精神生产如理论活动的领域相对地划分出来,而归入了比较靠近物质生产的‘实践一精神’活动的领域。”〔12〕这也是缺乏论据的。作者把“艺术掌握方式”与“艺术生产”等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在《导言》中并列的不同的“艺术的”与“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怎么会变成把艺术生产归入实践-精神活动的领域呢?
我想,作者可能是望文生义:既然艺术创作是精神活动,又是实践活动,既要物质材料,又要物化为艺术作品,所以艺术是“实践-精神”活动 。按此逻辑,我想,科学理论写作与宗教“活动 ,也既是精神活动,又是实践活动,既要物质材料,又要物化为科学著作与宗教经书、场所和礼仪行为等,它们也该是“实践-精神”活动了。按此逻辑,恐怕不仅是该把艺术掌握,而且还该把科学理论掌握、宗教掌握都归入实践-精神掌握方式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四种不同的掌握方式,也就变成一种相同的实践精神掌握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是符合马克思愿意的吗?
这篇文章还说:“宗教的掌握世界方式是一种兼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方式,……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是一种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但也排斥抽象思维方式,……艺术掌握方式则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13〕再参照前面引述的艺术掌握还综合科学认识的理性抽象的说法,可见作者的看法,宗教的、实践精神的、艺术的掌握方式都是兼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方式,没有多大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原话的重点是要说明四种掌握方式的不同。而人们对此却探究不深。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对马克思所说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是“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理解不很清晰而造成的。对于这一句话的理解,是一个关键的难点。弄清这个难点,就能进一步弄清四种掌握方式的区别。
四
同一个作者在另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提出的,艺术是一种既不同于理论、也不同于物质生产实践,但又既离不开精神又离不开实践的、属于‘实践-精神’方式的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14〕我们查看马克思的《导言》,其中并没有提出艺术是“实践-精神”方式。
作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只是认为理论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人类单纯选用‘思维着的头脑’的专有方式即思维方式来掌握世界的方式,……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方式则不纯粹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另一类综合了人类感性物质实践因素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而是包含了从理性思维到感性实践随多层次的丰富的内容”〔15〕。
为什么理论掌握是纯粹的思维方式,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则要综合物质实践呢?作者的理由是:“理论的掌握世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语言概念反映世界的思维过程,这里的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符号,语言与思维之间带有某种直接性,思维活动与语言运用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同一的……而其他掌握世界的方式……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方式不是直接同一的,……也包含着对世界的物质实践的改造、制作过程〔16〕。
这里所说的“物质实践的改造,如果是指实际改造世界,那么,我们要说:艺术,并不能实际上改造世界,它只能影响欣赏者的审美感情,进而通过欣赏者的行动去改造世界。如果说是指这种作用,那么,科学理论也能影响读者的思想认识,进而通过读者的行动去改造世界。如果这里所说的“物质实践的改造”是指艺术家头脑中的意象与其物化的艺术作品形象不是生活形象的机械复写,而是经过改造、制作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科学理论脑中的概念与其物化的科学理论著作也不是生活的机械复写,而是经过理性抽象、概括、推理、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的。
作者说:艺术掌握一定要把艺术构思物化成艺术作品。我们要问,难道理论掌握不也是要把理论思考物化成理论作品吗,不也是要经过“外在的制作和创造活动”吗?
前面引述作者说艺术掌握等“包含了从理性思维到感性实践的多层次的丰富内容”,运用到“艺术掌握”“宗教掌握”上不一定恰当,而运用到科学理论掌握倒是恰当的。因为,艺术、宗教等虽不排斥理性思维的因素,但毕竟主要不是理性思维,而科学理论则倒主要是理性思维。
在论及总的“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时,作者说“从人同世界的总体关系来说,它则应是指思维方式,认识、反映方式和物质实践方式、劳动生产方式的统一。”〔17〕既然作者承认科学理论掌握也是“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中的一种,怎么又唯独不承认科学理论掌握方式也是物质实践方式统一的方式,而只承认艺术、宗教等掌握方式是和物质实践方式相统一的方式呢?又怎么能把是否和物质实践方式相统一作为科学理论掌握和艺术掌握、宗教掌握的区别所在呢?又怎么能把“纯理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说成是“排除了物质实践因素”的呢?
作者把马克思与艺术、宗教掌握并列的“实践-精神”掌握理解为“日常的务实的精神活动”〔18〕,是我们大体上能够赞同的。但,他同时又把这三种掌握方式另归为“实践-精神”的一类掌握方式,并且说这是马克思的意思,就使我们感到缺乏根据。
作者进而又说:“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精神’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实践与精神的综合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既包含着人类对世界的物质实践方式、又包含着人类对世界的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19〕这实在是费解的。这种内涵照理说应该是指人类对世界总的掌握方式,应该包括理论掌握在内(因为作者也承认,理论掌握是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之一),但作者偏又认为理论掌握是纯粹思维,不包含物质实践方式的。
更为矛盾的是,作者又说,“马克思在《导言》里,在说明理论掌握方式不同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不同特点时,固然是从不同思维方式特点的角度加以比较的;但显然也包含着从不同实践方式的不同特点的更深层的比较在内。”〔20〕作者既然认为理论掌握是纯粹思维的,“排除了物质实践因素”的,那又怎么去比较它与其他掌握有“不同实践方式的不同特点”呢?
以上这些矛盾,可能总的来自作者要抬高“艺术掌握论”有关。作者说:“马克思则把艺术视为一种综合了人对世界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认识和反映方式与人对世界的艺术实践方式、艺术生产方式和艺术创造方式的‘实践一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是马克思关于艺术本质的最高宏观命题,……是人类历史上的艺术本质论的一切最大的科学综合的伟大变革”〔21〕。
我们从马克思《导言》中论及艺术掌握的原话中,实在看不出有这么高、大、全、深的内涵。在这段原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说科学理论掌握不同于其他三种掌握,是“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作者认为这个“专有的方式”就是纯粹思维,而“排除了物质实践因素”而其他三种掌握则是综合物质实践方式在内。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也还需要探讨。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探索一下马克思的原意,把这四种掌握的区别探讨一下,可能并不能概括出马克思艺术本质论的最高命题,却也许能对认识艺术的特点有一些切实的帮却也许能对认识艺术的特点有一些切实的帮助。
五
我认为,在精神上把世界当作什么来掌握,决定于掌握的方式与眼光。同一个事物,用不同的眼光、角度、方式去掌握它不同的方面,事物就会在头脑中呈现为不同的东西、形态和意象。它很可能不同于事物本身的样子。
四种掌握方式,各有产生的根源,各有长处和局限。实践-精神掌握,是在实际事务中把对象当作实用对象掌握,最早被人运用。其长处是很实在,容易运用;缺点是不能深入本质、规律。宗教掌握,最早是对未了解的世界事物的猜测和愿望,是世界虚幻和歪曲的反映。其长处是善恶分明,给人精神寄托和慰藉(人们很需要);缺点是引人脱离现实真相,容易麻痹斗志。艺术掌握,是人满足审美需要的必要方式;它把事物放在美审观照、体验中。其长处是不抛弃生动具体形象形式,诉诸感觉,强烈动情;缺点是不象科学理论条分缕析本质规律,综合与复制出事物整体。科学理论掌握是后起的;有了体脑劳动的分工,意识才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正确的理论掌握,能使人从理性上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全面反映事物各个侧面、层次、环节、阶段、方面、关系、领域,把他们抽象出来,又按其本来的联系,复制出整体;缺点是舍去生动具体样式,不如生活丰富。如脱离感性实践,可能干瘪、僵化,走入玄秘臆造,虚构的歧途,并不符合真实。
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精神掌握方式的,呈现为不同的东西。例如,“下雨”这一事实,科学理论掌握,就掌握其科学性质、本质规律、成因与后果。宗教掌握,就会虚幻地当作是冥冥之中的天神在显灵,是奖惩人间的报应。实践精神掌握,就把它当作有实用意义的对象,如它可能导致丰收或歉收,要避其患害,取其实利,出门要带伞,晒衣须收进等。艺术掌握,则把它当作审美情景来欣赏,与自己感情联系起来,就会出现“杏花春雨江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小楼一夜听春雨”、“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意象或意境。
艺术掌握,是把事物当作艺术(审美对象)掌握的思维方式,即掌握事物形象符合欣赏者审美意识(理想、趣味、情感、观点)的审美属性的方式。一般欣赏者与艺术家都能对世界进行艺术掌握,但艺术家审美修养、能力高强,善用艺术眼光去感受生活。例如,面对纤夫拉船的情景,画家脑中很快呈现出逆流勇进的画面构图;音乐家很快感受到,并构思出强烈的旋律乐曲;雕塑家敏锐地掌握住某一瞬间的最佳造型;戏剧家感受到强烈的戏剧性冲突;舞蹈家掌握到力与美的运动造型;摄影家能掌握住静止的某一能表现典型性格或意境的瞬间,等等。
狭义的艺术掌握是审美掌握中主要的重要的掌握。审美掌握包括狭义的对艺术品的掌握与对生活(社会与自然)的广义的艺术掌握。牡丹花,桂林山水,不是艺术品,但人们可用审美眼光;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观赏,这就是广义的艺术掌握,与审美掌握(把事物当作艺术品那样的审美对象去欣赏)同义。
艺术掌握的特点是运用审美感官(耳目)直接感知事物形象的美丑,进行情感体验。它相同于科学理论掌握之处是开始于感觉,又上升为理解后更深刻地感觉到内涵的“具体” ,服务于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同处是直接感知、观照形象,动人以情,不同于科学理论舍弃形象,抽象出概念,经分析又综合为“思维具体”,服人以理。
艺术掌握,相同于宗教掌握,是着重运用形象思维,融铸进自己感情、想象与愿望,影响人们情感与情操;不同处是,不把现实事物当作彼岸神鬼世界来掌握,引人脱离现实,沉浸于虚幻的天堂幸福美景与地狱惩罚的彼岸中。在艺术掌握中,事物反映到头脑中也要变形变相,但不是变成彼岸天堂地狱,而是突出事物契合欣赏者审美意识(理想、感情、趣味、观点)之处。
艺术掌握同于实践精神掌握处是,都面对事物形象,不作概念的抽象、分析与综合;不同处是不从物质功利上掌握事物实用属性以满足实用需要,而是非功利地掌握审美属性,满足审美需要。
艺术等三种掌握方式,不同于科学理论掌握“用头脑专有方式”,就在于:不是用逻辑思维抛弃感性形象材料,抽取出本质、规律,形成概念,经分析与结合,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脑中复制出包容事物全部侧面与关系的整体,而是只掌握某一部分属性、侧面、部分。艺术掌握,不可能象理论掌握那样全面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整体,其长处是能反映生活形象情景,感染和激起审美感性。我们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可以了解到从政治经济学里所看不到的具体材料,很生动、具体、细致、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物性格、内心感情等。但,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整体,还是必须求诸《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毕竟是得不到这个整体认识的。
艺术家如有对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和理论修养,又能把这些认识转化为对生活的真情体验,转化为审美感情,又能体现在转化为艺术形象的形式里,动人以情,如果欣赏者也有相应的理性认识,那么,这个艺术品当能有助于启发欣赏者联想到、加强认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对列宁说托尔斯泰的艺术能反映出生活某些本质方面,就该这样理解,而不能误解为艺术品能象科学理论那样揭示生活本质规律。如这样理解,就会使艺术创作走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歧途,而不是对生活作艺术掌握了。
多年来,文艺创作中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用科学理论掌握方式去掌握了本质规律,再用生活形象作图解、演绎本质规律的例证,而不是从感受生活开始到酝酿构思到表现阶段,自始至终运用艺术掌握方式和“审美的眼光”去感受、体验和构思表现生活的审美属性。
另一种创作中的错误倾向,是以为艺术掌握可以纯粹以自我感情去掌握事物,认为感情与理性思想完全无关,可以任凭个人情绪(还有下意识),爱把世界想象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可作歪曲与虚幻的随意反映。这样理解“艺术掌握”当然也是错误。这样的产物就是唯美主义、唯情主义作品。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艺术掌握”的特点,作深入的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以获得正确的深刻的理解,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美学要面向广阔的现实生活》,1993年4月14日,光明日报,第6版,“文艺论坛”版。
〔2〕〔3〕〔4〕〔5〕〔6〕《也谈艺术掌握世界方式》,1993年第2期《文学评论》。
〔7〕〔9〕〔10〕〔11〕〔12〕〔13〕〔18〕《“艺术掌握方式”新论》,1991年第5期《文艺研究》。
〔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4页。
〔14〕〔15〕〔16〕〔17〕〔19〕〔20〕〔21〕《艺术掌握方式的特殊辩证内涵》,1993年第1期《文艺研究》。
标签:艺术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文化论文; 形象思维论文; 宗教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