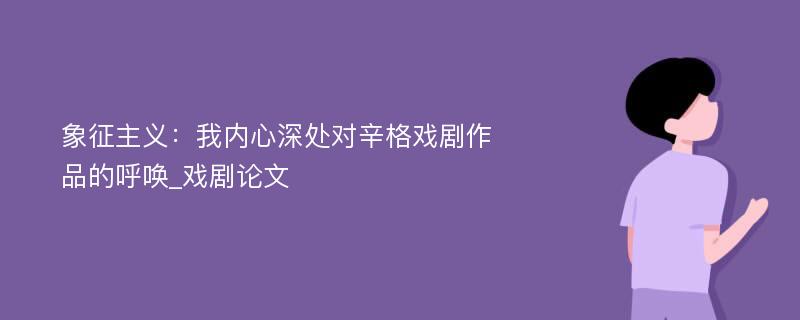
象征:发自内心的呼唤——评辛格的戏剧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象征论文,内心论文,作品论文,评辛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密灵顿·辛格是二十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杰出的领导人和剧作家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六部戏剧,以其独特的风格给爱尔兰戏剧运动和英国舞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评论界普遍认为辛格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被看作“爱尔兰戏剧运动第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注:桂杨清、郝振益、傅俊:《英国戏剧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然而我们又看到辛格在戏剧创作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蹈海骑手》就是一部典型的象征主义戏剧。有的评论家也把《圣井》归入象征主义流派。但辛格的戏剧既不同于只是局部运用象征手法的现实主义戏剧,也不同于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典型的象征主义戏剧。他的戏剧基本上是在具体的现实主义描述的基础上,赋予作品以总体上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在辛格的作品中主题象征是统领全局的,现实主义手法用于具体描述,为象征主题服务。这一独特的手法使辛格的戏剧具有了深刻的内涵与不衰的艺术魅力。
辛格戏剧的总体性主题象征和一般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有所不同。象征在戏剧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有了戏剧,象征手法便一直被运用着。由于象征是指用具体的事物来暗示某种抽象的概念,而戏剧又是一种视觉艺术,因此戏剧家往往采用象征体,尤其是具体可见的物体,来调动观众的联想,暗示抽象的概念,给观众留下强烈难忘的印象。例如尤金·奥尼尔《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那件结婚礼服,巧妙的象征着女主人公一去不复返的年华和纯洁的过去。爱尔兰剧作家奥凯西《朱诺与孔雀》中的圣灯象征着约翰尼的命运,圣灯的熄灭预示着约翰尼被杀的结局。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路旁的那棵树在第一幕中是光秃秃的。到了第二幕,树上长出了几片叶子,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与剧中两主人公“一切照旧”的状态相对照,这一可视的时间变化加深了观众对人生荒诞而无意义主题的理解。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曹禺也在《雷雨》中通过暴风雨中的周公馆引导观众联想到中国二十世纪初封建式资产阶级堡垒的岌岌可危和终将崩溃。象征主义戏剧流派否定客观地反映现实,强调表现直觉,把象征手法作为剧情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剧中不断地强调,使其成为影响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一流派的大多数作品中,象征手法主要还是表现为具体象征体的运用。如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马莱那公主》第三幕中出现的天鹅,象征着纯洁、善良。马莱那公主被杀后天鹅全从宫堡中飞走了,其中有一只还死了。同上述剧中的象征手法相比,辛格的戏剧中很少出现这种暗示事物发展变化、人物命运、甚至作品主旨的具体象征体,而主要在总体上带有象征意义,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等具体组成部分才有了各自的象征含义。
象征主义作品在效果上的多义性和朦胧感使读者对作品主题产生不同的理解成为可能,但也往往使作者的本意不易被观众或读者认识。这也许就是辛格的戏剧当初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原因。除了《蹈海骑手》,他的剧作当时大多不受爱尔兰观众欢迎。《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在都柏林上演时甚至引起爱尔兰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骚乱。(注:桂杨清,郝振益,傅俊:《英国戏剧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346页。)他所创造的戏剧人物,如《峡谷的阴影》中的娜拉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克里斯蒂不仅不被理解,还被当作是对爱尔兰妇女的侮辱和对农民的诽谤。在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辛格因此被看作是民族的叛徒。然而只要了解一下辛格的生平,我们就会发现辛格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之一。他曾于一八九六年参加莫德·冈领导的准军事组织——爱尔兰同盟,于一八九八年参与筹措了“爱尔兰戏剧文学社”,一九零四年成为阿贝剧院的创建人之一,对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个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的热血青年,显然不会用他的笔去背叛民族。相反,他以文学创作为武器为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正如爱尔兰伟大诗人、剧作家叶芝在《诗与翻译》的序言中所评论的那样,“他给了祖国所需要的——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遭到更多憎恨。”(注:转引自Margaret Drabble,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Literature,fif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在退出爱尔兰联盟时辛格写到“我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为爱尔兰的事业服务。”(注:转引自王佐良、周珏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辛格此后的经历证明这种“自己的方式”便是他独具特色的戏剧创作:通过赋予作品总体性的象征,赞扬爱尔兰民族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批评他们在追求理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动摇性,力图唤醒爱尔兰大众的民族意识,鼓舞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坚定不移地与殖民主义者作不息的斗争。
这一鼓舞与呼唤的象征主题是与爱尔兰民族独立斗争的特点紧密相关的。爱尔兰自八世纪起便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十五世纪时,英国都铎王朝入侵。一八零一年英国与爱尔兰签定了联盟条约,从此把爱尔兰完全置于其统治之下。虽然自十八世纪起爱尔兰人民便拉开了抗英民族斗争的序幕,但由于殖民统治力量强大,殖民者长期在政治、宗教方面实行双重统治,在经济上进行重重剥削,爱尔兰政治封闭,经济落后,革命力量薄弱。此外,由于爱尔兰民族力量本身又存在严重的宗教矛盾与政治矛盾,既有争取“自治”的“自由邦派”,又有要求完全独立的“共和国派”,因此爱尔兰民族独立斗争错综复杂,以至于一九二一年爆发了内战。外国与本国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和内战的破坏使爱尔兰人民长期生活在极度贫困与动荡中。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爱尔兰民族迫切需要一种坚定不移、生生不息的斗争精神;需要一种面对现实、敢于反抗的勇气。辛格通过他的悲剧和喜剧反映了爱尔兰独立斗争的这一特点和要求。
他的名作《蹈海骑手》写于一九零四年,叙述了莫尔耶一家三代男子丧生大海的故事,被认为是“现代戏剧中最优秀的独幕悲剧”。(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55页。)评论界一般认为这部剧“歌颂了渔民和大海的斗争, 人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的斗争”。(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55页。 )大海是支配命运的自然力的象征,而莫尔耶一家是人类的代表。通过他们敢于向大海挑战的行为,赞扬了人类的奋斗精神。然而联系辛格创作此剧时爱尔兰民族斗争的背景,我们发现暴虐凶险的大海更可以理解为残酷的殖民统治者的化身,理解为压迫在爱尔兰民族头上的反动力量。它不仅惊涛密布,骇浪滔天,威胁着岛民的生命,阻碍着他们的发展与繁荣,而且还浩大强悍难以征服。可是即便如此,莫尔耶一家并不屈服退缩。他们是整个爱尔兰民族的代表。无论是祖辈、父辈还是年轻的一代,男人还是女人,面对凶险的大海,他们坚强无畏地与之抗争。祖父、父亲倒下去,儿子们继续出海;五个哥哥葬身海底,迈克尔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乘船出海去集市卖马。就连姐姐凯瑟琳也无视眼前的危险,面对母亲的阻挠,替迈克尔辩解,道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小伙子就得出海去呗。”(注: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而女主人公莫尔耶看到家中最后一个男子也在大海中淹死时,她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平静地承受了一切。“他们一个个都去了,大海再也不能打扰我了……”(注: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我们还要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是长生不老的,我们应该知足了。”(注: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一个不怕强暴、不畏死亡的民族,是任何敌人都无法征服的。在莫尔耶这些平静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剧情象征,辛格在此不仅塑造了莫尔耶这一勇敢顽强的爱尔兰妇女形象,更重要的是歌颂了爱尔兰人民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反抗精神。
这种面对困顿和压迫坚毅不屈的反抗精神是爱尔兰民族值得自豪的优秀品质之一。而这一品质的形成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分不开的。爱尔兰当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多数人口分布在农村。因此真正能代表爱尔兰民族的是这些住在荒凉山区、偏僻岛屿的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深受本国和外国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也不优越。荒僻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坚毅不屈的品质,同时也养成了他们乐天知命、耽于幻想的性格。在幻想中,残酷现实带来的痛苦得以削弱而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得以增强。因此,坚毅不屈和爱幻想成为爱尔兰民族特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运动中,后者则会阻碍革命的成功。辛格深刻地意识到这一民族特性的弊端。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运用象征含蓄地向爱尔兰人民提出警示。
这一思想首先反映在《圣井》一剧中。创作于一九零五年的三幕剧《圣井》讲述了一对盲人夫妇的遭遇。按照剧情发展和象征意义,全剧可分为三个部分:杜尔夫妇双目复明前的生活,复明后的经历及再度失明后的选择。第一部分充分展示了爱尔兰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沉溺于幻想的特性。年近半百、饱经风霜、以乞讨为生的盲人夫妇象征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爱尔兰人民。生活虽然艰辛,他们却未灰心丧气。“他俩一点儿不伤心,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要是有人喜欢开玩笑,他们也会凑趣呢。”(注:汪义群:《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第396页。)然而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却建立在一个虚幻的精神支柱上。支柱的一端是对自己容貌的自信和陶醉,另一端是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和欣赏。实际上,杜尔夫妇容貌丑陋,而他们生活的地方只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山区。这一虚幻的支柱是乡邻们的善意谎言和他们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的产物,经不起严酷现实的检验。可杜尔夫妇却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怡然自得,编织着理想——渴望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剧情发展到第二部分,杜尔夫妇遇到了奇迹。一个过路的圣徒治愈了他们的眼睛。理想变成了现实,但幻想却破灭了。他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容貌和环境同幻想完全相反,还发现过日子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借助奇迹,辛格在戏剧中把沉溺于幻想的杜尔夫妇带进了现实。现实生活中虽然不会有这样的奇迹,但却不乏让人们了解现实的机会。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真实的斗争迫使人们面对现实,了解现实。但他们在认清现实后应该如何选择呢?
在《圣井》的第三部分,杜尔夫妇再度失明,而圣徒又来了。他们面临选择:治愈眼睛面对现实还是继续生活在黑暗中以乞讨为生?杜尔夫妇选择了后者,指望重新在虚幻的平静中生活。然而,如果说了解现实前他们的幻想是一种积极生活态度的表现,如今,他们的幻想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是不敢直面现实的退缩。最后乡亲们不愿再帮助他们,他们只得背井离乡,去过流浪的乞讨生活。通过这个结局我们可以看出辛格对这种退缩的态度是不同情、不赞成的。因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迫切需要的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态度。
辛格另一部涉及“幻想与现实冲突”主题的戏剧是他的代表作《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它被评论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爱尔兰剧本”。(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年11月版,第455页。)主要讲述了青年克里斯蒂在盛怒下杀死了父亲,逃到马尤海岸一个偏僻乡村后的离奇遭遇。有的评论认为这部戏剧“讽刺了某些爱尔兰人民好夸口的习性和美化歹徒的弱点”。(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1 月版, 第455页。)实际上,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审视, 我们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在离奇的情节中包含了深刻的寓意。作者通过象征再次批评了爱尔兰人沉溺于幻想的特点,指出他们对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理解不够深入并表达了自己对爱尔兰革命战士成熟的期待。
剧中的马尤村民在一定程度上是爱尔兰人民的代表,而女主角蓓吉又是马尤人的突出代表。通过马尤人特别是蓓吉对克里斯蒂态度的变化,我们再次看到爱尔兰人耽于幻想、回避现实的特点。戏剧开始,包括蓓吉在内的马尤人对流落到此狼狈不堪的克里斯蒂仅仅怀疑和好奇。当克里斯蒂吐露他杀父逃亡的真情时,马尤人立刻对他肃然起敬,蓓吉甚至爱上了他,因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尤人潜意识中对压迫在他们头上的宗教、法律和经济势力充满了抵触情绪。但马尤人只有反抗的内心倾向却缺乏付诸行动的勇气。他们渴望这种勇气,崇拜具有这种勇气的英雄。以暴力反抗父权的克里斯蒂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但在对克里斯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崇拜或爱慕的唯一基础是他杀父这一还未确定的事实。可以说马尤人的崇拜毫无现实依据。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实际上只是笼罩着幻想中的英雄光环的杀父凶手。可是克里斯蒂在前所未有的赞誉和爱幕的鼓舞下却出乎意料地成长起来。不仅变得出口成章,谈吐优雅,还在一年一度的竞技会上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了真正的英雄。当克里斯蒂的父亲老马洪追来,克里斯蒂杀父成为谎言,马尤人和蓓吉立刻抛弃了他,因为他们仍然沉浸在幻想中,只认定那个杀父的克里斯蒂是英雄,而不顾眼前克里斯蒂已成长为真正的英雄的事实。幻想和现实发生了冲突。为了挽回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的形象,克里斯蒂当众打昏了父亲。杀父暴行活生生地发生在蓓吉等马尤人眼前,幻想和现实再一次冲突,他们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把这原本当作“勇敢”的行为看作是“肮脏”的。为了不连累自己,他们甚至站到了克里斯蒂的对立面,要用私刑绞死他,而蓓吉正是这一背叛行为的带头人。蓓吉和马尤人这一戏剧性的态度变化生动而明白地展现了耽于幻想的爱尔兰人在追求理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动摇性。最后克里斯蒂父子离马尤人而去,蓓吉失声痛哭自己“从此失去了西方世界唯一的花花公子”。这个结局暗示了蓓吉和马尤人的动摇性只能阻碍理想的实现。
马尤人把杀父凶手当作英雄崇拜的行为同样还反映了当时爱尔兰人对民族解放斗争所需要的反抗精神缺乏真正的理解。深受压迫的马尤人需要敢于反抗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但他们却盲目崇拜“杀父英雄”的行为,这表明他们把反抗精神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为使用暴力。
克里斯蒂的经历则象征着爱尔兰民族解放战士成长发展的过程。他原本胆小懦弱。由于父亲逼他娶一个有钱的老寡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打昏了父亲。这其实是自发状态下的自我保护行为,并非具有自觉的反抗精神与“男子汉气概”。马尤人的尊敬和蓓吉的爱虽然鼓舞了他,使他成长起来,但到他夺得竞技会冠军时他仍未成为自觉的战士。和马尤人一样,他并不明白真正的男子汉气概、反抗精神意味着什么,以为杀父便是英雄行为。因此他才会津津乐道他杀父的过程,并不断添加虚构的情节;才会后悔没早一点杀父;才会当众再次杀父以挽回形象。第二次杀父后马尤人尤其是蓓吉的背弃帮助克里斯蒂走向成熟,使他认识到了马尤人的浅薄,理解了“男子汉气概”的真正含义。因此,当马洪苏醒要带克里斯蒂离开时,他一反那个对父亲诚惶诚恐,胆小如鼠的形象,变成了父亲的主宰。“和你一起走,是吗?我会的。像英勇的船长带着他未开化的奴仆。走吧!从今天起我要看你为我煮燕麦粥,洗马铃薯。因为从现在起,我是一切战斗的胜利者。走啊,我说!”(注:John·M·Synge,Collected plays (Great Britain:Penguin Books,1952) P:209.)
从以上几部剧作可以看出辛格作品的整体性象征是他呼唤民族独立心声的载体。而这一载体又建立于具体的现实主义描述基础上。现实主义因素使辛格的象征作品有别于一般的象征主义戏剧。典型的象征主义戏剧注重气氛渲染,因而作品多带有神秘色彩。如梅特林克《玛莱娜公主》的第四幕中,玛莱娜孤独地躺在房间里,大黑狗在黑暗中发抖,莫名其妙地吠叫;走道里有奇怪的脚步声;暴风雨像无数手指敲打着窗户……这一切无不给人以神秘而恐怖的感觉。而辛格的作品则几乎没有这种神秘的气氛。他的戏剧“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他认为生活的基本现实是戏剧的唯一源泉。”(注:王佐良、周珏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140页。)这首先表现在他作品的选材上。除《忧伤的戴尔德拉》,他的剧作基本取材于他在阿兰群岛生活期间的见闻,剧情有真实的生活基础。即使像《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这样情节离奇的作品,也是根据他所听到的真实事件创作的。在人物刻画方面,辛格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无论是能说会道的流浪汉,还是小偷小摸的补锅匠,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语言是体现辛格作品现实主义特色的重要方面。辛格的戏剧语言源自于现实生活,是对阿兰群岛农民方言的模仿。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写作《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时,和我写其它剧本一样,只用了一两个我在爱尔兰乡亲中从来没有听过或者我儿时会读报之前没说过的词。”(注:《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另外,辛格剧作中大量的景物描写也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无论是多风的山角、乌云滚滚的山区、孤零零的乡村酒店,还是明净的湖泊、富饶的田野,都是爱尔兰真实景物的再现。
辛格作品中的这种现实主义描述与总体象征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真实、客观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而又富有诗情的爱尔兰乡野风情画,使作品具有了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现了美与现实的协调统一,为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标签:戏剧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克里斯蒂论文; 爱尔兰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