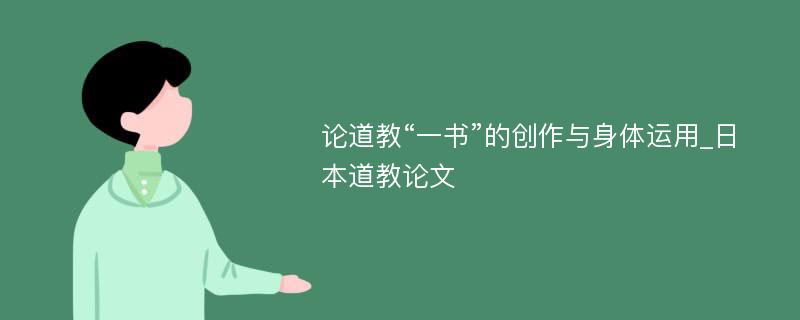
《道教义枢》论本迹与体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教义枢》是初唐道教的重要教义书,原题:“青溪道士孟安排集”,即是说编本书者为孟安排。据史料记载,孟安排活动於武则天时代,是一位地位较高的道士,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孟安排自号“青溪道”,所谓“青溪”,指荆州临沮县的青溪山,为东晋南朝道士隐居修炼的地方。《道教义枢》是以产生於它之前的道经《玄门大义》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去掉繁冗,广引众多道经编集成书的。《道教义枢》是否为《玄门大义》的节本?由於《玄门大义》的全貌今已不可得见,还难以下定论。日本学者麦谷邦夫的《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以〈道教义枢〉为线索》一文认为:“《道教义枢》基本上是一部忠实地缩编《玄门大义》的道教教义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参照了系统的教义书《通门论》和《玄门大义》的异本《玄门论》等,对事实加以订正,对叙述进行简化,补足,并补充了若干经证。因此可以认为,《道教义枢》的教义同《玄门大义》几乎是一致的,没有加进孟安排个人的观点。”[1]这一结论显得根据不足,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还不足以断定孟安排在《道教义枢》中没有将自己的看法写进去,只是简单地做点节录缩编的工作而已。《道教义枢》的编纂体例,分为“义曰”和“释曰”两个部分。麦谷邦夫认为:“《道教义枢》的各义首先用‘义曰’来概括《玄门大义》的各义的内容,接着以‘释曰’的形式来节略《玄门大义》。”[2]然而,也有可能在“释”的部分,孟安排将自己的观点补充了进去,作了某些创造性的发挥工作。否则,孟安排只是在做一件毫无创新意义的事情,这似乎并不符合孟安排制作《道教义枢》的本意。在《道教义枢序》中,孟安排说得十分清楚,他编写此书是要使“大笑之流,肃然悟法”,是为了给“勤行之士,指示玄宗”。既要让人“悟法”,为人“指示玄宗”,那么总该有点新东西启迪人,总不致於一味抄袭前人。在《玄门大义》的基础上编写《道教义枢》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是对道教教义进行新的总结,即有继承,又有创新,具有不同於《玄门大义》的自身特色,这一点是应当给予肯定的。《道教义枢》能历千余载而流传到今,已显示出它具有个性化的教义价值,它比《玄门大义》更简明扼要、更精当地概括梳理了当时道教的教义,于是《道教义枢》一出,《玄门大义》便在道教中失传了,只留下残篇剩卷。这正透示出《道教义枢》不是简单地“节录”《玄门大义》,它经过一番再创作,具有了更新、更高的教理价值。
《道教义枢》的思想学术来源不是单一的,其中所包含的哲学道理与道教重玄学说有紧密的关系,而其基本立场则是站在道教茅山宗的角度,试图融汇道教各派教理教义,作出一种综合性的总结。从方法论上看,《道教义枢》明显采用了重玄学的方法,提出“神凝於重玄”的主张,以重玄学的“四句”法去“通释”某些教义。《道教义枢》显然还受到佛教教义学的影响,反映出唐代道教教义吸取佛教而演化的线索。据《道教义枢序》,全书十卷,凡三十七条教义。今本第五卷“三乘”及第六卷“六通”、“四达”、“六度”、“四等”、共五条教义已佚,实存三十二条教义。本文即据此讨论《道教义枢》的本迹体用观。
我们讨论成玄英的重玄思想时,已指出成玄英对“本迹”与“体用”范畴的关注,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讨,对本迹的含义作了界定,并提出本迹相即、从本降迹、摄迹归本诸命题,结出了唐初道教界论说本迹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3]令人可惜的是,《道教义枢》未能将这一理论成果总结进去,没有专辟本迹义予以讨论,可以说遗漏了当时道教的一条重要教义。所幸的是,它在某些地方涉及本迹体用问题,使我们仍能从中观察到隋唐道教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其看法首先涉及什么是本?卷三《两半义》对此讲得较多:“神本澄清,既本澄清,何不澄清为本耶?今明经说澄清为本者,即示无本。既其澄清,复有何物?若其有物,何谓澄清?故《西升经》云:‘本出虚无’。既知颠倒,本来无本,即知生死,本来无始。既知本来无始,岂得今来有终?故《盟威经》云:‘众生根本,亦无始终’。《本际经》云:‘众生根本相,毕竟如虚空,妄想人生死,梦幻无始终’。今言九圣为终,氤氲为始者,是不终为终,不始为始。既以不始为始,无本为本,故云本于虚无与澄清也”。这一大段话的意思何在?它的主要意思就是证明“本”的内涵为虚无澄清,众生看不破,于是流浪生死,人生得不到解脱。以人生论为着眼点,劝人将生命的根本放置于虚无澄清之上,从而超越生死。我们知道,成玄英提出“无为妙本”,认为“复本”就复归于无物。成玄英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去论说,《道教义枢》虽不着眼于本体论,但其立论基础还是建立在以无为本之上的,即其人生论的哲理根基还是成玄英式的“无为妙本”,从中可以窥见魏晋玄学贵无派的影子。在卷二《三洞义》讲到大乘道教的“迹本”时,又提出道教传统的以气为本的观点:“洞真教主天宝君为迹,本是混沌太无元高上玉皇之气;洞玄教主灵宝君为迹,本是赤混太无元上玉虚之气;洞神教主神宝君为迹,本是冥寂玄通无上玉虚之气”。这实际上是南北朝以来道教流行的一气化三清之说,三洞教主皆是迹,为气本所生。以气为本说是否与上述“本于虚无与澄清”说相矛盾?一点不矛盾,这从其所说的气是虚无之气即可知晓。秦汉哲学家说“气”多指出其实有性,汉魏道教的气论亦从实存出发,南北朝以降,受佛教讲“空”的影响,道教气论呈现突出“虚无”性的价值取向,尤其反映在道教最高尊神的塑造上,三清被说成是虚无之气的产物。道教气论的这种变化,当与其以无为本的体认分不开,正是将宇宙之本看作“无”,道教传统中以气为世界本源的观点,自然便沾染上“无”的色彩,以无为本与以气为本由此合一。《道教义枢》阐述世界之本、人生之本就是这种合一的绝妙体现。
在论述“本”的同时,《道教义枢》没有说明“迹”指什么,但从其对迹的一些描述看,迹主要指现象,比如三洞教主的本源是气,迹则表现为具体的形象。迹虽是种表象,为“本”所规定,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有它自身特有的功用,尤其表现在帮助道士修道之上。卷一《三宝义》诸道经说道士形迹为什么与众不同:“《定志经》云:‘兴显道士,形与世隔者,黄褐玄巾,披罗衣锦,形既殊凡,心宜改俗’。故《本际经》云:‘衣弊履穿,谦光晦迹’。又云:‘舍俗服,玩黄褐玄巾,斯以迹引心,令超世网’”。道士的穿着打扮与世俗不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以此时时刻刻提醒修道之人牢记自己的身分,使自己的道心不泯,超脱凡心,越出尘世罗网,最终得道。在这时,“殊凡”的形迹所起的功用就是引导修道者的“心”不断超越尘俗,向着“道”靠近。由此看来,迹对于本起着补充作用,或者说起着某种导向作用,引导人向本回归。
返本,这是《道教义枢》十分明确的主张。卷二《七部义》讲太玄时提及“摄迹还本”,并引《盟威经》说:“法文者,法以合离,文以分理”,指出这句话的意思是:“众生离本,所以言离,故下文云:‘反离还合,合真舍伪,由法乃成也’”。所谓“离”,指的就是众生离开了根本;所谓“本”,指的就是向本的回归,与本真会合;“反离还合”的含义就是“摄迹还本”,亦即成玄英所讲的“归于妙本”。还本的主张,与《道教义枢》主张向道的回归是一致的,都是劝人修道,成就道身。这一点,从其结合法身论说本迹明确地透示出来。
据卷一《法身义》的说法,本迹总括起来有六种,“本有三称,迹有三名”。本的“三称”指什么呢?指的是:“一者道身,二者真身,三者报身”。这显然将佛教的三身说引了进来,并略加改造,[4]从而说明道教“法身”的根本含义。从根本上说,道教法身划分为道身、真身、报身这样三身,《道教义枢》引用诸多道经揭明这三身的内涵。第一,“道身者,《太平经》云:‘道无不导,道无不生’;《度人经》云:‘唯道为身’;《本际经》云:‘即是真道,亦名道身’”。所谓道身,亦即“真道”,说的是以道为身。第二,“真身者,《玉纬经》云:‘真,淳坚也,谓体无秽杂,常往嶷然’”《消魔经》云:‘近为真身’;《本际经》云:‘我之真身,清净无碍’”。[5]所谓真身,亦即清净无秽杂之身,淳坚无碍,实际上是道的清静无为特性的体现。第三,“报身者,报是酬答之名,谓酬积劫之行。《本行经》云:‘至今之报,为诸天所宗’。《本际经》云:‘元始正身,因无数劫。久习妙行,报得此身’”。所谓报身,亦即对积劫之行的报答之身,如元始天尊无数劫以来修习妙行,获酬报而得此身。这象征着道对人修行的报答,暗示人经过“久习妙行”可以成仙不死。
以上从“本”去说法身,那么迹的“三名”又指什么呢?“迹三名者,一者应身,二者分身,三者化身”。从本上讲,法身有三身,从迹上讲,法身也有三身,其含义如下:第一,“应身者,应是应接,谓随机显迹,应接群生。《请问经》云:‘以无心而应众生’;《本际经》云:应物根性,示色象,故名应身,亦曰生身。言生身者,随顺世法,诞育形体也’”。应是“道”对众生的应接,“道”从本降迹,显示色象,这种显示是“随机”的,对众生的应接是“无心”的。道之“随机显迹”是要“应物”,是种“随顺世法,诞育形体”的举动。第二,“分身者,分是分散,我一身散在多处,身虽非一,形相不殊。《本际经》云:‘分形散体,无有限量,止见一方,故惟百亿’。又云:‘诸分身者,是于报身,起无碍用’。《灵宝经》云:‘天尊分形百万,处处同时,是男是女,并见天尊,俱如一地’”。“道”的形象化,体现元始天尊具有“无限量”的分身法,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显示了“道”不受时空限制。第三,“化身者,化是改变无常,倏欻有无,种种殊相,非复本形。《定志经》云:‘天尊化作凡人,从会中过’。《本际经》云:‘我即化身,种种示见,人天六道,随缘施人,倏歘有无,权示色象’”元始天尊能够变化种种不同的身相,忽有忽无,随缘而作,变化莫测。迹”的三身表示“道”的显迹,道体的应用,以满足众生的直观需求。通过“迹”的三身,道身与修道者沟通,修行者不是纯粹从理性上去把握“道”之真身,而是有了形象直观的崇拜对象,这就使芸芸众生不再感到“道”的虚无飘渺,不可捉摸。
从“本迹体义”来说,“本迹不异不同。迹之三身,有其别体;本之三称,体一义殊。以其精智淳常曰真身,净虚通曰道(身)[6]气象酬德(答)[7]是曰报身,就气精神,乃成三义,不可穷诘,惟是一源。既是法身,当有妙体!且言身言体,岂无色无心?旧云:‘寂地本身,以真一妙智为体,故《灵宝经》云,玄通大智慧源也’。色是累碍之法,九圣已还,既滞欲累,并皆有色。真道累尽,唯有妙心,但此妙心,具一切德,寂不可见,名为妙无。动时乘迹,同物有体;心色虽妙,物得见之,故名妙有。对本论迹,迹无别体,视是本身,寂(借)用称为体耳[8],正明法身至本,无色无心”。从“体”去讲说本迹,二者“不异不同”。迹是体之用,故说迹有“别体”;本的三身则同体而“义殊”,依气精神而分别形成三种不同的含义,来源却是同一个——“道”。法身妙体与心法色法有关,色是有碍之法,只有妙心才显示“真道”,这种妙心又名“妙无”。至此,心本之“无”与道本之“无”终归一致,主体和客体融为一团,天人合一,自然顺理成章推出“法身至本,无色无心”的结论。如此将“心”与“道”接通,便为人之修道得道奠定了根基,于此也反映了《道教义枢》试图通过对本迹的讨论,把“心”作为修道的根本,要人抓住修心而修炼法身,获得真道。
联系“法身”讨论本迹,还与道性有关,这从“本迹义例”即可见。关于本迹义例,《道教义枢》卷一《法身义》先引他说,然后予以驳难:“有师云:‘众生本有法身,众德具足,常乐宛然,但为惑覆,故不见耳。犹如泥之杂水,不见澄清,万里深坑,沙底难睹,本相见时,义无有异’。一家云:‘本有之时,未有众德,但众生有必得之理,故言澄清湛然耳’。今难二解:若本具众德,岂被惑覆?遂为惑覆,何德可尊?若本无众德,今时始有,则是无常。又理是本有,理可是常,事既今有,事应无常;若理事俱常,亦应理事俱本,是故不然。今明法身本非三世所摄,何得已有,见有常有耶?亦未曾有无,何论隐显?今言神本澄清者,直是本来清净,竟无所有。若迷此理,即名惑覆;若了此理,即名性显;非是别有一理在众生中,说为法身是常是净也”。这段话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即“本有”、“始有”。这两个词,原本是佛教术语,佛家用以探求佛性问题。佛教所谓“本有”指众生本具佛性,终必成佛。佛教所谓“始有”意思较多,一指佛果从妙因生,众生本杂染不净,自非妙因,故众生之佛性为始有;一指众生有佛性,必得佛果,但在凡位时,原未得果,期望得果,故有为始有;再就是认为一阐提人现无佛性,未来当有。可见在佛性论中有“本有”、“始有”之争。《道教义枢》引道教中人借用这两个名词讲法身的观点,指责法身“本有”、始有”二说均不能成立。按照本有说,众生本来就有法身,众德具足圆满,但为迷惑所覆盖住了。按照始有说,众生本来“未有众德”,但众生有“必得”法身之理。针对此二说,《道教义枢》认为:(1)如果依本有说,众生既然本来具有众德,那就不会被迷惑所遮覆;(2)如果依始有说,众生本无众德,而是“今时始有”,那么就是无常。因此,二说都不能自圆其说,都有理论上的漏洞。《道教义枢》的看法是:“本来清净,竟无所有”。既非本有,也非始有,而是无所有,懂得了无所有的道理,就叫“性显”。说到此,法身、本迹与人的道性问题牵连起来,道性是经由“无所有”显现的,这个“无所有”也就是“本无”、“心无”。“无所有”也显示了不执着本有、始有二边的中道立场。
这种中道立场从其论说本身、迹身与常、无常中一眼可见:“有说云:‘迹身无常,本身是常’。又云:‘常应为迹,迹亦言常’。今明一往对缘,亦有此说。至论常与无常,并是起用,悉皆是迹;非常非无常,乃可为本。四句渐除,百非斯绝”。有种说法将无常与迹身对应,常与本身对应,又有种说法认为迹也可以说是常。在《道教义枢》看来,不论常还是无常,都是用,都属于“迹”,只有不着常与无常二边的“非常非无常”才是“本”。这正是双遣双非的中道立场“四句”、“百非”的中观方法论。
《道教义枢》卷一《法身义》花如此大量的笔墨论述本迹与法身,究竟是为什么?用打穿后壁的话说,是要证明道身的真实存在,人对道的追求并非是无望的、徒劳的,人经过不懈地努力,刻苦地修行,最终是能够成就道身的。修行必须得法,正确的方法是不执二边的中道,从“心”上入手,修心炼性,返回根本。对“本迹”也应作中道观,双遣双非,这才是种圆满的智慧。诚如卷五《三一义》解释臧玄静的观点时所说:“玄靖法师解云:‘夫妙一之本,绝乎言相,非质非空,且应且寂’。今观此释,则以圆智为体,以圆智非本非迹,能本能迹,不质不空,而质而空也”。非本非迹,也就能本能迹,否则无法把握本迹的真谛。
从《道教义枢》对本迹的阐说中,我们已经发现,它把“本”与“体”看作同等概念,而“迹”则与“用”相同。如果说“本”是虚无,与之对等,“体”就当是空虚。卷四《五荫义》认为:“诸法之体,莫不赖空。七窍五藏,资空为质;舟车屋宇,以无为用,而不以空成法者,今明空之为理,不可分别成坏,岂得用其成物体邪?今五根七窍有空虚者,是有法赖空为用,非取此空构为法体也!若以空成物体,物体既坏,空亦应坏,便是空有生灭,是故不尔”。法体的本质是空,这种空没有“分别”,无所谓“成坏”,与七窍五脏舟车屋宇的借空为用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因此,无生成毁坏的“空”并不构成物体,只是作为“法体”而存在。物体有生有灭,有成有坏,假如“以空成物体”,岂非意味着“空有生灭”,这不符合“空”的道理。这里的要害是区别法体与物体。《道教义枢》重视的是法体,即世界的本体,关注的是本体之“空”,而对物体之“空”,认为那不过是“有法赖空为用”,不能以这样一种“用”的空去建构法体。这就是《道教义枢》眼光中体用与空的关系。
作用与动静如何呢?卷十《动寂义》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动寂体用者,旧云四绝忘理。众生迷之,故入生死。圣人体之,故与冥一,所冥之理既寂,能冥之智亦寂也。但初发道意,誓度众生,不负宿心,所以化行。行之为用,要在形声,故应入生死,形极物声。本无形声,所以为寂;迹有形声,所以为动。至论:尚自无动无寂,岂得有形有声;既以无动无寂而分动寂,亦以无体无用而开体用,故以不寂之寂为体,不动之动为用。若言体用并为用,非体非用始为体者,亦动寂并为动,非动非寂始为寂耳”。动寂体用关系到人能否脱解生死。普通人不悟其中道理,所以入于生死场中,而圣人则体悟了个中三昧,所以超越生死。圣人以静为体,为化度众生,以动为用,故“应入生死”。说起来,本静迹动,但更正确地说,既然以无动无静而分动静,那么也当以无体无用而分体用。这样,不静之静是体,不动之动是用。如果说肯定体用是“用”,而非体非用才是“体”,那么可以推出,动静都是“动”,非动非静才是“静”。说到底,《道教义枢》论体用动静,又落入重玄派双非双遣的理论套路中,主张非体非用、非动非静。
《道教义枢》还论述了“道德体用”,指明何谓道体,何谓德用。如卷一《道德义》引陆修静的观点说:“虚寂为道体,虚无不通,寂无不应”。虚通静寂的道体应物而为用,结合动静而言,道-体-静为一边,德-用-动是另一边,不执着这二边,即为悟透了道德、体用、动静之间的关系。《道德义》认为,道与德是种体用关系,道是体,德是用。这一观点也主要采自重玄学派:“玄靖法师以智慧为道体,神通为道用。又云:‘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说其有体有用、无体无用,盖是无体为体,体而无体,无用为用,用而无用,然则无一法非其体,无一义非其功也。寻其体也,离空离有,非阴非阳,视听不得,搏触莫辩;寻其用也,能权能实,可左可右,以小容大,大能居小,体即无已,故不可以议;用又无穷,故随方示见。’”玄靖法师即南朝重玄派学者臧玄靖,从这里所引述的观点看,他认为道德是体用一源的,二者“一而不一,二而不二”,对此应该既非体又非用,不着二边,以“无体为体”,“无用为用”;道德作为体用在时空上都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可思议却又随时随地显现,变化莫测。关于道德体用关系,成玄英在其《老子注》卷二中指出:“道是德之体,德是道之用,就体言道,就用言德”。也强调了二者间不可分割的体用关系。其《老子注》卷五说:“冥真契道,谓之玄德”,德必须去契合道体,暗示道德关系中“德”处于从属地位,只是道体之用。成玄英在《庄子.徐无鬼疏》中更比较了道与德,认为:“一道虚玄,曾无涯量,而德有上下,不能周备也。……言德有优劣,未能同道也”。德是不能与道相提并论的,因为德不能象道那样“周备”,总有上德与下德之分,由此道与德的优劣也自然显现出来了。这种优劣之分是由二者间的体用关系所决定的。在成玄英眼里:“深玄为德之本根”,[9]既然“德”的本根是深玄之道,德只是“功用”,那么道优德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成玄英以体用说明道德之间的关系,与臧玄靖基本上一致,并进一步揭示了作为本根之道的决定地位。《道教义枢》继承臧玄靖、成玄英等重玄名家思想,对道德体用之间的关系予以进一步阐述,从而说明道体无限,其功用亦无限,世界万事万物都在“道德体用”范围之内。中国哲学一般是从道器、道物去讨论体用,道体器用,道体物用,这是人们所熟知的,而道体德用则很少有人讨论。能否可以这样说,南北朝到隋唐道教以体用论说道德,在中国哲学史上别开生面,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问题。
如果说成玄英论本迹、体用更为关注本迹,对体用涉猎不多,那么《道教义枢》则较多地谈到体用,这说明当时道教已有从本迹转向体用的趋势。本迹与体用实质上是同等范畴,本等于体,迹等于用。魏晋玄学讲本迹较多,尤其是郭象《庄子注》,这为隋唐道教所继承,隋唐以后,道教基本上用“体用”来表述,与宋明理学一致,这样一种转折,从《道教义枢》中已露出小荷的尖尖角。
注释:
[1]此处脱一“身”字。
[2]“德”当为“答”之误抄。
[3]“寂”当为“借”之误抄,意谓体借助于用而称为“体”。
[4]佛教三身指三种佛身。有不同说法:(1)法身、报身、应身;(2)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3)法身、应身、化身。
[5]“近”疑为“静”之笔误。
[6]《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第27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同上第270页。
[8]参见拙作《成玄英论本迹》,载《四川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9]《庄子.天下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