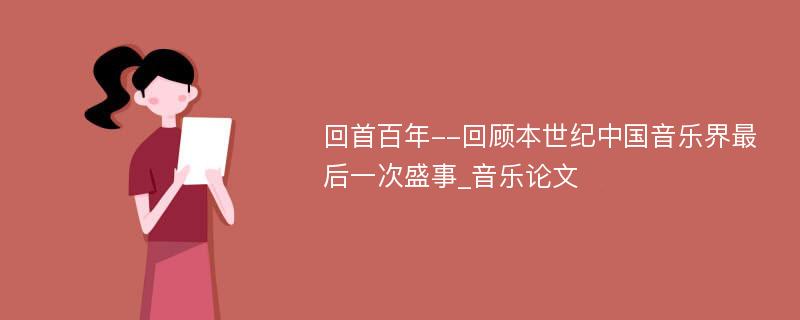
百年回望——记本世纪中国音乐学界的最后一次盛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世纪论文,学界论文,盛会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一个人的名义,来做整个学科的世纪回望,是因为在这个学科领域的各大部类中,无不饱含着这个人的心血,也无不存在着这个人的业绩。这个人,就是中国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近代科学范畴的中国音乐学奠基人——杨荫浏。
在杨荫浏先生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先后完成了《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苏南十番鼓》《语言音乐学论稿》《工尺谱浅说》等40余种音乐学著述,为中国音乐学研究诸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了缅怀先生的学术业绩,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学学术发展的历程,经文化部批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99年11月9日至12日, 在北京九华山庄连袂主办了题为“20世纪与中国音乐学——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正式发言代表有73人,他们分别来自大陆各地、香港、台湾及美、英、日、加拿大等国。论题涉及了杨荫浏先生学术业绩、学术观念、治学精神、人格风范的追思与再认识;20世纪中国音乐学诸领域历史轨迹的回顾与总结;中国音乐领域中的具体课题研究;21世纪中国音乐学前瞻等等。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议题的广度而言,它都将是本世纪中国音乐学界最后一次盛大的聚会,如同会议的组织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教授在总结中所说:正是因为杨荫浏先生广博的中国音乐学建树,使我们的会议能够形成一个多学科、多元化、整合性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参会代表中最年长者为94岁,最年轻者20来岁。以逾百人的五代学者,来纪念杨先生的百年诞辰,讨论这百年来的音乐历史,对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及其学术队伍的发展别具深远的意义。
11月10日,是这位与世纪同龄的音乐学家的冥寿。当晚,与会者云集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以崇敬的心情,参加了“杨荫浏先生采集、记录、整理传统音乐作品音乐会”。音乐会上演了苏南吹打(十番鼓)《一封书》;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琵琶曲《昭君出塞》《大浪淘沙》;以及由杨先生译谱的姜白石(宋)创作歌曲《杏花天影》《暗香》《翠楼吟》《惜红衣》《淡黄柳》《霓裳中序第一》;还有由杨先生填词、整理的宗教歌曲、乐曲等等。伴随乐声的起伏跌宕,人们仿佛听见了先生探索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脚步。
当年,先生仅有七岁,就开始学习箫、笛、笙、琵琶……自十五、六岁,就与道士、吹鼓手密切来往,并手抄其“十番鼓”曲谱。他“从幼年开始学习传统音乐的过程,也就是对传统音乐作深入调查的过程”(郭乃安)。其后,他又以一个音乐学家的敏锐,认识到“国乐的园地,是非常的广大”,但是它们有很多“还散在民间,在奏唱者的乐器上,歌喉中”,需要我们去“搜罗、分析、比较、归纳”。于是,在1949年以前,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一切机会,去接触社会上尚在流传的古代音乐。如收集吹打乐、十番锣鼓和古琴曲等等”(曹安和)。50年代以后,他又亲自参与并领导了长达十余年的中国传统音乐采录运动。终其一生,经他采集、整理成专辑的民族音乐材料(包括与别人合作的)就有31种。
音乐会上《一封书》的演奏谱,就是先生在50年代记录的。如此“大型套曲的多声部记谱,表现了采访后期工作的艰巨性与具体操作上的复杂性。……杨先生对主要乐器鼓与笛演奏技巧有着详细的考察与记载,特别是对鼓演奏的记录,每一个演奏细节都不遗漏……其记录的难度与精确度,迄今为止,未有人及”(袁静芳)。
正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深入体察民族音乐‘原生态’……从而磨砺了一双慧眼,能够洞穿广存于民间艺人及市井百姓中的音乐实况的真正价值”(栾桂娟)。因此他才能从《五台山僧寺流传宋时乐谱》中找到了辨认姜白石歌曲字谱的新线索,又从西安古乐中所用的流传至今的乐谱中发现了它和宋人字谱的关系,并从民间艺人的实际演奏中悟出了此种乐谱的运用方法,从而破译了宋代字谱,使七百年前姜白石创作的歌曲成为现代人可以聆听的音乐。
有人说,“先生完全以介入者的姿态来继承传统音乐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民间音乐所采用的抢救与推广并重的保护模式。阿炳音乐的再生就是一个例子”(韩宝强),如果没有杨荫浏先生和曹安和女士在1950年携带着那架录音机到无锡,如果没有先生将钢丝录音带上的音响制成唱片公开发行,阿炳那感人至深的《二泉映月》就不可能得到重生。但人们如果知道,早在先生十二、三岁之时就已经跟随阿炳学习琵琶和三弦,就会坚信,“当少年杨荫浏与穷道士阿炳相遇的那一刻,已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道教音乐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将其绚烂的音乐之花公之于众、播之于外、垂之于永久的人”(田青)。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当这首岳飞的“满江红”被举国之人传唱,人们是否知道,这是先生当年在“五卅”惨案的激忿中,以古曲《金陵怀古》曲调填岳飞词而成歌之作?
“同一信,同一信,天涯团契心心印”,当中国1200万基督教徒咏唱中国风格的“赞美诗”时,他们也许知道,为了“灵感”“文字”和“音乐的美致”,以及那些包含“国化创作的因素”,杨荫浏所付出的努力……
如果说音乐会让人们感性地体验着先生民族音乐实践的传奇,那么代表们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则对先生、以及20世纪的中国音乐学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与评价。
发言中共有37篇直接与杨先生相关。魏廷格和吴赣伯就先生“过度地注意国乐”之音乐思想与观念再作评述,并认为正是这一思想观念,造就了先生一生的伟业。赵宋光的《继承杨荫浏先生重视事实的学术风范》、简其华《学习杨荫浏先生的治学精神》、郭乃安《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杨荫浏治学的主要特色》、栾桂娟《世纪末的反思——杨荫浏百年诞辰启示录》、伍国栋《杨荫浏治学精神对我的影响》、郭树群《管窥杨荫浏先生学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等篇,则以“躬亲实践”的共识,专述了杨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专述了杨先生“中国人研究中国音乐”并植根于实践的真正涵义。也许先生真的是应历史的需要而生,所以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上唯有他能够全面接受古、今、中、外多重内容的基础教育,积累了文、史、哲、物理、数学及民间音乐、琴乐、宗教音乐乃至外国音乐诸领域的深厚功力。他一生坚持以唱、奏、抄、听、记、测、译的手段,时时保持与传统音乐的亲近(乔建中)。无论是兼长唱奏,或是深入民间音乐实际的调查,还是重视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都为他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
在这条新路上,他的史学“抛弃了‘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习”(缪天瑞),以民间留存的活的中国传统音乐作为音乐史学研究之基础,让音乐和创造音乐的人成为音乐史的中心(乔建中、伍国栋)。用翔实的史料和尽可能丰富的音乐实例来阐述中国音乐史的实在面貌,使一部“有音乐的音乐史”成为可能。
他的乐律学研究,坚持服务于音乐实践的主张,并以现代律学实验、计算和乐器音律的实践为基础,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律学史(陈应时、陈其射)。
他的音乐文献学,通过校释、汇考、表谱,以及将新的音乐史学的观念与旧的材料、有声的史料与无声的史料相比正的方法,为一般文献学做出了贡献和发展(王小盾)
他的语言音乐学充分利用了音韵学、音乐学、古汉语以及外语知识,在汉语和音乐的关系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真正把语言与音乐的关系直接论述到了曲调、节奏、乐曲构造等音乐的细微表现上,开创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孙玄龄、陶亚兵)。
他的宗教音乐研究广涉道教、佛教、基督教音乐领域,为后人留下了《苏南吹打曲》《十番锣鼓》《瞎子阿炳曲集》《智化寺京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佛、道、巫、儒音乐部分)《普天颂赞》《赞美诗新编》等等宝贵的资料与著述(田青、向延生、杨周怀、李淑琴)。
他在音乐文学的研究中一反以往仅从文学的角度而以“先诗后乐”“以乐从诗”为其发展历程之偏颇,找到了注重音乐本身内容与形式变化的正确道路(秦序)
他指出了琴学研究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掌握琴曲版本和史料索引;琴曲断代;打谱),对我们今天的琴学研究及学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王建欣)。
他亲自绘制乐器线图,并领导了广泛收集音乐图像和图书、乐器实物资料工作,将音乐图像学研究纳入到中国音乐研究的系统工程中(刘东升)。
他关于历史文字资料、文物图像与民间舞蹈实践相结合的观念,直接启示了舞蹈史的研究(王克芬)。
……
此外,王震亚、金湘、陈自明、吴钊、陈应时等人以及杨先生的女儿杨国兰回忆了先生孜孜钻研、诲人不倦、谦逊坦荡、求真务实的历历往事。其中金湘关于《怀念杨荫浏先生,走中国民族乐派道路》的发言感人至深。
黄翔鹏先生曾评价杨先生的“治史、治学观点、方法和范例。无疑地还将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进展中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影响深远”。在这次会议中,冯文慈、郑祖襄分别就杨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中国音乐史纲》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述,并对杨先生的思想变化与历史背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确实,杨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任务和课题,……有的是经他提出而他自己无精力去完成的;有的是虽经初步研究而没有最后下结论的;还有一些是由于某些局限而作出了不够妥当的结论的。作为后学,我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尽力把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既是对学术的贡献,也是对杨先生最好的纪念(刘勇)。研讨会上,又有崔宪的《探寻音乐内在的发展规律——从“音乐型态学”看黄翔鹏先生的学术继承性》,路应昆的《明代“线索调”略考》,吴文光、赵晓楠的《关于大曲[柘枝令歌头]、[柘枝令]俗字谱曲谱及其考、译》,刘勇的《民间乐种“四宫”与二十八调“四宫”》等等,都体现了杨先生学术研究事业的继续。
本次研讨会另有36篇发言涉及了史学、考古学、传统音乐研究、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等领域。其中既有对20世纪的回顾,又有对学科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古代史研究有刘再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回顾》、郑长铃《历史地评价陈旸及其〈乐书〉》、林青华《清代洋人钱德明对中国音乐史的贡献》;音乐考古学有王子初的《戎生编钟的音乐学内涵》;律学研究有牛龙菲《中国古典律学道器一元、律历一元的传统——兼及律学、律史研究方法论思考》、韩宝强《阿炳所奏〈二泉映月〉的音律研究》;近现代史有汪毓和《关于近现代音乐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潘乃华《在近代音乐史的轨迹中对中日两国音乐学发展的一些比较》、余少华《从中国传统雅乐观念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史》、黄旭东《如何实事求是计算校、团的“年龄”——值得探讨的现实性“历史问题”》;传统音乐研究方面有费师逊《音乐源流史与音乐功能学研究的前景》、曹本冶《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之道教科仪音乐研究项目》、项阳《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成公亮《〔凤翔千仞〕、〔孤竹君〕打谱后记》。
另有一组发言提出了中国音乐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譬如钟思第的《音乐跟社会有关系吗——当代中国音乐学的若干问题》、管建华的《语言学转向与重识国乐》、郑苏的《质疑“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对20世纪中国音乐界的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陈铭道的《以音乐学的名义——欧洲音乐学温故》、景蔚岗《到民间音乐中去学习》、周吉《试论民族音乐学家的“守士职责”》、方兵《被忽视的命脉——从唱片〈风吹过桥〉的改编看民族民间节奏特点的继承与发展》、丁承运《古琴的传承》等。
有关音乐教育问题的专论有彭莉的《一个年轻学生的思考——教学体会和问题》、荣鸿曾的《音乐研究与大学教育》、方建军《音乐学专业教育模式之检讨》、孙继南的《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史编撰刍见》、刘靖之《音乐史课程比较研究》。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刘明澜《清除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近代音乐史研究的隔阂》、袁静芳《20世纪中国乐种学学科发展回望与跨世纪前瞻》、萧梅《谈资料建设的继往开来》、山寺三知《20世纪日本中国音乐史研究文献书目》、曾遂今《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初论》、韩钟恩《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之今典》、谢嘉幸《面对21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等文,则就资料建设和学科建设提出了构想。
在11月11晚上的圆桌会议中,代表们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音乐的研究成果对外宣传。这个问题的起因与国外媒体对我国“舞阳骨笛”宣传的误导有关。代表们对如何宣传、宣传什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更多的代表认为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更好地研究。中、西之间的互相了解实际上潜在着不平等(韩钟恩),中国音乐的学术价值首先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谢嘉幸)。任何研究文本一经诞生,就有了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生命,杨先生没想到对外宣传自己,但他却已走向世界(牛龙菲)。汉语和英语各自有各自的环境,不能在一个绝对值上进行评价。中国的民族器乐并不意味着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了,得到外国人鼓掌了,就证明是好了(田青)。我们这次会议就好在由我们自己评价杨荫浏(谢嘉幸)等等。
圆桌会议讨论的第二个热点是传统音乐的教育问题。周吉在他的大会报告中以新疆的状况,指出了由于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以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为基础的现实,导致了少数民族优秀音乐传统消失的现实。这个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那么什么叫传统的传承,什么又是传统的消亡呢(赵宋光)?有代表认为,中国的传统一直在变,以琴家来说,管平湖的琴曲体现了由纯律向三分损益律的变化,而吴钊则有平均律的倾向(尹鸿书)。而传统的变化是什么人都阻挡不了的。比如正是因为余叔岩有变化、有创新,才得到了谭鑫培的青睐(汪毓和)。但有的代表认为,不能忽视变化的基础问题(苗晶)。唐代中国音乐的变化是以“华”化“胡”。而我们的古筝原来有丰富的定弦法,现在只剩下一种了,这种变化,叫做见异思迁。而所谓的古琴三律之间的变化,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已有的(丁承运)。现在学院派的古琴教学,流派消失了,一招一式都标准化了(吴钊)。管建华认为,音乐学可以说仅仅是学者的问题,但音乐教育则是全民的问题。而我们的“母语”教育存在的差距太大了。方兵以一名作曲家的创作体会认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是观念的变化,而不是技术的新与旧。……在中、西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传统传承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在中国音乐学领域存在了一个世纪。回溯杨先生在40年代初《国乐前途及其研究》文章中提出的“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以建立本民族音乐发展的坚实基础的观念,而时隔半个世纪,这个基础仍然漠视,这正是我国音乐教育最大的失误(栾桂娟),
如何将中国音乐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专业音乐教育乃至国民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应该是中国音乐学家们面对21世纪的共同课题。研讨会上,韩钟恩以博物馆/研究所/学院/学会学刊之间的资源共享,展望了21世纪中国音乐学界的“合体共振”。谢嘉幸则以继承民族音乐文化传统,振兴民族音乐文化;建设中国音乐文化信息基础结构;以音乐教育为切入口,建设音乐文化大厦;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发展中国音乐学术;以学术的广泛交流,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提出了建立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的希望。
20世纪就要过去了,“面向21世纪,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任重而道远”。这可以说是每一个与会者在重上征途时的切身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