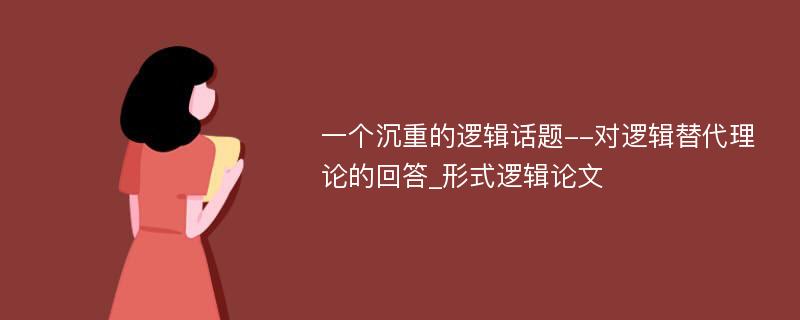
沉重的逻辑话题——答逻辑取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沉重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路写了一篇关于“金逻辑”的文章(注:王路《金岳霖的孤独与无奈》,《读书》1998年第1期。引文未注出处,皆见王文。),提出了说难清、理还乱的沉重话题。
王先生的逻辑观表露得直率:“在大学里开设现代逻辑的课程,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也就是要讲授金先生在三十年代倡导和讲授的那样的逻辑。”他把这理想未达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缺乏逻辑传统,政治影响,习惯势力的阻碍,哲学系教学大纲未列入必修课等。王文就是在此背景中评及金岳霖的孤独与无奈的。但金岳霖先生自己未必感到孤立与无奈,可惜死无对证。
中西文化传统有异,思维方式有别,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不争的事实是,以数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对中国人有吸引力。西方科学都体现西方的逻辑传统与思维方式,都是很抽象的。至于逻辑,总体看也是被中国人接受的。严复译《穆勒名学》后,逻辑学如八十年代的新老三论,为学者时髦。1949年前出的逻辑书,据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附录,就有104种(不包括中国名辩与印度因明书)。1950-1980年,据辽宁大学哲学系编《逻辑资料索引》,有107种。80年后的形式逻辑,王文说“至少有几百种”。
中国高校包括教育学院、党校、自学考试等文科的哲、政、文、经、法等专业,普遍开设传统逻辑课,数百学校的数万学生每年都在学。作为逻辑教师,深知学生大体是能接受的。高校逻辑教师有相当的比例,如王文所说,“甚至是中文系毕业的”。这说明什么呢?王文不是也说,“逻辑是大学里与语法、修辞并列的三大基础课之一”吗?怕不仅在中世纪,就是今日美国,据说“逻辑二分为‘形式逻辑’与‘实质逻辑’。……‘实质逻辑则必然涉及推理之前提与结论的实质内容”。(注:《中国哲学年鉴(198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译进的《逻辑原理》(湖北教育出版社)《大学生逻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非全是现代逻辑。西方还有非形式逻辑的世界性组织。在中国高校,文科主要学传统逻辑有其合理性,中文系开逻辑,由熟知语法、修辞的中文系毕业生教逻辑,很正常。他们象金先生教逻辑,“只好边教边学”,又为什么不能?
至于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普及逻辑知识之功,王文一面说,“当然是极大的好事”;一面又说,“这惊人的数字并不能说明逻辑得到广泛的接受,更不能说明逻辑有多么大的发展。”逻辑普及与逻辑发展当然有别,但“25万人有了逻辑书”,这不是“广泛的接受”,不是逻辑的发展吗?
上述种种,都不在王先生心中,因那不是现代逻辑。如传统逻辑被现代逻辑取代,王先生大约才会欢呼雀跃。王先生的理想并不高,他心中逻辑就是“讲授金先生在三十年代倡导和讲授的那样的逻辑”。这仅是现代逻辑中基础部分的命题逻辑与一阶谓词逻辑,是在传统逻辑演绎推理的复合判断推理与三段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抽象,更形式化与科学化,其精华如真值表和推理式,传统逻辑教材已有引进。而大多数逻辑教师尤其中文系教师乐于教传统逻辑教材,是因它距思维与语言实际更贴近。命题逻辑更抽象,不利于对文章(包括作文)的逻辑分析。传统逻辑分析文章指导阅读与写作大体够用,也确有用。
传统逻辑自康德后,习称形式逻辑。现代逻辑更是纯形式的逻辑,故有人说现代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传统逻辑理所当然被取代。这实是名称上引起的误会,传统逻辑如用康德“普通逻辑”称谓才准确。王文中说到的金先生高足王宪钧说:“数理逻辑是演绎法在二十世纪的新发展,它本身就是演绎逻辑。”(注:王宪钧《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逻辑学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它主要是数学的理论或就是数学。只有最基本的命题逻辑与一阶谓词逻辑是纯逻辑内容。而传统逻辑是一棵大树,现代逻辑仅演绎一枝的蓬勃发展。
传统逻辑与认识论、心理学,与人文及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它基于自然语言,研究普通思维涉及大量或然推理,有形式结构也有非形式性结构,它是思维成品如文章的分析性的解剖学研究,论证集大成于语用。而探术因果方法与假说,又涉及认识过程,其不足之处主要在认识过程中推理的地位与作用不明,也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发现发明与斗智等的逻辑机制未很好揭示,但于听说读写的接受(输入)与表达(输出)基本上能满足。现代逻辑利用人工语言,研究有效推理,追求必然思维,是形式化的推演,公理体系,严格证明,此种思维方式远不属普通人的日常思维,是高级的科学思维方式,更适合尖端性高深科学的需要。鉴于王文强调同,这里特别提出异。异中有同,不仅有承传关系,传统逻辑亦可借鉴现代逻辑,以求丰富和发展;现代逻辑也可适当运用于社会科学。
王文讲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实是逻辑界20年来围绕传统逻辑向何处去问题,引出的争鸣。坦率地说,取代论者多熟知现代逻辑,知传统逻辑之不足;但又多是专业研究人员,缺教学经历,似立逻辑科学潮头,过贬传统逻辑,脱离思维与教学实际。王文还说,“即使在金先生曾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似乎也是摆不上桌面的,它至少不如伦理学,连一个二级学科都不是。”我在这话中感受到王先生的孤独与无奈。王先生肯定知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现代逻辑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二的。而现代逻辑的大家自莱布尼茨,到布尔、德·摩根、康托尔、弗雷格、罗素、怀特海、希尔伯特、哥特尔、图灵等等,都是教学家,从数学进入逻辑与哲学的。纵使金先生看不懂有些现代逻辑书,这也毫不奇怪,每位学者与教师都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取代论者如何克服“习惯势力”,改变高校文科逻辑教学,当务之急是拿出能取代金岳霖领衔主编的《形式逻辑》的新一代教材来。20年过去了,《形式逻辑》仍是权威教材,这能怪“习惯势力的阻碍”吗?
(二)
对金岳霖逻辑思想,王文表现出无奈。哲学第一人、逻辑泰斗,讲过错话,赞难尽兴。
金先生自省说,“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这话如何理解?王浩曾说,“可以说《逻辑》以介绍西学为主,《论道》以结合中西来创新为主。而《知识论》以在西方学术框架中创新为主,但实际上每一本书又表现出金先生在哲学上若干独有的见解及较明显的思想方式。”(注:王浩《金岳霖先生的道路》,《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介绍为主还是创新为主,正是差异所在。金先生自己在《逻辑》初版序中说:“第三部介绍新式逻辑,全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直抄。”甚至说,“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门外汉。预备这本书的困难也就因这感觉而增加,有时候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注:金岳霖《逻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页及书前附文。下引金文,皆见附文。)“最糟”的根子,大约在此。
解放后,金先生学习马列主义;1958年访英,他宣布自己哲学信仰的转变。1959年,他写《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注:金岳霖《逻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页及书前附文。下引金文,皆见附文。)。近日因王文引发,始将该文一读。也经历过当时岁月,看那一串串上纲上线语言,倍感昔日荒唐。但金先生的批判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最糟”帽子虽大而无当,确是自己扣上的。今日审视金先生逻辑观,是否就该一概否定,全面回到《逻辑》上来,怕也未必。文章结尾,金先生提出形式逻辑能不能够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指导问题。这问题今日该如何认识呢?反观金先生自我批判文章,其得失症结仍在辩证唯物论在他手中究竟操作得怎样。历史教训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辩证唯物论用得好,改革开放成功亦是,精髓是实事求是。事业的种种挫折,又无不是违反了唯物论、辩证法。我是相信辩证唯物论的,也相信传统逻辑应接受辩证唯物论的指导。
以我今日理解,看近四十年前金先生文章,其主要不足,在未用好辩证唯物论。现代逻辑是唯物的,但不是机械唯物论,正符合辩证唯物论。传统逻辑演绎的抽象来自思维实际,是唯物的,基于演绎的现代逻辑演算,再进一步,更抽象,高于普通思维,正是文明能动性的高扬,金先生评之为唯心主义甚至主观唯心主义,不妥。现代逻辑是“绝对化、无对化、形而上学化”吗?也不是。应该说,形式化、公理体系的建立,合取、析取、蕴涵间关系的沟通,正是把形而上学思想方式抽象的合取、析取、蕴涵等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公理体系即辩证体系。传统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各自独立;现代逻辑揭示三律间的转化。金先生批判说,“强调这个转化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能利用这个转化来抹杀作为推论方式这三个规律底不同的特点。”三律不是一律,各有定义,特点原有。进而揭示转化,正是辩证化,何错之有?说现代逻辑“是把形式逻辑形而上学化”,不确。
如从传统逻辑着眼,金文确看出其若干不足。如演绎的“必然”,是科学;但如何看这“必然”?从认识角度看,“必然”是从“或然”来的,排除无效式才能留下有效式。人类找到“或然”通向“必然”的方法,是伟大发现。如孤立看“必然”,不见“必然”与“或然”的联系,片面贬低“或然”及或然性推理(类比、归纳),就落入了形而上学方法了。现代逻辑研究命题间的必然联系,研究有效推理,本无可非议;与认识论分家,摆脱心理主义,这才能更好研究纯形式的推演,亦无可非议;但由此引申到逻辑只研究推理,不研究有效推理、与认识论结合、有心理倾向,就不是逻辑,则过矣。这正是形而上学的逻辑观了。金先生认识到这种逻辑的不妥,而今日取代论者恰恰再拣起金先生抛弃的观点。
金文注意到演绎前提问题。上引文说,美国的实质逻辑亦正还在关心此问题。金先生从杜勒斯把反动命题作演绎前提,提出推理正确性与真实性的一致性,推理形式的阶级性,这无疑错了。但又说,“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我们的概念从哪里来呢?判断有什么事实根据呢?推论有什么前提呢?从完整的形式逻辑说,这些都是从归纳来的。”他把演绎与归纳、以至判断根据、概念形成问题都提出了,这种从思维过程即认识过程研究的逻辑,他称为“完整的形式逻辑”,这是他形式逻辑发展方向的新理解。传统逻辑中,概念是研究起点,在认识过程中,概念是认识结果。传统逻辑中,演绎与归纳、类比并列,各自孤立。在认识过程中各居何地位是新课题。如在概念、判断与推理间,在演绎、归纳与类比间,找到如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的转化关系,揭示认识过程的逻辑机制与形式,正是一种新逻辑观,符合唯物辩证法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金先生不仅接受了唯物辩证法,而且看到传统逻辑的不足、现代逻辑的偏颇,找到了修正传统逻辑的方向。
他把逻辑重新界定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之下,因此也是在辩证逻辑指导之下,在具体的思维认识过程中帮助我们得到更正确的思维和认识的工具之一的科学。”希望“形式逻辑是广大劳动人民日常运用的思维武器。”这样,逻辑由论证与证明的工具转化成认识与思维的工具了。这种逻辑,确切说,该称“认识逻辑”吧!由于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转化,实是传统逻辑的辩证法,揭示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奠基的思辨逻辑,恩格斯、列宁的辩证逻辑,方向是一致的。
黑格尔将认识过程三分为感性、知性与理性。知性的抽象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其逻辑就是传统逻辑或曰形式逻辑。黑格尔的理想是用他的辩证法去修正传统逻辑,对思维形式重新作“一条龙编排”。(注:周礼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这就是他的理性逻辑即思辨逻辑,恩格斯称辩证逻辑。
恩格斯、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都有很深研究,皆肯定其大方向,又指出其不足。列宁认为,“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总计、总和、结论。”(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页、第67页。)他提出总结认识史任务,并指出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注: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哲学笔记》第234页。)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从思维实际出发,总结认识过程的逻辑机制,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在逻辑基础上统一了。传统逻辑也就转化为辩证逻辑了。恩格斯强调过归纳与演绎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批评传统逻辑的互相平列体系,指出“辩证逻辑却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中发展出高级形式”。(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页。)他还以数学为喻,说微积分这高等数学“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辩证法在传统逻辑中的运用,正是辩证逻辑。理性逻辑基于知性逻辑的辩证化,就有高初级之分了。
黑格尔的逻辑学,主要表达他的哲学观。从逻辑看,也属逻辑哲学。他在“概念论”篇讨论思维形式的辩证关系。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导致头足颠倒,其排列又脱离思维实际,导致形式主义。但黑格尔的大方向是被恩格斯、列宁肯定的。
金先生的逻辑思想正转向黑格尔方向。1961年第1期《新建设》上,金先生就提出《关于修改形式逻辑和建立统一的逻辑体系问题》的建议,这是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上的发言。这观点后被称为“统一论”,胡曲圆、马玉珂、邹化政、邓晓芒等先生,亦持类似观点。周礼全在《〈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中说,“我猜想金岳霖同志是想把现有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或辩证逻辑统一起来而建立一个统一的逻辑。”他评论说,“我个人的学习与研究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能够表示确定的意见。虽然如此,如果有人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逻辑,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探索说,我不但不想表示反对,而且我还认为那是一个可贵的努力。”(注:周礼全《〈论“所以”〉中的几个问题》,《逻辑问题讨论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42-843页。)可惜金先生提出的统一逻辑只有设想始终未拿出方案来。
周先生还曾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是以辩证的方法来研究思维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内容、联系和发展。”(注:周礼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有的辩证逻辑家作过这方面的探索,如章沛主编的《辩证逻辑基础》(湖南人民出版社),在“推理的辩证法”节,提出“类比——归纳——演绎”与“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关系推理”(注:章沛主编《辩证逻辑基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299页。)两个系列。杜岫石主编的《形式逻辑原理》(注:杜岫石主编《形式逻辑原理》,辽宁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就是先类比、再讲归纳,后讲演绎的。笔者认为,类比——归纳——演绎结合组成推理链,推理链即认识链,其运行轨迹正是感性——知性——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推理链运行中,会推出新判断,形成新概念、新理论。科学体系由推理链成果组成。推理链正是“实事求是”的逻辑机制。在思维形式辩证化基础上,笔者将认识过程逻辑分解为接受逻辑(听与读的输入)、创造逻辑(发现与发明的整合)与表达逻辑(说与写的输出)。上述探索,金先生黄泉有知,能首肯否?金先生的新逻辑理想起码不是孤独的。
统一逻辑的始祖是黑格尔。他说,“思辨逻辑内即包含有单纯的知性逻辑,而且从前者即可抽得出后者。”(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182页。)黑格尔的公式是:
辩证法+知性逻辑=思辨逻辑
思辨逻辑-辩证法=知性逻辑
前苏联逻辑教师多坚持黑格尔的统一逻辑方向。1951年前苏联有一场逻辑大讨论,《哲学问题》编辑部的总结文章,把形式逻辑包括在辩证逻辑内命题,偷换成“形式逻辑包括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形式逻辑无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性,犯大忌了,被斥为折衷主义,“是最糊涂的、最错误的和最有害的路线,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路线。”(注:《逻辑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以后,形式逻辑辩证化或辩证的形式逻辑,都成忌语。
金岳霖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统一逻辑主张的,而且在学部委员庄重的集会上提出,有勇气有胆量,更是深思熟虑的。在以前,东北人民大学的刘丹岩曾著文支持统一逻辑,说“修改形式逻辑和创造辩证逻辑是一回事”。(注:刘丹岩《论逻辑学与唯物辩证法》,《辩证参考资料(2)》,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76页。)1959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高崇会的批评文章,指出“对这种学术路线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就在这几个月后,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统一逻辑主张,当时是犯大忌的。
金岳霖先生去世14年了,纪念他的书文有不少,他的统一逻辑思想连同推理形式阶级论等一起被否定了。辩证逻辑虽师祖黑格尔,但基本转向对辩证思维的研究,辩证思维即理性思维,抛开知性思维知性逻辑基础,别开分店,另起炉灶、失去承传,辩证法由指导思想、思想方法变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实回到形而上学,明显套形式逻辑定义与体系,还在《哲学问题》调子下运作,其结果是连《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都不承认它是逻辑。
按黑格尔观点,形式逻辑本该被辩证逻辑取代,辩证逻辑家信《哲学问题》观点,不愿取代。现代逻辑仅形式逻辑演绎一枝的发展,只能取代演绎,不可能取代整个逻辑,也取代不了的归纳、类比等。
(三)
在此,还得为形而上学辩说几句。形而上学可以是思想方法,也可以是世界观。作为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恩格斯、列宁都肯定过,它是科学方法一部分,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产儿,它至今仍很流行,今日不少科学体系包括形式逻辑都是其产儿。它是知性思维的方法,当然有不足,仅是片面、割裂、孤立、静止的知识。任何科学的起始与初级阶段都难免知性局限。如欲继续发展,就是向全面、联系发展,就得靠辩证法,整合知性,才能逐步逼近理性,逼近真理。真理门坎不是一步跨进的,必经形而上学阶段。如满足于形而上学成果,就是以形而上学态度对待知性,若进而将其绝对化,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世界了。
形而上学有方法论与世界观之别。毛泽东的《矛盾论》讲的是“两种宇宙观”。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前提下,将方法论等同于世界观,它是我国哲学家长期误解至今仍流行的观点。实事求是说,绝大多数人的最好认识止于知性,能达理性者,不是多数。许多错误决策,工作失误,说明其认识连知识性都未达到。何况理性与真理本是相对的,知性与理性间本无鸿沟。我看现代逻辑,确进入了理性,但仅限演绎;与认识论又分家,知性因素仍明显。它又把触角向各种学科伸去,又在向更高的理性攀登了。
传统逻辑,在黑格尔看来,是知性逻辑,是形而上学方法的产儿。它是思维成品的解剖学研究,其理论与体系的形而上学倾向明显。也有辩证法因素,如概念组成判断形成推理。如三段的公理倾向,如合取、析取、蕴涵的转化,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转化等,但总倾向是分解与组合关系,进一步将其辩证化,大有用武之地。但如直说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自然不通,但也不发生贬低问题。问题在,有人不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重要区别,唯形而上学是反,形而上学方法长期蒙尘,遭不白之冤,该平反了。这也是一种极左。
讲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统一逻辑可能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逻辑打上中国人思维烙印吧。果如此,正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了,它不止于引进与学习,加入了整合与创造。
标签:形式逻辑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金岳霖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逻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推理论文;
